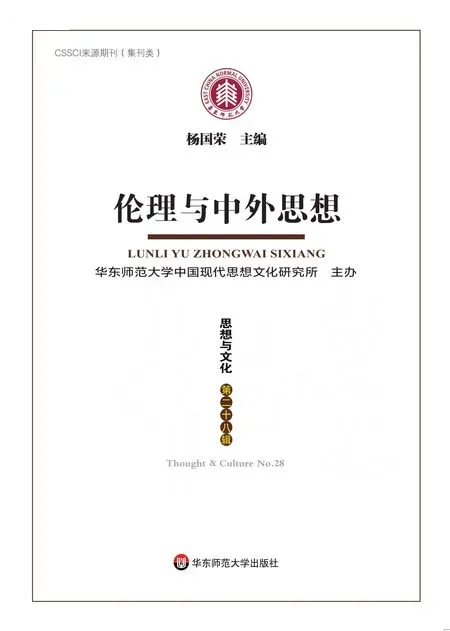《乐记》“礼乐之说”章“设—说”辨讹*
●
《礼记·乐记》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此句与《乐书》及荀子《乐论》相似,该句在《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荀子·乐论》分别作:



司马迁《乐书》、荀子《乐论》与《乐记》“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句的文字差别一在是“管”字还是“贯”字,二在是“说”字还是“统”字。
“管乎人情”、“贯乎人情”的差别是“管—贯”通假,“贯”是“管”之假借字。唐《慧琳音义》卷四十五“贯邑”引《考声》云“贯,管也”。此处“×乎人情”句应从《荀子·乐论》及《礼记·乐记》,因为“贯”没有“管”义,“管乎人情”即主管、主掌人情义。
何谓“贯”?“贯”字本是串钱之声,引申为贯通、积累,从“贯”的“惯”即积累之义。《说文·毌部》曰“以绳穿物谓之贯”,清代黄生《义府》卷下曰:“以缗穿钱曰贯,故有相续不绝之义。”何谓“管”?《说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说文》又曰:“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从品仑,仑理也,凡龠之属皆从龠。”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曰:“《诗》‘左手执龠’,传云‘龠,六孔’。馥谓六孔者管也,本书‘管如篪,六孔,以和众声也’者。”管是吹管,从竹,有乐孔之竹器,后延伸指竹管状之物。
古人又释“管”为“键也”、“管键也”、“管键者也”、“所以出键者也”、“鑰与管同物,皆为搏键之器”、“锁籥,其牡曰楗,其牝曰管”,又引申为“即关也”、“即锁”、“关主曰管”(1)宗福邦等主编: 《故训汇纂》,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80页。,此皆是由竹管引申管状的锁匙之物,又引申为关键、主宰之义等。《汉书·食货志》“管山林之饶”颜师古注曰“管,主也”,《史记索隐》引高诱曰“管,典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管,掌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四曰“管者,典也,主也……管库之士谓主此库者耳”。“典”亦有“主”、“掌”、“职”之义。所以“管”有主、典、掌、职之意,此今“管理”、“管制”之“管”。《荀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杨倞注曰“管,枢要也”,杨倞又注《荀子·富国》“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曰“犹包也”,此亦是“主”义而已。
郑注“管乎人情矣”句曰“管,犹包也”,孔疏曰“‘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者,言礼乐所说义理,包管于人情。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人情所怀,不过于此,是管人情也。”“管乎人情”之“管”释为“主”、“掌”比释为“包”更合适,不是礼乐包罗人情,而是礼乐主掌人情之义,此即《乐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礼节民心,乐和民性”之义(此两句“性”字本作“声”字,声近而误也,详见另文专论)。
所以,“贯乎人情矣”即“管乎人情矣”,“贯—管”是同音字假借,字义还是“管”字义。那么“礼乐之×”究竟是《乐记》、《乐书》的“说”字还是荀子《乐论》的“统”字呢?“说—统”两字的差别如何解释呢?郑玄并未注“礼乐之说”的“说”字,而孔疏则曰:“‘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者,言礼乐所说义理,包管于人情。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人情所怀,不过于此,是管人情也。”此是解“礼乐之说”为“说礼乐”即“言礼乐”义,意思是礼乐有不同,但言礼乐则必包管人情之义。宋陈旸《乐书》卷二十二释“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大体同孔疏,陈旸曰:
乐出于天地之和,莫适而非同;礼出于天地之别,莫适而非异。乐之统同,非求同于乐也,因其自同本和以统之而已。礼之辨异,非求异于礼也,因其自异别宜以辨之而已。同有所统,异有所辨,而礼乐之说盖有所不能忘焉。然礼乐法而不说,亦不过管乎人情者而已。荀卿曰:‘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圣人矣。’盖统之必有宗,故言管乎圣人。说之不过乎人情,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礼乐之管,而圣人又人情之管也。
《乐记》“说”字凡3见,除“礼乐之说”章外,还有另外2见,兹一并罗列如下:
(1) 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郑玄不注“说剑”,孔疏曰:“说剑者既并习文,故皆说剑也”。此解今读起来仍不清晰,不知孔疏此“说”是“言”、“谈”义还是他义。此“说剑”当是《淮南子·俶真训》中“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的“说”字之义,故《四部丛刊》宋本《淮南子》里有汉许慎之注曰:“诱,惑也,进也。说,释也。”
《乐记》里的“说剑”即是“释剑”之义,类似于今“脱”字。唯有“释剑”义与前后“射息—知孝—知臣—知敬”共同构成尚文之“五教”,尤其与前面“射息”相连相关。“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的意思是崇尚衣冕笏礼则虎贲之士释剑(脱剑),正与上下文义相同。郑注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孔疏曰:“裨冕,入庙之服也。搢笏,插笏也。虎贲,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军。”“虎贲之士说剑也”即“虎怒之士释剑也”。
故《礼记·乐记》的“说剑”即“脱剑”,此又同《礼记》里的《檀弓上》“说骖”、《檀弓下》“说齐衰”、《曾子问》“说衰与奠”、《文王世子》“不说冠带”、《玉藻》“说笏”、《少仪》“说屦”、《少仪》“说绥”、《杂记上》“说輤”、《杂记上》“说车”、《丧大记》“说髦”、《丧大记》“说繘”、《间传》“不说绖带”、《乡饮酒义》“说屦升坐”等“说”,实皆“脱”字之义。“说—脱”相通,未知是因为形声相同,还是“说”本有“脱”义,按《说文》则“说”本有“脱”义。
《说文》曰:“说,说释也,从言兊,一曰谈说。”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臣锴曰: 说之,亦使悦怿也,通论详矣。”《说文》段注曰:“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釆部曰: 释,解也。”郑玄注《礼记·乐记》“说之,故言之”曰:“说,音悦,和。”此释同《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说”。《礼记·乐记》于“歌之为言也”章,孔疏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者,言歌之为言,引液其声,长远而言之。‘说之,故言之’者,此更覆说歌意,前境有可说之事来感己情,则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者,直言之不足,更宣畅己意,故引液长言之也。”
《乐记》“礼乐之说”当然不是“礼乐之悦”或“礼乐之释”义,更未必是“礼乐之谈说”。然笔者根据《乐记》上下文及《荀子·乐论》对应“礼乐之统”之字义,推定《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礼乐之说”的“说”字乃“设”之讹也。“说—设”繁体本作“說—設”,形近,易字讹,且有先例。如《周易·睽卦》上九曰:“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清惠士奇《礼说》卷六曰:“‘先张之弧,后说之壶’,古说与设通。”清惠栋《九经古义》卷一曰:“‘先张之弧,后说之弧。’《释文》云:‘下弧字本亦作壶’。诸家皆作壶,今作弧者,声之误也。……后‘说之壶’,案《礼说》云:古说与设通。”王树枏《费氏古易订文》卷二曰:“传云: 壶,瓠也。案《礼说》云:古说与设通。”清顾堃《觉非盦笔记》卷二亦引《礼说》“古说与设通”之证。
以“谈说”之类解“礼乐之说”之“说”字实谬,此“说”当是“设”字误。“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即“礼乐之设,管乎人情矣”,唯设置礼乐以管理人情才是最合理的,才符合《礼记》该章及全书文义,也方体现儒家思想。“礼乐之设,管乎人情”,可谓《乐记》论礼乐之总纲。唐张守节注《史记·乐书》曰“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此“贯人情,辩政治”判断极是。人情是中心,良好政治及良治是目标。《乐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及司马迁《礼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之义,王充《论衡·本性》曰“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则皆可谓即“礼乐之设,管乎人情”之翻说。
古人训“设”为“施也”、“犹施也”、“施设也”、“施陈也”、“陈也”、“置也”、“置立也”、“谓置设”、“谓制置”等,故“礼乐之设”就是“礼乐之施”、“礼乐之立”等义,“礼乐之设,管乎人情”就是立礼乐、置礼乐以主掌人情之义,此与荀子《乐论》“礼乐之统,管乎人情”相同。而礼乐之设置当本乎人情人性及当教化人情人性的道理(2)林桂榛、王虹霞: 《〈乐记〉之“乐”》,《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3日。,正是“礼乐之设,管乎人情”或“礼乐之统,管乎人情”的儒家思想之要义。
“统”字有“理也”、“摄理也”、“治也”、“制治也”、“总也”、“总览也”,故今有“统治”、“总统”之词,属近义或同义两字构词。“统”是如此义,故“礼乐之统”就是“礼乐之治”、“礼乐之制”、“礼乐之统摄”的意义,所以《乐记》“礼乐之说,管乎人情”即《乐书》“礼乐之说,贯乎人情”,其“说”字无疑是“设”字之误而已,且它们显然都是化自《荀子·乐论》“礼乐之统,管乎人情”句而已。
《荀子》多言“统”,全书“统”字凡25见,而“设”凡19见,“统”多于“设”字,且含义深刻,如“礼义之统”、“仁义之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忠信以统之”、“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举统类而应之”、“知通统类”、“礼义无统”等。
《乐论》、《乐记》、《乐书》该处文字的差异处见下:
(1)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墨子非之,几遇刑也。明王已没,莫之正也。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其德也。乱世恶善,不此听也。(《乐论》)
(2)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乐记》)
(3)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乐书》)
《乐记》、《乐书》该处的文字差别只是当传写古《乐记》的文字差别而已,而古《乐记》化自《乐论》无疑,《乐论》的“和—理”、“合—别”、“统—管”、“穷—极”对说或并说明显要胜于《乐记》“情—理”、“统—辨”、“说—管”、“穷—知”之对说或并说,也胜于《乐书》“情—理”、“统—别”、“说—贯”、“穷—知”之对说或并说。而且《乐记》、《乐书》改“礼乐之统”为“礼乐之设(说)”,则于同句其他地方改有“统”字,即《乐论》“乐合同”被改为“乐统同”。
古人不仅说“礼乐之统”,也说“礼乐之设”。孔疏《乐记》“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处曰:“此一节明言礼乐之设不得其所则祸乱兴,故先王节其礼乐以防淫乱也。”(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九十五引之)元翟思忠《魏郑公谏续录》卷下有曰:“太常少卿祖孝孙奏请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设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明郑纪《东园文集》卷三曰:“礼乐之设,所以飨郊庙、宴臣僚,其事为至重也,故唐虞之时伯夷寅清而典礼,后夔直温而典乐,慎重之意何其至哉?”清罗有高《尊闻居士集》卷二曰:“礼乐之设,诗书易春秋之教,所以养人之微、达人之微者。”
[附]释《乐记》“乱”范畴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