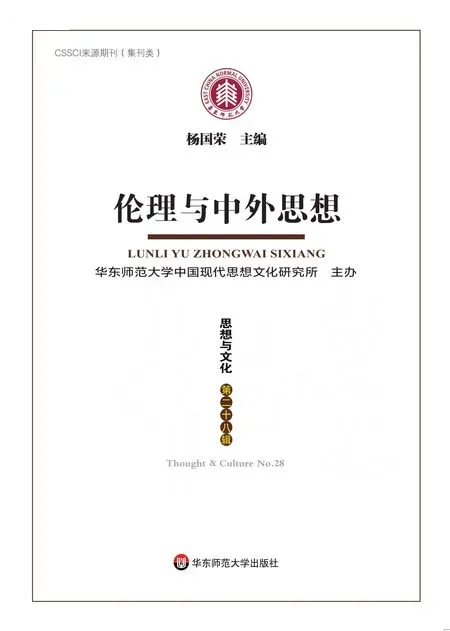一套《荀子》式的恶的理论: 以礼义及“群居和一”为基础
●
性恶论一向是荀子研究的一个重点,当然这有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以孟子视域为主的儒学研究的原因。孟子唱性善,而荀子道性恶,这是两者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或争端,且《荀子·性恶》本就是以孟子作为其设想中最主要的论敌。
从宋代理学明确孟子的儒学正统地位之后,就不断有学者试着以孟子视角的反面,即性恶作为出发点以整理《荀子》的理论架构,当代又出现了对《荀子》“性恶”的纯粹性恶、性有善有恶、性恶伪善、性朴等不同的解释方式。不过,这些对性恶的理解往往是在人性论视域下建立的。但事实上荀子的性恶一说不单止是一种人性理论,从其展开的论述来看,也同样反映了一种对于恶的认识。这一认识可以使得我们就此建立一套荀子式的恶的理论,从而对当下关于恶的理解有所贡献,而这也是本篇论文的主要目的。就此,本篇论文将先对荀子性恶表述作一解释梳理,随之借此以提出一套荀子式的恶的界定理论,并对其独特之处稍作说明。
一、 群居和一及荀子对恶的理解
在《荀子》书中,恶这一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人性所表现出的特质,从而成为了求诸善的个体致诚修身的原因;也同样在于它与荀子理想中的社群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荀子直接从社群的角度解释恶,《荀子·性恶》云:“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1)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8年,第434—43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恶从人性特质层面到实现一共有三个步骤:“争夺”、“犯分乱理”和“归于暴”。第一和第三个步骤便于理解,它们之间看上去似乎也可以直接连起来;但荀子却在这两个步骤之间选择放置了关乎社群层面“犯分乱理”作为关联前后的重要一环;且在其随后的关于“其善者伪也”的描述当中,提出的用于纠治恶的“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也与人的社会性相联系。因此,本文认为或许有必要在进一步讨论荀子的恶的理论之前,先就《荀子》当中社会的起源和“分”的问题作一简要说明。
在《荀子》书中《富国》篇的起始部分,荀子描绘了其所设想的最初的社会乃至政府的形成过程。荀子率先明确了人群内在的相同点和差异点,“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2)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175—177页。。人们虽然在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以及个体行为方式上有差距,但有着相同的欲求。假若仅仅是各自凭着各自的认识以行为,很容易因为一致的欲望对象而彼此展开争夺,导致不能和睦相处。
荀子把这种“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所可能导致的混乱归结为没有完整的行政执法机构,“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但同时荀子又指出,除了完整的行政执法机构维持秩序外,也需要考虑到一个人欲求物的多元性,“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人所享受的物质乃是整个社会不同个体不同工作成果的集合,而一个人没有能力去适配所有的工种。因此,荀子得出结论,“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3)本段引文出处同上。。
“明分使群”是荀子提出的解决办法,埃里克·哈里斯(Eirik Harris)与佐藤将之都认为荀子在这里所强调的“分”就是把资源、劳动、权利及义务在社会内合理分配的依据。(4)见Sato Masayuki, 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 Leiden: Brill, 2003, pp.352-353; Eirik Harris, “Xunzi’s Political Philosophy,” 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Eric Hutton(ed.), L.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6, pp.96-138。人们需要群居以克服在自然界的生存挑战,但人们有太多的欲望,而自然资源并不足够,因此在一定的分配方式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很自然地形成了。而很显然,《荀子》书中“分”的这种分配方式并不是纯粹描述性的,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并非任意一种分配方式都可以是“分”。《荀子·王制》曾对这种“分”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解释。
在《荀子·王制》中,首先荀子指出了人较之其他的物种而言的特殊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5)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164页。。其他的物种只有气、生、知而没有义,人凭借有义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尽管除了义之外,人有很多能力反而不如禽兽,但义弥补了这些差距,荀子接着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 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
从这里来看,《荀子》中的“分”除了可用于资源的分配之外,也使得人们的劳动分工可以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并在其基础上形成群体,借此可以充分利用万物并面对自然界的挑战。而“分”的制作及践履依赖于人用来将自身和动物相区分的“义”。
但人们如何能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义”的内容,又如何以人自身所具有“义”作为基础以“明分”呢?似乎这不是多数人能自然达到共识的范畴,否则也不会有《荀子》之前提到的争端了。就此,《荀子·荣辱》谓:“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70—71页。荀子认为答案是先王制作了大家应该共同恪守的礼义,并以此作为制分的依据。
对于荀子而言,这里的礼义是圣王所制定的用于合理、客观地反映差等的准则,可以与人自身所具备的“义”相呼应。人凭借其自身所有的“义”,能够理解并接受依据圣王礼义所制定的分。不过由于礼义及在其意义下形成的分只是一系列标准、准则,不能构成完整的制度,因此先王还需要根据礼义及分,制作出一套礼法来。不同时期的礼法之间是有差异的,譬如周初先王之制和尧舜之制就不完全相同。但作为礼法根本的分却是一致的,因而《荀子·王霸》谓“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214页。
因此,作为群居生活基础的分是一致的,无论制度怎么变化。那么,“犯分”显然就是一种对“群居和一”原则的潜在的挑战了,因为荀子并不打算承认有多种其他的分可以作为替代品。这种挑战会导致群居秩序的破坏,“而归于暴”,丢弃文明,而回归野蛮了。在社会层面上导致野蛮暴力的竞争或冲突,可以客观表现为上文所引《富国》篇的“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8)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176页。。
这便是《荀子·性恶》中所讲的“从人之性,顺人之情”所导致的混乱,若按原文“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可见荀子似乎认为这已可以用于说明性恶了。而将荀子这一对恶的理解作一重新表述,可解释为“一个人顺从自己的性,造成违反群居和一准则情形的便是恶”。
但这个说法显然还不完善,究竟什么是“顺从自己的性”呢?按《荀子·性恶》开篇所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若就“好利”而言,似乎荀子得出的性恶实质上是指向欲望的;但如果以此方式理解,却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单凭欲望本身是否足以造成恶的结果呢?艾文贺(P.J. Ivanhoe)曾指出一个例子,一个偷梨吃的人并不一定有偷梨的欲望,他可能只想吃梨。而吃到梨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9)Philip J. Ivanhoe, Confucian Moral Self Cultivatio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0, p.40.既然如此,驱使这个人为了满足吃梨的需求而去偷梨的因素不见得最终能被归于欲望。第二,就《荀子》全书来看,荀子并不主张舍弃代表欲望的情性。因此《荀子·非十二子》同时批评了“纵情性”的它囂、魏牟与“忍情性”的陈仲、史鰌,且《荀子·正论》又指责了子宋子的“人之情欲寡不欲多”,并肯定了圣王以人的情性制定赏罚的模式。似乎,对于荀子而言,情性并不是作为恶的存在物而需要完全舍弃的对象,只要其能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得以表达即可。
若就此来看,这似乎如同柯雄文(Antonio Cua)说的那样,荀子所说的恶,只是一种结果的恶,一个人想吃梨并没有善恶可言,但是为了吃梨而去偷东西则造成了恶。(10)Antonio Cua, Human Nature, Ritual, and History: Studies in Xunzi and Chinese Philosophy, Washington, D.C.: CUA Press, 2005, pp.3-38.那么荀子的恶的理论似乎变成了“破坏群居和一原则的后果就是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荀子又怎么能够得出“性恶”的结论呢?虽然一些早期的学者,譬如胡适、郭沫若等多认为荀子这种性恶的说法,只是描述性的,或者修辞意义上的,并非真正要去论证性恶。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性恶》篇接下来为什么还要去刻意反驳《孟子》的说法呢?
邓小虎则不同意这种仅限于结果恶的观点,特别强调“顺”在其中的意义,认为性恶的含义是人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会作坏事的一种自然趋势。(11)Tang Siufu, “Xing and Xunzi’s Understanding of Our Nature,” 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Xunzi, pp.165-197.《荀子·荣辱》中曾指出“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无师无法,则其心正其口腹也”(12)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64页。。邓小虎据此认为,荀子的观点是在没有师法的情况下,人们用于知道明理的“虚一而静”的心就像口腹一样,会被欲望及与其相联系的自然趋势所主导。虽然人最初的性质无所谓善恶,但这种自然趋势会使得人可以走向作恶事的方向,乃至引导人走向作恶的途径。
但这种自然趋势究竟应如何理解呢?庄锦章曾提出一种观点,试图抛弃用本质主义方式理解荀子性恶的径路。庄锦章认为,性不是《荀子》当中人最核心的要素,这里的性恶只是用于与礼义之伪所带来的善相对照,用以指出不接触礼义、不学习礼义的情形。(13)Chong Kim-Chong, “Xunzi on Human Nature,” Confucian Ethics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hen Qingsong and Shun Kwong-loi (eds.),Washington, D.C.: CRVP, 2008, pp.93-112.
相比于邓小虎而言,庄锦章的方式不再需要对最初的性质以及自然趋向作更多的界定和区分。这种方式避免了进一步发掘“顺是”含义的困难,也同时可能更近乎荀子原意。《荀子》书中所谓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等对性的描述皆偏向于自然整体的层面,而情、欲等因素只是性在某些方面的具体体现。本文在这里并不是想将荀子完全等同为成中英所说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机体主体者,(14)成中英的说法可见Cheng Chung-ying, “Xunzi as a Systematic Philosopher: Toward an Organic Unity of Nature, Mind, and Reason,”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35 No.1(2008): 9-31。但至少在性的这一方面,荀子似乎从没有对性给出一个更为细致全面的正面描述,而是倾向于将其与伪以及人力可为的部分作一对立。
《荀子·性恶》又云:“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可见前文荀子提出的克服性恶以师法圣王所学的内容,亦正是礼义法度。因此,既然推动礼义法度才是荀子性恶论所旨在的目的,我们与其对性作一个不甚精确的概括;何不反向地把顺从“生之所以然者”的性所导致的自然趋势理解为一种无礼义法度状态下的自然产物呢?至此,我们可以把荀子对恶的这一理解重新解释为:“一个人在无礼义法度状态下出于其自身固有的原因,造成违反群居和一准则情形的是恶。”但在对这一理解进一步展开前,这里我们还需要讨论一种额外的情形。
精神病人也可能会造成残酷暴力的血腥事件,但对此,人们却不见得一致地会将其视作恶。究其原因来看,这个精神病人可能行为不能完全自主,因而在某些情形下会被认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甚至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当然,这其中还牵扯了一些别的问题,例如依此意义而言,这个精神病人做的任何好事似乎也不应该被视作行善,不过很多时候似乎人们并不倾向于承认精神病人不可能作好事这样的观点,这可能和人们总是倾向于承认更多的善和更少的恶有关。但无论怎样,一个总是做好事的精神病人似乎比一个总是做坏事的精神病人更好,而且不止是因为做好事的精神病人可能在某些方面实质上帮助了正常人的原因。同样从生存权利而言,故意杀死一个精神病人似乎并不比杀死一个非精神病人在道德层面上相对更好;尽管精神病人显然不能和正常人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
不过荀子书中没有涉及对精神病人、完全喝醉的人等非完全自主状态下的行为主体、或者没有“义”的人作一系列的讨论,本文亦不打算对这一系列问题再作更为详尽的分析,因为这也并不是该篇论文的重点。但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分歧,荀子对恶的理解或者可以再作进一步的修改或限定,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人在无礼义法度状态下出于其自身固有的原因,造成了违反群居和一情形的是恶。”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完成了对荀子这一步的性恶论证的重新表述。当然如果要基于荀子关于恶的这一理解而表述成一项当代意义下的恶的理论,其中还有一些表述上的问题。首先是这一理解当中还有两个《荀子》书中专有的用词,一是“礼义法度”,二是“群居和一”。相比于礼义法度,群居和一显然更为清晰明白,其意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人们各得其宜,和睦共处。这一用词或许不必再作更为多余的翻译;而理解礼义法度,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荀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礼义法度的内容大纲,尽管我们可以从先秦文献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恐怕不能详尽,而且先秦的礼义法度于当今而言亦未必能适用;其次,由此而引申的无礼义法度状态又应当如何进行重新表述?它在《性恶》篇似乎原本是指向没有师法、无知于礼义法度的情形,但明知于礼义法度而违反礼义法度的情形,似乎也不应被排除在恶的范围之外。而就此关于荀子这一理解再理论化的表述问题,本文将在接下来这一节再作更为具体的讨论。
二、 《荀子》式的恶的理论及其意义
上文已经就荀子在《性恶》篇中对恶的理解作了一个重新表述,“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人在无礼义法度状态下出于其自身固有的原因,造成违反群居和一准则情形的便是恶”,但如果想就此得出一套关于恶的理论,其中关于礼义法度和无礼义法度状态的问题还需要重新进行厘清。此外,就荀子这一理解而言,这似乎只说明了“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人在无礼义法度状态下出于其自身固有的原因,造成的违反群居和一准则的行为”蕴含了恶;但假设要得出一套关于恶的理论,或许我们还需要考量,假若反过来说,恶是不是都是“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人在无礼义法度状态下出于其自身固有的原因,造成的违反群居和一准则的行为”呢?
至于无礼义状态是否包含明知于礼义法度而违反礼义法度,或者曲解礼义法度的情况,尽管在《性恶》篇来看,接受师法之化和礼义之道之后,人便能够由原初性恶的状态改变为“正理平治”的状态;但《解蔽》篇又指出“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15)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388页。,人可能因为心知能力受蔽而不能正确意识到“大理”或礼义,且《荀子》全书有许多篇章都在强调为善修身还需要额外一套工夫。
《荀子·解蔽》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又谓“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1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394—395页。。荀子试图通过心知解释人的实践理性及相关的能力,指出了心在认识及实践活动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正确认识道的这一层面上有着无可取替的作用,只有在心知道的前提下,人才能正确区分道与非道,并依据于道以正确地方式行动。在此意义下,无论是明知礼义法度而违反礼义法度,还是曲解礼义法度,都可以被理解为“出令而无所受令”的心知受蔽。这也正是桀、纣之行与商汤、文王之行迥异的原因,“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桀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成汤监于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文王监于殷纣,故主其心而慎治之”(1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388页。桀、纣的心知能力因佞臣而导致惑乱受蔽,从而导致行为悖乱;而商汤、文王以心为主,谨慎修治,不为受蔽,才能使得其行为合乎礼义。因此,我们在此可以再将“无礼义法度状态”重新理解为“对公共性价值及公共原则的心知之弊”。
另外,《荀子·性恶》也同样反过来对性恶的表现作了一个表述,“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18)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439页。较之“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而言,恶蕴含的实际意义“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似没有太大的差异,仍然属于违反群居和一准则。且就荀子来看,后者的形成原因亦不能离于对礼义法度的认知缺乏或者认识偏差,因而“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则足以达到纠治的效果。不过“归于暴”似乎多是体现在后果上,而“偏险而不正”则可能只指涉个体的行动动机或者心理状态。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荀子对恶的理解,关于违背这种群居和一的恶是更基于人的欲望,抑或更基于行为的动机或后果,在此笔者仅持一种中立的看法。但至少我们或许不应将实际后果外的心理层面排除在荀子这一恶的理论的概括范围外。那么简要而言,我们可以将当代意义下的荀子式的恶的理论重新解释为: 恶即是指代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行为主体由于其自身对公共性价值及公共原则的心知之弊,在完全自主的前提下实际造成或倾向于造成违背“群居和一”的情形。
事实上,“群居和一”的准则体现在整个社会组织的运行程度、各个个体就其角色职责的完成程度以及人们对于各项行为的接纳程度等方面,试图容纳整个群体成员的视角,这意味着一些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受害者或者直接受害者不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但也可能会破坏“群居和一”。譬如一个人变态虐待动物或者恶意破坏自然资源、人文景观的行为,也可能不为群体所接受而影响到“群居和一”的形成。同时,尽管在礼义价值及其所含意义上所构成的道德规范是用于维护“群居和一”的方法,但亦非必然能保证“群居和一”,且达到“群居和一”的目的有时亦不必然依赖于礼义。而只有同时由于心知之蔽而违背礼义价值且又实质上破坏“群居和一”的情形才会被视作恶。
譬如《荀子·仲尼》中所描述的齐桓公即是不全然蹈于礼义、但不破坏“群居和一”的一个典型。齐桓公“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19)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106页。,但其行为整体在荀子看来,仍然可以是“有天下之大节者”,使得齐国“贵贱长少,秩秩焉”。虽不及王道,但齐桓公也成为了五霸之首。不过由于齐桓公违背礼义,只能是“小人之杰”,而不入“大君子之门”。
要让加油站站点、库存发挥作用,就要有足够的运力保障。“和过去几年相比,现在农民用油都比较理性了。以前油价低时,农民喜欢集中一起买很多油储备起来,现在油价变化频繁,农民用油比较均衡,随用随买。”刘延奎向记者介绍道。
而一种导致破坏“群居和一”准则的行为,也同样可能契合于礼义价值,汤武革命便可以作为这类情形的例子。以周武王为例,在牧野之战中商周发生了大规模的残酷战争,造成了大量死亡,《尚书·武成》中将其情形描述为“血流漂杵”。在儒家传统中,周武王的行为显然是合乎礼义的,但战争造成了对大量家庭的伤害、社会组织的破坏。
对此,孟子曾由于其对仁的理解不能与行为后果分割,因而无法接受《武成》篇的说法,“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20)赵歧注,孙奭疏,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 《孟子注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1页。。但对于荀子而言,由于礼义价值与“群居和一”的保证方法不必全然相等同,这种情形则更容易接受,这既反映在《荀子》书中出现多次的“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的话语中对霸者的宽容,也反映在其肯于承认“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除了周灭商的战争外,也指出了周文王武力讨伐密国、阮国、共国、崇国的史实及周武王杀纣及妲己或恶来的事。(21)杨倞指出了两个说法,一个说法依据《史记》中的“武王斩纣及妲己”,另一个说法依据《尸子》中的“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然杨倞是唐代人,其所见原文与今本《史记》稍有出入,但其意相同;而《尸子》本佚,今辑本即取材于此,无从再考。详见《荀子集解》,108页。
为了更好地理解礼义价值和“群居和一”的维持之间的关系,或许我们还可以再作一个类比。当代的实证法学派曾将社会道德规范分作批判性道德(critical morality)和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两类。(22)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最早出现在奥斯丁的法理学当中。奥斯丁对法律传统作了梳理,界定了自然法(natural law)和实在法(positive law),前者是自然存在的或者上帝制定的法,而后者是人所制定的法。在此界定基础上,奥斯丁还对社会道德规则作了划分,他认为存在的实在道德包含着两类道德: 一是“本然”(as it is)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对这种规范的好坏不作考量的道德;二是“应然”(as it would be)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必须考量这种规范的好坏的道德。奥斯丁认为第二类道德规范与自然法或者上帝法有着关联。参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0。但“实在法”及“实在道德”在奥斯丁此书之后的用法有一点改变。奥斯丁法理学旨在建立一套精确的以主权者命令为核心的法理学体系,从而把一系列非命令(command)性质的法剔除出他的法理学体系之外,再进行讨论,习惯法(customary law)便是其中的代表。奥斯丁在排除习惯法的时候解释说,习惯法属于实在法,实质上已经将“实在法”这一概念所统摄的对象与他的法理学体系中“法律”概念作了区分。参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p.34。尽管实证法学试图区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适用于实在法。事实上,奥斯丁就将实在道德视作这样的一系列道德规则: 据此,以习惯法为代表的实在法得以建立起来。参见John Austin,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p.36。不过,奥斯丁并没有提出过批判性道德(critical morality)的概念;而哈特则进一步将实在道德和符合基本道德原则的、由理性推导且经过社会批判的批判性道德作了对立,并认为从批判性道德的角度出发,用立法的方式去强制推动实在道德是错误的。这种两分方式出自于哈特(H.L.A. Hart)之手,在他来看,前者是由公认的道德原则经过理性验证及社会批判而形成的道德规范;而后者则偏向于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惯例下形成的道德规范。(23)H.L.A. Hart, Law, Liberty, and Morality,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0.
接下来我们可以就具体实例作一讨论。至少就我们现在来看,堕胎并不是一件违反批判性道德的行为,应该得到允许。但在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中期的英国,堕胎违反了当时基督教背景下的实在道德,这也体现在了英国法律当中。1861年英国颁布的人身侵害法案(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 Act 1861)第58条和第59条禁止了通过药物和工具导致妇女流产的行为。其规定如下:
第58条 凡怀孩子的妇女,如意图使自己流产,而非法地给自己施用药物或其他有毒物品,或非法使用任何器具或其他手段;以及其他任何人,意图促使妇女流产,而非法地施用药物或其他有毒物品,或非法使用任何器具或其他手段,在无论妇女是否怀有孩子的情况下,即属犯重罪,如被定罪,最高可判处终身拘役。(24)原文如下: Every woman, being with child, who, with intent to procure her own miscarriage, shall unlawfully administer to herself any poison or other noxious thing, or shall unlawfully use any instrument or other means whatsoever with the like intent, and whosoever, with intent to procure the miscarriage of any woman, whether she be or be not with child, shall unlawfully administer to her or cause to be taken by her any poison or other noxious thing, or shall unlawfully use any instrument or other means whatsoever with the like intent, shall be guilty of felony, and being convicted thereof shall be liable ... to be kept in penal servitude for life.
第59条 任何人明知其行为会被用于非法途径或意图促使妇女流产的情形下,提供药物或其他有害物品,或任何器具或物件,在无论妇女是否还怀有孩子的情况下,即属犯轻罪,如被定罪,最高可判处拘役。(25)原文如下: Whosoever shall unlawfully supply or procure any poison or other noxious thing, or any instrument or thing whatsoever, knowing that the same is intended to be unlawfully used or employed with intent to procure the miscarriage of any woman, whether she be or be not with child, shall be guilty of a misdemeanor, and being convicted thereof shall be liable ... to be kept in penal servitude.
而即便是普遍被视作代表除北爱尔兰地区以外的英国废除堕胎的堕胎法案(Abortion Act 1967),也只批准了在注册的有证书的医学从业者或有两个以上医学从业者所“真诚地”给予意见而终止的怀孕(when a pregnancy is terminated by a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if two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are of the opinion, formed in good faith),且限定在可能孕妇造成伤害或危险、胎儿可能有严重可能导致身体或精神不正常、或胎儿未超过24周且可能在之后的孕期造成更大危险的情形下。而相对更为保守的爱尔兰及北爱尔兰直到2018年才立法废除原先的堕胎禁令。
尽管在批判性道德的要求下,堕胎是应当被允许的;但在当时的英国提出禁止堕胎的法案是否一定可以被算作是恶呢?类似的事情还包括如同禁止离婚,对同性恋者进行强制电击治疗的法令等,这一系列法案的提出都可以被视作是恶吗?人们或许会对这些法案的正误、妥当与否作一些商榷,但似乎很少会把它们直接视作恶。
当然反过来也与之类似,假如破坏实在道德而不违反批判性道德的行为,似乎也不应当被视作是恶。譬如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雪莱在牛津大学宣传无神论,王尔德发生了同性恋的行为,都违反了当时的实在道德规范,但并不违反批判性道德,我们现在也并不会将雪莱和王尔德的这些行为视作是恶。事实上不止如此,违反实在道德而不违反批判性道德的行为,至少包括道德理性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也不会认为这种行为是道德错误的。
本文在这里并不是想要将批判性道德、实在道德完全相等于荀子式的恶的理论中的公共价值及公共性原则、群居和一,事实上它们之间也有着不少的差异。譬如,相比起实在道德而言,群居和一则看上去拥有着更广的蕴涵。实在道德只指代业已存在的道德规范,而群居和一则对于社会组织完整性有着更多的要求。一些挑唆以制造争端的行为,若对某些少数群体的仇恨演讲(hatred speech),虽然可能在某些时间、某些场合下,演讲人的行为未必会被公众直接反对,也未必与旧的实在道德相违背;但因为其对社会组织潜在可能的危害性,仍可以被视作是破坏“群居和一”的行为,无论仇恨演讲是否违背了批判性道德。
但批判性道德与实在道德的区分,事实上可以让我们能更为明晰地认识到礼义法度或者说是公共价值及公共性原则所构成的一套规范,完全可能与以“群居和一”为唯一目的的规范有着不小的差异乃至发生冲突。就以《荀子》原文来看,礼义法度本身显然有着更多的致善的诉求,譬如《不苟》篇及《荣辱》篇中将是否“合乎礼义之中”定为“君子小人之分”,尽管荀子眼中齐桓公这样的“小人之杰”也可以使得齐国“贵贱长少,秩秩焉”。由此可知礼义除了具有面向整个社群的效用外,也意在帮助人们修身成仁。
三、 尾论
恶的问题可以分为对恶的界定以及对恶的生成机制进行探析这两类,哲学传统上一般以对后者的讨论为主,或许认为恶产生于是对善的认识偏差,或是认为恶具有一个本质源头等。然而对于前者,或许恶在某些宗教中更为严格的定义,但就世俗背景而言,这个问题则显得十分复杂。
首先,当我们使用“恶”去描述一个对象时,这个对象似乎是并不是固定属于某一个类型。人们可以说一项行为是恶的,但也可以说某一种欲望或者某一种人格等是恶的。尽管前文曾提到一个人偷梨吃不一定是基于偷梨的欲望,其吃梨的欲望是中性的;但这并不能否认欲望也可能会有善恶之分,例如具有偷窃癖好的人可能确实会有偷梨的欲望,甚至于在偷梨的背后并没有吃梨的欲望。
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叩问是否存在一种客观实在、无时间性的恶的真理,但就实然情况来看,恶的认识也常常与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有关。一个女性自主自发地婚后出轨的行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道德错误的。但在某些特定时间点下,它会被视作一种典型的恶行;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这个行为尽管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却不一定会被当作恶行。
一般而言,在人们的认知中,恶似乎都属于道德错误,但道德错误却并不都是恶。或许可以从程度上区分恶和道德错误,但人们似乎很难就恶与道德错误在程度上的分界点达成一致。因此,我想荀子式的这一恶的理论,“恶即是指代一个具有完整道德能力的行为主体由于其自身对公共性价值及公共原则的心知之弊,在完全自主的前提下实际造成或倾向于造成违背‘群居和一’的情形”,旨在从“群居和一”的质而不是从量上对恶进行界定,对恶的描述也不必限于某一类对象,或许可以为当代对于恶的理解与界定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