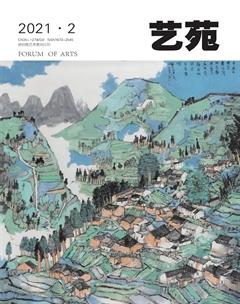《乌鸦与麻雀》:城市内外空间的建构
吴悦
摘 要: 中国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之前呈现了一种飞速发展的状态,此前对这段黄金时期的电影研究往往侧重于时间的表达,忽略了电影中的空间表述。此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很明显地展示出了其空间倾向。不论是都市电影,还是乡村电影,其中的空间结构都带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文章所要探讨的《乌鸦与麻雀》,不仅涉及到大众对于战后上海的复杂情感状态,还通过城市的具象空间搭建了城市内部的家国情感构建。相较于对城市整体的表述来说,文章更倾向于探讨具象空间的构建。
关键词:《乌鸦与麻雀》;城市;空间;家国情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的空间建构
城市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答案有很多种。亨利·勒菲弗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将城市表述为都市(urbain),都市是一个自由的概念:“是一种形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从土地的出产品到所谓文化的符号与作品。”[1]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时间、性别构形》一书中,将城市定义为:“城市不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道德秩序,一组态度,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个人类联系的网络,一套习俗和传统。”[2]张英进的著作将对中国电影研究的目光从时间转到了空间,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京、上海的城市空间。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构形”这一概念,并将“构形”的含义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表层来说,“它指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在这个层次中,读者或者观众很容易通过某些碎片化的形象,唤起对于城市的记忆与感觉。其次,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它指以文本书写城市的过程中运用的认知、感觉、观念工具”。在这个层次中,“构形”更多涉及的是一种感觉和认知的行为,它能够在一种“无形式的、不可解读的城市环境中把握空间与时间”。将第二层次的“构形”置于20世纪30年代华语电影的语境中,就不难发现,导演正是通过这种从小到大的认知来认知一座城市。在此种语境之下城市所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发展状况,更多的是被构建成展现善恶对立、家国情感的具象空间。
作为近代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上海是在西方殖民侵略的外力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俨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东方心脏”[3]。作为这样一座在外力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都市,上海既是金钱、财富、文明之都,同时也是罪恶、肮脏、黑暗之城。张英进将上海形容为一座“无法阅读”的大都市,它“常被看成孤岛,与中国传统隔绝,与中国的过去割裂,置身于现代的海洋,前途未卜”。作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独特存在,不管是文学还是电影,对于上海的描述从未终止过。《乌鸦与麻雀》就将故事的发生地点设于上海,通过这个城市中几个阶层的人对一间房子的争夺,来看处在40年代“民族救亡洪流”[4]53中的家国情感。
二、外部空间与罪恶之都
城市作为一个具象的空间结构,它承载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人的家国情感。从20世纪30年左翼电影运动兴起至抗战胜利后涌现出的无数的影片,大多数将故事背景置于城市之中。在《乌鸦与麻雀》中,导演就是以战后的上海这个具象的城市空间为依托,构建了一种在时代之下的家国情感。
大众对于城市的情感从来都是复杂的。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化进程较晚,且这种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力的介入才产生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民主、自由、启蒙等一切美好词汇的代名词。中国近现代的诸多运动,也是发端于城市,城市是知识分子变革社会的根据地。但到了30年代,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左翼的意识形态,他们要求更贴近群众。城市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成了罪恶、淫乱之所。战后大众对于城市的情感态度更趋向于复杂,一方面他们期待战争结束后可以迈入美好的生活,另一方面不断涌入城市的资本家、买办商人、投机分子把整个城市变得乌烟瘴气,大众刚从战争的泥淖中拔出又跌入了城市的漩涡之中。
《烏鸦与麻雀》将背景置于1948年的上海,作为影片的整个大的外部空间,导演展示了国民党溃败前夕,在上海大肆敛财和迫害进步人士的状况。“我们怀着和上海广大人民相一致的痛恨蒋匪帮、盼望解放军的心情,打算以这部影片纪录下蒋匪帮崩溃前夕的罪恶、狼狈逃走的丑态以及人民期待解放的情绪。”[5]10处于新旧交替、光明来临之前的上海民众,对于上海依旧抱有复杂的情感。他们一方面痛恨物价的疯涨和国民党的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在这混乱之中谋得一席之地。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小广播一家,作为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的代表,他们痛恨侯义伯把房子据为己有,在反对侯义伯顶房子的时候表现得也最为激烈。但是,他们又希望通过“轧金子,顶房子”来实现自己小市民般的愿望。
作为影片为数不多的外景展现,小广播夫妻二人去轧金子时所展现的银行及其周遭,是最能够指认作为“罪恶之都”的外部空间。大雨漂泊的夜晚、挤在银行前黑压压的人群、串通好轧金子的“黄牛”、被打的小广播、人群散尽之后的一地狼藉……无不在诉说着国民党所制造的罪恶。无数的人群在高出画面之外的银行的俯视之下,显得如蝼蚁一般。建筑对人的俯视和压迫,也是暗示着建筑背后所代表的力量对于大众的剥削。小广播一家在被打之后靠在银行对面的一角,镜头后景处泥泞、肮脏的街道,是对这种统治力量最直接的表述。同时城市街道的肮脏,在某种程度上也指认着城市本身的肮脏。
三、内部空间与家国情感
影片因为时代和现实的局限,有很多外部空间无法直接展示,主要的故事情节就发生在一间房子之中。但很有趣的是,整个大的外部空间之下,导演又将房子这个内部空间进行上下切割,将它分为四个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的小空间。在以上下为基点划分的空间中,明确了房子这个内部空间的阶级属性,并通过几个空间之间的合作和斗争来展现一种救亡和反抗的家国情感。
在这种以房子代表家国情感的设计之中,导演又在房子的内部细化了不同的阶级属性。从住在阳台房间的侯义伯及其姘头,到二楼小房间的华先生一家,再到一楼的萧老板一家和亭子间的孔夫子,导演在整个被切割的内部空间拉起两个整体对立的阶级——以侯义伯为主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代表的剥削阶级和以华、萧、孔为代表的被剥削的底层。在两个对立阶级的内部,导演又细化出诸多的枝桠,比如侯义伯和其姘头之间的深层矛盾;华、萧、孔之间差异性的观念。
侯义伯和其姘头是因金钱搭建起的关系,二人之间并无实质的情感存在,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矛盾都是建立在金钱之上。所以在侯义伯依旧掌握着经济权力之时,对于他对华夫人心怀不轨,其姘头也无法阻挠。影片表现的重点还是在后者。
住在二楼的华先生一家,是新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胆小怕事,对待政治态度暧昧,但又带着一种清高的神气。他瞧不上住在一楼的小广播一家,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来反对侯义伯,也不愿意低头去找侯义伯,在学校的斗争中也是畏首畏尾。在经过国民党的迫害和教训之后,他身上的清高和害怕才消逝,人也才清醒过来。从更深的层次上来说,华先生所映照的是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那一帮需要被改造的知识分子。
住在一楼的小广播一家,是影片主要表现的对象,他们是最典型的小市民形象。影片首先通过他们住所的拥挤和狭小来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之后再通过其他诸方面来塑造他们的小市民形象。在小广播身上也体现着这种小市民形象的双重特点:他们痛恨剥削,却又想爬入剥削者的阵营中去。
孔夫子在片中的政治隐喻性较强,他是一个传统文人,房子本是属于他的,但在国民党大肆倾轧的时候,他只能栖身于狭小的亭子间。如果说华先生代表的是需要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形象,那么孔夫子所指认的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然懦弱,但也能够说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具有哲理性的话语。
他们三人虽为同一阵营,想要反对侯义伯将房子顶出去,但因阶级属性、性格的不同,三人之间也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们无法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达成一致的意见,直至侯义伯的逼迫到了眼前,他们才幡然醒悟,想要联合起来对抗侯义伯。影片结尾处他们与侯义伯在楼梯上下的对峙,就是两个阶级的对峙,在这个时候楼梯下的萧、华、孔三家俨然是一个整体。他们作为被压迫的阶级,奋起反抗。而楼梯上下的这种空间结构,也是这种阶级差异的指认,只是最后侯义伯必须从楼梯上走下,走出这所房子,落荒而逃,这里所指认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之中,房子对于大众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更是家乃至国的象征。导演将整个40年代大的国家和民族情感,具化到对于中国大众具有特殊意义的房子中。侯义伯与小广播、孔夫子以及华先生对于房子的争夺,实质上是国民党与大众对于国的争夺。导演自己也曾阐述:“为了要在反动统治之下拍摄这部影片,我们不得不使用隐喻的笔法,以侯义伯这样一个官僚兼党棍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而以围绕房子问题的冲突作为影片的中心事件。房子,好比一座江山,它原来属于人民,后来被汉奸、党棍霸占了去,这些坏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是已临近末日,终于夹着尾巴逃跑,而房子重归原主。”
对于一个导演或者一个社会来说,不同的时代所含有的家国情感是不尽相同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社会和电影人所怀揣的家国理想更多的是赶走压迫者,让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走出来。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在反映水深火热这一现状的同时也对未来做了美好的期待。《乌鸦与麻雀》中侯义伯逃走,三户人家共度新年也正是这种期待和希望的展示。在本片中导演将战后的政治交锋弱化,将这种情感搭建在个体与个体的冲突中。作为战时的汉奸,战后摇身一变成了南京国防部官员的侯义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丑恶、伪善的国民党的象征。和他直接冲突的对象孔夫子,虽然是一种传统的落魄文人的形象,但他在无奈中却透露出睿智的光芒,以及加在他身上最隐晦也是最大的一条线索——儿子是共产党——更是拉开了两人的阶级,故事的最终结局也不言自明。亭子间最深的压迫加上隐藏线索的感情色彩,使得孔夫子最先起来的反抗变得合情合理,这种正面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喻着两党的正面交锋。反抗后侯义伯的落荒而逃、孔夫子的隔窗“送别”中隐藏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
如果说导演用侯义伯与孔夫子之间的冲突,在被切割的城市内部空间中搭建起了外部的家国情感,那么华、萧、孔作为这个空间内被剥削的阶级内部的差异性观念,正是导演搭建起的内部的家国情感。首先,以华、萧、孔为代表的个体在阶级上处于一致地位,这就为他们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想离开这个房子。在共同目标之下,导演利用个体之间观念从差异化走向同一化,来完成了内部的家国情感的構建。相对于孔夫子的善良和前期并无反抗意识来说,萧老板一家就显得十分现实,他们对于房子的态度十分明确——不离开。他们想要反抗,但自身并无实力,想要得到房子还得依托侯义伯。这对于小广播一家来说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存在,也正是这种矛盾,让他们彻底看清侯义伯的真面目,从而在孔夫子的带领下进行了真正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以萧老板一家为代表的战后典型的小市民的群体形象,他们一边斤斤计较地做着发财梦,一边又可以仗义执言,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正是这种群体搭建起战后城市发展的主体面貌, 他们是战后社会所需要的群体。在剧作上对于华先生这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安排是符合战后主流想要对于这类立场暧昧不清的群体的改造的。改造过后的华先生有了坚定的立场,和孔夫子、萧老板站到了一起。影片中内部家国情感的构建也随着华先生被释放归来而完成。
作为一部跨时代的影片,《乌鸦与麻雀》中所表现的时间性意义不必多说,在时间的交替之中,空间一直保持不变,但在这种不变之中,又暗含着变化。时间上的辞旧迎新,也是空间内部的辞旧迎新。赶走侯义伯,新年到来,红色的对联,房子中灯火通明,喜气洋洋,不变的空间中家国情感正在逐步改变。导演很巧妙地运用了房子这一具体的空间结构,来搭建“现代之城”上海之中的家国情感。缝合城市内部空间的房子与家国情感的是中国人对于房子和家的联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房子不仅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是一个家的载体,更是家国情怀的支柱。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到“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再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房子作为一个载体可以满足中国人对于家国的所有想象。而导演也正是从深层的民族心理出发,将战后的家国情感搭建在发展中的城市的内部空间中。
参考文献:
[1]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时间、性别构形[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4]陈婷.跨越时空的想象——以对《乌鸦与麻雀》和《小城之春》的解读为例看四十年代中国大都市与小城镇的影响呈现[J].新闻大学,2012(3).
[5]郑君里.纪录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个侧面——追忆《乌鸦与麻雀》的拍摄[J].电影艺术,1979(03).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