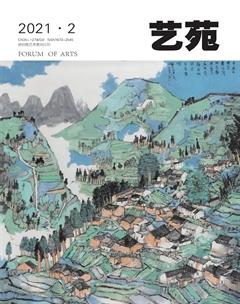再谈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
摘 要: 古剧主要指先秦至两宋时期的各种戏剧形态,以及与戏剧形成、戏曲形成有直接联系的杂戏、乐舞和讲唱艺术。就目前掌握的史料而言,古剧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若能搜集到更多的古剧史料(包括文献史料和文物图像史料),完善古剧研究的具体方法,开拓古剧研究的学术视野,将有可能大幅推动中国早期戏剧史研究的发展,进而全面改写中国古代戏剧史。
关键词:古剧;史料;方法;视野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民族艺术》总编廖明君先生邀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早期戏剧史的学术访谈,这次访谈的内容后来刊登在《民族艺术》2012年3期(第41-44页),题为《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以下简称《访谈》),那是十余年来我研究“古剧”的一个阶段性小结,也包含着自己对未来学术发展的若干设想。在《访谈》中,我阐述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其一,明确提出“古剧”的概念,并大体划定了古剧的研究范围;其二,指出与古剧相关的史料相当丰富,可惜学界对此关注不足,因而探索空间乃相当大;其三,指出史料编年是做好古剧研究的基础,而文献考证则是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其四,指出古剧研究者的视野必须开阔,建议适当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但同时要注意这种方法的利与弊;其五,指出古剧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多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积累的增多,以上观点颇有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的必要,下面拟谈七点,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点,“古剧”的定义应更加简练和周全。《访谈》曾指出:古剧包括了先秦至两宋时期的傩仪傩戏、傀儡戏、参军戏、假面戏、杂剧、院本、百戏、部分乐舞和讲唱艺术;此外,与之密不可分的演员、音乐、剧场、管理、信仰、民俗、历史事件等也应纳入研究范围。[1]41-44虽然,《访谈》将“傩仪傩戏、傀儡戏、参军戏、假面戏、杂剧、院本、百戏”这些重要的戏剧、杂戏都罗列出来了,但明显尚有遗漏。比如“目连戏”,早在北宋时期就能够连演十五天(参见《东京梦华录》卷八),至今在全国多个地方仍有遗存,没有理由不列进去;又如山西上党地区的“队戏”,从上党古赛写卷的记载和当代乐户的表演来看,约在宋金时期已开始发展,堪称中原古戏剧的“活化石”,所以也应列入;另如“皮影戏”,其起始未必能追溯到汉代,但唐代必已有之,两宋时期开始盛行,并流传于全国各地,自然是要列入的。不过,这样一项项列起来,有点过于繁琐,也难免会有遗漏,所以不妨将“古剧”的定义改进如下:“先秦至两宋时期的各种戏剧形态,以及与戏剧形成、戏曲形成有直接联系的杂戏、乐舞和讲唱艺术。”这样一来,既比原定义简练,又不致出现大的遗漏。至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戏剧”这个概念;在中国,它一般是指“演员扮演角色,当众表演情节、显示情境的艺术”(参见《辞海》“戏剧”条);在国外,它一般是指“A模仿B表演一个行动,而C在观看”(参见马文·卡尔森著,赵晓寰译《戏剧》,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这类定义,将“扮演”(或模仿、或表演)“情节”(或情境、或行动)“观众”(包括舞台)等“戏剧”要素都包括进去了,我认为可以直接运用于古剧研究;因此,古剧定义中“各种戏剧形态”的“戏剧”,即以这些“要素”作为判断依据。至于“与戏剧形成、戏曲形成有直接联系的杂戏、乐舞和讲唱艺术”,则包括“优语、马戏、猴戏之类的杂戏,大曲、部伎、舞队之类的乐舞,变文、词文、唱赚、诸宫调之类的讲唱艺术”,很多时候它们未必符合上述的“戏剧”概念,却对戏剧甚至戏曲的出现产生过直接影响,所以均不能摒除出古剧研究范畴之外。此外,尚有“戏弄”一词,虽古已有之,但被用作戏剧史上的学术概念,却始于任半塘先生的《唐戏弄》,书中第一章《总说·正名》指出:“‘戏弄乃由‘百戏和‘戏剧两个部分组成。”这一界定似乎不够准确,因为汉唐时期的百戏(在不同朝代又有“角觝戏”“散乐”等称谓)已包含多种戏剧形态,如《东海黄公》《公莫舞》(近来有人否认这是戏剧)“鱼龙幻化”“参军戏”“唐教坊四大歌舞戏”,等等;因此,不宜将百戏和戏剧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并统属于“戏弄”。所以笔者研究古剧时,不打算继续使用“戏弄”这一概念。
第二点,古剧史料的搜集应更加完备。所谓“古剧史料”,乃指与古剧发展密切相关,并且较具研究价值的历史材料。《访谈》曾指出:“古剧史料有限只是一种假象,我自2003年起有意识地搜集这方面的史料,现在手头上可以较为准确系年或断代的‘文献史料已有1300余条。此外,暂无法断代的文献史料若干条,‘考古和文物方面的史料又有若干条--后二项总数还未作正式统计。”[1]41-44多年过去了,这些数据都在不断地增长。比如,现在搜集到的可以较为准确系年或断代的古剧文献史料(学界通常称为“第一重证据”)已不下3000条(项),增長一倍有余,更加肯定了《访谈》中“古剧研究仍有广阔空间”这一论断。与此同时,作为“第二重证据”的“考古和文物史料”(包括图像史料)的搜集也更加完备,粗略估计算不会少于1800条(项)。值得注意的是,写作《访谈》时,我有点过分强调文献史料的价值和文献考证的重要性,现在却渐渐明白到第二重证据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多数情况下,年代越早文献史料相对越少,考古和文物史料的研究价值相对也越大;如果能和文献参证,作深入解读并提出新见,就更有意义了。在此,可以举山东沂南北寨村将军冢出土“东汉乐舞百戏画像石”及山东安丘县董家庄东汉墓出土“乐舞百戏画像石”为例。前石全长370厘米、纵 60厘米,整个画面主要表现人间宴乐百戏内容,从左至右可细分为四组,其中第三组展现了“鱼龙幻化”的演出场景;后石纵103厘米、上横126厘米、下横204厘米,同样刻画百戏内容,其左下角也有“鱼龙幻化”的演出场景。这种表演,在《汉书·西域传》《西京赋》《平乐观赋》《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谷永疏》等汉代文献中均见记载,但不及沂南画像石和安丘画像石具体直观,画像石还告诉我们文献史料所未记载的重要信息:“鱼龙幻化”运用了幻术、杂伎、舞蹈等手段,由艺人套着鱼状假形及骏马套着龙状假形进行表演,这是一种带有扮演性质的早期戏剧形态(参见拙文《“鱼龙幻化”新考及其戏剧史意义发微》,载《文学遗产》2017年4期,第132-150页)。将这些重要信息和更多的古文献结合起来考察,又会发现“鱼龙幻化”对于中国龙舞渊源的研究,对于古代西域诸国龙神信仰的研究,对于“百戏性质、以物为戏、胡戏入华”等重要戏剧史问题的研究,都有全新的启示和文物参考价值。
第三点,古剧研究的方法应更加多样。《访谈》曾指出:“古剧研究与成熟形态的戏曲研究颇有不同,因为基本没有剧本可据,所以要将眼光放在剧本以外的大量古籍上面。至于第二重、第三重证据也很重要,其如何运用则往往视研究对象而定,而且和研究者的性格喜好似乎也有一定关系,像我这种比较喜欢呆在书斋闭门造车的人,田野调查的方法和证据就使用得比较少。”[1]41-44这段话讲的是如何在古剧研究中运用“三重证据”的问题;很明显,当时我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方法获取的“第三重证据”并不够重视。这不奇怪,作为古典戏曲研究重镇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一向注重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方法是极少采用的(多数人甚至完全不用),我因长期受此学风熏陶,便形成了这种学术取向和固定思维。但随着研究深入,我漸渐明白到田野调查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有些问题是第一重证据和第二重证据难以解决的,兹举山西上党地区迎神赛社过程中演出的“队戏”为例。有关这种中原戏曲的“活化石”,不少文献均有记载,比如20世纪80年代陆续发现了《礼节传簿》《曲目文范》《赛上杂用神前本(甲)》《赛上杂用神前本(乙)》《告白文书本(甲)》《告白文书本(乙)》《告白文书本(丙)》《告白文书本(丁)》《告白文书本(戊)》《赛乐食杂集(甲)》《赛乐食杂集(乙)》《赛场古赞(甲)》《赛场古赞(乙)》《赛场古赞(丙)》《唐乐星行早七晚八图卷》《唐乐星图》等十几种民间抄本(多数抄立于清代,少数抄立于明代和民国,学界统称为“上党古赛写卷”),里面就有不少地方提及队戏。表面上看,凭借这批文献史料已足够学界展开研究,但事实却非如此;因为这批抄本虽保存了大量队戏剧目,却甚少反映队戏的演出细节,根据这些史料并不足以复原队戏的完整面貌。因此,想在队戏问题上有所突破,必须深入上党村落迎神赛社的现场,实地观摹和调查当地乐户的表演。前些年,我撰写《上党古赛写卷新探--队戏考》一文(载《文学遗产》2016年2期,第113-129页)时,提出了“正队戏源出宋代宫廷队舞、流队戏源出宋金城乡舞队”的新观点,就是综合运用第一重证据和第三重证据的结果,这也扭转了我对田野调查方法的偏见。换言之,读书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亦有走出书斋的必要。
第四点,古剧研究者的视野应更加开阔。《访谈》曾指出:“古剧研究确实须要具备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研究者首先要对文学史和戏剧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其次则是对一些近缘学科要有所认识,渐次再将视野扩展到其他的学科上去;……近缘学科中的音乐史、舞蹈史常识我们必须要有,尤其是先秦至两宋时期的‘古乐知识。”[1]41-44尽管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视野”的问题,但对于近缘学科(如音乐史、舞蹈史)的理解是比较偏狭的,仍局限在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上面。近几年,由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广东地区传统舞蹈研究》(2015-2018年,已结项),对岭南传统舞蹈作了一次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田野调查,看到了一批活态的傩仪傩舞、狮子舞、龙舞、凤舞、竹马舞、春牛舞、貔貅舞、鳌鱼舞、火狗舞、蜈蚣舞(甚至有类似于“药发傀儡”的舞蹈伎艺),不少是宋代或宋以前伎艺在广东地区的遗存,由此开阔了我的视野,增进了我对古乐、古舞、古剧的了解,对于“剧出于乐”“剧出于舞”等命题也有了新的认知。可以说,视野的开阔对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能提供帮助。至于“渐次扩展的学科”,我觉得宗教学和民俗学的理论知识尤为重要,特别在研究傩仪傩戏、目连戏、队戏这些“仪式戏剧”的时候。当然,在《访谈》中我还提到,随着视野的开阔,必然要展开“跨学科研究”,但这是一把“双刃剑”,至今仍须谨慎处理这类问题。
第五点,作为古剧研究基础之一的“史料编年工作”应更加审慎和精确。《访谈》曾指出:“我在研究古剧时主要使用了三种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也就是搜集原始史料,并予以系年、断代。……对古剧史料进行搜集和编年,方法和道理与编作家年谱几乎是一样的。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这种方法会比较笨。”[1]41-44时至今日,这种“笨方法”仍在践行之中,而我坚持认为,方法虽笨,却是有效的,只有细致编年,才能够令先秦至两宋的“戏剧史脉络”更清晰、客观地浮现出来。当然,编年工作若有一个环节出了错,整个历史序列就有可能被打乱,所以必须更加审慎和精确,我们可以举“唯以杂剧为正色”的年代考证为例作出说明。在一些宋人书籍中,有“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的记载;由此可见,时至宋代,杂剧已经成为教坊诸种伎艺中的正色,而且是唯一的正色,堪称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却未有人仔细考证过,从而令宋金元杂剧的形成和发展存在着历史缺环。如果考虑到宋教坊“十三部色制”的形成时间,则杂剧成为“正色”必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之后;如果考虑到宋教坊杂剧逐渐摆脱其对宫廷大曲队舞的依附,进而成为独立表演形态的时间,则其成为“正色”的年代上限应在孝宗乾道元年(1165)之后;如果再考虑到南宋教坊罢撤而导致民间艺人对教坊伎艺的“传学”,以及南宋乾、淳以来杂剧演出内容和演出形态的大幅发展,还有《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四朝闻见录》《桯史》《宋史》所载史料和成书时间等情况,大致可将“唯以杂剧为正色”的出现限定在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至理宗绍定元年(1228)这二十余年之内,大概是经过两到三代杂剧艺人的努力而最后完成的(参见拙文《“唯以杂剧为正色”年代考》,载《中华戏曲》第5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70-90页)。尽管“二十余年”看起来有点长,但比起以往学界笼统地说“宋代”,却已精确得多(二十余年还不及两宋时期的十分之一);此外,尚须考虑“唯以杂剧为正色”的特殊性,因为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再者,从“中国戏剧史发展长河”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将二十余年视为一个“时间点”。约而言之,在古剧史料编年工作中需要更审慎的考证,每找到一个类似的重要的“点”,几乎就可以清除早期戏剧史上的一个缺环。
第六点,在编年工作的基础上,可适当开展古剧分期的探讨。先秦至两宋是古剧时代,时间很长,为了便于日后戏剧通史的书写,理应划分时期。我目前的看法是可以分成三个较大的阶段:(一)戏剧史前阶段,(二)仪式戏剧阶段,(三)娱人戏剧阶段;以下解释一下这样划分的原因和依据。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第一章《上古至五代之戏剧》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其中巫又远早于优,换言之,远古巫师的出现乃古代戏剧史的原点,从那时候起到“中国戏剧”的产生,可称之为“戏剧史前阶段”。随着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中发现了“魌”字(参见《卜辞通纂考释》六《征伐》),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中发现了“”字(参见《甲骨文字释林》之《释》);均可印证《周礼·夏官》所载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说明商周时期盛行戴面具而舞的傩仪,实为后世傩戏之前身。此外,苏轼指出“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参见《东坡志林》卷三);王守仁、阮元等指出《大武》一类“颂乐”仿佛元代以来之“戏子”(参见《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研经室集》卷一《释颂》);均说明傩仪傩戏之外,商周时期还存在着“蜡礼、颂乐”等表演形态。它们都含有“戏剧扮演因素”,都与特定的祭祀仪式或巫术仪式结合在一起,不妨统称为“仪式戏剧”。因此,从甲骨文产生的商代后期开始,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可视作古剧发展史上的“仪式戏剧阶段”。到了西汉时期,从“角觝妙戏”(亦即“百戏”“散乐”)中产生了《东海王公》《公莫舞》“鱼龙幻化”“嘉会傀儡”等戏剧形态,它们以“娱人”为主要目的,宗教色彩大大减弱,与各种礼仪的结合也比较散漫,所以和“仪式戏剧”存在较大区别,由此开启了古剧发展史上的“娱人戏剧阶段”,并对六朝时期盛行的“参军戏、优戏”、唐五代時期盛行的“歌舞戏”、辽宋金时期盛行的“杂剧、院本、傀儡戏、影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约而言之,我暂拟将整个古剧发展史分成三个大段:远古至商周为戏剧史前阶段,商周至西汉为仪式戏剧阶段,西汉至宋金为娱人戏剧阶段。
第七点,古剧研究对于重构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意义还须继续强调。《访谈》曾指出:张庚、郭汉城先生的《中国戏曲通史》共1190页,有关古剧者仅75页,这种比例很不合理。针对这一现象,《访谈》提出了新的分配方案:如果一部全新的十卷本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问世,那么“古剧”部分应当占据三至四卷。现在看来,这一分配方案还要修改,即改为:如果一部新的《中国古代戏剧通史》共有十卷,那么“古剧”部分应该占据四卷(案,过往有些戏剧通史、戏曲通史也让古剧占据较大的比例,但能提供的古剧史料甚为有限,均不足以反映古剧的发展面貌)。道理不难解释,因为先秦至两宋时期的戏剧、杂戏等可以统称为“古剧”;而现存最早的汉文剧本《张协状元》大致产生于南宋后期,其后直至清末,续有大量杂剧、南戏、传奇、花部戏曲出现,它们大致就是成熟的“新剧”(亦即王国维先生所讲的“后世戏剧”);在时间上,“新剧”与“古剧”基本相接而有短期重叠,这样就区分出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两个不同的大类。[1]41-44既然只有两个大类,四、六分账就比较平衡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古剧是新剧的源头,古剧时代比新剧时代要长得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也不会比后者少,所以十卷中安排四卷是不过分的。无疑,新的分配方案意味着对古剧地位的重视,对古剧研究意义的强调,并进一步要求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者应该具备“全史观念”,否则《通史》是不可能写好的。
参考文献:
[1]廖明君,黎国韬.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黎国韬博士访谈录[J].民族艺术,2012(3).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