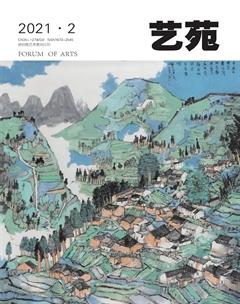论1930年代“联华”电影向农村题材的转向及两种创作类型
蒋佳音
摘 要: 在创作现实题材电影的主流要求下,19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出现了向农村题材转向的创作热潮。孙瑜的《小玩意》和费穆的《香雪海》是“联华”农村题材影片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分别显示出“希望”的农村观与“堕落”的农村观,它们代表着“左翼”电影导演对彼时农村问题的两种分析思路,背后亦对应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小玩意》和《香雪海》尽管各有优点与不足,但都蕴含着“左翼”电影家身处复杂国情中,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积极的挖掘与思考,对电影艺术性与教育性综合把握的追求。
关键词:农村题材电影; 孙瑜;费穆;《小玩意》;《香雪海》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电影界1930年代出现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热潮,是立足于发展现实题材影片的主流要求之上的。此前的早期电影内容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以才子佳人、神怪、武侠等题材为主,电影多为市民观众的消遣,是电影商人牟利的商品。随着新兴知识分子进入电影界,电影同文学、社会与革命理论的联系日益密切,电影被赋予了教化大众的使命。于是电影界产生了现实题材影片的主流创作观,在拍摄过一些优秀的都市现实题材影片后,影界人士,尤以“左翼”电影家为主,意识到电影若要进一步贴近现实,便需要到更“下层” 的农村环境中去创作。其中“联华”影业公司及其导演群更是通过公告、采访和作品等,明确了他们农村电影题材创作的转向,并在这次转向中,基于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分化出了两种创作类型,孙瑜的《小玩意》和费穆的《香雪海》正是这两种创作的代表作品。这两部影片不仅体现了“联华”导演对农村问题成因的不同分析思路,也彰显出彼时左翼阵营里的两种历史观。
一、20世纪30年代“联华”电影农村题材转向潮流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向农村题材转向的大环境。众多电影公司与影界创作者纷纷加入农村题材创作的阵营,如明星、联华、艺华等。其中,创办于1930年的联华影业公司,更是农村题材影片创作阵营中的翘楚。
电影农村题材的转向出现在30年代的隘口实则有其必然性:其一,以世界性的眼光看,30年代初期正是有声电影进行全球性推广的时期。有声电影的产生直接影响了电影所能具备的内涵的升级,电影作为宣传力量的功用被不断发掘与扩大。其二,从民国本土大环境看,外国的侵略、复杂的国情与贫困的环境共同导致社会矛盾问题加剧,城乡矛盾不断凸显,“经济侵略”与“农村破产”等概念逐渐成为社会热议之话题。农村题材创作热在文学创作中率先出现,“到民间去”(1)是20年代新文艺运动的重要口号。很快,文艺界出现了整体性的农村题材的创作转向。其三,1930年前后,影界逐渐吸引了大批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创作重心逐渐从旧文人热衷的婚恋、武侠、神怪等题材脱离出来,向着现实的道路进行深度挖掘。尤其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心,他们开始倡导创作反映现实、能起教化作用的电影。这种创作倾向对于当时社会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因而受到文化界的普遍赞扬,逐渐成为了电影创作的主流。1930年的“国片复兴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率先倡导此运动的影界人士正是“联华”创办人之一的罗明佑。“国片复兴运动”使国内影片公司迅速统一了战线,使国片制作均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此情形之下,以都市为载体的创作空间显然已远不能满足反映现实、教化民众的追求,“到农村去”成为了彼时影界的重要呼声。“联华”导演群便是从都市创作向农村转向的重要参与者。
“联华”的这种转向选择同样有其必然性。不同于“明星”“天一”等老牌影业公司,“联华”公司于1930年才正式创立。不过,由于“联华”是由华北电影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联合组成,它实则是先天优势深厚的“巨型”影业公司。加之“联华”创办的宗旨是“敝公司本革命锐进之精神……敝公司以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为制片之标语……”[1]23,这使它迅速成为现实风格电影创作的集中营。罗明佑发表的《为国片复兴问题敬告同业书》中认为:“我国自制国片……取材简陋……描写人生,未见深刻。迷信荒诞,夹杂其中。”[2]44这暗含着“联华”以映照现实为原则的坚定决心。
“联华”的影片创作,对于题材的扩展尤为重视。这也是为何彼时,“联华”名下能够聚集着一批“复兴国产片”运动中成绩斐然的导演,如蔡楚生、孙瑜、费穆、卜万苍、朱石麟等。很快,在他们都尝试过拍摄都市为背景的影片后,纷纷对都市单一的环境感到不满足,萌发了向乡村题材转型的想法。1933年,《联华画报》公开明确“联华”题材转向的计划:“联华二厂近来倍增努力,早为电影界惊异;兹悉导演孙瑜,蔡楚生诸氏,完成最新作品后,将更改变作风,揭起到农村去的旗帜,创造国产营业的光辉,以应新时代的需要云。”[3]孙瑜以拍摄都市武侠片进入影界,加入“联华”后,拍的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便已有从无望都市向乡村转移的剧情设计;在《野玫瑰》上映之后,孙瑜在《导演<野玫瑰>后》一文中写道:“‘到民间去:在今日的艺术界已经不是几个人的呼声了。在民间,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劳苦、勤俭、朴实的农工……影戏假如能用来描述民间的痛苦,至少可以促进社会的自警,让社会自己想一想,应该如何改善自己。”[4]6费穆则是在完成《人生》之后,决心实地考察农村以便进行创作:“在人生完成之后,他想去北方乡村耽搁一些时候,从事农村的考察。这不是说北方农村破产比南方更厉害一些,而是说北方的农村比较的更原始一些。”[5]不久之后,他拍摄了《香雪海》,彼时《申报·电影专刊》上有评论:“在本片中我们看到了导演手法仍旧和《人生》一贯的进行着。而值得我们一提的:便是费穆从纯粹描写都市生活的影片却很迅速地进展到描写农村生活。本片中没有低级的趣味,只有生动的穿插。没有低级观众所喜欢的庸俗,却很严厉地留意到电影的艺术,致力于技术的精进。”[6]蔡楚生则是在拍摄完《都会的早晨》后,接连拍了《渔光曲》《迷途的羔羊》等农村题材电影,多年后他回忆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在这部相当长的作品(《迷途的羔羊》)中,我把那一个时期的种种感受,都尽可能的写进去了……农村破产,农民备受兵燹天灾的侵害,以致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惨景,就是在听孩子们的陈说中和在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曾深有所感的。”[7]455在这一时期卜万苍的《续故都春梦》《凯歌》和朱石麟的《良宵》等作品,均涉及了表現农村苦难生活的内容。
二、强烈的农村意识:孙瑜和费穆的自编自导
在“联华”里,孙瑜和费穆是拍摄农村题材影片的主要参与者。两人在同一时期,受着同一股潮流影响,均把精力投入到了农村题材的影片创作中。《小玩意》和《香雪海》在创作上也显示出一定的共性。
1932年,有影人指出“联华”导演群创作的一种新现象:“前几年的中国电影界的现象,好像最多是‘导演兼主演,王元龙张慧冲张惠民以至王福忧等都是如此,但是最近这个现象又宣告无形消灭了,继起的却是什么‘导演兼编剧,而且是出之于素称人才拥挤的联华公司中。”[8]1孙瑜自从进入“联华”之后,所拍影片一直坚持自编自导,继《野草闲花》后,《小玩意》是他自编自导的第六部影片,他对于自编自导的操作模式可谓是驾轻就熟,并有了一定的风格凸显。而费穆的《香雪海》却是其自编自导的第一次尝试。尽管《城市之夜》与《人生》都引起了不错的反响,但论及费穆,影评界总是肯定其在电影剪辑、转场技术上的不同凡响,对于内容的涉及,最多也仅是指出导演在字幕上的独到运用。《香雪海》成为费穆选择将镜头展现与内容表达揽于己身的第一部影片,不仅意味着他向农村这个更宽广题材转型的强烈表达欲,而且就电影本身来说,必然拥有更突出的他的个人思想与个人化风格。
孙瑜的《小玩意》与费穆的《香雪海》分别创作于1933年和1934年。《小玩意》描写了一户农村手工业家庭——叶大嫂一家,因农村破产,无奈从乡村投奔城市,又在城市遭遇了更大的苦难。这一故事雏形在彼时社会实则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影片前半部分涉及乡村生活。电影以“晓”字揭开,展现了柳叶映衬下晨光熹微的江南美景,随后以行渔船视角描绘出整个江南乡村之风貌。乡村人物的生活状态显得朴实而淳善,纵然乡村里的生活受时代的影响而处处充满忧虑,但各色人物精神饱满,直到外国工厂流水线生产的玩具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使以手工生产小玩具的叶大嫂一家陷入生存困境。贫穷将叶大嫂丈夫的身体击倒,战争更使叶大嫂无奈带着儿女远离家乡,去繁华的都市求生存——而后证明这种生存的希望也是渺茫近乎于不存在的。《香雪海》的原片今已失传,但因当时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各类本事、剧照与剧评流传甚广。不同于《小玩意》,《香雪海》的故事环境全部发生在农村。阮玲玉饰演的少女因为被舅舅所逼要嫁给一个不喜欢的财主,因而第一次出家,后来还俗嫁给高占非饰演的青年农民,然而好景不长,军阀来临,丈夫只能离开妻儿,投军北伐。不久,母亲去世,儿子染病,于是阮玲玉便只能向神佛祈求,希望儿子能痊愈,丈夫能平安归来,如若达成愿再次落发为尼来还愿。最终儿子被医生所救,丈夫也从战争中平安归来,她不顾丈夫儿子劝阻,再次出家,但一年后又再次回归家庭。
综上可以看出,《小玩意》和《香雪海》不仅创作时间相近,自编自导的创作模式相同,且故事都是以女性角色作为绝对中心而展开,而这一角色都由“联华”当时好评如潮的明星阮玲玉来诠释。但由于孙瑜和费穆的创作思路不同,《小玩意》和《香雪海》最终化出了两种不同的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风格,并折射出两类导演不同的思维路径。
三、“外部”与“内部”:看农村的视角
农村题材对“导演兼编剧”这种模式的创作者有着更具严肃意义的考验。它对电影创作者的要求,不再仅限于故事的吸引人,抑或电影手法的娴熟运用,而是人物命运的构造中必然需要体现创作者对复杂国情的理解方式与分析程度。导演不再只是影片的导演,更是面对大众的观点表达者。农村题材的作品需力争“大众化”,如何向观众合理阐释中国的农村问题,是影片创作的核心与最大的挑战。因此,《小玩意》与《香雪海》都渗透着导演从艺术跨领域到社会学、历史观等方面的个人理解。
尽管影片结局不同,但孙瑜和费穆的共识是彼时中国农村问题重重,且这些问题极易导致农民悲剧。不过,农村问题的来源,孙瑜和费穆却有两种思维路径:孙瑜更偏向从“外部”来看农村,费穆则是从农村“内部”尝试进行分析。
所谓“外部”,体现在孙瑜将《小玩意》中叶大嫂一家的命运进行了一个明显的“由高向低”的处理。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在未被打扰之前,足够自给自足,是外部的世界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平衡,使农民破产。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农村的破产是经济侵略的后果,也是资本压制的后果,显示出农村在不自觉中受着阶级矛盾的深刻影响,进而产生城乡矛盾。这种视角其实相当符合彼时左翼的主流视角,符合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理论。对于农民本身,孙瑜不曾显露责怪态度,认为是环境限制了他们,他们的出身如此,因而是无辜的,他甚至还刻意地去强调农民具备的那种天然的勤劳与智慧。《小玩意》一题就对应着叶大嫂家制作的手工小玩具,这些玩具不仅是全手工制作,还包含着叶大嫂个人的创意。影片展现过这样一幕:一个胖子带着面具逗一群小孩笑,叶大嫂看见了受到启发,立马就做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戴面具的玩偶。此外,《小玩意》的含义还对应着叶大嫂的这份职业,是通过玩具逗乐孩童,给予人欢笑的,本身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时代下的他们又成为了真正的“小玩意”——无足轻重的存在,无论是农村还是都市都未曾找寻到生存的位置。
费穆的“内部”分析思路则是把经济侵略、战火等,仅当作是农村悲剧的催化剂,真正的原因在人,即农民的内部。《香雪海》展现了舅舅代表的强势且凶恶的家长与农民,与阮玲玉扮演的苦情忍受、求神拜佛、不主动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弱势者。农村的悲剧来源于主角身上这种长期懦弱的农村性格,和多数农民思想上的囹圄——依靠求神拜佛,而不是采取实际方式解决。从农民性格的缺陷去分析当时的农村问题,是一个被主流忽略的重要视角,直至影片上映,很多影人,甚至是资深的影评家仍不曾注意性格缺陷的重要性,反而误解了费穆关于“迷信”的处理:“我以为《香雪海》在编剧的方面,意识上已经有了欠缺,为了破除迷信,结果竟会走向提倡迷信之途……”[9]2姚英给费穆写的“信”里说:“我在门口街沿石上,听见了这样一句话:‘菩萨究竟有灵。完了,你的功全弃。”[10]31这些评论家们认为这是一部“反迷信”的影片,因此阮玲玉后来又再次导向迷信无疑是一个败笔。这是多数观众与影评人对费穆的误解。实际上,《香雪海》批判的是中国多数农民根深蒂固的、具有重大缺陷的思维惯性。在所有“联华”前期宣传的小报中,均强调《香雪海》为悲剧,但如果以所谓“导向迷信”的大团圆结局审视,又如何称得上是悲剧呢?《香雪海》真正的悲剧,应是这一家人历经苦难之后,阮玲玉饰演的角色思想从头到尾都未曾改变:看似一些苦难过去了,但若新的苦难到来,她依旧没有任何行动的办法,依旧是要继续去求神拜佛,从心灵安慰上继续祈求幸运的。苦难没有解决,解决苦难的力量也没有找到,这才是《香雪海》被制作者认为是悲剧的真正原因,也是费穆对于农村悲剧的回答:众多性格软弱的农民,不具有坚定的行動力。至于“迷信”,只是表现农村“内部”问题的一个合适的载体。
孙瑜和费穆的这两种思维路径,从更深远的角度看,不仅是对应着彼时“左翼”电影家们对于农村问题的不同思考,更是对应着“左翼”里两种看待历史的眼光。以孙瑜为代表的一派,大多和孙瑜一样有着留洋的经历,或者接受过新式的教育,比较接受阶级论等种种外国理论对中国的分析,用“外部”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在创作上表现出造成农村悲剧乃至中国社会彼时悲剧的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等观点;而如同费穆一般的文艺界人士,从传统家庭和传统教育中走出,对于农村乃至中国人的分析,则更容易从中国社会本身入手分析,认为“病根”存在已久,外来的种种影响不过是加速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爆发。两种迥异历史眼光的选择,遇到了农村题材电影的处理,便分化出了两种农村问题的表达方式。
四、“希望”的农村观与“堕落”的农村观
孙瑜创作的农村影像,显示出一种“桃源农村”的风格。他按照童年里的美好记忆,尽力呈现着对农村的美好想象。《小玩意》中有些过分美好的想象也招致了当时一些影评家的批评:“我们极佩服在他的智力上,同时,我们极惋惜在他的空想上,美化了的桃叶村,美化了的桃叶村的人物是在这半殖民地的中国找不出来的。”[11]乡村风景在孙瑜的镜头里,无疑是活泼而富有生机的,而且这种美好景象,并不随乡村人不如意的经历而变得萧条。《小玩意》是无声影片,孙瑜便充分利用字幕,提示出农村环境的美好:“春天再来,又是一年以后了在那曙光欲晓的一刹那,我们的湖山,依旧是那样的美丽。”活泼影像的风格,还呈现在农村人的群聚状态、人际关系中。对于人的挖掘,孙瑜有着明确的倾向:“我以为描写人后的丑恶,固然很有必要,可是一种高超的理想,亦有他的真价。人生原有光明与黑暗的二面,有丑恶,也有伟大的美。我们不必专事描写丑恶,教人灰心,不相信自己,更应当有伟大的理想,以指导社会。”[12]《小玩意》开场,一个老渔翁热心给叶大嫂一家送鱼,这是家庭之外的和谐人际影像的书写;场景到了集市之后,更是展现出叶大嫂身处周围男性之中备受欢迎的状态,也正是这种人格魅力,才让她吸引了一位来乡村实践的大学生。尽管对大学生这一人物的塑造当时亦有诸多批评,但必须承认叶大嫂魅力的散发,一定离不开其所处乡村热闹人际的烘衬,对青春與性的暗示,亦是孙瑜活泼影像的重要组成。综合来看,孙瑜认为农村本身是充满希望的农村,这种希望却被外来的力量所打断,因而中国人要像叶大嫂在影片最后呼号的那般,将抵制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作为当务之急。
反观《香雪海》,费穆在影片中重复呈现的梅花景象尽管也呈现出“画面的美丽,恬静的调子”[13]774,但显然并不活泼,而是花海之下难掩农村的破败。费穆镜头中的农村是具有“原罪”性的农村。农村里,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家族宗法制下,在家庭里享有压迫性权利的家长,譬如阮玲玉的舅舅,或是宗法乡村里有权利的富户,这类利益的拥有者不断地企图用利益置换更多的利益;更多的一类是阮玲玉代表的这类农民,是家族宗法制下的弱势者,以贫穷的男性农民与女性为主,譬如影片中被战火逼走的高占非和阮玲玉及其母其子。在人物镜头的呈现上,费穆选择俯拍加特写,拍出跪着祈祷的阮玲玉眼神中的悲情与无望[14]2,她所代表的弱势者,被不断地剥夺着权力,且毫无办法,“出家”成为无奈中的必然导向。影片上映时,影评人多称赞阮玲玉的演技精湛:“干那‘早烧香,晚点灯,敲木鱼,念佛经工作时候的凄凉悲切,是做得多么细腻动人。”[15]但未有一人提出,阮玲玉作为主角的种种“行动”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不仅因为“出家”是不合理的出路,还在于一个弱势农女二次出家的经历更证明她在遭遇不幸时,一如既往选择了烧香、敲木鱼——这些与争取更好的生活毫无关系的举动。这里面,农民面对苦难的方式是静止的,这是比压迫本身更令人悲哀、担忧的事实。且直到结尾,农村人依旧没有产生对抗苦难的行动力,逼迫式的家长、宗族依旧存在,弱女幼童依旧无援可依,而阮玲玉的“幸运”是几率渺茫不可复制的。农村的问题出现在农村人内部中,造成悲剧的,不只是因为那些个别的“坏人”,也因为多数软弱的“好人”。这种农村本身就是堕落无望的农村,需要改造的农村。
不过,由于对《香雪海》主题的误解,农村的“原罪性”很大程度上被观众和影评家们所忽视。说明剧本在表现农民软弱性格方面仍处理的不够明确,这与费穆用“倒叙”等设计来尽力追求电影独特艺术风格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与大众对农民性格思考本身便缺乏有关。而《小玩意》一片,在激发大众意识到国情艰难处境方面表现地更为突出,但类似对农民绝对同情的影片多了之后,作为城乡矛盾之“城”的一方,城市观众难免被放在价值取向的对立面,加之故事套路与意义又大多类似,在悲情之外,如何展现影片的其他艺术内涵,也成为此类影片创作的一大难题。但总体上说,“希望”农村与“无望”农村的呈现都渗透着孙瑜和费穆对影像艺术表现力的尽力塑造,使具有说教意义的农村片依然能够具备审美的趣味。
结 语
“联华”是左翼电影家的重要阵地,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电影”创作的高峰期,彼时孙瑜和费穆的创作,都秉持着“左翼”电影理论的要求:“左翼电影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形成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由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三者的结合而构成,具有先进性和包容性,对普通民众有精神感召力。”[16]132《小玩意》中对农村的刻画,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典型创作方式,用阶级分析,对农民破产与被压迫表现同情;《香雪海》更偏重通过农村故事显示出对民族主义的表达,且不是通过单纯的同情去换取观众的爱国热情,而是以批判与悲情的眼光,指出亟待改变的是农民本身,比起前者,无疑费穆的这种方式对人性本身的挖掘更深入,对电影艺术性的塑造更为注重,也更易给予观众心灵震颤。历史学家沟口雄三在分析中国近代时特别提醒:“历史应该从外部来看还是从内部来看。”[17]109在孙瑜和费穆代表的两种模式下,显然《小玩意》这种从外部分析,力求同情农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电影创作在当时所占比重较大。不过,这种模式虽然得到了影评界的大力支持,但重复久了观众难免对农村题材产生审美疲劳,这是导致农村题材最终遇冷的重要原因。(2)回看“左翼”电影的发展历程,农村题材是“左翼”影片的重要组成(3),因此在反思农村题材影片时,需要注意并重审《香雪海》这类从内部分析农村的影片的内涵,将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结合,对于左翼农村题材影片的历史研究乃至当今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释:
(1)“自1910年后期至二十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开始倡导‘到民间去。这一趋势无疑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理论和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参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 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2)“像左翼文学一样,最初左翼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农村题材……这些影片受到左翼影评人好评的同时,卻不同程度地受到都市小市民观众的冷遇。”参见尹鸿、凌燕《百年中国电影史1900-2000》,岳麓书社、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3)“左翼电影的成就主要有三点……二是在电影中讲述农村的故事和苦难的故事……”参见张慧瑜《历史魅影中国电影文化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参考文献:
[1]联华今后制片计划[J].影戏杂志,1931(2).
[2]罗明佑.为国片复兴问题敬告同业书[J].影戏杂志,1930(9).
[3]到农村去[J].联华画报,1933(6).
[4]孙瑜.导演“野玫瑰”后[J].电影艺术(上海1932),1932(1).
[5]沙基.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十七)(续昨)(六)《城市之夜》导演费穆(下)[N].申报·电影专刊,1933-10-28.
[6]费念祖.评《香雪海》[N].申报·电影专刊,1934-10-7.
[7]蔡楚生.从《迷途的羔羊》到共产主义的接班人[M]//蔡楚生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8]维太风.“导演兼主演”与“导演兼编剧”[J].开麦拉,1932(155).
[9]宜.看了香雪海[J].北洋画报,1934(1163).
[10]姚英.《香雪海》观后:给费穆先生的一封信[J].皇后,1934(13).
[11]沈西苓.评《小玩意》[N].申报·电影专刊,1933-10-10.
[12]沙基.中国电影艺人访问记(十三)(续本月十五日)(六)《小玩意》导演孙瑜(上)[N].申报·电影专刊,1933-10-19.
[13]林晋卿.评《香雪海》[J].电声(上海),1934(39).
[14]费穆导演“香雪海”中之阮玲玉[J].影迷周报,1934(2).
[15]深翁.关于《香雪海》的演员[N].申报·电影专刊,1934-10-6.
[16]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17]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上海:三联书店,2011.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