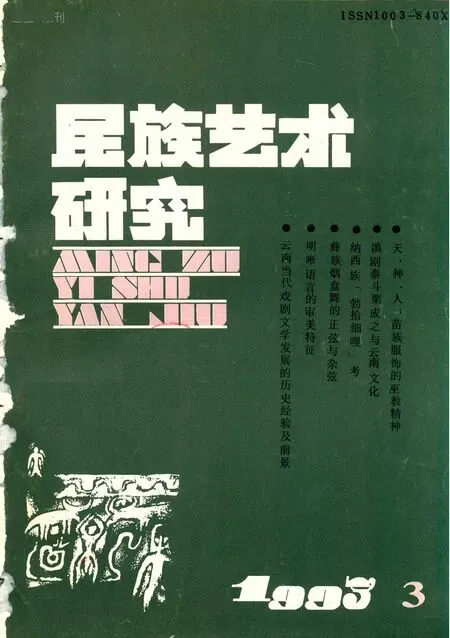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
——田联韬与学生们的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
路菊芳,孙 莉
费孝通先生自1978年始,不少于五次公开阐述“藏彝走廊”概念;并在多次重点强调“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时,提出“板块”型和“走廊”型两种类型;①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6页;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载《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会议论文集》,2003年11月,第3—13页。可知藏彝走廊作为“历史—民族区域”的重要性,以及“走廊”内民族文化交融互生的复杂性。由此,“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也就发挥了联接“北方草原少数民族音乐”“青藏高原音乐”“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梅山信仰仪式音乐文化圈”等“板块”型民族音乐文化区域的通道作用。尤其当下人类学、民族学“路”学研究的兴起,人类学学者赵旭东提出“走廊民族志”,提倡以走廊上人与物作为线索,采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去捕捉与探索其中人与物的流动,而走廊背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各个分支在一条通道上的相互接触、交流、融合、互惠。②赵旭东、李飔飏:《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的世界意识——互惠关系下“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第56页。那么,人与物的流通必然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传播交流,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创立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田联韬先生的开启和引领下,由该院少数民族音乐学科播下的一颗种子,贯通了西南地区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等音乐文化“走廊”“板块”的课题研究。由此,从音乐文化的广泛采集到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化阐释、方法思维解读的多模态研究;从定点个案研究到汇聚为整体的、多点的“通道”研究;廊道交错、圈层互生不仅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色,也铸就了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性格局。
一、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学术研究承传谱系
自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走廊”概念,该区域文化研究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学界少有学者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川滇黔的音乐文化更是如此,直到八九十年代才有一批少数民族论著,但都以汉族学者为主。①杨民康:《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民音乐》2019年第11期,第14—17页。田先生也是汉族身份,却早在1950年随部队进军大西南到重庆之后,就开始接触藏彝走廊一带少数民族音乐。并且先生从1960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到1984年调回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的二十四年间,先后去少数民族地区调研采风20次,考察足迹遍布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如藏族、苗族、傣族、佤族、哈尼族、侗族、布朗族、彝族等,也包括大西北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珞巴族等,所收集和掌握的少数民族资料比图书馆还丰富和全面②郭昕:《走向田野 走向边疆——记民族音乐学家田联韬先生》,《音乐时空》2015年第1期,第1—12页。。说其对走廊音乐文化殚见洽闻,全然不为过。完全可认为在学界尚未提出“藏彝走廊”时,田先生已躬行实践地踏上这条民族走廊,并开始他的考察、收集和创作音乐。
田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育人无数。他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二十多年(1960—1984年)先后培养了约40名作曲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学生为少数民族身份,藏族学生居多。1985年调回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后培养7名硕士生、21名博士生,学生身份有白族、藏族、纳西族、蒙古族、彝族、汉族等12个民族。③杨民康:《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民音乐》2019年第11期,第14—17页。在来自川滇黔的少数民族学生里,就有1986年招收的第一位硕士杨民康(白族)和1996年招收的第一位博士和云峰(桑德诺瓦,纳西族)。
在先生前期考察和研究的开拓、引领下,后辈学者们在同一领域进行了多方位的扩展和延伸。如第二代学人杨民康研究员,承续先生宗教音乐研究特点,除了研究布朗族、傣族南传佛教仪式音乐外,也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且所授第三代学人也多涉及了宗教仪式音乐研究。他所完成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是以云南彝语支民族及苗族宗教仪式音乐为主要对象的学术专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④杨民康:《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和云峰研究员同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则是其博士论文《纳西族音乐史》⑤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正式出版后,被学界评论为国内外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记载、研究纳西族音乐的历史专著。并在研究对象层面将内容进一步深化拓展,分别就当地宗教音乐、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及多民族音乐融合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代学人承续前两代学人研究风格,分别从不同族群(族性)和“民族区域音乐板块”“历史音乐文化走廊”“音乐文化圈”等不同研究视角继续予以拓展。三代学人在田先生引领下,从学术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思维等方面,形成了多点民族志视野下廊道交错、圈层互生的“通道”音乐文化研究。如图1⑥该图以中国经济网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http://www.ce.cn/culture/whcyk/cyzc/201412/30/t20141230_4231851.shtml和“茶马古道”分布图为蓝本,结合本区域学者研究成果,由路菊芳手绘,何兴旺制作完成。粗线实线为藏彝走廊,虚线为茶马古道,虚线圆圈为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即为三代学人在川滇黔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形成的空间布局。其中,“藏彝走廊”几乎覆盖了川滇黔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茶马古道文化从云南普洱向上走,与走廊交错延伸;而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则作为一种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现象,横越了云南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后文将根据上述田先生三代学人研究成果汇聚而成的“通道”脉络进行梳理。

图1 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研究格局
二、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的“多点”比较和“定点”个案研究
(一)田先生对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拓与建构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田先生开始把工作重点放在藏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创作上①田联韬:《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其创作作品《第三女神》(1982年)、《喜马拉雅随想曲》(2000年)等,以及《藏族地区传统乐器考略》(1993年)、《藏族宗教音乐初探》(1996年)等文论都是前期田野考察基础上的成果。先生主编的学术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2001年)里,除系统整理、分析和研究了藏族三大方言区传统音乐外,还初步建构了藏族和彝语支各民族音乐贯通性、联系性研究的格局。在随后发表的《藏族音乐文化与周边民族、周边国家交流、影响》(2002年)、《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2011年)等文论中,谈到跨界民族指“跨境民族”或“跨国民族”,涉及“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②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第55—59页。同时依文化圈的学术原理,提出了藏族文化圈研究的概念。之后,先生在《藏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与音乐色彩区研究》(2014年)③田联韬:《藏族音乐的地域性特征与音乐色彩区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3—15页。一文中进一步明确了藏语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与安多方言,以及9种亚方言的划分概念和标准。又在《藏戏剧种分类研究》(2012年)、《藏族巴塘弦子音乐考察研究》(2012年)、《西藏堆谐在四川康区的传播与演变》(2012年)、《藏戏剧种分类研究》(2012年)、《藏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研究》(2013年)、《藏族热巴音乐考察研究》(2013年)、《藏传佛教寺院的汉传佛教音乐》(2014年)等论文中,具体涉及了隶属四川省藏族康方言区音乐文化的考察研究课题,为本文有关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的研究拓宽了研究思路,开创了学术局面。
在田先生的以上文论中,多次提及康方言区主要包括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那曲地区,以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所属迭部、卓尼、舟曲三县和四川省南部的木里藏族自治县等地,地跨四省区。先生又在对藏族三大方言区的长期广泛考察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藏族民间音乐的三大色彩区:“卫藏色彩区”“康色彩区”“安多色彩区”。由此,完全可认为先生是“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此外,先生也着力培育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人才,为川滇黔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后辈学人对川滇彝、羌语支民族进行的“族性”个案研究
在田先生前期田野考察的开拓及其藏族音乐研究的先导下,后代学人对川滇彝、羌语支民族多从“族性”文化及个案研究视角展开研究。
第二代学人中关于彝语支民族音乐研究成果较丰,贡献较大的是和云峰研究员。其以“局内人”视角对纳西族音乐进行研究,成为藏彝走廊研究格局中的主要拓展者。纳西族是藏彝走廊一古老族群,南诏时期,磨些蛮也分布在四川凉山的安宁河流域,在历史传说、仪式文化上与彝族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其音乐文化兼具土著性、衍生性、融合性三大特征;而从有关纳西族音乐研究资料看,20世纪60年代后,国内外才有对纳西族音乐的专题研究。和云峰研究员克服当时资料奇缺的现状,从第一篇纳西族音乐研究《“古王国”之声——云南纳西族民歌浅谈》(1988年),到硕士学位论文《纳西文化背景中的传统音乐》(1991年)中对纳西族东巴音乐(宗教音乐)、勃拾细哩(民间大型丧葬乐器、歌曲组曲)及洞经音乐(丽江古乐)三大乐种研究,以及《纳西族东巴唱腔的旋律风格及分类》(1993年)、《东巴仪式音乐的若干调查与研究》(1995年)等诸多纳西族个案,汇集一手资料,爬梳文献,最终促成了其博士论文《纳西族音乐史》①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完成和出版。该书从音乐史学的视角透析纳西音乐文化,引经据典,为纳西族音乐文化的史学建构和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后来,和云峰研究员又陆续出版了《丽江古乐——源自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声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云峰纳西学论集》(民族出版社,2009年)、《东巴音乐——唱诵象形文字典籍及其法事仪式的音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多部学术专著,从多个侧面涉及纳西族音乐文化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进一步巩固了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格局。
第二代学人中,杨民康研究员较早对藏缅语族彝语支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其《七十二调与十月太阳历》②杨民康:《七十二调与十月太阳历》,《中国音乐》1987年第2期,第17—18页。(1987年)一文根据云南彝族、傈僳族民间流传的“七十二调”说法,借鉴历史学、民俗学等各方考据资料,通过彝族十月太阳历、彝族“打歌”,以及其他民族中关于七十二成数的传说,探究各民族之间交融发展及其对于音乐文化研究的价值。之后,杨民康研究员《中国民间歌舞音乐》③杨民康:《中国民间歌舞音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第1版,2019年第2版。(1996年)一书,将现代符号学和系统方法相结合,视民间歌舞音乐为一符号化艺术系统,通过音乐形态学、音乐语义学和音乐文化学三个研究步骤,先从宏观视角,由整体性、区域性和地域性风格层次对中国民间歌舞“多元分层、纵横交错”的分布格局进行描述后,再从微观视野对不同地区歌舞音乐的体裁类型、音乐形态特征等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已涉及文化圈、文化层和文化丛的研究理念,并且对中国不同地区歌舞音乐均以乐族相称,如藏族谐舞乐族、彝族打歌乐族的研究等,且每一类乐族都有其历史文化的溯源,以及乐舞形态的延展分析。
踏着前两代学人开创研究之路,第三代学人继续扩展。如巫宇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羌族释比音乐的功能、变迁与保护策略研究——以四川汶川阿尔村为例》(2016年,合作导师杨民康),以羌族释比音乐为研究对象,从定点研究的视野出发,结合长期驻扎村寨,跟踪释比活动访谈实录,分析释比唱腔音乐形态特征,及释比音乐与经文文本、羌人生活、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得出现代释比音乐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最后反思当下“非遗”保护策略等等,具有仪式音乐民族志微观系统描述的特征,成为藏彝走廊研究格局学人中第一篇羌族文论。再如路菊芳博士延续前两代学人彝族研究足迹,继续探索,其博士论文《彝族诺苏人的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建构》(2019年,指导教师杨民康),以凉山彝族音乐为研究范畴,将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作为研究切入点,运用人类学文化认同理论,通过与之并驾齐驱在凉山民间仍然传承的祭祖仪式体系比较分析,探究诺苏人如何通过节庆仪式建构他们当下的音乐文化认同。张晓丹的硕士论文《亲缘与地缘:马边县彝族毕摩仪式音乐研究——以沙玛曲比家的三场仪式为例》(2016年,指导教师杨民康),以凉山区域内马边彝族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借鉴社会学“场域-惯习”理论,解读祭祖仪式和婚礼仪式之间体现的地缘、亲缘关系,阐明不同社会场域中毕摩身份与行为的变化及影响。而解珺然的硕士论文《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彝族阿细人与撒尼人民间舞蹈音乐的比较研究》(2006年,指导教师杨民康)以云南彝族乐舞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研究、文化传播理论以及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口述史资料,对比研究弥勒县“阿细跳月”和石林县“撒尼大三弦舞”乐舞,并通过与前代学人“打歌”研究成果比较,进一步探索乐舞来源和文化成因。同时应用申克音乐分析法与文化本位模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比分析阿细人与撒尼人的不同乐舞形态,成为文章精彩之处。欧阳晶洁硕士论文《魂兮归去——关于普米族“给羊子音乐”的调查研究》(2013年,指导教师和云峰),以云南普米族的传统丧葬仪式音乐为对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民俗描写和音乐分析。高雯硕士论文《拉祜族葫芦笙舞曲的时空场域研究——以澜沧拉祜纳葫芦笙舞曲为例》(2014年,指导教师杨民康)以澜沧拉祜族拉祜纳支系的葫芦笙舞曲为研究对象,从“场域”观念出发,分析芦笙舞存在的载体特征;运用模式和变体的方法探究芦笙舞音乐的变迁,又从文化本位模式法分析葫芦笙音乐同场域之间的关系,进而阐释澜沧拉祜族拉祜纳葫芦笙舞曲在当代跨文化交流语境下的生存现状和变迁特征;该文体现了师门治学严谨、民族志研究步步深入的逻辑思维。
由此,在先生藏族音乐研究的开拓下,综合三代学人不同族群的“多点”研究,构成“藏彝走廊”通道研究的基本格局。
三、多点与古道: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
1980年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西南地区的“区域研究”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产生了一系列“流域”“走廊”“通道”等具有较强区域性研究的专题研究,①田阡:《重观西南:走向以流域为路径的跨学科区域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82—86页。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也由此发展而来。
第二三代学人中较早对茶马古道音乐文化提出研究的是和云峰研究员,其《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2016年)②和云峰:《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5—30页。一文,指出云南茶马古道不仅承载着巴蜀、古滇、夜郎、荆楚、百越、中原等的文化特质,也承载着汉族、藏族、彝族、白族、壮族、苗族、瑶族、傣族、佤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几十个民族文化的交融,同时沉积着傣族贝叶文化、彝族火祭文化、白族本主文化、纳西族东巴文化、藏族雪域文化等多种文化成分,且融合有小乘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多民族原始宗教等。各民族马帮长年累月地奔走在这条风光壮美、道路险恶的古道上,留下了丰富的马帮音乐文化,也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对同根文化的认同。此外,和云峰研究员在其纳西族音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泸沽湖畔云南摩梭人的乐舞》(1997年)、《太阳之子——基诺族的乐舞》(1997年)、《峡谷民族——中国傈僳族的乐舞文化》(1997年)等诸多研究成果,开拓了茶马古道的音乐文化研究。
第三代学人接力前人研究。其中,张璐博士从其硕士论文《云南他留人三种现存音乐文化的调查与研究》(2009年,指导教师和云峰)到博士论文《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文化现状的选点调查与研究》③张璐:《茶马古道云南段音乐文化现状的选点调查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2012年,指导教师和云峰)继续延展,并以多点考察的研究视域出发,将茶马古道云南段马帮音乐文化作为研究重点,研究群体涉及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藏族、彝族,以及摩梭人和他留人等诸多族群;以点带面地论述了此云南段茶马古道路途上的人文习俗、历史传说和音乐文化。此外,滕祯博士和孙聪博士的白族音乐研究是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如滕祯的博士论文《商乐同荣修身齐家——当代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深层结构研究》(2012年,指导教师杨民康),以大理白族洞经音乐为研究对象,从丝竹乐的构成要素、技法、规律等方面入手,采用模式与变体、横组合纵聚合等结构分析方法及理论,对大理洞经音乐深度剖析。但并非仅是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从不同音乐文化层、不同视角比较阐释洞经音乐的来源、音乐存在的原因等诸多音乐表象背后的文化因素。
纳西族、白族等相关族群作为“藏彝走廊”周边古老族群,以及“茶马古道”必经“驿站”,使“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两个通道既有重叠,又有交互补充。从地理学视野分析,两者都属于“通道”研究,只是流通内容、历史文化意义不同。从民族学视角看,“藏彝走廊”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区域,“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①李绍明:《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6页。其中流通的是人、物,以及人携带的政治、文化思想等。而“茶马古道”是民间开辟的商道,是“物”的流通,是经济商业的交融。总之,无论是民族文化特性的“民族走廊”,还是民间商业意义的“古道”,都是一条具有交通意义的“通道”,容纳着人与物的流动,在流动中发生着文化与族群的交流融合②赵旭东、李飔飏:《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的世界意识—互惠关系下“走廊民族志”的新范式》,《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3期,第47—56页。。
四、多点与板块型民族文化区域: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传统仪式音乐文化圈
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板块型民族文化区域研究理论,广义上也涉及了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传统仪式音乐文化圈研究课题。文化圈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田先生《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2011年)一文论述道:“文化圈是指具有相同文化特征、文化要素的地理区域”③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第55页。,同时提出广义藏文化圈指藏传佛教传播所至广大地区,狭义指以中国藏族地区为中心,以及西藏周边国家藏人分布地区的藏文化圈④田联韬:《藏文化圈边缘区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第55—59页。,为后人研究藏音乐文化圈及藏族传统音乐提供理论框架的指引。在第二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中,和云峰研究员的专著《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2013年)⑤和云峰:《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就是田先生所开拓、引领的藏音乐文化圈音乐研究课题在西南藏彝走廊和茶马古道上的拓展和延伸。
第二代学人中较早论述文化圈理论,并展开相关研究的是杨民康研究员,其《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1999年)一文谈道:文化圈是“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区域,是一定数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以程度不等的聚结形式在地球上传播的结果”。⑥杨民康:《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第5页。其实该理念早在作者《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一书中已有体现,只是当时未深入讨论。而他随后所从事的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传统仪式音乐文化研究,却在十余年间渐渐形成了带有文化圈方法论色彩的“多板块”(含南传佛教、瑶传道教和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等传统仪式音乐文化圈)研究布局。在其中的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研究“板块”里,可以归纳出如下几方面特点:首先,从第一篇相关研究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1990年)⑦杨民康:《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音乐文化初探》,《中国音乐学》1990年第4期,第82—88页。到出版专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再到论文《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2011年)⑧杨民康:《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的新变异》,《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5期。此外还有《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赞美诗的五线谱和简谱记谱法研究》,《中国音乐》2006年第1期、《中国古代基督教(景教)音乐传入史纲》,《大音》2009年第1期等多篇基督教音乐文论。,可以看出作者考察足迹涉及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滇东北地区的苗、彝、傈僳等民族,滇西北的滇缅、滇藏边境沿线一带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民族,以及滇缅边境中部德宏州盈江、陇川等县的景颇族与部分傣族,滇缅边境普洱市的澜沧、孟连县、临沧市沧源县等地的拉祜、佤、哈尼等大约25个族群,较全面、充分地展示了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传统仪式音乐的多族群文化形貌。其次,再根据时间脉络观察此六篇文论,其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20年,基本展示了他从“亚文化”“主文化”和“交叉文化”等不同层面对该类音乐文化变迁进行跟踪考察和研究的过程。特别其著作《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2008年),从宏观和微观、大传统和小传统、本土化和现代性等不同关系立场,系统论述了数百年以来西方音乐文化如何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结缘,又是如何变迁发展的轨迹;也说明了本土异质文化因素与外来文化因素相遇,构成了各种地域性风格并存的、共时性和多元化的一维;而“传统性”与“现代性”则体现在历时性和分层化的另一维。①杨民康:《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通过上述研究,使中国学术界对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过多关注“原始”“纯粹”的音乐的思维局限,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于关注受到东西方“大传统”影响而产生种种文化变异的现象。
第三代学人中继续探究这个领域的是张富兰硕士,其毕业论文《茨中天主教音乐调查与研究》(2018年,指导教师和云峰)就是以西藏教区云南总铎区——茨中教堂天主教与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该文应用了音乐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两者之间和谐共融的主要原因。
总之,上述学者的研究将云南不同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仪式音乐个案研究勾连在一起,由点到面,将之结合进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这个历史-民族区域文化板块进行分析和讨论;并以此为基点和平台,通过茶马古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音乐研究,将境内的藏彝走廊音乐文化与境外的东南亚、南亚音乐文化等不同的历史-民族区域文化板块联系起来,以开展更大规模范围的多点音乐民族志比较研究。
五、多点民族志:“板块与走廊”及跨学科研究思维与方法的交织和运用
田先生以一生的藏族音乐研究和广采少数民族音乐,开启藏彝走廊音乐研究格局。在后代学人继续拓展下,提出茶马古道音乐文化研究,并且生成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的研究课题,这一切同跨学科研究思维与方法的交织和运用分不开。
多点民族志是由西方学者乔治·马库斯首先提出(1986年)的研究方法②[美]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满珂译,《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4页。。本文所言“多点”思维包含两个层面:其一,从中观层面看,是由不同学人研究成果汇聚一起形成的“板块”与“通道”研究中,考察对象与研究意图的多点分布。如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文化和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圈的建构,即由不同学人多个民族志考察个案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格局。其二,从微观层面看,是学人个人的课题研究中考察对象与研究意图的多点分布。前文已述田先生的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思维和考察足迹里,早已呈现出多点音乐民族志、音乐文化圈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某些特征。后辈学人中,也不乏去应用多点民族志思维和开展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者。比如第二代学人杨民康研究员由《论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文化圈和文化丛特征》(《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4期)到《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论纲》《西南丝路乐舞中的“印度化”底痕与传播轨迹——兼论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的多篇文章,和云峰研究员《由点到面——云南茶马古道佛教音乐地域流布、选点考察与文化特征》(《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和赵书峰的《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论里,都显现出由以往的定点个案研究向多点比较和跨学科研究思维转型的趋向特征。此外,杨民康研究员《由音乐符号线索追踪到“隐喻—象征”文化阐释——兼论音乐民族志书写中的“共时—历时”视角转换》(《中国音乐》,2017年第4期),到《“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艺术民族志——兼论音乐民族志与相关学科的互文性渗融关系》(《思想战线》,2020年第5期)等文论,以及和云峰研究员的《中华民族多元音乐格局定型与变型的若干历史提要——兼论兄弟民族对中华民族多元音乐格局形成的历史贡献》(《民族艺术研究》,1999年第3期)等则体现了民族音乐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跨学科交流互融的结果。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田先生率领他的几代学生们,共同构建了廊道交错、圈层互生的音乐文化研究实践方略。
六、川滇黔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形态学分析
由于田先生是作曲专业出身,常以一种作曲家的视野看待少数民族音乐,一直比较重视音乐本体分析,冯光钰先生称之为“音乐学研究的作曲家视角”。①冯光钰:《田联韬学术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庆贺田联韬教授80华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7—80页。在田先生八十多岁高龄时,还撰写了《综合运用中西方理论方法分析藏族传统音乐曲式结构》(2017年)一文,充分阐述了先生面对此类问题时的一贯学术主张。当然,先生也并未忽略相关文化背景的考察和研究。如同有学者指出的,他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一书,“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音乐传统、社会生活、创作思维‘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规律”。②冯光钰:《田联韬学术研究的几个关键词——庆贺田联韬教授80华诞》,《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7—80页。第二代学人杨民康研究员承续先生学术研究思想,不仅对音乐形态本体展开立体性研究,而且将此类分析观念扩展到音乐与其存身的仪式,两者同型同构表演过程的整体性探究中。其著作《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及《中国民间歌舞音乐》中有关藏缅语民族仪式音乐和歌舞音乐的分析,就是在系统论和音乐符号学理论视野下,结合方法实践层面的音乐形态分析,也是将理论与实践予以贯通研究的典范。和云峰研究员《纳西族东巴唱腔的旋律风格及分类》(1993年)、《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功用、异变及现状》(1995年)、《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1996年)等论文同样承续了田先生注重音乐分析的学术取向,从音乐本体出发,对纳西族音乐类型、音乐风格系统进行了完整、全面、系统的探究。
第三代学人继往开来,延续传统,不断探索。如滕祯博士以文化本位分析之简化还原法剖析大理洞经音乐,同时应用互文性分析方法解读不同仪式音乐层面之间的关系。路菊芳博士运用申克分析法比较分析现代火把节仪式音乐形态特征,以此论证节庆仪式音乐符号表征与文化认同之间的显、隐关系等。解珺然硕士的论文《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两个彝族支系音乐、舞蹈及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上、下)③解珺然:《阿细跳月与撒尼大三弦舞——两个彝族支系音乐、舞蹈及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上)(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2期,第89—100页。,应用简化还原分析法,结合横组合纵聚合的文化模式分析,对云南彝族两个支系的音乐形态、演奏技巧、舞蹈模式、乐舞语境等展开比较研究,是很有参考意义的音乐形态分析范例。
结语:定点、多点、多模态与“族性”“通道”“板块”的融合
通过上文对田先生引领的三代学人研究成果的爬梳,可以看出在该研究领域里,已初步形成了以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为对象,以“通道”和“板块”研究为方法路径的学术布局。在这个以藏彝走廊音乐文化为主导的研究格局中,围绕音乐本体研究,并逐渐深入音乐表象背后,借鉴多学科思路,探究不同族群音乐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及原因,是现在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也是“多点民族志”视野中“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④王延中:《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社会发展研究》2020年第4期,第47页。一条不同族群历代繁衍迁徙的“通道”就是一部多元混融、一体多元的走廊音乐文化志。回首田先生从最初藏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格局的初步开拓和建构,到现在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通道”研究布局,正是三代学人研究成果由定点到多点,由个案到跨界族群比较,由音乐本体到多模态研究的发展过程。云南周边跨界族群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作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通往周边国家的必经区域,与茶马古道一起,将藏彝走廊与东南亚、南亚周边国家族群文化联接,开启了后辈学人对“通道”上、“通道”联接两端族群音乐文化更大范围的比较研究。
本文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微观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田联韬先生及两代后辈学人为川滇黔藏羌彝走廊音乐文化研究所做的贡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从梳理的情况来看,目前学者们立足于“历史文化走廊”和“民族区域板块”两种角度侧面进行的相关研究,既是以往对个别民族、地域音乐文化进行定点个案研究的顺承和结果,也是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展开跨族群、地域音乐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的开端。在这个新的学术领域和范围内,尚有许多音乐文化交融互生的问题有待探究。我们晚辈学人定会谨记先生的教诲,继承先生的遗志,继续在川滇黔音乐文化研究的途中一路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