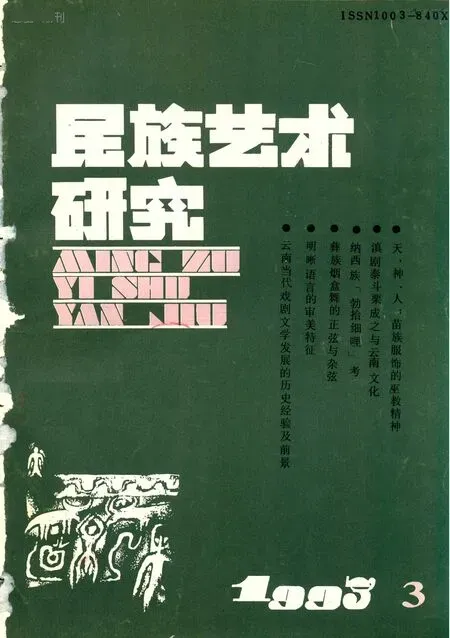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协同效应研究
——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动“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启示
石黎卿,石裕祖
2020年,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各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一一摘帽后,如何防止返贫,是脱贫后时期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1年4月29日),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的经济振兴和传统文化振兴是这个大目标下具有一定难度,同时又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目标。而在资源有限、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如何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通过多年持续考察,发现数百年来在白族聚居地水稻生产中自发结成的“秧賩会”及与之紧密结合的民俗文化活动“田家乐”,在特定的时期有效地推动了白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秧賩会”是经济的范畴,“田家乐”是文化的范畴,两者相互作用实现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机制正是上述协同效应的体现。这对于目前解决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共同振兴的问题有什么启示呢?这正是案例所关注并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白族“秧賩会”与“田家乐”——经济组织与传统文化活动的紧密结合
(一)大理白族“秧賩会”
分析“秧賩会”需要从更一般形式的“賩会”说起。“賩会”或简称“賩”①参见《康熙字典》“賩:[正字通]同‘賨’,[说文]南蛮赋也。[广雅]税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0页。,是云南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在货币、生产资料、劳动力等方面进行互帮互助的一种自发组织,例如纳西族的“化賩”和回族、汉族的“打賩”就是一种货币性的轮转互助储蓄组织,属于“钱賩”的范畴;而“秧賩会”则是白族在水稻栽插时节进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互助的一种组织。
本质上,“秧賩会”是一定数量的村民自发地组成的一个劳动互助组织,在“秧官”统一安排下、抢在有限的时令内依次完成会员的栽秧任务。“秧賩会”在每年大春栽秧时组建,栽秧完成后即解散,如果合作顺利,来年栽秧时节可以原班人马再组“秧賩会”。根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集成》②包括《洱源县卷》《大理市卷》《云龙县卷》《剑川县卷》和《宾川县卷》等。等文献记载,“秧賩会”仅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白族聚居地区出现。具体地点包括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市、洱源县、云龙县、剑川县、宾川县和丽江市玉龙县的部分乡镇。
“秧賩会”运行的基本过程包括:第一,组会。一般延续往年的编制,亦有部分新老劳动力的更替。第二,开秧门。正式开始栽秧之前的一个仪式,主要内容是请出“本主”③“本主”即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一种多神崇拜。起源于原始社会社神的崇拜和农耕祭祀,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先民的一种重要的民俗信仰,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文化内容丰富。白族人认为本主就是村社保护神,掌管本地区、本村寨居民的生死祸福之神,能保国护民,保佑人们平安吉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白族村寨几乎都建有本主庙。或其他神仙,并将该“秧賩会”的标志——“秧旗”插入劳动场地,增强“秧賩会”劳动的仪式感,并调动劳动的积极性。第三,从事集体栽秧劳动。分组进行栽秧,或进行栽秧比赛,其中穿插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和聚餐。第四,关秧门。活动规模较大时,称为“田家乐”,指劳动结束后的多种民俗歌舞、戏剧(白剧、白族花灯)、曲艺、杂耍的庆祝仪式,并解散当年的“秧賩会”。
“秧賩会”中的劳动者进行分工合作。核心人物为“秧官”和“副秧官”。“秧官”相当于总指挥,统筹整个栽秧过程的流程与安排;“副秧官”相当于会计出纳,负责重要事项的记录和资金的进出。其余劳动者大致分为几组:女性劳动者是栽秧的主力军,男性劳动者负责平整田地、挑秧苗等,另有部分成员负责敲锣打鼓、吹唢呐,呐喊助兴,调动气氛并掌握节奏。
(二)伴随“秧賩会”的独特民俗文化活动事项——“田家乐”④“田家乐”的白族语名称为“撒直”,直译即为“解散秧賩会”。本文所述“田家乐”泛指各种规模的解散“秧賩会”的民俗文化活动,而不限于名称为“田家乐”的活动。
在栽秧劳动结束后,“秧賩会”的使命即已完成,此时会员们聚集起来通过民俗文化仪式活动和多种民间文艺表演的形式进行庆祝,并宣布“秧賩会”的解散,属于“秧賩会”的“关秧门”重要环节。不同乡村的庆祝活动在内容、形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但主要目的是相同的——庆祝栽插圆满结束,以进一步增进会员感情。会员们则通过自娱娱人,各显神通,展露个人艺术才华,借此凸显本“賩会”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并彰显本“秧賩会”的经济实力和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积累。
其中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要数大理州洱源县凤羽乡的“田家乐”活动。除了祭祀酬谢“本主”等活动外,还包括“耕、渔、樵、读、士、工、商”等十余种内容形式的戏曲歌舞表演。有的乡村的表演规模略小一些,如大理喜洲镇的表演主要是“耕、渔、樵、读”的情节;剑川县各乡镇只通过“耍牛舞”的表演来体现“耕”的情节。还有些乡村一般都没有文艺表演,只是通过一些简单的仪式完成“关秧门”的任务,并以“打拼伙”聚餐来结束“秧賩会”。
以下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大理州洱源县凤羽乡“田家乐”田野调查个例。主要角色与活动内容包括:
1.秧官和副秧官:由“秧賩会”的两位负责人扮演。秧官:统管栽秧劳动全盘;副秧官:主管经费收支账目、后勤生活。
2.霸王鞭舞队:由30或40多个男女青年组成。霸王鞭舞在唢呐的伴奏声中,围圆循环地跳起20余种舞蹈传统套路,以表现和渲染“田家乐”欢乐、热烈的情绪和气氛。
3.“耕”:在“犁田老汉”教授“来兴”(哑子)和“来妹”(哑女)如何耕作、教猴子种地以及捉懒汉等情节中,表演者以唱、念、做相结合及诙谐的艺术手法,进行夸张表演,引起观众捧腹大笑,放松身心,散发出浓郁淳朴的白族乡土生活气息。使青少年从中学习农业耕作技能、提升道德修养,能够寓教于乐。
4.“渔”:夸张地表演“渔翁”垂钓时的乐趣。
5.“樵”:“樵夫”肩挑柴担,口唱白族山歌,沿街叫卖。
6.“读”:由一位“教书先生”率一群儿童围绕场地四周边走边唱,吟诵《三字经》。
7.“士”:护卫手执“五尺棍”维护场地秩序,差役负责抓“懒汉”“赌徒”和“吸毒人”;间或表演白族传统刀枪棍武术套路;“士”还兼任扛“栽秧旗”的旗手。
8.“工”:肩挑补桶、修甑子和修锅碗瓢盆的工具,在场中四周边唱花灯小调,边吆喝表演。
9.“商”: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口唱山歌、变小魔术、念快板书。
10.还有装扮成“懒汉”“赌徒”“吸毒人”的角色。他们服装褴褛,脸上、手脚上还满画着烂疮。
11.其他文艺表演:杂耍、板凳戏、百鸟朝王(巫舞)、白鹤舞、耍虎、刀枪棍棒等。
洱源县凤羽乡的大型民俗歌舞戏剧仪式活动“田家乐”一直延续至今,其文化影响力远播国内外,历经数百年而不衰。
二、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协同发展的协同效应
(一)“秧賩会”对白族地区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
“秧賩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对相关县、乡镇有“秧賩会”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的统计数据能清晰地看出其差异。为了分析“秧賩会”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各县市内对比研究有“秧賩会”乡镇和无“秧賩会”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项目在研究时考虑了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机械化水稻种植方式生产在2000年前后逐渐进入云南,很多乡镇的“秧賩会”开始逐渐消失,因此选择2000年的数据进行对比;
第二,由于大理市是大理州府所在地,机械化引入时间更早,且受旅游业等因素影响较大,数据统计剔除大理市的情况;
第三,由于县府所在地人均纯收入受影响因素与非县府所在地不同,所以在对比时剔除了县府所在地的数据。
对比结果见下表:

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从数据统计表可以看出:
第一,从单一县市来看,有“秧賩会”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都高于无“秧賩会”的乡镇。洱源、剑川、云龙和宾川四县,有“秧賩会”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高于无“秧賩会”的乡镇分别为3.75%、2.79%、0.88%和6.39%。其中,宾川县和洱源县的两类乡镇差距更为明显,体现了宾川县和洱源县的“秧賩会”和“田家乐”的活动规模更大,活动内容也更完整。
第二,四个县作为总体来看,有“秧賩会”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值高于无“秧賩会”的乡镇。两类乡镇的差距达到3.45%。
上述数据统计结果表明,“秧賩会”在推动白族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确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二)“田家乐”对白族地区乡村文化繁荣的作用
“田家乐”最初的内容形式较为简单,只是对水稻“耕”作劳动的艺术再现和传颂。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容不断扩充,包括了“渔、樵、读”,甚至还融入了“士、工、商”等内容情节;艺术样式上也不断拓展,包括了舞蹈、戏剧(吹吹腔、哑剧、白族花灯、板凳戏)、山歌、小调、曲艺(本子曲、白曲)、魔术、诗文、武术、杂耍、巫舞、刀剑棍武术,插科打诨(大头和尚)等各种艺术门类,真正推动了白族地区乡村文化艺术的繁荣,成为一种在白族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民俗活动。可以说,“田家乐”俨然是一台集白族歌、舞、乐、戏、“百戏”等于一体的白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大展演。为此,因其较高的文化历史和民族传统艺术价值,“田家乐”被入选为《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评价框架,白族“田家乐”的文化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历史价值。据考,白族地区早在约三千年前就已开始从事稻谷生产,①考古发现,大理州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出土的稻、粟、麦等多种碳化谷物遗存证明:早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早期,白族先民已经普遍栽种稻、粟、麦等多种谷物。而“田家乐”的原始雏形大致在春秋战国后形成②参考《云南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洱源县卷》第111—113页。,后经千百年的融汇、借鉴和发展,形成了内容丰富饱满、艺术形式多样、艺术门类众多的大型传统民俗艺术活动。“田家乐”“秧賩会”呈现了早期白族先民水稻农耕经济社会的历史创举。为此,在知名度、参与性和历史传承等方面的民族学、考古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第二,审美价值。“田家乐”之所以有很强的群众娱乐性,正是因为“田家乐”的活动符合白族群众的传统审美观。参与活动的村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编创人员,同时还是表演者,他们均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持有者。这就必然使得“田家乐”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个性,并反映白族地区的特定地域特征。例如“吹吹腔”“霸王鞭舞”“耍牛舞”“耍马舞”“百鸟朝王”“白鹤舞”“老虎舞”“白族调”等这些“田家乐”中不可或缺的歌舞戏曲表演,以及“秧官”“犁田老汉”“来兴”(哑子)和“来妹”(哑女)差役等角色的装束、道具和“秧旗”的形制等等,都是“田家乐”典型的地域特色文化代表符号。
第三,精神价值。“田家乐”在白族地区具有极强的文化认同感。“田家乐”的活动融入了白族地区独特的“本主”信仰,白族人民以此祈求风调雨顺以及好的收成。这种文化认同感使得“田家乐”活动在很多白族地区乡村都有开展,甚至远在湖南的桑植白族也通过向洱海边的白族学习这一民族习俗来实现民族认同。1980年,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插秧节源自云南,纷纷到云南来考察寻根,这也体现了“田家乐”的一种精神价值。
第四,社会价值。“田家乐”中耕田老汉教授来兴和来妹耕种田地的情节,是“田家乐”活动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情节,由于诙谐、夸张的哑剧表演方式,使其成为最受青少年喜欢的表演情节。人们在欢笑声中普及了生产劳动的知识,充分体现了“田家乐”的教育价值。“田家乐”活动中穿插融入各种惩恶扬善的乡规民约,如:惩懒、劝赌、戒毒等。这亦是对村民和青少年实施有效的社会道德教育。正因为“田家乐”在自娱自乐中潜移默化地施行具有传统道德教化、技能传授以及“耕读传家”、劳动光荣、抨懒颂勤、劝赌戒毒、勤俭节约的诸多价值,于是,“田家乐”理所当然地成为白族民俗传统文化中的一笔璀璨耀眼的精神瑰宝。
(三)“秧賩会”及“田家乐”推动白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协同发展的协同效应
一般的民间文化活动,可以通过旅游和文化产业等途径为乡村带来经济收益,形成一个创造经济收益的来源,可以把文化给经济带来的这种影响称为单向效应。然而,植根于农业生产活动的白族“田家乐”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量却不仅仅止于此。
第一,“田家乐”自然诞生于“秧賩会”之中。“秧賩会”把大家聚拢到一起进行劳动生产,使得劳动结束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劳逸结合、自娱自乐一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田家乐”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人员和内容等安排,也都明确地被“秧賩会”所决定。所以“田家乐”这一传统民俗文化活动与“秧賩会”这一经济组织具有天生的内在联系,密不可分。
第二,“田家乐”满足了“秧賩会”功能上的多种需求。“田家乐”自起源于“秧賩会”,本身就具有服务于经济活动的功能,其中包括劳动之余的身心放松、情感交流、劳动技能的教育与传播、亲友关系的融洽、乡规民约的巩固等。一方面,“秧賩会”规模越大,参与人数越多,组织纪律性越强,就会要求“田家乐”提供更多的活动内容和表演形式与之相匹配,进而推动民俗艺术品种、艺术样式的递增与繁荣;另一方面,“田家乐”的服务功能越有效,经济生产活动的需求得到更大的满足,经济活动的收效也越高。
第三,劳动者与文化持有者合为一体,是生产活动和文化活动相结合的天然润滑剂。“秧賩会”和“田家乐”的参与者,在生产时是劳动者,在文化活动时是艺术表演者,实现了劳动者与文化持有者合为一体。而且表演内容就是特定的农耕劳动生产和白族的生活内容,这便使得参与者具备了一种素质:在劳动时具备表演者的生动、诙谐;在表演时具备劳动者对劳动的理解和劳动技能。这使得在生产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时,文化活动的参与性、趣味性和自信心也得到提高,生产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浑然一体。例如,“秧官”对栽秧动作落后者,以幽默和善意的方式进行催促,大家在笑声中放松的同时,又不会有损落后者的脸面。这种能力是从“秧官”同时担任“田家乐”主持和管理栽插中获得的。“田家乐”中老农夫妇教授哑子哑妹的过程诙谐而有趣,教授的内容和技能来源于经济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教育了青少年,有效地提高了“秧賩会”的栽秧劳作效率。
第四,“田家乐”活动富有精神感染力,扩大了劳动和艺术的参与范围。“秧賩会”的栽秧活动只有青壮劳动力参与,但是“田家乐”活动老少均可参与,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民众对劳动的热爱,并实现了对民众精神的代际传播。另外,“田家乐”活动深受群众喜爱,会吸引尚未加入“秧賩会”的村民们参与进来,扩大“秧賩会”的规模和影响,使生产力得到提高。再者,“田家乐”受邀到邻近的村庄进行表演,则增进了乡村间的文化和生产合作,甚至还增进了民族间的和睦与团结。例如丽江九河乡白族村的“秧賩会”和“田家乐”活动就吸引了其他村寨很多纳西族、汉族村民的参与,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
第五,独特的白族人文资源与丰厚的民族地域文化积累,其影响力具有提振旅游经济开发的作用。“田家乐”民俗文化活动通过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多种休闲养生综合资源①如洱源凤羽镇白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徐霞客两度游过的清源洞、“百鸟朝凤”的鸟吊山、白石江瀑布。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三教宫,有鹤林寺、帝释山寺观群、灵鹫寺、积庆寺、玉皇阁、武庙、魁阁,以及镇风塔、镇水塔、镇蝗塔、文笔塔、渚安塔、留佛双塔等圣迹灵地。,以及轻松愉悦的参与性极强的自娱自乐特征,能吸引大批来客参与其中,于此获得身心健康,促进村民与游客互动。同时,“田家乐”活动中的一些文化艺术元素也提供了极丰富的文化产业资源,有利于经济开发。例如秧旗、升斗、荷包、铜铃、凤羽砚和凤凰帽、凤尾鞋等特色手工艺品。这些旅游和文化产业资源都可以直接推动经济的繁荣。
综上可以看到“田家乐”活动在第五个方面发挥了与一般民间文化活动同样的单向效应,有利于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前四个方面看,由于“田家乐”活动与“秧賩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形成类似于螺旋状的相互推动,使得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实现了良好的互相推进的作用。如此,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经济与文化互动双赢,便有效地实现了白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协同发展。这种螺旋式推进给乡村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形象地称为协同效应,以区别于一般民间文化活动带来的单向效应。
三、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共同振兴的思考
(一)“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兴、衰与再复兴
由于协同效应的存在,在以劳动力为主的农耕时代,“秧賩会”与“田家乐”曾经有效地推动了白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协同发展。其繁盛程度之高,一度吸引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丘恒兴(1988年)②丘恒兴:《中日民俗的异同和交流——访钟敬文先生》,《民俗研究》1988年第3期,第18—21页、57页。在对钟敬文先生的访谈中称,日本的“插秧节”与云南的“秧賩会”很相似,甚至有日本学者到云南来为日本的水稻文化寻根。杨国才(2001年)③杨国才:《中国大理白族与日本的农耕稻作祭祀比较》,《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64—71页。进而将大理白族的“秧賩会”和“田家乐”与日本稻作文化中的“花田植”和“田乐”进行了系统地比较研究。
但是随着农耕机械化在白族地区的推进,大大提高了水稻的栽插效率,家家户户可以独立地完成栽秧任务,而不需要乡邻的互助,因此“秧賩会”这一传统的合作劳动方式就失去了优势。从大理坝开始,“秧賩会”这一方式逐渐消失,而与“秧賩会”相生相伴的“田家乐”也一并消失④金少萍:《大理白族稻作祭仪及其变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48—51页。。
出于对传统民俗活动中蕴含的优秀文化艺术形式的保护和传承,“秧賩会”和“田家乐”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⑤以“栽秧会”的名称入选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得到政府的支持,使得其中传统文化的部分得以重现,进而得到“复兴”。程志君(2001年)⑥程志君:《大理周城白族栽秧会风俗变迁浅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第7—11页。对大理周城“秧賩会”的“传统复兴”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进行了分析;高峰(2019年)⑦高峰,刘彦:《散杂居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再造:合群经验的视角》,《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10—17页。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分析了桑植白族通过复兴“秧賩会”进行文化再造的过程。但是所谓“复兴”后的民俗活动虽然保留了原有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原生态的服务于经济生产的功能却已不复存在。曾经具备的协同效应也不复存在,只剩下单向效应。
(二)启示与建议
白族地区“秧賩会”与“田家乐”的兴、衰与复兴的过程,以及协同效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为新时期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传统文化的共同振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传统文化活动有不同的起源,只有源于经济活动的文化活动才会与经济发展产生协同效应。民族文化活动主要有两种起源,一是来自生产生活,例如“田家乐”产生于生产劳作当中;大理“三月街”①大理“三月街”:古称“观音市”,是西南地区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的贸易集市,被誉为“千年赶一街”,亦是大理州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民间文艺体育大交流的盛大节日。1991年起,三月街被确定为大理州各族人民的法定节日。产生于经贸活动当中,可以不断地根据生产生活的特点进行创新,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协同效应;二是来自宗教祭祀等,过去这一类的民俗文化多是由权利阶级用以限制大众的思想行为,这一类的民俗文化虽然也包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资源,但这一类民俗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联系不大,多是独立于经济而存在的。因此,即使通过旅游和文化产业等手段进行开发,充其量就是实现文化对经济的单向效应。
当今在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共同振兴的任务目标下,上述第一类的民族文化活动可以实现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应该作为地方政府重点扶持,进行挖掘、保护、传承和创新的对象。
第二,经济与文化互相推动才能实现协同效应。正如“秧賩会”与“田家乐”的鼎盛时期,以“秧賩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与以“田家乐”为代表的文化艺术活动互相推动,一度在白族乡村实现了协同效应。而一旦两者不再保持同步时,这种协同效应也不复存在。正如“秧賩会”生产方式消失后,“田家乐”这种民俗活动对于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也就消失了。
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却快得惊人。想要实现经济和文化同步互相推动,就需要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施以更为有效的举措,特别是在文化的教育功能、知识传播功能和文化信仰等方面,使得文化服务于经济的功能可以跟得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第三,优秀文化艺术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有生命力的文化艺术才能实现协同效应。从“田家乐”的发展历程来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其表演情节从最初的“耕”开始,到“耕、渔、樵、读”,再到“耕、渔、樵、读、士、工、商”,就是本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坚持不断创新,不断融入外来文化精华的过程。因此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文化持有者自觉参与,不断地吸收、融合、创造的过程。同时,对于外来文化也不是直接拿来主义,而是通过交流互鉴,为我所用。这样的文化艺术才更具有生命力,从而推动协同效应的实现。
因此,扶持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方式,应当包括鼓励文化持有者创新,特别要鼓励与当前劳动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文化创新。政府出资在乡村组织的脱离生产的传统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固然有其传承的价值,但是如果能让传统文化艺术活动融入新的生产劳动方式,文化才会是历久弥新的。
第四,劳动者直接参与文化创新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化艺术对经济的协同效应。前述文化艺术的发展可能会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提出的功能需求,“秧賩会”和“田家乐”的案例显示,要更好地使经济和文化和谐发展,由劳动者,同时也是文化持有者直接参与文化艺术创新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诚然,劳动者直接参与文化创新需要有坚实的群众文化基础和平台,舞台化的阳春白雪固然赏心悦目,但是要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振兴的文化艺术创新,需要发生在生产劳动的场地,形成于片刻的闲暇休息之时,如果劳动者有文化参与和创新的经验,以及坚实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就能更有效地潜移默化推动文化创新。
结 语
“秧賩会”和“田家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效地推动了白族地区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协同发展。回顾并探析这一典型案例,有助于在新时期找到能够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与文化共同振兴的有效路径。
在外来文化袭来之际,如何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民族文化艺术创新,有效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服务于经济发展,实现协同效应,通过透析白族“秧賩会”和“田家乐”的案例获得启示和思考,以期对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和文化共同振兴,实现民族文化繁荣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