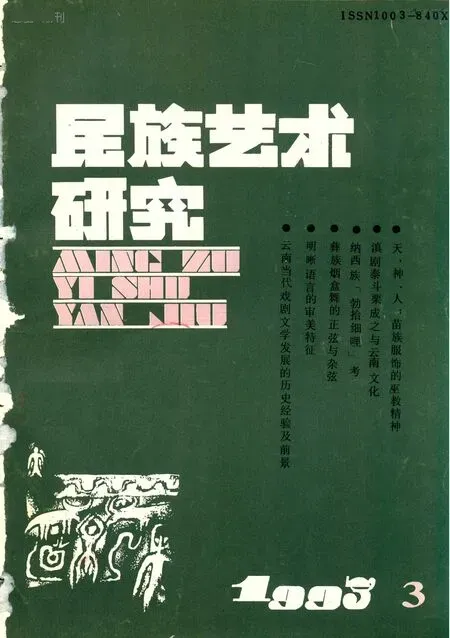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建构
李 杰
科技美术考古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它的独立价值是什么?自概念提出伊始,这些问题即被多方追问。科技美术考古学在一定意义上是艺术考古学发展到深入阶段,对应产生的问题性学科,旨在解决用艺术学和考古学方法难以解决的综合性问题。例如,我们在对历史遗存进行艺术分析的过程中,大多采用人文的艺术学分析方法,从创作理念和美术价值的角度来定性,这种方法显然难以形成准确的物质量化标准以及技法范式规则。而在对人文艺术家的解读过程中,则对遗物的形态结构和材料工艺等分析则较少涉及。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即是在现有美术考古学方法之上的补充,拟解决客观科学与主观创作之间的匹配问题,力求通过物质科学与艺术经验的相互解证,来确定物质内在结构与创作经验之间的历史统一性原则。本学科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具有显性的问题意识和确定目标的理论意义。随着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有关对象、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建构等核心概念,有必要在学术界进行广泛的讨论。草蛇灰线,以图专家伏脉。
一、概念的提出及定义
为什么要将“技术”提升到学科理论的层次?几十年来,考古技术的引进、发展,弥补了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方法论上的不足;然而,“技术”的突飞拓展,也与艺术考古学理论相对滞后形成了较大的反差。对科技美术考古学而言,理论与技术是一个整体概念,而技术与方法是理论的展现手段,没有理论支持的技术往往不能达到原来预想的目标,所以,理论的滞后必然会阻碍“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系统提升,而技术的发展也无法得其精义,只有理论与技术的偕同才会给这一学科带来健康发展的契机。
同时,从更大的范围来看,理论方法是否具有独立性是中国艺术考古所面临的必解问题。中国艺术考古学由于被强大的传统史学所统照,成为一门具有显性民族性的学科,强调补史证经的功能,导致在研究的构成中极易出现先设问题条件,使得研究伊始就预设了结论,造成以历史问题为导向的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界备受责议。科技美术考古学即是力图从物质量化条件和技术要求出发,增加问题条件的准确性和针对性,协调完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系统。
当代史学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多种历史价值观以多样性和模糊性的光谱式形态存在,多层次的史学意识并立,表达方式的矛盾相互交织并存。这种状态与18世纪的意识形态大交战不同,18世纪的交锋是新旧思想的对立,其核心是以理性自然出发的启蒙思想与神学的针对性交战,①韩子勇:《“意识形态”概念流变考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第4—10页。问题与异质显而易见,而当代史学的认识观交织混杂,极具模糊性质,这一现象不但影响着传统史学的发展,更具有交叉性质的艺术考古学的目标凝聚和问题阐释造成了更大的困惑。现代学科的细化既有其更加专业化的趋向,同时也造成了对问题的孤立表达,学科越成熟就越会排斥其他理论的介入,在诠释问题的时候往往缺乏宏观性的解释力。当代理论是一种综合性的原则研究,学科交叉是目前理论界的前沿研究方法,在艺术起源的研究中,有关人的生理、物理和心理的反应机制,是目前相对前沿的研究。因此,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介入了自然学科的理论,来说明人文研究难以被显性证明的不足。这种交叉研究在理论界褒贬不一,但随着相关研究的开展,逐渐看到在将自然学科的研究置入对“艺术发生”的解释中,未必会造成其偏离人文阐释的精神特质,相反,两者的交叉化用,大大拓展人文阐释的广度和深度。②刘梁剑:《数学人文:科学抑或人文学——南帆、曾军教授相关讨论引义》,《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8期,第84—89、158页。
基于探讨风格定义和延承关系量化等问题的解决途径,笔者提出了“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学科概念,得到学界诸多学者的鼓励,并尝试搭建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体系。③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项目:“科技美术考古学人才培养”,(项目编号:2019-A-04[072]-0614)。科技美术考古学属于交叉学科,是艺术考古学发展到深入研究阶段产生的跨学科研究系统。在学科归属上存在一定争议,就其研究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个向度,一个是趋向艺术学的风格定义向度,一个是反映时间和空间的考古学物质定义,此外,自然学科的介入更促进了各自观点的确认性。
科技美术考古学是以技术美学(Beauty of Technology)为统领,旨在解决艺术感性量化标准的一门跨学科专业研究科学,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来研究艺术呈现的量化分析和历史艺术实证逻辑的规律。与以自然学科支撑的科技考古学不同,其主体研究方法还是属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其中只是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数学模式和材料分析方法,其对意向性的生成分析是主体性视角下对实在性理论的阐释。同时,科技考古学基础方法论的还原也不构成对其他理论相互兼容的障碍,无论从有效意义出发还是基于量化理解的角度,其与科技考古学以及艺术考古学的根本差别也只在于方法论视角的限制和相互补充,而非立场的相互冲突。
科技美术考古学具有明确的跨学科属性,其理论方法兼有文理性质。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确立首先需要解决学科兼容的关系以及学科统一性和原则划分等问题,并在相同与异质研究属性之间形成紧密的内在结构,从而成为一种具有特殊领域、特殊理论、特殊方法和特殊技术的独立研究系统。因此,确立科技美术考古学,在学术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系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质的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
科技美术考古学学科的生成,主要是基于解决艺术考古学中的一些尚未明确的问题而设立,即如,物质本身对艺术创作的反射,技术手段与创作理念的通融等。在其理论建构期间质疑声音不断,主要的分歧是,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出发点是解决艺术物质的具体问题,是否有建立独立理论体系的必要?
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主要是通过量化和质性的手段进行“假设检验”。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本学科而言,理论应基于学术层次进行讨论的内容,与具体的实际问题无关。然而,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理论指导的“假设检验”往往会导致定性模型的偏差;忽视量化标准中的干预变量,很难在整体研究中把握好物质与背景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当物质序列和历史文本出现局部断裂的时候,问题检验就更需要理论的宏观支撑来完成因果结论的判断。理论是提出问题假设的前提,没有理论构架的支持,科技美术考古学中复杂的交叉研究很难避免导向的错误和检验方法的适配偏差,特别是很难进行概念的界定和清晰地描绘路线。
在理论中,首先是由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组成,两者在存在状态上存在明晰的区别和矛盾。但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两者更多的是相互关联和内在的统一,并具有互相解释和证伪的功能,其根源即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表现出来的“内在本性”①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的价值。因此,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理论是一种可以被证伪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般性的解释(generalexplanations)方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传统物质与意识的二分法已显简陋,特别是传统考古学下的物质观需要进一步深化。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相对次要的条件或可打破理论的框架结构,但只要这一理论能够对大多数问题作出阐释,就是相对完整和可以使用的理论,并不会因少数反证而失去其价值和意义。
同样在科技美术考古学中设定的物质排列和延承规律的序列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孤证打破这些理论构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科技美术考古学的方法存在不可弥补的漏洞,恰恰是随着考古发现而不断出现的特例资料的补充和方法的创新,推动了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
二、理论的确定性原则:基本逻辑观的生成进路
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从宏观上确定其基本逻辑观,也就是建立哲学认识上的认知路径。简单来说,逻辑是对一个问题的推理和论证的学问,这是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所具备的以特定思维方式支配自身发展的动力,不同思维逻辑会对社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指向。也就是说,逻辑思维方式的转变对人的社会存在方式之间具有显著的因果关联,③宁丽娜:《论中国近代逻辑观的生成进路及其文化价值》,《哲学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14—122页。虽然逻辑思维活动注重问题推导和论证的有效性价值,同时,逻辑思维的规范性、逻辑基本要素的条件清晰性、推理数据的可印证性以及论证过程的有效性,促使思维方式向着理性主体方向展开,这使得社会的有效进展必然会借助强逻辑的科学性来建构主流文化的价值走向。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建构需要了解历史社会的逻辑思维观念,以宏观透视问题为基准。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逻辑观念与现代思维概念并非具有一致性,不同时期的思维认识也不是一个线性成长的过程,其与社会主导意识的需求有关。当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史实,我们必然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认识观来协判“历史”,需要立足历史整体发展的唯物主义立场来形成现代宏观判断。因此,站在现代史学角度,不是任何已发生的史实都有资格成为“历史”,历史只会关注对于当下最具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科技美术考古学强调以史为鉴,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瞩目今天。
我们知道,理论逻辑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感官形成的知觉逻辑推理,另一种是“对实在的认识,是关于某种存在物的认知规律。”④童强:《理论与艺术理论》,《艺术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36—44页。第一种的单纯性思辨形式是西方前哲学的主导模式,这是我们传统中很少接触的观念,即如李泽厚在《存在论纲要》首语所说的,本无形而上学存在论传统的中国“哲学”。①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前言(下篇:存在论纲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关于形而上学的认识,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脱离实在的假象,对现实并无实际指导价值,这是一个站在东方认识观下的假想认识。其实,形而上学的理论推理本身具有显性的价值意义,②西方哲学是从数学最深的内核中产生出来的。[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虽然其是在假想中进行的逻辑推论,但是这种理论也是基于人的基本经验的综合表现,即如,几何学中的各条边线,本身不是现实物质,只是假设之上的抽象存在,这种假想中抽象化的推导过程即是形而上学理论的集中体现。③[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页。其只是呈现出一种关系性,但并不妨碍对现实存在的指导价值以及对实在物质的理解。
在对历史物质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会忽视宏观认识的重要性。科技美术考古学的设立,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历史物质的整体认识观的问题。形而上学虽然不去对应现实物质,但其严密的推导具有显性的普适性。由于抽象的存在,它所能涵盖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对现实物质整体分析显然非常重要,“最高的抽象思维是控制我们对具体事物的思想的真正武器。”④[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因此,基于问题研究的科技美术考古学更需要针对物质对象的宏观认识来进行分析,并对物质特征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指导性。
科技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具体的历史物质,虽然抽象的逻辑对事物的总体认识具有普遍价值,但具体物质之间的互动原理则还需要面对具体现实,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从具体物质或现象的对应分析中发现规律和事实逻辑。墨家是中国逻辑学说的代表,在推理中展开说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梁启超指出,墨家论理的“思维作用”有三个特征:一曰概念,二曰判断,三曰推论。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墨子学案(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3页。与西学不同,这是一种基于物理判断的哲学。此外,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即是一个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理论概念,但是,宋代以后,中国哲学观念转向心性感悟,从而将格物与致知的顺序进行了倒转,用物理来印证心性顿悟的道德经义,致使中国将经验知识与哲学体念分开,形成道和技的两条道路,使得较为成熟的传统技术经验无法上升到理论形态,很难将物理知识转换成体系化的系统构成,经验知识很难规模发展。
虽然历史物质具有明确的不可更改的实在性,但其所反映出的艺术特质则不能完全被绝对化。这些承载艺术信息的历史物质既包含自然科学所反映的确定性因素,同时也包括感性的、无意识的、创造性的多种复杂因素,即便是从宏观上来看,我们也很难用一套理论来对其进行总结。因此,当我们面对信息交杂的考古物质,并对其进行体系化建构时,既需要把握好整体的宏观影响决定性,同时又需要保持物质的客观性和事实的证实性因素。显然,这种理论需求在基于中国特性物质基础的同时还需借助形而上宏观理论的统合。简单来说,李泽厚的生产实践与历史理性互证,以“经验变先验结合”“历史建构理性”来阐释历史艺术物质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溢出哲学”⑥刘悦笛:《研究中国哲学,李泽厚始终走着“自己的路”》,《北京晚报》2020年10月2日。之外的中国式理路,这对中国科技考古学的物质本质理论探讨具有指导意义。就艺术物质本质而言,事物的构成原理存在于物质本身,只有通过体系化的分析才能被认知。特别是面对有诸多时间性的历史事实的时候,简单的物质对应是不够的,需要将这些具有共存意义的物质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宏观的物质体系,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具体艺术物质的时代特性。
在社会活动中,逻辑的理念往往会作用于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则会对当时的文化形态形成影响并以物质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观构成,就宏观发展的角度而言,既要有中国传统格物致知的技术路径分析,同时也要从逻辑概念的高度对艺术考古物质进行空间把握,从史实出发,将实证与推导相结合,寻求发现“事实逻辑”的体系化构成。此即科技美术考古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本立场。
三、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知
社会科学领域的母题与主题都是具体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反射,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集体意志的体现。这种意识本身是一种单一的认识观念,是将复杂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图集合产生的主导意识。从其本身的形态而言,它是假想出的现实存在条件,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规范框架。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它也是统治阶层的广泛规范意识,并构成指导社会发展的抽象含义系统,进而形成一个国家的思想体系。
能够成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它必须具有形象的母题价值;其次,还需具有明确的主题意义。也就是说,它要具有体现艺术价值的基本条件。此外,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中心时间范围遵循中国考古学的基本限度,从远古时代经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后期。这一时段的艺术创作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人类早期受到创作条件和技术手段的初始限制,各区域基本形成较为统一的整体延展轨迹。而在先秦至隋唐阶段,由于贵族社会的影响和政治的限制,作为主流思想的表达形式,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较为统一的进展轨迹。因此,中国科技美术考古学作为中国美术考古学的主要分支,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一区间具有母题价值和意义主导的物质遗存作品。
就物质形式分类角度而言,研究对象主要分为:石器时代的石作、泥作、壁画、岩画等作品;青铜时代的石作和泥作雕塑、铜器、玉器的表面纹饰等;秦汉时代的建筑、构件遗存、城址遗迹、墓室壁画、画像石等;魏晋至隋唐的墓室壁画、石刻线画、墓葬构成和洞窟壁画等。这些艺术作品均具有共性母题和主题,其中出现的孤立母题,由于无法对应于沿承规律,所以对系统研究而言并无意义和价值。
历史规律具有一定的整体逻辑性,而考古艺术物质本身总是呈现为片段性。“对待长时段的历史也必须有规律地把握。假如没有对历史内在联系和规律的探讨,仅限于玩弄历史的碎片,永远达不到对历史真实的深刻理解。”①丰子义:《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哲学研究》2019年第11期,第3—12、126页。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对历史的阐释,必须正确认识到历史规律和考古物质之间的关系,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时——一方面,不能简单地套用基本规律来否定物质的特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杂乱无章的历史物质来限制历史规律的历史宏观性。面对纷繁复杂的考古艺术作品,从什么角度来统合两者的关系,是科技美术考古学开展研究的路径核心问题。
科技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即是要对符合时代限制的考古艺术物质作出阐释。因此,要对这些“作品”的历时阶段承载意义作出解释,才能对阐释主体的时代特征进行合理的定位。基于这一目标,我们要确立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方式,首先须分清楚对于历史的认知主体具有共时的社会性,而不是现在的历时性结果,才能较为准确地定性“时代的产物”。②[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3页。因此,对时代典型母题的阐释是了解艺术考古物质时期特点的基本要素。
各时期的“母题”都具有普适化典型性特征。母题是特定时期有社会或政治所限定的典型形象。它既是一种形象,同时是一种社会视角。汉画石像中的人物是典型的母题形象。例如,“孔子见老子”主题表现中的孔子等人物,“二桃杀三士”主题绘画中的齐景公、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的人物形象,既是具有明确主题的典型母题形象,同时,这些母题出现在广阔区域的主题绘画中,具有横向的普遍共时性。因此,母题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具有普识性认识的特征,同时,在这一段时间或延续时期中具有普遍传播的历程,并对应考古物质的形式规律,使内在背景与外在形式保持统一,拓展物质对象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它应该也是社会表达主题或主题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的母题才能嵌入历时性的传承过程中,才具有系统研究的价值。①赫云、李倍雷:《母题与主题在艺术学的史与论中的定位》,《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4期,第5—13页。
四、考古物质与历史价值相统一
对于科技美术考古学而言,考古物质与其历史价值是两个层面上的具有异质性的基本维度,各自的内在原理和表现特征,处在不同的认识层面。建构这两个维度的统一相适的理论结构,是科技美术考古学的路径方向。
考古物质是历史环境下的人所创造的基于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时代产物,具有显性的“实在”性。从认知角度来看,能够反映事物的知识性基础本质,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客观性的“实然状态”。②孙伟平:《彰显价值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向》,《哲学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3—22、124页。历史价值维度是经过哲学反思后对历史整体进行定性的结论,是人与社会的超现实“应然状态”。
科技美术考古学是问题性研究学科。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必然需要以实证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然而,问题式研究的缺陷是单一研究较为清晰,但将这些问题放置在统一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中,则会显得比较凌乱,很难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规律。特别是在传统考古学研究领域,多以旧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强化物质的存在特性,但却不能全面地反映“人”的社会主体意识的能动性,甚至在分析的路径中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分离并置,造成事实与价值的分裂。这一现象主要是由考古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考古学主要方法运用的出发点即是从事实物质的角度获得客观科学化阐释,使得一些关于历史价值的宏观认知,也遵循“科学化”的路径,导致属于哲学维度的价值认识缺少系统性的质性研究,“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其常常将价值理念当作事实问题来处理,从而造成了不少理论和实践的混乱。“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因此,科技美术考古学在开展研究的同时,需要从价值角度对实证研究进行分类和控制,对问题的阐释进行宏观的指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面对众多历史遗产的时候,在对纷杂的艺术物质进行分析的时候,会以历史价值为主体进行问题定性,指导问题研究形成规律特性。
那么,从理论角度,我们应该怎样形成考古物质与历史值统一的认识观?物质与意识的二分法已很难对考古艺术物质的理论呈现作出完美答案,对传统考古物质观必须进一步进行结构的深化。马克思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较为合理的思路。马克思解释“实践”是基于人的感性表达的实践活动,突出人的内在主体性的抒发表达,从人的社会主体性方面来系统理解问题,以“人的内在尺度”对“对象的外在尺度”进行有限的平衡。从事实维度总结考古艺术物质对象的本质和总体规律,以辩证的否定理论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使历史价值的转向与考古物质的变化形成自觉契合。
五、方法论认识观
就解释方式而言,艺术考古学主要是使艺术物质、历史文化和表达文本有机关联,并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联系方法。考古艺术物质的存在价值主要取决于是何种认识观解释辅证其作用价值。也就是说,在某一种研究方法学说中,某一类考古物质如果可以附和证实这一方法的正确性,这类考古物质就是高价值材料,反之则是低价值材料或无价值材料。
随着中国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面对中国考古物质的研究必须完成具有中国意义方法论的建构,艺术考古学需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方法体系。中国艺术考古学从提出伊始,就已经形成了几套主流方法论系统。古典艺术考古学主要是利用考古物质的表现特征,来证实艺术史或历史学的观点,以二者的相互印证来解释文本历史现象,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文本提供一个物质文化语境。①何彦霄:《考古的文本转向与文本的物质转向——从古典考古学看“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读书》2020年第10期,第80—88页。随着考古研究范围的扩展,特别是史前文明在考古发现中的分量持续加重,这种附和文献的研究就显得难以适应物质的发展分析进程。以密歇根大学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逐渐引进至对史前考古研究当中,特别是有关社会进化论学说的确立,首次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化模式,这对我国的早期文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后,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及考古发现的区域关联,研究者认为早期的社会转折,并非呈现线性进化的状态取向,形成了淡化社会进化中相互推进的跳跃发展学说。近30年,中国考古学已基本摆脱了了简单的类型学和层位学为核心的研究方法,多学科介入促成了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快速成熟,同时也带动中国艺术考古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前沿理论的立体化分布。
考古物质本身都具有各自的独立性质,将它们组成一个系统就需要将单元以线性的方式链接成为一个整体。然而,个体单元物质的性质和形态必然不具有同一性,所形成的连接也会是非线性的呈现。我们知道,考古物质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不规律性,因此,在系统中选取单元物质的典型性就成为必要条件。
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与传统的单一样品论证方法不同,为了使系统具有较高的问题指向,在采集物质样品的时候,通过有序分布时间间隔秩序和连续时间的“长时段”构成,将其构成系列性线性分布,并通过特征元素归类和曲线校正进行数据上的拟合,再以独立物质数据之间的相互性进行线性匹配规划,最终获得误差较小的系统秩序性和正向性线性典型规律。
在观念哲学中,将思维的过程和动力看作是人的主观意念的创造,是纯粹理性推导所形成的逻辑形式。然而,人的成长是社会的产物,从现实角度来看,思维逻辑是依托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现象的交互,才能形成具有系统性的思维方式,②高来源:《实践视域下的指号、意义与思维——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参照对元实践哲学问题的探究》,《哲学研究》2020年第8期,第117—126、129页。因此,历史逻辑思维是历史物质与史学观念的综合表现,并成为理论的整体性。科技美术考古学是探讨传统人文科学与实践性交叉的可能性学科,它建构实践性思维模式,在历史实践维度下,通过回观历史境遇下的人与社会、物质的现实交互来理解考古艺术物质的本身意义和延承动力所在。
六、科技美术考古学的运用案例
人类的早期阶段,物质技术的发展往往指引着社会形态的走向。顾颉刚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就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大路。③顾颉刚:《古史辩·自序(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自然科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量化标准的设立上,其作用主要体现在集合的作用和分化的系统性。例如,考古学自“区系类型”量化模式提出后,证明中国史前文化是“重瓣花朵”结构,④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38—50页。“中原中心”定式对黄河流域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的过分强调已经被扭转。⑤李伟新:《“最初的中国”之考古学认定》,《考古》2016年第3期,第86—92页。同时,通过量化分析和关系对比,又发现了各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①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写组《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特别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支撑方法——标型学、类型学、层位学等,均是以量化对比为核心的。
早期文明研究受限于文本的缺失,必须紧紧围绕考古物质的发现而展开,因此,考古学往往以技术的转折代表社会的转折和进步。在考古学中,年代的确定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秦汉之后主要依靠文献和考古纪年来确认时期,史前考古限于文本的缺陷,因此只能依靠物质本身的技术信息来测定年代,其中较为成熟的方法非14C测定法莫属。仇士华领衔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年项目组,以碳十四分析法配合“系列样品”的连续测定法,对早期夏文化、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文化分期、丰镐遗址、西周燕都遗址、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等进行了年代测定,并在20世纪末期建立了世界先进水平的碳十四测年AMS加速器质谱制样系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配合中新石器时期年代序列的细化研究,在骨样品碳十三(δ13C)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元素分析法建立了蛋白类食物氮十五(δ15N)分析方法,完善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法。近年来更有食性分析、DNA分析、环境分析等手段,从多角度丰富了史前物质测年方法。
对史前艺术考古物质的精确断代,是科技美术考古学研究中确定艺术发展延承轨迹的基础数据,是美术物质风格定性的前提。测年方法的成熟创造了艺术考古学进行艺术发展延承规律的基础条件,是考古美术物质系列样品分布秩序的排列依据。而考古学中的标型学亦是建立艺术谱系的基础。这些方法虽然准确,但对科技美术考古学中的文化分区和艺术属性的确定,仍需借助人文质性分析的统合和升华。
测年对史前艺术的发展具有明确的作用,但并非所有史前研究都以传统科学的方法为基础。新兴的自然科学的介入对史前文明的研究起到了突围的作用,特别是对艺术的起源问题,除了量化分析之外还需借助多科学的前沿方法来交叉论证。
有关艺术的发生研究从古希腊延续至今,一直存在多种观点的交锋,各种学说因时代的发展而补充其支持条件,至今并未在理论上形成主导学说。近年来,科技美术考古学引入生物学、脑科学、心理学等的前沿研究方法,对解决艺术发生的动源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案。
艺术的发生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学术界。20世纪末,传统的模仿说、游戏说、表现说、巫术说和劳动说基于心理学的主导介入以及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打破了从哲学角度分析艺术起源的思维惯性,但通过深入研究,仍发现心理本质论②张帆:《信念——认知的本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62—66页。也未能从本体角度解释艺术发生的动力来源。近几年,文理交叉研究的新方法给这一命题带来了新的研究途径,采用生物学和脑科学等的前沿研究中的反射发生理论基本证明了艺术发生的动能,主要是由于原始人的左右半脑尚未达到分工协作,主观意识较弱,行为活动主要依靠本能反射的冲动完成。③Olumide A.Olulade el al.,“The neural basis of languagedevelopment:Changes in lateralization over age,”?PNAS(2020).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905590117而进化到约公元前2万至前1万年左右,脑区神经逐渐区分了左右半脑的分工合作机制,人的主观意识增强。因此,这种本能冲动的图绘创造与主观意识的几何创作之间的反差,证明了艺术发生的动源出自物理反应下的被动反射。
史前美术考古从单一物质发展到确定的模型,并随着艺术物质发现的增加再次走向不确定性,显示出日渐复杂的多层结构。这种复杂的认知群必须依靠自然科学的明确定性来串联,科技美术考古学的价值即是通过量化标准将艺术问题的结构和历史的延承结构对等起来。
艺术本身所负载的情感、质性、感知和深意有显化的感性特征,而理论则强调的是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很难直接用理论的形式去对感性的艺术进行概念化理解。因此,对中国考古美术作品的定性研究是建立科技美术考古学学科建立必须面对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的解释方法并不寻求理性的解释语境,往往以共建艺术化的文本来诠释另一种艺术的呈现和内涵,例如顾恺之的传神论、谢赫的气韵说等等,以致形成了明清之后题诗解画的传统。这种阐释方法独具中国特色和诠释魅力,然而这种以意表意的方法会让观者产生更加意象化的感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显然,采用这种“理论”的解释方式不是现代理论所提倡的确证性解释方式。
就历史美术作品而言,无论何种阐释方法都无法绕开作品的本体角度。有关本体论的认识,各学派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形成认知上的区别。就整体认识观而言,中国的本体观念主要分为三种:其一,居于整体宇宙观倾向的哲学义本体观;其二,以宗教认识方法所阐释的天理和心学认识观,即为宗教义本体;其三,也就是最原始的朴素认识观,指物质本身具有的形体和存在形式,主要在“体用”意义上应用,即为体用义本体。①方朝晖:《论“本体”的三种含义及其现代混淆》,《哲学研究》2020年第9期,第38—48、18页。对应于科技美术考古学的问题设定和解决定义,其本体论认识观主要在“体用义本体”上展开。
无论考古发现还是传世作品以及文本记录来看,都显示出中古时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确立和成熟时期。有关古代美术的风格定义,学术界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主要是大多学者缺乏艺术实践基础,面对考古作品中的具体技艺、观念缺乏经验性的理解,直接进入背景文化研究,忽视了对本体元素的分析。
科技美术考古学对于美术风格确认的研究,主要在“体用义本体”上展开,不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同时还在解决具体作品问题和时代作品问题上具有明确的实操性和界别性。②李杰、弓淼:《中国美术考古学的风格谱系研究——以汉唐之间的平面图像为中心》,《美术观察》2016年第4期,第105—109页。当我们面对一幅考古发现的平面图像作品,如何对其进行时代风格定性和延承关系的节点判断,科技美术考古学有着独属自己的量化分析方法,逻辑性本体因素的定性,从直观视觉角度提炼出作品本体视像的基本元素,作为阐释其风格的表达基点。
对中古时期平面绘画图像进行本体元素分析,会发现最为重要的创作本体要素是造型特性、形式构成、线型轨迹和空间秩序。科技美术考古学以这些典型要素作为验证主体,通过逐项的对应分析建立一套本体元素视觉描述规范,从可视与可述结合的角度创建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
中国传统的造型特性是一个时代的认识观的形象化表达法则,不是对“客观人物”的本身翻版,③H.Werner.Comparative Psychology of Mental Development.Chicago:Follett Publishing Company,1948,pp.67—82.而是由具有明显认知倾向的典型化形式特征,与社会经验相契合的普识化造型。例如,佛教中的一佛二菩萨和《历代帝王图》中的人物比例关系,都是基于社会认知中的地位关系而决定的。
中古时期的形式观念注重人物结构的表达趋向和线面的秩序感觉。人物画中的结构线群主要表达形体的构成,而装饰性线群则是结构之外的丰富画面的节奏表现,并在汉唐之间完成了从弱结构向强化结构的转折。
中国古代绘画中最为重要的是“线”的表现性,在几千年的用线史中,创造出了极为丰富的时代线型风格。早期的线条主要起到划分色界的作用,其本身并无艺术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线型从“存形”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一阶段的线型从无规则逐渐转向秩序性强化的平行用笔的铁线描线型。隋唐时代由于书法用笔的加入,唐代绘画中的“线”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为其灌注了更多的精神内容。此时的线条对刻画人物内心活动与表情动态的一致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④彭修银:《中国绘画艺术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至此,传统的“线”已经在特定的用笔驾驭下,转向采用“描”的处理方法。从中古时期用线观念的转变来看,传统的用线轨迹,就用笔的物理角度而言主要分为匀速行笔、平行线型类和变速提按,变化丰富多端。平行笔的速毛笔施压头尾相同;而提按线型则是在行笔中加入了垂直提按的运笔,使线型产生粗细不同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空间关系并不是仅仅局限在画面之内,利用“游观”的观察方式,削弱了人的视觉焦点所产生的空间状态,使画面产生无限深远的假设空间。同时,创作者会将不同地域的事物统一在同一个画面之中,使得表现对象呈现跨越时空的状态。①[美]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
科技美术考古学的风格定性方法,是从创作本体角度进行切入,通过对本体风格元素的量化定性,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时代风格和延承规律的序列程式的。更具意义的是这种基于“体用义”的本体论价值观对科技美术考古学的学科独立而言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
结 语
科技美术考古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学科理论体系,具有明确研究问题目标的理论自觉性。科技美术考古学具有显性的跨学科属性,由于解决问题的手段较为复杂,因此需要建立明确的“事实逻辑”立场以及考古物质与历史现场的统一来创建自己的整体系统关系,以历史逻辑思维、历史物质与史学观念的综合统一,来搭建整体性的理论认识观。基于这一理论观念的建构,建立相同与异质属性之间的内在紧密结构,来处理学科兼容的关系以及制定问题设定原则,从而成为一种拥有特殊领域、特殊理论、特殊方法和特殊技术的独立研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