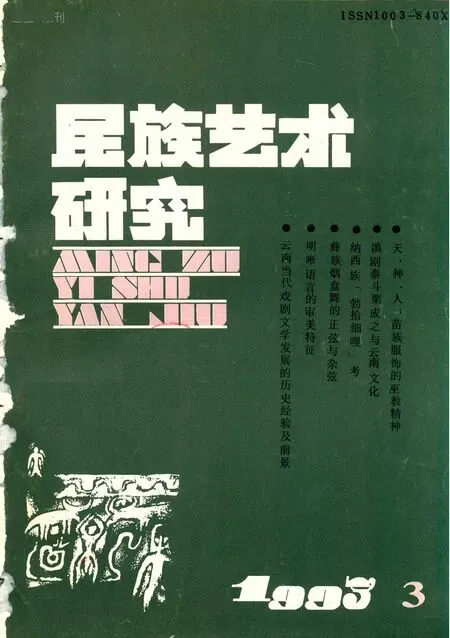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中的现代北京形象
——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
赵成清
北京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曾经是元、明、清等封建王朝及北洋政府的首都。1928年6月28日,民国政府将南京定为首都,改北京为北平。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于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①王聚英、张迎潮、尤秀斌:《定都北京是人民与历史的选择》,《文史精华》2009年第8期,第12页。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定都北平的决议,改北平为北京。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明,定都北平,将之更名为北京,是应有之义,是历史的选择,它显示出人民政权的北京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南京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从此,北京开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和人民政权的象征。古老的北京因此以充满时代色彩的绚丽画面,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术表现的内容,一批杰出作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术的经典之作。
一、纪实与想象:国家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美术形态的正式确立。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全面建设和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术,国家首先即通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行了讴歌。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其改名和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中具有的“开国”的意义,首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创作中得以阐释和呈现。以“开国”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既是历史纪实,又包含着艺术想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困难与抗争中走向独立与自强,从积贫积弱、筚路蓝缕走向伟大复兴,这一波澜壮阔的大型历史事件记录在画家“开国叙事”的创作中。
围绕着“开国”前后一段时期的历史事件,艺术家们以中国画、油画、年画等形式创作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图1)、张乐平的《庆祝开国大游行》、黄均的《庆祝国庆》、陈菊仙的《祖国颂》、卢沉等的《当代英雄》、王洪亮的《开国大典》、马泉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段江华的《东方红·1949》、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图2)、陈坚的油画《红地毯述》《共和国的将帅们》、李成民的《开国大典·人民万岁》、张敏杰的《公元1949》等,这些作品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之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原文出自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转引自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图1 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230cm×402cm,1953年创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 唐勇力,《新中国诞生》,中国画480cm×1706cm,2012—2015年创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3年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具有史诗意义,曾被毛泽东评价为“有大国气派”。它是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油画民族化的经典之作。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绘画展览,由蔡若虹、江丰、王朝闻成立的组委会组织了华东和北京地区数十位画家进行创作,然而,创作中并没有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主题。因此,中国革命博物馆专门委托中央美术学院就此进行创作,因此,董希文受命完成了这一作品。该绘画作品是对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画面中的左侧,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与各界代表站立在毛泽东的身后。为了营造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万众欢呼的宏大气势,画家有意识删减了毛泽东右前侧一根立柱和一盏宫灯,从而为画面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构图和造型上,其画面融合了中国民间美术与工笔重彩的特点,红灯笼、红地毯、红柱子、红旗衬以蓝天、白云、黄菊,在明净的天空下,汉白玉石栏旁,鲜花绽放,迎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整幅画面富丽典雅,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方法彰显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重大主题,表现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开国盛世。《开国大典》的重要性无须赘言,事实上,在构思、创作与修改的过程中,它融合了许多人的思想。由于各时期党内斗争的因素,靳尚谊、赵域、阎振铎、叶武林等画家不断对该作重新复制和修改,从而凸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国家形象”塑造的格外重视。
1960年,卢沉主笔、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5位教师集体创作的中国工笔重彩画《当代英雄》同样再现了开国之际的国家领导人与革命英雄。在蓝天白云与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背景衬托下,当代英雄昂首向人民大会堂迈步。在这幅画面中,毛泽东身着白色中山装,居于画面的焦点上,两侧人物均居于水平线之上,画面显得统一有序。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合理布置众多人物,需要巧妙的构思。与《当代英雄》相似,在表现开国主题时,2012—2015年,唐勇力创作的工笔人物画《新中国诞生》同样选择了水平构图,该作高480厘米,宽1706厘米,当时63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被一一图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画中人物成一字排开,高低错落,但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在《当代英雄》和《新中国诞生》中,水平的构图、站立的人物与体量巨大的柱子形成鲜明对比,目的恰恰是为了创造一种稳定的秩序感。经历长期的四分五裂与战争创伤,中国人民急切渴望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开国事件的再现,对领袖和将士形象的描绘,既成为一种历史纪念,也是一种对共和国的形象塑造,这种宏大叙事的手法在社会主义美术创作中被摆在了重要位置,该作打造出北京天安门的国家形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建设这一新兴国家的美好画面。
在不同时期,开国叙事的演绎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靳尚谊虽然认为当代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以“开国”为叙事主题很难超越董希文的《开国大典》这一作品,但对唐勇力的《开国大典——新中国诞生》(图2)仍给予了高度认可,认为“该画形象生动、造型精准、色彩壮丽绚烂,重新谱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时刻。”与董希文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不同,唐勇力的开国叙事并未表露出董希文20世纪50年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炙热感情,他的绘画被一种理性化的“图案”表达所取代,充满了冷静、客观和智性的反思,表达出对当下情境中如何发展中国未来道路的关怀。
在开国叙事中,国家领袖、人民军队、革命英雄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社会各界人士一道成为艺术描绘的主要对象。同时,开国叙事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并不仅仅局限于记录开国大典,另一事件与此紧密关联,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影响至深,即北平的和平解放。1959年,叶浅予据此创作了绘画作品《北平解放》(图3),作者以工笔形式表现了北平和平解放时,人民子弟兵进城、万众欢腾的场景。该作以民间年画的设色与装饰手法点缀了天坛、午门等北京景色,将北京城中军民同庆的鱼水情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也体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安定局面。与叶浅予的年画《北平解放》这一主题相同,1977年邓家驹、沈尧伊、张汝为、吴长江集体创作油画《和平解放北平》,描绘了解放军队伍从正阳门进城的庆典时刻。队伍前方骑兵们手执红旗,身后是有序的队伍;一侧的两个报童,一位手举五角星,一位拿着标语;画面精心刻画了一位白发老妪与解放军指挥员热情相拥的场景,身后则是夹道欢迎的人民群众。该画构图疏密得当、气氛欢快热烈,同样反映出古都和平解放给人民带来的欢乐。

图3 叶浅予,《北平解放》,中国画,197cm×130cm,1959年创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国”为主体,以“家”为延展,继而衍变出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家国”图像,其中,天安门图像的历史演化一步步反映着北京视觉形象的发展。天安门广场,自近代之初就是革命的发源地,1919年5月4日,为反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签订,北京大学为首的三千多名大学生云集天安门进行宣传抗议,自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帷幕。1949年,北平解放后,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时,张仃为首的设计小组建议在国徽图案中强调以天安门为中心,以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和结束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以北京天安门为依托描绘“国”与“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绘画主题。1961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本科毕业的李秀实创作了《晨》,描绘了清晨的天安门广场,人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无独有偶,1963年,同样毕业于中央美院的周思聪以中国国画创作了相似主题的《清晨》,以天安门为切入点,表达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自豪。此后,1964年,孙滋溪创作了家庭合影式的油画作品《天安门前》(图4),该作亦是以天安门为叙事切入点的经典画作。在《天安门前》中,作者恰当地运用了天安门这一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将“国”与“家”的形象组合在一起。自上而下看《天安门前》的画面构成,充溢画面的天安门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领袖画像悬挂在天安门城墙之上画面中家庭的正上方。最下方是和睦融合的一家亲合影;近景是北京郊区公社的老、中、青、少4代人,包括农村干部、插队知青、复员军人等。左右两边中景、远景人物,有边防战士、少数民族的代表团、红领巾小学生,还有幼儿园阿姨带着小朋友在金水桥上散步玩耍。画面中间的支部书记,以北京市劳模李墨林为原型创作,喻示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祖国大家庭,表达了现代家国观念。2003年和2005年,孙滋溪又分别以历史记录式的手法对20世纪70年代下乡知青和90年代城市民工为主体的天安门前合影进行了创作。

图4 孙滋溪,《天安门前》,布面油彩,153cm×294cm,1964年创作,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天安门图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每一时期的人物与事件背后都有着各自的时代精神。在周令钊的历史油画《五四运动》(1951年)中,青年学子在天安门前呼号抗争,为了祖国命运而无所畏惧,作品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选取开国前后一段时期的历史事件或象征图像进行描绘,也为中国现代美术带来了重要的收获,从早期的历史现场到当代最大限度地历史情境还原,艺术家以不同手法及对天安门主体的思辨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崇高敬意。
二、权力与秩序:民族和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进一步展现国家权力和整合社会秩序,中国现代美术创作对国家领袖、人民军队和各族人民的形象进行了重点塑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特殊节日进行了专门表现,象征中国社会主义政权核心的北京形象再一次成为视觉图像中的焦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事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中,突出对节日阅兵的再现,追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发展与壮大的历程,表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求索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根据全国政协决定,将阅兵列为国庆大典的一项重要内容。1949年以来,天安门广场共举行过14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仪式,以展示中国综合国力,向全世界传达中国力量与民族精神。在这些阅兵仪式的图绘中,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形象,得以展现和阐释。
1950年,安林依照文化部指示创作了《毛主席大阅兵》(图5)这一作品,该作再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场景。画面左侧,在党旗的辉映下,毛主席站在一辆军车上向右侧接受检阅的装甲兵行军礼,整幅画面以斜透视的方式表现了宏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这幅作品中没有直接出现天安门的形象,根据内容推测,检阅的地点是天安门前的街道。同样的阅兵题材年画还包括樊恒的《彭德怀元帅检阅三军》(图6),这幅作品中,彭德怀元帅站在军车上对着观者的方向行军礼,背景是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方阵,从画中对彭德怀顶天立地的构图方式以及作者创作的观看角度来看,他有意识地塑造了彭德怀的高大形象以示缅怀。这幅作品对应了20世纪50年代的阅兵年画创作传统。

图5 安林,《毛主席大阅兵》,年画,20.5cm×29cm,1950年创作,私人收藏

图6 樊恒,《彭德怀元帅检阅三军》,年画,88.5cm×63.5cm,1985年创作,私人收藏
2016年,为纪念建党95周年、建军89周年以及长征胜利80周年,大型系列油画展《9·3大阅兵油画——习近平主席阅兵油画》,通过不同的方队展现了中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现了新的历史时期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威武形象。
在天安门广场题材作品中,人民子弟兵的形象也得以刻画。如1953年罗工柳的宣传画《光荣的最可爱的人》,塑造了一位站在天安门前的功勋累累的战斗英雄;1976年裴常青的年画《来到毛主席身边》,刻画了一名年轻军人携带着母亲与小女儿来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的瞬间。
对军队和战士进行正面描绘,是军队美术题材创作的基础。同时,表现军民关系的作品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价值认同,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激发起大家热爱人民军队的感情。
天安门下“工农兵”组成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年画和宣传画中普遍出现,成为固定的美术创作模式,如1953年费声福创作的年画《和平万岁》,1977年新金县文化馆创作的宣传画《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安耀华的宣传画《热烈庆祝五届人大胜利召开》(1977年)等作品,都以天安门为背景,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与人民的关系,突出军民鱼水情和军民团结一家人的主题。
21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化和旅游部开启了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尤其强调了军事历史与现实题材的美术创作。一直重视弘扬军队艺术文化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则组织美术家深入革命老区和现实生活,挖掘与创作出一大批表现时代精神、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优秀作品,并进一步以美术创作表现中华民族“和合”的民族文化和审美观念。
在中国古汉语中,“民”与“族”曾各自存在,直至近代从日本传入该词,它的运用与民族主义思想发展有密切关系。英国社会学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曾提出“正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中国古代帝制时期,统治者一向以民族大一统为主旨,发展到近现代,孙中山一度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至革命成功,口号才改为“五族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政策开始推行,主张民族平等与团结,并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因此,在超民族意识形态体系中,一种新的视觉图像被创造出来,即以工农兵为主体,以象征国家政权的天安门为背景,各族人民大合影或大联欢的画面。如:年画作品中李琦、冯真的《民族大家庭》(1951年),陈菊山的《祖国颂》(1961年)、杨俊生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1964年)等,宣传画作品中袁运甫的《祖国万岁》(1956年)(图7)、李志国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977年)、哈琼文的《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胜利》等。在这些作品中,各族人民汇聚一堂、载歌载舞,军民关系融洽,尽管各族人物形象不同,服饰与风俗各异,但都表现出了民族复兴中的向心性:拥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特质、共同的归属意识以及共同的价值认同。

图7 袁运甫,《祖国万岁!》,宣传画,1956年
在诠释民族复兴的审美理想时,尚辉说道:“艺术并不仅仅止于视听审美,艺术总是表现了具体时空中的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态度,这无疑也是艺术不断向前延展的动力。我们虽不能完全做到像约瑟夫·博伊斯所说的‘艺术是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但‘艺术的社会化’应当是社会艺术家始终怀揣的一种崇高理想。当中国社会真正迎来复兴繁盛的时代,艺术创作中的宏大叙事所呈现的壮阔与明朗、阳刚与崇高无疑也应当成为民族复兴的审美理想。”①尚辉:《宏大叙事诠释民族复兴的审美理想——十艺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对于激越人文情怀的抒发》,《美术观察》2013年第12期,第13页。在开国大典、节庆阅兵、民族联欢各种历史叙事的图像中可以看到,每当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安定团结时,一种宏大气魄的中华复兴图景也在所对应现实的美术创作中应运而生。
三、绘制与设计:图式创生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国家中心,也成为表达爱国主义思想的向心力所在地。20世纪70年代初,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的爱国歌曲传唱大江南北。在国家认同和民族复兴的艺术话语中,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代表,也是首都北京的象征,代表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北京天安门也是人人向往的圣地。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美术创作中,以天安门为核心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政治图像。然而,即便在这种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仍有一些美术创作别出新意地打破了惯常的“天安门图式”,他们通过第三者的视角表现了理想中的天安门形象。如:同陶天月在《就要听到北京声音》中通过农民收听北京广播来转译北京形象。1975年程十发创作的中国画《我爱北京天安门》,同样未直接表现天安门,却给观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在这幅充满童趣的画面中,几个天真烂漫的儿童站在一张桌子旁,憨态可掬,画面中并没有任何关于北京形象的刻画,却主题鲜明、一目了然地表达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颂。
天安门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其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对称和均衡的古典建筑图式。作为政治和艺术符号,它鲜活而充满色彩,被艺术家广泛运用于绘画和设计中。在中国画创作中,周元亮的《天安门工地》(1958年)利用天安门工地改造这一题材表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百废待兴、进行工业建设的场面。画面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刚刚完工,人民开始栽花种树对首都进行绿化。另一幅代表作品钱松喦60年代创作的《天安门颂》,以虚实相生的中国画意境表现了主体的天安门、空旷的广场以及万壑松风。与传统中国画山水、花鸟、仕女及道释人物画等创作题材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要求绘画作品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就要求画家不得不走出画室,深入生活,体察现实。相对于周元亮、钱松喦对天安门的局部描绘,古一舟、惠孝同、周元亮、陶一清、何镜涵的《首都之春》(1959年)以巨幅长卷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首都北京初春时以长安街为横轴的城市面貌。200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王梦湖、程振国、陈克永、郑山麓、贺成才等人合作完成了巨幅制作《新北京盛景图》,画面高2米,长55米,以俯瞰的角度与气势磅礴的场面描绘了北京的壮丽景色。在这些鸿篇巨制中,天安门只是一个局部,但它始终位于画面的中心,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
年画创作中的很多作品,在表现党的领导、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同样体现出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创新精神。如李慕白的《狂欢之夜》(1954年)融合了月份牌画的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技法和年画的形式,描绘了一群青年男女在夜幕降临的天安门前跳起了舞蹈,极具生活气息;那启明的《春风得意》(1963年)以天津杨柳青传统年画勾勒设色的手法表现了儿童在天安门前放风筝的场景。
除了绘画形式之外,在剪纸艺术创作中,侯一民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王奇荣的《欢庆国庆节》(1973年)、吕胜中的《天安门畅想》(2000年)等作品也以独特的艺术手法传播着北京天安门的形象,它们以不同的媒介和风格展现了北京视觉形象的多样性,由此丰富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创作。
天安门的形象塑造还见于国徽的设计与绘画中。依照1949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关于国徽图案的征求启事,国徽设计应该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中国特征;第二,政权特征;第三,形式须庄严富丽。最终,在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两个团队的合作下,经过反复论证研究,推出了国徽的设计图案——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设计之初,梁思成曾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他认为,作为明清皇宫的大门,天安门是封建王权的象征,而且东西方画家均能够画出,表现力不足。①马叙伦、沈雁冰:《国徽审查组报告》,1950年6月21日。但张仃对国徽中加入天安门的构想是,天安门广场不但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还是开国大典举办的地方,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与胜利,在政治上具有突出的象征意义。此外,作为中国古典建筑,天安门端庄、雍容和富丽,同样符合完美的艺术要求。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与设计史中,有关孰是国徽真正设计者的争论较多,梳理其创作史实,不仅梁思成、林徽因、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邓以蛰、王逊、高庄等一批杰出的设计师和美术史家参与其中,众多国家领导人和学者也参与了评审并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如毛泽东、周恩来、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陈嘉庚、李四光、邵力子、田汉、马夷老、沈雁冰、马叙伦等人。由此可见,以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设计凝结了集体智慧,并非由某一设计师单独完成,是经过集体认同的国家政权形象。细心者可以发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天安门城楼上并未悬挂国徽,原因正在于毛泽东希望邀请专家组对此慎重设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年画与宣传画中,以北京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形象也被大量地表现于其中,如王世祥1959年创作的年画《祝祖国万寿无疆》,画面中摆着一盘寿桃,画面上方的国徽散发着万丈光芒。在刘庆瑞1963年创作的年画《节日的天安门》中,一组组方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着列队庆祝活动;每一组都环绕在巨大的花篮四周;而居中的方队中间,是醒目的国徽。同样,在宣传画中,1963年翁逸之的《各族人民亲密团结 伟大祖国繁荣富强》中,前景是各族人民的群体肖像,远景是中国的壮丽河山及现代化场景,画面中心则是国徽。1974年王伟戍、沈绍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在描绘各族人民时,同样强化了画中国徽图案的运用。此类有意识地表现国徽标志的宣传画代表作还有张育良的《祖国大地百花争艳》(1979年)、黄炯的《中国万岁》(1981年)、贾鸿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989年)等作品。
从对历史记录到绘画设计,天安门的图像在美术创作中被不断地复制和挪用。它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带有强烈的时代和地域烙印。可以说,在现代北京形象的构建中,天安门的这一政治符号最为显著。它是北京历史文化的记忆,是中国政治板块中的核心。同时,以此展开的叙事和抒情也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与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由衷拥护。
以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为主题创作的美术作品,在题材、形式、风格与内容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红色政权的伟大。它让人们追忆起血与火铸就的战争岁月,同时再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发展历程。通过描绘开国叙事、重大节日阅兵、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全国各民族人民欢庆一堂等场景,一部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当代史图像得以完整地记录下来,展现了强大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歌颂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抒写了人民大众的快乐和幸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天安门图像,不仅是中华民族逐步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见证,还全面描述了1949年至今社会主义美术和社会主义主流美术的发展形态,它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弘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主流美术的价值观。同时,它并不囿于宏大叙事和崇高主题,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美术生态发展。对于构建新型美术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天安门图像的美术探索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并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新篇章。
四、主流与个体:价值反思
对于久经磨难的中国人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构的北京视觉形象总体上趋于相似。北京,既是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区。以天安门为中心,长城、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一系列政治符号组成了北京独特的象征体系。但是,这种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很多艺术家试图在官方体制与主流思想之外,重构天安门为代表的北京形象。如:油画作品余友涵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1990年)、岳敏君的《大团结》(1992年)、赵半狄的《蝴蝶》(1992年)、王劲松的《天安门前留个影》(1992年)、李天元的《锻炼》(1993年)、章剑的《天安门系列》(2005年)等;此外,宋东的行为《哈气》与张晓刚的油画《天安门》都对以往的历史叙事和价值建构进行了反叛。
不可否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摸索前行的道路上,为了巩固政治文化秩序,美术创作中出现了程式化、表相化与庸俗化的现象。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浮夸风的艺术表现和政治工具化的集权意识都严重阻碍了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正常发展,北京的形象塑造一度显得僵硬而虚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对此进行的反思和批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但是,当“天安门图像”被政治波普为代表的艺术市场过度消费后,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民族虚无、心理扭曲等各种弊病也随之而来。可贵的是,在现代北京形象构建的过程中,国家认同和民族复兴的主流价值观从未改变,整一性和差异性始终并存,许多艺术家坚持以真情实感和本真的艺术语言表现北京的图景。从20世纪上半叶陈师曾的中国画《北京风俗图》、白立鼎的素描《北京香山》与刘海粟的油画《前门》,到50年代古元的水彩画《什刹海之夏》与《北京古城》;从90年代袁运甫的壁画《万里长城》,到21世纪马海方的人物画《皇城根下》、薛行彪的油画《大京九》、丁一林的油画《科技的春天》,这些作品表明:除了政治景观,北京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同样值得重视,那些日常生活、个人趣味与国家政治一道建构了现代北京的视觉形象。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史景迁、喜仁龙、德米特里·凯瑟尔的镜头记录下,人们看到了昔日北京——在帝国的余晖中,静谧而苍凉,但却隐藏着重重危机。而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天安门的形象既是红色的象征,又立体、生动并朝气蓬勃——它体现了政治主体、文化象征和艺术自由的多元面貌。
著名作家老舍曾以炽烈的情感形容北京:“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①老舍著,舒乙编:《想北平——老舍笔下的北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
北京的形象又源自其内在的精神。现代学者林语堂如此写道:“什么东西最能体现老北京的精神呢?是它宏伟、辉煌的宫殿和古老寺庙吗?是它的大庭院和大公园吗?还是那些带着老年人独有的庄重天性站立在售货摊旁的卖花生的长胡子老人?人们不知道,人们也难以用语言去表达。它是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不可名状的魅力。或许有一天,基于零碎的认识,人们认为那是一种生活方式。那种方式属于整个世界,千年万代。它是成熟的,异教的,欢快的,强大的,预示着对所有价值的重新估价——是出自人类灵魂的一种独特创造。”①林语堂:《大城北京》,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21世纪的今天,老北京仍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价值追寻和审美塑造的观念引导下,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北京视觉形象还在不断地被构建,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伟大复兴之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