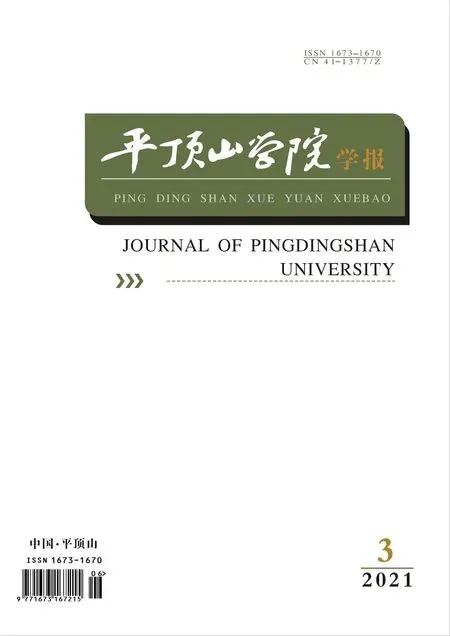张载“学即能移”的哲学阐释
孙军红
(西安外事学院 民办教育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77)
张载教育思想注重“多栽培学者”,传孔孟之道,“功及天下”。其首要的前提是了解“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这一对观念。一方面,如气质善者,需固守,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另一方面,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用张载的话说:“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1]266人的气质之性有美恶,那是因为“阴阳者,天之气也,亦可谓道。刚柔缓速,人之气也,亦可谓性”[2]324。此性是“人之气”,也是气质之性。“性未成则善恶混”[3]23,当气质之性没有成就天性时是善恶相混的,所以君子不以它为本源之性[4]。
“夭寿”二字,在《孟子·尽心章句上》中是这样出现的:“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5]夭,短命。寿,长寿。夭寿是命之短长的意思。
把人的“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联系起来,在孟子看来是“不贰”,在张载看来,“皆是所受定分”。张载从“学即能移”这一侧面,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与“贤者”相联系,即“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并另主张“学者先须变化气质”[1]274,从而达到“求为圣人”的教育目的。
一、何谓“学”
张载认为:“为学所急,在于正心求益。”[6]375学就是“正心”,因此具有宽泛意义上的自砺的含义,而其最宽泛的意思,就是“学做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2]321。
他认为学习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张载说:“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1]278对于初学者而言,道心惟微,因此不应该即时昭示。张载认为:“今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3]31对刚开始学习的人与学有所成的人,教起来也应该有所差别:“道初亦须一意虑参较比量,至已得之则非思虑所能致。”[1]280初学者必须积极勤勉地求索,可是,到第二节——从颜子以至于孔子——却不一样。就像上面所引的最后一段,这一节包括获得直觉即“非思虑所能致”之一种感悟,使人进而成为完人,即圣人。
除上述界定“学者至颜子”与“由颜子至仲尼”二节的标准外,张载还将它说成是“始成大人者”和“大而就圣者”。第二节的目标在成圣,可是,达到这一节的终点,却只能是自然生发的。而第一节中由初学进而成为“大人”,却是可以黾勉而至的。张载对这一点十分强调:“盖大则犹可勉而至,大而化则必在熟,化即达也。”[7]216“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1]266由于凭着勤勉用功就能达于“大人”之境,张载一再敦促弟子们勤勉勿怠。
一方面,“大抵语勉勉者则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则犹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须学问”[7]77-78。“惟知学然后能勉,能勉然后日进而不息可期矣。”[3]27王夫之注:“知学,知择执以至于中也;不息,则成性而自能化矣。不知学者,俗儒以人为为事功,异端以穷大失居为神化;故或事求可,功求成,而遂生其骄吝,或谓知有是事便休,皆放其心而不能勉;虽小有得,以间断而失之。”[8]139所以他劝诫学生学习只有终身继续不已,学问才会“日增日得”。
(一)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
这个“学”实质上就是接受儒家价值理念的熏陶,对儒家道德进行学习和实践。《礼记·学记第十八》:“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9]如果要教化臣民,成其美俗,一定要从“学”入手,强调“学”对移风易俗的重要性。教育所担负的不仅是传承知识,而且也是移风易俗。
张载提出:“领恶而全好者,其必由学乎!”[3]24王夫之注:“好善恶恶,德性也;领者,顺其理而挈之也。阳明之德,刚健而和乐,阴浊则荏苒而贼害以攻取于物,欲澄其浊而动以清刚,则不可以不学。学者用神而以忘形之累,日习于理而欲自遏,此道问学之所以尊德性也。”[8]117谓去除恶行恶事,也是“其必由学乎”。这个“必”字,就说明要从教育下手,才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
张载进一步解释说:“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3]23“恶尽去则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3]23“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3]23张载认为,气质之善恶虽是人与生俱来所受的定分,但人的善恶所成却取决于后天努力——禀气之偏者,可以通过后天不断的“学”,逐渐摒除和矫正“气质之性”中的“恶”,从而最终返归到至善的本性[10]。
(二)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气与习
张载提出:“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1]273这个论述强调“志趣”在学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立“天下之志”。张载说:“能通天下之志者为能感人心,圣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3]34王夫之注:“天下之人,嗜好习尚移其志者无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许。故不但兵农礼乐为所必务,即私亲、私长、好货、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为性之所弘。圣人达于太和氤氲之化,不执己之是以临人之非,则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无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于和。”[8]174
张载提出:“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7]97张载胸怀“天下”,既有“天下之心”,又立“天下之志”,于是在他的思想中便有了“为天地立心”的观念。张载说:“如志于道,致广大,极高明,此则尽远大。”[2]332他明确地把“志”同一个人的才能、事业结合在一起,强调志向远大是成才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王夫之注:“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盖言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也。天载物,则神化感通之事,下学虽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于近小,以苶其气而弃其才也。”[8]182另一方面,“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1]287。只有树立远大的志向,才能“才大、事业大”。并举例:“今人为学如登山麓,方其迤逦之时,莫不阔步大走,及到峭峻之处便止,须是要刚决果敢以进。”[1]283反之,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则会“易足”“无由进”。
其次,“只看志如何”。张载说:“有志于学者,都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学者不能坚勇。”[2]321人必须坚定信念,因为“志”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否则,“学”也是枉然:“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6]375在他看来天资愚笨不足畏,最可怕的是没有志气。
再次,“可久”与“日新”。张载说:“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3]35他强调只有“志坚”“志久”即牢守远大的志向,才能学有所成、长久保持良好的德行。一方面,“君子”不仅要“志趣高远”,而且要“守道笃信”[1]247。相反,“偷惰之夫咸有立志”[1]247。另一方面,要“信笃持谨”。张载说:“吾学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奋。足下信笃持谨,何患不至!”[2]321张载自谦地讲“吾学不振”,更不是“强有力者”,所以“不能自奋”。如果不能“笃信”,何能“持谨”?
最后,“胜其气与习”。“气者在性学之间,性犹有气之恶者为病,气又有习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于齐,强学以胜其气习”[2]329-330,因此,“某所以使学者先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熟缠绕。……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又学礼则可以守得定”[2]330。外在之“气习”往往会遮蔽人之内在本性,“学礼”则可以解除外在“当世习熟缠绕”,解去了“缠绕”,人便自然洒脱[11]。
二、“移”什么
张载说:“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所谓“气质恶者”,即为人欲所蒙蔽。如何拂去?那就是通过“设教”。“圣人设教”的目的,便是要人人都可以把“气质恶者”通过“学即能移”转而“为贤者”。一方面,“圣人设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为尧舜’,若是言且要设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则圣人之语虚设耳”[1]283。另一方面,“上智下愚,习与性相远既甚而不可变者也”[3]23。
(一)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
第一,在张载看来,“性”所涉之“有无虚实”,其实质则为“一物”。张载说:“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3]63如果“不能为一”,那么,“非尽性也”[3]63。由于每个人“气禀”的清浊昏明不同和通蔽开塞的差异,便形成智愚善恶差异的人[12]。举例说明:“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3]63“饮食男女”表现为人对物质生活的欲望,亦称“习俗之气”或“攻取之性”。 张载“合虚与气,有性之名”[3]9一语,就是说,“性”是合太虚与气化之“两”而成的。正是依赖于合成的机制,“性”作为总体才能生成:“性其总,合两也。”[3]22张载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性论观,强调“兼而不偏”方可“尽性”,通过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方可达到“继善成性”之境界[13]。
第二,“性美而不好学者无之,好学而性不美者有之,盖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2]332。使性不美转化为美,强调“矫轻警惰”[1]271。其意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1]268。其次,“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1]271。矫,纠正、匡正。轻,轻浮、浮躁。谨慎自己表情上的喜怒,这只是矫正表面的东西而不知道治理其根本,应该矫正轻慢的态度、警戒怠惰的行为[14]644。最后,“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1]271。天赋好不值得骄傲,只有矫正错误去向善,矫正懒惰而勤劳,才值得自豪[14]644。
(二)气质恶者迁移为贤者
第一,“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1]266。何为“贤人”?张载说:“克己行法为贤。”[3]46求为贤人,就是使受教育者通过“好学不倦”等途径,而成为“好仁而恶不仁”“好恶两端并进”的能够行“中道”的贤人。
第二,“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3]23气质之性在于对外物有所追求,张载称之为“攻取之性”。他说:“攻取,气之欲。口腹于饮食,鼻舌于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属厌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3]22所谓“攻取之性”是指人的嗜欲即饮食男女等物质的和生理的欲望,对于人的这种欲望,张载认为是不可以消灭的。
(三)善反之
张载说:“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3]23“反之本而不偏。”[3]23“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3]22所谓“反”,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化“气质之性”,回复到正清善美的“天地之性”。“性于人无不善”则是强调人人皆可“反”。
三、追求“孔颜之乐”
二程曾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5],但他并没有指出“孔颜之乐”所乐何事。要弄清楚其所乐何事,必须首先分析“贤哉回也”章中箪食瓢饮与颜子之乐的关系,并由此问题进展到自乐与乐他的理论问题,最后才能较清楚地观照所乐何事的问题。
在儒学发展史上,张载也是一位“学以修身力行”的榜样。第一,“夙夜从事”。《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16]382他协助边防长官蔡子正办理军务,对抗击西夏入侵做了很多工作。所谓“夙夜从事”,即张载从早到晚勤于军务,推而广之,也即夙夜在公。第二,“终日危坐一室”。《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16]383第三,“至僻陋”而“处之益安”。《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载:”横渠至僻陋,有田数百亩以供岁计,约而能足,人不堪其忧,而先生处之益安。”[16]383
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孔子最为赞赏的是颜回。 颜回于十四岁拜孔子为师,此后终身师事于孔子[17]。《论语·雍也》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8]可以说,张载继承了孔颜之乐,做到了“至僻陋”而“处之益安”。
综上所述, “学即能移”是张载极其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中包含着“性未成则善恶混”“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的认识。只有通过 “学”,方能“移”,即收到“性不美则学得亦转了”“ 气质恶者迁移为贤者”等效果。很自然的,“学”既要“善反之”,又要追求“孔颜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