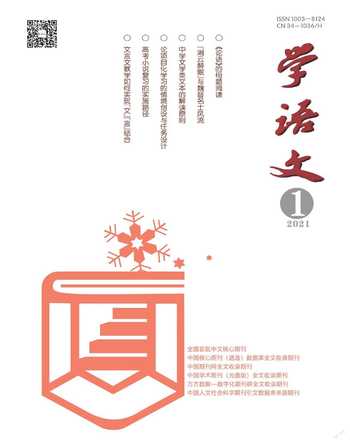许国《屈原论》析论
摘要:许国《屈原论》是继司马迁《屈原列传》之后唯一一篇专论屈原的文章。《屈原论》针对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而发,其主要观点是: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其自沉出于忧国之义、爱君之情和存君兴国之志,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屈原虽然有“怨”,自沉汨罗,仍不失为忠臣;屈原之死咎在其君。许国创作《屈原论》的原因主要有:楚辞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学术风向的变迁,许国个人的性格、政治遭际与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关键词:宗臣;自沉;存君兴国;寄托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徽州与楚辞研究”(编号:AHSKQ2015D68)中期成果。
许国(1527—1596),字维桢,明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安徽歙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先后出任检讨、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詹事、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十二年,因“平夷云南”有功,拜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万历二十四年去世,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号文穆,著有《许文穆公集》。
《屈原论》[1]不见于《许文穆公集》,为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辑录,是继司马迁《屈原列传》之后唯一一篇专论屈原的文章。文章结合时事和自身遭际,就当时热议的话题——如何评价屈原及其沉江一事,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一、《屈原论》的主要内容
许国开篇明义,宗臣于国义不可去、情不能忘,为“忠愤所激”,以身殉国,其志可谅。接着,许国对比分析了当时大臣忧国之心不如屈原的现象,认为屈原作为宗臣与国相为休戚,与君相为存亡,面对国之颠陨、君之昏聩而“感激悲憤,捐生以明其志”,而当今大臣却无心于国,“危不入,乱不居”,“合则从,违则去”。继而再次强调屈原自沉出于宗臣爱君之情、忧国之义和存君兴国之志,屈原内心也不愿自沉,希望能臣主俱荣、国家荫受其福,不得已才沉江明志,并非为了心之所欲。
《屈原论》着重对时人评价屈原的三个观点进行辨析。
第一个观点是:“人臣事君,进退惟命。是故适遭其穷而幽忧没世者为怼,欲洁其名而暴扬君过者为悻,不忍一朝之愤而自经于沟渎者为谅。彼沉江者怼耶?悻耶?谅耶?”持此观点的人基于“人臣事君,进退惟命”的观点,对屈原进行批评,认为屈原的行为是怨怼君王,“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不能明哲保身。这种观点来自班固、颜之推、朱熹等正统儒家学者,是道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对此,许国并不认同。他认为论其行当观其志,而《离骚》最能反映屈子之志:“《离骚》者,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史谓其睠顾宗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噫!斯可以观志矣。”许国认为,如果屈原是为了“身之黜”“名之辱”“爵位之失”而死,可以评价为“怼”、为“悻”、为“谅”,但从《离骚》来看,屈原为存君兴国而死,没有什么过错,上述评价是不对的。
第二种观点是:“夫不得于其君,古之人有安之者矣;不怀于其国,古之人有去之者矣,而奚必于江之沉也?”这一观点认为屈原既然不得于君,就该坦然接受或离开,不必沉江。对此,许国亦不认同。他认为,如果臣子情系君之存亡、义关国之休戚,一定不会去国。屈原作为宗臣,在他的眼中国是国与家的综合体,君既是君又是亲,断无可去之义,只有死。继而许国又分析说,楚王因不信任屈原导致一切不幸,“楚之亡也,不在负刍为虏之时而已,在灵均被谮之日”。屈原在乎的不是自身之黜陟、名之荣辱、爵位之得失,而是国家的前途命运,但不在其位,无计可施,只能以死明志。因此,屈原之志堪与“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君子可以谅其志矣”。
屈原自沉有失明哲君子的风范,这是扬雄、班固、朱熹等历代正统儒家学者的观点。此外,有明一代士人普遍持有“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事君观,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认为,“道与势之纠缠”,是明代士人的尴尬境遇,如何达到“势以道为依据而道借势以流行的和谐一致”的理想状态[2],一直是明代士人为之抗争和持续探讨的话题。如明初方孝孺以身殉道,《明史》赞曰:“忠愤激发,视刀锯斧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3]然亦受到时人讥讽,如王廷相将其与文天祥相较,认为方孝孺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招致杀身之祸,此种行为“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慎言·鲁两先生篇》)明中后期,时局混乱,仕途险恶,政治风波频起,党争激烈。加之心学的兴起,士人更加重视自我、重视个体价值。因此,君臣意见不一,臣子谏止不从,则上疏求去,鲜有死谏或殉难者。许国本人在万历十九年国本之争中,五次上疏求归,并被人拿来与同遭罢黜的申时行相较优劣:“人谓时行以论劾去,国以争执去,为二相优劣焉。”[4]据《许文穆公集·焦竑序》,时人评价许国:“浮薄险躁之人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者,徵公不足以当之。”[5]总之,屈原不得于君就该去国,不必沉江的观点,既是历代道学家的普遍观点,也有着许国所处时代社会政治和个人遭遇的深厚背景。同时代的心学楚辞研究者汪瑗“屈原非水死”的观点,就是这一时代特征的产物。他在肯定屈原忠君爱国的同时也为他辩解,认为事君之忠与同姓之义并无必然联系,历史上微子、箕子、孔子等都有同姓去国的经历;屈原也并非投水而死,“临渊自沉,身没名绝,是苟死也,孰谓屈子为之哉?”而是去楚隐居避祸,“其终去楚者,又将隐遁以避祸也。孰谓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轻身投水以死也哉?”[6]此观点可谓大胆、新颖,但失于武断,被《四库提要》讥为“务为新说,以排诋诸家”。许国则从屈原心理、情感出发,对其不肯去国、自沉汨罗的动机及其遭遇不幸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观点新颖、客观、合理,既是自我剖白也是对批评自己的声音的回应。
第三种观点是:“夫为臣不用则亦已矣,而殉之以身,不已过乎?且使人皆以身殉其忠,君谁与共国者?”孟子曰:“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岂若是小丈夫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朱熹曾在此基础上评价屈原曰:“圣贤之心如此,原虽未及,而其拳拳于宗国,尤见臣子之至情。”[7]朱熹批评屈原不能象孟子一样不遇而无悻悻之色即“怨愤”之情,也没有做到不遇则去,即所谓“忠而过”。许国在文中直接表明自己不赞同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可见,许国着力批判的第三种观点就是朱熹“忠而过”的观点。许国认为,论道以《中庸》为标准,取人则要看大节,可见他反对“过于中庸”说,他以申生、齐女为例,认为二人虽自杀并不妨碍他们是孝子、贞妇,屈原作为臣子自沉汨罗也不妨碍他是忠臣。继而,许国直接否定了朱熹“过于忠”说:“为臣而诚忠焉,虽过庸何伤乎?”并指出,抛开屈子之忠徒议其过的作法不妥,比不臣更甚。许国对屈原给予无限同情,认为贾谊、司马迁等忠义之士对屈原应当去国的感慨及惑于时论者对屈原“谅”“悻”“怼”的评价,均未能真正的理解屈子之志,认为屈原作为宗臣并无去国之义、忘君之情。最后,许国将屈原与伍子胥进行对比,“伍子之沉君也,其咎在己”,而屈原自沉“其咎在君”,“人臣不行遭变,而至于以身殉焉”,并最终得出结论:“予以为有屈子之志则可,苟无屈子之志,是则伍员而已矣”。同时代的心学楚辞研究者王世贞、李贽等也持有相似观点,如王世贞认为“务光之溺渊也,以节也;灵均之溺湘也,以忠也”,“屈氏非诚忧其身不遇,忧楚之日为秦,而主不顾返也”;李贽认为,屈原作为宗臣“势不能活”,“情不忍活”,不是顾名义而死;显然许国的分析最为深入、详尽。
二、《屈原论》创作动因
(一)楚辞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学术风向的变迁
屈原评价,历来是楚辞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刘安、司马迁、班固、朱熹、洪兴祖、王世贞等楚辞研究巨擘都曾论及。明中期以前,朱子之学统治学界,《楚辞集注》被奉为圭臬,楚辞研究一尊朱子之注。“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连许国的祖籍“程朱阙里”徽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心学的冲击和影响,“自阳明树帜宇内,其徒驱煽薰炙,侈为心学,狭小宋儒。嗣后新安大会,多聘王氏高弟阐教,如心斋、绪山、龙溪、东廓、师泉,复所近溪诸公,迭主齐盟。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矣。”[8]心学的流行为学界带来一股“标新立异”“崇尚新奇”的学术风气,受此影响,楚辞研究领域亦打破因循守旧、独尊朱注的局面,积极求变、创新,“求真是之归”;主张从“心”出发,从一己情、意出发,以“性情”说诗。在屈原评价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观点,王世贞曾总结当时存在两种屈原评价倾向:“自太史公与班固氏之论狎出,而后世中庸之士,垂裙拖绅,以談性命者,意不能尽满于原。而志士仁人,发于性而束于事,其感慨不平之无所之,则益悲原之道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则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辞则楚,其辞非楚而旨则楚。”“中庸之士”认为屈原“忠而过”“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其文“词侈多怨”;“志士仁人”则认为屈原忠君爱国,“怨诽而不乱”。许国《屈原论》就是在时局和学术思潮的影响下,站在“志士仁人”的立场上,针对“中庸之士”的观点而发。
(二)许国个人的性格、政治遭际与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许国性格质直刚强,遇事敢于犯言直谏,直接指斥谴责朝臣错误,“无大臣度”,士人以此不附。“在阁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击,不能被以污名。”又据《许国传》,万历十八年,福建守臣上报日本勾结琉球入寇,“国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务攻击,致大臣纷纷求去,谁复为国家任事者?请申谕诸臣,各修职业,毋恣胸臆。帝遂下诏严禁。国始终忿疾言者如此。”另在国本之争中,神宗本许诺万历二十年春册立,十九年秋,工部郎张有德提出要为仪注提前做准备,“帝怒夺俸”。许国、王家屏等担心神宗变卦,“引前旨力请”,神宗不悦,责备许国“大臣不当与小臣比”,许国不得不上疏请归。[9]可见,许国个性、政治遭际与屈原十分相似,而“大臣”“小臣”之辩及为臣之道等也是当时热议和终结许国政治命运的话题。许国《屈原论》针对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而发,实质就是许国对为臣之道、事君观及君臣关系的看法。他将治骚与学术、时事和身世遭际联系起来,借治骚寄托情怀、抒身世之感,继承、发扬了宋元以来徽州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
综上,许国《屈原论》的主要观点是: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其自沉出于忧国之义、爱君之情和存君兴国之志,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得失;屈原具有存君兴国之志和“瑾瑜比洁,日月争光”的高洁品行,虽然有“怨”,自沉汨罗,也不妨碍其为忠臣;屈原之死咎在其君。从方法来看,许国《屈原论》针对时论而发,不囿于理学或心学的学术桎梏,从“心”和“性情”出发,着重从心理、情感上分析了为什么屈原作为宗臣无可去之义,不武断臆测,也不牵强附会,比同时代学者分析更深入、全面、合理。他从“诗言志”“诗可以怨”的诗教原则出发,从《离骚》文本出发,考察屈原之志及其自沉原因,正视其中之“怨”,并说因为屈原之志其“怨”可谅,实事求是,不泥古,也不一味求新。他从君臣关系角度分析屈原悲剧原因,指出君应倾心信任臣子,并将悲剧原因归咎于君王,大胆新颖。他发扬楚辞研究的寄托传统,通过分析评价屈原的三种时论,对“人臣事君,进退惟命”“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等观点进行批判,也表达了自己对为臣之道、君臣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许国《屈原论》情感真挚,语言简练,逻辑谨严,鞭辟入里,寄托深远,堪与《屈原列传》比肩。
参考文献:
[1]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七十二家评楚辞》,广陵书社2008年,第15931至15939页。
[2]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3][4][9]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4030、5774页。
[5]许国:《许文穆公集》,明万历三十九年许立言刻本。
[6]汪瑗撰、董洪利点校:《楚辞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9、35页。
[7]朱熹撰、蒋立甫校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8页。
[8]施璜:《紫阳书院志》卷一六《会纪》,黄山书社2010年,第291页。
(作者:王轶,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编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