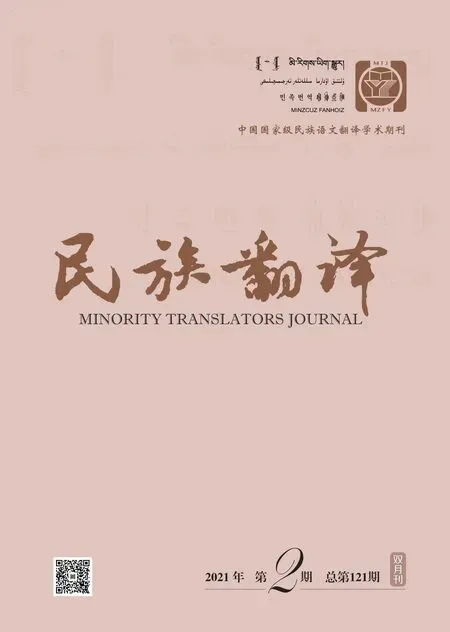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实用主义翻译规范*
——以侯奈因为例
⊙ 王雪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29)
公元8-13世纪是阿拉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阿拉伯帝国国家稳定、经济强盛、文化事业得到发展与繁荣。经济与政治强势的阿拉伯帝国,出于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广泛吸收并发展了被征服地区各民族人民(包括不同种族信仰)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形成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百年翻译运动,成就了延续至今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场旷世规模的翻译运动,在世界文明继承与传播中的丰功伟绩,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在译学上的意义与价值却鲜有探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技翻译活动”。[1]75前无古人经验可以借鉴参考,因而,它所形成的翻译规范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旨在从翻译规范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史无前例的百年翻译运动,探讨其中关于翻译的价值观和行为原则。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无论是对认识这场实践还是着眼当下的现实意义,都有着积极的价值。
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随着阿拔斯王朝于公元750年建立,并将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阿拉伯帝国迎来了历史上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巴格达不仅是一座繁荣的国际城市,而且还成为世界学术文化中心。公元830年,哈里发麦蒙(al-Ma’mun)敕令创建了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House of Wisdom),召集了大批优秀翻译家,统一组织和集中领导全国的翻译和学术研究活动。从此,翻译活动进入新的高潮,百年翻译运动由此全面展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指的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持续一百多年的译述活动。是发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古代东西方文明成果译介、注释活动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精彩的一个阶段。”[2]在时间上它被确定为“起自麦蒙时代,即伊斯兰教历198年,止于300年”[3](约公元830—930年)。百年翻译运动期间,阿拉伯人的主要兴趣在古希腊的科学技术。周放指出:“科技翻译才是阿拉伯翻译运动的重点”。[1]76埃及著名学者艾哈迈德·爱敏也认为,在阿拔斯时代前期的翻译运动中,“希腊人的智慧在科学和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都被译成了阿拉伯文”。[4]古希腊各个学科的最重要著作,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的数学及天文学著作,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医学著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哲学及逻辑学著作,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巨著都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使得大量珍贵的文物典籍乃至在欧洲早已失传的学术著作有幸保存了下来。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翻译家,其中最伟大的翻译家当属侯奈因·本·易司哈格(H•unayn ibn Ish•q)。他是景教徒,精通希腊语、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尤其擅长将希腊语翻译成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麦蒙时代,他担任智慧馆馆长,主持翻译工作。他不仅自己翻译了大批希腊典籍,还指导其他译者进行翻译,围绕他形成一批译者,包括他的儿子、侄子、学生和从事翻译活动的医生等二十余人,西方学界统称为侯奈因及其同仁(H•unayn and his school)。[5]可以想见,作为主持阿拉伯帝国翻译工作的首席翻译大师,他本人对翻译的认识以及在实践中采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必然会对其同仁和整个翻译行业产生影响。侯奈因本人也在其《书信集》①(Risla)说到,他的盖伦医学著作翻译确立了翻译过程的一些理论指导原则,他的侄子还努力仿效其做法。[5]因此,聚焦侯奈因的翻译原则,梳理总结其翻译策略与方法,也就等于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百年翻译运动的主要翻译规范。
二、侯奈因及其实用主义翻译原则与方法
(一)侯奈因:翻译家的长老
侯奈因·本·易司哈格(809-873年)是阿拉伯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和著名学者,被阿拉伯人奉为“翻译家的长老”(The Sheikh of the Translators),欧洲人称之为“Joannitius”。侯奈因将许多希腊经典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最为显赫的成就是翻译了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权威盖伦(Galen)等医学家的重要希腊医学文献。据侯奈因本人记述,在盖伦著作的129部译著中由他完成的就有100部。[6]由于他的翻译,阿拉伯语成为医学领域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他的译文准确、练达,注释详尽,在医学及哲学术语方面大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语汇,创造出了一批与之相对应的医学、哲学、动植物名称及天文学名词的阿拉伯语语汇,对阿拉伯语成为中世纪学术语言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7]
(二)侯奈因实用主义翻译原则
据史料记载,早在百年翻译运动之前阿拉伯世界就出现了文化译介活动,但发展速度不快,翻译所涵盖的范围也不广,成果也不甚多。[8]在这样一个对翻译尚未形成清晰认识的时代,侯奈因作为译者的个人惯习(translatorial habitus),不仅为自己确立了翻译标准,也为其同仁建立了翻译规范。依据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界定和后人对“惯习”概念的研究,“惯习”同时具备“被结构化”和“结构化”的特征。[9-10]惯习的被结构化指的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与影响,从而形成稳定的习惯行为;结构化则指的是这种习惯行为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以一种固定的形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规范的“构建”过程。[11]侯奈因翻译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具体而言,就是强烈的读者意识。他在《书信集》里开宗明义地说明:“为了公允地评价一个译文的优点,我们必须要知道译者和受众的经验,以便理解一个文本怎样才能适合他的能力或愿望。”[12]2实际上,《书信集》中多处指出侯奈因将传递信息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不是无条件地去保留原文中的结构和词汇特征。[13]在翻译中,他充分考虑到接受者的需求和期望,并按照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对译文做出调整与选择。侯奈因之所以采取这种以读者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是因为,首先在文化态势上,他生活在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政治经济稳步发展,阿拉伯帝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之前,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希腊文化大都是叙利亚人译介的。出于对希腊文化的尊崇,叙利亚译者对原文亦步亦趋,结果其译文拘泥于原文,语言艰涩难懂。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在侯奈因这一代译者身上已经丝毫不存在了。再者,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一场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翻译活动,不存在其他文化翻译活动中的宗教顾虑,因而译者对承载信息的原文语言有较大的灵活度。另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侯奈因所从事的翻译都有明确的委托人,包括国王哈里发、王公大臣及不同学科的学者。侯奈因在《书信集》中详细记录了翻译所服务的对象,以及为其所做的相应策略调整。有时他会根据对赞助人的了解主动做出调整,例如,在翻译盖伦的《声音》(Voice)一书时,他根据委托人的知识水平对译文进行了调整。有时他会按照客户提出的明确要求进行翻译,例如,在翻译盖伦的《初级骨骼学》(BonesforBeginners)时,赞助人要求其译文尽可能易于理解。[5]更有甚者,由于对委托人的要求做出误判,侯奈因又不得不重新翻译,例如:
最近我在Bakhtīshū的请求下按照一贯的方式翻译了这本书,采用最有说服力和流畅的风格,最可能地接近希腊原文,而不背离叙利亚语的规范。然而,他要求以一种更加易读、通顺和自由的方式重新翻译。我按照他的意思照办了。[12]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并不意味着在准确性上打折扣。相反,侯奈因非常注重译文信息的准确性。可以说,准确性也是实用性的一部分。对于科学翻译而言,没有准确性,自然也就没有实用性可言。他认为译文准确的前提是原文准确,所以首先他要确保流传下来的原文是准确的,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他根据其他可以找到的希腊文版本和叙利亚文版本对原文进行修订和改正,以此形成一个完整、忠实的原文。侯奈因在其《书信集》中写道:“我多方游历去搜集这些作品,证明这些作品的可靠性,然后进行修订,舍弃看起来是假的作品,然后进行翻译。”[12]1并且对于一份手稿,会尽可能搜集不同版本,比较、确定相对准确的原文内容。其次,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他注重文本信息传递的准确性(information-centered),而不是文本语言层面的准确性(text-centered)。英国东方学者瓦格普尔(Uwe Vagelpohl)指出“从《书信集》中可以看出,他因为想要为自己或者其他从业医生提供最准确的医学信息而减少了对语言忠实度的努力”。[13]262此外,为了追求准确性,在晚年,他还对早期的一些翻译作品进行了修改,“将他早期的作品翻译成意思更加明确的译文”。[14]因为他认为译者的经验非常重要,随着自身翻译经验增加,对背景知识的理解及翻译能力都会得到提高,这时再回头对早期的译文进行修改,更能提高其准确性。除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外,对于儿子和侄子翻译的一些作品,他也会仔细审校,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在确保准确性的前提下,侯奈因在具体翻译过程中采取了以下翻译方法来实现其实用主义翻译原则。
1.运用本土通行概念
侯奈因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首先体现为运用行业通行的术语和概念进行翻译。如前所述,侯奈因及其同仁的翻译有着明确的用户群体,即皇室、贵族和社会中的学者,他们代表着当时阿拉伯世界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侯奈因及其同仁必须考虑当时的学术氛围,在翻译中采用时下通行的学术概念,才能获得这些客户的接受与认可。如果在译文中保留几个世纪之久的原文中的术语,无疑会成为世人的笑柄。[5]众所周知,侯奈因还是一名知名的宫廷御医。在翻译自己专业领域的文献时,尤其是遇到原文和译文概念在表述上不对应的情况,他会充分利用自己所熟稔的专业知识来表达自己对翻译内容的确凿理解,以获得译文读者的认同。如,Overwien对比了希波克拉底的《急性病摄生篇》(RegimeninAcuteDiseases)原文和译文之后,发现侯奈因将原文第22章中的“inner vein at the elbow”(肘窝处的内部静脉)翻译为“basilic vein”(贵要静脉)。经过考证可知,“basilic”一词虽然最初来自希腊语,但侯奈因翻译之前早已出现在其他译文中,并通行于阿拉伯医学领域。[5]从“视域融合”角度而言,译者的翻译活动并不是被动的文字转换,而是带着已有的知识积极参与译文的构建。因此,可以说侯奈因的译文是其已有前见、当下的情境和文本所形成的“视域”相融合的结果。
2.阿拉伯本土化(Arabicization)
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必然会为译入语输入大量的陌生词。如何翻译好异域概念并让译入语读者接受,是侯奈因及其同仁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药理学涉及大量需要描述和辨别的植物名称,这给侯奈因及其同仁的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最大,阿拉伯语医学领域的术语空缺令他们举步维艰。[15]为了确保翻译效率,侯奈因首先遵守约定俗成原则,沿用前人已有的译名,而不新增译名。百年翻译运动之前,希腊古籍大多被翻译成叙利亚语并广泛流传于多语言并存的阿拉伯帝国。百年翻译运动初期,与学术语言相对丰富的叙利亚语相比,阿拉伯语在此时就显得不足。因此,继续沿用阿拉伯人已经接纳的叙利亚对应术语是一个顺利开展翻译的做法。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对于一些虽然已有前人翻译的译名但其意义在阿拉伯世界相对陌生的概念,侯奈因则从读者角度出发,将其翻译成便于理解的阿拉伯语。例如,他对自己老师曾经翻译过的叙利亚语和波斯语的一些概念,给出了新的阿拉伯语对等概念。[6]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接受,有时侯奈因还会在阿拉伯语译名后面补充到“希腊人称之为……”或“在叙利亚语该词指的是……”,甚至波斯语的对应译名,用读者可能理解的其他语言进行对应。[16]13
然而,随着翻译规模越来越大,已有的译名远远不能满足翻译需要的时候,就需要创造新词。侯奈因在创造新词方面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是简单地采用音译或者直译的方式来处理新词,有时先留下空白,在搜集阅读完与之相关话题的其他书籍之后,再回头根据获得的互文理解给出恰当的阿拉伯语译名。[6]即使采取音译的时候,侯奈因也会提供相应的解释。例如希腊术语“anorexia”(厌食症),侯奈因最初先给出音译名称,并加上波斯语译名和定义性解释,便于译文读者理解,“等对该词汇以及背后的概念很熟悉后,再创造出一个阿拉伯对应词汇”。[15]13对于anorexia这个词,他们后来创造了阿拉伯术语“but•lnal-shahwa”(abolition of desire)。
阿拉伯本土化反映出侯奈因的民族本位文化心理。虽然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之适应本民族文化,促进本民族社会发展,但还是积极努力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之间寻求或建立对应关系。
3.一语二译法(hendiadys)

侯奈因对这种翻译方法有着特别的青睐,除了传达医学术语的完整意义外,还有其他一些应用。第一,“一语二译法”有时也是一种显化策略(explicitation),用来传达原文所隐含的意义。例如,侯奈因在一段有关尿液检查的翻译中用两个动词“settle”(sakana)和“clear up”(s•af)翻译希腊原文中的专业词汇“καστημι”(to settle,即“沉降”)。第二,“一语二译法”还是一种意义具体化策略(concretization)。当原文的意义模糊时,侯奈因会根据上下文对词意进行合理具体化。例如,在描述大自然对一切物种施以调节限制,使一切安然有序发展时,对原文中表示“are well-ordered”的这个希腊概念,具体丰富为表示“adhere to one path and to one system”意义的阿拉伯词组。第三,“一语二译法”起着语义强调的作用。例如,他将希腊语中表示“consistent with”的短语翻译为表示“is consistent with and corresponds to”的阿拉伯语并列词组。为了强调医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理解能力,他把表示“accurately,precisely”含义的希腊词翻译为表示“reliably and distinctly”含义的阿拉伯语并列词组。
从以上种种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医学术语还是非专业领域的词汇,“一语二译法”都有着广泛的运用,构成了侯奈因鲜明的翻译风格。从翻译的结果来看,用于专业术语的翻译意在提高译文的准确性,便于读者充分理解;而在非专业领域的翻译中则起到强调作用,因为并列的阿拉伯词语大多意义相同或相近,与原文词出入不大,也没有明显增加新的词义。
4.语境充实法
就内容而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移译活动,而且是对希腊各学科古籍的整理、校勘和译述。侯奈因等人不遗余力地在各地搜集原始手稿,仔细甄别原稿的质量,其目的并不是一字不差地用译文保存或重新建构这些典籍的“原型”(archetype),而是在考证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与研究,从而推动各个科学的发展。对于侯奈因,这种研究性翻译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翻译中增添注释。这些注释内容前面都有“侯奈因说”(H•unayn said)来引导,以区别于译文正文。Osman分析认为,“或许是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侯奈因是最早使用注释翻译(annotated translation)的人之一,并将其确定为一种常用的方式,清晰地标明文本哪部分是他的话,哪部分是原文的内容”。[6]51首先,这说明侯奈因对翻译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即翻译是对原文内容的译文转换,原文中没有的内容则通过注释的方式加以表达。这与其他文化,如,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中的“著译不分”或“译述不分”有所不同③。其次,用当今的文化人类学翻译概念来说,侯奈因的注释翻译就是“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的一种常见类型。这一概念由阿皮亚(Appiah)提出,按照他的界定,“丰厚翻译”主要是“将文本置于原文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18]如前所述,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目的不在保存希腊古籍而在于译介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因而侯奈因的注释就不仅仅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而保留源语的文化特征,还包括一些对原文内容的进一步阐释。可以说,侯奈因在翻译过程中同时扮演着译者和医学专业人士的角色。他的注释将文本不仅置于原文的“文化网络”,在译文中充实原文的语境信息;又置于译文的文化语境,从而充实丰富着译文的语境。而后者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侯奈因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正如Vagelpohl分析侯奈因翻译的《流行病学盖伦评注本》(Galen’sCommentaryontheEpidemics)时指出的:“执业医生特别喜欢译文中丰富详实的注释,这个译本所催生的其他医学文献说明该译本广泛运用于理论、实践和临床情景之中”。[19]
侯奈因众多的翻译中,盖伦评注的《流行病学》中所增加的译注最具代表性。据Vagelpohl统计,希波克拉底的《流行病学》共7卷,盖伦为其中的第1、2、3卷和第6卷做了注评。侯奈因翻译的这4卷阿拉伯语译文中共包含17个译注。这些译注内容有的仅有3至4行,有的则有一整页手稿之多。[13]具体而言,侯奈因的注释有以下几种情况④:
首先,当遇到原文手稿中内容缺失的情况,他用注释为自己的填补作解释道:“根据我理解的盖伦评论类似引理(lemmas)的方法,以及盖伦写作的一贯原则,我擅自对缺失内容进行了填充。”[13]269-270
其次,侯奈因对原文中具有较强源语文化关联的术语和概念提供较为具体的词源与文化阐释。例如,在《流行病学盖伦评注本》第3卷第一部分中,侯奈因对其中的一个名称提供了词源解释:
侯奈因说:Silenos这个名字源自于塞勒涅(Selene),即月亮女神。很多希腊人习惯从表示月亮的词汇中选取一个指代癫痫病患者,来表达癫痫大多是按照月亮周期发作的。[13]277
再者,他在注释中对原文语言层面遇到的问题及其对翻译造成的困难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在第2卷中,侯奈因发现一个多义的希腊语语言结构无法在阿拉伯语中做到充分的对应,一开始打算舍去不译,但又经过考虑还是将其翻译出来:
侯奈因说:在希腊语,这条定理可以被切分成不同的解读方式。每一种切分解读方式都是盖伦所指出的意义中的一种。但是在阿拉伯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条定理不合乎阿拉伯语的规范,无法完全通过阿拉伯语获得理解。一开始我考虑舍弃不译,但我又觉得这条定理的思想会对那些研究者有所帮助,又决定无论如何将它翻译出来,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却是有益处的。能够读懂的人会因此受益,而不能受益的人则可以忽略,不受任何影响。真主保佑![13]277
最后,医学阐释。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从业医师,侯奈因还在注释中对原文的专业术语提供了详细的医学解释。例如,在第3卷译文中,侯奈因对“peritoneum”(腹膜)一词注释如下:
侯奈因说:希波克拉底用peritoneum来表示包围整个胃部的薄膜,希腊人称其为peritoneum。这层薄膜位于肚脐上部附近,如果发生破裂,将会产生疼痛,造成恶心和呕吐秽物。这种病情无法避免,因为小肠位于该部位,而且很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如果小肠从薄膜破裂处流出,很可能会阻止食物秽物。出现这一病情,疼痛、恶心和呕吐症状就会发生。希波克拉底说如果薄膜在右侧位置发生破裂,尤其会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这是“盲肠”和“结肠”所在的位置。大肠部位的公共区域若出现下破裂,一开始不会很疼。他特别提到这点,并说“一开始”,因为随后,病情会愈以恶化,疼痛持续扩大。[13]271
在这个注释中,侯奈因不仅解释了peritoneum是什么,而且对该部位可能发生的病症做了详细的医学描述。上述内容作为副文本的注释同正文有着相同的学术价值,表现出译者认真、严谨、准确、实用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对原文医学知识阐发的注释内容具有实用价值,才会吸引医师积极阅读、评论和研究。
诚然,侯奈因也有不加说明随意增加信息的时候。例如,Vagelpohl分析认为,他的译文中关于盖伦回忆自己在做医师助理头几年所看到的一些不当医疗操作情景,实为侯奈因个人的经历。[13]145
5.删减法
实用主义翻译原则另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去除在译文语境看来冗余的内容,从而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这也是侯奈因常用的一个翻译方法,从其本人对删减内容所做的注释说明来看,所舍去的部分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原文作者个人语言表达特色的内容。例如,侯奈因在翻译中对盖伦习惯使用希腊名人名言的做法做了删除处理,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侯奈因说:盖伦引用荷马,柏拉图以及其他古人的格言,来说明它们之间的语法一致性是不恰当的。而阿拉伯语没有合适的对等表达,因此我没有翻译这些引言,这些引言在阿拉伯语中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些引言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让人感到愉快或者有用。[13]285
从这段注释中可以明确看出,删减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对等表达(no suitable equivalents)”“没有什么用处(no useful purpose)”和“无法理解(incomprehensible)”,可以说是一无是处,只能舍去不译,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态度。
二是由于手稿残缺或者错误造成理解困难,但又不是影响重要信息传达的内容。例如,他在《书信集》中写到:
在下文中,盖伦提到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但是,我翻译成叙利亚语的这份希腊手稿有大量的错误。如果我不熟悉习惯盖伦的语言,并且了解他其它作品的大多思想,我很可能就理解不了原文的意思。但是我既不熟悉也不习惯阿里斯托芬使用的语言,也理解不了所引用的内容,因此,只好忽略不译。忽略它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读完之后,发现其中的内容盖伦已经在别处说过了,因此,我认为我也不应再过度关注它,而应该关注一些更为有用的内容。[5]154-155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侯奈因采取的并不是基于文本的翻译路径(text-based approach),他的翻译理念并不是要忠于原文。相反,他所采取的是基于信息的方式(message-based approach),再加上他本人对盖伦的尊崇,所忠实的是盖伦及其医学思想。这样的理念使他在翻译中“得意忘言”,对原文的语言形式进行大胆处理。
三、结语
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是阿拉伯“黄金时代”的重要文化活动,侯奈因则是这场百年翻译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我们考察并把握这场运动脉搏的关键人物。他具备精湛的多语能力、深厚的医学背景、丰富的翻译经验,是阿拉伯历史上伟大的译者。与此同时,他还担任阿拉伯最高学术机构智慧馆馆长一职,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培养一批出色的翻译人员,并组织规模化的翻译工作。因此,侯奈因及其同仁的翻译理念与实践也代表着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的规范。在翻译过程中侯奈因秉持明确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既要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又要充分做到译文对读者有用。为实践这一原则,他在翻译中运用阿拉伯业已通行的术语和概念进行翻译拉近与译入语文化的距离,对外来词语进行解释以辅助读者接纳,通过信息重复以确保准确,丰富充实译文语境信息和删减冗余提高译文的接受度。这些实用主义翻译原则指导下的具体操作,使其译文得到广泛赞誉与研究。本文以侯奈因为代表,考察了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不仅旨在宏观上认识这一历史盛事,更在于促进我国翻译学界拓宽视野,以他者为镜,更好认识自己与世界。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侯奈因《书信集》内容参考了德国东方学者Gotthelf Bergsträsser的阿德双语•unaynibnIshq:ÜberdieSyrischenundArabischenGalen-Übersetzungen一书,特此说明。
②本节所举“一语二译法”实例选自Vagelpohl译注的《希波克拉底流行病学第一卷》(第1-3部分)附录中的专名、主题英译索引(Index of proper names and subjects to the translation)(pp.678-702)和希-英-阿拉伯语三语词表(Greek-English-Arabic glossary)(pp.703-732)。
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历史上对翻译这个概念的认识与今天完全不同。有西方学者指出,在西方世界,翻译的概念并非是固定不变的(fluid),不同历史阶段里翻译同释义、总结和注释之间的界限往往是非常模糊的;王德威在评价五四文人对翻译的混乱认识时指出:“我们对彼时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须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
④本节与下节所选取的侯奈因译注引自Vagelpohl的InTheTranslator’sWorkshop一文中的附录,附录中Vagelpohl提供了侯奈因翻译的《希波克拉底盖伦评注版》第1-3卷和第6卷中所有注释的阿英双语对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