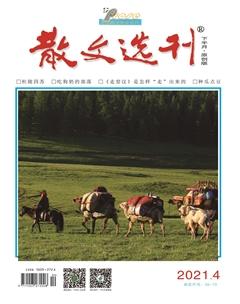《走窑汉》是怎样“走”出来的

《北京文学》是我的“福地”,我是从这块“福地”走出来的。1985 年9 月,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走窑汉》,这篇小说被文学评论界说成是我的成名作。林斤澜先生另有独特的说法,他在文章里说:“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上了知名的站台。”汪曾祺先生也曾对我说:“你就按《走窑汉》的路子走,我看挺好。”
我的老家在河南,1970 年7 月,我到河南西部山区的煤矿参加了工作。我一开始写的小说,在河南的《奔流》和《莽原》杂志上发表得多一些,一连发表了八九篇吧。时在《北京文学》当编辑的刘恒,看到我在河南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写信向我约稿。我给《北京文学》写的第一篇小说《对象》,发表在《北京文学》1982 年第12期。大概因为这篇小说比较一般,发了也就过去了。但这篇小说能在《北京文学》发表,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难忘的。我认为《北京文学》的门槛是很高的,能跨过这个门槛,我的写作自信增加不少。刘恒继续向我约稿,他给我写的信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在信中说:“再一次向你呼吁,寄一篇震的来!把大旗由河南移竖在北京文坛,料并非不是老兄之所愿了。用重炮向这里猛轰!祝你得胜。”刘恒的信使我受到催征一样的强劲鼓舞,1985 年夏天,在我写完了长篇小说《断层》之后,紧接着就写了短篇小说《走窑汉》。写完之后,感觉与我以前的小说不大一样,整篇小说激情充沛,心弦紧绷,字字句句充满内在的张力。我妻子看了也说好,她的评价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这篇小说我没有通过邮局寄给刘恒,而是趁一个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直接把小说送到了《北京文学》编辑部。那时我家住在建国门外大街的灵通观,《北京文学》编辑部在西长安街的六部口,我家离编辑部不远,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可到达。因为那天是休息日,我吃不准编辑部里有没有人上班。我想,即使去编辑部找不到人也没什么,我到长安街遛一圈儿也挺好。我来到编辑部一间比较大的编辑室一看,有一个编辑连星期天都不休息,正在那里看稿子,而且,整个编辑部只有他一个人。那个编辑是谁呢?巧了,正是我要找的刘恒。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刘恒接过我送给他的稿子,当时就翻看起来。一般来说,作者到编辑部送稿子,编辑接过稿子,会说,稿子他随后看,看过再跟作者联系,不会立即为作者看稿子。然而,让我难忘和感动的是,刘恒没有让我走,马上就为我看稿子。他特别能理解一个业余作者的心情,善于设身处地地为作者着想。刘恒在一页一页地看稿子,我就坐在那里一秒一秒地等。他看我的稿子,我就看着他。屋里静得似乎连心脏的跳动都听得见。我心里难免有些打鼓,不知道这篇小说算不算刘恒说的“震”的,亦不知算不算“重炮”,一切听候刘恒定夺。在此之前,我在《奔流》上读过刘恒所写的小说,感觉他比我写得好,他判断小说的眼光应该很高。小说也就七八千字,刘恒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看完了。刘恒的看法是不错,挺震撼的。刘恒还说,小说的结尾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我的小说结尾出乎他的预料,刘恒的做法也出乎我的预料,他随手拿过一张提交稿子所专用的铅印稿签,用曲别针把稿签别到了稿子上方,并用刻刀一样的蘸水笔,在稿签上方填上了作品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
1985 年9 月号的《北京文学》,是一期小说专号。我记得在专号上发表小说的作家有郑万隆、何立伟、乔典运、刘索拉等,我的《走窑汉》所排列的位置并不突出。但在上世纪80 年代,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对作品排在什么位置并不是很在意,看作品也不考虑作者的名气大小。对于文学杂志上出现的新作者,大家带着发现的心情,似乎读得更有兴趣。
小说发表后,我首先听到的是上海方面的反应。王安忆看了《走窑汉》,很是感奋:“好得不得了!”她立即推荐给上海的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读后激动不已,随即写了一篇评论,发在1985 年10 月26 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评论的题目是《这“活儿”给他做绝了》。程德培在评论里写道:“短短的篇章,它表现了诸多人的情与性,爱情、名誉、耻辱、无耻、悲痛、复仇、恐惧、心绪的郁结、忏悔、绝望,莫名而无尽的担忧、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甚至生与死,在这场灵魂的冲突和较量中什么都有了。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写得太棒了!”当年,程德培、吴亮联袂主编了一本厚重的《探索小说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走窑汉》。后来,王安忆以《走窑汉》为例,撰文谈了什么是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并谈到了推动小说发展的情感动力和逻辑动力。说实在话,在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王安忆的分析,使我明白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对我今后的创作有着启发和指导意义。
北京方面的一些反应,我是隔了一段时间才听到的。有年轻的作家朋友告诉我,在一次笔会上,北京的老作家林斤澜向大家推荐了《走窑汉》,说这篇小说可以读一下。1986 年,林斤澜当上了《北京文学》主编。在一次约我谈稿子时,林斤澜告诉我,他曾向汪曾祺推荐过《走窑汉》。汪曾祺看過一遍之后,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好。林斤澜坚定地对汪曾祺说:“你再看!”等汪曾祺再次看过,林斤澜打电话追着再问汪曾祺对《走窑汉》的看法。汪曾祺这次说:“是不错!”汪曾祺问作者是哪里的,林斤澜说:“不清楚,听说是北京的。”汪曾祺又说:“现在的年轻作家,比我们开始写作时的起点高。”在全国第五次作家代表会上,林斤澜把我介绍给汪曾祺,说这就是刘庆邦。汪曾祺像是一时想不起刘庆邦是谁,伸着头瞅我佩戴的胸牌,说他要验明正身。林斤澜说:“别看了,《走窑汉》!”汪曾祺说:“《走窑汉》,我知道。”
可以说,是《走窑汉》让我真正“走”上《北京文学》,然后走向全国。将近四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在《北京文学》发作品,有时一年一篇,有时是一年两篇。在《北京文学》创刊70 周年之际,我专门统计了一下,迄今为止,我已经在《北京文学》发表了35篇短篇小说,5 部中篇小说,一篇长篇非虚构作品,还有七八篇创作谈,加起来有60多万字,都够出两本书了。
走窑汉,是对煤矿工人的称谓。我自己也曾走过窑。煤还在挖,走窑汉还在“走”。我持续不断地写作,与走窑汉挖煤有着同样的道理。“走窑汉”往地层深处“走”,是为了往上升;“走窑汉”在黑暗里“行走”,是为了采掘和奉献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