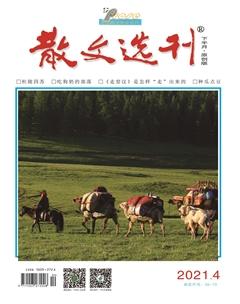给父亲上坟
查云昆

每次给父亲上坟,我和女儿小雯都会在父亲的坟堆上用硬土垡压满纸钱,仿佛在坟头贴上了一枚枚邮票,寄去对父亲的思念,像捎去这荒地半空跌宕的伤情。每次给父亲上坟,我和女儿小雯都会在父亲的坟堆上用硬土垡压满纸钱,仿佛在坟头贴上了一枚枚邮票,寄去对父亲的思念,像捎去这荒地半空跌宕的伤情。
依稀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给祖辈们上坟的情形。祖坟离家不远,在一个铺满青草的土坡下面,依坡而立的,是一座座破土而出的坟茔,每一座坟茔标记的,则是祖辈们在生的礼赞和死的挽歌历程中整个生命终止的符号。
父亲带着我给每一座坟头上压纸钱。每压一座坟,父亲都会给我介绍坟茔里躺着什么人,尽管叫不上名字,却也还说得出称呼。父亲一生都生活在艰劬的境遇中,从家里的长子到丈夫,再到七个子女的依靠,他肩上扛的是一大家人。祖辈皆为贫寒之家,作为农家孩子,我打小就与自然有着密切的接触,童时的种种意象至今依然深深印在脑海中。
儿时的我是个捣蛋鬼,一次,偷爬邻居家的院墙掏鸟蛋,不慎将邻居家用土坯堆砌的土院墙给推倒了,自己也摔在了地上,怕被捉到,根本顾不得疼痛,从地上爬起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儿就不见了身影。后来,父亲上门给人家磕头作揖,还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将人家的院墙砌好。
长大成人,是一种可怕而又无奈的愚昧;即便是对最美丽的童話,也会感到无聊。
在我求学艰苦的岁月里,我常为家穷而伤心落泪。高考落榜的那段时日,父亲经常在半夜三更睡不着起来抽烟筒。随着袅袅升起的烟雾,父亲的皱纹越来越浓,两眼越来越深陷,眼角那刀刻一样的皱纹和霜染一样的双鬓,还有一声声无奈的叹息,这一切深深地灼痛着我的心。
第二年,在得知我考上大学并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父亲满脸都充满喜悦,但随后那张充满喜悦的脸一下子又凝固了,那表情就像小孩子欢欢喜喜跟着大人去看电影却又被拦在了门外一般张皇而又绝望。因给哥哥们娶妻本就欠了好多外账,能不能让我到省城读书,父亲心里没有一点儿底。在跟小雯讲起当时的情形时,她觉着不大可能。
父亲死后不到半年光景,小雯出生了。在医院产房外从医生手中接过刚出生的小雯,那一刻,我仿佛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就在那一刻突然间失去了时间概念。自此,我每天总会有那么一丝丝牵挂或者是心动在无数个偶然之间,尤其是看着小雯一天天长大,一天一个变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表情变化都能让我兴奋不已。
现回想起那一个个幸福的温馨时刻,我总在想,当年的父亲在关注着我的每一个变化时是否像我关注小雯那样?
儿时冬天的夜晚,我双脚冰冷,父亲总会将我的双脚拉到自己的胸口,不停地搓揉,用他的体温来温暖我,而那时的我,竟然如此的不懂事还欣然接受。就在小雯六七岁时,她总会在大冬天钻进我的暖被窝,将脚板紧紧贴在我的胸口来取暖,我才感受到,什么叫爱!
父亲年过五十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尤其是在每年的春夏之交,他常被上吐下泻的痛苦和不安侵扰着,这样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
我是在父亲64 岁生日前夕结的婚。婚后不久,我带他到县里的医院检查,经诊断,肝癌晚期!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击打得全家老小肝胆欲裂,谁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穷人是生不起病的。一旦患病,尤其是绝症,患者只能在痛苦中煎熬,慢慢等死罢了,父亲也不例外。当时我刚处于人生爬坡阶段,微薄的薪水只能维持日常用度,兄妹们又都欠债,每家人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加之医生告诫,已无半分治愈的可能,就是花再多的钱,都是空添家里的负担。乡亲们知道父亲患病卧床后,早晚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好多人在病床前拉着他的手不放,还有人在他面前号啕大哭。我知道,父亲一生受人尊敬,那是兑现了他“别人敬你一尺,你要敬人一丈”的结果。
被病魔整整折腾了三个月,父亲瘦得皮包骨头,整个模样都变得让我们全家老小感到异样的陌生,却又是那样的熟悉。就在我们浸泡在泪水里时,父亲已经连续十多天都吃不下饭了,尤其在最后的那几天,他仅靠两三匙米汤、菜汤和少量的水勉强维持着生命。
一天往家跑两三趟的赤脚医生告诉我们,腹水越积越多,大便越来越干涩,疼痛越来越明显,你们不要再给他喂汤水了!医生的话语无疑给我们全家老小下了父亲死亡通牒。
父亲口渴难忍强烈要水时,我们却也只能按乡医的叮嘱,用棉球蘸水涂抹在他干燥起皮的嘴唇上。但这一天终将到来,可我们全家老小却无回天之术,拼命地拉着父亲,可死神却硬要将他和我们的手死命地掰开,我们无力拉住他,感觉他的手指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直至彻底松开。
死亡是如此深重的灾难!作为儿子,却只能携子女上坟来悼念和寄托哀思。
记得父亲出殡的头晚,天空碧澄澄,蓝晶晶,月亮像一面新磨过的天镜,亮铮铮的清辉银粉一样纷纷扬扬洒下来,无声地落在老家的院中,新鲜,纯净。
然,好景不长,转眼间,天变了脸,突然阴沉了下来,顿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紧接着,黄豆般大的雨滴就像脱弦的箭镞一样斜射了下来,在灰尘铺满的地面上射出了一个个大坑。雨越下越大,发了疯似的,天空和大地模糊一片,仿佛连在了一起。
父亲已离开十五年了。再过三四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待我百年后陪伴长眠地下的父亲时,相信,小雯每年会带着她的子辈,或者孙辈来给我上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