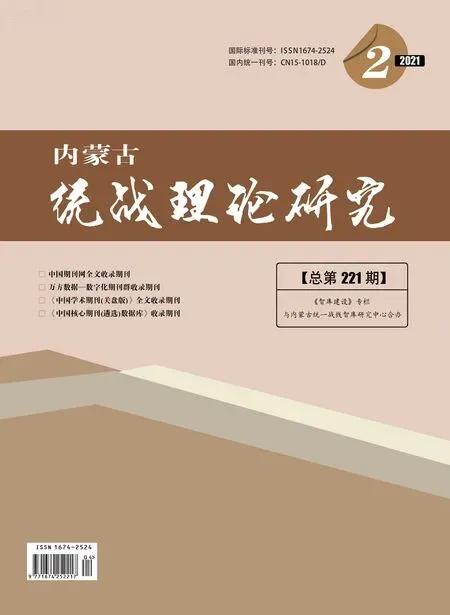历史文化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演变
◇ 文/西藏社会主义学院 周洪军 李文韬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由此与之相关的议题一度成为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综观现有研究成果,一些学者都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渊源归于千百年来形成的“华夷一体”的族群观,但对二者的相互关联等基础性研究却鲜有涉猎。鉴于此,本文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华夷一体”族群观的承继关系做一简要探查。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头:“华夷一统”族群观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共同体最初呈现为在一定族群观指导下构建而成的族群共同体。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据以构建族群共同体的“华夷一统”族群观经历了从“夷夏之辨”到“华夷一体”的转变。
早在夏商之时,“华夷”之说就已出现,其中“华”或“夏”是居于中原地区的人们的自称,而他们对居于四周且在文化上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则称为“夷”。到了西周时期,“华夷”之说又增添了“分服”意蕴,就是根据其与周王的亲疏关系将全国的邦分为畿蛮夷戎狄“五服”。此时,虽有“华夷”“亲疏”之分,但是这种划分是整体内部的划分,强调普“天下”各族群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至此,“华夷”之说羽翼渐丰。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派代表人物对“华夷”之说加以丰富与完善,其中最为完备的当属孔子提出的“夷夏之辨”思想。孔子在《春秋》中以反问的方式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在这里,孔子无疑是主张,在“大一统”之下明“夷夏之辨”,在对“四夷”进行“辨”的基础上施以“以和为贵”策略。其后,“夷夏之辨”逐步得以完善与发展,厘定并包含了“夷夏有别”和“夷夏之变”两重涵义。其中,“夷夏有别”不仅是指“夏”和“夷”之间在生活习惯、传统风俗等方面“有别”,而且还指二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有别”,体现为“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夷夏之变”是指传统儒家基于对“夷夏”可变性的肯认,主张让文化程度较高的族群与“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蛮、夷、戎、狄”)深度交融,使二者相互趋同、相互促进。
秦汉时期,“华夷一体”思想在中原士大夫阶层得以萌生并发展。汉昭帝时,桓宽在其编著的《盐铁论》中强调:“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僭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在这里,将中央和边境比作“腹心”和“支体”的关系。非仅如此,大多少数民族政权也对中央政府有着依附感和认同感,一些首领甚至认为,无论是“华”还是“夷”,只要具有较高德行,都可以成为受天命的皇帝。匈奴汉国高祖刘元海在称帝时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在这里,刘元海尽管是在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但是居于其思想意识深处的“华夷一体”思想还是根深蒂固且显而易见的。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较为突出的大分裂时期,在“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各族裔政权都以华夏正统文明承袭者自居。在这一时期,传统上不被纳入“正统”范畴的各少数民族政权,都纷纷赋予“正统”以新义,进而提出华夷皆正统。《魏书》坚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这样,拓跋鲜卑建立的魏朝通过追述华夷共祖为自身正统地位寻求血缘上的合法性。南北政权对华夏正统地位的激烈争夺,表明了它们对华夏传统政治伦理和历史文化的深刻认同,彰显了对华夷共祖共融的“华夷一统”理念的深刻认同,从而发展出“华夷皆正统”的全新理念。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北魏孝文帝开启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着力推进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氏族的交融与合流,使二者在政治上荣辱相共、在血统上凝为一体,不仅促进了多民族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极大地推进了“华夷一体”的进程。
隋唐以降的历代封建王朝,“华夷一家”理念倍受封建王朝推崇。隋文帝杨坚强调:“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唐太宗李世民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玄宗李隆基对少数民族不分“夷狄”同等接纳,认为“万邦述职,无隔华夏”,主张“王者无外,不隔遐方”。明太宗朱棣强调:“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非仅如此,“华夷一家”理念也被少数民族政权领袖接受。金熙宗完颜宣主张:“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元太宗孛儿只斤·窝阔台认为:“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清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强调:“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留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到了乾隆时期,“华夷一家”理念得以进一步发展,认为天下“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从而将其提升到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层面和高度。可见,隋唐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论是汉族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将“华夷一体”视为自然且必然之事。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雏形:“大一统”理念的内涵
“大一统”理念涵括三重主要蕴含:“天下一统”的疆域观、“王权一统”的政治观和“儒家一统”的文化观。
(一)“天下一统”的疆域观
疆域是族群共同体存在并发展的最为重要自然基础和空间条件。因而,族群共同体首先呈现为一种疆域共同体。在此维度上,“华夷一统”族群观主张“天下一统”的疆域观。
“天下一统”的疆域观最早源于“天下一统”的“天下观”。“天下观”最早可追溯至夏朝建立之初。夏启在武力消灭有扈氏后,即着手废除当时实行的部落“禅让制”,通过“钧台之享”使各族臣服于自己,确立了自己“天下”之“共主”的地位,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夏朝——由此得以建立。至此,“天下观”得以初步构建。到了商朝,指代商之朝廷的词汇包括“中商”“大邑商”“中土”和“土中”等,而作为商之朝臣的四方诸侯则根据地理方位被称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表明了商朝在当时整个“天下”中居于中心和核心地位,“天下观”由此得以清晰呈现。此时,作为“天下观”之核心概念的“天”或“天下”,意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认知能力所及的整个物理世界。
西周时期,在“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四方”“四海”“九州”“畿服”等概念,从而“天下一统”理念开始萌生,其核心主张为:整个“天下”范围的所有邦国,无论其距离周远近,无一不属于周天子管辖范围。在战火纷飞的战国时期,“大一统”地理观念又进一步得以完善与发展,产生了“九州说”“五服说”等概念。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呈现为一个“‘中心清晰,边缘相对模糊’的政治体”。
秦汉时期,“天下”的涵盖范围以中原大地为中心而不断扩大。秦王嬴政秉承着传统上流传下来的“天下一统”观念,在灭六国基础上大举征战四方,使帝国疆域不断拓展,治域内族群也日渐增多,从而使“天下一统”理念得以初步实现。西汉武帝时期,帝国疆域在周遭多个方向都得到拓展:向西张骞凿通西域通道;向北霍去病、卫青三度击退匈奴;在东北地区设置乐浪等四郡;向南彻底征服闽越和南越并控制了海南岛;向西南设置健为等七郡。东汉时期,大将窦宪攻击匈奴致其分裂为南北两部,又出塞三千余里追击北匈奴至燕然,解决了长期威胁帝国北疆的匈奴问题;明帝时又在原哀牢国辖地内设置哀牢、博南二县。至此“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秦汉之后,唐代秉承“天下一统”的疆域观,不仅推进了疆域空间的拓展,而且还在新拓展的边疆地区普遍实施羁縻制度,先后设置800多个羁縻府州,形成了“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的“大一统”局面,从而对疆域“大一统”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后,作为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元朝先后消灭了南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并将西藏真正纳入中央政府管辖范围,从而在空前广阔的帝国疆域内实现了“大一统”。到清朝时期,中国这一坐落于亚洲东部的“大一统”帝国的四至基本确定下来: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太平洋西岸诸岛,北起广阔的荒漠,南至浩瀚的海洋。
纵观古代中国文明史,无论地理疆域大小,不管治理状态如何,辽阔疆域的完整与统一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普遍的、共同的、永恒的追求。正是对这种“天下一统”疆域观的追求和践行,“天下”之疆域不断扩大并稳固。
(二)“王权一统”的政治观
要维系一个特定族群共同体,最根本的是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政治形态,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一套秩序体系。就此而言,族群共同体同时也是在特定政治理念引导下构建而成的一种政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华夷一体”族群共同体是在“王权一统”政治观的引导下构建而成的一种政治共同体。
早在先秦时期,“华夷一体”族群观之政治大一统意识已初步形成。《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这里,将“正月”归属于周王,用以表明天下都听命于周王的政令,这是“大一统”概念首次出现在有据可考的文献资料中。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多元多中心的格局”,各家各派先贤人物纷纷致力于寻求政治“大一统”的路径和良方,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政治纷争过程中,秦国通过对当时最为先进“王权一统”理念的深入践行,尤其是采纳并秉持了丞相李斯所提出的“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政治策略和主张,得以从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开启了征伐天下的艰难进程,顺次灭掉与其齐名甚至曾一度更为强大的其他六国,结束了长达两个半世纪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成就了一统六国的霸业,并在幅员辽阔的治域内创立并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王嬴政自任“始皇帝”,拥有不受任何制约的至高无上权力,从而实现了政治形态从“万邦之国”向“天下一统”的历史性转变。
秦朝创立的一整套体现着“大一统”政治共同体理念的国家政治制度,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在其治域内施政与管理的主导性策略和指导性理念。两汉时期,在陇右、河西地区大力推行郡县制,在西域地区推行都护府制,在西北羌族聚集区实行属国制和护羌校尉制。自隋朝始,统治者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对于归附和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开始实行“以夷治夷”的政策,让他们自己管理本民族的事物。唐朝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平定东突厥之后,开始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八百多个,既保留了少数民族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又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国家统一行政设置之中。元朝时期实行内地府州与边疆土司制度、藩属制度、朝贡制度等差别化治理的制度设计,并通过行省制把蒙古与西藏首次纳入帝国的统治疆域,不仅真正实现了空间疆域上的“天下一体”,而且还在整个帝国治域内呈现出“王权一统”的政治局面。到了清朝,统治者大力推进边疆——内地政治一体化进程:在东北,将三将军辖区改建行省;在西北,废除新疆的伯克和札萨克制度并改设行省;在北部,废除蒙古各部的札萨克分封制,增设州县和改设行省;在西南,提高驻藏大臣的主事权力,并在西藏各地实施与内地近似的行政管理秩序。
可见,在秦汉之后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何种族裔逐鹿中原,最终的治理模式无一不是追求帝国政治统治的完整统一,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态一直以稳定的“王权一统”为主流。
(三)“儒家一统”的文化观
政治上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在一定意义上,“华夷一体”族群观所涵括的“大一统”意蕴,是在“儒家一统”理念所激发的认同机制的作用下而形成的。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文化断流的国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重要而关键的无疑在于“大一统”意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建构和维系。前秦时期,共同体的维系主要依赖于自三皇五帝以来的道统论说,尤其是西周时期创立的礼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战国时期的乱世局面正是“礼崩乐坏”的消极后果。面对这一局面,儒家创始人孔子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中,把实现“天下”思想文化整合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诉求和价值追求,主张借助“文化一统”来确立并维护“天下一统”的“王道秩序”,并以“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之名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儒家作为“百家”之一,之所以能够胜出,在于它是当时最忠实的道统传承者以及最坚定的“文化一统”理念践行者。
事实上,“儒家一统”的文化观不仅内在地要求“独尊儒术”,而且还为秦汉以后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与稳固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西汉建立之初,尽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但思想文化上的纷争远未平息,有时甚至还达到危及政权稳固和政局稳定的程度。面对这一局面,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下诏征求治国方略,最终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董仲舒在被委以重任后不负重托,在吸取儒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体系,开始推行“独尊儒术”的政治策略,使之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促进并巩固“王权一统”的策略工具和有效手段。其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不可亡。”在这里,王夫之将“儒家一统”置于国之为国的首要基础重要地位。
可见,对于传统的帝国政治秩序和政治形态而言,儒家思想文化无疑是一种绝好的思想凝聚剂和文化整合剂。无论何种族裔或政治力量入主中原,基本上都认可并推行“儒家一统”的理念和传统,借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统辖效应为政治统治合法性正名,为实现政治统一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论证,进而提升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完善:新时代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族群共同体逐渐发展为民族共同体。在这里,民族共同体是指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具有特殊历史文化联系、稳定经济活动特征和心理素质的民族综合体。基于这一概念,考古学家夏鼐于1962年发表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首先提出并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1988年费孝通先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视角,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和统一体的观点,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更加成熟与完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话语体系。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全新概念由此产生。笔者试从上面所述及的疆域观、政治观、文化观三个重要维度上,分析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对“华夷一体”族群观的扬弃与超越。
(一)在疆域观维度上:从“天下一统”到领土主权完整
在传统的疆域观中,疆域单纯指族群共同体生存于其间的地理空间。到了近代,随着主权概念的出现,传统的疆域或领土概念又叠加了一层主权意蕴。一般意义上,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辖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与疆域或领土相比,主权更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对此,习近平在论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将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相提并论,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这样,习近平在借鉴吸收“天下一统”疆域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强调完整与统一的领土主权观。这一全新观念,在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对传统疆域观的扬弃和超越。
其一,承认并尊重他国领土主权。传统的“天下一统”疆域观是排他性的,强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否定并排斥除“王”之外拥有合法疆域的可能性。新时代领土主权观继承了传统疆域观对国家疆域统一性与完整性的重视与强调,主张“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然而,它不仅强调本国拥有领土主权,同时也承认并尊重其他主权国家的领土主权,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主权原则,强调“世界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
其二,维护领土主权应采取和平手段。在传统疆域观指导下,不论是夏启武力消灭有扈氏,还是秦王嬴政实现一统六国,甚或蒙元先后灭掉南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奉为圭臬的无一不是丛林法则,所采取的手段从未外乎武力征服。新时代领土主权观固然没有否定维护领土主权的武力手段,强调“军队必须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履行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根本职责。”同时也给出了以和平的方式维护领土主权的选项,主张“中国将坚持同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有关争议。”在这里,“有关争议”主要是指领土主权问题上的争议。
(二)在政治观维度上:从“王权一统”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如上所述,传统的“王权一统”政治观强调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威的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性,以实现王权治域内的政治统一与行政高效。新时代政治观继承了传统政治观对政治权威统一性的推崇与注重,强调“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在此基础上,后者对前者又实现了扬弃与超越。
其一,握有一统政治权力的“王”从帝王转向了人民。在传统的“王权一统”政治观中的“王”,指的是独享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封建帝王,其借助手中的权力实现对治下臣民的专制统治。与封建社会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迥然有别,我们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可见,新时代政治观中的“王”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我们党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目的不在其自身,全然在于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对此,习近平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其二,政治权力的运行从王权独尊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纵观封建社会发展史,历代帝王政治权威的获得并维持是通过武力压制而实现的,而且其政治权力的行使是排他的、自上而下的。在很大程度上,“华夷一体”的过程就是封建帝王对生活于不同区域不同族群推进一体化统治的过程。然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下,由于少数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同属于“王权一统”之中“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独有的各种生活习惯、文化传统等被得到充分尊重,并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予以维护和保障。对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习近平强调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就是要求“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强调“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而是在维持国家政治统一基础上的民族和地方自治。
(三)在文化观维度上:从“儒家一统”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在封建社会中,长期以来尊奉的是以仁爱、正义、自强等理念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借其思想“凝聚剂”和文化“整合剂”作用的发挥,对统合文化思想、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习近平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文化价值的思想精髓,强调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其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他同时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因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以及核心价值观。与封建时代所秉持的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同,当代中国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前者实现了扬弃与超越。
其一,文化价值从为封建治权辩护到为人民服务。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之所以推行“儒家一统”的文化观,是为了借儒家核心价值观所主张的“三纲五常”来实行愚民政策,并通过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统辖效应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从而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独裁统治。与之相对,新时代文化观主张在文化建设中要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中,“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坚持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是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张相一致的。这样,新时代文化观将人民群众置于主体地位,从而实现了对“儒家一统”文化观之价值主体的原则性颠覆和根本性转换。
其二,核心文化价值与非核心文化价值关系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管新时代文化观与传统的“儒家一统”文化观同样强调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作用,但在对核心价值与非核心价值关系问题上却走向了对立。后者坚持儒家文化这一核心价值的独尊地位,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之相对,新时代文化观主张,在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领域核心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最早是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又赋予其时代性、创新性意蕴,强调文艺创作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族群文化关系上,这一文化观体现为对民族文化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尊重与包容,强调“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其三,对核心文化价值的遵从从文化强制到文化认同。如上所述,在封建社会实现“儒家一统”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是对“百家”之非核心文化价值予以“罢黜”的强制手段,进而确立儒家之核心文化价值的“独尊”地位。与之相对,在新时代文化观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核心”地位的确立源于人们心理层面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对此,习近平强调:“要把维护民族团结作为生命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值得强调的是,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要切实促进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必须在经济层面上使他们切切实实地得到实惠。鉴于此,习近平在会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代表时强调,“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意在通过实现共同富裕来强化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认同。
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借鉴吸收了传统“华夷一体”族群观的思想精华,而且还通过政党宗旨、时势考量等诸多因素的融入,在疆域观、政治观、文化观三重重要维度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