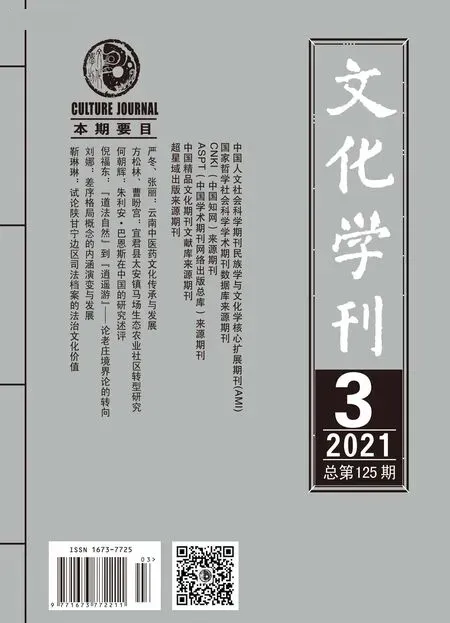浅论旧体诗与童诗教育之关系
陈柏彤
目前,旧体诗在儿童教育实践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如一些面对儿童、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学堂,开设《三字经》《千字文》《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课程,从文言入手,引导孩童规范行为举止、背诵文化常识、学习声韵知识;还有部分幼儿园或小学推广国学操、韵律操,将《三字经》等教材或《春晓》《望庐山瀑布》等古诗融入体操,让孩子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不难看出,作为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要载体的旧体诗,备受学校、各教育机构的青睐。但是,从儿童阅读写作方面的运用来看,旧体诗并未成为教学的主要参考对象;此外,也有不少诗人、学者对是否可以将旧体诗引入童诗教育提出异议。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主要探讨旧体诗能否引入童诗教育及如何引入童诗教育的问题。
一、旧体诗参与童诗教育的必要性
旧体诗是相对于新诗而言的,笼统地讲,其主要指在韵格、对仗、声律方面有严格要求的诗歌体式。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对于经过千百年发展的旧体诗,其阅读已经符合了国人普遍的审美习惯与文化传统,即使在新诗产生百年以后的今天,它也得到很多人的喜爱与追捧。一般而言,读者印象中的旧体诗都是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诗歌大家的作品,是抒发成人情感、抱负的言志之歌,与被长期忽视的儿童群体仿佛没有多余关联。事实上,中国一直有诗教的传统,钱理群先生曾在《呼唤“诗教传统”归来》一文中指出诗教与儿童教育的关系。他认为,诗教不仅适合儿童的天性,而且在保护与开启、培育儿童的自由想象力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对于儿童生命个体的终身发展及民族精神的发展都至关重要[1]。从这个层面来看,具有诗教功能的旧体诗有必要融入童诗教育中。
在整个文学序列中,诗歌是最具敏感度、对审美要求最高的艺术样式。诵读旧体诗,有利于儿童美育的培养。音韵句式整齐、语言凝练,是大部分旧体诗共有的特点,如被多种教材广泛收录的《春晓》。虽然它的语言较为口语化,但是其韵律和谐、朗朗上口,且通过听觉、视觉、知觉的交错构成具体可感的清新意境,能提高儿童认知美、感受美的能力,有助于儿童产生高尚的审美趣味。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诗缘情”是一个极富代表性的美学观点,如《静夜思》《赠汪伦》等诗歌融描写抒情为一体,委婉地表达思乡、离别、祝福之情,能够丰富儿童的情感体验,陶冶其性情;此外,旧体诗几乎没有使用助词、连词进行衔接,若要理解其中的意味,一方面要靠对文字的诗意感受与体会,另一方面要依靠词句间的想象补充,而它的这一特点能帮助儿童拓展的想象空间(诸如《嫦娥》等诗的故事场景、《草》等诗的自然风物等),在儿童感受美、体验情感的同时,培养其创造美的能力。
旧体诗的思想启蒙功用也特别值得关注。传统的启蒙读本有《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这样脍炙人口的选本,但近代以来,因新文学发展、现代教育、传媒方式变革的多重影响,旧体诗也不断受到质疑与否定,遑论推广、发扬其启蒙的作用。李咏吟在《诗教与儿童精神生活的自由》一文中提到,诗教在中国古典教育体系中具有特殊的身份角色和功能任务,在儿童期进行诗教有两个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建立个人与古典文明、民族文化思想传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活人类本源的精神自由与想象力[2]。因此,以旧体诗传承古典文化的精髓,不仅能向儿童传递热爱生命、亲近自然、探索世界、珍惜亲情、关心现实等正面价值观念,它也是对抗缺乏诗意的日常生活、工业技术下人性异化、发掘生命本源精神的重要方式。许多通俗易懂、水平较高的诗歌,如《静夜思》《悯农》《卖炭翁》《木兰诗》等作品都能成为儿童阅读的范本。
不仅如此,学习适宜的、经典的旧体诗,还与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息息相关。比如,很多旧体诗将山水、林泉、月色作为描写表现的对象,像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诗句体现了自然的整体和谐之美;苏轼的“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柳宗元的“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等诗句展示出人与自然亲昵共生的思想,这些旧体诗较为明显地昭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念,为现代生态伦理观念构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带来重要启示。又如,《示儿》《长歌行》等诗表达了精忠报国、鼓励发愤图强的思想感情,且易诵易懂,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热爱祖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这也与当今社会传承民族文化、发扬传统美德的要求相一致。
不难看出,从美育、启蒙等价值维度来看,旧体诗应该充分参与童诗教育的进程。
二、旧体诗与童诗教育之冲突
在《书,儿童与成人》的第一章“成人长期以来对儿童的压迫”中,保罗·阿扎尔谈到一个实例,童年温柔美好,是不需背负压力的时光,却被成人抹去。他们说要带儿童穿越田野,实际想教他们如何丈量土地;他们说要带儿童去路易叔叔家与同龄的朋友相遇,吃美味的点心,没想到儿童去上了一堂关于电力和地球引力的课程。也就是说,那些属于儿童的天真和好奇没有得到保护。具有启蒙作用的旧体诗在童诗教育中也存在类似冲突,譬如忽略儿童情感、强调全部读懂、灌输诗性以外的科学知识等引导方式,会遏制儿童想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诗美体悟能力的发展。
首先,现代儿童所阅读、学习的旧体诗知识产生于儿童还没有获得主体地位、没有获得成人关注的古代社会,因此强调尊重儿童天性、培养独立健全人格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注重仁、礼、孝、忠、义、敬、信、悌的古代蒙童主流价值观相冲突,部分旧体诗知识不利于儿童的心灵成长。例如,《千家诗》选录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及杜甫、岑参、王维《和贾舍人早朝》的同题应和之作,通过“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的描写,极尽渲染了宫廷生活的庄严奢华,体现了一种皇权至上、君为臣纲的观念。同时,还有《三字经》等不属于旧体诗的韵文课本,在“养不教,父之过……亲师友,习礼仪”的教导中,培养儿童仁、义、诚、敬、孝的价值观念。诚然,这些内容具有一定正面教育作用,但也应注意,过多的理性要求和行为规范或许会违背儿童的天性,影响儿童不受限制的、不设边界的思想表达。
其次,虽然旧体诗中有不少浅显易懂、适合儿童阅读的好诗,但总的说来旧体诗的语言、对仗过于规整,句式没有层次和跳跃,标点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读者自由想象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以当下十分流行的旧体诗启蒙书籍《笠翁对韵》《声律启蒙》为例,这类传统蒙学教材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注解详尽、涉猎广泛,是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文本,但是,像“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等规定性的、绝对化的旧体诗知识的学习,可能不利于儿童语言丰富性和想象力的发展。应该说,诗的精神是自由的,如果诗性的思维被固定的法则制约,那也就失去了读诗作诗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千百年来,旧体诗对读者造成了巨大审美惯性,也束缚了普通读者乃至儿童读者对诗歌的理解。比如,读者一般情况下听到“菊花”就联想到萧瑟、登高,看到“月色”就自然地与思乡挂钩,涉及“松柏”就认为与傲骨不屈有关,读到“鸿雁”就能想到书信,等等。这些意象所构筑的必然不是开放的、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诗意王国,而是高雅的、规整的、具有明显边界的意义世界,难以触及儿童自由生命精神的根本。
再次,旧体诗虽然表现手法丰富,但缺乏现代意识,未能凸显儿童主体。从情感方面来看,当下教授给儿童的旧体诗要么展现静物、自然风景(如王维的《画》、朱熹的《春日》、杜甫的《春夜喜雨》等);要么描绘田园生活(如高鼎的《村居》、吕岩的《牧童》等);要么抒发友情、乡情、报国情以及人生志向(如杜甫的《春望》、于谦的《石灰吟》等),这些诗均注重倾诉成人情怀,没有表现出属于儿童的活泼天真、调皮娇憨的丰富情感。从手法方面来看,旧体诗常用抒情、烘托、动静结合、渲染、描写等手法表达诗人所思所感,强调自我抒怀、文字铺排,缺少对话意识,但现代诗不同,其将“你”“我”“他”“它”等人称代词引入诗歌创作,充满趣味性。例如,古代儿童写的童诗大都如“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唐代五岁林杰的《七夕诗》),严格遵循诗歌规范,结合神话传说与民俗风情,清晰地交代七夕过节场景,具有客观、理性、写实的特征。而现代儿童诗歌创作大有不同,像“爸爸说:水里的泡泡是鱼吹的。妈妈说:水里的泡泡是鱼玩的。我说:水里的泡泡是鱼的眼泪”[3]3这样的诗句,从“我”与父母童稚的对话中,显现出三个平等的“人”,突出儿童的主体性;还有“小船小船,你要开到哪里去?我要开到大海里去,看看我的小鱼和小虾”[3]11,像这样完全从儿童立场出发,通过对话式的问句、长短不一的句子,传递儿童情绪,发出属于儿童的声音,展现儿童诗人的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精神。
也就是说,旧体诗会从内容、句式、法则、体式等不同方面对儿童心灵的成长、主体精神的获得、想象力的发展产生一定制约与阻碍。
三、旧体诗如何对接现代童诗教育
王泉根先生曾提出儿童诗有两个尺度,即诗的尺度与儿童的尺度。参照这一判断标准,旧体诗如何成为适合儿童学习的诗,如何对接少年儿童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如何帮助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提升他们的诗美鉴赏能力,是当前旧体诗的教育所面对的主要问题。
从范围来看,中国的旧体诗歌创作传统源远流长,优秀作品数不胜数,因此应该遴选出更丰富的、适合儿童学习阅读的诗人诗作,为儿童提供滋养心灵与精神的土壤。经过各个版本语文教材多年的编排与筛选,服务于教学的旧体诗“经典”体系基本初具规模,其主要诗人有曹操、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苏轼、王维、杜牧、杨万里、白居易、陶渊明、孟浩然、韩愈等,他们的主要作品有《观沧海》《峨眉山月歌》《夜雨寄北》《游山西村》《题西林壁》《泊秦淮》《竹里馆》《小池》等,这些诗人诗作或表现出一种体味人间真情的心绪,或抒发对世间百态的感喟,其语言含蓄凝练、通俗浅近、明白易懂,艺术形象鲜明生动,符合少年儿童的理解接受能力,即使有一些意境深邃、富于哲理的表达,也可通过由浅及深、丰厚的思想层次,使少儿读者易于接受。不过,浩如烟海的旧体诗作品真的就只有这些适宜于儿童阅读的诗歌吗?或许,一成不变的“经典”会造成审美眼光的单一。笔者认为,那些具有叙事特征、神话元素的故事诗,还有那些内容丰富、活泼有趣、朗朗上口的童谣儿歌(如《古今风谣》《演小儿语》所选录的儿歌)等,都是有待开掘的宝藏,应将其纳入教学选录范围。它们既能展示旧体诗的民间元素、多样化语言,又能启发少儿读者的多元审美思维。
从目的来看,儿童诗的教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必去刻意培养未来的诗人,也就是说,旧体诗教育目标在于培养“人文的涵养”[4]36,而非思想、文字或知识的规训。林文宝先生在《试论儿童“诗教育”》一书中总结到,儿童具有好奇、好动、好游戏、好群、天真纯洁、好胜、想象丰富、注意力短暂、好模仿的心理特性[4]26-27,相应地,诗教育的本质应该是“游戏情趣的追求”[4]36,诗教育的实际效果在于“才能的启发”[4]36。近年来,古诗教育的方法越发多样,教师通常采用诵读、歌曲创作、诗文游戏、配图叙述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帮助少年儿童感知诗歌形象的开放性、多面性,另一方面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正如林文宝所言,诗是心的呈现,“诗作得好,作不好,是另一回事,作诗的心灵倾向,是人生教育所不可缺的,也是最重要的”[4]36。因此,儿童阅读、仿写旧体诗,不应作为一种知识技能,而应成为其表露情感、体味人生、感受语言的途径。
从写作、应用方面来看,应该注意遵循“体悟规则而非记诵规则”的标准,通过具体教学让少年儿童体会比喻、反复、对仗等手法的内涵,在促进儿童认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联。有学者认为,儿童语言具有语汇有限、容易出现语法错误、发音困难、专用语调和专用语汇等特点,因此诗的教学终点就在语言,只有通过对语言内涵意义的了解,才能提升思考层次。例如,李白的《古朗月行》常被作为经典教学范本,特别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的咏月名句,将“月”与“白玉盘”“瑶台镜”这些物象相对应,既丰富了“月”这一简单词语的内涵,也充实了儿童对这一自然景象的认知。当儿童领悟这些诗句后再去描写与月有关的情境、赏月的心绪,他们的词汇结构与认知基础就会有明显的不同。
总之,重新翻检并扩展旧体诗的选择范围,有助于现代儿童民族精神、多元审美思维的生长;明确涵养人文、启发才能的教育目标,能帮助儿童感悟心灵、体味旧体诗的多重形象特征,发展其想象力;遵循轻规则、重体会的学习标准,则有利于科学提高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现代儿童教育是在充分尊重儿童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的前提下展开的,因而旧体诗的教育也应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进行。

秦 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