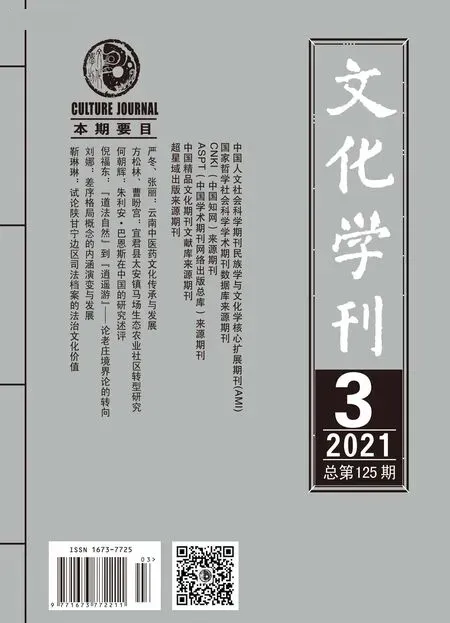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演变与发展
刘 娜
一、背景论述
自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理论以来,社会关系网络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甚至一度在学界掀起了多学科研究关系网络的热潮[1]。在这种影响下,很多中国学者也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经验,对中国的社会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系网络对不同群体的求职过程、职业流动及社会支持的影响等方面。相关研究浩如烟海,不胜枚举。张文宏在《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30年》一文中曾做过非常详尽的梳理[2-3],在此不作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借鉴西方社会关系理论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认为西方社会网络研究本身存在很大缺陷,其对关系强弱度的划分实际上隐含着一种静态的和单时点的分析视角,缺乏对关系的动态分析,而关系是动态的、多维的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应该从实践中关系的流动性来看待关系,探究行动双方是如何在实践逻辑中经过错综复杂的策略互动来建构关系的[4];二是认为这套源于西方社会的强—弱关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实。格兰诺维特划分强、弱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社会上的任何两个独立性个体之上的,但是在中国并不能作这样的假设。在中国,人们对“关系”的理解不单指只有通过交往才能结成的纽带,更多还是指一种空间或格局的概念,强、弱特征并不明显。比如,即使两人没有交往,但只要存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就可以义务性地和复制性地确保他们之间的亲密和信任关系[5],也即中国人遵循的不是关系或信任的强弱,而是各种各样的关系认同,这与西方非常不同[6]。因此,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把西方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社会。
如果说前者是对西方社会关系理论的补充、修正和发展,那么后者则是对其基本概念和理论架构的批判,倡导建构一套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现实的本土社会关系理论。的确,经过学者的多年努力,一套本土化的社会关系理论体系已经呼之欲出。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对“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本土化概念的阐发上,尤其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研究最为细致、系统和深入。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对社会转型时期差序格局的内涵演变进行分析。
二、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意涵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层结构时提出来的。费孝通没有用严格的学术定义来界定什么是差序格局,而是用投石入水这一形象的比喻来解释这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关系格局就好像石头扔进水里所激起的一圈一圈的波纹,以自我为中心,离得越近,关系越亲密,越远,关系越疏离[7]。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推移而形成的关系结构,就是差序格局。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差序格局是乡土社会建立社会联系的基本方式,也是稀缺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权力、身份、地位和财产等资源无一不是按照差序格局的模式进行分配的[8]。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对传统礼俗社会的抽象概括,提出后便成为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概念之一。20世纪90年代社会关系研究在中国兴起后,学者也开始对差序格局所隐含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的意涵进行探讨。格兰诺维特在提出弱关系理论时,是从四个维度来判断关系的强弱度的,即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1]。而在中国,关系的概念是从某一个体层层推出去的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的群体概念,这种由中心推移出去的可伸缩的关系网络有内外之分,却无明显的强弱之分[5]。所以,在区分关系类型时,学者更多是按照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从血缘、亲缘、地缘及业缘关系上进行划分(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通)。如钱再见将社会关系网分为“内网”“中网”和“外网”[9]。内网,即由于与生俱来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初级社会关系;中网,是在扩大了的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外网,则是人们日常社会交往中难以波及的外围社会活动领域,它是人们建构关系网的潜在关系资源。还有学者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形式,将社会关系分为“继承性关系”和“生成性关系”:“继承性关系”类似于“先赋性关系”,主要由血缘、亲缘和地缘构成;“生成性关系”类似于“获致性关系”,主要由业缘关系构成,是个体通过经济、社会活动的参与而创造出的关系资源[10]。当然,这几种关系并不是严格区分的,它们之间也可能部分重叠,如业缘与血缘关系之间,或地缘与亲缘关系之间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重叠的。尤其亲缘关系,与其他关系的复合程度更高。
“差序格局”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来的概念,但对我们当代社会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如张文宏等基于差序格局理论,探讨了转型时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情况。他们发现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社会网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以血缘和婚姻关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依然占据最重要的地位[11]。农村居民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和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家庭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处于中心的位置。另外,张文宏针对城市居民的调查也发现,虽然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伴有一些现代性扩展,但仍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与自我关系越密切的人,越会较早进入自我的网络提名名单;并且,工具性内容随着提名的延后而增加,而情感性内容则随着提名的延后而减少[12]。
不过,虽然差序格局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结构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其内涵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了差序格局理性化或工具化的倾向。
三、内涵演变:差序格局理性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差序格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情感和儒家伦理的差序,利益逐渐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之一。如王思斌通过对河北省泊头市农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关系是一个由血缘、姻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交织而成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非亲属关系穿插其中的巨型动态网络系统[13]。这种网络关系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同亲属家庭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又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亲属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之间除了沟通感情外,更为注重经济上的互利互惠,社会关系的感情色彩日益淡薄。不过,亲属关系的核心地位总体而言依然没有动摇。
差序格局的这种变化也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李沛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的概念,旨在丰富差序格局的现代性内涵[14]。他通过对我国香港地区华人社会关系的考察发现,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是否有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自身的关系网络中,而且从中心向外推移,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对工具性价值较大的关系,中心成员会通过各种手段特别加以维护。关系越亲密,越有可能被用来实现利益目标。
相似地,杨善华、侯红蕊也提出了“差序格局理性化”的观点[15]。他们发现利益在形塑乡村社会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中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差序格局理性化的趋势。还有学者观察到,在差序关系的建构过程中,人们虽然强调内外有别,但熟人、亲人、自己人等“内群体”并不排斥“外群体”。由于社会资源分配渠道的多样化,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人们会以内群体为基础来临时构建关系网络,以尽力扩大人际关系的范围[16]。简而言之,在差序格局的理论中,包括人情、伦理、血缘、地缘和利益等多个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而随着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影响差序格局形成的各种指标的权重也发生变化,经济利益等指标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出现了学者所观察到的“差序格局理性化、利益化”的倾向。
差序格局的这种创造性转化受到部分学者的尖锐批判。肖瑛将其命名为“新差序格局”。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新差序格局“一方面涵摄传统差序格局的结合模式……另一方面又是纯粹的工具主义化”,人们参与其中的终极目的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展社会资本,为满足个人物质欲望和获取权力资本创造便利条件。这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唯利是图的新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差序格局的道德性[17]。周飞舟则认为肖瑛的看法过于片面,简单地将“关系”视为工具性的结构,而忽视了差序格局的伦理基础,认为这实际上是以“利益—权力”的技术分析替代了真正的社会研究。他主张不应该脱离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把行动作为纯粹工具理性的行动进行分析[18]。那么,差序格局是否真的已经蜕变为工具化的利益获取机制?曾经作为差序格局重要维度的伦理、情感是否真的已经消弭殆尽了呢?
四、利益并非决定差序的首要因素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变迁,差序格局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影响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因素。正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差序格局并没有消失,反而实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17]。可是利益是否真的是人们建构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呢?并非如此简单。很多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虽然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所改变和扩张,但以家庭为中心的亲缘关系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如学者在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时虽然观察到一些新变化(如上述张文宏、王思斌、杨善华等人的研究),但都认为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亲缘关系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城市中也不例外。学者在对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进行考察时也发现,虽然相较于传统社会,个体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亲属关系不再拥有控制和支配个人的权力,但是这种自主性并没有削弱亲属间的亲密情感[19]。互助互惠的亲属关系,并不是都出于利益的考量,许多支持和帮助都是纯粹的、单向的、不求回报的。而且,亲属间交往的频率和亲密度依然呈现出按照亲缘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排列的差序格局,关系越远,情感联系和互动互助越少[20]。
这些发现与差序格局理性化的结论似乎相互矛盾。但如果能够对差序格局中不同类型关系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就会找到答案。差序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以亲缘关系为内核向外层层推移的。关系的亲密度以及担负的相应责任和义务则层层递减。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亲缘关系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起到了社会结构稳定器的作用。如刘娜在分析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时发现,那些经历了长距离社会流动的被调查对象,仍然保持了与亲属的密切联系,虽然他们的亲属并不能够为他们提供新环境里所需要的资源和帮助[21]。与流动前相比,虽然交往频率有所减少,但他们与亲属的亲密程度没有任何变化,无论对父母、兄弟姐妹还是其他亲属皆是如此。而朋友关系则大不相同,那些没有与他们同步流动的朋友大多数都被淡忘了,无论是亲密朋友还是泛泛之交。这充分说明,即使利字当头,仍然内外有别。他们的关系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的分化。内核高度稳定,坚守情感和传统伦理的行事原则;而外围则比较松散,利益导向明显。这与其他学者的观察一致。如徐晓军发现,经过市场多年的渗透,乡村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系统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内核与外围两极分化的结构。外围已高度利益化,与之对应的则是内核部分的高度情感化[22]。翟学伟也发现,为了获取更多资源,人们会以内群体这种固定的关系为基础来临时构建关系网络,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内群体呈现出固定化、高度情感化的倾向,而外群体则呈现出流动化、高度利益化的倾向[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亲属关系与利益关系是互斥的,学者们关于差序格局理性化的判断也并非全然错误。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亲属关系与利益关系的融混和交织。也就是说,伦理、情感、利益等诸要素都在差序的人际关系建构中发挥着作用,强调任何单一方面的因素都是不客观的。对经济利益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摒弃亲属关系;相反,亲属关系可能在获取资源方面发挥着首要作用。很多研究表明,先富群体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落后亲属,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境况,带动他们向上流动。项飚关于浙江村的研究[23],以及曹子玮、李培林等很多学者对农民工的研究都证实,亲缘与地缘这种与现代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传统社会网络,却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24-25]。这充分说明,亲缘关系与经济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的交织、融混是一种现实的存在[26]。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并没有破坏关系结构本身的差序格局,而且亲属关系依然居于差序结构的核心位置。
五、结语
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学者就提出了关系社会的概念(如梁漱溟的关系本位、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等),但直到西方的社会关系理论引介中国后,社会关系研究才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在对西方的社会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基础上,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将社会关系与中国本土化的概念,如“差序格局”“人情”“面子”等概念结合起来,尝试建构出一套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关系理论体系。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对差序格局概念的阐发上。学者发现,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差序格局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利益导向更加明显,但是利益取向并没有改变亲属关系在差序格局中的核心位置。亲属关系与利益关系融混交织在一起,使得亲属关系成为获取资源、实现流动的重要渠道。

秦 云纹 咸阳窑店采集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