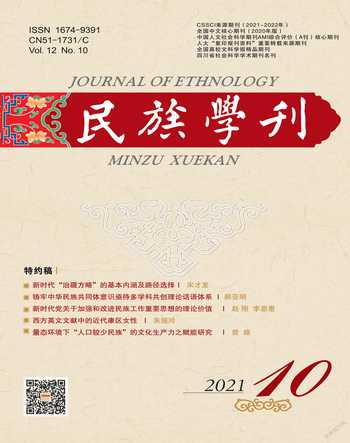西方英文文献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人大量涌入位于西藏与四川腹地之间的康区,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与康区藏族女性的接触交流日益增加,留下了大量英文书写的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西人笔下勾勒的康区女性形象日渐完善,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区女性美丽出众的相貌、多元的婚姻状况、吃苦耐劳的品性、聪慧能干的“阿佳”以及离群索居的尼僧等几个方面。不过,由于观察者身份背景、个人旨趣的不同,其考察角度、评述立场、看法、观点等纷纭复杂,对康区女性的褒贬亦殊异。西方英文文献中康区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渐增长的兴趣。近代西人关于藏族女性的记载和评价是西方社会认识和了解康藏文明的一扇窗口,为传统的女性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关键词]康区;女性研究;西方视野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0-0029-10
作者简介:朱娅玲(1974-)女,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藏学。四川成都 610064汉语和藏语文献中对藏族女性的记载自古有之,为我们开展相关藏族女性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如,汉文文献《隋书·西域·女国传》和《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的青藏高原上的“女国”,明显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而藏文文献《贤者喜宴》则记载了吐蕃法律“不与女议”和“莫听妇人言”这类否定妇女参政的规定[1]。这种规定既是父系社会男权逐渐加强的结果,又与佛教对妇女的偏见有关。不过,真正具有现代女性研究意涵的实证研究,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于式玉在边疆实地考察所做的研究,她完成了《藏民妇女》《藏民妇女的一生》《介绍藏民妇女》等系列文章[2-4],以女性人类学的范式开藏族女性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后,藏族女性研究才全面兴起,相关论著相继问世,如张云的《论藏族妇女的地位》、诺布旺丹与巴桑卓玛的《藏传佛教的两种女性观》、马戎的《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仓决卓玛的《西藏妇女权利地位今昔谈》、刘正刚和王敏的《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探析》等。[5-9]尤其是,玉珠措姆近年来所发表的《“西藏的小上海”——康定锅庄与藏族中间人研究》和《现代康区历史上的女土司》,更是藏族女性研究中的新亮点。[10-11]
除了玉珠措姆的相关论述,上述论著主要以汉、藏文献为基础,对藏族女性的婚姻家庭及社会地位等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虽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但对外文资料的利用则相对不足,尚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
近代以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西方人在康区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并且留下了大量游记、日志、纪行和考察报告等。其中,不乏对藏族女性的记叙与评论,如,澳大利亚探险家、地理学家、传教士、人类学家、藏学家叶长青(J. Huston Edgar1920;1924)①;美國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传教士葛维汉(D. C. Graham1930)②;加尔各答商会代表库珀(T. T. Cooper1873);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A.E. Pratt1892);赖里(Mina Ririe1904);美国医生哈德(Mina P. Hardy1922);美国医学家、体质人类学家莫尔思(W. R. Morse1926)③;美国人文学者费尔朴(Dryden LinsleyPhelp1922)④;苏格兰人类学家、传教士、藏学家顾福安(Robert Cunningham1912)⑤;美国物理学家、传教士、人文学者戴谦和(Daniel S. Dye1926)⑥以及麦克劳德(R. A. MacLeod1923)等。此外,英国外交官、人类学者孔贝(G. A. Combe2002)⑦、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2010)⑧当年的著述已出中文版。
事实上,这些以英语为主要载体的文献数量庞大,与汉、藏文献一样,无疑是研究近代康藏社会的第一手宝贵资料。这类丰富的学术资源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利用,从而推进藏族女性研究。
本文主要聚焦于对西人就康区藏族女性的描述和评析之文本研究,以西方视野下的近代康区女性为切入点,运用英语文献作为主要的分析材料,并结合相关的中文材料,就西人对近代康区女性的外貌与婚姻状况、品性、锅庄“阿佳”以及出家尼僧等四方面所做的描述和记录进行梳理与探讨,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更为具体化。以近代西人“他者”的角度对康区女性的论述,既是对传统史料文档的有益补充和参照,也给少数民族女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重要的借鉴。
一、身体与多元婚姻形态:西人眼中的近代康区女性
(一)身体与外貌:他者的眼光
藏区自古就有“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之说,意为最正宗的宗教立在卫藏,最好的马匹产在安多,最美的人出在康区——这里的康区包括了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等“三州一地”的康方言分布区⑨。自古以来,位于四川腹地与西藏之间的康区,乃是连接各藏区的交通枢纽和汉藏贸易的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人笔下所描摹的近代康区女性形象大都吻合藏族的传统说法,每当提及康区女性的容貌与性格特征,几乎所有西人记忆深刻,他们往往不吝溢美之词描述她们出众的外表,都认为她们美丽活泼。如,1920年,澳大利亚探险家叶长青从理塘返回打箭炉⑩,邂逅一位“即便在文明社会也难觅的佳人”,她容颜姣好,轮廓分明,眼眸晶亮,身姿轻盈,有女神般撩人的魅力。正如他在《打箭炉到理塘之路线》中所赞美的:“观察这位天真的、孔雀般的尤物风情万种地施展魅力,实在有趣。她自知其孔雀羽毛和风雅姿态已映入我眼帘,我便顺其自然地欣赏起她的美貌”[12]。又如,1930年,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在《世界屋脊之旅》中对藏族女性同样也是赞誉有加,“藏族女性容貌俊俏、美丽动人。有一次参观神灵节表演时,我听到身旁的外国女士连声赞叹,夸奖她们相貌出色,且魅力非凡”[13]。
当然,为了突出藏族女性外貌之明艳动人,西人写作时常常大肆渲染她们穿着打扮的诸多细节。当加尔各答商会代理库珀1868年游历川边时,就在他的游记中写道:“打箭炉的藏族其实大部分是汉藏混血儿,长像好看,女子尤其漂亮。男性爱穿汉服,梳辫子;女性坚持穿艳丽的藏装,蓝色长袍,腰间扎黄腰带,喜欢戴各式珠宝首饰”[14]216。尤其是在描述他所偶遇的藏族女子时,还特别强调了这些藏族女子身上所具有的不受汉族礼教文化所约束的粗犷与奔放之美,“她们衣着考究,面容姣好,披宽松蓝袍,内衬蓝色长裙,佩戴着金银珠宝,因来自偏远地区,神色里没有汉族妇女那种标志性的羞涩”[14]176。
有关藏族女性服饰盛装的描写甚多,如1892年,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在打箭炉观赏女子们跳舞时,他便观察到藏族女子佩戴大量绿松石和红珊瑚,包括项链、手镯、胸针等,款式古朴,粗犷大气。妇女们载歌载舞,热情洋溢。[15]同样,1904年,赖里接待一对“藏王”夫妻时,他对女客人的印象尤为深刻,“她们穿着全套藏装,美丽非凡。红绸绕进乌发,辫子盘在头顶,发质柔亮。神情活泼又愉快,戴精美的银耳环项链,穿蓝丝藏袍,腰间黄丝巾系裙,垂在袍外”。[16]
不难看出,以上种种描述客观而生动地勾勒出一个世纪前近代康区女性的外貌特征,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西人由衷的赞美。在他们看来,藏族女子相貌之美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性情开朗乐观,“活泼愉快”,“没有汉族妇女那种标志性的羞涩”。就此自然美而言,如女性人类学家于式玉所评议论的:“(与汉人和回教妇女相比)惟有藏民妇女,是与大自然同体的!在生气勃勃的时候,有生气勃勃的样子,兴高采烈的时候,有兴高采烈的样子,绝无矫揉造作令人莫测的态度。她们真个是天真活泼的典型人物”[3]56。另外一个特征是女性普遍喜欢传统的“藏式服装,佩戴珠宝首饰”。传统的藏族服饰历来以色彩鲜艳明丽,首飾繁杂精美著称。近代以来,特别是在汉藏两种文化不断交汇融合的康区,“男性爱穿汉服”,在着装上日趋汉化的情境里,藏族女性无论贫富贵贱,大多坚持穿戴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因而成为西人眼中一道明媚靓丽的风景。这既印证了传统“康巴人区”之说,也反映了藏族女性热情奔放的爱美天性。
(二)多元婚姻形态:女性的身体自主性与社会文化根源
婚姻家庭作为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西人对藏族婚姻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三种类型:一妻多夫、族际婚姻和临时婚姻。每当谈及藏族的婚姻形态,人们似乎首先想到藏族社会特有的一妻多夫制,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提及:“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17]英国官员贝尔(Charles Bell)也在其著述中记载了藏族官员向他介绍一妻多夫婚俗的有关情况。[18]有的西人认为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属于临时性的安排,“因为核心家庭才是生存的理想单元”[19],另一些人则对其道德准则提出质疑,如苏格兰人类学者顾福安在《“阿佳”与一妻多夫制》中就有所置辩: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一妻多夫制是极有趣的话题,但对于渴望将启蒙思想带给藏族的传教士而言,它是巨大阻碍。藏人对一妻多夫心满意足,甚至认为这比一夫一妻更让人幸福。虽有舆论支持,但它已被科学证明是某些种族在特殊文明阶段的社会措施……如果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确实具有优势,为何当今文明的火炬会将其驱逐?如果文化是人类智力的结晶,为何当今文明国家均禁止其存在?[20]19
在此,通过一系列的质问,顾福安严厉批评一妻多夫制是违背社会伦理和文明进程的陋习和传教的“巨大障碍”。然而,顾福安站在基督教“启蒙者”的立场,简单地套用西方的婚姻模式和价值标准来评判藏族的一妻多夫制,忽略了它产生的经济文化条件和特殊社会内涵,反映出他自身知识背景的局限性和对藏族社会的偏见和误解。事实上,一妻多夫在数量上并不占藏族社会的主导,只是藏区多种婚姻制度中的一种而已。当今学界一般认为造成此婚姻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由于藏区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资源稀缺,小私有者发展经济必须集中有限的生产资料和劳力,为防止土地分割,保持家庭财产完整,一妻多夫制便应运而生。[21]387
其次,西方人还关注到流行于汉藏边疆的族际婚姻状况。1871年,库珀在打箭炉游历时发现汉藏通婚非常盛行,他在《商业先驱记行》中说,“当地人不重视族内婚姻,藏族女子很少找同一阶层的男子结婚,而更愿意嫁给汉族商人或官兵。在她们眼里,商人或士兵是一种荣耀的、令人羡慕的职业。”[14]2161922年,哈德在《藏族女性》中记载,如果一个藏族女孩到了十七八岁还没有出嫁,就会觉得难堪。巴塘有很多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的官兵,“几乎每个汉族士兵在河流口岸都有一个藏族的爱人”[22]22。美国人文学者戴谦和也指出,“(打箭炉的)藏族女子倾向于嫁给汉族男子,但是藏族男子娶汉族女子的情况却并不多”[23]23。实际上,这些西人记载的汉藏通婚状况与著名藏学家任乃强所记述的颇为一致,如其所言,“现在西康住民,什八九为番,什一为汉人,百分之五六为其他民族。汉人之中,什九为扯格娃,什一为纯粹汉人而已。”所谓“扯格娃”,即“汉父番娘所生之子女”,也就是汉藏混血儿。[24]由此可见,清末民国时期,族际婚姻在边疆地区的确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故在中西方文献中均有不少相关记载。不过,除了对族际婚姻的盛况进行表层描述之外,还有少数西人将其与汉、藏民族之间沟通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如,戴谦和在《打箭炉印象》中指出,“通过统治教化和族际通婚等多种形式,汉族的文化及文明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扩张力影响周围的少数民族。这股蓬勃的影响力并非刻意而为,但又不知不觉切切实实地在汉藏边疆存在着。”[23]23他把婚姻家庭的影响力与“统治教化”的社会影响力相提并论,至少说明族际婚姻在沟通不同文明及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发挥了重要的连接作用,无疑是汉藏文化交流与交融的典型例子。
西方人关注的第三类婚姻形式是由族际婚姻演变而造成的临时婚姻。在康区,如果一段族际婚姻由于外界因素的干扰而迅速中断,便转化成临时婚姻。在西人笔下,导致临时婚姻的既有战乱或時局动荡等外部因素,也有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内部因素。如戴谦和所记,“每当汉族士兵或商人撤离边疆的时候,总是有些藏族女子不愿意随丈夫搬回内地,于是城里留下了母亲和大量混血儿[23]23-24。同样,哈德亦有所载,“每当汉族军团需要转移驻地时,他们要么绝情地离开妻儿,任其忍饥挨饿,要么另寻其他士兵接替自己”。[22]22顾福安的回忆就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1911年,一支汉军从波密返回,队伍行至打箭炉,忽闻赵尔丰在成都遭难,军队急忙出城,留下100多名年轻藏族女子和70多名混血儿。”在他看来,“临时婚姻与其说是一种习俗,不如说是一种紧急事件……其危害即使不比一妻多夫制严重,同样也是严峻的社会问题”[20]19-20。
尽管在这些记叙中,西人用了“紧急事件”“危害”“社会问题”等字眼来描述女性在临时婚姻中所遭受的不利影响,刻意强调汉族男子的“绝情”与藏族女子被沦为婚姻牺牲品的悲情——这样的看法虽然有着事实的根据,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其实这也反映了藏族女性在婚恋关系中的自主权。在大量藏族男子入寺为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她们自由选择了与拥有“荣耀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的汉族商人和士兵结合;而当丈夫因故被迫撤离边疆时,她们亦敢于终止婚姻关系,自愿选择留守故土。这与同一时期汉文化中的“媒妁之言,夫唱妇随”形成巨大反差,说明在藏族性别文化意识中,没有传统汉文化强调的男女性别的主从规范。在婚恋方面,男女平等,藏族女子不必受制于男子。也正因如此,人类学家李安宅就建议汉族妇女应该效仿藏族女性,像她们一样拥有“缔结和中断婚姻关系的自由”“从男性的从属地位获得独立”[25]。
在探究康区多种婚姻形态共存现象的深层原因过程中,葛维汉的评析多有值得称道之处,持论比较平和而公允:
现在有不少观点认为藏人生性淫荡,缺乏基本道德。毫无疑问,藏人中确有不道德的行为存在,正如任何民族都有不道德的行为一样。然而,藏人亦有他们固有的道德观。无论是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或是临时性婚姻,他们都遵循当地的风俗并受到社会的约束。藏人有自己明确的道德规范,任何违规行为都会受到其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惩罚。[13]22
其论点颇得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精髓,这无疑也证明葛维汉对康区多样化的婚姻状态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体察。就多元婚姻形态的成因而言,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所指出的,“藏族婚姻形态的多样化,部分的是藏族社会观念的反映,部分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灵活性,同时也是藏族持续不断的社会变动的结果”[21]386。可见,在20世纪初,来自美国的葛维汉,他能不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左右,认为藏族多元婚姻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便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他对藏族婚姻形式所做的分析仍然比较客观,其观点依然显得较为中肯,而且颇有见地。
二、品性与阿佳:透视近代康区女性的切口
(一)品性
除了体质上出众的美貌,西人普遍认为藏族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特别能够吃苦耐劳,故而呈现品性之美。正如葛维汉所指出的,“每个家庭至少让一个儿子出家,男性多信佛为僧,生产劳动转移到女子身上”,甚至,在他眼里,“在吃苦耐劳方面,藏族妇女堪称现代社会的亚马孙族女战士。在藏族社会中,包揽下所有重活儿、累活儿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13]22不约而同的是,美国医生哈德在《藏族女性》中也写道,“在巴塘,庄稼生长过程中所有的农活全都由女性承担,男性只偶尔参与耕地或播种。如遇干旱季节,成年女性和小女孩都要去担水浇灌。”[22]23更令他们感到殊俗的是,曾在藏区考察的体质人类学家莫尔思发现,即便是生育期的女性也没有终止劳作:“藏族女性通常在劳动的间隙,找僻静无人处悄悄分娩,然后带着婴儿回家,第二天又带着新生婴儿照常出门去干活”[26]。应该说,这一英雄分娩行为与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 1981)所描绘的卡拉哈里沙漠昆人妇女独自在村外树丛里分娩的再生产习俗[27],颇有类似之处,而与汉人强调传宗接代的、精心照料的坐月子习俗构成鲜明对照。
显然,诸如此类的记录,既形象地刻画了藏族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符合汉文史籍所记载的社会现实:“西藏男子怠惰,女子强健。普通男子所操之业,在藏中大抵为妇女之职务”[28]。藏族女性“既主内又主外”的角色意识与传统汉族社会“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大相径庭,女性在社会生产各方面付出远超男性的劳动强度,“男逸女劳”这一鲜明的对比让远道而来的西人深为感叹。
在西方人眼中,藏族妇女不仅在田间牧场劳动,在家中操持家务,而且在担任苦力、支应徭役方面与男性并无差别。如游历过巴底巴旺的费尔朴就发现,他雇佣的藏族苦力挑夫,“既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包括儿童,其中一个14岁的少女背着35斤重的行李跟考察队一起跋涉了好几天。”[29]藏区的差役摊派,总是男女一视同仁,并无性别差异。叶长青也指出,“乌拉”是封建社会沿袭的一种以人畜劳役为特征的徭役制度,藏区分派的乌拉徭役,无论男女皆要承担,女性尤为辛苦。他甚至专门以《差乌拉的女孩》为题,赋诗一首,难掩一掬共情之泪:“幸运仙女是我的姓名,但我的命运是与又瘦又瘸的牲畜同住,挣微薄的收入……霜雹冰雪,日晒雨淋,拖着疲惫的身躯跋涉,抱怨无用,因为我是差乌拉的女孩。”[30]西人的这些亲身观察所见,与汉文史籍如《西藏图考》所记,并无二致,“土民之服役者,名乌拉,凡有业之人,勿论男女,皆与其选”,“其俗女强男弱,遇差徭辄派及妇人”[31]。不难看出,由于历史的积淀与佛教的盛行,藏族男子多入寺为僧,导致社会劳动力严重缺乏,藏族女性不仅要担负繁重的经济生产任务,还是封建赋税差役的主要承担者。西人的记录一方面忠实地反映了康区沉重的赋税徭役体系的运作情况,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辛苦操劳的藏族女性的关注与同情,从而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性研究日益增长的趋势。
(二)阿佳群体:近代康区女性的特殊样本
在打箭炉,有一种集旅店、货栈和商贸中介功能为一体的特殊机构,称为锅庄,主要为藏区商旅提供食宿、货物寄存、行情咨询、联系交易和汉藏翻译服务,其锅庄管理者一般为藏族女性,客商称其为“阿佳卡巴”,意为“尊敬的女主人”,简称“阿佳”。总而言之,“阿佳”特指锅庄的女主人。
近代西方人赴藏考察或传教,途径打箭炉,偶尔住宿锅庄,故有机会与锅庄女主人打交道。在交流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些阿佳精明干练、诚恳热情,其精神风貌明显有别于普通藏族妇女,因为她们不仅通晓藏、汉语言和康区各地的地脚话,且熟悉贸易行情,交结甚广,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作为藏族女性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虽说阿佳的总体人数并不多,但给近代西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较早记录打箭炉锅庄及阿佳的西方人是库珀和普拉特。1871年,库珀在打箭炉住店,虽是藏人开的旅店,但建筑风格却是汉藏结合式样,打理生意的是“一位30来岁清秀的藏族女子”,而她的丈夫以前是“明正土司手下的兵士”。库珀在此受到“女主人的热情接待”,对住宿非常满意。[14]2041892年,普拉特留宿打箭炉客栈,对住所的印象颇佳,如他所记,“我所居住的客栈非常地舒服,主人是位藏族妇女,她把生意打点得妥妥帖帖的。由于她的丈夫远在拉萨,她既是客栈的管理者,也是汉、藏语的翻译。她收入很多,家境宽裕”[15]136-138。
不过,作为住店的客人,实际上库珀和普拉特与女主人的交往毕竟十分有限,其二人仅是留下只言片语的介绍而已。只有到20世纪初,随着西方人与阿佳的接触逐渐增多,相关记载才渐渐丰富起来。这一时期对阿佳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其称呼的由来、办事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其中,对阿佳群体的观察和研究最为深入的是顾福安,他曾驻打箭炉长达35年,又深谙藏语。在探究阿佳称呼的由来时,在其代表作《“阿佳”与一妻多夫制》的开篇中写道,“A-gya”是藏语,意为“大人或首领”,在打箭炉,这个词有特殊含义,因为所有的阿佳都是女性。[20]18不过,有关阿佳一词的本源,娶藏族女子为妻的英国外交官孔贝在其专著《藏人言藏》中则有不同解读。在他看来,“Aja”不是藏语,仅在打箭炉使用,与藏语的“噶伦”或“伦波”相似,指官衔比王低,但比“本”高的首领。在查拉,有“王”、阿迦(Aja)、头人等官衔。阿迦与锡金的“卡基”或王的大臣类似。那48个家庭的后代被打箭炉藏人叫作阿迦。[32]事实上,对比这两种解释不难看出,孔贝所指的“48个家庭”即打箭炉的48家锅庄,而其笔下的“阿迦”(Aja)即顾福安所称的“A-gya”。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顾福安还运用西方适者生存的法则,对阿佳的办事能力进行了观察和评价,认为她们比其丈夫更善于打理家庭内外事务。在婚姻家庭之中,她们作为颇有魅力的一家之主,全权掌控家务,故其领导能力毋庸置疑。他还发现,阿佳的丈夫都崇拜其才能和智慧,他们甘当家庭主夫,照顾孩子。在婚姻家庭之外,阿佳代表了性格强势、有魄力、甚至有些专横的女性群体,尤其是富有的阿佳出行时,通常有大队人马跟随,甚至包括喇嘛在内。在宗教节日期间,她们比男性更加耀眼夺目,费尽心思地打扮出彩,让丈夫表达对自己的忠心和臣服。[20]19他对阿佳精明能干的办事作风有着颇为生动的描述:
每当提及阿佳,汉、藏商人都表现出极大尊重和钦佩。她们的商业能力丝毫没有妨碍其待人接物之道。无论做的生意有多大,有多重要,她们都事无巨细,从容应对。实际上,所有内地到西藏的茶叶贸易都经由她们双手,每年交易额达2000万两银子。这个职位不仅需要商业能力,还得有圆滑的处事方式。多数情况下,阿佳受过良好教育,能读写藏文,又精通汉语。如果生意做大,还涉及一些会计和算术的知识。无需多言,这一切她都能高效地应对。[20]18-19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佳教养良好,但其实绝大部分女性根本没有条件接受教育。正如麦克劳德在《藏区的教育》中指出,“寺庙是唯一的学习场所……康区的大部分俗人都是文盲。除了少数有条件的贵族家庭,女性的教育几乎被完全忽视。”[33]实际上,在当时寺院垄断教育、社会经济落后的环境下,除阿佳之外的多数藏族女性的教育都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旧的教育妨碍了妇女才智的成长与发挥。在旧西藏,教育为僧人所垄断,寺院即是学校,家庭妇女自然无法受到正规的教育。
只不过,凭借对锅庄商业的有效管理和婚姻家务的出色经营,阿佳才在康区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这样的社会地位,自然让远道而来的西人深感诧异,纷纷在著述中加以记载。1896年,英人伊莎贝拉·伯德在川西北旅行时发现妇女拥有显著的地位,她在游记《长江流域旅行记》中写道:“她们不仅享有与男人相同的权利,而且还受到相当的社会关注,她们随时都在享受她们的兴趣爱好。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是一名赶骡人或是一名土司。常常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自由自在地在一起,男女之间的社会交往完全没有任何束缚。”[34]
同样的,顾福安也对阿佳较高的社会地位颇有感慨与触动:
当我们想起围绕西藏四周的是许多把女性看成劣等生物的国家时,不得不说,阿佳拥有如此高社会地位确实引人注目。要知道,周边许多地方女性的地位甚至不如宠物。印度、突厥斯坦、中国等实行一夫多妻制,只有西藏有一妻多夫制。在突厥斯坦,根据伊斯兰教义,男人可娶四房妻子。在印度和中国,传统陋习禁止女性参与社交活动。然而,藏族几乎不受周边地区的影响,这也表明了藏区的偏远与隐僻。西藏四周高山环绕,人们过着独特又有趣的生活。至少在藏东地区,女性社会地位比较高,若当地人的精神生活也受其管理,她们将占绝对主导地位。[20]19-20
顧福安进而借助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就阿佳社会地位较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藏区位置偏远,不受周边文化影响,乃是造成其独特社会习俗的原因。然而,对于藏区女性社会地位较高的缘由,中国藏学家柳陞祺的看法则稍有不同,他在《西藏的寺与僧》中指出,“藏人之重视佛事,实不亚于科举时代士大夫们之重视功名。他们认为有资格献身于佛,斯为上品;至于世俗之务,已属低级。所以他们在家务方面,让妇女占一席地位,并不见得就是尊重女权。”[35]这就是说,从主位视角而论,藏族男人所追求和崇尚的在于佛事,俗务不入其眼,故而女性得以掌理世俗事务。由此可见,虽然顾福安的评析考虑到地理环境的作用,却显然忽视了宗教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不过,尽管他的看法并不全面,但其宏观的视角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后来的女性研究依然具有显著的借鉴意义。
三、从尼僧特殊群体解读近代康区女性
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出家女性逐渐成为僧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为佛教文化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公元8世纪,莲花生大师剃度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位比丘尼益西措杰,自此开启了藏地女性皈依佛门的先河。[36]1其中,信奉藏传佛教的尼僧,被尊称为“觉姆”,是藏族女性中的一个极为特殊的团体。
康藏地区寺庙众多,其中喇嘛庙多,尼庵少。近代西人很少见过尼僧,而进入尼庵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据目前所阅文献来看,关注这一尼僧现象,并有机会进入尼庵实地考察的仅有叶长青,他在其所撰写的考察报告《藏族的尼庵与尼僧》中,就尼僧的传说、居住环境、生活状态等方面进行了初步介绍。令人称奇的是,他对藏族出家女性的关切,竟然始于一则传说:“在西部藏区靠近印度的地方,有位尼僧主管着一处重要圣所,佛教界称她为‘宝石母猪。将宝石跟母猪相提并论的情况实属罕见,但藏人自有其解释。相传两百五十多年前,尼泊鲁斯人入侵,强行闯入圣所,正当尼僧身处险境,命悬一线之际,一群母猪出现,尼僧乘机混入猪群,化险为夷,躲过一劫”。尽管叶长青并不认可传说的真实性,但他从中读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藏人的宗教神灵可化身为女性,女性也可成为圣所的管理者”[37]62。因此,对于他来说,尼僧似乎是来自未知世界的神秘物种,相关故事和传说激发起他强烈的好奇心與探险欲。1923年,他终于获得机会探访了号称东部藏区最大的一处尼庵遗迹,并对其进行了翔实而生动的描述:
我们来到了一处被废弃的遗址。所有点点滴滴的迹象显示,过去曾有人群隐居在这既似兽穴又像墓坑的环境里。她们与世隔绝,远离尘嚣,宁可躲进黑暗而不愿暴露在光里……近距离观察这些毫不起眼的洞穴,很容易误认为是岩壁上不规则的凹陷。
然而,这些洞穴确是人类遗迹,既不是窃贼藏身的窝点,也不是流浪汉的床位,而是女性皈依者容身和修行之所。普通尼僧的住所通常是一个5×4×3英尺的狭小空间,毫无艺术感的设计,只是为了增加居住者的痛苦感受。逼仄空间不为舒适享受而建,但凡要添置书籍、炊具、或任何零碎物品,即便身材矮小的人也立生“罐装沙丁鱼”的拥挤感。尼僧每次出入都须弯腰躬身,睡觉时,要么像狗一样蜷曲,要么像佛陀一样盘坐,无法舒展平躺。狭窄的200平方码范围,据说曾有300位修行者。尼僧出家的缘由不得而知,但即便对看破红尘的厌世者来说,这样的条件也着实艰苦。[37]63
显然,他所见的尼庵遗迹应当属于群落尼僧的居所,因为他所描述的特征与当代学者德吉卓玛的研究发现相契合。德吉卓玛根据尼僧不同的修行和生存形式进行分类,将其主要区分为女活佛、业印母、住寺尼僧、群落尼僧、云游尼僧、苦行尼僧和住家尼僧等类型。其中,群落尼僧通常居住在偏远山区,共同修行,一起生活,她们的僧舍为“依山开凿的山洞,洞内空间很小,有一个小灶台和尼僧休息的地方,条件十分简陋”。[36]281所以,叶长青笔下“洞穴”般的僧舍与德吉卓玛所说的群落尼僧“依山开凿的山洞”,实为同一居住空间形态,故推测应为群落型尼庵。
1924年,叶长青又参观了甘孜的一座尼庵,这座尼庵坐落在海拔13000英尺的偏僻幽谷,远离其他村落。尼庵高墙耸立,大门紧闭,荒凉得犹如沙漠中的废墟。四周沉寂,“没有秃鹫嘶叫,没有血猎犬吠,也没有全副武装的岗哨”,却由“刚勇的女战士”用绳护住,将“有臭味的”俗人拒之门外。因为得到了主持的许可,他得以如愿进入这神秘之境,接触到这个“佛教意义上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出家人团体”。当时,庵内有106位尼僧,纪律严格,所有男性,即便是亲属,也不得穿过方圆3英里的“禁区”。[38]26-27
正因为如此,叶长青的《藏族的尼庵与尼僧》这份考察报告便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见闻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从尼庵出来,我抬头看见庙外兀立的岩石上,赫然一块碟形凹陷处有凝固血液和尸身碎片,空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当地向导解释说这是天葬台,是放置尸体的地方。尼僧所做之事,就是将尸体砍成碎块喂食秃鹫。”[38]65根据这则记录,甘孜的这座尼庵外部设有天葬台,除去日常的宗教活动,尼僧也兼任天葬师。然而,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天葬师通常由男性担任,既有僧人,也有俗人。因为由尼僧兼职天葬师的情况极为鲜见,所以他报道的情况较为罕见,故其真实性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由于离群索居、行事低调等,在西方人笔下的康区女性中,信奉藏传佛教的尼僧是他们接触和交流最少,却特色鲜明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与尼僧有限的交往与交流中,西方人留下为数不多的记载,反映了对康区女性出家人初步的认知和了解,以及对她们清苦尼庵生活的关注和同情。
四、结语:近代康区女性的社会地位——别样的女性研究视角
随着近代西方人在康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活动频率逐步加强,以及与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女性交往的日益增加,他们视野中的康区女性形象也日渐立体且丰满。在对女性众多的评价中,西方人不约而同地褒奖她们出众的美貌,认为康区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造就的女性不但体质健美,而且乐观坚韧。加之她们普遍具有吃苦耐劳、勤勉能干的品性,西方人往往不吝溢美之词来夸赞其迷人魅力,这无疑印证了藏族“康巴人区”的传统说法。
康区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多元化的婚姻状态也成为西方人兴趣所在,让他们印象颇深。在西方人眼中,印度、突厥斯坦、中国等实行一夫多妻制,只有西藏有一妻多夫制,藏族社会似乎没有周边地区的“夫权”问题,藏族妇女不仅恋爱自由、婚姻平等,且不必受制于男子。西方人把这一点归因于康区的偏远与隐僻。西方人尤其惊叹于阿佳这类在康区社会特殊的女性群体,认为她们泼辣干练,引人注目。对独特的一妻多夫制,西方人褒贬不一、各执一词:有的批评它是违背人性和文明进程的落后现象;有的则认为无论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是族际婚姻,藏族女性都遵循当地习俗。前者基于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观点严厉批判一妻多夫制为社会弊病;后者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包容,表现出对康区妇女多元婚姻选择的宽容和理解。
总而言之,西方人对康区女性的报道,特别是那些基于实地考察的客观见闻,无论其真实程度如何,都从侧面生动呈现了西方人视野中的康区女性之形象和特征,西方人笔下康区女性形象的勾勒与塑造,既反映出西方世界对东方康藏文明的认知和想象,也折射出近代西方社会对女权运动、女性研究等话题日益增长的兴趣和关注。虽说他们难免会有主观臆想的夸大其词,甚至进行萨义德东方主义意义上的充满浪漫和异国情调化的身体凝视,易于以其习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描述不可述说的他者。也就是说,他们极易将藏族女性幻化为“高贵的野蛮人”,以寻找一个堕落了西方社会的替代物,有时所说所论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种乌托邦想象。然而,即使在有猎奇性观看之成分的背后,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的确有局外人透彻的现象学观察,能够洞察到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诸多方面。
本文的研究表明,第一,以美、英、澳为主体的华西传教士或外交人员有关康区藏族女性的描述和分析,弥补了某些中文、藏文文献方面的缺失,为我们更加全面认知和了解近代康区女性补充了宝贵的素材。第二,这些考察与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局外人较为敏锐的他者眼光,无疑有利于我们发现康区女性研究中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线索。第三,从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说,这些记载和洞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不同的社会理论以及可资与当下比较的素材,故而有助于我们整体推进相关话题的女性研究。如,西方人笔下的那道康藏人区的靓丽风景线,究竟是东方主义的一种乌托邦想象,还是女性主义有关何为女人的普遍状况的一种解释?
注释:
①叶长青(J. Huston Edgar,1872-1936),1898年受中国内地会派遣来华。1910年加入皇家文会华北分会,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
②葛维汉(David C. Graham,1884-1962),1932年受聘于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到华西协和大学执教,任华大古物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等学会会员。
③莫尔思(W. R. Morse, 1874-1939),1909年来华,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的创办人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创始人之一。
④费尔朴(Dryden Linsley Phelps,1891-?),1921年受美国基督教浸礼会来华,在华西协和大学任教。1922年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
⑤顾福安(Robert Cunningham,1883-1942),笔名藏族人。1907年受内地会派遣来华。1926年被选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荣誉会员,为爱丁堡植物园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
⑥戴谦和(Daniel S. Dye,1884-1977),1908年受美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他所创立的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是华西地区第一座博物馆。作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要创始人之一,戴谦和历任学会秘书、会长及杂志主编。
⑦孔贝(G. A. Combe,1877-1933),1901年来华,20世纪20年代任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英国驻打箭炉领事。他娶藏族女子仁钦拉姆为妻。
⑧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Lucy Bishop, 1831-1904),英国皇家学会第一位女会员、旅行家。1896年在长江流域及四川西北部汶川、理县、马尔康梭磨旅行,并著有游记。
⑨另两大藏区分别是卫藏与安多,前者位于西藏的拉萨和日喀则一带;后者指青海除玉樹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区、甘肃的甘南州、四川阿坝州的部分地区。
⑩康定古称打箭炉,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高原古城,三国蜀汉始有打箭炉之名。
古希腊神话中的亚马孙族女战士,指高大强悍的女人。
参考文献:
[1]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M].黄颢,周闰年,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2]于式玉.藏民妇女的一生[J].边疆研究通讯,1942(2).
[3]于式玉.藏民妇女[J].新中华,1943(3).
[4]于式玉.介绍藏民妇女[J].旅行杂志,1944(2).
[5]张云.论藏族妇女的地位[J].西藏研究,1992(2).
[6]诺布旺丹,巴桑卓玛.藏传佛教的两种女性观[J].中国藏学,1995(3).
[7]马戎.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J].民族研究,2000(6).
[8]仓决卓玛.西藏妇女权利地位今昔谈[J].西藏研究,1999(3).
[9]刘正刚,王敏.清代康区藏族妇女生活探析[J].中国藏学,2005(4).
[10]YudruTsomu.Guozhuang Trading Houses and Tibetan Middlemen in Dartsedo, the “Shanghai of Tibet”[J].East Asi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view, June 2016: 71-121.
[11]YudruTsomu.Women as Chieftains in Modern Kham History[J].Inner Asia, 2018(20):107-131.
[12]J.H.Edgar.Tachienlu to Litang before the Chinese Conquest in 1905[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20(11):8.
[13]D.C. Graham.A trip to The Roof of The World[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30(12):22.
[14]T. T. Cooper.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 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M].London: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1871:216.
[15]A.E. Pratt, 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2:139.
[16]Mina Ririe.Letter from Kiating[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1904(5):113.
[17]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18]Charles Bell.The People of Tibet[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28.
[19]Robin Fox.Kinship and Marriage[M].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87.
[20]R.Cunningham.The A-Gya and Polyandry[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12(7-8).
[21]王尧,黄维忠.藏族与长江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387.
[22]Mina P. Hardy.Tibetan Women[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2(2):22.
[23]D. S. Dye.Some Impressions by the Way to Tachienlu[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6(9):23.
[24]任乃強.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382.
[25][美]比阿特丽丝·D·米勒.西藏的妇女地位[J].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3),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333.
[26]W. R. Morse.Tibetan Medicine[J].Journal of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26-1929:129-131.
[27]Marjorie Shostak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8]许世光,蔡晋成.西藏新志[M].上海自治编辑社印,1911(7):48.
[29]Dryden Linsley Phelps.An Expedition through Bati-Bawang[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September 1922:6.
[30]J. H. Edgar.The Ulag Girl[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36:12-13.
[31]黄沛翘.西藏图考(6)[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88-193.
[32][英]孔贝.藏人言藏[M].邓小咏,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117-118.
[33]R. A. MacLeod.Education in Tibet[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3(10):8.
[34][英]伊莎贝拉·伯德.长江流域旅行记:1896年英国女旅行家在长江流域及四川西北部汶川、理县、马尔康梭磨旅行游记[M].红音,杜永彬,等,编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380.
[35]柳陞祺.西藏的寺与僧[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50.
[36]德吉卓玛.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
[37]J. Huston Edgar.Convents and Nuns in Tibet[J].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2(5):62.
[38]J.Huston Edgar. Saints in a Buddhist Sense[J].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24(11):26-27.
——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