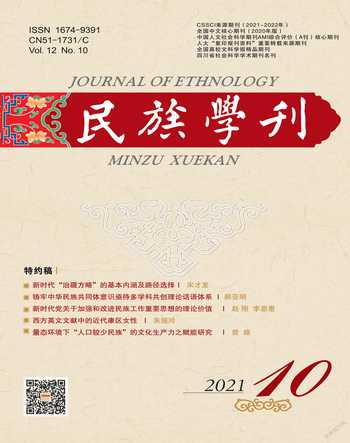情感表达与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
杨丽萍 赖程程
[摘要]以歌代言的壮族诗性传统的传承主体以丰沛的情感表达对宇宙、天地、山川以及圣靈的崇敬之情,也通过民歌演唱表达喜怒哀乐的情感。壮族歌者心之所系、情之所寄、梦之所萦、魂之所牵和灵之所托,皆同他们的心灵感悟和情感表达密切相关,他们的情感生活实乃壮族诗性传统得以传承与延续的人文根基。因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壮族民歌习俗的保护与传承,应当涵容世世代代壮民族的情感体验和壮阔情怀,通过体悟壮族的情感世界,探索壮族诗性传统的传承,领悟壮族诗性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核心精神,感知壮族诗性传统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与心灵寄托的文化智慧,唤醒日趋淡漠的诗性文化记忆,铭记壮族经历过的欢乐与忧伤,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建立起符合天地人伦本性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悟与表达机制,凝聚民族复兴的文化源泉。
[关键词]情感表达;壮族文化;情感人类学;诗性传统
中图分类号:I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0-009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诗性传统与文化建设的整合研究”(14BZW170)、广西民族教育研究发展中心“壮族文化传承与广西民族学校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2020MJY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丽萍(1968-),女,广西全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教育;赖程程(1985-),女,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与教育。广西桂林 541004人类学作为以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始终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关注人类的精神领域、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从泰勒的“万物有灵论”到博厄斯的“文化相对论”,文化人类学始终蕴含着对自然万物和“他者”文化的敬畏与尊重之情。马凌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描述了原始部族在库拉贸易以及其他生活习俗中的欢快、恐惧等情绪[1]9。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情感有可能是灵魂与生俱来的,他深入论述了安达曼岛民死亡仪式中“哭”的文化现象,分析“哭”情感宣泄与亲属制度的关联,还认为社会关系的形成、巩固或是断裂正是源于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倾诉。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述了不同文化语境中“愁怨”“羞愧”“愉悦”的情绪展演。[2]222米德一直关注人类的烦恼、浮躁与忧虑的情感问题。她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探讨了男女不同性别的“温情”“平静”“粗鲁”“嫉妒”“凶蛮”“暴戾”的情感特征。[3]14西方其他人类学家也或多或少也论及研究对象的情感世界,但是,多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研究。直至20世纪70年代,情感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相关研究关注人类不同族群的感官经验、情感体验、情感表达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1986年,卢茨(C. Lutz)和怀特(G. M. White)合撰《情感人类学》一文,正式提出情感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motion)的学术范式。[4]古巴裔美国学者的露丝·贝哈在《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一书中,将个人情感体验融入田野之中,把民族志与回忆录巧妙地交织起来。[5]韩国民俗学者崔吉城以“哭泣”作为情感表达的一种民俗事象,描述“孩子的哭泣”“歌谣中的眼泪”“离别的眼泪”“爱国者的眼泪”和葬礼、婚礼、巫术中的哭泣以及男女不同的哭泣现象。“感情的表现幅度以及涉及死亡的感情流露,与各自社会固有的制度和观念息息相关,即使说感情具有人类普遍性,却也不得不承认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里具有多样性的体现。哭泣文化的差异不是悲哀之类感情的差异,而意味着通过哭泣去表现的结构有所不同,也就是表现方式的差异。”[6]胡红在《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古琴文化》一书中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分析了情感与艺术的关系,梳理了传统和现代人类学的情感研究。[7]宋红娟提出“定向性情感(orientative feeling)”“显性情感类型”“隐性情感类型”等概念,提倡在有关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中加入情感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关注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及其日常生活体验。[8]
人类情感的孕育和萌生离不开个体感官机制的运行,但是,其文化根源是地方性知识和特定区域族群的传统习俗和社会情境。就自古以来就有以歌代言的传统的壮族而言,壮族的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通常以诗性语言作为情感表达的媒介,将诗歌吟咏作为人与神、人与人、个人与社会表达情感的重要途径。对于壮族民歌研究领域,数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是歌谣源流、刘三姐与歌圩的关系、民歌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化价值、民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而壮族诗性文化研究的深化发展,有必要借鉴情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探析壮族民歌蕴含的情感世界,分析壮族歌者的情感生活与壮族民歌习俗的互为表里关系,进而探讨情感体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关联,思考情感表达与诗性传统延续的制衡机制。
一、壮族诗性主体情感的体验与宣泄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民歌文化的核心内涵是源于对“喜、怒、哀、乐、忧、思、伤”的情感体验和诗性表达。诗性主体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中,周遭发生的事情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都会让人生发或积极或消极的复杂的情感体悟。不同民族的歌者为何而喜乐?为何而怒恨?为何而哀伤?为何而忧思?体现了各自不同的人文情怀以及情志所寄寓的重心。而不同的歌者如何借助诗性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情感?如何运用隐喻、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有何艺术效果?则有赖于不同歌者身处何种诗性文化语境及其诗性修养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纵观壮族诗性传统的衍生与延续的总体历程,壮族民歌中的情感体验涉及天地人文与国恨家仇,涉及生老病死的人生旅程,壮族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体验在公共性文化空间以及人生礼仪等诸多语境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宣泄。
(一)“喜乐”情感的体验与表达
人的喜悦之情的产生源于人的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愿望得到实现、郁闷得到宣泄、寂寞得到排遣、苦累得到消解,理想成为现实的高兴、快乐、欢欣、愉悦、开心、澄澈、明朗、清爽、轻松而笑逐颜开的身心感受和体悟。与“喜乐”相伴生的是满足感、成功感、愉悦感、超脱感、自由感。人生为何而喜?为何而乐?既是情感特征与民族心理的表达,也是特定民族宇宙观、价值观、信仰观的体现。
从壮族诗性文化传统审视,壮族是乐观的民族,是善于用诗性语言表达喜乐情感的民族。壮族历史上流传着浩如烟海的表达“喜乐”情感的韵文作品,直至当今壮族各地民歌的传承依然以“喜乐”作为至为重要的吟唱目的,“以歌贺喜”“以歌为乐”成为至关重要的儀式表达与情感体验方式。在创世史诗中,壮族先民为天界、地界和人间秩序得到安顿,为动物、植物、人类各得其所而喜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壮族歌者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而欢欣鼓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壮族歌手编创了大量的民歌表达欢庆之情。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壮族歌者为愿望得到实现,需要得到满足,情感得到表达而感到高兴,每逢新生命诞生、新婚缔结、新居落成的仪式场合,常应邀为主家唱庆贺歌,充分表达主客各方的喜悦心情。譬如,壮家新生婴儿降生之后,女婿携活鸡等礼物至婆家报喜,外婆闻知后喜不自禁地唱道:“昨夜做梦游仙坡,今早起来见喜鹊;听见女婿来报喜,外婆笑得嘴难合”,为成为外婆而感觉到“甜过冬蜜滴心窝”;待到三天后,外婆携亲属到男方家贺“三朝”,主家唱:“家堂添丁好风光,全家老少乐洋洋”,外家回:“亲戚女友齐贺喜,保佑外孙得安康”“今天我女当妈了,光彩也照我外婆。”小孩满月时,外婆送背带,主客同唱《背带歌》:“昨夜桌上灯花开,一股暖风进心怀;吉利日子来到了,今早喜迎外婆来。”外婆回:“月琴挂在画眉嘴,唱得阳却到处飞;红花背带背孙女(子),背出一只鹧鸪媒。”双方都借助循环往复的对答,尽情表达喜悦的心情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良好祝愿。待到小孩满百日,主家也邀请外家和亲戚唱《百日歌》,小孩满一岁,则唱《对岁歌》。
在传统社会,壮族青年男女喜结连理,实为人生一大喜事。虽然女方在出嫁前,会约请同伴唱《哭嫁歌》,表达依依不舍以及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会伤心落泪,但是,在婚礼上,新郎新娘双方家庭以及亲友都以喜悦的心态,以美妙的民歌祝福新郎新娘琴瑟和鸣,幸福美满,百年偕老;在祝寿仪式上,寿星“全家老少乐融融”,亲友祝福寿星“长寿如同村边榕”“家中儿孙乐陶陶”“祝福阿公身体好,鹤发童颜捧仙桃。”这些《祝寿歌》令人倍感欢欣。在新居落成之后,壮族歌手编歌庆贺:“主家建成美华庭,满堂吉庆喜盈盈;六亲九眷齐来庆,添福添寿又添丁”。[9]
“求乐”是人类的本能,壮族民众“求乐”“娱乐”“取乐”的方式源于他们的内心世界,“以歌为乐”是祛除苦恼、烦闷、无聊、悲伤等负面情绪的灵丹妙药,所以,壮族歌者自觉不自觉地在走路时唱,干活时唱歌,在就餐过程中尤其是仪式场合的进餐过程中也唱歌。人们习惯于在开心时唱歌表达喜悦的心情,在不开心时唱歌以排遣烦恼的情绪,在苦中作乐正是体现了壮族的文化智慧。
(二)“怒恨”情感的感知与宣泄
儒道释所强调的“仁厚”“宽恕”“隐忍”“戒嗔”“冷静”等价值观,意在消解“愤怒”“怨恨”“恼怒”“愤懑”的情感。儒家主张以仁厚情怀对待世间万物;道家倡导超越“喜怒哀乐”的束缚而臻至“恬淡朴素”“无念无欲”的超脱境界;佛教“五戒”“八戒”的核心意旨是“诸恶莫作”,杜绝“贪、嗔、痴”。然而,“愤怒”“怨恨”“恼怒”“愤懑”“仇恨”等情感是人类天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利益受到侵害,生存受到威胁,人性受到践踏,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萌生愤怒之情。“怒与恨”情感的生存缘由复杂多样,表达方式和调控机制千差万别,“怒与恨”同“善与恶”的对应关系更是变化莫测。在情感人类学的视域中,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不同群体在不同的语境中为何而怒?对谁发怒?如何表达愤怒之情?在日常生活中,面对良善之人动辄发怒,是伤天害理的行为;当遭受凌辱而没有愤怒与怨恨之情,则是懦夫的心态。
当国家遭受侵害,民族生存危机面临挑战,面对入侵之敌而“怒发冲冠”,是一种英雄气概。壮族历史上经历并体验过无数的国仇家恨,壮族社会生活中也有许多土豪劣绅以及其他作恶多端的人,他们的胡作非为理所当然令人发指。唐宋以来,壮族地区实施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历代王朝和土司的敲诈勒索让壮族饱受苦难,民不聊生,不得不怒火中烧,揭竿而起。近代以来,清王朝以及地方军阀对壮族民众横征暴敛,加剧社会矛盾,走投无路的壮族民众与其他民族同胞面对内忧外患、制度腐败,丧权辱国,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义无反顾地以满腔悲愤和国仇家恨,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斗争当中,坚决抵抗国外势力的侵略,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求生存,也由此留下了不计其数的表达怒恨情感的文学作品。
怒与恨的情感隐含在人的本性之中,“以歌代言”的壮族民众用歌声表达对来犯之敌以及官僚恶霸的横行,进行淋漓尽致的倾诉,这种情感表达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流露,而且更多的是社会心理的外显。怒恨情感离不开个人的内在体验,而其社会反响以世代传承则有赖于大众的认知和认同,广大民众有相似的情感经验,方可对这类民歌产生共鸣,使得这些民歌获得长久的艺术生命。
(三)“哀伤”情感的萌生与倾诉
人生在世,命运多舛,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困扰,面对生活中时常发生的无可挽回、无法弥补的亲人故去、家道中落、人心险恶,世态炎凉,人们自然而然萌生悲哀、伤痛、愁闷、无奈、伤心的情感。壮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表达“哀伤”情感的民歌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和主题:其一,为失去亲人而哀伤;其二,为生活凄苦而哀伤;其三,为命运不济而哀伤等。譬如,壮族哭丧歌在特定的充溢哀伤氛围的场景中演唱,曲调低缓,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歌师善于运用哀婉的曲调,抒发失去亲人而悲痛欲绝的哀念之情,勾起念亲之情,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哀嚎痛哭,同时提醒后人莫忘前人的养育之恩,“今夜不哭待何时?”
在广西宜州市安马乡古育村,廖士宽根据自身无嗣之苦用勒脚歌编成的《哀叹身世之歌》在艺术上堪称五言十二行勒脚歌的优秀之作。该长歌严格按照勒脚歌的格律编写,合乎平仄以及押腰脚韵的规律,后人读来感受到深切的悲怆之情。梁士宽生前将歌编好,请人刻于墓门之上,成为至今发现的唯一用古壮字刻在石碑上的壮族长篇抒情悲歌。该长歌共15首,原诗120行,用勒脚重复回环的唱法则变成45首,180行。全诗讲述了作者年轻时艰苦创业,渐至丰衣足食,娶了两房妻室,皆无生育,收养两个养子,为其娶妻生子,这两个养子却忘恩负义,离开廖士宽。该长歌叙事与抒情相交融,比喻形象,抒情手法独特,唱来回肠荡气,感人至深,今人唱来依然催人泪下。
壮族哀伤之歌抒发了强烈的悲哀、凄婉、怨忿的感情,是一种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心灵倾诉。在类别上总体上可分为家庭悲歌、苦工悲歌、孤儿悲歌、童养媳悲歌、盲人悲歌、寡妇悲歌、鳏夫悲歌等等,悲歌中怆天呼地、痛人心肺的沉痛呼号,是不幸命运悲剧的深沉体验,壮族哀伤情感既内在于个人,又是社会文化和歌咏传统演化的产物,从中可以感知壮族个人情感和集体情感的抒发路径。这种哀伤情感的生发、升华、转换既是个人生命历程和内心世界的反映,也是壮族民歌作为言情表意手段对于身心体验的情感反应。
(四)“忧思”情感的启悟与言说
忧虑与思念是人类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壮族民歌以精妙的诗句表达,对亲人、对朋友、对家乡以及国家表达忧思、忧愁、忧伤、忧患、忧虑、忧郁之情,以诗性言说,抒发对爱恋对象的思念和思慕的情怀。与汉族将“心”作为思维和情感表达器官有所不同的是,壮族人认为,人的喜、怒、哀、乐、忧、思、伤等情感是以“喉咙”作为感知与表达器官的。刘向《说苑》中《善说》记载的《越人歌》的最后一句“堤随河湖”,“河”便是壮语中的“喉”,原歌的“喉中感受”,译成汉语就是“心中感激”。
人类忧虑与思念的情感源于个体的生命经验,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不同的生活场域萌生不同的心理感悟和情感体验。不同个体因年龄的变化而生发不同的忧虑与思念。对于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担忧的是如何找到意中人,对异性的思念会随着生命的成长以及自我感知度的增强而愈加情深意切。到了中老年阶段,更多的是为家人和家属的诸多事务以及自身如何安度晚年而忧虑。远走他乡的人会情不自禁地萌生“乡愁”,同样,儿行千里母担忧,彼此的思念衍生出许多动人心怀的优秀文学作品。
富有诗性传统的壮族民众对“忧虑”与“思念”的言说,自然而言具有鲜明的诗性文化色彩,善于运用诗性隐喻以及比兴手法表达忧思之情,常常忌讳直接的倾诉,而用曲折委婉的意象表达念之深和意之切。广西横县各地流传的民歌《十忧娘》在新娘出嫁后的第二天在新郎家演唱,男女双方约请歌手代表新娘和新郎对唱。女方表达忧虑的重心是女儿出嫁后,再也不能常常见到母亲了,担忧嫁到贫困家庭,“日来月往忙碌去,夜间无米难思量”,而担忧女儿无田种,“哪样有米来养娘”,担忧家婆凶恶,家公挑剔,大嫂刻薄,担忧没屋住,“北风过岭又来凉,点灯一盏伴明月,寒霜雪落难亏娘”,担忧与同队别离:“十忧尽怕离同队,一离同队而离娘;眼看青天双泪落,偕人作乐又何尝。”男方歌手则对岳母的种種担忧给予解答,力图解除女方家人的种种担忧,劝导女方“路头遥远莫凄凉”,表示要努力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不要为赡养爹娘而忧心,家人之间和睦相处,姐妹情深如同江水长流,而“老人讲多莫见怪,万望后代福禄强”,要相信总会有栖居之所,因为“雀在树上还有对,谁人露宿在村场”。[10]
壮族民间更为常见的表达“忧思”主题的民歌是青年男女在定情之后的“思情歌”“苦思歌”。壮族聚居区山水田园为年轻人自由表达感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每逢歌节,动人心扉的歌声常在山间地头回荡,在这些生机盎然的山野中,坠入爱河的青年男女可以发自内心地倾诉对恋人的爱慕和思念之情。这类民歌用夸张的手法,表达对恋人的深切思念。譬如,新近在云南省广南县八宝镇发现的记录在日常用具上的图符式的壮族歌书,这些意象性图符蕴含着800多首民歌,用“拿袜”“肠相结”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相思与苦恋之情。“拿袜”图符蕴含的民歌是:“妹心不在焉,拿袜又忘鞋;妹袜在梯下,妹鞋在云下”。该诗“不直言相思,却选取‘拿袜忘鞋这个细节,表现女子因为思念情郎而心不在焉的情态,真实有趣。”[11]
与“肠相结”图符相对应的歌词是:“念妹泪不止,肠子拧成绳。拧成绳八股,八股不离散,绷紧如弓弦。爱慕妹美貌,年年盼厮守。”[11]用“肠子拧成绳”作为比喻,以生理上的纠结表达思念的苦楚。而“泪水湿枕头”图符则用夸张手法表现思念之深切与痛苦:“泪水流成泉,泪水流成潭。泪水浸湿枕,沾湿一身衣,洗三年不褪。”[11]这种夸张的言说感人至深。
二、诗性传统延续的情感人类学反思
壮族诗性传统的整体结构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说理长诗、抒情长诗以及短篇歌谣等韵文体作品,这些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核心精神可谓包罗万象。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不只是壮族民歌的搜集以及数字化保护,而是一种心灵体验模式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性主体有不同的情感世界和情感表达方式,若要延续壮族诗性传统,还需要借助情感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反思壮族民众情感世界的当代变迁,尤其需要领悟神圣性的敬畏心理,体悟家国情怀,以情感培育为根基,建构壮族诗性传统延续的新机制。
(一)情感表达机制的变迁与壮族诗性传统的断裂
不同历史时空中不同的群体的内心世界迥然相异,吟咏的主题自然而然有所不同。不同时代的诗性主体有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路径。对于“以歌代言”的壮族民众来说,“心之所想”便是“歌之所唱”。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当壮族歌圩逐渐失去“倚歌择偶”的功能,人们对歌不再是为了追寻人生的伴侣,不是为了缔结婚姻以组建家庭,而是为了情感的娱乐,“思念”情感的表达并非真实对恋人的眷恋,虽然表达思念的诗性语言和艺术手法没有变化,但是,唱“思念歌”更多是为了开心,或许还是调侃,通过唱山歌打情骂俏,是为了给日常枯燥的生活增添乐趣。演唱思念歌不再受到歌手年龄与婚否的约束,已婚者在许多场合可通过演唱思念歌以及其他情歌,让自己和听众获得心灵的愉悦,获得心理的满足,而非为了强化亲密关系,更不指望由此在生活中建立真实的依恋之情。
此外,在传统社会,壮族先民和壮族歌者更关注涉及洪荒岁月天地形成的宇宙事,在国家更替壮汉民族由对立走向和谐共处的过程中,壮族诗性传统伴随着社会动荡以及历史的沧桑巨变,以诗性语言记叙了爱恨交织的天下事和家国事,而历史进入到现代科学知识越来越普及的时代,人们的视思之所及变得更为宽广和辽阔,但是,诗性表达主体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却日渐变得狭小,天地起源与宇宙运转之类的主题逐渐被遗忘,家国情怀与民族命运的省思亦日趋淡化。这种遗忘和淡化将对壮族诗性传统延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神圣情感的体验与诗性传统的保护
与其他民族相类似,壮族先民对大自然的认知也经历了从朦胧到清晰的渐进式演化的复杂过程。在壮族社会发展的蛮荒岁月,人们只能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界的不同,只能借助幻想的方法去认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只能通过想象,解释日升日落、电闪雷鸣、草木枯荣的缘由,认为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天体的运行,人与大地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物我互渗、共生共荣的神秘关联,由此衍生出壮族先民们的神圣情感。
在许多具有神圣性的仪式空间中,壮族神职人员用多种语体描述天、地、神、人的起源以及万事万物的来历,篇幅或简或繁,或长或短,日常生活中的讲述通常用神话叙事的方式想象宇宙的起源,而在仪式空间中,壮族神职人员用歌咏的方式演唱传统经书。前者通常被当做神话作品,后者则是创世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的存在形式不同,而情节结构和内在文化意蕴却大同小异。
以姆六甲、布洛陀、布伯、盘古、伏羲兄妹为主体的壮族创世史诗因为地域差异和演唱者不同,流传着复杂多样的抄本,有五言体、七言体、勒脚体或者嵌句等形式。虽然形式不同,而内在的精神意蕴都是凭着各自想象和文化智慧,借助诗性的幻象,遨游在广袤的宇宙间,忽而在天上,忽而回到地上,穿越上、中、下三界,充满着奇特瑰丽的想象。壮族的宇宙观不同于西方文化将世界分为“自然”与“人文”“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的二元结构,也不同于佛教的“今生”与“来世”、道教的“仙界”与“俗界”划分模式,而是借助诗性想象构拟了天、地、水、山、木、花、人、鸟、蛙以及其他自然物彼此关联而浑然一体的富有壮族特色的宇宙观、天人观,这种想象和认知经过了漫长的萌芽和衍生过程。因为:
“现代人类的成人认知不仅产生于发生在好几百万年的时间段内的基因事件,而且还产生于文化事件,这些文化事件发生的时间跨度是数十万年,同时,也产生于个人事件,这些个人事件发生在个体发育的时间尺度上,其时间跨度是几万个小时。”[12]
直至21世纪,壮族民众在很多仪式场合吟诵《布洛陀经诗》,自发地参与布洛陀祭祀仪式。壮族崇拜布洛陀等神灵,既是对神灵神通广大的功力的膜拜,也是怀着感恩之心,对神灵恩德表达怀念与崇敬之情。因为布洛陀作为壮族的人文始祖,他开天、造地、造人造火、造米、造牛、造人间万物,安排自然界的秩序和人间秩序,人文世界由此得以化成。
值得深思的是壮族表达生老病死的人生事以及表达喜怒哀乐忧思伤的情感事,成为亘古不变的核心主题。但是,壮族普通民众尤其是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壮族年轻人总体上未能领悟壮族先民对大自然中的天地神灵的敬仰与崇奉之情,并不了解壮族创世神话和创世史诗中蕴含的天地观和宇宙观,也缺乏对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以及动植物的基于神性思维的想象和认知。因此,壮族诗性传统的保护,离不开让越来越多的壮族人传习仪式专家在神圣空间所吟诵的涉及洪荒岁月天地形成的宇宙事、沧桑巨变的天下事等主题的神圣性民歌,学会传唱以《布洛陀》为代表的创世史诗,了解以创世史诗为核心的经典作品所蕴含的对大地神灵的崇拜心理和神圣感情。
(三)家国情怀与壮族诗性传统的赓延
壮族家国情怀和历史记忆还蕴含在壮族民间流传的浩如烟海的民间歌谣之中。这些历史歌谣记叙了明清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壮族聚居区烽火连绵的历史事实,大量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题材的历史歌谣,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壮族的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
壮族歌咏习俗是民族的心声,是民族思想感情外化的结晶,素有以歌代言歌唱传统的壮族人民,用歌声伴随历史的脚步,从远古走来,表达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的真切感知与爱憎情感,壮族民歌创作和诗性文化传统忠实记录了壮族社会的演进历史。
从历史记忆和家国情怀的角度审视,壮族人民为了民族革命而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同胞同生共死,共赴疆场,义无反顾,体现了坚强意志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壮族以中华民族认同为根基的国家认同得到进一步强化。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的小康社会建设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追寻,壮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国家认同与情感归依更为明晰。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代壮族歌者生活在和平年代,耳闻目睹的是新世纪斑驳陆离的现代生活,对于诗性传统中描述的蛮荒岁月、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对暴政的抗争,大多已经成为壮族文学史上的历史记忆。年轻人通常与饱受磨难的前辈们拥有不一样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民族英雄的敬仰之情。相当一部分年轻歌者的情感世界,民族身份认识模糊,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出现“空壳化”“标签化”的现象。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学理念,强调情感是诗歌的根基,诗歌只有用丰沛的感情扎根才能稳固。因此,传承和弘扬体现家国情怀的壮族民歌传统,有必要借助强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认知,培养壮族歌者的家国情怀,自觉地以真挚的感情,延续体现壮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心理的诗性杰作。壮族年青歌者需要拓展文化视野,深入体悟前辈歌者的情感世界,传唱的民歌不仅是戏谑性的情歌,还应关心天下事、家国事,培育家国情怀,传唱以《布洛陀经诗》《莫一大王》为代表的民族史诗以及其他具有经典意义的叙事长诗、说理长诗、抒情长诗,由此体悟壮民族的充满喜怒哀乐忧思伤等情感的精神世界,涵养壮族诗性传统的深厚人文根基。
三、结语
歌唱源于人的内在情感的深切体验,情感体验和表达既是歌唱的动力,同时也是诗性基因和诗性传统得以世代延续的文化根基。人类心智对变幻莫测的外部世界的反应以及人精神的觉醒,显现出人类生命意识中的个人感知经验。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指出:“当今之世,伴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不舍追求,精神的痛苦叠加而生,……就在这危亡之际,个人却随意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疑问成了最大的特色,不仅对上帝、科学和社会主义疑云漫漫,而且对任何东西的信仰亦都荡然无存”。[13]因而,面向未来的壮族诗性传统的延续以及壮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的深化发展,有赖于深度理解情感人类学的理论精髓,从浩如烟海的壮族诗性文化发展史中理解壮民族情感世界和情感表达机制。通过深度理解壮族诗性文化蕴含的民族观、国家观、伦理观、人生观和喜乐观,激活壮族诗性传统中蕴含的想象、比兴、象征、隐喻、节奏和韵律等诗性文化基因和审美表征手段,让现代壮族文化传承主体领悟壮族诗性传统的文化内涵和核心精神,感知壮族诗性传统中蕴含的情感表达与心灵寄托的文化智慧,唤醒日趋淡漠的诗性文化记忆,铭记壮族经历过的欢乐与忧伤,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建立起符合天地人伦本性的人與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体悟与表达机制,凝聚民族复兴的文化源泉,推动壮族社会的进步和人生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英]马凌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6.
[2][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222.
[3][美]M.米德.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M].宋践,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Catherine Lutz & Geoffrey White.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51986:405-436.
[5][美]露丝·贝哈.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M].韩成燕,向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韩]崔吉城.哭泣的文化人类学——韩国、日本、中国的比较民俗研究[J].开放时代,2005(6).
[7]胡红.情感人类学研究与古琴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135.
[8]宋红娟.情感人类学及其中国研究取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6).
[9]覃九宏.传统礼仪山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167.
[10]甘书明.茉莉仙子[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340-341.
[11]黄舒娜.壮族八宝歌书及其价值[J].广西民族研究,2017(1):97.
[12][美]迈克尔·托马塞罗.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M].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23.
[13][美]M.米德.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M].周晓红,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