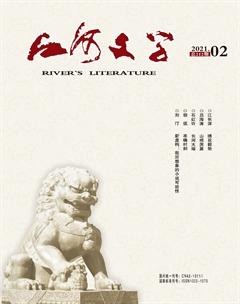余笑忠的诗
余笑忠
凝神
这一刻我想起我的母亲,我想起年轻的她
把我放进摇篮里
那是劳作的间隙
她轻轻摇晃我,她一遍遍哼着我的奶名
我看到
我的母亲对着那些兴冲冲喊她出去的人
又是摇头、又是摆手
剥豆子
那年年成不好,夏天干旱,秋天多雨
从田边地头拔回的黄豆禾,有的
已经烂了。后面的几天
照天气预报说的,也没有一个
像样的日子
如果有好日头,那些豆荚会裂开
我和弟弟、外甥在母亲身边围坐
为微薄的收成
重复简单的劳作
我故意把手抬高一些,这样
从豆荚里剥出的每一粒豆子
落进筐里,显得掷地有声似的
这样,每一粒豆子
好像有了不一样的份量,就好像
不止是我们四个人,听到这声音
暴雨中的低语
暴雨一遍遍洗刷着玻璃窗
我坐在窗前一动不动
远处,沉闷的雷声催促着什么
玻璃窗的另一面,愤怒的暴雨
犹如热锅中的螃蟹
夜里,闪电以其快速的明灭
告诉我们不要和广大的遗忘对视
夜雨像莫名的悔意。在我的梦里
晚归的父亲拖着浮肿的双腿
石头,带着它的伤痕
从高处滚落
我要瘦下來,像喜马拉雅之鹤
清空肠子,净其骨骼,敛息静气
为翻越
连绵的万仞雪山
红月亮
想起和父亲在大河里看见红月亮的那个傍晚
那是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我们的腹中
空空如也。红月亮
升起在东边的山头上
为什么它变成了红色的?
带着这个疑问我和父亲望着月亮
不同于父亲和我
不同于流经我们的河水
在少年的我看来,孤悬的月亮是没有源头的
那一轮红月亮
那一刻,全世界的河川都归它
但只有流经我们身边的河水
在不一样的月光下,泛起小小的波澜
雨
每一场雨中,我看到的只是
雨的背影
它明亮的前额另有所属
我看到的只是拖泥带水
旋即进入大地的雨
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何其短暂
每一场雨,都在为我们探路
那些被车灯照亮的雨
有着被惊醒的小兽的面容
而你,正是其中的一个
我所经历的每一场雨
是千万个不知深浅的你
一起赴汤蹈火
引水
取水之前,往压水泵里
倒上一瓢水,我们学着顺势按压
井水汩汩而出,这么快
就涌泉相报
后来我们用上了自来水
水龙头更加慷慨
只是再也无从知晓
水,来自哪里
已无饮水思源之必要
但要谈起井水,我还是会想起
黎明时分弯腰按压水泵的动作
少年的我曾大汗涔涔
如果遇上这样一个井台
我知道,我仍然会跃跃欲试
让井水灌满两只木桶
我知道,还是那样,在担水之前
——我甘愿卑躬屈膝
庙堂
在旧宅的荒地上,婶婶盖了一间庙堂
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小的庙堂
一人勉强可以容身
只有香案,没有偶像
她礼敬的只是祖先
因此,它甚至不能称为庙堂
于我婶婶而言,它显示了一种存在:
“在我有生之年,我必躬身祈祷
在我有生之年,它将洁净如新
我将一天天变小、变暗,它将
美轮美奂。”
夜读张岱又闻布谷
子夜时分,又听到布谷啼鸣
在我们的城市夜空
让我记起我是一个农人
这一年痛失春天
这一年多出一个闰月
农历纪年徒增一次月圆
枕上听布谷,声音时高时低
让我记起昔有西陵脚夫
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
念无以偿,痴坐伫想曰:
“得是梦便好!”
这半年,城郭人民,裹足不前
犹似陪他痴坐。但无论如何
我不称今年为庚子
我不称布谷为杜鹃
雍容
你见过单腿独立的鹤。
“鹤立鸡群”?你知道,那只是
一个比喻,鸡和鹤,从不会同时出现。
我熟悉这样的场景:母鸡领着一群小鸡,
鸡娃太幼小,像简笔画那样可以一笔带过,
它们不停地唧唧喳喳,像对一切
都连连叫好。
母鸡步态从容,抬起的一只腿,
缓慢地着地,这使它看起来
也像单腿独立般优雅。
每每急匆匆从它们身边跑过,
少不更事的我,完全不懂得母鸡的焦灼,
那时,我乐见鸡飞狗跳……
在朝西的房子里
从来如此,在朝西的房子里
冬天,迟来的阳光像余光
你也可以与喜阴的植物为伴
它们有修长的茎,簇拥的绿叶
但省掉了花
有时阳光洒在上面,像浇花
乐观
路边两棵小树,每逢仲春
浓密的枝叶合拢了
像一道拱门
我乐于看到
人们弯腰从那里经过
如果,这只是园林工人偷懒之故
那就让他们继续偷懒
如果,是他们手下留情
就请他们继续手下留情
冬天,那里畅行无阻
人们无需弯腰屈身
但我觉得那里仍有一道拱门
就像果树,在我们眼中
一直是果树
哪怕它光秃秃的
就像你,哪怕你一再加深
我的昏迷
责任编辑:邱红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