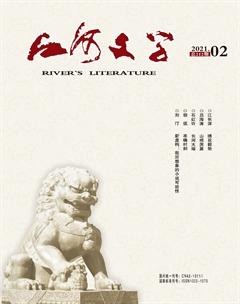绣花鞋垫(短篇小说)
江长深
1
那年冬天,铺天盖地的雪下了几天几夜。山野和村寨被雪浪统治着,白茫茫一片无声无息。惯于夜行的狗瑟缩在巷里不敢出声,长长的七里街清冷异常,如水寂静。突然,夏荷家的大门敲响了,咚,咚咚,咚咚咚,急,但不失節奏。惊醒的夏荷一头撞进秦青石的怀抱,手缠脚绕与之融为一体,不让青石起床开门。
“这冷的天,这雪的夜,没有急事谁会敲门?”青石说出的话是轻的,拍夏荷的前胸后背的动作也是轻的,话完,红花被窝一脚掀开,起床的动作坚决有力。
“乱纷纷的世道乱纷纷的人,何况这冷的天这雪的夜?”夏荷言轻语细,两手两脚依然青藤绕树,柔软而略显执著。
咚,咚咚,咚咚咚,敲门声更急。青石缠绕不住,边起床边说:“世道乱,走投无路的人才多,能帮不去帮,能救不去救,别人心安我不安,别人害怕我不怕。”
话至此,夏荷奈何不得,手脚无力再缠绕,慌忙寻衣找裤,陪青石起床。
大门打开,寒风雪气直冲进来,像毛刺一般钻进他俩热热的身子,青石和夏荷各打了一个寒战。门口站着的是学堂教书的李先生,文弱瘦静,投在风雪中的黑影身单影孤。
“青石,有件事你能不能帮帮忙?”李先生看他俩哆嗦,话出口有些迟疑。
“帮。”青石也不问什么事,一口就应了下来。他虽然没做过李先生的学生,但敬重李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小时侯娘经常教导他:树高无低鸟,贵人无贱事。
风吹过,夏荷嗅到寒冷中夹裹着一股血腥味,再嗅,血腥来自李先生。她生出隐隐的不祥预感,胃里酸水直翻腾,她强制噎住,喉管也硬了。她不说话,只用指甲在青石的掌心里深扎下去,再深扎下去,皮肉都要扎破了,青石却不理会,包容地大手握着小手,握住了她跳动的心,也握住了她心里想要说出的话。
“李先生,屋里暖和,进屋说吧。”大门吱呀一声,全开,风雪成团跟进,灌满一屋。
“几句话,就门口说吧。”李先生立在风雪里,三言两语道出了因果,黄安保卫战失败了,跟他一起参战的好多兄弟牺牲了。现在战事紧急,丰棺厚葬这些兄弟已不可能,但生死一回,也算是惊天动地,钉口薄木棺材遮避身体不为过吧——李先生对青石说:“我知道你是个本分的手艺人,新婚又不远,这事不难为你,行,你跟我走,不行,你回我走。”李先生的话入情入理,收放自如。
黄麻起义的事,青石知道一些。李先生领头举的事,活捉了国民党县长,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农民政权,县北一带还开始斗地主分田地。可是,穷苦人当家作主的好日子才开个头,被赶跑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反扑了。他们纠集汉口、信阳,金寨的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合围过来,围剿县城的起义部队。黄安保卫战打得很胶着,很残酷,也很传奇。民间有小道消息传得神,说李先生的起义部队看懂了国外的一位大胡子写的书,得了天助修了神功,一个个刀枪不入来去无风,敌人四面合围一个人也没围住,只收获了一座空县城。这支得天助有神功的队伍早就不见了踪影。让青石不明白的是,如此神奇的队伍,怎么也会有失败?怎么也会有牺牲?这打打杀杀的世道真的好残忍,好可怕。
李先生没听见青石响亮地回应,却看见了青石身边哆哆嗦嗦的夏荷,心中的迟疑继续回转。他不想为难这对燕尔新人,说了声打扰你了,对不起。转身就走。
秦青石在满脑子神兵天将的传说中缓过神来,对着白雪中长长的黑影喊了声:“李先生,我来了。”他急匆匆赶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夏荷说,“荷,等着我。”
看着雪地上一行义无反顾的男人脚印,夏荷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了一声“慢”,就迅急退回内屋,取出一双毛皮鞋、一双绣花垫跟了过来,“脚还赤着呐。这冷的天,这雪的夜,快,快换上。”
青石垫上绣花垫换上毛皮鞋,深深一拥夏荷,话又重复在她耳边:“荷,等着我。”
雪夜的白,似白非白,临门而立的夏荷目光追寻着一前一后两个黑影在茫茫的雪白中渐渐远去,渐渐小去,直到天空地旷,直到无影无踪。
2
青石这一去就没有回来。
多少年后一个相似的雪夜,夏荷听雪无声一夜未眠。她素衣素裤来到门口,对着白皑皑的山、白茫茫的道深情呼喊:“回来啊——青,青啊——回来哈。”
夏荷的声音,沉重、悲凉、凄婉,催雪花落,惊宿鸟飞:“你的手艺那么好,渔樵耕读、百年好合那复杂那美丽的图案你都能雕能刻,李先生交办的事早该办完了吧?回来哈,青。家还是你走时的样子,床是新婚的床,被是新婚的被,你刻在床头的百年好合还鲜着,我绣在被面上的百年好合也暖着,就等你回呐。”
夏荷听娘说过,再大的人也有丢魂失魄的时候。人丢了魂魄,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记忆,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要至亲至爱的人喊魂呐。何时丢的何时喊,在哪丢的在哪喊。荷希望她的呼喊能让青丢失的魂魄回归,记起曾经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找到回家的路,回到她的身边来。
夜没有应答,风有了回声,雪花旋起来,直往门里扑。夏荷木木的,也不退避,迎着风雪站着,雪花融进睁开的眼,冰冰凉凉的,冰得心胸寒彻,冰得泪水长流。雪花融进张开的嘴,嘴哆嗦,喊出的话也哆嗦:“回来啊——青!山高路远你莫怕,寻着声音回来哈?回来啊——青!天南地北你莫怕,寻着声音回来哈?你走时说过的话我记得,你叫我等,我天天等。我叫你回,你怎就不回呐?”
不知何时起,秦伯静静地站在夏荷身后,夏荷喊一声:“青,回来啊——”他就应一声:“回来了。”夏荷喊一声:“回来啊——青。”他就应一声:“回来了。”夏荷大声喊,他大声应。夏荷小声喊,他小声应。夏荷哭着喊,他哭着应。直到哭声惊醒了孩子,哭着喊着要爸要妈,秦伯就不应了,叹出一口气,改了话题:“别喊了,荷,回吧,回吧。喊了这些年,喊了这些夜,是死是活也没个音讯,命长命短求不得,缘分尽了求不得。还是听我一句劝,趁着年轻,走一家吧。望儿是青石的血脉,也是老秦家的传承,你能带你带,你不带我们带,负不了你,亏不了他。”
夏荷听了,摇晃着头,话仍然轻细仍然固执:“伯,青走时说过的,荷,等着我。我听青的,他叫我等我就等,一天不回等一天,一年不回等一年。等到青丝老,等到白发生。”
看着一天天清瘦一天天憔悴的夏荷,秦伯无奈何。他把秦家的后生召到厅前,说:“兵荒马乱的时局,乱了规矩没了章法,内里有好孬递不出去,外面有是非也传不进来,憋死个人啊。好端端一个人跑出去,一晃四五年了,是死是活,也没个音讯。等是等不出结果的。你们不能躲在家里,得走出去,一边做手艺一边寻人。心要细一点,嘴要多一点,脚要勤一点,是人是鬼总得有个了结。荷还年轻,我们老秦家对她要有个交待,望儿一天天长大,我们这些长辈也得给他一个说法啊。”
老秦家是木工世家,秦伯是家长又是掌门人,他的话没有人不听。后生们凭着一手好活计,半年时间走遍了大别山,走遍了鄂豫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带回的多是些半信半疑的传言:传黄安保卫战失败后,李先生的起义部队坚持在木兰山打了几年游击,在一次反围剿战役中,几近全军覆没。传李先生为掩护部队转移,不惜暴露身份吸引敌军,殊死战斗几天几夜,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军活捉,抓进了南京监狱,至今生死未卜。传残剩的队伍冲出鄂豫皖,转战川陕边,在秦岭大山中发展壮大后,响应党中央号召,北上抗日去了。部分老弱伤残,安排在民间,以打工卖艺维持生计,等候战略转机。
与青石有点关联的线索也有一条。秦家后生在巴中城的一条街市上看到了一些零散的具有鄂东特色的手工家具,刀工手法出自老秦家家传。细而再访,还在这些手工家具中看到了渔樵耕读、百年好合的木板雕刻,而这些木板雕刻与青石新婚木床上的雕刻如出一辙。后生顺着这条线索找到店铺老板。老板说:是有一个鄂东匠人在他家呆过,人年轻,木工手艺出奇得好,看啥雕啥,雕啥像啥,这些雕刻正是出自他手。
这消息让夏荷听到了希望,更坚定了等下去的决心。
3
直到新中国成立,青石还是没回来。
战火熄灭后的七里坪街家有几人无,房有几间空。新政府成立后工作人员逐家逐户登记失散人员,走访军人家属,慰问烈士亲人,十里长街几乎家家都走到了,唯独没到夏荷家中来。
夏荷不解,上门去问究竟。民政科员小孙解释说:“目前我们收集到的军方和地方的所有资料,都没有关于秦青石同志的任何信息。你能提供相关资料和相关证人吗?”
夏荷想起那个冰封雪拥的夜晚,想起了形单影孤的一个人,说:“祠堂教书的李先生算不算证人?”
小孙一听大惊失色:“妹子,快莫说,快莫说。李先生被捕后生死成迷,有消息说是被我党派出的锄奸队镇压了。秦青石同志若与其他人扯上关系还好说,成不了好人起码算不上坏人,若与李先生扯上关系,要么就是死人要么就是敌人。这消息不传出去犹可,传出去,你和你家的日子不好过,小望儿一生也没有出人头地的光景啊。我们都是七里街的老街坊,我不害你。你今天说的话我听当没听,知当不知,不向外人重复一字。妹子,我可警告你,你的这张嘴日后也得把严封死,任何人,任何时,任何地,打死也不能再提啊。”
夏荷一听,心有万千不解,但不敢再多说一字。
也不知秦伯是怎么想的,他不顾七十岁的高龄重背木工工具箱孤身闯荡川陕,半年后空着两手回来,倒在床上一病不起。生命垂危时,他把夏荷召到床前,说:“兵荒马乱的年月,七里这条街上走出去那么多人,能回的风风光光地回了,不能回的风风光光地写进了青史。青石是好是坏不明不白,是死是活不知不晓,天大的灾祸我们老秦家认了,但不能连累你,不能害你。听我一句劝,趁着年轻走一家吧?你还年轻,日子还长着呐。”
夏荷眼中满是泪水,她不敢看秦伯,只把目光定定地看着门外那条蜿蜒伸去的山路,话极轻婉意极稠浓:“伯,我三媒六证嫁给秦家,贫富不移,生死无悔。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青能回,我是青的人,青不能回,我做青的鬼。”
夏荷先是铁着心铁着嘴硬撑着,说着说着就撑不住了,泪水浸着话流成了河:“伯,我不要风光也不要青史,我只要青活着,只要青回啊。”
秦伯一声长叹,再没有后话出来。
4
秦伯带着遗憾走完了风雨人生,同樣走完的还有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
有民政科员小孙的警告在先,夏荷不敢在公开场合为青石喊魂了。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已的房间设了一个秘密的招魂坛,坛上供奉着一尊观音像,像前摆放着香炉蜡坛、摆放一些时令特产。平常的时日不燃香蜡火纸,她只是默默地站在招魂坛前,泪在眼中流,话在心中说。每到十五月圆夜,不管多忙多累她会净手静心,上香燃烛,然后毕恭毕敬地跪在观音像前,求菩萨保佑青石平安,保佑青石不生病痛,保佑青石能早日归来。青烟低绕,蜡烛泪流,观音就在眼前,她在默默的对视中倾诉着心底的思念与祝福。她相信青石,相信他的手艺能够给她幸福一生,相信他们的婚姻能天长地久。
夏荷与青石因手艺结缘。青石是木工,手艺致精致秀,特别是雕刻,随便一块木头,经他的手一摸盘拿捏,就是惟妙惟肖的景致。学堂扩建成功,他送了一幅渔樵耕读的屏风,见多识广的李先生看了叹为观止。一向恃艺清高从不恭维别人的父亲在夏荷面前大为赞赏,说,看人看手,看手看心,这娃儿日后了不得,了不得。
夏荷从父亲的评价中记住了青石。
夏荷的父亲也是手艺人,治国济世的大道理不懂得,居家过日子的小道理却明镜似的清楚。置身乱世,权贵的显赫如海水潮汐朝夕生变,富人的钱财也如烟云流水聚散无痕,都依靠不得。如果学精了一门手艺,不怕世道横生变故,不怕贼人惦记心中,日子总能平平安安地过下去。所以秦家上门提亲,当着媒人的面,夏荷是心应嘴不应,父亲是心应嘴也应了。
夏荷的绣活也了得。她乘着八抬大轿进秦家,给秦家每人送了一双自绣的鞋垫,用针、配色都有讲究,图文、寓意也各有追求,有福禄寿喜,有长命百岁,有金玉满堂,有王侯将相,人人见了人人喜欢。巧合的是送给青石的那双,人物、花鸟,意境、氛围竟与青石刻在婚床上的图案不谋而合。青石喜出望外,在挑开她的红盖头之前,捧着她的手看了又看,亲了又亲,与她说的第一句话与父亲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看人看手,看手看心。
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百废待兴。娘家的后生们把身手置于更大的舞台,裁缝铺开到了北京上海。红红火火的七里坪裁缝铺暗淡关张。夏荷就在自家门口支起一块小木板,给街坊邻里缝缝补补做些零散活儿,糊身上衣糊口中食,糊望儿的书本学费。
夏荷在娘家虽然没有掌柜坐台,但自小耳濡目染,女工活儿样样精湛。街坊送来的布料,剪谁的衣缝谁的裤她只看谁一眼,不度量不比画,试样和尺寸就埋在心里,剪裁缝制心到手到,挑花绣朵灵动真切。过几天来试衣,男儿穿在身上庄重大方,女儿穿在身上水嫩花俏,没有人不高兴,没有人不喜欢。劳动得到认可,酬劳费用少不了,但极随意,有钱也可,无钱也无妨,一个南瓜几棵白菜,心到意到就够了,她从来不在多少厚薄上计较。
那年月物资短缺,布匹凭票供应,衣裤做完,剩下的边角余料也珍贵,夏荷从不浪费,拼拼凑凑,缝缝补补,一幅袖套,一双鞋面,一方手帕就出来,看着这些多出来的物件,主人哪能不开心,不高兴。她的门面窄,案头小,活儿总是做不完。
夏荷心细手巧,能拼能凑的物件多,但细心人发现,她从不拼凑鞋垫。如若有人问起,她从不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回一句:我做出的这些小东西不好吗?你不喜欢吗?
听了这些回话,再好奇的人也不好往下追问。
5
春天过了是秋天,夏雨初停飞白雪。日子虽是无常,但终在季节的变换中匆匆而过。
夏荷门前的那条路,修了改,改了修,曾经的蜿蜒蛇行已变得笔直宽广,曾是隔在山外的风景如今历历呈现眼前。三月杨柳青,五月杜鹃红,八月桂花香,十月枫林秀。季节易变,夏荷的心不变。她白天坐在案前,看眼前的路,看路边的景,看过往的人,心里想得多,心中的话也多:“青啊青,不转的山也转了,不转的路也转了,你怎么就转不回来呐?人老了,眼花了,你刻在床头的百年好合看不清了,我绣在被上的百年好合也褪色了,你再不回来,荷就没有心力心气等你了。你再不回来,荷就不能做你的人,只能做你的鬼了。”
门前山高,门前路远,门前花开花落,门前春去秋来。夏荷守着案头,双眼痴痴地望着,把话说在心里,把泪也流在心里。
没了父亲,缺少家庭主角,对望儿的影响还是有的。从学校到社会,每走一步,都有表格要填写,家庭成员不能省略,父亲何年何月从事何种工作无法绕过。有一年煤矿招工,七里街道推荐了他,望儿手捧政审表格犯了难,父亲这栏怎么填?填历史清白,招工干部问:“你父亲失踪多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能算清白?”填历史清楚,招工干部又问:“你父亲是好人清楚还是坏人清楚?”望儿无话再说。
望儿是知事明理的,委曲只吃在心中,泪水只流在肚里。他感激七里坪街道把机会给了他,政审没通过,他不怪爸妈不怪指导填表的招工干部。他默默地把表格收回,一把塞进衣袋,手在衣袋里撕啊掐啊,一张表格化为一团白雪。
七里坪街在血雨腥风中浸泡了半个多世纪,街坊们见过太多的生死,也历经过太多的悲欢,青石的历史是清白还是清楚并没有往心里去,他们仍按自身的节律生活着,按自身的好恶爱憎着,一有招工上学的好事儿,望儿还是同街坊的其它儿孙一样得到推荐。只是经历过那次失望,望儿就暗自掐断了飞翔的翅膀,对着远方那片尉蓝的天空敬而远之。看着母亲一天天老去,而案头的活却越来越多,他就从母亲的手中接过了剪刀。
6
青丝白发一甲子,青石仍然没有回来。
当年近九十的夏荷和七十多岁的望儿怀揣着四川通江烈士陵园一张宣传画册从七里坪街出发时,天台山的枫叶红得正灿烂。娘儿俩一路颠颠簸簸到达通江,连绵的巴山早已白雪盖头。雪山之下新落成的通江烈士陵园碑林肃穆,雪落无声。望儿搀扶着夏荷走进烈士纪念馆,在无名烈士遗物展厅找到了陈列着绣花鞋垫的展柜,年轻的女讲解员应邀向他俩讲述了关于那双绣花鞋垫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期,主力红军北上后,留下一批伤病员在一老乡家养伤,被叛徒出卖后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万分危急之时,有一个人举枪冲过来与敌人正面交火,引过了敌人的全部火力。红军伤病員安全撤离,那人却被敌人的乱枪打死,头颅被割去邀功领赏了,尸体甩在乱坟岗。医院院长安顿好红军伤病员后,赶回来为无名英雄处理后事。他发现英雄着的是便装,除了贴身衣袋里藏有这双绣花鞋垫,再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物件。
简短的故事很快讲完,讲解员看见两位老人眼圈发红,关切地问了一句:“二老对这双鞋垫感兴趣,多次来电、来信问其详情。今天又亲自冒雪前来,莫不是与这双鞋垫有着特别的渊源?”
夏荷先是点头后又摇头。她躬下身把眼睛贴近展柜玻璃看了看,伸直腰让望儿捶了捶,然后掏出手绢擦了擦眼,再次躬下身,重把眼睛贴近展柜的玻璃。这回,她足足看了十多分钟。望儿的腰也躬下了,嘴贴在夏荷的耳根上,暗暗地问:“娘,像不像?是不是父亲出门时你送的那双?”
夏荷双眼离开了展柜玻璃,慢慢伸直腰,默默地摇了摇头,表情失望至极。
望儿有些不忍,他掏出宣传画册,一会儿看看画册上的照片,一会儿看看展柜里的鞋垫,催说:“娘,再看看,再过细看看。”
夏荷轻叹一声,说:“儿啊,娘用心做出的物件,十年百年落眼便认得。不需再看了,这不是娘手出的东西。”
这时,一直默默站在一边静观事态发展的馆长走了过来,十分热情地把两位老人扶进贵宾接待室,一杯热茶过后,开始了如下对话:
“二老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亲眼看看这双绣花鞋垫?”馆长的话是关切的,但不乏追寻探究。
“是的。我娘无意间从我们七里坪街一位游客的画册中看到了这幅鞋垫的照片,觉得很眼熟,就把这张宣传画册讨下来,要我寻寻这幅鞋垫照片的来历。我按照画册提供的联系方式多次与你们沟通,但无法确定画册上的鞋垫就是我娘年轻时绣的。我娘放心不下,一定要亲自过来看看。”望儿的回答真诚而实在。
“老人家,你已经看过了,展柜里是你绣的那双吗?”馆长关切地问夏荷。
“像,但不是。”夏荷的头摇了摇,回答很干脆。
“老人家,能说说你那双绣花鞋垫的特别之处吗?”馆长的眉宇间隐隐流露出一丝期待。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绣的针法不同,走线的序法不同,线色的配法不同。”心有所失的夏荷把话说得轻描淡写。
“老人家,能说得具体些吗?”听完夏荷的话,馆长觉得他们馆内又一个未解之迷已露出端倪,长久的期待将有结果,他迫不及待地追了一句。
屋内空调暖,窗外白雪飞,尽管眼前的鞋垫不是她心中那双,但见物思情,夏荷的心一下子回到了七十多年前,回到了三更灯火五更寒的夜晚,干净简洁的绣房,明亮的豆油灯下,一个圆圆的竹篾箩,一把炫丽的五彩线,一叠干干净净的家机布,倾注着她的所有用心:“我的那双绣花鞋垫,周边绣的是同心针,一针双线,用的是金丝线,绣的是并开并走的万寿纹;中间部位绣的是交心针,红绿两色相交,先红后绿,绣的是红绿回应的龙凤纹;鞋垫正中绣的连心针,线是真丝钱,针是发丝针,针眼小,针脚密,首尾连结,环环相扣,绣的图案是百年好合。”夏荷娓娓地讲着,看似平静,看似圆熟,但她的心在澎湃、在撕裂,那错杂游走的针针线线似在她心尖穿过,巨痛无痕,血流无声。
馆长听呆了。他深知这双鞋垫意义非凡,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倾注老人如此用心!
夏荷还沉浸在记忆中,她的手象征性地指了指门外展厅,继续说:“展柜里的那双,线的色彩不错,图案绣的也不错,就是针法不对,色彩排列的顺序也不对。”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馆长不仅听出了这双绣花鞋垫的精彩与奥妙,而且听出了渗透在精彩与奥妙里的那份稀世情缘。他知道深藏于一双鞋垫近百年的秘密即将展开,他既期待又恐惧,既惊喜又悲痛。他轻轻地击了击掌,藏在内室的那位讲解员应着掌声走出来,先在二位老人面前深鞠一躬,然后将手捧的一个红木漆盒递给馆长。馆长起身接过,缓缓地打开盒盖,走到夏荷跟前,语轻情重:“老人家,你看看,这双绣花鞋垫与你绣的那双如何?”
夏荷一落眼,目光就直了:百年好合!百年好合!百年好合!人物、花鸟,意境、氛围全是她的独创,用针、配色、起走、转合正是她的用心!她抢过红木漆盒抱在怀里,语无伦次地说:“我的,不,青的,是那个大雪夜我送给青的,新皮鞋配新鞋垫。望儿,望儿,这就是你父亲的东西啊。你父亲,青啊青,你让我找得好苦好苦啊,青。”夏荷深拥着红木漆盒,边哭边说,“青啊青,你一句话,三个字,让我等了七十年。七十年啊,青,你风筝脱手,音讯全无,原来你在这里。我的个青啊——啊,啊,啊——”
故事来不及讲述,哭声伴着泪水奔流,在烈士纪念馆汹涌澎湃,搅起绕梁的回音,悲怜惨烈,惊天地泣鬼神!
7
雪,还在下。远处延绵起伏的秦岭一身素白,苍茫静谧。
客车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缓慢爬行,断续的青烟化在白雪里,水墨一般浸润飘逸。公路崎岖险峻,三里高架桥,五里大山洞,客车爬得昏昏囊囊有气无力。到冬天了,车上的乘客不多,三三两两地散落各处,或闭目养神,或无聊地翻动着手机,一个个昏囊而疲惫。
夏荷和望儿依偎着坐在车的后排边角处。夏荷把通江烈士陵园管理处重新复制的百年好合的绣花鞋垫紧贴胸口,双眼定定地看着车窗外飞卷的雪花,看着远处白雪皑皑的秦岭,她在深情呼喊:“青啊,回家哈。”
望儿紧握着母亲的手,轻声应答:“回来了。”
“青啊,山高路远你莫怕,回来哈?”
“回来了。”
“青啊,有名没名你莫怕,回来哈?”
“回来了。”
“青啊,七老八十你莫怕,回来哈?”
“回来了。”
“青啊,是伤是残你莫怕,回来哈?”
“回来了。”
……
离开通江烈士陵园时,馆长带着她们娘俩参观了无名烈士墓园。
风大雪大,一望无际的无名烈士墓碑像银河中闪烁的星火,在茫茫白雪中发出温暖的光芒。馆长立在白雪中,话很真切很动情:“老人家,真遗憾,你们不远千里来寻亲,我却无法告诉你们,哪一块碑石下埋的是你们的亲人秦青石同志的英骨,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躺在这每一块无名碑石下的都是像秦青石一样的优秀儿女,都有着秦青石一样精彩而传奇的人生。他们生与秦青石一样伟大,死与秦青石一样光荣。你们可以将任何一块碑认定为秦青石碑,他活在你们的思念里,也活在所有人的心目中。”
馆长说完,望儿对着茫茫白雪上垅起的一片碑林跪下了,这个七十多岁的老男儿第一次失声痛哭:“父亲,七十年,望儿来看你了。”
哭声如雷,在无名烈士墓园上空震响,如林的碑石被哭声击中,在寒风中庄严肃穆。雪花无声飘落,一阵风来,雪雾经天纬地。
看着雪地里长跪不起的望儿,夏荷在低声自语:“青,听见没有,你的儿喊你了,回家吧,青。七十年异地他乡,爱你的儿,爱你的妻来看你,来接你。今天,就跟着爱你的儿爱你的妻一起回家吧。”
……
客车一声长鸣,驶进又一个长长的隧道,隧道兩边灯影昏黄,车内加倍暗淡,母子俩呼应的声音也随之暗了下来,一声声如曲如歌,一声声如诉如泣——
“青啊,山高路远你莫怕,回来哈?”夏荷双手抱着绣花鞋垫,喊声小了。
“回来了。”望儿搂着母亲瘦小的身躯,回声也小。
“青啊,有名没名你莫怕,回来哈?”
“回来了。”望儿听到的只有母亲的胸音,他用胸音应答。
“青啊……”
“回来了。”胸音也没有了,望儿看到的只是母亲的口型,他用口型应答。
“……”胸音没有了。
“回来了。”
“……”口型也没有了。
“回来了。”
呜——呜——客车从长长的隧道驶出,一道霞光从东窗射进来,车内霞光一遍。望儿看看依偎在怀中的母亲,已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责任编辑:林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