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查尔斯·赖特诗歌中的“地方”*
肖小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提 要】“地方”是美国当代诗人查尔斯·赖特诗歌创作的重要媒介和主题。赖特的诗歌创作是记录其记忆的独特形式,而“地方”则成了他打开记忆的方式。诗人毕生所作均为抒情诗或者说非叙事诗,但“地方”却让他的非叙事诗在整体上架构起一部宏大的叙事性个人自传。在赖特的诗学精神中,人应以谦卑的态度师从“地方”,学习“地方”的精神,寻找可以救赎自己的光。
美国桂冠诗人(2014-2015)、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国家图书奖获得者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 1935-)以其独特鲜明的风格而著称。诗人将其毕生的艺术精力和才华专注于“地方”(place)和“风景”(landscape)之上,批评家乔·墨菲特(Joe Moffett)在其专著《了解查尔斯·赖特》(Understanding Charles Wright 9)一书中说,“赖特著作两大反复性主题为:精神(spirituality)和地方(place)。”他在总结学界有关赖特研究的成果时认为,“批评界关于赖特的评价集中在他专注于与地方相关的永恒主题以及当今生活中精神的意义两个方面”(Moffett 2008:9)。另一批评家威力亚德·施皮格尔曼(Williad Spiegelman)认为,地方是赖特诗歌中精心设计的背景(backdrop)。(Spiegelman 2004:172)赖特本人在接受专访时也不断重复阐述,“基本上,我的写作围绕三样东西:语言、场景和上帝的意志”(Wright 2001:121)。赖特所谓的“场景”实际上是一个诗学层面上的概念,它既具体又抽象,具体的一面体现在真实的地方和景物。因此,总体说来,“地方”在赖特诗学精神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是赖特诗歌研究不可回避的路径。关于“地方”,截止目前,学者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一是因其地理属性,“地方”可以忠实地反映诗人作为美国南方人的文化身份(Moffett 2011:121)。二是通过“地方”的具体实物性描写,诗人意在创造神秘或虚无的精神性存在(Costello 2001:325-345)。三是“地方”在赖特诗歌中起到背景或舞台的作用,诗人借以表达他的日常生活、困惑、追求、过往经历和对未来的畅想。更重要的是,诗人在此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自我与灵魂深处的自我进行有趣的交换(interesting exchange)(Arcus 1998:562)。上述三种论述的确都不无道理,但大多都是基于诗人的局部创作甚至单个作品。当我们把视角覆盖至赖特生涯的整体创作风格上时,可以发现,“地方”像一条中轴线,将诗人的全部作品无形中串联在一起。尽管他的诗歌几乎都是非叙事性的(non-narrative),但在阅读中能清晰地感知作者的成长经历、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甚至他个人的社会关系等,读者仿佛在读一部完整而丰富的个人传记。究其根源,“地方”在其作品中扮演叙述者的角色,代替作者讲述个人既往的历史和情感;换句话说,赖特的诗歌某种程度上说是其个人的回忆录,而“地方”既是这部回忆录的原点,又是它的终点。赖特对“地方”的理解别具一格,他一方面消解了“地方”的日常普遍性意义,另一方面,成功地赋予了“地方”新的内涵甚至新的职能。因此,从赖特的整体创作来把握其诗歌中的“地方”不仅有助于挖掘“地方”的新意而且将更好地领会他的创作思路和艺术精神。
1.生命是另一个“地方”的记忆
人们普遍认为,记忆是个人联系自我,提升自我,审视自我与世界关联的方式,它是个人身份的标记,是打开我们灵魂的科学钥匙。“我们可以通过探究记忆,发现它的事实,然后可以征服灵魂的精神领域。”(Hacking 1995:200)在艺术世界,记忆激荡人的情感,激发想象力,人们根据记忆中的物象和场景,可以提炼美,创造精神境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2020)曾说:“假如我的确是一个诗人,我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甚至在某些看起来并不美丽的时刻。但是最终,记忆把一切变得美丽。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即是将情感、回忆,甚至对于悲伤往事的回忆,转变为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巨大好处在于,我们从不将它完成,我们总是处于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之中。”有学者甚至认为,“记忆就是对当下态度的建构性辩护”(constructive justification)(Bartlett 1932:208)。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情感世界有别,认知能力不一,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各有千秋,那么每个人记忆世界里的内容肯定各不相同,呈现记忆的方式也会各成形态。法国记忆学专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其《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表示,我们每个人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回忆过去。而早在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就记忆的特征表示说,记忆总是和意象联系在一起(Aristotle 2001:171)。对诗人赖特而言,记忆总是和“地方”关联。“我们的生命,似乎是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的记忆”(Wright 2011:152)。换句话说,生命就是一种记忆积累的过程,诗歌创作是其记录记忆的独特形式,而“地方”则成了他打开记忆的方式。
赖特长达60 余年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他个人记忆开放的过程,他的10 余部诗集就是他生命记忆与艺术思想的结晶。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各种地名十分醒目,它们不仅在艺术思想和精神情感的表现力上占据着突出的地位,而且对读者来说在理解和领会诗人的创作意图方面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有些甚至可以从诗人部分诗集与诗作的取名上就能揣摩其用意。1990 年诗人出版的诗集《塞奥尼亚》(Xionia)的标题是赖特曾经的居所名称,原房东给房屋起名为“爱奥尼亚”(Ionia),后来诗人与妻子在该名字前特意加了个字母“X”以示区别。诗集中的诗歌均是赖特在“塞奥尼亚”房屋居住期间内完成。诗人以自己的住所之名来冠名诗集,用意显著。对他来说,那是他个人生活中一段特有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弥足珍贵。诗人1995 年出版的《奇克莫加》(Chickamauga)诗集之名是一座小镇的名字,该镇位于田纳西州查塔弩加(Chattanooga)附近乔治亚山脉的北边,1863 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曾在那里爆发过一场著名的战役。诗人还以它为题专门创作了一首小诗,他在解释该名称时曾说:“《奇克莫加》一诗是用来表达一种非常抽象的历史概念。我给该诗集命名的具体原因是,那是我曾祖父在内战受伤的地方,我希望能以此来建立某种联系,某种家庭的联系”(Denham 2008a:37-38)。显然,“奇克莫加”一名隐含着两种不同的记忆,一是诗人个人的家族记忆,二是国家与民族的集体记忆。无论哪一种记忆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生命书写。诗集《阿巴拉契亚》(Appalachia)之名对诗人来说也有着特殊的含义,阿巴拉契亚既指北美洲东部南北走向的一座山脉,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域之名,赖特曾在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对那里记忆深刻,感情尤为深厚。他在访谈中解释该诗集命名的原因时说,“对有些人来说,阿巴拉契亚可能是天堂的反义词,但我生长于此,我爱这里。我往往将西北卡罗拉州、东田纳西、南弗吉尼亚、阿巴拉契亚的所属部分视为天国”(Denham 2008b:138)。赖特还以“死者的阿巴拉契亚之书”为名创作了系列组诗,共六首。赖特所生活过的阿巴拉契亚,当时是美国南方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批评家曾用“经济被剥夺了的地方”(economically deprived)一词来形容该地的经济条件与人们的生活状况(Denham 2008b:138),但对赖特来说,那里依然是天堂,是他情感赖以寄托的地方。除诗集外,赖特以地名来命名的诗歌数量甚多,如《黑水山》(Blackwater Mountain)、《北汉奇岭》(Nothhanger Ridge)、《天谷骑士》(Sky Valley Rider)、《哈丁县》(Hardin County)、《贝斯山盟约》(Bays Mountains Covenant)、《拉古纳·丹特斯卡》(Laguna Dantesca)、《驱车驶过田纳西》(Driving through Tennessee)、《回到雅克小屋,我听到一曲希腊老歌》(Returned to Yaak Cabin,I Overhear an Old Greek Song)等等。除诗歌标题提及地名之外,赖特诗歌作品中所涉及到的“地方”更是难以统计,大至国家、州、城市,小至乡镇、街道、房屋、公路、后院、花园、山脉、河流湖泊等地,这些“地方”都与诗人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它们都是开启诗人诗歌创作阀门的钥匙,是诗人灵感发生的源泉。
赖特以“地方”来追溯自己的记忆,以记忆为诗歌创作的养分,那么他记忆诗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透明》(Transparencies)一诗似乎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而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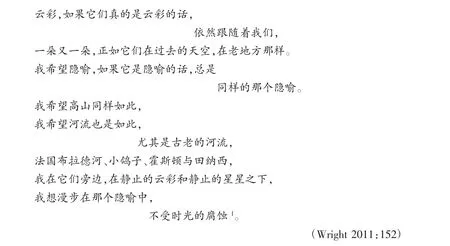
以上是诗歌的前两节,诗人开门见山,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生命,似乎,就是记忆”。这个陈述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命有多重要,记忆就有多重要;二是生命的过程似乎就是记忆的过程。那么,地方与生命和记忆有何关系?显然,在诗人看来,地方是生命和记忆的条件,是它们存在的空间。随后,关于生命与记忆的关系,诗人采用一种极富想象空间的诗意表述——“生命是记忆的隐喻”。关于隐喻,只有本质相似的两个事物才有成为隐喻的可能,那么,生命和记忆有何相似性?诗人借用树木、小溪流、云彩、高山、河流等来加以说明:它们总是保持着事物的本性——它们总是它们该有的样子,尤其当它们在老地方时。所以,诗人不由得发出感叹:“我想漫步在那个隐喻中,/不受时光的腐蚀。”不言而喻,诗人希望生命不止,记忆不变。

诗人在第三节再次强调自己的愿望:生命不变,记忆不变。记忆就像琥珀一样,琥珀在形成之后,即便历经亿万年时光,其品质从不更改,清澈透明,这也是他给此诗取名为“透明”的原因。同样,他希望,记忆无论历经多少时光,都不会受时光的侵蚀,保持它最初的品质。


事物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它的本质,不仅生命在变化,记忆与地方也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对诗人来说,关于记忆与地方的创作某种意义上就是生命的书写,其价值不言自明。
2.地方:从抒情到叙事
我们知道,诗有抒情与叙事之分。抒情重在言情、达志、或者明理。而叙事,就是讲故事。叙事可分叙述和故事两个部分,或者说“讲什么”和“如何讲”。实际上,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含有抒情和叙事双重成分,叙事的背后往往有情感表达的目的或者受情感的驱动,而任何抒情艺术的最高境界大多和故事有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因为触动情感的地方通常来自于故事。
赖特自谦,表示自己不擅长叙事,“在我认识的人中自己是最不会讲故事的人”(Denham 2008b:40)。但又表示,由于生长于美国南方,因威廉·福克纳等文学家的缘故,南方文化中似乎有天生的讲故事的强大基因,所以,赖特就希望“自己能被认可为南方人”,而“不仅仅只是南方诗人”(Wright 1988:159)。其言外之意就是,他的诗歌是抒情的,但他却渴望自己能用故事的方式讲述出来,很显然,他对自己在叙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颇感失望。从赖特研究专家丹尼尔·克罗斯·特纳(Daniel Cross Turner)的评论中可以印证赖特的这一说法,“赖特的自我意识中,暴露强烈的怀旧之情。在他顽固的非叙事性诗歌中,与南方诗歌中强大的叙事冲动形成了惊人的对比。”所以,他完全同意赖特本人对其作品的评价:“毫无任何故事线索的痕迹”(No trace of a story line.)(Turner 2012a:87)。
所谓故事线索的痕迹,指的是构成故事的几个基本要素之一:事件或情节。那么,赖特的诗歌是否真的就“毫无任何故事线索的痕迹”?如果拿赖特的诗歌作品作个体研究,的确很难发现具体事件或情节的脉络,因此,说其毫无故事线索的痕迹一点也不为过。但当视野投向他的整体诗歌作品时,却能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轮廓——作者个人的成长历程,其中不乏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受教育的环境和过程、诗歌创作经历等这些构成故事线索的要素,我们把这种自我成长历程的叙事称之为自传性叙事。而发现这个自传性叙事的主要线索或者说形成这个叙事线索的主要原因就是:“地方”。
上文已有提及,“地方”是诗人打开记忆的方式,而赖特诗歌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记录记忆。我们知道,记忆就是一种回溯的过程。而根据学界的普遍观点,“回溯的结果不管有没有被说出来或写出来,都具有明显的叙事性”(邹涛2014:90)。赖特以诗歌的方式对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个个地方进行回溯,从而构建起一个宏大的自我叙事框架,这个框架之内,诗人尽管以抒情取代叙事,但我们仍能通过“地方”,清楚地了解诗人的个人经历。某种意义上说,赖特的抒情是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我们不妨以一些具体诗歌为例来探讨赖特诗如何通过“地方”这个引子来搭建其自传性叙事的总框架的。如《哈丁县》(Hardin County)一诗,它的标题下记有“CPW,1904-1977”等字样,CPW 是诗人父亲姓名Charles Penzel Wright 的首写字母,1904-1977 是其父亲的生卒年份。诗歌的标题“哈丁县”是赖特的故土,他以记忆中的家乡之名创作,并纪念自己的父亲。而《德尔塔游客》(Delta Traveller)一诗,标题下的“MWW,1910-1964”就与其母亲有关,MWW 是诗人母亲姓名Mary Winter Wright 的首写字母,1910-1964 是他母亲的生卒年份,而标题中的Delta 是其母亲出生的地方。同样,该诗是诗人献给母亲的挽歌。《天谷骑士》(Wright 1991:39)一诗标题中的“天谷”也是一个嵌入诗人记忆深处的名字,那是一所仅有8 名学生的教会学校,赖特15岁那年就曾在那里就读。该诗尽管抒情色彩浓厚,但少有地出现了一些叙事性的细节,如时间和一些场景等:“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火刑:/八月下旬,充足的空气,树叶/奇形怪状,低调的壮观,/窗棂上如犯了罪的灰尘,/悬挂的熨烫齐整的西裤/像挂在黑色挂钩上的肉:”“叮叮当当的圣歌,错误的歌曲:/这个为了你,15岁,走失在/地下回溯的宽广水域;”诗人无意间通过其中的个别小细节就成功地给我们提供了他在那所学校读书时的学习与精神状态等片段。《北汉奇岭》(Northanger Ridge)(Wright 1991:42-43)是诗人记录他14 岁那年参加男生营(boys’camp)的记忆,“礼拜天,犬父被释放:/漫长的路上孩子们的双脚/像雨滴在尘土中留下的痕迹;风/为自我辩护,然后退去;热度/像一只手放在每个人的头上;/滑动,然后咳嗽。此刻,犬父/加深我们的误解,观点更加复杂。”该训练营又叫“圣经营”(Bible camp),诗歌中提到的人物“犬父”(Father Dog)是一名牧师,该诗显然是为回忆他当时参加这一活动而作,诗人在诗歌的末尾特意标注“圣经营,1949”等字样,给读者提供了一点叙事的线索。而《大学时光》(College Days)一诗从标题中就可以判断出诗人创作的部分意图:回忆他的大学生活。诗歌的第一行就是“北卡罗纳州、摩斯威尔,1953 年9月”,诗人将其入读大学的时间和具体学校等材料提供给读者,让读者在勾勒诗人生活经历的画面时又有了新内容。《去中国之路》(China Trace)既是诗人创作的一首短诗也是一部诗集的名字,赖特借此来告诉读者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慕之情,事实上,他曾多次坦言,自己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在诗人的“致敬”系列诗歌中,如《致敬埃兹拉·庞德》(Homage to Ezra Pound)、《致敬阿蒂尔·兰波》(Homage to Arthur Rimbaud)、《致敬保罗·塞尚》(Homage to Paul Cezanne)、《致敬切萨雷·帕韦泽》(Homage to Cesare Pavese)等,可以了解到赖特所受影响,在赖特的个人诗学中,这些人物既是艺术大师,又是他心中朝拜的神圣之地。《孤独而特别的松树》(Lonesome Pine Special)一诗则选择了一些特别的地方来呈现作者的记忆,说其特别,是因为很少有诗人会去触碰的视角——从公路去延伸至国家和地方的记忆尤其是诗人个人独有的记忆。特纳曾以该诗为题材探讨美国南部过渡时期公路的发展变化(Turner 2012b:121-138)。诗中共出现10 条道路,其中前9 条是实际存在的路线,根据先后顺序分别为:U.S.25E、佛吉尼亚U.S.23、爱达荷75 号线、U.S.52、乡村路508 号、U.S.176、U.S.2、北卡罗纳州U.S.23、蒙塔纳的索洛乔路,第10 条是虚拟的北卡罗纳路。除这些公路外,诗歌中还提及如下这些地名:诗人的家乡金斯波特、肯特基、弗吉尼亚的怀特维尔(Wytheville)、北卡罗纳州、爱达荷州的海利(Hailey)、蒙大拿州的卡利斯佩尔(Kalispell)、田纳西等,这些“地方”都是诗人曾经较长时间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而这些公路都是诗人来回穿梭各地的通道,是他连接家乡与外部世界的纽带。诗歌尽管没有提供具体而详实的场景细节,但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中会浮现出一幅幅有关诗人在公路上奔波的鲜活画面。
类似上述有关“地方”的诗歌在赖特的创作中数量甚多,因篇幅关系,我们无法一一例举,这些“地方”大多都是诗人经历过的处所,赖特以记忆的方式将它们记录下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通过这些地方给我们绘制了一幅丰富而完整的个人轨迹图,这样的轨迹图何尝不是一部有内涵有情节的自传史。尽管赖特毕生以抒情而创作,但却巧妙地借用一处又一处的“地方”给我们讲述了他完整的个人历史。我们不妨借用赖特本人的话来论及自传的意义:“任何人的自传,至少在他本人眼里,都是由一串串无数的闪光的时刻组成。那是我们毕生在组集的一条项链……我认为,艺术总是在追求事实,真实的往往是虚构的,或者说是想象的,我们应该努力地重组、重构与重现,自传最终将变成传记”(Wright 2001:107)。
3.让自己师从这块“地方”
我们知道,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终极目的就是通过反思人与他者的关系来探索人存在的意义。赖特以“地方”作为诗歌创作的媒介和主题,显然,“地方”成了人和他者这二元关系中的他者。在我们传统的价值观中,人总是被理所当然地处于这二元关系中主体、主动、甚至主宰的地位,而他者则被人为地置于客体、被动、被主宰的“地方”。这种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自古至今影响深远,即便在极力张扬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消解权威、重建主客体秩序等思想的后现代社会,其威势依然强劲。但是,赖特的诗学思想却逆势而为,在人与地方的二元关系上,他倡导“让自己师从这块地方”(Indenture yourself to the land)(Wright 1991:26)。
根据词典释义,indenture 一词的意思是“与某人签订师徒合同将之收为学徒”(Hornby 1998:755)。在赖特看来,人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在位置顺序上应该是地方在前,人在后,按照他的说法,“地方”与人隐存着两种关系:一是契约关系;二是师徒关系。这两种关系实际上组合成“师徒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人通常可以租赁“地方”,一旦租赁关系确立,人们就可以开发和利用“地方”。在两者关系之中,人无疑占据着绝对主动、甚至主宰的地位,而“地方”成了名副其实的客体。但赖特却反其道而行之,尽管地方与人只是师徒之间的合同关系,但二者之间何尝不是一种类似于租赁与被租赁的关系呢?显而易见的是,二者关系中,“地方”占据着主导甚至主宰的主体地位。赖特的这种反传统思想当然不止是单纯地追随后现代思潮而为,而是弘扬着一种符合时代发展气息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如前文所述,墨菲特曾总结“赖特著作两大反复性主题为:精神和地方。”实际上,这两大主题之间有很大的重合度,二者之间息息相关,赖特诗歌中的“精神”或“精神力”往往依靠“地方”表达出来。在《诗艺》(Ars Poetica)一诗中,赖特表示:“精神无处不在”(Wright 1990:38)。那么,“地方”将表达出什么样的精神?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大多数其他南方诗人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或地方里面的历史更感兴趣,我对地方感兴趣是当我看它或看到它时……地方往往一定会分解为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与场景取代了思想和人的反应,而不是因为它与现在和过去的事物有关……“地方”是某种连串的关联性情感……我往往将地方视为上帝的启示(revelation),一扇通往光(light)的门”(Denham 2008b:137-138)。因此,赖特诗学中地方具有宗教的力量,它的精神显然是神圣而纯洁的。因为受上帝的启示,所以让人向往。“光”不仅在赖特的诗歌中反复出现,在他接受访谈时也不断被强调,它是一种精神性的神秘存在,人找到光就意味着得到了拯救。赖特让人师从“地方”,其用意就是让人师承“地方”的精神和力量,去发现那神圣的光。
“让自己师从这块地方”出自赖特的《头胎》(Firstborn)一诗。该诗是诗人回忆第一个孩子出生而作。诗人初为人父,除了其兴奋之情,他还希望用言语来表达点什么。“一个人能对儿子说些什么呢?”(Wright 1991:24)经过审慎的思考,赖特以一种非常庄重而严肃的方式给孩子寄语:
我想要表达的是
——我只对你说
我已坚信的东西:
让自己师从这块地方;
想象着你触碰着它的毛边
无论何种天气,一而再再而三地;
想象着它的色彩;努力地
模仿,日复一日,
晨光的升起与黄昏的落下,
它们所有生物的活动;
让自己屈服,心情喜悦;
这是持久的法则。
(Wright 1991:26)
赖特的寄语显然是他本人感悟生命后浓缩性的思想精华,他以笃定的语气,表达着自己的精神向往。在“地方”面前,他给孩子的建议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模仿。模仿什么呢?“晨光的升起与黄昏的落下,/它们所有生物的活动;”显然,这只是要模仿事物的表象,真正要模仿的是潜隐在表象背后的精神,那是自己生活所依赖的这块土地所散发出来的蓬勃而神秘的气息。二是让自己屈服(surrender yourself)。在土地面前,赖特要求孩子以谦卑的心态去学习和模仿,为了强调谦卑的重要性,他更是补充“这是持久的法则”(the law that endures)。“endure”一词含有“持久”与“忍耐”的双重含义,显然,在赖特的潜意识里,人对“地方”应抱有宗教信仰般的情怀,他曾说,地方是人类的伟大教堂(Denham 2008b:138)。在《头胎》一诗的结尾,诗人阐明了师从“地方”的终极意义:
留下斑纹,在你的血液中歌唱;
它们的声音是你听到的声音,
它们的形状是你看到的形状
无论怎样,无论何时你都要
将精神集中在那记忆中的地方
——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光。
诗中的“它们”指代“地方”。赖特在此表明,师从“地方”就是为了找到“光”。因为,在前面已有提及,在赖特的诗学精神中,“光”最终可以救赎。《南方的十字架》(Southern Cross)是赖特代表性著作,是他个人创作思想走向成熟而稳定的转折点。诗集的标题显然是诗人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南方是诗人的故土,十字架代表着上帝对世人的爱与救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赖特以“地方”与十字架的结合完美诠释了他思想中“地方”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
4.结束语
综上,笔者发现,赖特诗歌中的“地方”大多与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这些地方承载着诗人的个人记忆,而书写记忆是赖特诗歌创作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方”成了赖特诗歌的叙事策略,通过这些“地方”,诗人勾勒出一个宏大的个人传记的框架,读者通过这些“地方”,可以比较详尽地了解诗人的生平、创作经历、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等。在赖特的“地方”诗学中,“地方”与人的关系像一种师徒之间的契约关系,它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对此的认知,其中的深意值得深入思考。
注释:
1 文中所引诗歌译文均为笔者自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