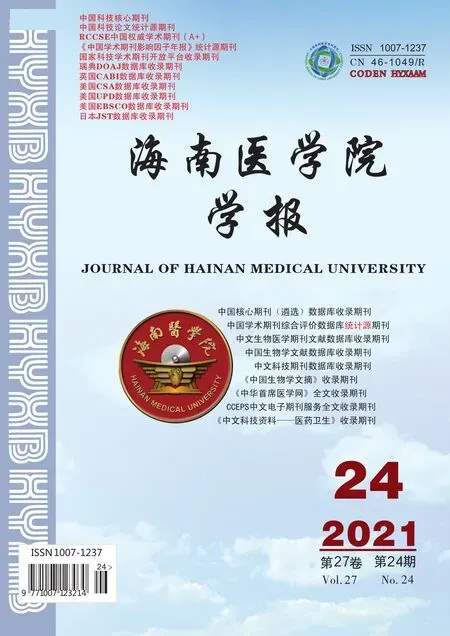新冠病毒变异株“缪”毒株的最新研究进展
王 蓉,王彩红,姚晓文,周玉霞,于晓辉,张久聪,3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消化内科,甘肃兰州 730050;2. 甘肃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甘肃兰州730000;3.武汉火神山医院感染六科,湖北武汉 430050)
新冠肺炎是由SARS-CoV-2 引起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疾病,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自新冠病毒出现至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遭受了第二波乃至第三波的严重疫情。目前新冠病毒突变出了许多变异株,例如SARS-CoV-2 关切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VOC)和关注变异株(variant of interest,VOI)已经被报道,并且已经造成了更严重、传染性更高的新冠疫情[1]。VOI 的级别较VOC 低,因此VOI 目前的威胁要低于VOC。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 年8 月31 日新冠疫情每周公报中称,VOI 中的“缪”毒株可能具有较高的疫苗耐受性,能逃避之前感染或接种疫苗带来的免疫力,因此成为目前关注较多的变异毒株[1]。本文就“缪”毒株的特性及流行病学等进行详细综述。
1 SARS⁃CoV⁃2 病毒的结构特点
SARS-CoV-2 病毒是一种有包膜且不分段的单链RNA 病毒,具有5′-帽结构和3′-Poly A 尾,属于冠状病毒亚科贝塔冠状病毒属。根据血清型和基因组特征,冠状病毒亚科分为4 个主要属:阿尔法冠状病毒属、贝塔冠状病毒属、伽马冠状病毒属和德尔塔冠状病毒属[2]。SARS-CoV-2 病毒颗粒被宿主细胞提供的脂质双分子层所包裹,其中含有核酸及4 种主要结构蛋白:核衣壳蛋白(nucleocapsid protein,N 蛋白)、刺突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 蛋白)、包膜蛋白(envelope protein,E 蛋白)以及膜蛋白(matrix protein,M 蛋白)[3]。
M 蛋白的功能决定了病毒颗粒的形状,能促进膜的弯曲,有助于结合核衣壳[4]。E 蛋白在病毒的组装和释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与病毒的致病机制有关[5]。N 蛋白能通过不同的机制与病毒RNA基因组结合。S 蛋白在病毒附着、融合和侵入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S 蛋白能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决定宿主的嗜性和传递能力、介导受体结合和膜融合[6]。通常,冠状病毒的S 蛋白在功能上分为负责受体结合的S1 结构域和负责细胞膜融合的S2结构域[6]。S 蛋白具有受体结合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RBD),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有很强的相互作用。S 蛋白含有S1 亚基,其受体结合域能与靶细胞上的ACE2 受体结合;S 蛋白的S2 亚基含有已知可相互作用的七肽重复序列1 和七肽重复序列2,可形成六股螺旋束的融合蛋白,其融合和感染都非常接近[7]。此外,研究表明,SARS-CoV-2 病毒S 蛋白的受体结合域与ACE2 的结合亲和力比SARS-CoV高10~20 倍,这可能是SARS-CoV-2 比SARS-CoV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和传播性的原因[8]。
2 新冠病毒的变异特点
新变种出现的4 个关键问题是它们对病毒传播性、疾病严重性、再感染率(即逃避自然免疫)和疫苗有效性(即逃避疫苗诱导免疫)的影响。病毒基因结构的变异对预防、诊断和治疗具有相当重要的医学和生物学意义。与以DNA 为基础的生物相比,RNA 病毒通常被认为复制其遗传物质的准确性较低,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校对和纠正机制[9]。SARS-CoV-2 的进化速率很低(约1×10-3个置换/位点/年),在病毒的30 000 个碱基对中,每个谱系每个月固定1~2 个核苷酸变化[10]。这些核苷酸的缺失、插入或替换可以是同义的,对病毒几乎没有反应,也可以是非同义的,导致氨基酸序列的改变。大量的感染者和每次感染过程中产生的高病毒载量为SARS-CoV-2 变异的产生和选择提供了许多机会。
目前新冠病毒的几个组合突变定义了新的谱系,而最显著的是新冠病毒变异株容易在S 蛋白的S1 亚基上携带突变,S1 亚基包含RBD,并负责病毒与ACE2 受体的结合。当这些突变发生在S 蛋白,特别是其RBD 时,可能会影响受体或抗体的结合。研究证明,在S 蛋白的RBD 内的N501Y 突变导致与人ACE2 受体的更高亲和力,可能增加新冠病毒的传播性[11],E484K 突变以及E484Q 突变与免疫逃逸有关,并增加与ACE2 亲和力[12]。L452R 突变位于RBD 内,可能与遗传性或免疫逃逸有关并被证明可导致治疗性单抗Bamlanivimab(LY-CoV555)的结合-逃逸[13]。研究证明S 蛋白突变D614G(从614位天冬氨酸到甘氨酸的单一氨基酸替换)对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显著增强了甲型慢病毒载体的感染性。通过分子模拟,研究者认为G614 氨基酸取代破坏了闭合构象的稳定性,而不改变开放构象的稳定性[14]。向开放状态的转变被认为是病毒融合所必需的,因此,结构上有利的开放状态与生化分析所显示的较高的传染性是一致的。除此之外,N-末端的突变也是潜在的问题,因为许多高度有效的中和抗体都针对这个区域[15],然而发生在基因组其他区域的突变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描述。
3 “缪”毒株的特性
3.1 VOI
截至2020 年12 月底,出现了累积多种突变的新变种,称为VOI,指的是拥有能够影响病毒传播能力、症状严重程度以及免疫逃逸的遗传突变[1]。它们会导致表型改变,或具有怀疑导致这种改变的基因组突变,已在多个传播事件或多个国家中被发现。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有5 种变种:埃塔(Eta)、约塔(Iota)、卡帕(Kappa)、拉姆达(Lambda)及缪(Mu)。变异株的出现被证明与传播性增加、毒力增加或临床疾病表现的改变、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或现有诊断、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有效性降低有关[16]。
3.2 “缪”变异株的发现及流行病学
2021 年1 月在哥伦比亚首次出现的一种新的SARS-CoV-2 VOI,定义为B.1.621 谱系,在8 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缪”毒株(μ),并将其列为VOI[1]。尽管测序病例中“缪”变种的全球流行率目前低于0.1%,但这一变种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地的流行率一直在上升。截至2021 年6 月,在哥伦比亚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当中,有53%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缪”毒株,2021 年3~8 月,哥伦比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增加[17]。虽然在初期伽马毒株占主导地位,但2021 年5 月开始,“缪”毒株超过了包括伽马毒株在内的所有其他变异体,并从那时起主导了哥伦比亚的新冠疫情。
自该变异毒株发现之后,南美和欧洲一些国家也报告了一些较大的疫情,截至2021 年9 月12 日,共检测到缪毒株5 656 条序列,已在49 个国家发现了缪毒株的踪迹[18]。截至2021 年9 月7 日,已在美国的49 个州检测到新冠变异病毒“缪”毒株,约有两千多的美国人感染该变异毒株,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多感染该变异株的国家[19]。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9 月确认,今年6 月和7 月在机场检疫中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2 人感染的是新冠变异病毒“缪毒株”。这是日本国内首次确认感染该类型变异株[20]。截至目前,韩国国内共报告3 例感染“缪”变异毒株的新冠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分别来自墨西哥、美国和哥伦比亚[20]。2021 年9 月3 日,秘鲁卫生部通报称,秘鲁全国已有10 余个地区报告共67 例感染新冠变异病毒“缪”毒株的确诊病例[21]。2021 年9 月2 日,中国台湾省发现了1 例“缪”毒株感染。2021年9 月3 日,中国香港共发现3 例“缪”毒株感染个案,其中2 人是6 月上旬来自哥伦比亚,1 人是7 月下旬来自美国,并且该患者已经接种过两剂BioNTech 复必泰的新冠疫苗[21]。在已经确诊的“缪”毒株感染者中,有已经完全接种过疫苗的患者,例如香港从美国入境的确诊者,可以明确“缪”毒株具有中和疫苗接种后产生的免疫力的潜力。
3.3 “缪”毒株的基因组学及进化特点
“缪”毒株这个单系类群在最初是被分配于B.1谱系,2021 年1 月,哥伦比亚加强了对SARS-CoV-2病毒的常规基因组监测,截至2021 年5 月,GISAID数据库中共有908 个来自哥伦比亚的序列。B.1 谱系是最具代表性的血统(有229 条记录),因为它从大流行开始就出现的频率较高,而“缪”毒株即B.1.621 谱系从2021 年1 月到目前为止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检测到。在哥伦比亚,由国家萨卢德研究所领导的国家基因组特征计划自SARS-CoV-2 大流行开始以来对其谱系进行了实时监测[22]。2021 年3月和4 月的第三个流行高峰,出现了具有高突变积累的B.1 世系后代即为B.1.621,以及B.1.1.7、P.1 和VOI 在一些城市的发现[22]。
SARS-CoV-2 的蛋白中存在多个氨基酸的替换,S 蛋白是负责受体结合和膜融合的病毒蛋白,也是中和抗体的主要目标[23]。监测SARS-CoV-2 新变种的出现是全世界首要任务,因为某些非同义替换可能与生物学特性有关,例如改变配体-受体亲和力、通过自然获得的多克隆免疫或疫苗接种后抗体的中和效率和传播力[24]。“缪”毒株的遗传背景包括以前在几个VOI 和VOC 中发现的一些氨基酸变化。
“缪”毒株存在大量不同的同义和非同义替换,包括N-末端结构域的Y144T 和Y145S,受体结合区的R346K、E484K 和N501Y,S1/S2 裂解位点的P681H,以及S 蛋白中的146N 的插入。经证实了几个趋同的替换是由广泛的原始人群的高遗传变异率,以及单克隆抗体疗法和疫苗接种的选择决定[25,26]。在SARS-CoV-2 病毒S 蛋白中的替换是常见的,但在“缪”毒株的变异中,一些独特的替换是相关的,例如,E484K 的存在与恢复期血浆中和活性较低有关[25],可以帮助变种逃逸抗体,使病毒得以避开免疫系统的阻击;而N501Y 则是改变了病毒突刺的结合受体,可以帮助变种更容易传播。69/70 缺失高峰与E484K 和N501Y 替换一起降低了中和抗体的能力[27]。在SARS-CoV-2 病毒中插入145N 是SARS-CoV-2 病毒变异的第一个证据,其在感染、传播和致病机制中的意义尚不清楚。
“缪”毒株有多个尖峰蛋白突变,一些与其他VOC 相同,如:E484K、N501Y、P681H,而另一些是新的突变,如:R346K、Y144T、Y145S 和146N 插入。在2021 年4 月,在SARS-CoV-2 病毒基因组调查中,意大利研究人员检测到一个以“缪”毒株谱系典型刺突突变为特征的序列。对该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whole genome sequencing,WGS),确认了“缪”毒株的谱系[28]。因此,追踪了这名具有非特异性症状的患者的所有接触者,从而确认了其他6例SARS-CoV-2 病毒阳性患者的身份,这些患者的基因样本接受了WGS 检查,并被归类为“缪”毒株血统[28]。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评估这7 个意大利SARS-CoV-2“缪”毒株谱系序列之间的进化关系,研究者采用的所有序列都与美国的SARS-CoV-2“缪”毒株序列形成了一个单系簇。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首次从最早阳性患者的样本中分离出病毒,并在WGS 确认其身份后不久用分离的病毒进行了中和试验,在第二次接种BNT162b2 疫苗后10~20 d 收集了患者血清,所有血清都有效地中和了SARS-CoV-2“缪”毒株,表明该VOI 不是疫苗效力的关注点[28]。事实上,“缪”毒株的中和力很强,即使比SARS-CoV-2B 的中和力要低得多。研究数据显示,尽管S 蛋白有多个突变,但“缪”毒株可以被BNT162b2 疫苗引发的抗体中和[29]。因此“缪”毒株的“免疫逃逸潜在特性”的突变,意味着目前的疫苗对它的抵抗效果较差。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此还需要开展更多研究予以证实。
截至2021 年4 月底,在一项包含了“缪”毒株的所有基因组的研究表明,虽然在每个“缪”毒株序列和亲本B.1 谱系的所有密切相关序列之间都发现了非常高且无法解释的遗传距离,但整个分支模式和谱系内距离表明多样性较低[30]。在大流行的第三个高峰早期在哥伦比亚传播可以由多种因素解释,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新出现的血统的遗传背景,导致传播方式的变化。目前的SARS-CoV-2 病毒基因组监测战略包括在主要城市和边境城市,特殊关注群体、具有独特临床特征和严重程度的患者中抽样,新出现的“缪”毒株的感染高频率也可能与SARS-COV-2 病毒基因组监测的加强有关。
4 结论与展望
自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以来,全世界已出现了一系列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导致了新冠疫情的加重和反复。新冠病毒会不断变异,大多数突变对病毒特性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有些突变可能会改变病毒传播的速度、传染性、引起的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对疫苗和治疗的有效性造成影响。目前在新冠病毒的多种变异株中,德尔塔变异株使全球新冠感染率激增,仍然是威胁最大的变异株。自2021 年1月在哥伦比亚发现以来,“缪”毒株因其可能具有较高的疫苗耐受性,能逃避之前感染或接种疫苗带来的免疫力。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监测到该毒株,虽然其影响尚不及德尔塔变异株,但是由于其免疫逃逸,有可能降低部分中和抗体和疫苗的有效性,“缪”毒株可能比原始冠状毒株传播性更强,需要警惕其进化为更严重甚至威胁更大的新冠变异毒株。新冠肺炎疫情形式仍然严峻,全世界感染者及死亡人数仍在增加。中国虽然在前期的疫情防控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的变异特性,多种变异毒株的出现,造成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目前新冠肺炎的控制除了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积极接种新冠疫苗也很重要,现有的疫苗已经证实可以预防原始冠状病毒以及对德尔塔等变异株有相应的中和能力。但是对于“缪”毒株,因其具有免疫逃逸潜在能力,目前的疫苗可能对其无法产生保护,因此就需要进一步研发新疫苗以及更多有效的治疗以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致病作用,进而保护人民的健康安全。
作者贡献度说明:
王蓉:文献检索,选题和设计,文章主要的撰写和文章修改;王彩红、姚晓文、周玉霞:参与相关文献查阅;于晓辉,张久聪:参与选题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