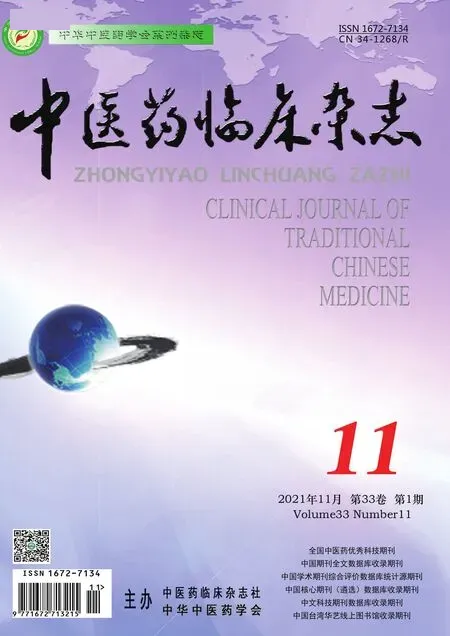从痰瘀致病探讨Wilson病*
刘睿,李静,杨文明
1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安徽合肥 230061 2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合肥 230031
痰瘀是痰饮和瘀血互相作用在疾病过程中形成的病理产物。痰饮是由人体水和水代谢紊乱而形成。通常,较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痰可分为有形之痰和无形之痰。有形之痰,是指可见、有声的痰液,或可触及的痰核;无形之痰,是指只见征象,不见其形的痰病。本文所讨论的痰偏于后者。瘀血是由体内血液停积而形成,包括体内瘀积的离于脉外之血,以及血行不畅而瘀阻于经脉、脏腑内的血液,且久病多瘀。痰和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二者可单独致病,又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从而致病。经过长期大量的临床研究发现,痰浊、瘀血是Wilson病的基本病因病机,痰、瘀二邪贯穿于疾病的始终,痰瘀互结是本病最常见的证候类型[1],因此痰瘀在Wilson病的发生、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对痰瘀的认识
早在2000多年前,医家就对痰瘀有了一定认识。《五十二病方》和汉墓医简中均记载了活血化瘀兼行气化痰的方剂,《黄帝内经》提出痰瘀的相关说法,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率先提出“痰饮”、“瘀血”之名,此后历代医家对痰瘀皆有阐述,痰瘀病机逐渐形成。
痰瘀同源
《灵枢·痈疽》云:“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灵枢·邪客》又云:“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灵枢·营卫生会篇》曰:“中焦亦并胃中……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由此可见津血均源于脾胃的水谷精微,由脾胃运化、输布,可谓津血同源。痰是津液不化的病理产物,瘀是血行不畅或离经之血瘀积的病理表现。张山雷认为:“痰涎积于经隧则络中之血必滞”。《血证论》曰:“血积既久亦能化为痰水”。朱丹溪[2]亦指出:“痰夹瘀血,遂成窠囊”。痰浊源于津液,瘀血源于血液,是津血不归正化的结果,追溯其源,其一源二歧,临床上往往相互为患[3]。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痰挟瘀血,遂成窠囊”,说明痰瘀同病,极力倡导痰瘀同治[4]。现代研究也表明痰瘀同源具有内在物质基础。郑彩杏等[5]论述了痰、瘀异同之处,她认为痰证患者可表现为血液黏、浓、凝、聚等血液流变学改变和微循环异常,说明痰、瘀具有共同的生理病理学基础。丁雁等[6]对痰瘀进行了现代研究,他们认为对“阻滞”的认识是中医痰瘀同源理论的关键。他们运用结扎大鼠右侧颈总动脉的方法,造成缺血的病理现象,即为中医“瘀血、痰阻”的病理特点。选取监测PLt、MPV、PDW 、P-LCR等指标,使用祛痰通络的药物治疗后,上述各项指标可恢复正常。
致病特点
郭蓉娟等[7]认为“痰瘀”是痰瘀互生、胶结而成的产物,是一种不同于二者的新的更强的致病因素。常表现为痰瘀胶结、易滞络脉,痰瘀固着、难以清除,起病隐匿、持续进展,致病多端、症状繁多,酿化蕴毒、变证丛生等特点。《类证治裁》云:“……痰则随气升降, 遍身皆到”,同样揭示了“痰”具有变化百端莫测之性。孟锋等[8]认为痰、瘀常互为因果,正所谓“怪症多痰,久病多瘀”,诊治疑难病证时要重视痰瘀同治。宋明锁等[9]认为痰为浊物,随气上逆,最易蒙蔽清窍,扰乱心神之清净;瘀血上扰少阴,轻则心神不安、烦躁,重则其人如狂,二者共同可导致神志病患。并且痰浊、瘀血存在部位广泛,病理表现繁多,故而病证错综复杂、变幻多端。郭昊睿[10]亦认为痰瘀易导致疑难杂症,“怪病多痰”、“奇病多瘀”,棘手之症可从痰瘀致病着手。
痰瘀与Wilson病
Wilson病,即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11,12]。基于种族和个体的差异,铜离子在体内各脏器沉积的速度、部位的先后及分布的水平不同,本病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主要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锥体外系症状、肝硬化、精神症状、角膜K-F环及肾功能损害等。本病发病率约0.5~3/10万,在我国较多见。[13]中医无Wilson病病名的确切记载,主要依据其临床表现,归为“肝风”“颤病”“强直”“积聚”“鼓胀”“痉病”等病范畴。中医历代医籍均对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景岳全书·痉证》写道:“凡属阴虚血少之辈,不能养营筋脉,以致搐挛僵仆者,皆是此证”。《温热经纬》认为:“木旺由于水亏,故得引火生风,反焚其本,以致痉厥”。现代医者对Wilson病的病因病机也有所见解。鲍远程[14]认为本病重在“排铜毒”,需辨别轻重缓急,风、火、痰、湿、瘀等邪为实,肝肾亏损为虚,针对病因病机不同,综合运用解毒、泻热、祛瘀、通络等治法。杨任民等[15]强调本病应从火邪论治,认为铜毒内聚,蕴生肝胆湿热为本病的致病机制。杨文明等[16]认为Wilson病以“肝风”和“癥积”二者多见,其基本病因病机为先天不足、铜毒内生,浊毒化生湿热,热灼肝经、引动肝风,痰瘀内停、而成癥积。程婷等[17]从伏邪病机出发,认为伏邪致病的本质与肝豆状核变性的发病特点基本吻合。中医认为本病病位主在肝、肾,起于肾、累及肝,与脑髓、心、脾相关,其证候要素主要与虚、瘀、风、痰有关。“脑为髓之海”,肾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上通于脑。本病临床初期因禀赋缺损见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临床期证型常见湿热内蕴、痰瘀互结,纵观整个病程早期多虚,中后期多实,虚中挟实,虚实夹杂,这与其他疾病所具有的先实后虚的病机明显不同,其特点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16,18-19]。痰瘀往往同时存在,贯穿本病始终,导致病情缠绵难愈。
1 痰瘀在Wilson病中的致病特点
本病为标本虚实之证,禀赋不足,肾精亏虚应是本病发病的基础。禀赋不足,肾阳虚损,一则开阖失司,水湿上泛,聚而为痰;二则命门火衰,脾阳不温,脾失健运,聚湿生痰;三则肾阴不足,虚火煎灼,亦可炼津为痰。痰浊黏滞,易阻碍气机,气血运行不畅,瘀血遂生,久之形成痰瘀互结之候。“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痰瘀久结于内,则损伤正气,致多脏受累。[20]
2 痰瘀在Wilson病中的具体表现
痰瘀之邪易阻滞气机、变化多端,故而可使气机紊乱、络脉失常、脏腑失调,病程迁延难愈。
心主神志,脑为元神之府。在中医学的范畴中,心、脑皆与神相关,相互影响。痰瘀在脑,阻碍气机升降,清阳不升,蒙蔽神明,可致眩晕神昏;痰瘀停于心,内扰心神,可致神志异常,夜寐不安。痰浊内盛,瘀血内停,铜毒内阻于肝,致肝失疏泄,气机壅滞,加之湿热熏蒸,胆汁排泄受阻而外溢于肌表,可见黄疸;或气机阻滞,血运不畅,痰瘀互结,可成“积聚”;肝失条达,气滞血瘀,水湿内停,则成“鼓胀”。痰瘀阻于脾胃,脾气不能升清降浊,脾胃失和,可见胸脘痞闷、纳呆、呕恶;肝失条达,脾失健运,则小便短少,大便溏薄。痰瘀在肾,阻于肾络,肾络受损,络道狭窄甚至闭塞,临床可见氨基酸尿和肾结石、尿蛋白。 痰瘀缠绵,胶着难去,流窜经络,可损伤络脉,经脉不通,则见肢体抖动、震颤不已、肌肉强直、舌体僵硬。痰瘀阻络,铜毒郁于体内,沉于肌表,可见皮肤色素沉着,症见肤色黯黑,肌肤甲错;沉于角膜,可见角膜K-F环。
痰瘀易于阻滞脏腑,扰乱气机,使铜不能排出,伤及肝、肾、脑、角膜等脏器之络,临床可出现被累及的各系统的相应症状。现代研究表明,表现出各种临床症状的脏器均能发现铜的沉积。病理显示铜沉积在脑,可引起以豆状核为主的基底节空洞形成,神经细胞和胶质变性;铜沉积在肝,可引起肝细胞坏死、门静脉及其周围炎症和纤维化,电镜下见线粒体增大,含铜的溶酶体颗粒增多[13];铜是人体内多种酶的活性成分,参与人体的物质代谢,其作用与中医“脾”的运化功能十分吻合,故而铜含量的异常会直接影响脾胃的功能[21];采用kubeanicacid 染色可见铜颗粒沉积在近曲小管、肾小囊壁层的上皮细胞中,对肾功能造成损伤[22];脑-内脏型Wilson病患者腹部肌肉病理可见肌纤维大小轻度不等,线粒体功能异常,提示铜元素亦可流于肢体、经络[23];Wilson病患者皮肤色素沉着则是由于黑色素细胞内铜离子增多,酪氨酸酶活性增加,由酪氨酸氧化形成过多的黑色素,并沉积于皮肤,出现皮肤黑变[24];铜离子沉着在Descemet膜的周围形成棕绿色的色素沉着,即角膜K-F环。
治 疗
我们经过长期的研究,痰瘀互结是Wilson病最常见的证候类型已被普遍认同,痰、瘀二邪在本病的致病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故而杨文明教授认为从痰瘀论治是治疗本病的重要方法[25]。临床宜采用祛痰化瘀,活血散结的治疗原则,基本方药为肝豆灵汤(郁金、陈皮、黄连、大黄、莪术、丹参、姜黄、金钱草、泽泻等),并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并随症加减。方中郁金、莪术、丹参、姜黄等活血散结;陈皮燥湿化痰;黄连、大黄、金钱草、泽泻化湿通腑。诸药合用,共奏祛痰化瘀,活血散结之功。此外,现代研究显示本方及方中单味中药同时具有保护被损伤脏器的作用。如高雁楠等[26]研究表明肝豆灵可增加尿铜的排出,降低Wilson病患者尿蛋白含量,具有保护、修复肾脏作用。徐磊等[27]研究证实肝豆灵片能改善痰瘀互结证型患者的肝功能,提高临床疗效。杨成林等[28]研究显示丹参可以下调肝内HSP70 的合成,进而减少由高铜应激所引发的肝损伤。
综上所述,先天不足,运化失常,水湿内阻而成痰,血液内停则生瘀,痰可致瘀,瘀可生痰,痰瘀互结,可发为本病。痰瘀互结为Wilson病的主要证候,对其发病起关键作用,且贯穿于病程始终,致使Wilson病患者出现各种临床症状。因此,痰瘀于Wilson病有重要意义,从痰瘀病机对Wilson病进行研究可成为今后应考虑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