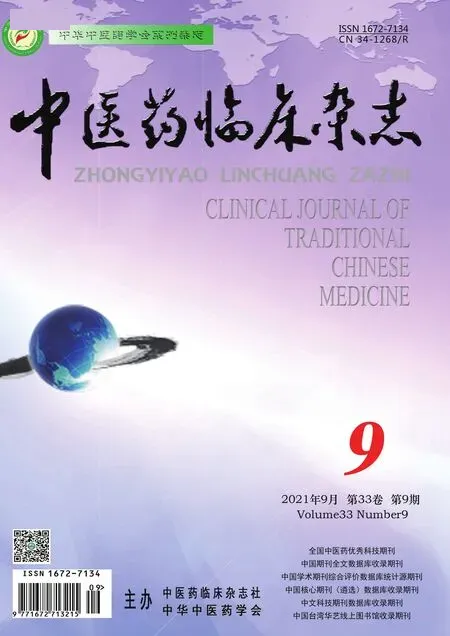曹建雄应用“大方”治疗肿瘤经验浅析*
赖桂花,王菲,周芳, 聂多锐,文玲,向婷婷, 杨婧,曹建雄,2
1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长沙 410208
2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长沙 410007
曹建雄教授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从事恶性肿瘤的中西医防治30余年,熟练运用中医理论治疗肿瘤常取得满意疗效,尤其是对恶性肿瘤的辨病、 辨证、辨体论治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随着现代生活不良习惯以及环境的改变等多方面因素,肿瘤的病死率逐渐上升,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危害。中医学将肿瘤归属于“岩”“积聚“癥瘕”等范畴,曹师认为,肿瘤往往是由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劳逸失调、禀赋有异等多种致病因素长期作用于机体,具有病情复杂、危急以及病程迁延不愈等特点,临床上遣方用药思路用常规模式难以解决问题,需用“大方”以应之。“大方”源于《黄帝内经》,实践于张仲景,多位临床医家对其有不同的探讨,笔者在临床上跟师曹建雄教授临证学习四年,发现曹师对“大方”在肿瘤疾病中的临床应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现进行浅析如下。
“大方” 的溯源
“大方”的源流始于《黄帝内径》,其中《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提及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 从“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中可看出《黄帝内经》中对于“大方”的定义为13味及以上药物组成的方剂,同时“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久之,少则二之”,意指剂量大者亦为大方[1]。自《黄帝内经》后,古代医家对“大方”的运用也多有研究,如《金匮要略》中应用鳖甲煎丸(25味药)治疗病机复杂的疟母,为“伤寒金匮中第一大方”,张仲景认为疟母属于数邪互结,病机复杂,故需合数法为治,针对疟母之气滞、血瘀、湿聚、痰凝、正虚而集行气、活血、祛湿、消痰及补益诸法为一,主次分明,标本兼治,全面照应,实为应用“大方”之典范[2]。在《伤寒论》中小柴胡汤药味不多,但柴胡剂量用到8两,炙甘草汤仅9味药,而生地黄用了1斤,其剂量之大也具有“大方”的含义。另外《宣明论方》中的防风通圣散,《证治准绳》所载之调营饮等均为“大方”的应用。唐代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 感病轻用药须少,病重用药即多”,意为病情深重时所用药味要多;王孟英亦说:“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其危”,意为病情危急时需要用大剂量中药以力挽狂澜。近代多位名老中医如施今墨、岳美中、万友生、姜春华、裘沛然、周仲瑛等在临床上均活用大方治疗疑难杂病。综合古今医家的临床经验,多数学者认为所谓“大方”是基于中医辨证论治并遵循复方配伍原则的药味在13味以上且 (或 )药量偏重的方剂[3]。现代《中国医学大辞典》[4]中对于“大方”的解释:即药力雄猛、分量重、品味多。曹师认为肿瘤疾病属于多因素复合致病的复杂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常法难以扭转病势,因此,针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基本病机,曹师善用“大方”辨证治疗肿瘤且取得良好疗效,曹师对于“大方”的理解有以下3层含义:①使用大剂量单味中药;②数种治法并用组成复方;③使用药性峻猛中药。
曹师对肿瘤的中医认识
曹师认为,肿瘤往往是由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劳逸失调、禀赋有异等多种致病因素长期作用于机体,导致出现正虚邪实的病理性质,正虚有气血阴阳亏虚,邪实则以热毒、痰湿、血瘀等为主,而在临证时发现肿瘤患者病机多以虚实夹杂为主,如气滞血瘀证、痰瘀互结证、热毒蕴结证、痰毒互阻证或者气虚血瘀证、阳虚寒凝证等证候,因此肿瘤患者往往病情复杂、病邪深痼,正虚是本,邪实为标,常虚实夹杂,寒热交错、邪毒互结,阴阳失衡。曹师总结中医辨证论治肿瘤具有以下特点:①肿瘤辨病病种多,除肿瘤本身以外还兼有内科疾病;②肿瘤病因、病机复杂,临床上往往表现为表里寒热相兼,虚实气血错杂,外感内伤杂揉;③肿瘤患者病程缠绵难愈;④病邪深痼、峻厉[5]。这四点的共性意味着肿瘤病情具有严重性、复杂性、矛盾性、长期性,用常规方剂可能难以解决问题,因此曹师擅长运用“大方”以全面照顾病情,用整体的观念审视患者的病情,遣方用药时注意整体与局部结合,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针对肿瘤患者不同病因病机、症状、合并症以及体质,结合辨病论治及辨体论治组方成“大方”,法以寒热并用、补泻同施、气血并调、正邪兼顾,集多药为一方,融数法为一炉,平衡全身邪正关系,从而使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6]。同时曹师认为肿瘤疾病需要大方才能起沉疴,否则杯水车薪,药轻病重,贻误病机,反受其害[7-8]。
曹师应用“大方”治疗肿瘤
1 大剂量使用单味中药
曹师认为,病情复杂的肿瘤疾病非一般药力所能取效,因此治疗肿瘤或者肿瘤并发症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善用大剂量单味中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正如黄和等[9]说:“夫医以人存,药因病用。临证之际,常量稳投。自是温和平当,于新病轻症,尚可愈之,而于重症顽疾,则其效可虑矣,时或非以打剂重用难救其危机,难愈其痼疾。”如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正气严重不足时,曹师认为大虚宜大补,此时投以大剂量黄芪治之,临床上使用黄芪剂量高达90~120g。曹师认为,肿瘤患者感癌毒邪气日久,脾胃运化失常,引起脾胃失和,气血往来不利;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乏源,则神无所养,阴阳不交,而致肿瘤相关性失眠[10]。临床上常用半夏秫米汤加减治以调和营卫、通利中焦枢机、交通阴阳,早在《内经》时代就有半夏秫米汤治疗失眠症的记载,该方半夏用至五合,折今约为42~65g,因此曹师临床上治疗肿瘤相关性失眠时半夏常大剂量使用[11]。曹师通过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对骨转移疼痛的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解,认为骨转移疼痛为沉疴痼疾,临床上大剂量使用某些特殊药物常取得了一定的止痛效果,如对于寒湿痹阻型骨癌痛,常用小活络丹加减,其中川乌、草乌皆为温热辛散之品,具有鼓舞人身阳气之功,以发散乘虚入于经络骨间,而久居不去之寒湿邪气,发挥散寒除湿、温经通络止痛的作用,因此临床根据患者疼痛程度使用川乌、草乌10~15g[12];对于阳虚寒凝型骨癌痛,曹师常用附子粳米汤加减,方中半夏附子同用本属于配伍禁忌,但曹师遵“有故无陨,亦无陨也”之旨,法崇仲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论,认为毒药、相反药配伍且大剂量使用只要辨证准确反而能有效辨治大病,因此治疗骨癌痛时常用大剂量半夏配伍附子30~60g,临床上不仅取得良好的止痛效果,还可逐渐减轻西医止痛药物用量。另外若见肿瘤患者全身疼痛时,天南星30g,安痛藤30g,独活60g以上,白芍30g以上均有一定的止痛效果;若见患者属于风湿疼痛则重用细辛至30g以祛风胜湿止痛,打破了“细辛不过钱”的古训[13];乳腺癌患者改良根治术后常引起顽固性皮下积液,临床上曹师常用大剂量毛冬青消肿利水;小剂量浙贝母有清热化痰之功,而当肿瘤患者辨证为痰热壅盛者,浙贝母用至30g不但有化痰止咳之功,亦有软坚散结之力。肺癌患者咳嗽剧烈者,浮海石用至30g起到良好的镇咳效果;骨肉瘤患者治疗方药中天仙藤可酌情用至60g;治疗肾癌时凤尾草酌用30g;直肠癌时刺猬皮酌用30g;金钱草30g用于胰腺癌、肝癌等肝胆胰疾病中;若宫颈癌患者见崩漏者,应用红参15~20g可获得良好疗效;大剂量赤芍应用于胰腺癌患者见高黄疸者;对于溃疡性胃癌患者,应用大剂量全蝎、瓦楞子、半夏、乌贼骨制酸;在治疗肿瘤伴有冠心病患者时,应用葛根90g以上可加强通经活血之力以解痉止痛[14];连翘常用量9~15g清热解毒、消痈散结,而大剂量30~60g连翘应用于化疗后引起呕吐,止呕效果突出[15];白术常用量时可健脾湿利尿,而使用至30g以上时,有通便之功,对于放、化疗后毒结便秘,或者脾胃虚弱不耐攻伐的肿瘤患者尤为适用[16];以上均为曹师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辨病大剂量使用单味中药的经验用药总结。
2 数法并用组成大方
《素问·至真要大论》曾提出“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即奇方(相对而言属小方)治病不效,就应当用偶方(相对而言属于大方)治疗。后世很多著名医家论证了复法大方在许多难治性疾病方面的作用。如张仲景《金匮要略》薯蓣丸专治“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由21味药组成,使用健脾、补气、滋阴、养血、温阳、祛风、理气多种治法,攻补兼施、寒热并用、阴阳气血共调,也是“大方”的典型应用[17];补土派的李东垣其组方的药味也较多,如临床常用的清暑益气汤有17味组成,升阳益胃汤由16味组成,中满分消汤也有21味,均是药味较多的方剂,虽然组方相对较大,但其组合有序,配伍严谨。目前仍在临床使用的大方还有很多,如安官牛黄丸,苏合香丸等在危急重证上使用,化癓回生丹常被临床用于肿瘤的治疗,均是复法大方在临床治疗中的具体运用[18]。曹师认为,肿瘤疾病病机复杂,如表里同病,寒热错杂,或虚实相兼,或新病又兼宿疾等,此时机械地使用一证一方,既失于变通,又药力单簿,在临床上往往不能满足患者的需要,因此常需要组合运用数种治法且处方药味数目超过常规的复法大方,但临床上大方组方需要全面掌握患者病情,统筹兼顾,才能解决疑难疾病,临床上亦发现复方的功效往往并非单方功效简单叠加[19]。
3 使用药性峻猛之药
药性峻猛如大寒、大热、大辛、大苦或有毒之药常应用于危急重症中邪气较盛而正气未虚者,前人称“以毒攻毒”,常起到“毒药起沉疴”的功效。曹师善用虫类药物治疗性肿瘤,如全蝎、蜈蚣、水蛭、僵蚕、蝉蜕、斑蝥等,虫类药物为血肉有情之品,其药性多峻猛强烈,尤善搜剔通络,可入里入络,其效或破或消,直达病所,使之力挽沉疴,攻克肿瘤之顽邪。正如吴鞠通谓:“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坚不破。”但是虫类药物不可久服,因为其药性峻猛易伤正气,一旦邪祛,得效即止,慎勿长期服用。
4 临床应用大方注意事项
临床上大方的使用符合肿瘤的病情需要,但是曹师认为应用大方时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药味药量要精准,临床上应用大方治疗肿瘤的组方过程中,对中药药味的选择和药量的把握一定不能脱离病、证及患者本身,切忌凭一时之勇简单粗暴的应用大方,更不能乱用重剂,针对各证应用的中药一定要精当准确,同时注意彼此的协调平衡。辨证论治为中医精髓所在,故此在大方的组方与应用上,也要在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下进行,在多病同患、多证相兼的恶性肿瘤治疗中,遣方用药时需要辨证论治结合辨病、辨体论治,来明确其病因、病机、病性,才能内外详察,见微知著,掌握疾病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根据患者错综复杂的证候、症状及正气盛衰、病邪深浅、体质强弱来组合大方。②必须顾护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古人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大方的剂量相对较大,大药则药性猛烈,若较长时间服用,可能使脾胃受到损害,脾胃受损,就会影响后续的治疗,严重时甚至可能终止治疗。另外,由于某些中药的特殊性,气味甘寒燥烈、性能峻猛,可能药力过猛导致败伤胃气。因此,在运用大方时必须注意患者胃气的保护,对脾胃纳运较差者,要尽量避免易损伤脾胃的中药;其次,是在大方中适当加入健运脾胃的中药,如陈皮、焦六曲、谷麦芽、砂仁等健脾和胃之品。总之,尽量顾护脾胃、保证脾胃功能健运,则大方药物能得到充分吸收利用,发挥出其应有的疗效。③中病即止,后续常方调理,当患者病情稳定时,脏腑气血功能得逐渐恢复,就应及时调整处方的组成,以免大方中的祛邪药长期使用损害加重脾胃负担。如苦寒药大量久用会损伤脾胃,理气药大量久用可导致耗气动气,滋补药大量过用会滋腻太过,阻碍脾胃的健运,并产生新的阴阳失衡[20];《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大剂量中药应用即大毒治病,当病十去其六,就可扭转病势,这时宜逐渐将“大毒”逐渐过渡到“常毒”的方剂,巩固疗效,有利于疾病的恢复。④注意心、肝肾功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大方、大药临床应用过程中要观测心、及肝肾功能等的变化,以防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结 语
肿瘤属于临床的疑难杂病,往往病情复杂、病情危重,常方难以截断病势,曹师通过详察病因,细究病机,针对各病因病机给予相应的治法,或投以药性峻猛之剂,或对某一特效之药的剂量超常规地加大量的应用,临证不乱,沉着应对,常获良效。正所谓《黄帝内经》中所言:“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方”在肿瘤疾病中的应用正体现出了“有病则病当之,无病则体受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