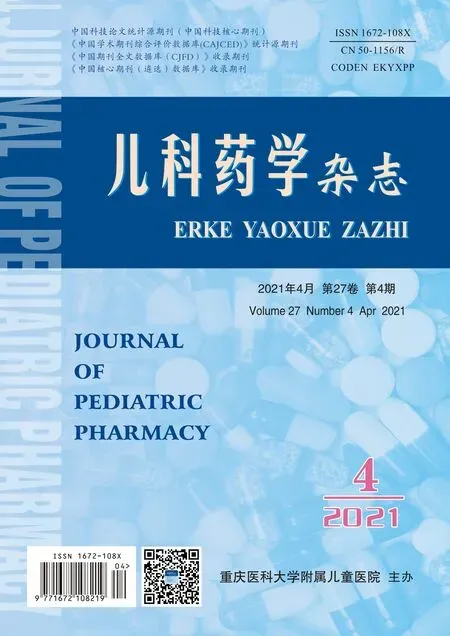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研究进展
秦雨 综述,洪思琦 审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发育疾病重点实验室,儿童发育重大疾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14)
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genetic epilepsy with febrile seizures plus,GEFS+)是一种常见的家族性癫痫综合征,儿童期起病。自1997年Scheffer和Berkovic的初次报道以来,GEFS+作为一种新的综合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GEFS+家系致病基因及临床表型多样,不同家系药物治疗效果差异显著。本文就GEFS+的概念演变、发病机制、基因型、临床表型和治疗方法进行综述。
1 GEFS+概念
GEFS+是由全面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generalized epilepsy with febrile seizures plus)衍化而来。Schiffer I E等[1]于1997年通过研究一个热性惊厥大家系中总结得出并首次报道全面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2001年国际抗癫痫联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将GEFS+作为一种新的综合征列入癫痫综合征分类中。有别于其他癫痫综合征,GEFS+诊断以家系为整体进行,并不局限于个体[2]。随后,大量的研究发现,GEFS+家系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具有临床表型异质性和基因遗传异质性且存在局灶性发作。自2008年以来,Schiffer I E教授更新了GEFS+的定义,将GEFS+中的字母G由Generalized改为Genetic[3],并进一步扩大了GEFS+的概念范围,目前,它己经扩大到所有与热性惊厥有关的遗传性癫痫。
2 GEFS+发病机制
GEFS+是目前公认的一种离子通道病,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与以下几方面相关。(1)遗传易感性。遗传因素与GEFS+的关系非常密切,以热性惊厥为例,不同种族发病率显著不同,欧美国家发病率2%~5%[4-8],显著低于亚洲国家的5%~14%[9-10]。25%~40%热性惊厥患儿有阳性家族史;有热性惊厥发作的患儿,其同胞出现热性惊厥(FS)的风险为9%~22%,同卵双胞胎一致率高于异卵双胞胎。遗传因素对FS的易感性也体现在不同个体,发作温度阈值不同。(2)温度影响离子通道功能[11]。在生理和一定发热范围内,特定的离子通道功能受大脑温度调控,大脑温度的提高可能导致神经元电发放率、幅度及同步性增加,导致癫痫发作。值得注意的是,热水浴的高温也可引起GEFS+患儿的癫痫发作,表明温度升高本身亦可诱发癫痫发作。目前高温致癫痫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3)炎性介质与癫痫的发生密切相关。有研究报道,癫痫患儿脑组织以及惊厥发作患儿血清和脑脊液白细胞介素(IL)-2、IL-6、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与惊厥发作成正相关[12],而抑制IL-1β减少癫痫发作[13]。目前尚不清楚这种不平衡的炎症调节如何导致癫痫[14],有假说认为可能与局灶性或全身性不受调节的炎症风暴导致异常的神经连接和神经网络过度兴奋相关[15-17]。
3 临床表型与基因型
3.1 临床表型
与其他癫痫综合征不同,GEFS+需根据家系中多个成员的临床表型来诊断。既往认为其共同特点是家系成员中必有或均有热性惊厥表型。张月华等[18]在最新研究中指出,无热性全面强直阵挛发作和局灶性癫痫发作可独立出现在GEFS+家系中,强调FS并非定义GEFS+的必要条件。
从单一到复杂、从轻微到严重,GEFS+家系成员的癫痫发作类型差异显著。常见的表型为FS,典型FS是在排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和其他代谢性病因的前提下,3个月~6岁儿童在体温>38 ℃后发生惊厥;其次是热性惊厥附加症(febrile seizures plus,FS+),表现为6岁后仍有热性惊厥发作,伴或不伴有无热的全身强直阵挛发作(generalized tonic clonic seizures,GTCS);其他的临床表型包括FS/FS+伴其他全身性发作(如失张力发作、失神发作、肌阵挛发作)及FS/FS+伴局灶性发作。最严重也较罕见的表型为癫痫性脑病,包括肌阵挛站立不能性癫痫(myoclonicastatic epilepsy,MAE,又称Doose综合征)、婴儿期严重肌阵挛性癫痫(severe myoclonic epilepsy in infancy,SMEI,又称Dravet综合征),两者多为药物难治性癫痫。特发性全面性癫痫(如儿童失神癫痫、青少年肌阵挛癫痫等)亦可见于GEFS+家系成员。
一项多中心研究[18]纳入分析了60个GEFS+家系(新入30个家系)共409例,重新归纳了GEFS+新的临床表型谱:经典的遗传性全面性癫痫(22/409,5%),既往无热性惊厥史的局灶性发作(16/409,4%),无热全身强直阵挛发作(9/409,2%)。热性惊厥仍然是最常见的表型(178/409,44%),其次是热性惊厥附加症(111/409,27%)。
3.2 基因型
目前对GEFS+主导基因尚无定论,1998年SCN1B被最早证实为GEFS+致病基因。2000年,在GEFS+患者中首次发现SCN1A基因突变,2001年发现SCN2A和GABRG2基因突变,2004年和2009年分别证实GABRD和SCN9A基因突变与GEFS+相关。目前研究认为,GEFS+主要基因包括SCN1A、SCN2A、SCN1B、SCN9A、GABRG2和STX1B,易感基因GABRD、CACNA1H、HCN2719-721PPP在GEFS+遗传机制中起到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证实[18]。
3.2.1SCN1ASCN1A定位于常染色体2q24.3,编码电压门控钠通道α1亚基,目前在GEFS+中对SCN1A的相关研究最为常见,但也仅有10%左右SCN1A突变被报道与GEFS+有联系[19]。SCN1A基因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具有不完全外显的特点,外显率60%~70%[20],其涉及临床表型广泛,包括轻型的全面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到最严重和难治的Dravet综合征,其中最相关的表型为FS。张月华等[21]对39个GEFS+家系共196例受累者进行家系表型谱分析,发现其中以FS(46.9%)表型最多,其次为FS+(31.6%),其他表型FS/FS+伴局灶性发作(6.1%)、无热全面强直阵挛发作(5.6%)、Doose综合征(4.1%)和Dravet综合征(1.0%)相对较少;而儿童失神癫痫、无热全面强直阵挛伴肌阵挛、部分性发作、FS+伴肌阵挛仅各有1例患者。既往研究发现SCN1A主要为错义突变,也存在截断突变[22-23]。错义突变多在钠离子通道蛋白核心区域之外,其临床表型一般较轻,但若发生在重要功能区域则常表现为Dravet综合征,表明癫痫表型与SCN1A基因突变的类型和位置有关[24-27]。同时,SCN1A基因的位点多态性也与部分临床表型有关,且提出T等位基因可作为GEFS+患儿发病的风险因子[28]。
3.2.2SCN2ASCN2A作为SCN1A的同源基因,定位于染色体2q24.3编码钠离子通道α2亚基,其突变已证实与多种癫痫有关:如良性家族性新生儿-婴儿癫痫发作(BFNIS)、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综合征(GEFS+)、Dravet综合征(DS),和一些棘手的儿童癫痫脑病。目前SCN2A多在BFNIS中报道,而GEFS+相关报道少见。已报道的相关突变位点c.562C>T(p.Arg188Trp)、c.1399G>A(p.A467T),主要表现为FS[29]。
3.2.3SCN1BSCN1B定位于染色体19q13.11,编码电压门控钠通道β亚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SCN1B-C121W是现已知的第一个GEFS+相关致病突变,但SCN1B在GEFS中的突变较SCN1A和GABRG2少见,Kruger L C 等[30]通过动物模型研究推测该突变不是功能丧失,而是导致功能获得性突变。
3.2.4GABRG2GABRG2定位于染色体5q34,编码GABAA受体的γ-2亚单位,GABRG2在GEFS突变率高达9%[18]。其突变类型主要有剪切、移码、无义和错义突变,当发生无义突变时,表型程度大多较重,而错义突变则表型相对轻微。
第一个GABRG2相关GEFS+基因突变p.K289M源于法国,该家系有17例患者,大多数临床表现为FS且一部分人进一步发展为癫痫[31]。而同年发现p.R43Q突变的澳大利亚家系,主要表型为FS和CAE[32]。2002年Harkin L A等[33]报道了p.Q351X突变的法国GEFS+家系,先证者表型SMEI,但其母亲和兄弟则表现为FS。此外,SUN H等[34]报道的p.W390X突变7例患者中,6例表现为FS+,1例为FS。虽然王娴等[35]指出GABRG2基因型与GEFS+表型的联系尚不十分明确,但从上述报道中推测GABRG2突变的可能倾向于FS/FS+。
3.2.5 其他 既往研究认为在GEFS+家系中,钠通道突变伴经典特发性全面性癫痫罕见,而SCN1A、SCN1B和GABRG2突变伴额叶癫痫和颞叶癫痫先后被报道。SCN1B、GABRG2和STX1B突变相关GEFS+家系均有出现Doose综合征患者相关报道[18]。
GEFS+临床表型谱及基因型复杂多变,目前对某种基因型是否存在特定临床表型倾向关系无法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4 治疗
目前对于GEFS+的抗癫痫药主要依据临床表型及发病机制选择,如传统抗癫痫药中丙戊酸、卡马西平既往常被分别作为全面性发作及局灶性发作的一线药物,新型抗癫痫药如左乙拉西坦、拉莫三嗪等因其安全性较高、副作用较轻,临床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抗癫痫药物对GEFS+患者的疗效与基因突变有关,且在基因突变情况不明的情况下,依据临床表型选药出现病情加重的案例常有报道。因此,在有精准医学支持条件下,通过基因进一步选药有可能实现疗效最大化。
4.1 SCN1A
针对SCN1A突变所导致的GEFS+患儿,常用药物包括丙戊酸钠、左乙拉西坦、托吡酯等。而与其相关的难治性癫痫,如Dravet综合征常需要联合用药,国外研究报道氯巴占可作为一线用药[36]。值得注意的是,钠离子通道阻滞剂(卡马西平、拉莫三嗪等)在Dravet综合征中常可诱发癫痫加重而忌用[37]。
有研究发现基因位点突变导致药物疗效不尽相同[38-39],Bertok S等[40]在216例癫痫患儿中进行基因多态性分析发现同一位点不同氨基酸表达,抗癫痫药物治疗效果不同,进一步提示抗癫痫药物治疗疗效与SCN1A突变产生的氨基酸性质密切相关。
4.2 SCN2A
对于SCN2A基因突变导致的癫痫性脑病,仍以钠离子通道阻滞剂作为一线药物,特别是苯妥英钠对该基因引起的早期癫痫可有更好的疗效。在钠离子通道阻滞剂无效时,可考虑选用左乙拉西坦[41-42]。但有研究发现,SCN2A基因相关的BFNIS患儿可能出现包括苯巴比妥、托吡酯、丙戊酸钠、左乙拉西坦在内的药物抵抗,为实现癫痫控制,部分患儿需联合用药2个及以上(平均4.3个)[43]。
4.3 GABA类似物
4.4 其他
大麻二酚是一种新型抗癫痫药物,属于大麻类,目前可减少Dravet癫痫发作次数已得到验证[47]。Ⅱ期临床试验已经完成,现Ⅲ期试验进行中,探讨大麻二酚在Dravet综合征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48]。随着精准医学的不断完善,未来将有更多癫痫基因治疗靶点药物涌现。
对于GEFS+家系中的难治性癫痫,非药物治疗地位也逐渐上升。Ko A等[49]报道,患有SCN1A、SCN2A基因突变的患者对生酮饮食尤为有效,有效率分别为77.8%、100.0%。因此,对于存在SCN2A、SCN1A基因突变的GEFS+患者,如药物治疗疗效不佳,应尽早考虑生酮饮食。
对于难治性癫痫,手术切除疗法虽被许多文章报道,但该疗法是否适用于遗传性癫痫仍存在争议。对于明确合并有局灶性或单侧致痫病灶者(如皮质发育不良、发育不良肿瘤、血管病变和脑软化症),可考虑早期手术切除,因有研究指出对于尚处发育期的大脑,早期手术干预可减轻不良反应[50]。除此之外,姑息性手术方案,如迷走神经电刺激(vagal nerve stimulation,VNS)、胼胝体切除(corpus callosotomy,CC)等也被尝试应用于Dravet综合征中。1项纳入13项研究(68例)的荟萃分析显示,应用VNS后52.9%的患者癫痫发作减少≥50%,得出迷走神经刺激可降低DS患者癫痫发作频率的结论,且其中7项研究还指出VNS可额外获益[51]。而胼胝体切开术虽有应用于在DS,但目前仍缺乏有效性研究数据[52]。
5 展望
GEFS+是儿童常见的遗传性癫痫综合征,存在显著的表型和遗传异质性。同一基因突变类型不同、核苷酸改变不同、氨基酸突变位置不同,所致GEFS+临床表型及治疗也不尽相同。不同基因是否对某一种临床表型有倾向性,研究尚不充分,表型异质性与基因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随着精准医学的发展完善,相信我们对GEFS+的认识将更加深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