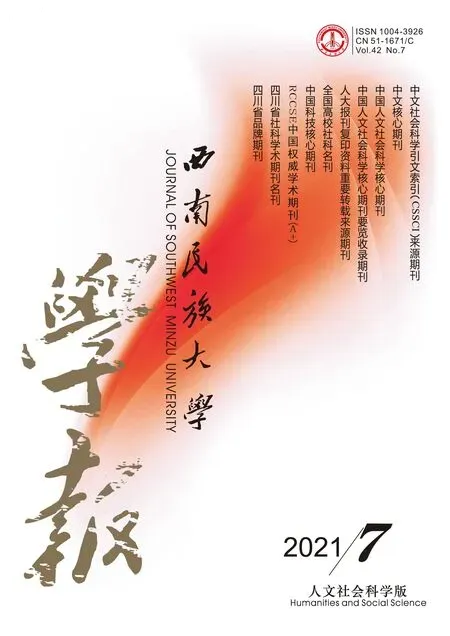“机器同伴”:新型亲密关系下的“人机共情”现象思考
何双百
[提要]随着社交机器人逐渐出现在家庭、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日常生活与媒介交流环境里,他们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在人与机器建立新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同理心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与机器人的社会互动是基于“拟人化”,即对人类社会能力的想象投射,然而此说法争议较大。本文拟将社交机器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人机互动的现象描述,探讨我们能不能对机器人产生同理心这一认知谜题;然后进一步讨论“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需要对机器人移情”等问题;最后在直接感知理论(DPT)的基础上提出“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论”这一描述性框架,探索社会化在“人机共情”现象里达成的重要作用。
社交机器人是数字时代技术、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出现的新角色,它们作为伙伴而不是工具与人类进行社会互动和合作的应用领域正在增加,也让社会各领域下的人-机交互问题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对社交机器人的概念进行限定,因为国内有学者认为,“社交机器人是指社会网络中扮演人的身份,拥有不同程度的人格属性,与人进行互动的虚拟AI形象”[1],但本文要探讨的社交机器人首先排除那些虚拟AI形象或利用算法生成的社交媒体账户,而是那些能够“遵循社会行为和规则与人类或其他主体进行互动或交流的自主机器”[2],它们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存在,还在不同的协作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治疗师、训练员、调解员、照顾者和同伴等,拥有诸如洗碗、哄小孩睡觉、演奏、种菜、预测天气、回答问题、安抚等多种功能,因为这种机器人更能够给予用户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感觉”,它们不仅是“工具”,更是扮演着“社会伙伴”的重要角色。
一、“机器同伴”:人机互动的现象描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倾向于使用熟悉的社交模式与机器人进行互动,对机器人表现出同情等情感反应,甚至赋予他们道德地位,但这些现象通常被集中在一起被归类为“拟人化”而非“同理心”的实例,毕竟我们通常不认为机器人有“头脑”,随着那些能够对人类语音、图像进行识别的、有“人情味”的社交机器人的不断涌现,人与机器人开始建立起类似“同伴”的新型亲密关系。
(一)社交机器人的兴起
“社交机器人”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渴望,即创造一个符合个人欲望和需要的人类模型。古罗马作家奥维德(Ovid)在他的书《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充满想象力的描述了一个关于塞浦路斯人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该故事讲述了有着超高艺术天赋的皮格马利翁,把所有的激情和时间都集中在创造一座体现自己理想女性的雕像上,最后皮格马利翁创作成功还迷恋上这座雕塑,不仅用华丽的服饰、昂贵的首饰装扮它,还把它当作伴侣一般与它同床共枕、跟它讲话。①这个故事的寓意是非常明确的:人类的创造力和发明精神指向于对生命的理想化的形象模仿。社交机器人也是为了与人交流这个目的而设计的,当社交机器人与动物或人相似时,人与机器之间就会产生一种自然且直观的交流,因此,流行的社交机器人也能够成为宠物或同伴。1999年,索尼首次推出爱宝作为一种触摸敏感和互动宠物,它被设计成一个朋友或娱乐伙伴;②由法国Aldebaran Robotics(仿人机器人研制企业)开发的双足人形机器人Nao(脑)看起来像个玩具,然而它可以听、看、说,并被编程来模仿人类的行为甚至实现复杂的交互;③号称“最善解人意”的社交机器人Paro(帕罗),其“设计的初衷是与人进行身体上的社交互动”,[3]它有着人造白色皮毛,让人一看到它就想触摸它并很快对它产生依恋,它支持治疗和护理,由于改善情绪、缓解压力效果明显,在日本经常被个人或夫妇作为宠物伴侣购买;在日本大阪还有一款“柔情机器人”(Affetto),②艾伯尔描述它“长着一张婴儿脸,有两只小胳膊,皮肤摸起来跟婴儿一样,当它们撅着嘴、哭闹发出咕噜的说话声,转动眼睛感兴趣的看着参观者,这时,人们禁不住想要建立与它的关系”。[4](P.319)
20世纪90年代开始,心理学等领域就尝试系统地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表明,“与社交机器人互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认知能力和情绪反应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5]情感及服务型机器人的研发规模和研究领域都有所扩大。近年来,日本将发展机器人作为迎接高龄化社会,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重要一环,重点研发护理病人、料理家务、陪伴老人、照顾残疾人等家庭服务型机器人,围绕人和机器人之间建立的新型亲密关系的讨论也开始出现。⑤亲密关系包括“内在的信任、爱情和友谊等”。这种亲密关系的探讨不仅涉及人体内的哪些心理或情感神经机制被激活,同时还启动了人机互动的新的话语机制,即被爱和被信任的机器人从物质领域中解脱出来,安置到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谈论的机器人不再属于机器、物体、物品的范畴,相反,人们谈论它就像平常谈论我们所爱和信任的人一样,也相信他们会反过来爱和信任我们。浅田捻(Minoru Asada)在日本从事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30余年,他相信未来机器人将与人更紧密的一起生活,并向人类提供身体和精神上的支持,为了消除人与机器人之间的鸿沟,“他希望机器人能够识别情感,不仅模拟情感,而且甚至还拥有情感,他还想要展示移情和善解人意,唤醒同情的社会机器人,因为只有到那时,与人类组成的一个真正的集体才会发挥作用”[4](P.317)。
(二)“人工移情”的概念挑战
如果机器人要成为我们的同伴,就需要具备满足我们社会需求的基本条件,这种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移情,在社会心理学中,对于移情的内部过程看法并不统一,因此移情的一些定义与情感传染、模仿、同情或同感等概念重叠。在《论移情问题》的前言部分,E·施泰因(Edith Stein)将移情定义为“对陌生主体及其体验行为的经验”[6],移情作为一种特殊的感知行为,可以让我们理解外来心理体验,“我们自己的人格是在原始的精神行为中显现出来的,而其他人或外来个体的人格则是通过移情体验的行为而显现出来的”[7]。认识自己和他人人格的可能性是通过移情来保证的,移情不仅被认为是一种身体上的精神活动,还是一种精神行为。威斯帕(Wispé)则将移情定义为“一个观察者在情感上做出反应,因为他觉察到另一个人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一种情感”[8](P.17-19),移情不仅仅是一种交流,还是一种模拟的透视:通过镜像神经元的激活,预期地归因于和解码他人行为的能力。我们倾向于接触、共鸣和模仿他者的精神生活,“理解他者行动的原因需要运用我们的移情能力,在自己的头脑中重现想法,并富有想象力的理解他人的观点”[9](P.272)。尽管移情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复制他人的精神状态,但移情者和目标处于相同或至少相似的情感状态。所以普雷斯顿(Preston)等进一步认为,“移情不仅包括情感过程,还包括认知和亲社会行为,因此,同理心往往与帮助行为或友谊有关:人们往往对朋友的同理心强于对陌生人的同理心。”[10]
虽然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关于人类对真实人物或虚构人物移情的文章,却忽视了移情在人机交互中的作用,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能够表达情绪的社交机器人的不断出现以及人工智能情绪的研究越来越多,人们对与不同形式的“人机共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浓厚的哲学兴趣。一些研究者甚至希望把人类共情机制嵌入机器人系统,从而催生出“人工移情”(Artificial Empathy)这一概念,该概念被浅田捻及保罗·杜穆切尔等人正式提出,用来指那些社交能力建立在激发人类情感反应能力基础上的机器人的行为。⑥在《与机器人共存》(Living with Robots)一书中,保罗·杜穆切尔(Dumouchel)讲述了机器人学领域从人工智能到“人工移情”的一个基本转变,预示着人类进化的拐点,也带出当前最具探索性的一个问题:同理心作为人类“特权”受到挑战,换言之,当机器人制造专家将人工移情编程到机器人身体中,那种传统的关于人类情感是离散的、私人的、内在的看法正在改变。⑦施梅特坎普(Schmetkamp)等认为,“机器人可以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感知世界,它也拥有感知和评估周围世界的视角,尽管不像人类一样复杂,但能作出判断,甚至发展出动机的视角”[11]。中国学者颜志强等把“Artificial Empathy”翻译成“智能体共情”,并以此为主题结合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对现有与智能体共情有关的理论模型做了系统阐述和实证研究,不管是人工移情还是“智能体共情”,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尚处于萌芽阶段。“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着已经开始建构机器人共情的相关模型”。[12]德瓦尔(de Waal)提出的“俄罗斯套娃模型”⑧和德赛第(Decety)等提出的“双加工模型”⑨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模型。浅田捻建议设计智能体共情要以俄罗斯套娃模型为基础,重点考虑两个关键的加工过程:情绪共鸣和情绪/认知共情,颜志强将情绪共鸣解读为“个体对他人情绪的一种自动化的情绪共享,情绪/认知共情的功能模拟则需要借助于机器人的学习能力。”[12]从技术角度来说移情是很难建模的,但是对于机器人成为我们社会中的社会主体又是必不可少的,浅田捻不仅主张“人工同情”,并提议“将情感认知发展成机器人的一部分,以准确设计人工移情”。[13]
“人机共情”现象的探讨不仅需要在认识论层面把精神哲学或现象学、神经科学、仿真理论、感知技术等多方面纳入考量,还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需要思考:人类移情系统是否适用于机器人移情?机器人到底有没有“头脑”和情感?如果它们有,我们如何感知和接触它们的状态和经验?将具有情感能力的机器人引入我们的社交环境有何道德风险?
二、“人机共情”:认知转变及伦理思考
我们对机器人产生认同感,希望与机器人建立情感联系既有益处,也有弊端,有学者如特克尔(Turkle)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欺骗,会导致“我们遗忘生而为人的特别之处,遗忘真实交谈的意义。”[14](P.379),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如果能够模仿情绪,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能,人工智能不需要让人们相信这些交流信号背后有真的感情,只需知道它们对沟通会很有帮助。”[15](P.148)
(一)对机器人移情的认知转变
在《社交机器人与社会关系的未来》一书中,认知科学家乔希·雷德斯通(Josh Redstone)提出“将人们对社交机器人的情感反应设想为真正的移情反应”,但最终他驳斥了机器人和人之间存在“真正的同理心”的观点,他将这一场景解释为人的一种“感知幻觉”。[16](P.177)精神分析学家尔盖·蒂塞隆(Serge Tisseron)认为,“真实”移情的重要特征是它是相互的,或者说它是“外生命的”,[17]根据定义,它排除了动物和机器人。“人工移情”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我们移情的极限,包括移情的概念。如果将移情能力扩展到非人类到底是构成了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改进”,还是导致移情概念的毁灭?换言之,如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我们是否关心移情和它的未来?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务实的“技术”问题。大量反对意见认为,机器人并没有真正的感觉或体验任何东西,它们也没有真正的精神状态,如欲望或信仰,它们是通过编码、设计和叙述来创建的,并且在与人、环境的交互中被“调整”,也就没有能动意识。既然同理心是针对某人精神状态“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自然我们无法对机器人产生同理心。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以上认识论问题,那么机器人将无法成为人类移情的接受者,我们可以试着从与机器人互动并与机器人建立社会关系的人类的感受出发来理解这一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创作小说或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依赖想象力来获得没有看到的东西,移情现象学方法的早期先驱之一施泰因也认同,想象或再现在共情理解的多阶段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想象机器人的感觉,这里重要的“内容”不是机器人“头脑中”的东西,而是人类与机器人互动时的感受,移情主体是否需要和他人有同样的感觉变得也不重要。事实上,机器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情感,机器人是由物质材料组成的,这是所有思想和功能的基础,特克尔(Turkle)认为,“如果你把机器人当作一种全新的物种,那么机器人的情感是合理的,就像动物与人的情感也各有不同,也就没有必要再拿机器人的情感和人做比较,这意味着讨论情感的真实性是无意义的”。[14](P.306)所以与其问机器人是否拥有自己的情感,不如探讨我们希望与机器人形成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人表现它们自己的情感?以及我们该不该对它们产生同理心?
(二)亲密关系下的迷恋与恐惧
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Floridi)分析过我们渴望与机器建立关系的两大原因:首先,人工伴侣是为了满足人类对社会情感纽带和关系的特殊需求;其次,社交机器人可提供娱乐、新闻、教育、医疗等服务。[18](P.652-653)一些社交机器人模拟感觉(同伴),而另一些只是帮助提升(助手)。然而,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越紧密,就越会激起人们的迷恋和恐惧。一方面机器人与人类协同工作,它满足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当我们衰老,机器人会伺候我们;当孩子无人照看,机器人会照料他们;当我们生处逆境,机器人会给予我们能量,人们沉醉于这种连结带来的舒适,这种连结不受任何亲密关系的束缚”。[19](P.11)虽然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机器人表面看起来无害和友好,但由于机器人不像人类那样能感觉到情绪(缺少由神经元和遍布全身的神经系统组成的大脑的生物基质),表现或模拟情绪可能被认为具有欺骗性,将社会上需要照顾的人群(老人、儿童、有特殊需要的人)交给机器人,是否意味着致使社会弱势群体陷入不真实的关系存在?在特克尔看来,“这种辅助手段取代了交谈,反而侵蚀了我们的同理心”。[19](P.181)这种可以调动人的高情感电荷的拟人化的机器人,创造了一种“欺骗”性的“关系幻觉”,它威胁着人们远离“真实”的社会关系。
对于人机关系过于亲密的担忧和恐惧还有很多,比如机器人无法逃脱或保护自己,可能会增强人们的攻击性、傲慢或自我放纵的倾向;由于机器人允许人类沉迷于任何令人愉悦的活动,包括令人厌恶的、不健康的或公然非法的行为,机器人可能成为上瘾或不受抑制的疯狂行为的载体;由于仿人机器人具有仿人特征,所以它们能表达人类在特定角色或功能中的姿势或行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通过描绘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来强化偏见;随着关键决策越来越频繁地由人工智能承担,对自主机器人的持续依赖可能会使人们不愿意承担需要以道德敏锐性、实践智慧和敏感性来处理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等。
也有一些代表性观点对人类向机器移情持乐观态度,比如:战略论、反野蛮论以及实用主义者的共享社区论。[11]第一种战略论认为,为了成功地进行互动,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推断并理解我们的互动对手在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机器人的互动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同理心,都只是为了某种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合作者,第二种观点更具道德规范性,该观点认为,如果不同情他人,我们就有变得野蛮或麻木的风险,反过来,同理心可能会培养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提高我们的道德品质,正如康德提出过一个关于人与动物的关系的论点,它暗示我们不应该对动物残忍,因为这将损害或败坏我们的道德品质,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社交机器人。不过也有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家已经表明,移情不一定会促进积极的亲社会态度,也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第三种观点与前两种有交集,但更多的是从现象学角度对互动双方的关系以及人的自我理解作出解释,这一观点认为,与他人共情可以让我们熟悉“存在于世界中”的他者,开阔我们的视野,改变我们的观点,从而塑造我们的社会交往和道德行为。
事实上,只要我们已经与机器人分享了行动和环境,只要移情和社会认知能够改善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我们也可以假设,我们与机器人的互动将从移情的角度受益,这种关系就够不上是一种欺骗。201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机器人与弗兰克》(Robot and Frank)讲述的就是一个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症状的老人与照顾他的机器人发生的故事。弗兰克最开始对这个机器人很“排斥”,但是后来他想到可以利用机器人重新开始他以前的飞贼生涯,便开始跟机器人合作建立起信任关系,逐渐把机器人看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在两人多次抢劫被警察注意后,弗兰克被迫要决定是否要删除机器人的“记忆”以销毁犯罪证据,这让弗兰克特别苦恼。电影虽然不是以表现人机共情为主题,但这种同理心却无处不在,而且还带给我们一种更深刻的启示,即电影主人公被设定为一个“缺乏自治”的理性的人,机器人设定的初衷是陪伴、照顾并帮助他成为一个“正常的人”,然而它却成为了人的“犯罪搭档”。不可否认,电影暗示了操控社交机器人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反过来也应该看到,执行好或坏的决定都取决于真正具备道德行为意愿的人,移情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如果把机器主体的心理状态理解为数据,决定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帮助自己的机器人。
三、非对称社会互动:“人机共情”的感知“氛围”
如果用单个的共情理论如镜像神经元理论、推理论、模拟理论、直接感知或想象理论、交互理论、叙事理论等来分析“人机共情”,很难描述得特别透彻,我们需要打破边界找到一种开放的理论视角,机器和人互相理解的一个关键就在于探讨人是如何看待机器人的,它们为“人机共情”的探讨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本文简要勾勒出一个描述性的框架: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论,旨在从现象学视野提供一个相对合理的视角来描述人与机器人这种不对等的主体移情现象,虽说这可能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但至少称得上是一个理解“机心”的可行之路。
(一)非对称社会互动下的行为“感知”
传统意义上的共情通常发生在社会互动过程当中,要求共情主体和共情对象都具有意识、情感等心理能力,暗示社会互动双方的能力对称分布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显然,不管是具备“高阶社交能力”的机器人还是“低阶社交能力”的机器人,与人进行互动都是一个情感能力极度不对称的社会互动过程,这种情况下人类主体如何抵达“机心”?扎哈维(Zahavi)提出的“具身存在于世界”的直接感知理论(Direct Perception Theory,DPT)为人机共情提供了一种思路,DPT是一种非推理的读心理论,它设想我们可以直接通达他人的基本情绪状态和运动意图。“在这些情况下,感知他人的情绪状态类似于感知诸如桌子或椅子等的属性,好比我们看到一个人微笑时,不需要推断他们是快乐的,因为快乐直接呈现在他们的表情中”。[20]DPT理论为人类移情和人对动物的移情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本文借用此概念把它从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互动延伸到人与机器人之间,提出一个“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的新概念,重在探索互动双方在情感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实现移情的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描述这种“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最好是将其与另外两种移情理论(理论论和模拟论)相对比。理论论(Theory Theory,简称TT)假设我们要“基于一套因果解释定律去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21]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简称ST)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建立在我们模拟他人的思想、情感、信念和欲望的能力之上”。[22](P.64-65)然而以扎哈维为代表的现象学家对以上两种理论提出了批判性反驳,认为这两个理论都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构成的:一个主体的内在心理状态基本上是“隐藏的”,其他人无法直接感知体验到。我们进入他人“内心世界”的唯一途径,要么是通过理论和假设(理论支持的立场),要么是通过对他人处境的想象模拟,让我们“穿上对方的心理鞋”(模拟论)。然而移情目标所经历的与移情者所经历的精神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理论论和模拟理论所想象的交流互动,只不过是两种笛卡尔式思维之间的互动,施泰因同样对此进行了批评,她认为:“通过‘模仿’所获得的并不是他人的体验,而是我自己的体验。因此,模仿理论不能成为对移情发生的一种解释”。[7]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将“共情”概念从心理学引入到现象学主体间性的研究当中,主体间性在胡塞尔的视界中就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如何在自身的意识经验中构造出他人。换言之,在交互过程中,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可以表现为他的行为(表情、手势、动作等),而我们可以从他人的行为直接感知他的情感、欲望及信念,这个“他人”也包括虚拟人物。正如现象学电影哲学家维维安·索布恰克(Vivian Sobchack)所指出的那样,“电影及其人物不只是投影,他们有身体和声音,他们允许自己和接受者之间的准主体间体验,它们甚至可能产生触觉印象”。[23](P.136-137)如果移情在虚拟人物中能够实现,对于有一个存在的、嵌入的、可以与人相互作用甚至能够干预人的行为的社交机器人实体,更容易嵌入到我们感知的环境中,这种具身化和语境化赋予机器人一种行为表达和身体体验的方式,身体体验在哲学家戈尔迪(Goldie)看来就是一种情感,因为它总是以某种方式来表现害怕或羞愧,他把移情看作是一种“在有限的时间跨度内(一段感情插曲)对他人的感觉体验,是一个人集中想象另一个人的叙述(思想、感觉和情感)的过程或程序”。[24](P.195)
如果人类“感知”到机器人的“行为”是可行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可供人类感知到的行为就能代表对方全部的精神状态了吗?直接感知并不能保证完全通达“他心”,对于一些简单的行为和语言活动,我们可以直接感知,但是对于复杂的活动,那种“内在的”“隐藏的”精神状态不可能都能够通过身体行为表达出来,亦或者全部被其他人立即感知到,何况移情对象是经由数字编程的机器人,需要感知的是一种不统一的、异质的、程序集合的“模拟情感体”。所以,主体间性虽然在人机共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不是我们唯一可依赖的,我们还要了解这种感知在人机互动过程中是如何真正起作用的,这时,就不能把“内在的精神生活”与“外在的社会生活”割裂开来。
(二)通达“他心问题”的感知“氛围”
尽管笛卡尔的二元论概念饱受质疑,却被当代很多主流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学者所继承,在传统的哲学进路中,心灵和身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身体成为隔断心灵间的壁障,直达‘他心’的核心就是跨越非透明的身体,这显然会给‘读心’或移情带来困难性和复杂性。”[25]赖尔(G.Ryle)的行为主义对心身二元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将心灵还原为身体行为的表达特征从而实现了身体一元论的转换,认为旁观者可以通过重新扮演别人的公共行动来体验其私人经验。显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不太认同这种看法,他试图通过否定心身二元论和行为主义一元论来推动“他心问题”的范式和视角转换。于维特根斯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别人的情绪,而不是脸部扭曲的状态,我们可以立即用高兴、忧伤还是无聊来形容这张脸,也就是说,情绪是一种人格化的表现,主体的身体行为本身,就如同它被思想的意义所浸透”。[26]所以理解“他心问题”还离不开语言的进一步解释。在解释活动中,自我和他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持续的互动状态,“他心意图”就会不断地呈现,维特根斯坦关于“他心问题”的论述更像是现象学中的意识体验流及主体间性理论。
当我们与“他者”互动时,从“他者”的身体行为到我们的感知这一步非常关键:外在的行为究竟能否和内在的情感画上等号?我们不应该假定精神上一切事物都有其特有的表现形式,就像“怀念”和“难过”好像很难光从表情上做出区分。在和没有“主动意识”和“自我认知”的机器人互动的时候,感知其行为看上去更是难以企及,如果对方没有丰富的情感,我们感知和理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通达“他心”的困难并非是我们不能感知到它们内在的“情感”,而是与它们有限的“表达”及“虚拟”的体验有关,好比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感情或欲望肯定跟自己“内心”发生的事情有关,而不是公开表现出来的行为有关,何况人既有表现行为的能力,也有隐藏行为的能力,换做行为表达有限且缺乏情感体验的机器人,这种不确定性更甚。
事实上,感知机器的行为不能脱离机器身体和技术的瞬间协调,也不能脱离特定时间和地点在场人员的交流行为,这是一个共同构建的行为,社交机器人不需要在外表和动作上做到“生物学上的精确”,也不需要强迫人们相信它们有情感和意识。它所要做的是满足人们对“行为的期望”,从而让人与之互动时不那么令人沮丧的只把它们看作纯粹技术或操作的工具,而是可以理解的“伙伴”。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恰恰因为我们的移情对象是机器人,这种情感的“欺骗性”反而更小,因为欺骗性主要存在于复杂的生命形式中,就算是有一定机器意识的机器人其行为表达方式也因为受制于“程序命令”或编程而变得“显而易见”的,它们所能“表达”出来的情感就代表它们“真正”的情感,只是对于这种情感的感知,同样不是“直观可见”的,它离不开感知者先验的认知能力。胡塞尔用“共现”(Appräsentation)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步,“共现”是人的一种先验能力,“当我们在感知物体的时候,虽然只看见了该物体的一个侧面,但我们仍然能够在意识或感知到这是一个完整的物体。”[27](P.153)因为在任何与他人共情的尝试之前,都有一种超越性的潜在关系的“背景”,“共同的身体意图”或“情感图示”构成了我们与他者发生互动的背景,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好比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是在生活实践和交互过程中涌现的,类似于‘场’,无形但又时刻存在,正是在这种互动氛围中,人们对他心的感知才是活生生的和真实的,所有的东西都附着一种氛围,一种不可描述的特征”。[25]
梅洛·庞蒂认为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身体存在结构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基弗斯坦(Kiverstein)用“生命形式”印证了梅洛·庞蒂这一观点,“生命形式”是一存在在世界上的结构,是一种行为模式,它可以跨越物种边界、普遍的结构,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支持人类对非人类的直接社会知觉(DSP)。[28]机器人也有自己的“生命形式”和形成解释的行为背景,这种解释基于一个共享的社会现实。
综合以上,这种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的心理施动过程具备以下特征:它表现为移情主体之间感知能力的不对称,主要依赖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的先验认知能力和移情对象的行为表现,有交互“氛围”生成的社会环境是移情达成的背景。社会性和意识性可看作是移情达成的必要条件,高度拟人化的机器外表以及与人类的深度互动使社交机器人具备社会属性,只是其模拟的“意识”和计算的“情感”成为人们理解“人机共情”最大的障碍。
四、结论
也许当前的智能机器人还不能真正理解自己所表现的“内容”或执行的“程序”,但是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医疗方面,我们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移情在建立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用“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理论”框架来描述人机共情可提供一个更开放的理论空间,借用德勒兹的“异质性”概念,我们可以把人类与机器人情感双方看作是同一整体下的异质部分,为了能够理解这种情感,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情感环境,使我们自己也成为机器情感理解环境的一部分,这样就能够把机器“情感”理解为人与机器人共享的存在模式,如果我们要和机器人共享现实,我们就必须将机器人的行为看作是世界“正常”的部分,我们可以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它,这是一种特殊经验的分享。
本篇论文试图解构移情概念中主体的边界,允许机器人进入人类移情的世界,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更能激发人类情感反应的社交机器人,首先探讨我们能不能对机器人产生同理心这一认知谜题,然后过渡到是否应该以及为什么需要对机器人移情等问题,最后在直接感知理论(DPT)的基础上提出“非对称社会互动感知论”这一描述性框架,探索“人机共情”现象如何达成。可以预见,随着智能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出现具备意识能力的超级智能机器人,那么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也会迎来巨变,该探索将为我们理解自己、理解人机互动提供新的认识论。“人机共情”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作为一种工具,我们从实用的角度与之互动,但是作为一种伙伴,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情感,并在情感投入中获得情感回报。
注释:
①参见:[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1-133页。
②参见:[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奎、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0页。
③关于“Nao”的介绍,参见:《神通广大的人形机器人“NAO”》,科技日报,https://robot.ofweek.com/2018-04/ART-8321206-8110-30220328.html,2018年4月11日。
④关于柔情机器人的介绍,参见:NORRI KAGEKI,MeetAffetto,aChildRobotWithRealisticFacialExpressions,IEEE Spektrum,No.2,2011.
⑤上述观点参见:Mark Coeckelbergh,ArtificialCompanions:EmpathyandVulnerabilityMirroringinHuman-RobotRelations,Studies in Ethics Law and Technology,Vol.4,2010 .
⑥参见:Minoru Asada,DevelopmentofArtificialEmpathy.Neuroscience Research,Vol.90,2015.
⑦上述观点参见:Paul Dumouchel,Luisa Damiano,LivingwithRobot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⑧参见:de Waal,F.B.M,Preston,S.D,MammalianEmpathy:BehaviouralManifestationsandNeuralBasis.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No.8,2017.
⑨参见:Decety Jean,Fotopoulou Aikaterini ,WhyEmpathyhasaBeneficialImpactonOthersinMedicine:UnifyingTheories.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No.8,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