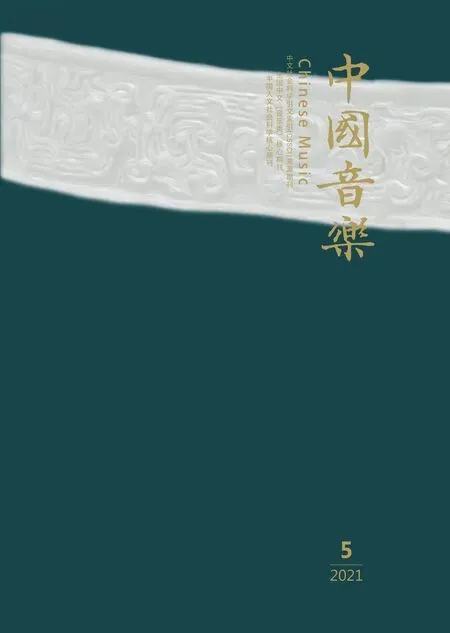乌珠穆沁部图林·哆考
○ 吴 云
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前,蒙古各部均为相对独立的部落,各部内部都有众多姓氏家族,他们以“部落”这一血缘关系为主要构成组织,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形成部落氏族社会,传承部落文化。乌珠穆沁部拥有众多姓氏,包含阿如鲁德、阿鲁楚德、额日古德、巴鲁努德等111个姓氏。①参见高·阿日华:《乌珠穆沁蒙古人》(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每个姓氏名称虽不同,但因乌珠穆沁部的首位部落首领翁衮都喇儿将所辖子民统称为“乌珠穆沁”之时,该部就已包含众多氏族,因此,这些氏族属同一个亲属集团,共同组成了乌珠穆沁部。其部落认同建立在以氏族为单位的整体部落基础上,他们共享部落记忆,具有相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有着与其他部落不同的性格特质和血缘纽带。他们所生活的区域、所操语言都具有一致性,且有统一的部落首领,有乌珠穆沁部特有的饮食习惯、服饰风格和风俗习惯,具有高度凝聚、统一的部落认同意识。
蒙古汗国成立后,蒙古各部从独立部落被整合为统一的民族,形成以蒙古各部族为中心的部族联合体。至此,蒙古各部成为蒙古族的一支,也成为蒙古汗国的一员。1207年,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征战西北,统一了西北森林中各部落,包括乌珠穆沁部。从此,乌珠穆沁部从林中百姓的氏族部落身份转变为蒙古族共同体的一员、蒙古汗国的一员。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后,蒙古各部及内部诸氏族,形成以蒙古族为民族身份的多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了各部落间的差异,构建了民族身份意识。作为“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②〔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5–66页。,其身份意识“不仅是以血缘、地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共同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③贾志刚:《民族认同论》,2011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页。,与此同时,在相同的民族身份认同下,各部还保留着独有的文化内核。而此种“和而不同”的两种身份认同较好地体现在了各部图林·哆上。它作为蒙古族共享的礼乐文化,是蒙古族各部在蒙古汗国时期建构统一的政权认同和区分各部的重要文化符号。
目前,学术界对乌珠穆沁部图林·哆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对其唱词进行阐释、对其曲调的地域性风格流派进行辨析、对其相关禁忌进行阐发等方面,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争鸣一直在继续,对当今乌珠穆沁部民间留存的两套图林·哆的辨析、对其流传地区、何时产生、为何产生等关键问题上一直仍未达成共识。认识源流意义上的乌珠穆沁部图林·哆,理清其流变过程,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历史谜题”关系重大。
笔者在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乌珠穆沁部变迁史,对两套图林·哆的变迁历史做了考证,认为随着部落变迁,图林·哆在清朝后就已发生嬗变,从原本的一套体系又增加了一套。
一、清朝前的乌珠穆沁部图林·哆
乌珠穆沁部贵族阶级的音乐生活主要体现在宴会和祭祀仪式中,而图林·哆是贵族宴会和祭祀仪式必不可少的礼仪性长调歌曲。图林·哆为蒙古语音译词,原蒙古语词由“图日”“哆”和介词“音”构成。“图林”实际是“图日”和介词“音”进行连读时所发的音。“图日”本意为“朝政、法则、声誉、婚宴”;④内蒙古教育出版社:《蒙汉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75年,第706页。“哆”即歌曲。为尊重局内人的观念表达,本文沿用其原生态表述,统一以蒙古语音译词图林·哆进行表述。
清朝前的蒙古族在军事上不仅横跨欧亚大陆,还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政权,虽在明代被打压,但仍具有一定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因此,清朝前的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不仅极具政治色彩和宫廷气息,它还是贵族阶级在宴会和祭祀仪式中彰显其贵族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它具有“朝政、家国”等内涵,体现出庄严肃穆、庄重典雅的艺术风格。此种意境的塑造不仅因歌曲本身的艺术特征,更由图林·哆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由它特定的演唱法则和礼俗禁忌所决定。
蒙古族崇尚数字“3”,宴会上素有“敬三杯酒,唱三首歌”的习俗。清朝前的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亦有三首,分别是《圣主成吉思汗》《亦禾宝格德宝勒根杭盖》《无比尊贵的喇嘛》(也叫《亦乐古森额日和图》)。⑤三首图林·哆的乐谱见道·桑杰:《乌珠穆沁民歌》(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202页。根据礼仪制度和图林·哆的演唱禁忌,乌珠穆沁部汗位继承大典、可汗的寿宴、继承或晋升官位庆典、新年参拜可汗、王爷(部落首领)等宴会和祭祀仪式,要在地位尊贵的可汗或是活佛、抑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的祝词中开始,其他在场人士需以一句“祈盼祝愿成真”作回应。随后,以图林·哆《圣主成吉思汗》拉开宴会的序幕。该歌曲体现了乌珠穆沁部对可汗的崇敬和景仰之情,蕴含乌珠穆沁部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意识、对长幼尊卑的礼仪制度、伦理道德观和对民族历史的铭记。在其演唱禁忌中,还规定其演唱顺序要求遵循《圣主成吉思汗》《亦禾宝格德宝勒根杭盖》《无比尊贵的喇嘛》的顺序进行演唱,且不可演唱这三首图林·哆以外的歌曲为序曲,更不能演唱爱情歌曲和悲情歌曲。在演唱中,“不得入内,不得外出”⑥〔蒙〕敖特根:《蒙古人民共和国部族学》(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85页。,要求正确地唱出曲调,完整地唱出唱词,认为唱错或唱不完整是很不吉利的,这既是出于对歌曲的尊重,也是出于对宾客的尊重,更是出于对祖先的尊敬。除此之外,还对图林·哆的演唱场合进行了规定,要求只可在贵族宴会中演唱,不可随意演唱。
乌珠穆沁部图林·哆在贵族宴会演唱中的固定套曲形式、固定主题、固定演唱程式、固定演唱场合与语境、对歌曲正确完整的演唱要求等习俗、禁忌和法则,对仪式形式和内容上的恪守与遵循,无不体现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仪式性、礼俗性和秩序性,也体现出乌珠穆沁部崇尚吉祥,向往美好、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和情怀。将上述三首具有庄严肃穆的历史感的长调歌曲,作为贵族宴会上演唱的图林·哆,不仅因其曲调和唱词符合庄严肃穆、富有礼仪秩序的贵族宴会气氛,更因其相关的禁忌和行为规范源自蒙古族传统的民间信仰与意识。在禁忌与规范的表征下,图林·哆隐藏着乌珠穆沁部的精神世界与追求,它是蒙古族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下对蒙古族传统礼仪的渗透与体现,是对祖先崇拜的集体情感之表达,也是强调部落集体意志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方式,更是在重申传统,加深集体记忆,以获得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所带来的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方式。
除《蒙古人民共和国部族学》等文献记载了对图林·哆的相关禁忌之外,笔者在乌珠穆沁地区采风时获得的信息也与之形成了互证。据乌珠穆沁部学者纳·布和哈达介绍,自古以来,乌珠穆沁部仪式和宴飨礼仪都遵循着详细而严格的规则和程序,即有特定的序曲、特定的顺序和特定的结束曲。他们将此类礼仪性长调歌曲统称为图林·哆。⑦参见纳·布和哈达、色·萨仁苏和:《乌珠穆沁长调叙事民歌研究》,孟根乌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研中发现当今乌珠穆沁地区虽在图林·哆的仪式性和相关禁忌上高度一致,但图林·哆包含哪几首长调歌曲、哪首歌曲为序曲、哪首为结束曲等指向性信息却存在两套说辞。对此,笔者从其文化主体乌珠穆沁部的历史变迁入手作了进一步考证。
二、清朝后乌珠穆沁图林·哆之流变
(一)两套图林·哆之谜
蒙古各部陆续归顺满清后,清朝对蒙古族地区实行了盟旗制度,蒙古社会的结构单位由原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结构转变为由军事、行政结构单位的结构。具体来说,乌珠穆沁部于1646年被分设乌珠穆沁右翼旗和乌珠穆沁左翼旗,还分别建立了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单位—“扎兰”“苏木”,在乌珠穆沁右翼旗下设5个扎兰,共21个苏木;在乌珠穆沁左翼旗设有2个扎兰,共9个苏木。⑧参见纳·图布敦、瓦·纳木吉乐苏荣、昭·斯楞东日布、昭·东布日勒:《乌珠穆沁史话》(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从部落到旗县的转变,是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变化,是行政地域的改变。在此种制度体系的变化下,乌珠穆沁部结束了原始的部落游牧生活,开始了以“旗”为行政单位的定居生活,从原本完整的部落被分化为两个旗,生活方式从自由迁徙的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式的畜牧业生活。在此过程中,其行政权虽仍归属部落首领,但部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转而形成了以各旗为中心的新的认同意识,即地域认同与行政认同。而随着这些变化的到来,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据《乌珠穆沁史话》记载,清朝乌珠穆沁左翼旗的图林·哆包含《前世积福》《圣洁的天空》《额日德尼嘎拉巴日森》《翁根格日乐》和《圣主成吉思汗》⑨参见纳·图布敦、瓦·纳木吉乐苏荣、昭·斯楞东日布、昭·东布日勒:《乌珠穆沁史话》(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五首长调歌曲。此记载在数量和曲目上均有别于清朝前的情况。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接触了上百位民间艺人,其中不乏毕生从事乌珠穆沁部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们对图林·哆庄严肃穆的礼仪性特征和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有着绝对性的统一认识,但对其包含哪几首歌曲等具象化的问题却说法不一。面对此情况,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只有部分艺人对该问题有正确认识。若如此,这代表当今流传的两套图林·哆中,有一套不属于乌珠穆沁部图林·哆。第二,民间艺人对图林·哆没有认知偏差,确有两套图林·哆。若如此,为何原本已高度规范化、套曲化了的图林·哆在今会存有两种版本呢?于是,笔者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第二轮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工作。
在笔者探究艺人的背景资料后发现,图林·哆的不同版本与艺人所属地域有关。今内蒙古锡盟西乌旗的乌珠穆沁人普遍认为图林·哆有三首;东乌旗的乌珠穆沁人普遍认为有五首。数量和曲目上的分歧在今天的东、西乌珠穆沁人身上具有普遍性。笔者认为,此种普遍性的认知差异绝非在短时间内可建立。进一步探索后发现,这一分歧主要与1646年清朝对乌珠穆沁部进行的盟旗制度密不可分。清朝分而治之的盟旗制度和边禁制度使乌珠穆沁部以旗为单位,逐渐限定在某一特定地域范围内,从血缘逐渐转向地缘,从流动向静止的地域性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促使乌珠穆沁右翼旗和左翼旗形成不同的文化空间区域格局,使部落血缘纽带逐渐让位于地缘纽带,部落的范畴逐渐被赋予了某一特定空间的含义,进一步使包括图林·哆在内的音乐文化走向以地缘为主的表现方式。被划分为两个旗县后,原属于乌珠穆沁部的三首图林·哆,在这种行政区域的分化中发生了分歧,即右翼旗延续了上述三首长调为图林·哆;而左翼旗从右翼旗被划分为独立的旗县后,与当时的右翼旗“平起平坐”,基于此种政治基础之上的地域认同与行政认同,必然促使其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礼仪音乐体系,加强其地域认同与行政认同。而图林·哆作为部落贵族礼仪音乐,其深厚的政治因素、不可替代的地位在乌珠穆沁部早已根深蒂固,通过图林·哆完善自身文化信仰体系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左翼旗在建旗后逐渐建立起了新一套的图林·哆作为礼仪音乐。
左翼旗图林·哆作为后新建的礼仪音乐体系,为何保留了《圣主成吉思汗》,摈弃了其他原图林·哆曲目,又新增了其他四首长调呢?对此问题的解释,要从这四首长调谈起。《圣主成吉思汗》作为清朝前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之一,代表的不仅是对铁木真个人的敬仰、崇拜之情,更是对蒙古汗国的建立者和开拓者的歌颂之意。对蒙古各部而言,这是蒙古族民族共同体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和绝对信奉的民族主义。因此,即便被清朝统治,该歌曲仍被左翼旗奉为图林·哆之一。另四首图林·哆《前世积福》《圣洁天空》《额日德尼嘎拉巴日森》和《翁根格日乐》⑩四首歌曲的乐谱见纳·布和哈达:《乌珠穆沁叙事民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6、475、541、540页。均为佛教歌曲。这与清朝在乌珠穆沁地区大肆宣扬佛教、修建寺院,寺庙成为乌珠穆沁部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等诸领域的交流中心⑪参见《东乌珠穆沁旗旗志》编委会:《东乌珠穆沁旗旗志》(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的史实相吻合。
(二)乌珠穆沁左翼旗宴会结束曲之由来
左翼旗成立后,民俗礼仪及仪式歌曲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歌曲《阿比达佛》上。该歌曲是左翼旗宴会特有的结束曲。据纳·布和哈达对那仁其其格进行的访谈,该歌曲产生于清朝前,但后来的左翼旗将此歌定为宴会结束曲。至今,此曲一起,今东乌旗宴会便随之结束。此种仪式习俗的延续,其意义已跨越了它单纯作为一首歌的意义,它更具承载民俗仪式的符号意义。而佛教歌曲成为宴会结束曲、成为一个既定的规则延续至今,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朝时期佛教对乌珠穆沁地区的影响之深。
据记载,1722年至1794年这72年间,左翼旗新增建了六座寺庙,喇嘛人数也越来越多,每座寺庙都有相应的敖包。到了18世纪末,单是嘎黑勒寺庙中的喇嘛人数已达到600名之多。⑫参见纳·图布敦、瓦·纳木吉乐苏荣、昭·斯楞东日布、昭·东布日勒:《乌珠穆沁史话》(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此社会背景下,乌珠穆沁部图林·哆融入了更多佛教歌曲,还以佛教歌曲作为宴会结束曲。这符合清朝大肆宣扬佛教的宗旨和左翼旗的佛教普及情况,也符合新建的左翼旗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礼仪音乐体系的状态。于是,左翼旗开始将这五首长调奉为图林·哆。这就解释了为何两个旗同属一个部落,其图林·哆却不完全相同,也解释了左翼旗以佛教歌曲作为宴会结束曲的现象。
(三)两套图林·哆流传地区之谜
上文已揭示当今两套图林·哆之谜,但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两套图林·哆在流传地区上存在分歧。今西乌旗以上文中提到的三首歌曲为图林·哆,而今东乌旗却同时流传着两套图林·哆,即有的认为是《圣主成吉思汗》《亦和宝格达宝勒根杭盖》和《亦拉古森额日和图》;有的认为是《前世积福》《圣洁的天空》《额日德尼嘎拉巴日森》《翁根格日乐》和《圣主成吉思汗》。对此,笔者作了进一步考证和调研。
1945年乌珠穆沁人大规模迁徙至今蒙古国境内,致使左翼旗的9个苏木仅剩下3个苏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锡盟东部联合旗,将乌珠穆沁右翼旗、剩下3个苏木的乌珠穆沁左翼旗和浩其特左翼旗地域纳入其行政管辖内。1956年将东部联合旗改为西乌旗,又建立了东乌旗,将原乌珠穆沁左翼旗大部分疆土、原乌珠穆沁右翼旗的一半领土、原浩其特左翼旗和浩其特右翼旗的部分疆土划分至东乌旗,⑬同注⑪。形成了今西乌旗和东乌旗地域。此次疆土划分直接导致了原右翼旗的近半数人口所属旗县的变更。距今,他们被纳入到东乌旗行政管辖还不到70年,仍秉持着原右翼旗信奉的三首图林·哆的礼仪制度。因此,在今东乌旗做调研时才会出现该旗民众对图林·哆有两套说辞的现象。在乌珠穆沁部有众多研究本部落文化的地方学者,其中,巴德玛苏荣老人对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也有着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其观点与笔者不谋而合:持“东乌旗‘图林·哆’有五首”这一说辞的民众均为原左翼旗人,持“东乌旗‘图林·哆’有三首”这一说辞的民众均为原右翼旗人。这恰恰说明了原右翼旗人被纳入到今东乌旗之后,仍保留着原右翼旗身份认同。
(四)图林·哆的内涵与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改变,乌珠穆沁部图林·哆不仅在数量和具体指向上发生了变化,其内涵与意义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前文已阐述图林·哆一词中的“图日”具有“朝政”“政权”之意,再加上清朝前蒙古族曾建立过政权,使当时的图林·哆颇有政权意味;清朝的乌珠穆沁部被划分为两个旗县,这一时期的图林·哆不再具有国家政权之意,而被赋予了“旗政权”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昔日居于社会顶端的蒙古王公贵族和寺院高层喇嘛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种变化在贵族音乐生活上的重要体现便是王府乐队面临解体、王府贵族府邸特定的音乐生活失去了表演语境,作为贵族音乐的图林·哆从过去严格的宫廷礼仪音乐逐步走入民间,“以‘半活态’形式封存在民间”⑭杨玉成:《蒙古族长调分布及其现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68页。杨玉成指出:“‘半活态’,是指活态传承人虽然存在,但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民俗语境消失,从而处于‘休眠’状态的存在形式。”,逐渐成为了黎民百姓日常宴会上的、在一定程度上遵循演唱禁忌的礼仪歌曲。至此,乌珠穆沁部图林·哆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体现出时代性内涵与意义。
小 结
在部落层面上,蒙古族文化的产生以游牧文化为基础,以血缘为认同的部落为单位。随着以部落组织为单位进行迁徙,蒙古各部文化的产生和变迁也不断变化着地域范畴,也是在此种动态过程中,蒙古各部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同时,蒙古各部文化的形成,还有一重要因素,即清朝对蒙古族地区进行的盟旗制度。这一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还改变了其原始的以血缘为组织单位的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地缘为共同体的组织单位,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统一体逐渐分散为以地缘为纽带的集合体,部落分布被赋予了地域空间概念,于是有了当今同一部落分属不同旗县的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地域性差异开始凸显,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认同观念上。图林·哆在乌珠穆沁部被清朝划分为右翼旗和左翼旗时发生的变迁,即是部落认同逐渐居于次要地位、转而强调地域认同的最好例证。
根据乌珠穆沁部图林·哆在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特点,可将其分为清朝前、清朝后两阶段:清朝前,在以血缘为组织方式的部落统一体中,图林·哆在宫廷仪式和贵族宴飨中得以发展;清朝,乌珠穆沁部身份的变化、地域认同和行政认同的产生、血缘认同的淡化,再加上清朝对蒙古族地区的一系列政策,使其文化受到佛教文化影响,造成图林·哆在右翼旗和左翼旗中数量不同、曲目不同、佛教歌曲增多。后随着国家重新做行政划分和疆土划分,使两套图林·哆同时出现在了今东乌旗。另外,乌珠穆沁部图林·哆的内涵也随之体现出从朝政歌曲到彰显旗政权的仪式歌曲、再到民间宴会仪式歌曲的时代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