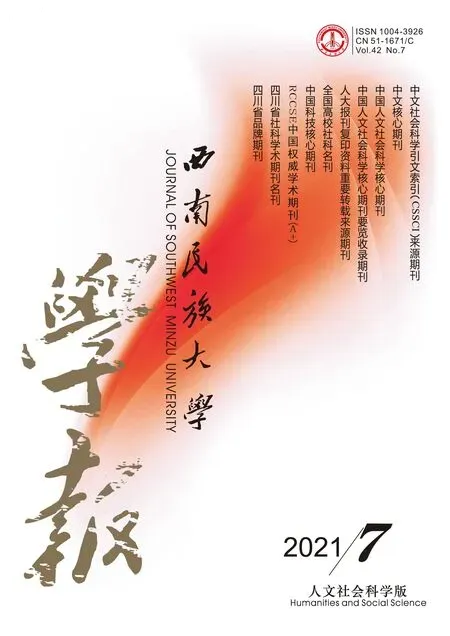吐蕃时期政教关系新论
李元光
[提要]“王辛同治”是吐蕃前期政权治理的基本模式,当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开始学习周边民族的治理模式,建构法治与引进佛教,强化赞普集权,限制本教对政权及社会事务的干预。本教是维系吐蕃政权的法理根基,佛教是顺应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文化。随着时局的变迁,统治者对“两教”有不同的偏好。对统治者来讲,宗教与自身信仰无关,是维护统治与争权夺利的工具。厘清吐蕃时期的政教关系,有助于理解西藏历史上政教关系的本质与“政教合一”的演变逻辑,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
一、吐蕃前期的政教关系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最早的吐蕃,“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寨,……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1](P.173)所以,鹘提悉补野在部落间的“相互剿灭”中胜出,成为雅隆河谷一带诸部落之首领,据称其聂赤赞普是第一代藏王。
吐蕃前期的政教关系,可用“王辛同治”一词来概括。它表达的是吐蕃政权与本教水乳交融的关系。本教为西藏最早的本土宗教,据传它比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还要久远。一般认为吐蕃本教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在象雄(羊同)本教传入吐蕃之前,吐蕃就已有各种各样的原始本教,史称笃本。如土观大师所述:原始本教“只有下方作镇压鬼怪,上方作供祀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事而已,并未出现笨教见地方面的说法”;中期本教即伽本(恰本)是“支贡赞普王(第八代藏王)时,藏地的笨徒还无法超荐凶煞。乃分别从克什米尔、勃律、象雄等三地请来三位本徒来超荐凶煞。其中一人行使除灾巫术,修火神法,骑于鼓上游行虚空,开取秘藏,以鸟羽截铁,显示诸种法力。一人以色线、神言、活血等作占卜,以决祸福休咎。一人则善为死者除煞,镇压妖厉,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这三人未来藏以前,本教所持之见地如何,还不能明白指出,此以后本教也有了关于见地方面的言论。据说伽本乃溶混外道大自在天派而成的。”后期本教即局本,又称居尔本,意为翻译本,是佛教传入藏地后,本教徒“将一些佛典,改译成为笨教的书”所成[2](P.194-195)。
(一)本教在维护王统方面的作用
学界认为,在各种史籍(含藏文)中,未发现在赤松德赞前有佛教参与政治的记录,即使在赤都松赞普铲除噶尔家族这样的大规模政治斗争中,也不见佛教势力的介入。因此,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到吐蕃王朝赤松德赞设僧官以前,本教一直是其“王家宗教”①,它在维护王统方面作用如下:
1.拥立赞普为王
据本教典籍记载,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本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著名的班度五王子之一的嘉僧,因遭到放逐,在藏地寻求避难,是“扎拉赛、地神苯和十二智慧苯的其他苯教徒查验了他的标记,用芳香水为之洗浴,并立他为王,取名为聂赤赞普。”[3](P.345)《雍仲本教史》也根据《象玛救护种姓母》记载了本教徒拥立聂赤赞普为王的这一过程。[4](P.59-60)在藏传佛教典籍《布顿佛教史》中重复这一故事:当王子“来到赞塘果玉地方,被当地本教徒看见,说他沿着天索和天梯而来,是位天神,后问他是谁?回说是赞普;再问他从哪里来,他手指天空,彼此不通语言。于是众人将他置于木座,四人用肩扛抬,让他做‘我等之君长’,尊为聂赤赞普,是为藏地最初之王。”[5](P.192-193)《西藏王臣记》也讲聂赤赞普下凡时,正好碰上放牧的十二个本教徒,认为此人是神子下凡,来作藏地之主,“遂以肩为座,迎之以归,因此遂称为‘聂赤赞普’,此与《青史》中所说的赤·赞普·沃德,同为一事。”[6](P.9-10)此说还可参见《汉藏史集》等藏传佛教文献。上述说法虽掺有神话不足为信,但连竞争对手藏传佛教典籍也认可本教徒拥立藏王,却是不争的“史实”。
2.证王权神授
在早期本教信仰中,对天神的信仰是其重要内容。吐蕃赞普们必须借助本教“神子”之说,赋予政权以神性从而获得民众认可的“合法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降世天神之上,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七位,墀顿祉之子即岱·聂墀赞普来作雅砻大地之主,降临雅砻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1](P.174)据《本教史料汇编》中《扎巴林扎》记载,象雄王国时期,在吐蕃没有国王,也没有诸侯,但有辛饶的宗教传播,以辛南喀囊瓦多坚为上。最初的神散吉珍玛坚对斯巴桑波说,现人类无王,动物无助,请转一位王子。于是,父桑波同母曲坚按照人类的风俗居住在一起,生下九子九女。后又经过九子九女一代又一代的神奇繁衍,直到聂赤赞普的诞生。[7](P.148-152)本教试图说自己是吐蕃政权的缔造者,从而证明王权与本教不可分离,藏传佛教史籍也大多附和这一说法。
3.保盟誓
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直至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权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盟约”成为联盟政体维系王室与各部落(邦)政治、经济及军事同盟的核心纽带,因此赞普不得不同各个奴隶主家族(帮主)不断订立和确认盟约,是典型的“盟存政立,盟去政废”的政权。靠什么来担保盟约得到各部落的严格遵守呢?盟约的“见证人”是不大靠得住的。而当盟誓由本教巫师主持并按本教仪轨进行,本教为盟约保驾护航的作用就突显出来了。这时的盟约不但有人作证更有神作证,而神作证比人作证既多了一份神圣不可亵渎的崇高,更有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神力加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②、马、牛、闾(驴)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此牲。’”[8](P.178)《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大事记年》(PT188),记载了从狗年(公元650年)起的120年间,每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虽然每年记录的文字只有寥寥一二百字,“盟誓会议”总是充斥其间,足以说明“盟誓”对政权的重要性。
4.问社稷
吐蕃时期,上至征伐大事,中至事业成败、下至生产生活,无不问询于本教巫师。“邦色苏孜与当聂闷忠心耿耿于赞普驾前,卜问:如向李迷聂征讨,能否获胜?得此卦辞:以后,属地将扩增一倍,途中遇大财运,大吉。卜问个人、亲属生命安危,问敌人是否来犯,均吉。”[9](P.78)这是在决定“征讨羊同”之前的一次卜问。吐蕃正是通过这次卜问,举兵将其消灭。
“邦色苏孜问社稷二十次皆为‘则木巴约档’(一种卦象)吉。三代人与国王、社稷、兴旺;其后,社稷衰败。或,人神不悦,引来魔怪、妖精、瘟疫、厉鬼等。国王与尚论生命危险,凶。”[9](P.80)主持这次卜问是当时的大相邦色苏孜,从卜问的内容看主要是社稷兴衰与赞普个人的安危。
仅列上述两例说明,本教在政治军事决策以及辅佐王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土观宗派源流》“考诸王统记,仅说‘从聂赤赞普至赤吉脱赞之间,凡二十六代均以苯教治理王政。’”[2](P.194)另据《西藏王臣记》:“王族世系共有二十七代。其在位时,咸以苯、仲、德乌三法治理王政。”[6](P.11)另据本教经典《斯巴续部目录》记载:“赤德祖赞以前,王政由雍仲本教辅佐。”[4](P.99)
5.御民之术
《贤者喜宴》这样描述所谓“获财”③四种“因本”的社会作用:“囊辛本教之裴兑坚,它是为了祈福,求得人财两旺。垂辛本教之裴村坚,它是为了施舍送鬼用品,克服违缘。恰辛本教之久梯坚,它是为了指明善恶、阐述诸漏神通。图辛本教之村哈坚,它是为了卜算人之生死。”[10](P.10)《西藏王统记》指出:“当时王政以仲、得乌作为御民之术。”[11](P.35)由此可见,当时的本教操纵着普通众生的生活,大到生死福祸、祭神驱鬼,小到是非诤讼以及求医问药等方方面面。本教还将个人的际遇、人间的福祸归结为神鬼的旨意,为统治者制造的人间的苦难推卸责任,同时要求民众不得违反“天神”的旨意,否则将遭到瘟疫、洪水、雷击、冰雹等灾害的惩罚。
(二)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响
本教对维系政权是一柄双刃剑。由于本教创立于象雄国,经师阶层均出自此国,而起源于雅隆河谷的悉补野家族建立的吐蕃政权,在松赞干布征服象雄前只是它的邻国,吐蕃赞普们得时时提防这些“外人”,因为经师阶层与比吐蕃新政权更强大的象雄王国的利益休戚相关。
1.本教成为臣属挑战王权的工具
在“王辛同治”的政治格局中,本教以吐蕃政权缔造者身份分享王权。《藏族雍仲本教史妙语宝库》引《本续日灯》中的记载:“所谓‘天赤七王’,每一国王有守护‘本辛’各一人,本、辛有很大权势。”[4](P.80)传统上由本教经师用象雄语给赞普起名也说明这一点。《雍仲本教史》记载了本教与王权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是在“第八代藏王子贡赞普时,形成了‘赞普王权大、大臣议事(权力)大、辛本教能力大’的政治局面,于是有大臣对子贡赞普说:‘现赞普陛下与诸辛本教师长相等,所有属民已被辛本教所收拢,因此,他们对诸辛本教大师的崇敬已大于赞普,如果现在对诸辛本教不采取贬低措施,那么到(赞普)儿子之时,肯定将被本教所夺(按:指权力)。’因此子贡赞普决心灭本教,本教因此衰败。子贡赞普也因此心受妖魔蛊惑,遂邀洛昂达孜比武。”[10](P.21)洛昂达孜十分恐惧,当晚梦到本教护法化身授予巫术,从而打败子贡赞普,篡夺王位。[4](P.94)
即便经过“法王”赤松德赞几十年大力抑本兴佛,在他离世尸骨未寒时,本教势力即卷土重来,反对他的丧葬超荐用佛教仪轨,“欲为举行苯教丧葬”。牟尼赞普只好召集佛本两派论议。年幼的牟尼赞普虽高居中堂,但他左边是崇本的大臣,右边是本教大师,“未见为众僧设有合适的席座”[12](P.27),显然实权已落入本教势力之手。这也表明哪怕是赤松德赞时期,也不能高估佛教在吐蕃的影响力,它大抵只能称得上是“王家宗教”。走出皇室,影响操控吐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还是本教。所以在这次辩论中首席崇本大臣钦·赞协列斯才有底气放话:若要选择佛教,“从此国政大事有请佛僧做主,国王服侍有劳佛僧操劳,保边守土之责有请佛僧担当。”[12](P.30)在吐蕃历次权力的争夺中,本教的拥趸者清楚,他们的权力来自本教对政权的制约,失去了本教,也就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2.本教的山头政治
据本教《光荣经》讲:“古代,在人类即将降生那一界之初,祈祷三狮战神分别降生。第一位降生在一座金山上,山右侧有一条翠绿色峡谷。第二位降生在一座螺壳白色山上,山左侧有一条蓝灰色峡谷。第三位降生在一块石水晶附近的光湖里。它们衍生出人类,因此,每个氏族都化现出一位战神,每位战神都有一支神兵大军,每支神兵大军都有一位保护者,每位保护者都有一位护法神。”[3](P.105-106)虽然吐蕃前期,大众都信奉本教,但本教的核心观念是泛神论与多神论,信仰天地日月山水等自然之神。不同的神灵驻留于不同的山山水水,受到不同群体的朝拜。各地由于共同信仰一山或一水之神而形成一个个分散的社会集团(部落),造成社会的分裂,形成“山头政治”不利于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
即使在吐蕃强盛时期,当松赞干布年幼继位之时,吐蕃仍发生过盟友的叛乱。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羊同),牦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父王囊日伦赞被进毒遇弑而薨逝。王子松赞幼年亲政,对进毒为首者诸人等断然尽行斩灭,令其绝嗣。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1](P.165)又如琼保·邦色苏孜这样对吐蕃王朝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大臣也是晚节不保。他曾“割藏蕃小王马尔门之首级以藏蕃两万户来献,(其土地民户)均入于赞普掌握之中。”[13](P.142)但晚年因设计暗害赞普事情败露,“琼保·邦色乃自刎毕命。”[1](P.165)还连累其子昂日琼只好割下老父首级,向松赞干布自首,请求赞普不灭其家族,得到赞普赦免。
由于吐蕃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权是靠盟约维系的,而本教的多神崇拜所带来的“山头政治”一直影响吐蕃政权。分析吐蕃王朝崩溃后,整个西藏社会分裂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山头政治”的宗教因素不可忽略。即使到了公元20世纪上半叶,更敦群培仍在讲:“每翻一座山,就有一种不同的宗教,数千位智愚不等的人,哄起而信从,人们各自宣称‘唯有此派,真实不欺’,对如此之自我标榜,同宗派的人听后,将会欢愉喝彩,而他宗人听后,将会嗤之以鼻。”[14](P.20)
3.本教的非理性因素
早期本教总体来讲是一种非系统化、理性化的宗教,其“占卜”“招魂”“超荐”“驱鬼”“禳灾”“牲祭”“断讼”“处罚”“诅咒”“法术”等充斥着各种非理性因素。仅就“牲祭”来说既即不理性也不文明,且对经济有一定的破坏作用。据《空行益西措杰传》(拉萨旧木刻版)记载,本教每年秋天要举行“鹿角祭”,将许多公鹿一起杀死,取血肉献祭;冬天要举行“本教神祭”,将牦牛、绵羊、山羊等公畜各三千头杀死,同时将上述牲口的各一千头母畜活活肢解,用以祭神;春天还有“本教祖师祭”,用粮食和树木进行所谓的“烧烟”祭;世人遭遇病患时要献祭赎命,视其经济状况从杀公畜母畜各一头至三千头不等;当人身故后为制服鬼神,也要举行上述杀牲祭祀。这也成了佛教徒一再攻击的把柄,“辛苯教徒,滥杀畜牧诸如牛、羊、马等无数,‘直珍’和‘觉米’等以火焰来多次举行‘祭鬼’,‘苯甲堆’等仪式,前恶未尽又添新罪,执迷于错乱之教。”[12](P.29)对一个新兴向荣的新政权——吐蕃王朝来讲,必然寻求更先进的文明取而代之,故当代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认为:“由于看到大规模杀牲祭祀对吐蕃畜牲业造成严重损害,松赞干布才下令禁止本教。”[15](P.6)
二、松赞干布开启的“法治文明”
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位后凭借武力统一全藏,建立了吐蕃王朝。在他之前,经过三十多位赞普的经营,吐蕃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当时已“制造升、斗及秤,以量谷物及酥油,此外,还出现了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自汉地取得历算及医药”[10](P.14-15)等等。因此,东嘎·洛桑赤列认为:“松赞干布时期藏族社会基本上是奴隶制,但也产生了封建经济关系的萌芽。”[15](P.10)随着王朝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王辛同治”以及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的政治体制难以适应新政权的需要。为排除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响,限制本教对政权的过度干预;更为了将原来落后的部落联盟政权改造为更加高效也更加集权的政体,吐蕃王朝吸收借鉴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治理模式和先进文化,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和文化创新,其中政教关系是其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纵观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其宗教政策与制度的调整改革无不充满政治算计,为改变吐蕃早期形成的本教对政权的钳制,从松赞干布开始,引进法治削弱本教对政治及社会事务的全面干预;引进佛教削弱本教一尊独大的地位;引进外来文化削弱本教的文化霸权。
首先,制定“六奎”④:(1)“将吐蕃划作五大如(军政区);(2)划分18个地区势力范围;(3)划分61个‘桂东岱’(军事千户部落);(4)将‘雍之人部’划分为‘更’及‘扬更’;(5)由三尚一论掌管中央集会会址;(6)三勇部卫戍边地哨卡。”[10](P.31)
其次、在松赞干布前的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权中,并未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统一的文官层级治理体系。因此,松赞干布在划分设置“六奎”的同时,设置吐蕃奎本、香雄奎本、苏毗奎本等加以管理。“六奎”及“奎本”的设立,使治权从中央一直延续至基层的“哨卡”。他设“五如”时设“如本”,设“六十一个‘桂东岱’”时设“东本”,在东岱之下又设“将头”。“奎本”“如本”“东本”为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最高军政指挥官,由各部落首领或贵族担纲,他将军事组织与氏族部落组织合二为一。这种军政体制,不仅强化了中央的集权,政(军)令畅通,而且使吐蕃“全民皆兵”,在日后的征战中所向披靡,使唐王朝吃尽了苦头。
松赞干布还借鉴唐朝的典章,把部落联盟与文官制度结合起来[16](P.152),试图把占据领导地位的悉补野部落首领与其他被领导的部落首领之间的原始部落结盟关系,变成一种带有封建专制性质的臣属关系,在王朝中央建立起庞大的“内外中三大臣”官僚体系,将过去“盟主”与“盟臣”关系转变为“君主”与“大臣”关系。同时改革最高决策的“盟约会议”,常设“尚论”于“小会议室”,使政权的运作方便高效。随着王权的强化,赞普已掌握了对臣下及诸豪门部落首领的生杀予夺大权,建立起以赞普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治理体系。
第三,制订法律典章制度。《贤者喜宴》记载了松赞干布制定法律的初衷:“往昔,因无法律以致众小邦离散。况且,若无法律则犯罪猖獗,我之众属民亦将沦于苦难之中,故此,应当制定法律。”[10](P.31)于是“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法律及事业之楷模。”[10](P.30)可见向周边民族借鉴并制定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防止分裂,维护政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据该文献记载,当时颁布的《六种大法》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其制定的法律中有明显限制打击本教势力的内容:一是位于《六种大法》之首的《以万当十万之法》规定“九大论”决断内政、外务;又在《王朝准则之法》中规定王朝事务可行与不可行,以及克敌制胜等均由法律决定;加上《六种大法》之《扼要决断之法》和《权威判决之总法》明确规定了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以及处理程序。这就大大限制了本教过去决定军政大事“问社稷”以及“决讼”的作用。二是在“六种告身”即玉、金、颇罗弥(合金)、银、铜、铁中,本教徒仅获“小银文字告身”,与王臣身边的管理人员及边境哨卡地位相当。三是在律条中规定:“为后世利益而推行佛教,对显贵有缘者(所讲)之佛教,则不讲授给无缘之贱民。”[10](P.52)“显贵褒以佛法,贱民贬为纺织工及本教徒。”[10](P.51)再加上松赞干布迎娶两位信佛的公主,以及翻译佛经、修建寺庙等情况来看,他有意引进佛教,将佛教作为上等人的荣誉标志,规定“佛贵本贱”,以此羞辱和打击本教徒,因此本教文献认定这是吐蕃历史上“第二次灭本”⑤。我们认为抑本是可能的,但“灭本”是说不上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松赞干布主要不是用“兴佛”来“灭(抑)本”,而是用“法治”手段限制本教势力对王权和社会的干预控制。
第四,松赞干布大力推动文化事业。法典的颁布离不开文字,“然为顺应浅慧众生之心机,正确执行政教法令,治理王政,王心思维,文字乃众德之本。”[6](P.15)于是派出吞米桑布扎前往印度学习并创制文字。同时“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了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10](P.30),“仍遣豪酋子弟,请入国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8](P.10)“教民习书,马饰文彩,创兴礼仪。”[11](P.47)
松赞干布法治文明建设的功绩,《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颂道:“黔首民庶高下尊卑不逾不越,轻摇薄赋,安居乐业。”“吐蕃古昔并无文字,乃于此王之时出现也。吐蕃典籍律例诏册,论、相品级官阶,权势大小,职位高低,为善者予以奖赏,作恶者予以惩治;农田耦耕一天之亩数;牧场一件皮褐所需之皮张数;笼区长度均作统一划定,乃至升、合、斤等一切量度,举凡吐蕃之一切纯良风俗,贤明政事,均为此墀松赞王者之时出现也。一切民庶感此王之恩德,乃上尊号‘松赞干布’。”[1](P.169)
总之,松赞干布时期政权的统一、政治体制的改革、典章制度的建构、先进文明的学习借鉴,一方面限制了本教的权力,原来由本教巫师执掌的“卜问”“决讼”等处理军政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交给了法律与制度。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吐蕃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从一系列敦煌吐蕃的法制文书及诉状来看,民众之间的纠纷可以靠法律来解决,而不是凭势力大小与巧取豪夺。特别是其中多次提到的用“命价赔偿法”代替习惯上“血亲复仇”更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7](P.585)所以,松赞干布对社会的“法治”及“封建专制”改造虽然强化了赞普的集权,终因经济基础所决定,仍然是一奴隶制部落军事联盟政权。正如东嘎·洛桑赤列所说,至多是“产生了封建经济关系的萌芽。”[15](P.9)
三、兴佛抑本的宗教政策
公元8世纪初,赤德祖赞上任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高举佛教的大旗,进一步削弱本教对王权的干预。佛教与本教相比在政权治理方面有如下优点:
第一,佛教全盘接受本教关于赞普是“天神之子”的观点,同样维护王权的“神性”法理基础。由吐蕃最早的僧官韦·赛囊写就的《韦协》一书,同样用“天神之子”称呼赞普。在关于赤松德赞的葬礼是用本教还是佛教仪轨的辩论大会上,当时著名的佛教大译师毗卢遮那虽然历数本教导致象雄等国“国政衰亡”,但他称颂赞普是“寂护之世系,三怙主之化身、大慈悲之主、黎民之王、神之子嗣”。“此处把‘寂护之世系,三怙主之化身、大慈悲之主’的佛教说法和‘黎民之王、神之子嗣’等苯教的称呼糅合一起,可谓用心良苦。”[12](P.133)更不用说后期佛典在追述吐蕃历史时皆沿用本教“天神之子”说法。所谓“用心良苦”说白了,佛教一方面继承本教神化王权之说,另一方面一来到藏地即封松赞干布为“圣观世音的化身”[12](P.3),将“法王”“转轮王”的名号赠予最高统治者,使其王冠上增加一道佛的光环。“神圣”叠加“慈悲”,“替天行道”加上“诸善奉行”,双管齐下,共同“见证”着政权的崇高与伟大。第二,佛教教义、教理系统成熟,理性化程度高,有利于克服本教非理性因素对政权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第三,佛教的“苦”“空”“轮回”教义,让民众安于现状,将幸福寄托在来世;其“诸恶莫作”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第四,佛教作为新兴外来宗教同吐蕃传统部族势力没有瓜葛,易于赞普掌控。第五,佛教代表的是适应吐蕃社会发展潮流的进步文化,用东嘎·洛桑赤列话说:“正是由于佛教内容与当时藏族社会的经济关系是相适应的,所以松赞干布才能信奉和发展佛教。”[15](P.11)
最后,高扬佛教还有另一层原因,在松赞干布时“东方之咱米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香雄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了半个世界”,基本完成了吐蕃王朝的版图扩张。在统治者看来,接下来所进行的扩张战争不仅破坏了同周边的和睦,同时壮大了各地贵族奴隶主势力,他们凭借在战争中的贡献及日益壮大的实力,常常拥兵自重,甚至“欺凌”赞普,噶尔家族就是典型代表。于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即赞普王室“主和”,贵族大臣们“主战”。而佛教所倡导的“息战弥争”和平思想正是王室对付贵族大臣的有力武器。所以,赤德祖赞继位后,一方面提高佛教在政治上地位,另一方面就是同周边缔结和平,这成为赞普王室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大臣权力的两大法宝。据历史资料记载,从赤德祖赞继位的公元705年算起,至赤热巴坚时的公元821(唐穆宗长庆元年)的116年间,吐蕃同唐朝共订10次盟约。在这些和盟中,反复提到“舅甥一家”“社稷如一”,其背靠实力强大的唐王朝,压制内部大臣及地方势力的意图明显。
(一)提高佛教在王朝中的地位
从现有史料来看,尽管佛教在松赞干布时已从汉印等地传入吐蕃,但真正由赞普大力弘扬始于赤德祖赞时期,据敦煌藏文写卷《于阗教法史》记载:“公主(金城)在吐蕃修建了一个很大的寺庙,给寺庙献上土地与奴隶、牲畜。全体比丘来到这里,生活均由公主供养,吐蕃之地大乘教法更加宏扬光大,十二年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幸福。”[18]《汉藏史集》等对此也有记载:在于阗由于政治动乱发生了排佛事件,不少佛教信徒被迫流亡外地,有一部分进入吐蕃,金城公主知道后,向赞普建议收容这些佛教徒。这段史实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将土地、奴隶、牲畜赐予寺庙;二比丘生活由政府供给。[19](P.52)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为后来赤松德赞大规模施行这一制度开了先河。赤德祖赞还先后三次派出使者到印度和汉地专门求取佛法,相比松赞干布是应公主要求派人求法不同,这是赞普本人的主张与行为,表明发展与推崇佛教是出于政权建设需要,是政府行为。
赤德祖赞的崇佛遭到了本教大臣抵抗,据史载赤德祖赞去世后,“王子随即执政,但尚未成年,因此,舅臣玛祥仲巴杰说道:‘王之寿短,乃系推行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本教行之。谁推行佛法,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并制定小法(专门惩治佛教)。”[10](P.122)当时的信佛大臣被定罪流放;来自汉印等地的和尚遭驱逐;安放在小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历尽磨难,通过多方谋划和努力,才在“搬不动”的理由掩护下得以埋入地下;连桑希从汉地请来佛典也只能“埋藏秦浦的荒山缝隙之中”;韦·赛囊(益西汪波)好不容易从菩提萨埵(静命)处请来的真经也无用武之地,慑于玛祥之“小法律”,只好“到地方上隐藏起来”,佛教发展一时陷入低谷。赤松德赞成年后,召集崇佛大臣设计将反佛大臣玛祥活活关进坟墓,才使这场法难得以终结。
(二)佛教代替本教成为王家宗教
我们看到佛教在吐蕃传播与兴盛的一大特点是“至上而下”,由王室及贵族首先信奉并加以推广。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作为“王家宗教”而存在的。雅克·巴科在《吐蕃王朝政治史》中认为:“赞普是第一位皈依佛教的人,佛教是从王位上开始传播,……它不象在印度那样是自我传播的,而是在政权的压力下扩展的。”[20](P.28-29)上文提到赤松德赞剪除玛祥执掌实权后,采取了一系列“兴佛抑本”措施:
首先是令桑希取回从唐朝求得的一千部佛经,随后又令桑希会同“汉人梅果、天竺阿年达等精通汉语者加以翻译”。同时,赤松德赞在建中初年就开始向唐朝启请汉僧入藏,据《册府元龟》卷九八零记载:“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诱、文素一行,二岁一更之。”其次是迎请静命大堪布赴藏宣讲佛法,并按静命要求派人请来密宗大师莲花生。第三“于大臣和属民中选聪明利根子弟七人,使从菩提萨埵(静命)出家。”[11](P.121)吐蕃首次有了本土的出家人——“七觉士”。第四修建桑耶寺。第五制定佛教法律,建立兴佛盟誓碑。从此挑战佛教就是挑战法律,且违背誓言,给佛教上了“双保险”。第六成立佛教组织,任命僧官。第七制定“三户养僧制”,提高僧人的政治地位。从此佛教寺院开始有了自己的奴隶和经济基础,标志着佛教僧伽组织由原来依附政权的非独立的社会阶层,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属民和土地的新兴的奴隶主阶级。第八规定“佛法之会议室”地位高于“大尚论之会议室”,实质上从此开始“佛法之会议室”成为吐蕃王朝最高决策机构。第九主持“渐顿之争”,平息佛教内部争议。第十在宫中设立供奉三宝的道场。将佛教道场设于宫内,将宗教溶入政权。此后佛教经过800多年发展,当教权高于政权时,我们又看到了相反的路径,将政权溶入宗教,即在五世达赖喇嘛期间,将政权机构设于甘丹颇章(哲蚌寺内的一幢别墅),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第十一大兴密教,继莲花生之后,一批著名的印度密宗大师也先后来到西藏,如法称、净友、觉密等。简明方便又快速成佛的密法,一传入藏地便吸引了大众的目光,很快扎根西藏,即使后来发生了严酷的“朗达玛灭佛”,也由于密宗自身简明快速的特点使它能迅速转入地下,为后弘期佛教的复兴留下了“星星之火”。第十二推进佛教大众化,赞普“为使全体属民归依佛教及必须奉行佛法,遂决定在中心卫地及边地均委派轨范师。并令所有尚论之子孙及王妃每人均持书夹学习佛法。”[10](P.229)推动佛教的大众化发展,展现了赞普兴佛抑本“以佛治国”决心。
赤松德赞大力振兴佛教,限制本教,被本教徒说成是“第三次法难”⑥,并认为这次法难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的“灭本”,一些藏传佛教文献也附和这一说法。前者打“悲情牌”,后者突显“法王”赞普将佛法定为一尊,使本教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到底是“灭本兴佛”还是“抑本兴佛”,虽一字之差但失之千里,它涉及吐蕃王朝政教关系,有澄清之必要。
关于当时的“佛本之争”,本教典籍《囊协幻钥》记载:“国王(赤松德赞)召集群臣说:‘我要从印度迎请佛法作我的皈依处。’对此,郭赤桑亚拉说:‘年轻的神子,尊敬的国王,在祖辈国王中,止贡赞普因灭本法而夭折,年仅三十六时被臣民罗昂达色所杀;松赞干布灭本而折寿,三十六岁时去世,且佛庙为雷击,请吸取祖辈教训。’”[4](P.103)据本教《斯巴续部目录》讲,赤松德赞不为所动,“于是召集了很多本佛教徒,在山口搭起五彩的布帐篷,在札玛真桑宫殿中,让佛本一较高下。……开始比试神变法力。……比试的结果虽然在许多经、教言中都说本胜于佛”,但王却判佛教胜。“本教徒不服输,但一是国王因夙愿作用而喜欢奉行佛法;二是喜佛之臣在本教和国王之间挑拨;三是由于众生福气小,且多有恶行;四是吐蕃的众生没成为教法精髓雍仲本教的所化等原因,于是本教又一次被灭”。[4](P.103-104)而藏传佛教最早的典籍《韦协》也记载了这次佛本之争:“双方不斗法术,只论教理。佛法教义显得贤善而广博、精湛而深奥,而苯布词穷理屈,……于是(赞普)下谕旨,自始不准奉行苯布,不得以杀害众多牛马及动物作殉葬品。”[12](P.15)上述两派文献记载表明:由于本教擅长法术仪轨,而佛教长于教义教理,所以本教典籍认为比的“神变法力”且“本胜于佛”,而佛教典籍则认为“只论教理”且“苯布词穷理屈”。尽管双方对事件描述有差别,但都一致肯定最终结果是赤松德赞“灭本兴佛”。
我们认为提“灭本”有夸大之嫌,佛本之争实质是吐蕃王室与臣属的权力之争,说到底是政治(政权治理)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吐蕃王室一方,高举佛教大旗,利用佛教在教义教理上的优势,打击本教势力,维护王权独尊的地位。而本教大臣一方,则利用佛教立足未稳,本教在民众中具有较高威信,加上本教同吐蕃政权在传统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度融合关系,运用本教教义与巫术将一切天灾人祸算在佛教的头上,试图复辟“王辛同治”的政治格局。所以,王室“抑本兴佛”并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由此我们看到一奇怪现象,在赤松德赞及其后的历次“兴佛盟誓”中既掺杂了本教的思想更吸收了本教的仪式。记录“兴佛盟誓”的桑耶寺碑文及噶琼寺碑文都有“祈请一切出世天神、世间天神及非人作证”等话,桑耶寺碑文还加一句“赞普父子及所有小王及臣工赌咒盟誓”。[10](P.186)从形式上看,“赌咒盟誓”显然是本教而非佛教的形式,请神作证也只能本教的思想而非佛教思想。同样在桑耶寺兴佛盟誓碑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奇怪现象,就是反佛大臣达扎路恭的签名。他在佛本之争中,先是站在本教一方公开反对佛教,但当赞普决意兴佛,本教失势之后,他转变态度,并在《兴佛诏书(誓词)》上签字。赞普并没有因为他当初的反佛而将其剪除,反而因其检举揭发逆臣谋反及征战有功而加以重用,还为其树碑立传。这充分表明,在宗教纷争中,宗教派别只是一个标签,支持或反对哪一派与宗教信仰无关,而是与这些派别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及利益相关。宗教不过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打着宗教旗号进行政治斗争也是西藏旧政权的一贯手法。
再看之后牟尼赞普开创的“四大法会贡”⑦,本意是要解决佛教寺院的供给问题,但采用的方式却是本教传统的祭祀形式,不过因佛教不杀生,担心民众依本教祭祀习惯献上牲畜,才特别明文规定“除牛羊之外的金银财宝和生活资料”[11](P.132)。但事实上“官方一直保持着牲祭习俗直到吐蕃王朝崩溃之时,在821-822年赤祖德赞在位时,为纪念与唐朝和盟而竖立的石碑上写道,宰杀牲畜使盟约更显庄严”[3](P.312)。这在汉文史料中也得到印证,762年当吐蕃与唐朝在长安订立和盟时,唐王朝以为吐蕃信佛,因此专门将和盟地点安排在向佛寺,但吐蕃“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无向佛寺之事。”[8](P.63)要求改在专门接见外交使节的宫庭内进行。
综上所述,由于本教在维护吐蕃王权上有前述五大功能,赞普也不可能真正“灭本”,因为消灭本教就会连带消灭自己执政法理基础(君权神授),相反他还要利用本教的思想及仪轨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所以至多是“抑本”,也就是要消除前述本教对政权的负面影响。
(三)佛教难挡政权的争夺与衰败
赤松德赞逝世后,经历了牟尼、赤德松赞、赤祖德赞三位赞普,他们继续推行“抑本兴佛”的政策,将佛教在吐蕃的发展推向极端。
牟尼赞普虽在位不到两年,但其“大宏佛教,对诸受供大师及与出家沙门,恭敬承侍,供其资养,奉如顶冠。”[11](P.132)他推出兴佛新政:“在逻娑(大昭寺)及昌珠寺院建立了毗奈耶律和法供,在桑耶寺建立了经藏和现证菩提供,”即“四大(法会)供”。同时发布诏谕:“汝等所有属民,于我先父之诸寺庙,除牛马兵器外,皆当以金银、财帛、珠宝、玉石、所有何宝,尽力为供。”[11](P.132)
当他看到有属民连一件像样的衣物都贡献不起,“仅以破袍碎布为供者”时,竟然指责其“信心太浅”,当属民回应已倾其所有“无以为供”时,他又感叹:“同为我之治下臣民,不应贫富如此悬殊。”据称他曾三次均贫富,但贫富差别很快又与先前一样。在当时的制度等条件下,以及短暂的两年执政期间竟能搞三次均贫富,连法主·索南扎巴也怀疑“何暇三次均分食粮牲畜?”[6](P.46)但当时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以及普通属民的赤贫状况却是毋庸质疑的。究其原因,赤松德赞放弃其先祖的睦邻友好政策四面出击,东攻唐朝、西战突厥、南侵南诏,甚至谋划“并瞻洲(地球)三分有二之地”[6](P.45-46),这些穷兵黩武的征战已严重消耗了自己,加上从赤德祖赞以来近百年的崇佛,修建了大量寺庙,供养了大批不事生产的僧人,也使府库亏空。到公元798年赤德松赞即位时,“桑耶寺僧侣供食中断,只有说话的气力,寺院的仓库被毁,寺院的墙基处积满了鼠粪,所有僧舍的房门均被贼盗走”[10](P.243),呈一派破败景象。这充分说明,当吐蕃王朝内斗时需要佛教作为工具,排挤异己的政治势力,而当政权巩固后开始向外扩张,试图完成“帝国”梦想时,作为“息战弥争”的佛教早已被抛在脑后,什么由“上级官府贡献”“三户养僧制”“兴佛盟誓”等等全都不再发挥作用。于是当牟尼赞普要再次兴佛时不得出新招,搞起了“四大(法会)供”。定期举行三藏供养法会的举措也开西藏佛教史先河,“其经藏供规,相沿至今未替”[6](P.45)。这一制度明显将供养义务扩展到了王朝的所有人,只是在当时两极分化严重,民众挣扎在生死线上,没有任何财物供施,所以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真正恢复桑耶寺供给的是赤德松赞执政后,桑希的女儿等显贵们,[10](P.243-244)但“四大(法会)供”却成为后来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赤德松赞继位后,在政教治理方面的贡献表现在继承先辈做法,采用兴佛盟誓诏书的形式,确认佛教的至尊地位。这次参与盟誓签名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创新之处有[10](P.245):(1)规定赞普子孙从幼年起直至掌政止,均需从比丘中为其委任善知识,使之学习佛法。本条意义在于试图将未来的赞普培养成宗教领袖,为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实施“政教合一”作准备,对后世影响尤大。(2)规定僧侣不得被给予他人为奴,不得强行征税,不得被彼等列入俗人范畴而予以诉讼。授予僧人法外特权对佛教发展是利是弊值得商榷,虽然佛教有自己一套约束信徒的宗规戒律戒规,但它的着眼点及规范的毕竟是宗教这个小社会(团体),而僧人除了生活于这个小社会,还要活动于大社会,当他们不受世俗社会法律制约时,个别人就有可能为所欲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乱象是否与此相关值得探究。(3)规定此后凡新立之王妃抑或新委任之政务大臣等等,均应参加盟誓。有学者认为王妃参与盟誓表明提高王妃在政治上的地位。但我们认为,与其说是提高不如说是确认王妃在政治上的地位。因为尽管松赞干布时制定的法律就规定“女不参政”[10](P.36),但外戚大臣篡权的现实,曾迫使母后赤玛伦联手赤都松赞普合谋剪除噶尔家族并主政于内[21](P.4-5)。其后,赤松德赞生母之争及谋害王子等重大政治事件,王妃都充当过主角。因为王妃背后代表的是舅氏家族势力,因此,不能把吐蕃时期联姻制下的王妃仅仅看着是“棋子”,她们有时也会充当“棋手”。要求王妃必须参与兴佛盟誓表面上是“提高政治地位”,实则是要求她们不得有异心,不得参与反佛活动,是对其行为限制。同时,佛教自松赞干布时传入吐蕃,其间几起几落,在吐蕃发展的阻力主要来自王朝内部的反佛势力,因此规定新任大臣参与盟誓的做法也是对的历史经验总结。
赤德松赞的继任者赤祖德赞极端崇佛,他将发辫编成两条,其上系以丝绸,向左右两边展开,让僧侣坐其上,称为二首部,以表达顶礼僧伽。他也因此被称为“日巴坚赞普”(意为有发辫的赞普)。他还为自己建造宏伟的本尊寺——伍祥多贝美扎西根佩寺。任用沙门(钵阐布)充任首席大论(宰相),“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8](P.178),以致布顿说他“献国政于出家人”[5](P.204),开启了僧人主政的历史,这对后世影响巨大。将“三户养僧制”改为““七户养僧制”,对敢于“目瞪手指”僧人者要“挖其眼断其指。”[10](P.261)然而物极必反,当崇佛变佞佛时,必招致民众的不满和大臣的反叛,加速了其政权的垮台,以致赞普本人、二位钵阐布贝吉云丹及娘定埃增相继被杀。
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后,由于“发生了霜、冰雹和瘟疫,于是就扬言是推行佛法之故,遂有此不祥。”[10](P.277)这是本教攻击佛教的一贯伎俩。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毁佛事件,据《贤者喜宴》记载,毁佛者将佛像抛入河中;拉萨、桑耶两地寺院先是被改为屠宰场,后又沦为狐穴狼窝;其它寺院亦遭到破坏;凡能找到的佛教经典或投之于河,或焚之于火;佛教高僧大德多被杀害;大部分僧人逃往边地或沦为俗人;一些僧人被强行充当上下马凳,又令一些僧人背鼓行猎。也就是要从信仰和文化上彻底摧毁佛教。最后佛教高僧拉隆贝吉一箭结束了朗达玛的性命,同时也结束了吐蕃王朝的历史,从此佛教与本教走上了既自主又融合发展的道路。
结语
纵观整个吐蕃王朝政教史,本教与佛教的此起与彼伏,反映了政权的兴与衰,但宗教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及争权夺利的工具,不能夸大宗教在吐蕃王朝盛衰上的作用。后弘期形成的历史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上作者多为宗教徒,往往夸大了宗教在吐蕃王朝兴衰上的作用,甚至将其写成一部宗教史。因此,我们要仔细鉴别,对吐蕃王朝兴衰的根源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综合探究,从而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历史观,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释:
①借用麦克唐纳的术语,笔者认为将本教称为“王家宗教”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政教关系,应当说当时的本教既是“王家宗教”也是大众的宗教。参见石太安著,耿昇译:《喜马拉雅的社会与宗教》,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225页。
②疑为犬,参见《旧唐书》,罗广武译注《两唐书吐蕃传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4页。
③获财:主要指四种因本对世间社会的作用,不同于五种果本。
④奎:原指计划、方案,引申为制度、措施等。参见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45页。
⑤本教典籍认为,“第一次灭本”发生在前述第八代藏王子贡赞普时。
⑥本教认为第一次法难发生于第八代藏王子贡赞普时期,第二次在松赞干布时期。
⑦据称这是西藏林卡节及拉萨传昭大法会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