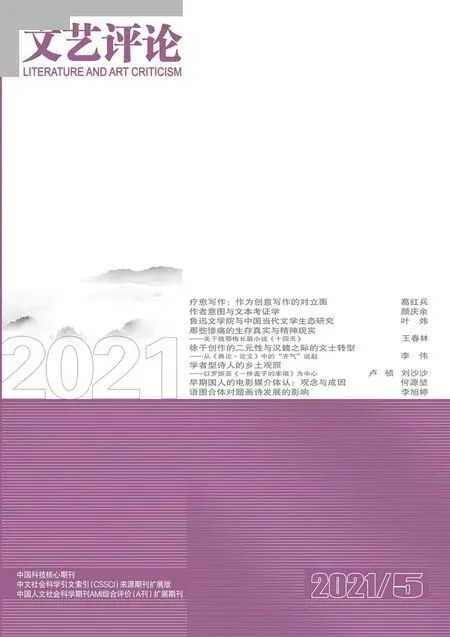早期国人的电影媒介体认:观念与成因
○何源堃
1930年代是中国民族电影观念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在此之前,国人通常只是将电影看作是休闲娱乐,而到了这一时期,国人普遍意识到电影的媒介本性,认识到电影强大的宣传能力,开始将电影视作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意识形态载体,电影工具论一时之间成为主潮,无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治团体,还是彼时文化艺术界的进步人士,都推崇电影的教化宣传作用,践行着以电影传播民族精神和进步观念的创作活动。电影观念的转变催生了“左翼电影”和“教育电影”等强调电影媒介功用的电影理论,以及《三个摩登女性》《都会的早晨》《城市之夜》等富有宣教性的电影,由此形成了1930年代理论与实践彼此印证的繁荣局面。
对于1930年代电影宣传观念形成的原因,已有电影史论著普遍倾向于从社会变化角度提供解释。如程季华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人民觉悟的提高和抗日运动的开展,电影观众已经开始对当时电影界的黑暗状况感到不满,向电影界提出了‘猛醒救国’的劝告”①。胡克认为,“1931—1937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并存,国难当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这导致阶级、民族、国家等重要社会观念在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传播,电影在当时是最普及的商业文化,在大中城市影响最广,自然被作为重要的传播方式”②。蹇河沿认为,外来侵略导致了“人们内心的忧患和恐惧意识逐渐加重。这个时候银幕上飞檐走壁、瓢忽诡异的剑仙侠客,确实无法给观众带来任何观影的快感,所有有良知的中国观众都对电影界的不良状况感到不满,向沉浸在流俗娱乐的电影界提出了抗日救亡巨大呼声”③。这些研究将社会变化与电影观念变化相联系,普遍强调30年代初期外来侵略、阶级矛盾和社会心理变化对电影观念的影响。
但是,站在回望历史的角度,将特定社会思潮与电影思潮相结合,虽指出了电影观念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却一定程度上窄化了视角,既忽略了电影产业内部长期以来的观念变化,也忽略了电影观念转变的历史复杂性,由此遗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在1930年代广泛的电影宣传教育观念出现之前,国人是否已经对电影的媒介特性形成了一定的认识?1930年代初期中国已有发达的报刊媒介,同时也有成熟的文学、戏剧、戏曲等软媒介,为何国人还会将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宣传诉求寄托于一度只是休闲杂耍的电影媒介,从社会各界纷纷涌入电影界?除了社会变化提供的外部刺激,电影事业自身是否也提供了观念转变的内在动力?这些问题显然无法简单地从电影观念转变的社会背景中得到合理解释,而必须“以事实决事实”④,回到历史语境和早期电影理论中寻找答案。
一、在地化电影实践与电影媒介意识的形成
要重新还原早期电影宣传观念发生的复杂性面貌,首先必须梳理新观念赖以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因为只有基于对电影媒介本性较为完备的认识,国人才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把一度只是娱乐商品的电影用作动员大众的宣传“武器”。
首先,通过对1930年代之前电影理论的大致梳理,可以发现国人最初的电影媒介意识大致生发于1920年代初期对“影”与“戏”关系的思考中。如周剑云认为,“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术照下来的戏”⑤;徐卓呆认为,“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上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⑥;侯曜认为,“影戏是戏剧之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他都具备”⑦。在这些早期电影人的观念中,电影是从属于戏剧,戏剧的特性就是电影的特性。“影既是戏”的观点背后潜藏的逻辑显然是把“电影”看作了复现戏剧的工具,一种纯粹的无属性载质,就如陈犀禾所言,在早期电影人眼中,“影只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⑧。在这些论述中,虽然没有直接强调电影是“工具”或是“媒介”,但是已经流露出对电影媒介属性的无意识体认。在对电影媒介属性的认识上,顾肯夫的《描写论》表述的更为具体,他认为,“所谓影戏者,以影传戏也,戏为主而影为宾也”⑨。顾肯夫同样是从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中出发进行阐述,但从他的表述中,可以明显看到已经把电影视作了一种传播手段,而传播的内容就是戏剧。早期电影理论中“影”与“戏”的二元论说突出了一个事实,即早期电影观念中内容和形式是分离的,作为内容的“戏”显然更为重要,“影”只是被看作承载“戏”的工具。
从理论的表述来看,早期电影人对“影”模糊的媒介体认显然与中国早期的电影实践经验密不可分。与西方从记录现实开始对电影摄影手段的探索不同,中国自一开始就把电影用作既有艺术形式的复现工具,就如郦苏元所言,“由于中国电影的历史是从电影的传入而不是电影的发明开始的,加之当时技术落后,囿于闻见所致。人们把目光伸向久远,目的在于探寻电影是否与先已存在的艺术有着某种天然联系,以确定它所占有的位置”⑩。中国电影始于对戏曲的搬演,从1905年的《定军山》到1909年的《纺棉花》,在中国本土制片的前四年中,所有的影片都是对京剧的翻拍。这些影片大多由任庆泰导演,内容基本是截取戏曲中的打戏片段来进行表现,因此较好地利用了无声电影突出动作的特性。澳大利亚汉学家玛丽·法克哈便特别强调了这种行为的媒介实践性质,她说,“任庆泰没有为银幕改编戏曲,他只是为无声电影媒介选择了最适合的片段”⑪。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人虽然没有认识到电影所具有的媒介特性,但是在无意识之中还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记录手段,选择用它来转录彼时流行的戏曲曲目,记录下名伶的身姿。
在戏曲片的探索之后,是戏剧主导电影创作的时期,大致从二十世纪早期持续到2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戏剧届人士大量进入电影界,将舞台艺术的经验带入了电影创作之中,以戏剧演员和戏剧剧本支撑起电影创作,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初步繁荣。通过与戏剧的“联姻”,电影虽然发展迅速,但烙入了更多舞台艺术的痕迹,使自身几乎成为戏剧的银幕翻版。因而,基于以“舞台艺术内容”主导“电影艺术形式”的实践经验,早期国人便倾向于通过戏剧来定义电影,把电影视作是舞台艺术的记录工具,较为明晰的电影媒介意识也由此生。可以说,在早期电影人眼中,电影的本体究竟是什么,以及电影的摄影手段有多大潜能,都不是多么重要,重要的是电影能发挥何样的功能,尤其是对于传播戏剧能起到多大的帮助。因此在《〈影戏杂志〉发刊词》《影戏概论》《影剧之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等早期的电影理论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对电影功能的论述。顾肯夫在《〈影戏杂志〉发刊词》中,比较戏剧与电影(影戏),指出电影比戏剧制作费用更低、传播速度更快、观看成本更少、留存时间更长、面对受众更广。⑫显然,顾肯夫所分析的电影比之戏剧的最大优势就是它更加易于传播。同样,在《影戏概论》中,周剑云和汪煦昌详列了电影的六种功效,分别是:“(甲)娱乐精神;(乙)通俗教育;(丙)增广见闻;(丁)帮助演讲;(戊)永久保存;(己)普遍性质。”二人论证这些功效实现的原因,认为主要是电影能够“普罗万象”、“纯然逼真”和易于传播。⑬可见,在20年代初期,早期电影人已通过对影戏实践的经验总结,对电影媒介层面的功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2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文人大量进入电影届,一方面是文明戏没落,各大电影公司面临“剧本荒”的窘境,需要主动引入受欢迎的通俗文学资源;另一方面即是鸳派文人已经认识到电影的媒介价值,有意识地把电影当成了重要的宣传阵地。1910年代后期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萎缩的时期,“五四”发生以后,由于新文学的抵制和抨击,“在1916年和1917年之际,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刊物纷纷停刊,如《礼拜六》于1916年9月29日百期停刊,另外《中华小说界》、《民权报》、《眉语》、《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余兴》、《小说海》、《春生》等著名刊物也相继停刊。通俗文学在新文学的强大攻势下全面转人战略性的退却”⑭。到了20年代,鸳鸯蝴蝶派开始复苏,为了与新文学抗衡,鸳派文人成立了更多新刊物,还成立了青社和成星社等文学团体,以拓展阵地。这时的中国电影产业已颇具规模,电影的媒介价值也已得到充分认识,于是鸳派文人有意识地把电影作为重要的宣传阵地来开拓。一方面,鸳派文人利用电影这一媒介进行小说改编,以文学之外的方式传播作品,另一方面,鸳派文人直接将电影作为书写手段进行电影文学创作,就如盘剑所言,鸳派作家“在参与电影创作的同时也仍然在继续着文学创作,或者竟把电影也当作一种文学来创作”⑮。曾经被新文化运动所忽视的电影,短短几年后转而成为其抨击对象用以传播作品的重要武器,并形成几乎荡涤电影市场的娱乐浪潮,可见1920年代中后期国人已经对电影的媒介价值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并且有意识地将电影用于宣传。
二、外国影片冲击与电影宣教呼求的产生
如果说早期国人对电影媒介价值的认识为1930年代初期电影观念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特定的刺激因素则是促使观念转变的必要条件。目前,在各种电影史著述中,普遍将“九·一八”事变视作电影观念的转折点,强调外来侵略对电影观念的影响,但是通过对1930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动向以及电影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还有一个促使电影宣传观念迅速滋长的因素,那就是外国影片的冲击。
1933年1月1日,明星影片公司发布《明星影片公司一九三三年的两大计划》,计划中提及:“截至现在,欧美影片所表现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观点,差不多都是把我们当成一种很卑鄙,很渺小,很怯弱的一个民族,这在外国制片者固然有他们的用意,但我们不能从电影艺术上显示我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也是遗憾之一”⑯。出于宣扬民族精神的目的,明星公司转变制片方针,放弃娱乐影片,计划拍摄“五千年的中国”和“戏剧化的生产运动”,以凸显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可见,明星公司制定新计划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抵抗外国影片的意识形态冲击。此外,1930年代初期的进步电影理论,也常常通过引证外国影片消极影响的方式来强调电影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例如,黄君如通过论证外国宣传影片的殖民效果,认为“电影是站在艺术的尖端,组织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思想和行动”⑰。阿英以凤吾为笔名所撰写的《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提出,“帝国主义的电影,除了很少数的关于弱小民族的以及暴露的稍有意义外,大多数,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向殖民地进攻的,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麻醉大众的”⑱。要应对这种现实,阿英认为中国必须开展电影文化运动,以影画答复“帝国主义的大炮”。王尘无在《中国电影之路》中批驳艺术中立论,指出:“美国电影不就是主要工业之一吗?所以电影是不含任何作用的艺术,这种虚伪的谣言是不值得一顾的。因为在这种虚伪的谣言底下,电影早已给他们实际上利用为拥护本身利益的工具了。”⑲因此,王尘无认为,面对西方影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冲击,中国电影必须承担“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任务。概而言之,30年代初期进步电影人士对中国电影的宣传教育呼求,并不仅仅是立足于外来侵略,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外国电影的恶劣影响,可以说正是外国影片的冲击,让国人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电影这一媒介不光具有逼真复现现实的本体特性,还具有充当“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大宣传功能。
具体来看,1920年代中期是好莱坞大举入侵中国市场的开始,出于对中国放映业的看好,“自1920年代中期起,美国好莱坞的米高梅、派拉蒙、联美、福克斯、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后八大公司均陆续来华,处理影片输出事宜,环球、派拉蒙还先行一步设立了办事机构”⑳。好莱坞的进军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电影在中国的主导局面,到了1930年代,“中国所有上等中等的影戏院,均与美国的影片公司订有放映合同,譬如某一家戏院和米高梅签定了合同之后,该戏院便不能放映任何其他一家的影片,中国人的中国影戏院,只许映美国人的片子,有时候,中等的影戏院如果要开映中国片子,没有得着美国影片公司的恩准,便会受到严重的处罚”㉑。可以说,到了1930年代初期,美国影片对中国电影事业已经形成垄断态势。美国影片在带来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侵略,尤其是在192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的美国影片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国家宣传内容和对中国的种族主义偏见,这些内容逐渐引起国人的警觉,并促使国人开始思考电影在宣传上起到的作用和对观众认知产生的影响。英国史学家马修·约翰逊就曾考证,由于在1920世纪初期,大量由西方人拍摄的纪录和搬演的中国战争片以及民族志影片唤醒了西方的种族主义情绪,亚洲的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的恐惧,所以在1920年代左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影片中开始频繁出现对中国的想象式丑化,“傅满洲式”形象一时之间成为西方种族主义的宣泄口。当这些影片传入中国,“不仅对彼时中国民族电影产业的出现与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向电影制作者们逐步灌输了一种观念,即视觉技术和大众媒介会极大地影响国家主权”㉒。于是,在外国影片的意识形态冲击之下,为了抵抗外国影片,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强调电影这一媒介所具有的强大宣传能力。如孙师毅通过列举外国描写下层民众的影片,论证电影“其效用的广大普遍,其力量的显著与磅礴,在在都是以使它成功为一种超各样艺术的权威”㉓。李晋柏将电影的教育效果和意识形态作用相联系,指出“电影是综合的艺术,他实在是个社会的导师,负有社会教育最大的责任的!他能导社会于纯朴高尚,发扬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㉔。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20年代后期,电影宣传观念已经局部地出现,并逐渐积聚势能,弘扬民族精神的电影诉求也日渐高涨。
而后,到了1930年代,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反抗外国电影殖民,强调电影宣传教育的呼声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1930年2月21日,美国影片《不怕死》在上海上映,由于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和贬低,该片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强烈抵制。南国等剧社随后联合发表《上海戏剧团体反对罗克〈不怕死〉影片事件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在经济上,在文化上,无所不用其极,而近更假借电影之表现,在国际上,作丑恶之宣传,作迷惑之麻醉,淆乱黑白,混人听闻,其影响固不仅侮辱华人而已”㉕。抵制《不怕死》的事件愈演愈烈,最后掀起了相当规模的“抵制辱华影片”民族主义运动。再如,鲁迅在1930年3月将日本左翼电影人岩崎昶所写的《作为宣传、煽动手段的电影》(宣傳·煽動手段としての映畫)一文翻译为《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并在译者附记中感叹:“欧美帝国主义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胡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胡涂的教化。我想如电影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书,现在是万不可少了!”㉖鲁迅所言的主旨虽是对欧美影片的意识形态批判,但是中国影片的自甘堕落和不能表现民族精神也是形成“糊涂教化”的重要原因。又如,1930年7月,《南国》月刊推出“苏俄电影专号”,在发刊词中,田汉将列宁所说的“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这句话置于卷首,强调电影是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最直接的、最有普遍性的工具”,呼吁中国向新俄学习,改变逃避主义的创作现状,用电影去助力“中国民族之解放”。㉗可见,在社会剧变还未发生之际,由于外国影片的意识形态冲击,国人的电影观念已经逐步从休闲娱乐向宣传教育发生偏斜,电影行业内部对进步电影的呼求也日益高涨。
三、1930年代初期媒介环境与电影用于宣传的必然
1930年代初期电影观念的转变之所以广泛而深刻,是因为除了电影行业内部的观念变化,还有大批其它各界人士秉持以电影进行宣教的目的进入电影界,这些进步人士以左联成员为代表,促使电影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兴电影运动”。这一时期,电影之所以被视作重要的宣传武器,享有比之报刊、文学、戏剧等其他媒介的优先性,一方面是因为国人已经通过外国影片充分认识到电影强大的宣传能力,另一方面也与彼时的媒介状况不无关系。
首先,1930年代初期中国的整体媒介环境仍处于比较贫乏的状态,主要的宣传工具仍是报刊。同时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发展广播电视网络,如美国在1920年代便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广泛覆盖的商业广播网络和教育广播网络,拥有了报刊以外强大的宣教工具。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在1925年完成了全国广播网络的覆盖。此外,日本、苏联等国家也在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本国的广播事业。而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内部政权分裂,且面临外来侵略的威胁,广播事业虽然起步较早,但是发展缓慢,广泛覆盖的人民广播网络1950年代才得到建立。由于缺乏广播这样强大的宣传工具,所以1930年代初期所能依托的主要媒介就是彼时相对完善的报刊网络。但是在这一时期,在“对内可使国家政治清明,对外可使国家主权独立”㉘成为新闻界的普遍呼求时,中国报刊在时事宣传上却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请愿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要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大公报》主张‘缓抗’。《大公报》发表了一些评论,主张‘镇静应付’,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干预和美苏表态”㉙。可以说,面对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当局所施行的消极抗日政策和对舆论的压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报纸这一宣传喉舌,使人们不得不寻找发声的替代品。此时,电影媒介虽不如报刊媒介发达,但受到的管控力度较弱,且可以相对隐蔽地进行暗示性宣传,于是就成为重要的备选宣传阵地。此外,1930年代中国报刊虽然比较发达,但分布仍然很不平衡,远未成为广泛传播的大众媒介,这决定了报刊和依托于报刊传播的文学的影响力就相当有限。1935年,《世界日报》的创办者,著名报人成舍我在《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一文中就曾指出:当今的“报纸内容,不是大众所需要读的,报纸的定价,又不是一般劳苦大众所读得起的。中国报纸不能发达,这两点实在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中国办报数十年,到现在,他的读者,还只是限于极少数的政治人物和所谓知识分子,不能伸张到民间去”㉚。可见,直到1930年代中叶,报刊的主要受众仍然是中上阶层,无力承担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作用。
与报刊的传播限制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已经成为被广为接受的大众媒介,它传播的地域范围或许仍然存在局限,但是强大的传播能力却已经毋庸置疑。1927年有文献记载,在青岛“上至太太奶奶们、下至商店伙计们闲来无事谈谈张织云啊、杨耐梅啊,内中最欢迎的是黄君甫,痛恨的是王献齐”㉛。从商店伙计到太奶奶,电影受众的阶层跨越显然是极广的。30年代初期,《申报》也有文章统计了彼时的电影受众情况,指出观众可分为:“一、摩登青年们——他们常挽着异性而往,目的在藉影片里的恋爱故事,以推进他俩恋爱的程度;二、太太们——她们看京戏,看神怪舞台剧觉得腻了,于是到影戏院里来逛逛,藉资调节;三、绅商们——有闲的绅士阶级,有钱的大贾们,他们每星期看一二回影戏,散散心,解解闷儿;四、穷小子们。”㉜可见,1930年代初期,社会各阶层都已成为电影的受众。此外,1930年代前中国的影院也形成了不同层次,能充分覆盖不同阶层的观众。据陈一愚统计,影院中既有卡尔登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大光明大戏院、南京大戏院、国泰大戏院等面向中上层阶级的,票价高昂的豪华影院,也有东海大戏院、圣乔治露天影戏院、凡尔登露天大影戏场,跑马场影戏院和花园电影院等面向劳动阶级和底层民众的,票价相对低廉的普通影院。㉝可见在1930年代之前,观影行为就已不再局限于中上阶层,而是成为了普通人的一种日常消费。
1930年代有声电影的出现更是增强了电影的普及性,使文化程度较低的观众也可以理解影片,有助于发挥电影的宣传作用。根据国民党1934年的社闻《本社有声影片在闽大受欢迎》记录,国民党利用有声电影在福建做宣传,“一星期间,在福州开映,先后招待八十七师将士,公安队,保安队,宪兵队,各团体,各界人士,前来观映者,约20万人”㉞。可见,1930年代有声电影的接受范围已非常广,宣传效果也非常可观。此外,有声片中的歌曲也起到了极好的辅助宣传作用,时人已充分认识到,“适当的乐歌,也是更能增加观众对影片故事,剧中人的遭遇,感情等的理解”㉟,这种宣传效果,从《渔光曲》《大路歌》《毕业歌》等富有教育意义的歌曲的广为传唱便可见一斑。
概而言之,1930年代初期,电影能从各种宣传媒介中脱颖而出,不仅是因为其自身强大的宣传能力已经为国人所认识,还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宣传媒介报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电影虽然在农村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但是已经是彼时受众范围最广的大众媒介,足以承担起动员大众和教育大众的任务。
结语
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可以发现早期国人的电影媒介体认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它并非断裂式地突然发生,也无法以“九·一八”或“一·二八”为时间节点进行阶段划分。相反,这种转变是长期的、历史的,它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理论积累,到外来刺激引发局部转变,再到社会剧变形成广泛共识的过程。首先,早期以“影”传“戏”的在地化电影实践使国人形成了朦胧的电影媒介体认,由此国人开始思考电影这种艺术介质的价值,发现了其逼真复制和易于传播的特性。随后,外国影片越来越明显的文化殖民倾向,激发了国人的反抗精神,使国人意识到电影这一媒介还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进而开始强调电影在宣扬民族精神和教化民众方面的重要性。此时,电影观念在电影业内部已形成局部转变。到了三十年代初期,由于外来侵略的发生,抗日救亡成为广泛的社会呼求,此时报刊媒介被高度控制且存在自身传播局限,于是更贴近大众的电影艺术被视作组织群众和教化群众的重要工具,各界人士纷纷涌入电影界。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刺激下,主流电影观念才得以迅速地从休闲娱乐转向宣传教育,至此,盛极一时的娱乐电影浪潮逐渐衰退,富有教育意义和批评深度的现实主义电影逐渐走上台前。
①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80页。
②胡克《中国电影理论史评》[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③蹇河沿《中国电影观念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④王国维《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A],王国维著《观林堂集》[C],黄爱梅点校,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5页。
⑤周剑云《影戏杂志序》[J],《影戏杂志(上海1920)》,1921年第2期。
⑥徐卓呆《影戏者戏也》[J],《民新特刊》,1926年第3期。
⑦侯曜《影戏剧本作法》[A],丁亚平主编《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1897-2001)》[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4页。
⑧陈犀禾《中国电影美学再认识——评〈影戏剧本作法〉》[J],《当代电影》[J],1986年第1期。
⑨顾肯夫《描写论》[J],《银星》,1926年第3期。
⑩郦苏元《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⑪[澳]玛丽·法克哈、裴开瑞、刘宇清、沈大春《影戏:一门新的中国电影的考古学》[J],《电影艺术》,2009年第1期。
⑫顾肯夫《发刊词》,《影戏杂志(上海1920)》[J],1921年第1期。
⑬周剑云、汪煦昌《影戏概论——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讲义之一》[A],罗艺军主编《20世界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7页。
⑭黄永林《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页。
⑮盘剑《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J],《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⑯《明星影片公司一九三三年的两大计划》[N],《申报》,1933年1月1日。
⑰黄君如《电影的殖民政策》[N],《申报》,1933年11月1日。
⑱凤吾《论中国电影文化运动》[J],《明星》,1933年第1期。
⑲尘无《中国电影之路(下)》[J],《明星月报》,1933年第2期。
⑳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㉑李凇耘《国片复兴声浪中的几个基础问题》[J],《影戏杂志》,1931年第3期。
㉒[英]马修.D.约翰逊、张华《战地之旅:早期外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构建》[J],《当代电影》,2018年第1期。
㉓孙师毅《往下层的影剧》[J],《银星》,1926年第1期。
㉔李晋柏《论电影与教育》[J],《银星》,1927年第12期。
㉕《上海戏剧团体反对罗克〈不怕死〉影片事件宣言》,载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㉖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J],《萌芽月刊》,1930年第3期。
㉗田汉《〈南国〉月刊苏俄电影专号卷首语》[A],田汉著《田汉全集(第十八卷)》[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页。
㉘吴凯声《新闻事业与国际宣传》[A],黄天鹏编《民国丛书·第二编·48》[C],上海:光新书局,1930年版,第251-255页。
㉙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㉚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J],《报学季刊》,1935年第3期。
㉛赵醒梦《电影在青岛》[J],《电影月报》,1927年第7期。
㉜岛生《电影院里的形形色色》[N],《申报》,1932年11月29日。
㉝陈一愚《中国早期电影观众史(1986-194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㉞《本社有声影片在闽大受欢迎》[J],《励志》,1934年第21期。
㉟唐棠荫《谈一九三四年的电影歌曲》[J],《青春电影》,193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