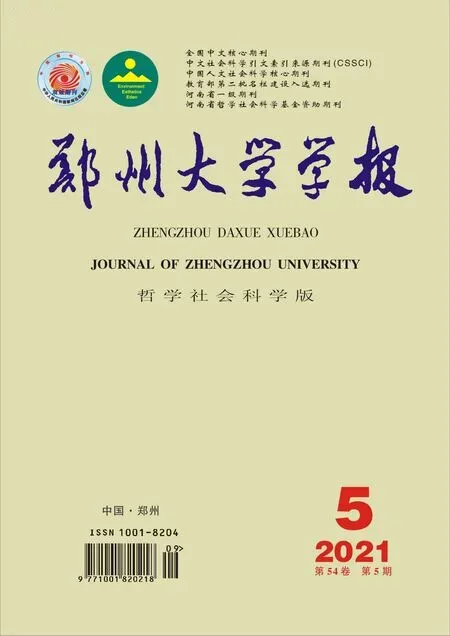唱给“自己的歌”:《奇幻山谷》中的上海书写
刘 向 辉
(1. 许昌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2.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自1989年出版《喜福会》成名以来,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一直深耕于母女冲突叙事,创作出《接骨师之女》等一系列广为推崇的作品。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看来,关注母女冲突既是谭恩美难以逃避的主题,也是其个人天分所在[1](Pvii)。在2013年出版的小说《奇幻山谷》中,谭恩美发挥一贯的“母女关系”书写传统[2](P81),讲述了一段极具上海风情的情感纠葛故事,揭示了如何在“两个世界”之中生存的问题[3](P34)。与谭恩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奇幻山谷》中的母女不再是华裔母女,而是具有文化杂糅性的母女:从美国来到上海的白人母亲路路·明特恩和生在上海的中美混血女儿微奥莱。这部具有革新意义的谭氏小说问世之后同样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主要探讨作品中的身份与情感[4]、身份商品化[5]、文化建构[6]、绘画诗学[7]、越界性[8]等。这些研究固然是对《奇幻山谷》的深度解读,但却忽视了作品中颇为重要的上海书写。
《奇幻山谷》中的上海书写不仅笔墨多,而且对作品主题表达和谭恩美自身均有重要意义。该书以1905年至1939年为时间节点,通过主人公微奥莱跌宕起伏的“青楼爱情故事”展现了一段极具谭恩美个人想象色彩的近代上海社会风情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上海社会风俗变迁的“断代史”。谭恩美对上海的书写并不是为了重述历史,而是以“微奥莱”之名言说“外祖母”的上海故事,即试图通过文学想象或者重构上海“小历史”来为外祖母“立传”,构建主动发声的女性形象。谭恩美这种以“所见即所愿”[9](P173)的创作观为逝者“立传”的行为,既在家族层面追忆缅怀了外祖母,又在心理层面表达了对“我是谁”的追问与探索。
虽然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以丰富的想象力为逝去多年的外祖母发出了强劲的致敬声音,但其想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与近代上海饱经沧桑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同构关系。在同构过程中,谭恩美通过塑造路路和微奥莱这一对儿勇于“歌唱自我”的母女形象,构建出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共鸣的上海意象。在近代上海的动荡年月里,路路和微奥莱尽管都为自己唱出了生命赞歌,但她们的歌声却以不同的曲调赋予上海异样的情感色彩。对于冲破家庭藩篱从美国远到中国的白人路路来说,上海是一座充满欲望的猎奇之城;而对于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中美混血儿微奥莱来说,上海是一座融入血脉的情感家园之城。
一、“自己的歌”:《奇幻山谷》的“上海”缘起
由于家族与上海的深刻渊源,谭恩美对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一种独特的情结,她也时常关注着与上海有关的许多事物。根据谭恩美2017年出版的回忆录《往昔之始》的记述:她和家人大约于2010年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观看了一场关于上海艺术文化的展览,其中特别留意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高级青楼女子的生活状况,并立刻想到要在她正在创作的小说中增加一个人物形象。在博物馆的礼品商店里,谭恩美发现了《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以下简称《上海·爱》)这本对《奇幻山谷》创作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术性著作。在随后的一周,谭恩美开始通过认真阅读《上海·爱》以及其它几本同类著作来详细了解上海名妓文化。在翻阅到《上海·爱》中的《上海十大美人》(1)参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的中文版《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第68页中的照片。一张拍摄于1911年的照片时,谭恩美有一种朦胧的熟悉感,因为照片上的名妓衣着与其家里照片中外祖母的衣着颇为相似。这张拍摄于1910年的外祖母照片(2)参阅Fourth Estate2017年出版的谭恩美回忆录Where the Past Begins: A Writer’s Memoir第170页中的照片。是谭恩美最喜欢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不仅拍摄于同一时代,而且都拍摄于上海。正是照片拍摄时间和空间的叠合性诱发了谭恩美质疑外祖母真实身份的“危险”行为[9](P165-173)。照片绝非一个简单的“镜像”,而是一种最为复杂、最具问题性的再现形式。它总是某种特定观点(美学的、论辩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的反映。阅读照片则是进入一系列被眼前图像的虚幻权力所遮蔽的隐秘关系,主动探寻更广泛历史层面上的美学、文化和社会意义[10](P29)。尽管内心不愿承认外祖母作为青楼女子的“可能真实”身份,但作为小说家的强烈“好奇心”却驱使谭恩美在想象世界中“按图索骥”地“还原”外祖母的“青楼女子”形象。经过反复细致的照片比对和文献研究后,作为生活在21世纪的女性,谭恩美虽然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待名妓世界,但却必须以“外祖母在1911年希望被看待的方式”去看待她,也必须去思考外祖母当时想要以何种方式被后人铭记。在此基础上,谭恩美开始依托自己的情感道德品性去想象一种自己所愿的“可能真实”[9](P173)。这种“可能真实”的重心不在于赋予外祖母一种“青楼女子”形象,而在于展现外祖母是一个有思想、有胆识的独立女性形象,这也正是谭恩美借助“家族血缘传承关系”表达独立自我、塑造自我心灵的一个路径。这样一来,“外祖母”就作为一个人物原型被谭恩美“移入”到当时正在创作的小说中,即后来出版的《奇幻山谷》。
有了“外祖母”的移入,《奇幻山谷》的家族自传意义就更加突显。在这个家族自传中,一向坚持“我写作是为自己”[11](P216)立场的谭恩美自然不会遗忘自己的声音。她把惠特曼的诗歌《动荡的捉摸不定的岁月》作为题记就是对“歌唱自我”主题的暗指,其中“‘自己’永远不能垮——那是最后的实质——一切之中唯它是肯定无疑的”(3)这句诗的译文包括诗名《动荡的捉摸不定的岁月》的译文均采用的是赵萝蕤的版本,也正是2017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译本《奇幻山谷》扉页上采用的译本。下文凡是涉及沃尔特·惠特曼诗歌的译文均出自这一译本,不再一一说明。一句更是点题之笔。虽然不像惠特曼在《我自己的歌》中这样直抒胸臆地“歌唱自我”,但谭恩美却把《奇幻山谷》当做一首唱给“自己的歌”,正如她在2013年2月13日写给《奇幻山谷》的编辑丹尼尔·哈尔彭的信件中所说:“你喜欢作为该书题记的惠特曼诗歌《动荡的捉摸不定的岁月》,我非常开心。这本书里的一切都在探讨‘我是谁’。”[9](P277)因此从创作伊始到创作结束,谭恩美都试图在作品中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而《奇幻山谷》中无处不在的上海书写正是引导谭恩美思索的空间载体。
二、被凝视的上海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意外地成为中外利益共同体。在以租界为核心区域的这一共同体中,中外并非平分秋色,而是明显地呈现西强中弱、西主中辅的特点[12](P133-144)。在《奇幻山谷》中,谭恩美以租界中的高级妓院“秘密玉路”为空间视点生动展现了中外利益交织的政治经济格局。尽管从性别政治的角度看,妓女是父权政治毋庸置疑的“被压迫者”,但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娱乐区的发展过程中,她们直接参与了娱乐区空间规则的建构。在妓院这种“生活”和“生意”交织的空间里,近代上海的妓女,尤其是租界里的高级妓女主导着一种特殊的空间文化,俨然实践着“女主人翁”的特权[13](P46-47)。这种特权与象征殖民霸权的白皮肤融合起来的话则更具统摄力。它不仅意味着女性在特定空间实现了对传统父权格局的颠覆与瓦解,而且意味着女性在权力的裹挟下开始占有“公共性”的政治经济资源。在这种权力与利益博弈的格局中,主人公微奥莱的母亲路路充分利用了“女主人翁”与白皮肤合谋而成的霸权,以“舍我其谁”的姿态凝视着上海的一切。作为当时在上海唯一拥有自己顶级妓院的白种女人,路路曾多次向西方媒体宣传自己的“秘密玉路”:“无数财富在这里被创造出来,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我对双方的介绍以及他们的第一次握手开始的。先生们,对于每一个想在上海发财的人来说,我的经验都可引以为鉴:当人们说一个点子不可能成功时,通常它也就胎死腹中了——然而,在上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14](P8-9)路路这段言辞无疑是一个向自己所属的西方世界招揽生意的帝国主义广告。在其广告中,上海俨然是一个实现财富梦想的天堂,而她创办经营的“秘密玉路”正是通往财富天堂的必然桥梁。在路路眼中,上海是一块儿可供西方人任意攫取的蛋糕,而攫取的手段主要是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这种财富分配机制不是纯粹的偶然,其实质是中西政治经济权力关系博弈失衡的外显,而失衡的天平显然偏向西方国家,因此她所言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主要是指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攫取。
作为来自美国的白人女性,路路对上海的凝视既包括对上海情人陆成的个体凝视,也包括对上海的整体凝视。路路的确是因为陆成远赴中国的,但其内心的真正诱因并不是与陆成的情感,而是源自为了摆脱美国家庭束缚而产生的叛逆心理。来自东方异域的陆成恰好充当了路路的猎奇对象,并成为她凝视欲望的牺牲品。1897年在旧金山家门口初遇陆成这个“恍若中国帝王的男人”时,情窦初开而急于寻求灵魂伴侣的路路尽管“完全没有想过他(灵魂伴侣)会是个中国人,但刚一见到他,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了解他的全部”,并“忽然”产生了占有他的欲望,明确表示“我想要占有他中国的心、中国的头脑和中国的灵魂,想要占有他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也包括他那藏在蓝色丝绸长袍下面的身体”[14](P393-394)。在莫名“占有欲”的驱使下,主动出击的路路不仅轻松俘获了陆成“恍若帝王”的“中国身体”,而且利用陆成实现了去上海、远离家庭的愿望。路路与陆成之间的男欢女爱看似是青春期的激情宣泄,实际上却是19世纪末中美政治经济背景下身体与权力角逐的隐喻。
在这场偶然而发的一见钟情式“爱情游戏”中,与路路一样处于青春激情岁月的陆成,在《排华法案》等政治因素的干扰影响下是不敢轻易向白人女性求爱的,而只能选择一种被动接受姿态。对于路路来说,“勾引”陆成虽然在美国主流社会也会遭到一系列反对与抵制,但她却至少敢于凭借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感主动出击。路路的主动出击主要出于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欲望,而非对陆成的“真爱”。在路路心中,陆成只是其多个情欲对象中的一个,而陆成的身体只是一件满足其猎奇欲望的中国物品。对于他们之间“罪恶的景象、触觉和感受”的结合,路路始终有着清晰的认识,即使在身体狂欢与思绪飘忽之时她也没有抛下“我们不是同一人种,我们两个的结合是下流的”的念头[14](P415)。多年之后路路更是直接自白:“那个中国男人(陆成)激发了我的猎奇心理,为了使自己的欲望正当化,我就骗自己说,他有东方人的智慧,一定能够带我远离不幸的生活。”[14](P413)如此一来,陆成就充当了路路猎奇之旅中被想象凝视的对象。在被凝视的过程中,陆成虽然也可以反过来“看”甚至“摸”路路的身体,但他的“看”与“摸”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主动选择,而只是权力规训下的一种物品展演,其身体自身也成了白人视域中的恋物对象[15](P360)。因此,路路与陆成之间的“看”与“被看”构成了一种视觉权力关系,其本质是白人借助种族权力运作机制对“黄色”可见之物的种族生产[16](P16)。
路路对上海的整体凝视主要发生在“秘密玉路”这个集中体现中外利益共同体的独特空间,而凝视的机制是帝国霸权与女性身体的合谋。在“秘密玉路”,她对以上海(人)为代表的中国(人)进行赤裸裸的蔑视,称“中国人是喜欢担惊受怕的民族”[14](P3),把“华人看成低自己一等的生物”[14](P8),用“瞧瞧这群傻子”[14](P44)的恶语来描述为庆祝清朝灭亡而欢呼沸腾的上海民众,更是高调地向西方报纸记者宣称:“如果你想在上海赚钱……就利用人们的恐惧吧。”[14](P6)她完全是站在殖民者的“高位”对上海进行文明等级划分。在路路的凝视中,上海是一个充满胆小鬼、傻子以及劣等人种的藏污纳垢之地,而她恰恰就在这样一个污垢之地疯狂攫取利益。在这种以国际贸易为纽带的租界利益格局中,路路既是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参与者乃至构建者,也是直接受益者。她之所以能够在商战惨烈的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其自身在华洋之间纵横捭阖的交际能力之外,还在于其背后的帝国霸权。这种帝国霸权尽管大多时候只是一种无法触摸的软实力,但对于作为西方人的路路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保护伞。因此即使面对清末民初动荡政治局势给生意带来的不利影响,路路还向客户故作“自信地宣称,新的共和国不会插手我们所居住的公共租界的事务”,因为“租界是属于我们的绿洲……只受租界的法律与政府管辖”[14](P47)。至此可以清晰地看出,路路已经把自身利益与以租界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势力绑定在一起,而上海只是被她无情凝视和榨取的财富之地。
反讽的是,战争的加剧和西方人内部的尔虞我诈却迫使自诩为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路路离开上海,而在离开时路路对女儿微奥莱说:“上海正在改变,这里可能再也不会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到了旧金山以后,我们可以重新开始。”[14](P83)路路基于个人独特经验所言的上海之变,对于西方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改变不仅仅指上海作为东方猎奇中心的价值丧失,更是指其作为敛财天堂的价值丧失。在上海,路路早已失去了对陆成这个曾经代表“中国”的符号的观看欲望,同时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中逐渐失去“呼风唤雨”的发财机遇,因此选择离开是她结束这段东方猎奇欲望之旅的必然结果,而回归旧金山寻求或许根本就不在那里甚或只是幻梦的失散儿子,只是为她离开上海赋予了“合法性”而已。尽管路路在这段“成也上海败也上海”的猎奇之旅中并未收获真正的爱情,但却唱出了一曲属于她自己的女性奋斗之歌。不过她的歌声在作为中外利益共同体的上海具有浓郁的文明等级论基调和傲慢色彩,是对近代上海的无情凝视与野蛮矮化。
三、作为情感家园的上海
微奥莱对上海的情感认同是在遭受身份困境的背景下逐步实现的,而她身份困境的根源在于当时中美共有的排外主义种族观。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中美跨种族婚姻都是遭受排斥或禁止的。在加利福尼亚,从1878年州议会通过的州法修正案到1880年的《加州民法典》再到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都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针对外派的留学生,清廷学部出于多种考虑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17](P22)。因此当时白人女性路路与华人男性陆成的结合本身就充满不合法性,而他们所生的混血女儿微奥莱则更具非议性。类似微奥莱这种非白非黄的混血儿在上海既得不到外侨社会的承认,也得不到华人的接纳,只能沦为两种文化的边缘人,在就业、社交诸方面都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17](P17)。在《奇幻山谷》中,谭恩美虽然通过赋予微奥莱妓女身份,有意淡化、弱化甚或回避了混血儿面临的国籍、教育、工作、社交等棘手问题,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微奥莱沦落天涯的凄惨生活。
对微奥莱来说,母亲离开上海就像一场幻梦式的末日审判,使其瞬间跌入无依无靠的青楼生活。与母亲路路相比,混血儿的身份标签使微奥莱不仅难以拥有母亲曾经拥有的“女主人翁”特权,更遑论控制占有“公共性”的政治经济资源,反倒使其更容易沦为父权制社会的欲望消费物。然而在近似万劫不复的青楼生活中,微奥莱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在逆境中不断寻求希望、寻求新生,用坚强意志抒写出一曲亦悲亦喜的生命之歌。在谱写悲喜交织的生命之歌时,某种意义上作为白人母亲东方“殖民遗产”的微奥莱对上海不再持有居高临下的凝视姿态,反倒在复杂微妙的融合过程中对上海有了一种归属感,正如她历经磨难行将告别月塘村这个魔窟时所言:“我脑中的上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满足的感觉。”[14](P390)换而言之,微奥莱已经在上海这个纯粹的地理空间中增添了一条“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18](P5),以浓郁的“恋地情结”把上海升格为具有情感意识的家园。微奥莱对上海的依恋是一种颇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因为上海是其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18](P93)。这种精神依恋足以让上海成为其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微奥莱对上海产生依恋的关键因素是两段迥然不同的爱情:对爱德华的灵魂之爱和对方忠诚的叶落归根之爱。爱德华的出现对于久为青楼女子的微奥莱来说就像一股清泉,使其生活顿时有了新的希望。与爱德华的相处不仅让微奥莱告别了孤独感,深切体会到“渴求的安全感和信任感”[14](P218),而且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真的被爱着”[14](P220)。在真爱的滋润浇灌下,飘零多年的微奥莱终于与坦诚善良的爱德华走入幸福的婚姻殿堂。正当他们夫妇二人携手共筑愈加美满的家庭生活时,肆虐的西班牙大流感却夺走了爱德华的生命。戛然而止的婚姻并没有影响微奥莱对爱德华刻骨铭心的爱,她不仅时常从他们的女儿芙洛拉身上看到爱德华的影子,而且她“将永远深爱着他,因为,他这个浪漫主义着拯救了我的人生,他比谁都了解我,而且他让我毫不怀疑地坚信,他真的爱我”[14](P266)。与爱德华的幸福爱情虽然短暂,却给予了微奥莱无尽的新生和希望,因此至少从爱情意义上看,上海对于微奥莱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而是一个值得用情感去体验和记忆的家园。
情感的滋润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日常生活经验,逐渐让微奥莱对上海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作为中美混血儿的微奥莱或许无法明确自己的身份归属,但她对上海发生的风云变幻却有着自己的判断,尤其是对帝国主义欺压中国的行径有着清晰的情感立场。针对巴黎和会之后山东没有回归中国这一事件,微奥莱明确指出:“不管我本人有多么像个美国人——然而在我心里,中国才是我的故乡。在我看来,联军对中国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14](P265-266)微奥莱此刻根据上海体验把中国视为故乡的做法是对上海的肯定与认可。这种主动把个人经验与国家命运融合的“认家”行为充分展现了她对上海持有的“满足感”。遗憾的是,她这种既体现浪漫爱情又彰显家国情怀的“满足感”并未持久,因为接连失去丈夫和女儿的微奥莱为了生计问题再次进入青楼世界,并被诱骗到堪称魔窟的月塘村。不过,微奥莱逆境之中依然没有沉沦,而是依靠“一定要找到女儿芙洛拉”的信念支撑,遵循爱德华送给她的《草叶集》中的诗句“要竭力抗争啊,绝不顺从”的引导,最终艰难地返回上海。返回上海之后,微奥莱来到方忠诚这位在青楼世界曾经给她带来爱情幻想的纨绔子弟身边,以工作关系与其相处。微奥莱原以为对方忠诚已经卸下情感包袱,但在美好回忆和现实纠葛的激发下他们居然萌生真爱,步入婚姻殿堂。微奥莱与方忠诚之间“迟到”的爱情虽然不像她与爱德华之间的爱情浪漫与炽热,却是久经磨难之后的一种“岁月静好”,是叶落归根式的圆满爱情。
在方忠诚的协助下,微奥莱多年之后终于实现了与女儿芙洛拉和母亲路路团聚的愿望,但团聚之时其内心似乎并没有掀起激荡的波澜,而是平静地与女儿一同用脚丈量、用心感知当下的上海和过去的上海。当女儿问她如果当初其母亲没有离开上海她的生活会怎样的时候,微奥莱说:“我曾想过住到别的地方去,但我并不想变成另一个人。我就想当我自己,而且我一直是这么做的。”[14](P530)微奥莱的告白既是在心灵层面吟唱“自己的歌”,也是对上海表达一种情感认同,让上海成为她表达自我、发现自我的一种隐喻。正是在上海这个特定的空间中,微奥莱通过日常的“定居”不断重复对地方的体验,使上海“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成为具有“满足感”的情感家园。因此,当母亲和女儿邀其回归美国时,微奥莱婉言拒绝:“我不能留下忠诚一个人。”[14](P531)微奥莱之所以放弃以美国公民身份离开上海,是因为早在她母亲弃她而独去旧金山的那一天她就认为她“本应作为美国人的生命也跟着飘走了,从那一天起,我不再知道自己是谁”[14](P532)。更重要的是因为她已经心有所属——属于忠诚、属于上海、属于中国。微奥莱最终选择与忠诚留守上海既是对美国身份的拒斥,也是把上海视为家园的肯定,这也正是她找回自我、歌唱自我的真情表达。
四、结语
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通过对路路和微奥莱母女形象的生动刻画,描绘出具有不同情感色调的上海意象,从女性视角构建出颇具近代上海风情的家族史,特别是以想象的形式让外祖母从静态的陈年照片中走向斑斓多姿的生命舞台,为其唱出一曲“自己的歌”。她的家族史想象不是为了通过编年叙事呈现“历史真实”中的外祖母,而是借助主观化的上海书写来构建“情绪真实”的外祖母,进而解答其对“生命真实”的追问,这也是她创作《奇幻山谷》的动机。正如她2012年9月23日写给编辑丹尼尔的邮件所言:“我强烈需要了解上几代女性对我性格的影响……想更多地了解外祖母——她的天性、个性、对待机遇和逆境的态度……我认为其中存在着母亲从未所知的隐秘细节。”[9](P269-270)因此谭恩美在《奇幻山谷》中竭尽想象之能事揭开外祖母的神秘面纱,塑造出微奥莱这个自强不息的女性形象。这种自强不息的品质正是谭恩美借助“所见即所愿”创作观所表达的想象真实,无怪乎她在《奇幻山谷》中“不厌其烦”地引用惠特曼《我自己的歌》中“我不能,也没有谁能代替你走那条路,你必须自己走”的诗句。这段诗句俨然成了微奥莱的座右铭,当然也是谭恩美“送给”外祖母的座右铭,而又何尝不是谭恩美自己的座右铭呢?因此谭恩美基于两张上海老照片创作的《奇幻山谷》既是唱给外祖母的生命赞歌,也是唱给她“自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