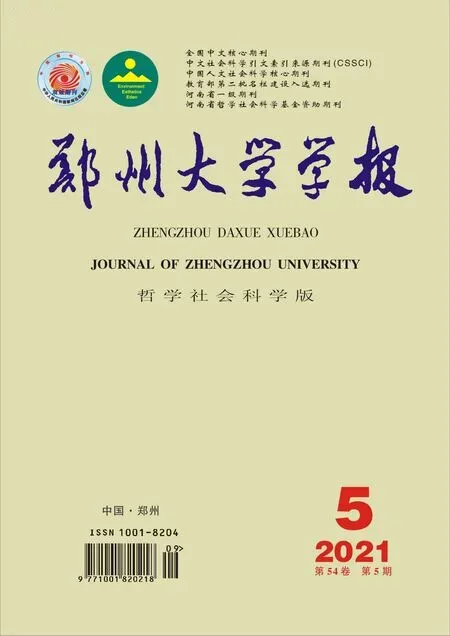公元8世纪的中日“书籍之路”
——基于第12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
王 勇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12)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佛经的汉译始自东汉明帝年间,东晋以后得到官方支持而迅速发展,隋唐时出现专业的翻译机构“译场”,译经事业由此进入全盛时期。汉译佛经在汉字文化圈内畅行无阻,加上中国、朝鲜、日本等地高僧撰写的章疏也在各国间流通,因而在东亚形成一条川流不息的“书籍之路”[1]。笔者试以第12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为例,探析当时中日书籍流传的相关问题。
一、四份正仓院文书
唐开元十八年(730),僧智升编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或“开元藏”),收录“一切经”总数为5048卷。仅仅5年之后的735年,日本入唐僧玄昉携带5000余卷佛书而归,推测是把《开元录》打包带回了日本。这些唐写本佛经传到日本后被大量传抄,并迅速流通到各地寺院。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日本天平宝字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奉写一切经所解》,当时日本的“一切经”总数竟然达到5372卷,比《开元录》还多324卷。其中的谜团何在?本文缀合正仓院文书收录的4份佛经目录,复原唐天宝十一年、日本天平胜宝四年出发,于两年后回国的第12次遣唐使的求书历程,试以揭开这个谜团。
第1份文书是《可请大乘经本目录》。该文书收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类收”条。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两年前的九月二十四日,日本任命了第12次遣唐使官员。另据时间稍后的《东大寺六宗未决义》(775)记载,遣唐使任命后不久,僧纲所向寺院各宗发文,征集所需的书目,《东大寺六宗未决义》即存有5份“欠本”目录。《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列出35部佛书,推断也是这一时期各宗上报的求书目录之一。
第2份文书是《可请本经目录》。该目录列出149部书目,除了大乘经外,还有小乘论、贤圣集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目录包涵《可请大乘经本目录》35部中的34部,并对其中21部添加了书籍的具体信息(作者、译者、卷数等),因此推断《可请本经目录》是僧纲所根据各宗提交的书目汇总、整理、编撰而成。据《东大寺六宗未决义》,这份总目录交到遣唐使手中,以便他们入唐后按图索骥。
第3份文书是《奉写一切经所解》。该文书落款的时间是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收书24部107卷,尾书明言这是天平胜宝四年出发、两年后回国的遣唐使携归,而且都是首次传入日本的“新本”。由此推断,这是遣唐使根据“阙本”目录购求到手的书目列表。前面所说的《可请本经目录》包含《可请大乘经本目录》35部中的34部,而遣唐使携归的24部中有13部出现在《可请本经目录》,这绝非偶然现象,3份目录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第4份文书是《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该文书收在“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类收”条下,收书176部684卷,囊括遣唐使携归24部中的20部(除“目录外经”4部)。日本学者多认为是第12次遣唐使携带入唐的搜书目录,这个推测可以完全排除。从《可请本经目录》可知,日本所需之书,书名、译者、卷数等信息皆不精准,而《未写经律论集目录》不仅标出确切信息,而且还标出写经所需纸数。更可疑的是,第12次遣唐使是天平胜宝六年正月才回国,“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他们人还在大唐。笔者推测这份文书类收时间有误,应该在此之后、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之前。
以上4份文书,在正仓院文书中互不关联,但是把4份文书串接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第12次遣唐使入唐求书的脉络:日本任命遣唐使后,僧纲所向寺院各宗征集“欠本”目录,这是第1份文书;僧纲所汇总各宗递交的目录,整理编撰成一个总目录,委托遣唐使购求,这是第2份文书;遣唐使根据“欠本”目录购求书籍,携带回国上呈朝廷,这是第3份文书;朝廷对遣唐使携归书籍遴选后,确定抄写书目,并支付所需纸张笔墨等,这是第4份文书。
仔细识读第3份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还有惊人发现:遣唐使携归的24部书籍,虽云“并是旧元来无本”,但约有三分之一此前已传入日本,而遣唐使带回的恰恰都是零卷,有些书后还注有“欠”字,如“《大庄严法门经》欠上卷”“《阿育王经》九卷欠第七”等。比对此前日本的写经记录,发现此前日本只有《大庄严法门经》“下卷”,故此次由遣唐使带回缺失的“上卷”;《阿育王经》完本10卷,因故只购求到9卷,特注明“欠第七”,以俟下次遣唐使购求。
由上,对于奈良时代日本的一切经为何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原因基本上有四个方面:一是入唐僧尽其所能带回所有书籍;二是日本高度关注唐朝译经动态,凡日本所无的或新译的,举国家之力购求之;三是因天灾人祸一旦出现残卷断篇,必向唐朝购求补充之;四是日本一切经收藏的门坎比中国低,如对于圣贤集、别生经等也来者不拒。
二、唐与日本一切经数量差异原因
无论古今中外,书籍的越境传播,大多会遭遇语言的阻隔,需要藉助“翻译”的手段。然而在东亚,由于汉字具有表意功能,文字足以超越音声的壁垒,使视觉交际成为可能。因此,经由“书籍之路”传入日本的汉文书籍,可以直接供识字阶层阅读,并通过抄写而扩大读者群。
在隋唐时期东亚的书籍流通中,佛教书籍占据很大比例,这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佛教被视为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是东亚各国努力学习的对象(1)据《日本书纪》五五二年十月条,百济圣明王遣使日本,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附表云:“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辨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天皇欣喜而曰:“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此外,《日本书纪》还记载了日本派出遣隋使的动机,即听闻隋朝天子“重兴佛法”,所以派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二是在造船业和航海术不太发达的隋唐时,佛教徒是敢于到海外冒险的少数群体(2)例如公元752年,第12次遣唐使抵达长安,谒见唐玄宗时,提出聘请儒学名士萧颖士、佛教高僧鉴真去日本传教。然而萧颖士与鉴真的反应截然相反:萧颖士托病推辞,鉴真不顾玄宗皇帝的反对偷渡日本。;三是隋唐时东亚地区很少有人懂梵文,因此汉译佛经成为各国摄取佛教的唯一媒质。
唐写本佛经从中国传播到周边国家后,一般情况下以抄写的形式被快速且大量复制,从而扩大传播面与受众群。以日本为例,奈良时代(710-794年)设立了大量公私写经机构,朝廷雇佣的专业写经生以及寺院的僧侣,夜以继日地抄写传自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佛经,形成规模巨大的“一切经”抄写事业。
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开始抄写一切经不迟于飞鸟时代(592-710年),在天武天皇二年(673)三月,朝廷曾召集写经生在“聚书生,始写一切经于川原寺”[2](P332)。虽然此次写经规模不得而知(3)距此二十余年前的白雉二年,天武天皇曾“于味经宫,请二千一百余僧尼,使读一切经”(《日本书纪》),推知天武二年的写经不会少于2100卷。,但可以断定天武天皇不满足于一切经的数量,仅仅两年后即派出使者,到全国各地收集佛经。
奈良时代迎来遣唐使的最盛期,直接从唐朝传入的书籍数量急速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入唐僧玄昉带回整部一切经。据《续日本纪》记载,玄昉随第9次遣唐使于养老元年(717)入唐,这次遣唐使成员中还包括被日本文献誉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3] (P423)的吉备真备(大臣)、阿倍仲麻吕(朝衡)等,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玄昉在唐留学将近20年后,于日本天平七年(735)携带“五千余卷”佛经回国。
玄昉带回日本的“五千余卷”佛经,推测是唐开元年间的一切经。其主要依据是,开元十八年智升编撰《开元释教录》,经过甄别确定收入一切经的“现定入藏录”,共著录1076部5048卷,卷数与玄昉携归的“五千余卷”大致吻合。
据传唐玄宗对玄昉非常器重,给予他三品官的待遇,允许他身着紫衣袈裟。在中国文化圈内,“紫色”象征高贵的身份,按照唐朝的典章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穿“紫衣”,而僧侣身着“紫袈裟”,一般由皇帝敕许才可以。由此推断,多达“五千余卷”的一切经,单靠个人之力难以短时间内抄完,大概是玄昉回国前玄宗皇帝作为褒奖而馈赠的一份大礼,体现了唐朝对于传播佛教文化的积极态度。
如果以上推演无误,那么在智升编撰《开元释教录》后仅仅5年时间,入唐僧玄昉便将其悉数传回日本,可以说唐代东亚书籍流通之规模与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体量庞大的一切经传到日本后,马上由光明皇后主持的写经所接手抄写,并开始在日本知识阶层流传。这批新写经因为附有光明皇后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的《愿文》,通常称作“天平十二年经”或“五月一日经”“光明皇后愿经”等,据正仓院文书《写经请本帐》载:“自天平八年九月廿九日,始经本请和上所。”[4](P54)可知,抄写时间始于玄昉归国的翌年九月。
开元年间的唐写本一切经东传日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奈良时代的写经事业。大约20年后,据天平宝字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奉写一切经所解》,当时奉日本朝廷之命抄写的一切经总数达到5330卷,较之《开元释教录》著录的5048多出282卷,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与此同时,天平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光明皇后发愿以玄昉携归的唐写经为蓝本开展的抄经事业,经过约20年持续努力,总卷数达到约7000卷之巨,也远超《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数。日本学者山本幸男、山下有美等认为,光明皇后的愿经一方面以玄昉携归唐经为底本抄写,另一方面又收录被《开元释教录》摒弃在外的别生经、伪疑经、录外经等,由此在总数上超过了唐开元一切经(4)有关这个问题,请参看以下诸论文:(1)山本幸男:《玄昉将来経典と「五月一日経」の書写(上)》,载《相愛大学研究論集》第22号,2006年3月;(2)山本幸男:《玄昉将来経典と「五月一日経」の書写(下)》,载《相愛大学研究論集》第23号,2007年3月;(3)山下有美:《五月一日経における別生?疑偽?錄外経の書写について》,载《市大日本史》第3号,2000年5月。。此说应不无道理,唐智升在编撰《开元释教录》时,入藏门坎定得很高,且重视梵本而轻忽本土,连道世《法苑珠林》那样的名著也拒之门外;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入藏条件就比较宽松,除了前述别生经、伪疑经、录外经之外,唐、新罗乃至日本高僧撰写的章疏类也极力收集采录。
正如先学们所指出的那样,唐与日本之“一切经观”的差异,是造成两国一切经总数落差的重要原因。本文希冀在此基础上再推进一步,即以第12次遣唐使为例,通过解析入唐前准备的阙书目录(《可请本经目录》)与回国后递呈的搜书目录(《奉写一切经所解》),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唐代佛书东传的轨迹,破解奈良一切经数量巨大之谜。
三、释《奉写一切经所解》
飞鸟时代开启端倪的写经机构,至奈良時代在律令制度框架下继续发展,逐步形成职责明确、功能齐全、制度完备的“写经所”——除了朝廷运营的写经所,还有皇亲、贵族、寺院等设立的类似机构。
“奉写一切经所”(原称“奉写一切经司”)系直属朝廷、为天皇服务的官营写经机构,“解”则是日本律令制度中下级递呈上级的官方文书体裁。在整个奈良时代,奉写一切经所发出数量众多的“解”,所以一般在文书前冠以“某年某月某日”加以区别。
据前揭天平宝字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写一切经所解》,当时一切经的总数为5330卷。时隔2个月之后的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又发出一份文书《奉写一切经所解》,内容是为了追加抄写新增的107卷佛经,要求朝廷支给纸张、笔墨等。也就是说,在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这个时间点,日本官方的一切经数达到5437卷,比《开元释教录》的入藏数多出389卷。
这份《奉写一切经所解》完整地列出了拟追加抄写的107卷佛经的书目及用纸量,其中大乘经26卷、大乘论1卷、小乘经1卷、小乘论47卷、圣贤集10卷、别生经9卷、目录外经13卷,抄写这些书籍合计需要1852张纸(5)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作“1832纸”,实际统计为1852纸。。为了接下来叙述方便,先将这份文书所列的24部107卷书目编号列表如表1。

表1 《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书目及用纸量
这份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公文,在书目之后、落款之前有一则日式汉文的尾书:“ 以前经论,并是旧元来无本,去天平胜宝六年入唐回使所请来。今从内堂请,奉写加如前。谨解。”[4](P496)
这段简短文字有多重意义。首先,“以前经论,并是旧元来无本”,此处“以前经论”指该文书所列24部107卷佛书;“并是旧元来无本”的意思是“这些都是此前日本所没有的经论”,换句话说均是从唐朝传入的新本。其次,“去天平胜宝六年入唐回使所请来”,此处的“入唐回使”指完成朝贡使命归国的第12次遣唐使,《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条记载:“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来归,唐僧鉴眞、法进等八人随而归朝。”详尽记载了遣唐使归国的年月日。最后,“今从内堂请,奉写加如前”,遣唐使不论官员还是随员,均肩负收集书籍之使命[1],留学僧俗回国后将书籍递呈朝廷接受验收,故此处“内堂”代指朝廷,尤其指光明皇后设立的朝政机构“坤宫”(6)坤宫:天平元年圣武天皇立藤原光明子为皇后,设立皇后宫职掌管内务;天平胜宝元年圣武天皇禅让,皇太后光明子为扶持孝谦天皇,参照唐玄宗改中书省为“紫微省”、武则天改尚书省为“中台”,改皇后宫职为“紫微中台”,使其成为令外朝政机构,其长官为紫微令(后改为“紫微内相”),拥有不经过太政官、中务省而直接奉敕行事的权限;天平宝字二年淳仁天皇继位,改紫微中台为“坤宫官”,职责是“居中奉勅,颁下诸司”。,此机构持续抄写一切经长达20余年,遣唐使带回的经论如同玄昉那样,第一时间供坤宫写经所抄写,故有“今从内堂请”之说。
需要澄清的是,天平宝字四年光明皇太后去世后,一般认为坤宫便被废除了。然这份文书联署人池原公的头衔是“坤宫少疏”,说明坤宫依然存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斐国司解》出现“坤宫官厮丁”字样[4](P523-524),证明光明皇太后去世之后“坤宫”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
四、对石田茂作“补缺卷”的解读
第12次遣唐使携归的佛书“并是旧元来无本”,这句话令人惊讶和好奇。因为随同这批遣唐使赴日的唐僧鉴真也携带了大量书籍,然而鉴真携带的35部中有17部此前已经传入日本,难道遣唐使携带回国的书籍全部是“新本”吗?如果是的话,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日本著名佛教史学家石田茂作对此存疑,通过比对奈良时代一切经抄写目录,指出《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阿育王经》均非初传之书。具体而言,《大庄严法门经》早在天平十四年就有抄写记录,不过仅是下卷,此次传回上卷,于是上下卷始得合璧;《宝雨经》也有天平十四年的抄写记录,所抄写的是第二卷、第五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此次由遣唐使传回欠缺的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至于《阿育王经》,石田茂作的表述比较含糊:“以前虽有五卷,此次补其缺卷而成十卷完本。”[5]
石田茂作指出《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阿育王经》3部为再传书,再传的理由是日本原有传本都是卷帙不全的阙本。按照这一标准继续追查下去,发现前揭《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24部中有7部属于阙本:
☆(06)大庄严法门经 上卷
☆(08)宝雨经 五卷(一、三、四、六、七)
★(13)阿育王经 九卷(欠第七)
★(16)金七十论 二卷(欠第一)
★(18)集古今佛道(论)衡 一卷(第一 欠三)
★(20)摄大乘论释 九卷(欠十、十一)
☆(22)一切经正名 第四卷
石田茂作虽然敏锐地发现了“阙本”这一盲区,即遣唐使只带回所缺之卷,不带日本已有之卷,揭示了日本入唐求书机制中一个新的特征。然而,他的分析还不足于解释上述7部“阙本”包涵的所有问题。如按石田茂作的说法,《阿育王经》日本只有5卷的阙本,那么遣唐使带回“九卷”,至少有4卷成为复本,这与《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仅传回缺卷的情况不同。那么遣唐使“只带回所缺之卷,不带回日本。
笔者初步核查奈良时代的写经记录,发现《阿育王经》的写经记录有15次,内中5卷本最多,有10次;4卷本次之,有2次;其余2卷本、1卷本、卷数不明者各1次。由此可知,奈良时代有多个版本的《阿育王经》传到日本,然而在15次写经记录中没有一次是超过5卷的,这颇令人产生怀疑。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5卷与梁代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10卷,属于同本异译,即同一种梵文佛经的不同汉译本[6]。从遣唐使“不携复本”的求书特征考虑,有一种可能性是此前的既传书为安法钦译本(5卷本),而遣唐使的新传书为僧伽婆罗译本(10卷本)。如果这样解释,遣唐使“只带回所缺之卷,不带回日本已有之卷”的说法还是能够成立的。
即便如此,还有若干问题存在。倘若第12次遣唐使带回僧伽婆罗译10卷本《阿育王经》,为何单单缺少第七卷,只带回9卷呢?注目于《阿育王经》后的注文“欠第七”之“欠”字,发现前述7部阙本中有4部注有此字(标★印者),这些卷帙不全之本似非石田茂作所言为“补其缺卷”而携归者,事实上标有“欠”字之卷均未带回日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五、二份“可请”书目比较
石田茂作以《大庄严法门经》《宝雨经》《阿育王经》为案例,对遣唐使如此精准地带回日本传本的缺卷,赞叹之余又对不明其中机理而甚感遗憾:“此次入唐回使带回的经论,似乎事先应该有所预案,才能有的放矢搜求书籍。据此推考,国内学匠自然知道哪些经论不足,遣唐使入唐之际或许受其委托,然后入唐按图索骥。至为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如此大量的未传经卷,经由入唐回使之手传入我国,堪称经典传来史上值得特笔大书之壮举。”[5]石田茂作察知遣唐使出发之前,接受国内学匠之求书委托而“有所预案”,其洞察机理之慧眼值得敬佩。然而他又感叹“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一无所知”,给后学留下一大难题。笔者追踪这个问题多年,目前稍稍理出些头绪,兹介绍几件相关史料。
《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十二)》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类收”条下,辑录5份缺失年月日的文书,其中以“可请”起头的2份文书(《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可请本经目录》),推测与第12次遣唐使搜书活动有关。
天平胜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日本朝廷时隔约20年任命了第12次遣唐使官员。天平胜宝四年的三月三日,遣唐使举行拜朝仪式准备离京西行。如果《大日本古文书》的系年无误,那么在遣唐使出发之前两个月汇编的《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很可能就是石田茂作所言国内学匠为遣唐使准备的搜书目录。证据之一是,《可请大乘经本目录》收录的35部佛书,下列6部由此次遣唐使带回(序号系依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
(1)方广大庄严经 十二卷
(2)大乘方广总持经 一卷
(3)文殊师利现宝藏经 三卷
(4)证契大乘经 二卷
(5)无极宝三昧经 一卷
(7)浴像功德经 一卷
考虑到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遣唐使携归书目,“大乘经”目录下总共列出8部,其中6部与《可请大乘经本目录》重叠,如此高的比例当非出自偶然。
与这份文书相关的是同一时期的《可请本经目录》,共列出149部书目,除了大乘经之外,还包括小乘论、贤圣集等。虽然《大日本古文书》将两者类收在“天平胜宝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条下,但从记载的方式与内容分析,《可请本经目录》显然晚于《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可请本经目录》收录了《可请大乘经本目录》所列的35部中的34部书目,兹列出两者记载不同者做一比较(见表2)。

表2 《可请大乘经本目录》与《可请本经目录》书目记载不同比较
据宝龟七年二月五日《东大寺六宗未决义》记载,朝廷任命遣唐使之后,僧纲所(管理僧尼与寺院的政府机构,设在药师寺)即向各大寺宗派发牒,征集“未度来书”(未传到日本的佛书),由僧纲所负责甄别汇总编成目录,交给遣唐使入唐搜集。笔者揣度,《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大概是某大寺或宗派递交的“未度来书”,仅列书名卷数而无其他信息,内容也限于大乘经;僧纲所收集各宗各派的“未度来书”后,经过整理归类并加注相关信息(如作者、译者、纸数、书籍别名、卷数考证等),方便遣唐使入唐收集。如“般泥洹经二卷”目下注云:“或直云《泥洹经》,亦云《大般泥洹经》。诸藏中一卷者,唯是上卷,欠下卷也。”又“释迦谱十卷”目下注云:“别有五卷本,与此广略异。”显然是为搜书者指定具体目标。
《可请本经目录》较之《可请大乘经本目录》,增加了大量详细而具体的书籍信息,由此提高了遣唐使蒐书的效率,比对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所载书目,下列13部书籍由遣唐使成功带回(序号系依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
(1)方广大庄严经 十二卷(大方广普贤菩萨所说经,一名《神通游戏》,或曰《大方广经》)
(2)大乘方广总持经 一卷(或无“乘”字)
(3)文殊师利现宝藏经 三卷(或二卷,或无“现”字,或直云《宝藏经》)
(4)证契大乘经 二卷(亦名《入一切佛境智陪庐遮那藏》)
(5)无极宝三昧经 一卷(或无“三昧”字)
(7)浴像功德经 一卷(三藏义浄译)
(13)阿育王经 十卷
(14)禅法要解 二卷(一名《禅要经》)
(15)劝发诸王要偈 一卷
(16)金七十论 三卷(亦名《僧法论》,或二卷)
(17)胜宗十句义论 一卷
(18)集古今佛道论衡 四卷(或三卷)
(19)甄正论 三卷
第12次遣唐使带回的24部佛书中,13部与《可请本经目录》重合,占半数以上,而且书籍的信息(译者、书名、卷数)高度一致,两者的承继关系毋庸置疑。
六、《未写经律论集目录》收录时间考
从玄昉735年带回《开元释教录》、736年光明皇后立刻开始抄写的速度看,第12次遣唐使754年带回的书籍,直到761年才“从内堂请,奉写加如前”,似乎衔接时间过长。填补这个时间空白的是《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这份文书收录在《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十二)》“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类收”条下,日本学者考定为委托第12次遣唐使搜集“未度来书”目录,并认为此书目系天平胜宝四年日本所需的写经底本[7]。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未写经律论集目录》被归为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文书,而前一年三月三日“遣唐使等拜朝”而渡海入唐,这份书目又如何能送到遣唐使之手呢?唯一的可能是《大日本古文书》将其类收于“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时间有误。
《未写经律论集目录》收入佛教经典176部合684卷,内中大乘经46部124卷,大乘律1部1卷,大乘论11部23卷,小乘经57部88卷,小乘论11部197卷,贤圣集传50部251卷,几乎都是玄昉携归经论中所未见的。这个书目比之前述《可请本经目录》,与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重合度更高,遣唐使携归的24部书籍中,除“目录外经”项下4部(《花严十恶经》《一切经正名》《集要智因论》《摄大乘论释》),其余20部全部出现在《未写经律论集目录》中(见表3)。

表3 《未写经律论集目录》与《奉写一切经所解》收录书目及用纸比较
《未写经律论集目录》与《奉写一切经所解》的另一个相似点,便是每部书后均标明抄写所需的纸张数,虽然所记载的每部书纸数多略有出入,但足以说明这些书籍均已传到日本,因此能估算出写经所需纸张。据此可以断论,《未写经律论集目录》绝非日本学者推测是求书目录。
由此推论,《大日本古文书》把《未写经律论集目录》类收于“天平胜宝五年五月七日”文书群显然有误,因为第12次遣唐使天平胜宝六年正月十六日才陆续回到日本,书籍送抵朝廷以及写经所制定抄写计划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据《续日本纪》记载“遣使奉唐国信物于山科陵”是天平胜宝六年三月十日,笔者推测《未写经律论集目录》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后至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前。
按照日语熟语习惯,“可请目录”指应该入唐求索的书目,“未写目录”指已经入掌但尚未抄写的书目,“奉写目录”指抄写既有书籍的目录。
七、奈良时代的入唐求书体制与中日书籍之路的延续
以上通过4份正仓院文书——《可请大乘经本目录》(752年)、《可请本经目录》(752年)、《未写经律论集目录》(754-761年?)、《奉写一切经所解》(761年),大致勾勒出第12次遣唐使“书籍之路”的轨迹:
750年:任命遣唐使(《续日本纪》);
752年正月:各宗上报所需书目(《可请大乘经本目录》);
752年正月至三月:僧纲所汇总书目整理出阙本目录交遣唐使(《可请本经目录》);
752年三月:遣唐使拜朝出发(《续日本纪》);
754年正月至三月:遣唐使陆续回国,将从唐朝带回的佛经交给僧纲所(《续日本纪》);
754年三月以后:僧纲所整理遣唐使携归书籍,除“目录外经”全部列入写经计划(《未写经律论目录》);
761年三月:朝廷确定实施抄写遣唐使携归书目(包括“目录外经”)计划(《奉写一切经所解》)。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其一是《可请本经目录》共列出149部书目,但遣唐使仅带回其中的13部(天平宝字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奉写一切经所解》),那么没有带回的136部怎么处理?其二是遣唐使总共带回24部书籍,除了13部可以推断是根据《可请本经目录》收集的,余下的11部书籍全部是日本的“阙本”或“欠卷”,这些信息又是从何处获得的呢?解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便是《奉写一切经所解》中所列的下面4部带有★号的书籍,即:
★(13)阿育王经 九卷(欠第七)
★(16)金七十论 二卷(欠第一)
★(18)集古今佛道(论)衡 一卷(第一 欠三)
★(20)摄大乘论释 九卷(欠十、十一)
这4部书籍的一个共同点,是书籍后面均标记着一个“欠”字。《阿育王经》共10卷,带回9卷,缺第七卷;《金七十论》共3卷,带回2卷,缺第一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共4卷,带回1卷,缺第一卷、第二卷,说明日本已有1卷;《摄大乘论释》共15卷,带回9卷,缺第十卷、第十一卷。
书目后为何要标上“欠”字呢?说明此次遣唐使没有完成预定的求书计划,留下的任务交给下一次遣唐使去完成。笔者认为,《可请本经目录》中没有带回的136部,可能是作为“阙本”移交给下一次遣唐使;《奉写一切经所解》所列遣唐使带回的24部书籍中,不见于《可请本经目录》的11部,应该是上一次遣唐使遗留下来的“阙本”。
日本国立写经机构任务繁重,第12次遣唐使带回的书籍,5年后终于轮到开始抄写。这次出现的巨大变化是,日本朝廷最后决定,遣唐使带回的书籍全部抄写,包括专家建议剔除的《目录外经》。
中国的一切经门坎很高,一般《目录外经》《别生经》《贤圣》入藏把关甚严。日本的一切经则非常开放,只要是中国传来的几乎全部照单收录,甚至还收入日本人的著作,因此奈良时代的一切经总数超过《开元释教录》也就不奇怪了。
日本到中国求书是国家行为,遣唐使带回好书是可以升官发财的。日本从7世纪初的遣隋使,到9世纪中叶的遣唐使,每次使节团均肩负着到中国求书的使命,200多年没有中断。日本不仅到中国寻找本国没有的书籍,而且还寻找缺失的卷、新的译本、字体端正的好本。
综上所述,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为书籍之路开发出一条高效率的书籍流水线,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