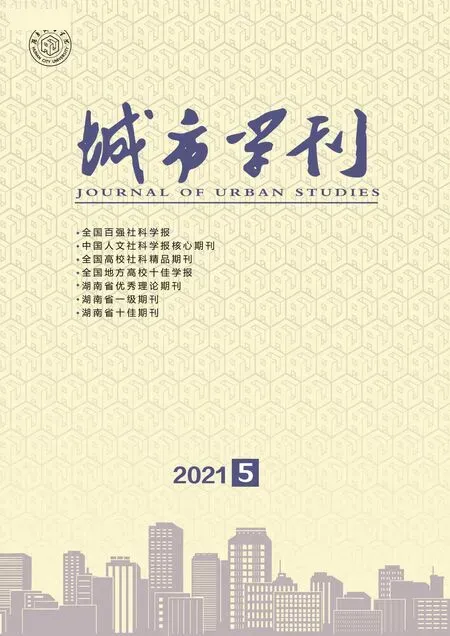论杜甫开元天宝时期诗歌中的时空意识
柳春蕊,王艺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反映在一切意识的投射物之上。文学作为作者意识与情感建构融合下的产物,同样以二者为基本尺度以建构一个新的世界。然而与现实时空不同的是,文学中的时空有更大不确定性——时间超越线性向前的规律而可任意加速或倒转,空间也延伸到物理上也许无法到达的最细微或最广漠处——一切全凭作者创造。因此,作家的时空意识可成为我们探寻文学世界的有效向导,刘若愚说:“对诗歌的作者确定他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方向所用的一个方式作一个考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首诗所表现的世界是怎样从它的语言结构中显现出来的——这又有助于我们评价诗人在发掘语言的潜力以及满足他和我们的创造冲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1]对于语言的重新关照是时空意识最终可抵达的目标之一,同时我们也可籍此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
纵观杜甫的人生,开元天宝时期作为创作的起始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杜甫生于玄宗即位之年,第二年即开元元年,一个盛世的开始。然而到玄宗退位时已是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的战火已经燃起,盛世的帷幕就这样拉下。在这四十四年中,杜甫经历了少年壮游与中年求仕,十年长安的磨砺已将放荡轻狂摧折殆尽,仅留一位“被褐短窄鬓如丝”的萧条长者形象。杜甫青年时期技法青涩、意气激昂之作,也逐渐分化出不同面貌。干谒诗工稳华贵,记游诗闲宕细丽,而言说心迹之诗又多沉痛洒脱。开元天宝时期杜诗风貌这一明确的转折,当是由于天宝六载杜甫入京参加应诏考试,却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借口而落选。[2]因此,可以天宝六载为界比较杜甫诗歌中的时空观,来观察开元天宝年间杜甫诗歌技法的成长及其个体心境人格的根本转变。
一、空间观念
杜甫入京前的诗歌,最早可追溯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始漫游齐赵时期。那年杜甫二十五岁,正值意气风发时,诗歌中已可见辽阔的空间视野。如《登兖州城楼》的颔联和颈联,“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3]首起便是居高而下的视野,所见宏阔,“俯仰千里”。[3]9又如《对雨书怀走邀许十一簿公》起句便是“东岳云峰起,溶溶满太虚”,[3]27只见山上云起,云满天际。又如《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诗中首联“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闻道洪河坼,遥连沧海高。”[3]53虽只交代黄河泛滥之由,也是以天地沧海为空间背景。这重视野不仅作为背景开拓了诗歌中场景的边际,也使得诗中意象有了舒展的空间,整体的格局豁然开朗。
这一时期杜甫最有代表性的诗作无疑为《望岳》,不再以空间为写作之背景,而是直接构成写作的中心: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3]4
泰山本为五岳之首,于其山脚望,以“夫”字引起,“是收拾大山水心眼”,[3]4所见未了之青、阴阳昏晓皆以泰山整体言之,浩然无际。后两句又为山巅视角所见,不仅见眼界辽阔,更见襟怀浩荡,正如清代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所言,“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坐镇”。[3]3
杜甫不仅写景记事诗中设置广阔的空间,写物同样如此。言马为“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3]34;言鹰则“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3]39以不设边界的开阔背景为物之自由心性的外在体现。无怪为注家指认二篇,“亦借酒杯浇块垒,都为自己写照”。[3]41于《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中“霜蹄千里骏,风翮九霄鹏”,[3]126虽然所写骏马与凤凰都是比喻意义上的物象,但依然以“千里”“九霄”作为其腾跃飞翔的背景。
天宝六载后杜诗依旧延续了开阔的空间观念。只是由于身在长安,所见之景多为皇家圣地或贵人所游之景,因而空间的塑造更多华贵气象。《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3]174上句而言,碧瓦、金茎作为宫廷特殊物象已尽显气象,然而单独视之却不足以塑造整个空间。反而是“初寒”“一气”之类虚无缥缈的元素,因为自身没有形状,逸散自由,而使得空间的延展成为可能。清代叶燮在《原诗》中尤为推重“碧瓦初寒外”一句:
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竞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4]
寒气本为天地之气充塞宇宙,寒之“初”即与严寒所不同,碧瓦为一气之寒划分界限,而此句杜甫强调的又是宫廷寒气以“外”那广漠清冷的空间。一句之中,几重空间已见。下句作为自然景物已极为开阔的“山河”“日月”与宫中建筑“绣户”“雕梁”并置,且用“扶”与“近”表示山河日月都无法与之比肩,可见皇家之赫赫威势。相似的还有《行次昭陵》中“风云随绝足,日月继高衢”[3]185一句,也是将自然壮阔之景与人为之建筑相联系。《乐游园歌》则也是写“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阊阖晴开䛈荡荡,曲江翠幕排银牓。”[3]215以地势之高而开阔、宫门大开之旷荡写贵公子之华贵作风。
以神话或传说中超乎自然的神境为背景的渺远空间也在此时出现。《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方丈三韩外,昆仑万国西。建标天地阔,诣绝古今迷。”[3]507方丈与昆仑皆为仙境,“三韩”为古朝鲜半岛南部的三个小部族,以示方丈之远。“建标”本指立柱,然而伫立天地之间的高大则又承接前句对仙境的描写,超脱现实以外。《承沈八丈东美徐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天路牵骐骥,云台引栋梁”一句,[3]494“天路”与“云台”也同样并非现实所有,这与此类型诗歌的目的有关。杜甫希望以诗歌为干谒手段而获得官职,因而仙境的描写不过为夸张的手法,以示豪门之贵。清代黄生曾在《杜诗说》中谈论杜甫与张垍之诗,“起四句语叙其门第之高峻,常人仰之如神仙”。[3]508因此,此类神境空间不似一般描写,不仅强调其似梦似幻之感,更彰显仙境于人世间的疏离与不凡。
另一重对于宽广空间的描写则多为杜甫在长安再一次受挫以后所产生的归隐心绪之反映。天宝十载(751年),杜甫于皇帝祭祀太庙与南郊时作三大礼赋献上,得到了皇帝“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5]的机会,但最终还是铩羽而归。此后的两三年中,杜甫还曾再献《封西岳赋》和《雕赋》等,但未获玄宗任何反响。这使其陷入巨大的失望与迷茫之中,在诗中也开始滋生出归隐世间的怨语。在天宝十一载(752年)所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便言“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3]276辽阔的东海万里被杜甫视为心之理想归宿,只愿化为不驯之白鸥翩然飞去。《送韦书记赴安西》中杜甫也表达了相似愿望:“欲浮江海去,此别意苍然。”[3]326沧海以外,青天也是杜甫心之所向的另一重去处,如《赠陈二补阙》中“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3]401十年长安困守使杜甫无论是在躯体上还是心境上都受到了太多的拘囿,早已为“局促伤樊笼”之状态,[3]476因而如青天或沧海一样渺无边际的绝对广大、自由的空间就成为杜甫心中终极家园之所在。
以上三种开阔空间都为诗歌中的一隅,而能和杜甫入京以前所作《望岳》对标、以空间为写作中心的当推《同诸公登慈恩塔》: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3]295-296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起句极高,慈恩寺本为人世高塔,然而顶端越过苍穹,烈风无止无休,有气接宇宙混茫之感。“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将外部空间与人内部心胸打通,二者皆旷放之境。其下先叙登塔之事,再写登塔之景。塔内本是蜿蜒曲折,“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然寺为佛寺,“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又将狭小空间扩展为佛法无边之界。登塔所见为全篇空间之最,“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前四句呼应此前慈恩寺并入宇宙的高度,以平视的目光打量星河与神祗,极言塔高。明末清初,黄生在《杜诗说》中也指出,“声字若无理,不知正形容登时去天五尺,或若闻之”。[3]297其下四句面对为现实中景物,则俯视切入,高山破碎,河水清浊难分,连长安皇城也是迷蒙黯淡的。固然是因为登高远望所见如此,同时也是诗人对时事忧虑的客观投射。“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此句的背景是阔大华美的神境空间——瑶池与昆仑,与前相似,神境不过是表面的能指,真正的所指还是不可直言的皇家。最后四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虽重在以“黄鹄”为代表的君子与“随阳雁”所代表的小人之对比,然而飞鸟意象本身就是以无垠之天际为背景,结尾仍是气象宏大。
当然杜甫的空间也有小而美的明净场景,多写园林山水。如在何将军府中所作十五首(《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便是在较清幽的空间以内。“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3]357“百顷风潭上,千章夏木清”[3]359可见何将军山林范围并不小,然而杜甫并未强调这一点,而是着重其雅致、清幽的氛围:“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3]365“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3]380“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3]422所写景物皆是花、竹一类小物,其背后留白的空间自然也有限;地点前所修饰的景物也是“薄云”“清天”“流水”,此类景物本是随物赋形,受到园中整体感觉的局限,自然所展现的背景空间也趋于精巧。
二、时间观念
以时间流逝的主体来看,中国诗歌中的时间观念大抵可以分为个人的、历史的、宇宙的。在开元天宝年间,杜甫的时间观念仍局限于前两者,但又有变化。在杜甫入长安以前,很少能看到对于个人时间流逝的喟叹,仅在《龙门》中以川水为喻有所表现。“往还时屡改,川水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3]74诗人与时间在这里是一致的关系,他们都在朝着前方移动,不变的好像只有山水。但是看着往来的行人,诗人却更加感到了自己生命的有限。正如金圣叹以己意揣度杜甫当时所思,概括出两重意蕴:一是川陆间无数人往来,“乌能定其谁当更来,谁不更来?”二是吾生有涯,“彼天下往来人,即岂有不尽之日哉?”[3]75但此外杜甫更多通过怀古以抒发历史的感慨,这一点会在下一部分有所提及。
天宝六载(747年)以后,杜甫先后经历应诏考试的落选、献赋失败,又处处干谒不成,对岁月的流逝极为敏感,也更多个体性感伤。《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对于在长安的蹉跎岁月便直言“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3]277《九日曲江》:“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3]397此时杜甫已四十有二,正如清代王嗣奭《杜臆》所言:“谓浮生百年,去日已多,比之一年,如秋已半也。”[3]397可见杜甫借节序言人生,更显出年岁逝去的凄凉。又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3]262以及《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3]266二者都以一天中的暮色时刻来隐喻整体生命的进度,一切都似欲落西方的夕影,毫无生气,只有时日无多的悲哀。高友工在论述抒情传统时曾经对这种心态作出考察,认为这是由于诗人对于时间的本能的逃避,又出于自身对社会的关心而不得不返归其中,二者冲突便使得“人生的短暂感”成为“不断重复的母题”。[6]杜甫也是如此,对家国社稷的关怀是其一生的命题,也成为身上的缰索。未完成的抱负与生命本能使其对于时间的流逝永远都是焦虑的、逃避的,但是他永远也无法如隐士一般超然世外也超然于时间,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总是使其不得不抬头观察,时间究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
历史的时间在杜甫入长安以后主要见于用典的手法。典故可以使得诗歌时间骤然回返到历史时刻,但最终映照的还是现实的人事。这种双重的效果使得诗歌中的时间不再是简单的单线条,而是回环地交织,立体而细腻。杜甫在长安常常写作干谒诗,既要求文采,又要写清楚自己的境况以寻求帮助,同时也不能太直白显露,用典自然是首选的方式。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3]161汉末河南尹李膺与孔融实际是韦济与杜甫自己的化身,陶潜与葛洪作为隐士的代表也是杜甫在当时状况下无奈的向往。《赠比部萧郎中十兄》“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3]149于山阳隐居锻铁的嵇康与杜甫分享着同一份怀才不遇;《敬赠郑谏议十韵》结句“君见途穷哭,宜忧阮步兵”[3]312中穷途而哭的阮籍也与杜甫拥有同一份末路感。《贫交行》中“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3]317则以管仲鲍叔牙千载仍存的友情与今日人心凉薄相映照。杜甫对典故的使用不仅在开元天宝年间,一直贯彻到其后的写作中,并成为其诗歌一大特点。黄庭坚评价“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明白直露地以古人入典并非杜甫的最高水平,“善于熔铸成语以为己词”,即将前人所言炼化为自己独到的语言风格,才是老杜更为可贵之处。
天宝中期以后,杜甫已开始写作整体相连的组诗,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及《重过何氏五首》等,清吴瞻泰《杜诗提要》点出两组诗歌“首尾布置成章,篇各有意……可为多篇程式。”[3]383《前出塞》《后出塞》在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浦起龙《读杜心解》评《前出塞》:“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甚无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篇大转韵诗读。”[3]257既然组诗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其内部的时间也可以整体视之。《前出塞》《后出塞》相比于《何将军山林》十五首,诗歌时间不再是短期时段内线性的流逝,而有加速、跳转、回忆等布置,更为精巧。《前出塞》一至四首的时间全为出征途中。其一“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3]242是出发参战的士兵自语,其二中军士虽然“出门日已远”,[3]244然而还在路途之中“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3]244相比于此前的不舍、对于发动战争的不解,此时全是少年跃跃欲试的兴奋。其三心境更为复杂,既有“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3]246对于自身命运的担忧,也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3]246此种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其四为被徒长呵斥以后对家人的思念与对从军苦辛的感知。其五以后时间开始加速流逝,从初入军中立下“几时树功勋”[3]248的愿望到练就一身“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当擒王”[3]250的好武艺在战场上杀敌,应当比在旅途中花费的时间要久,然而却在两诗之中就已过渡完成。其七“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还。”[3]251也可见士兵去国之远,征战时间之长。到了最后一首诗已是“从军十年余”,[3]254主人公十余年从军光景在《前出塞》后五首诗之间悄然流逝,与前四首只写其寥寥数月从军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后出塞》的时间变换虽没有《前出塞》明显,但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前二首分别写应募和行军途中,三四写边将征战,最后一首就已是“跃马二十年”后归乡之景。[3]645其中还间有“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的回忆。[3]645可以说,此时杜甫对于组诗中时间的精妙掌控已有后期《秋兴》中错综复杂时间结构的影子了。
三、时空观念的融合
空间和时间在大多并非泾渭分明,巴赫金认为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在艺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7]因而以上对于时间或空间的片面分析也仅是大略言之。实际在杜甫开元天宝时期的诗歌中,时间和空间观念已有十分和谐的融合,二者或是可以相互转化,或是并置同提,构建出一个完整的诗歌世界。
空间与时间虽可以双向转化,但是由空间转向时间这一方向出现的频次明显更高。首先,可以借由建筑或景物,将空间转化为时间。在杜甫创作的初期,已经熟练使用此种手法。或许是因为建筑本身具有将时间转化成为空间的“纪念碑性”,当诗人在古迹的空间中游走时便对历史有更加深刻而生动的体会。在《登兖州城楼》中,他着眼于破败的石碑和荒城,“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3]8“在”和“余”既可以指空间上的留存,也可以指现实时间所在;相似的,在《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中,遗留的城垣也作为感慨的对象。更为巧妙的是,杜甫还引入了当时情景下的另外两种存在——池中的荷花与宴会上的丝竹之音。仇兆鳌对于“圆荷想自昔,遗堞感至今”[3]84的点评就道出了如此安排之妙:“荷种湖中,本当言今。堞在古城,本当言昔。今昔互换,尤见曲折。”[3]86这种同时将建筑与景物作为转化空间为时间的中介还可见《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3]49宋之问与杜甫祖父杜审言曾同朝为官,一同做过修文馆学士,文学上也志同道合,可谓交情颇深,因此杜甫对于宋之问故居有着更加复杂的情感。曾经辉煌的池馆如今已经破败不堪,唯有山河树木依旧,时间的变化与轮回在这一空间中得到了双重展示。
入京以后,杜甫两次游览昭陵的诗歌也延续了这一手法,以建筑及景物作为空间向时间转化的中介。如《行次昭陵》“松柏瞻虚殿,尘沙立暝途。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3]185又如《重经昭陵》“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3]200昭陵中百年未曾改变的景物,无论是松柏还是飞云,都成为触发时间流传的玄机,时间在此重空间中成为流动的存在,过去与现在相互影响,使今日之杜甫得以感受历史瞬间,只是曾经的开国之日已失去了往昔的辉煌,空余寂寥。
空间与时间相融合的另一种方法是将二者隐藏在景物中,以景造境。所谓境,即时间与空间的凝结,有小大之分。小境多为一时一地之景,如《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3]69风林流水草堂营造了风雅的空间,而“纤月”“衣露”“暗水”“春星”则暗示夜已深沉,使得此时空间更多一重幽谧氛围;还有《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尊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3]127宴会小范围的景物透露出当日时节为炎夏,宴会开始在晚夕。而樽罍之旁的池塘与凫雁所栖之华灯又是在夏日夜晚相互辉映,使得整个空间流光溢彩,尽显王家盛宴之奢华气象。较大范围之境则是超乎一时一地,进入更广阔的时空之中。如《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3]107渭北为杜甫所在,江东为李白所在,两地相隔万里。杜甫于春日怀想李白在江南之春,也如自己一般于日暮之时,同一时刻错落写出。《秋雨叹》:“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3]467虽然时刻已确定是秋雨之时,空间已经拓展至四海八荒,二者相合便得无处不雨、无日不雨,整个空间充斥着秋雨连绵、避无可避的压迫感。《渼陂西南台》起句也有类似之处,“高台面苍陂,六月风日冷。蒹葭离披去,天水相与永”,[3]456空间由开阔之高台起,经由蒹葭扩展至天际与水间,六月渐冷之风不仅塑造了美陂清冷的氛围,从天而起拂过水中的运动轨迹也使得整个空间流动了起来。
供试牧草为同德老芒麦(Elymus sibiricus cv.Tongde)、垂穗披碱草(Elymus nutans)、星星草(Puccinellia tenuiflora)、青海中华羊茅(Festuca sinensis cv.Qinghai)均来源于青海省牧草良种繁殖场,青海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 cv.Qinghai)来源于青海省畜牧兽医学院。
杜甫开元、天宝时期的集大成之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作为时空融合的完美典范进行分析。诗歌开篇“夫子自道”,讲述内心“窃比稷与契”的伟大志向及现实遭逢: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沈饮聊自谴,放歌破愁绝。[3]668-669
数十年岁月流逝并未被直白点出,而是借由“老大”“白首”一类词暗示年龄的增长。空间上有大与小的两重对比:以“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中高楼广庙一类广阔的建筑空间来比喻盛世,又以“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中一望无际的海洋作为寄托君子志向的空间,而对于小人之志则仅仅是以蝼蚁的巢穴这样极端狭小昏暗的空间作比。时间和空间的象喻融合在杜甫对于自己的期望中——“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在这一理想的时空世界中,杜甫将自己许身之愿与忧黎元之心同君子之志一样寄托于江海之上,以潇洒的态度面对日月光阴的流逝。
第二段记自京赴奉先途中所见: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3]669
杜甫经过骊山的旅途时间实际只有半夜,然而在记录玄宗骊山游幸时并未以现实的时间为尺度。仅仅从此段的描述看来,并不能确定玄宗仅一次出游是这样旌旗蔽天、卫士众多、宴乐欢会的奢华场景,还是次次皆如此。同样,下二句写为宫廷织布的寒女与受鞭挞的丈夫,也无法使读者得知这种暴行是否时常发生。时间的遮蔽使天子之乐和贫民之悲都被放大与延长。这一段空间也是开阔的(“蚩尤塞寒空”“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但与前一段不同,只是帝王极大排场的表现,而非君子内心充塞宇宙的志向,具有讽刺意味。而这种讽刺意味最终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重空间的对比中达到极致。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3]669-670
此刻由上一段语义暧昧所造成的时间凝滞又恢复为日常时间,但是亲见幼子去世的悲伤这种情感的放大又使得时间趋于转慢。空间上也相应由户外冰河转入家门内压抑窄小的空间。然而在其后所抒发对更广泛的人民的同情中,空间也转换到一个包含有千家万户普通人的世界。在结尾收束于“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又将空间拉到更为高远的终南山之上,与此前讲述自己的江海之志相照应。
四、从时空观念中看杜甫前期的精神成长
纵观杜甫开元天宝时期的时空观念,有许多一以贯之之处,这是其人格挺立的根基。同时,其流动性中也含有杜甫精神成长的脉络。
在空间上,宏大与辽阔是杜甫不变的追求。入京之前的杜甫似乎永远是那个站在泰山山顶心雄万夫的青年,身在浮云中,目视众山外。这种气度固然来自他的家世,远祖杜预是西晋文武兼擅的名臣,既是晋灭吴之战的统领,又曾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流传后世;祖父杜审言是前朝以才名著称的大学士,矜诞狂傲,认为“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5]5735即便是不出名的父亲杜闲,也是从五品的兖州司马。家声的显赫固然提供给杜甫优渥的成长环境,让他有条件在青年时期即漫游吴越及齐赵,所到之远即使现在也令人惊叹。最让杜甫引以为傲的还是自己的天赋——他也明白“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是怎样的惊才绝艳,在晚年的回忆中才会坚持将这首面目模糊的小诗作为自己文学的起点,将凤凰作为自己一生的图腾。
抵达长安以后,事情从不遂杜甫所愿:天宝六载参加考试,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荒谬理由而落选;天宝十载后数次向皇帝献赋,除“待制集贤院”,也未获得更多积极的反响;即便杜甫将目光投向干谒权贵这条道路,在天宝十载到天宝十四载的四年中,约有二十首干谒诗,却未因此而收获一官半职。此时杜甫已经不再像年轻时眼高于顶,他也开始困惑彷徨,甚至卑躬屈膝,但是在空间上却决不妥协,总是要将自己的归宿谋划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和天空。这是比泰山山顶更高更远的地方,也是凤凰应当栖止之处。在精神空间,杜甫永远是向外舒展的。
时间观念里,杜甫对于自身和历史间关系的处理也可见其成长。青年杜甫对历史时间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这使得诗歌中充斥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对于这一心理,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李泽厚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憧憬和悲伤进行的分析,“它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青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春花春月,流水悠悠,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8]人在少年时期往往是通过这种对时间的体认而树立“自我意识”。因此可以说,对于历史时间的关注同样是杜甫自我关注的方式。杜甫对历史的特殊情感,在闻一多先生来看,很有可能与其在书斋中度过的少年时光有关:
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9]
青年杜甫虽然对于古人有着这样的温情和敬意,也借助这些古老的故事反思、寻找自己在现实中的位置。然而在入京以前,杜甫并不能说与一些古人有真正精神上的遇合,因为他缺少在广漠尘世里真真切切的挣扎。然而长安十年让他无师自通地学习到了这一切:衰老与疾病慢慢开始纠缠上了他,每天也要思考明日的蔬食从何而来。于是杜甫渐渐能够从那些同样不幸的古人里瞥见自己的影子。
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杜甫不仅仅将眼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投向更远处,这使得杜甫开始与总是顾影自怜的诗人区分出来。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仅为君主忧心社稷,更关心社稷中每一个真实的个体。当看到宴会上君主赏赐群臣的华美布料,他没有将钦羡的目光停留于此,而是立刻想到制作者可能面临的困境;哪怕是自己的小儿子因为饥饿失去了生命,他在哀痛中仍然听到了远方遥远的哭声——那是比自己处境更要艰难的人。
杜甫异常敏锐的时空意识使我们有机会从中摸索描绘出他在开元天宝时期的精神肖像:无论是对开阔空间的坚守,还是对历史和自我有了崭新的认识,亦或开始关注更大的群体,都是其人格的完善和成长。正是这一阶段的精神成长才得以奠定杜甫为后世所认可的忠厚、仁爱等文化个性,使其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