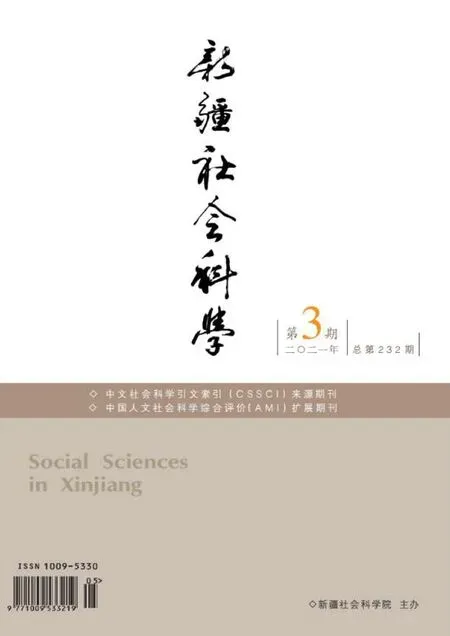新冠疫情、疫苗突破与经济复苏的逻辑与建议*
李富有 王少辉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新冠疫情逐步趋于终结,新冠疫苗也有效被突破,经济复苏就成为当前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导致了新冠疫情,而新冠疫情又是本次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那么,疫苗突破是否就能终结新冠疫情?疫情终结是否就意味着经济复苏?这些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厘清经济复苏的逻辑,关系到我们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努力。基于此,文章尝试对新冠疫情、疫苗突破与经济复苏的问题边界和逻辑进行剖析,结果发现:疫苗并非是疫情终结的必要条件,疫苗的主要贡献在于巩固疫情防控的胜利果实以及增强公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而经济复苏有其本身的自然规律,疫情终结仅仅解决了劳动者“能不能上班”的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劳动者“有没有班可上”的问题。因此,要从经济复苏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出发,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和必要的刺激干预,才能促使我国经济快速重回健康增长的轨道。
一、引言
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肆虐已经长达一年,世界经济发展严重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将是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国家,(1)高伟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是今年唯一正增长主要经济体》,《经济日报》2020年10月15日第1版。这主要归功于中国也是目前全球唯一完全控制住疫情蔓延、最接近终结疫情、最早全面复工复产的国家。这表明,新冠疫情毫无疑问是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只要新冠疫情继续蔓延,经济衰退就没有拐点。(2)郑健雄:《新冠疫情、经济衰退与中国应对——基于马克思产业资本理论的视角》,《学术研究》2020年第12期。截至2021年4月21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4105亿,死亡病例超301万。(3)http://www.legaldaily.com.cn/government/content/2021-04/21/content_8487946.htm.目前,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对疫情的防控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成效,所以,我们预期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发展蒙上的阴影在短时间内将难以消除。
然而,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这一年里,全球股市却表现出了持续性的亢奋,全球股市在2020年2月10日见底之后,已经持续上涨超过一年。截至2021年4月21日,中国上证指数最大涨幅达到41%,创业板指数最大涨幅达到93%;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最大涨幅达到113.7%;德国DXA指数最大涨幅达到88%;日经225指数最大涨幅达到87.7%。虽然,我们都明白“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价格会围绕价值不断波动”等经济规律,股价在短期内背离价值本是无可厚非的事,即在经济衰退期间,股市的上涨可以理解为是资本对未来短期内经济复苏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预期,(4)王箐、王钟黎、李士雪、薛付忠:《“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股市价格波动的短期影响》,《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6期。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本次全球性牛市持续的时间和累积涨幅与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以及疫情持续蔓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不过,全球股市上涨也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除了全球央行的“大水漫灌”之外,(5)潘超、程均丽:《全球疫情冲击下的我国央行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南方经济》2021年第1期。新冠疫苗突破的新闻报道也是资本市场看好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在梳理每一次新冠疫苗突破的新闻报道当天和全球股市前后几天的走势就不难发现这一规律。这一现象说明“新冠疫苗突破”在人们的认知中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载体,即新冠疫苗的突破虽然不能短期终结疫情,但至少能够解除对人们经济活动的限制,能够使经济发展自然复苏。而事实上,中国于2020年3月就全面控制了疫情蔓延,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6)邓晰隆:《新冠肺炎疫情下“农民工务工结构重塑”的对策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目前成为了全球唯一的经济正增长国家,但是和2019年同期经济增速相比,2020年经济增长仍然无法与之匹敌,这说明破坏经济发展的原因并不一定就是经济重新复苏的充分条件,如果搞不清楚激发经济复苏的逻辑,我们在经济复苏道路上的努力就很有可能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距离目标就越远”。基于此,本文将尝试对新冠疫情、疫苗突破与经济复苏三者之间的问题边界、相互作用逻辑进行剖析,希望以此能够厘清经济复苏正确的运行逻辑。
二、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回顾和梳理
(一)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总量的影响
2021年1月18日,中国政府公布了2020年度经济数据,全年GDP总量为1 015 986亿元,较上一年度增长了2.3%。(7)张怀水、陈星:《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1 015 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每日经济新闻》2021年1月18日。从数据来看,增速仍较2019年同期变缓,这说明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总量的影响还是较大的。如果再将各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对照我国对疫情控制效果的时间节点来看,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新冠疫情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较高的相关关系。我国新冠疫情于2020年1月下旬全面爆发,随后,武汉封城、全国各地也都陆续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疫情防控行政措施,直到3月20日新华社发布了“关于全面复工复产的政策解答”,也就是说一季度政府工作重点在于最为严格的疫情防控和生活必需项目的复工复产,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情况为同比下降6.8%。(8)朱启贵:《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与中国对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武汉于2020年1月23日“封城”,于4月8日“重启”,武汉的重启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经济主要行业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但并非所有行业都完全摆脱了疫情的影响,毕竟旅游和一些娱乐场所的开放直到7月24日才有序进行,(9)俞悦:《影业复工!北京电影院7月24日恢复营业》,中国经济网,2020年7月24日。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数据为,二季度同比增长3.2%,三季度同比增长4.9%。而事实上,在7月24日以电影为代表的娱乐场所全面开放之后,全国复工、复产、复学等基本上都已经完全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与之对应的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也达到同比增长6.5%。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实际上是通过疫情防控对人们活动自由度的限制来实现的:一季度是疫情的爆发期,人们被迫居家隔离,生产和消费自由度被严格限制,导致一季度经济严重下滑;第二、三季度主要行业全面复工复产,但居民的消费自由度却因为旅游和娱乐等行业的有条件限制并未得到全面恢复,所以,经济有明显复苏但未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而7月24日后,无论在生产还是消费方面,疫情对人们自由度的行政限制几乎完全消失,而反映在经济数据上,第四季度GDP增长也达到的6.5%。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总量影响的逻辑,至少在数据特征上表现为新冠疫情发展或被控制的程度影响着人们生产和消费自由度的程度,人们生产和消费自由度的程度再影响着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程度。
(二)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结构的影响
我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成为全球最先完全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由此,我国也成为经济最先恢复正常的国家,2020年全年经济同比增长2.3%。从2020年前三季度相关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311 901亿元,同比下降5.9%,但全国网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却达到91 275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实物商品线上零售额为75 619亿元,增长16.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4.2%,(10)马浩歌:《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 576亿元同比增长4.3%》,《新京报》2020年11月16日第1版。这说明在疫情的冲击下,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驱动动能正在逆势释放,产业转型速度明显加快;但另一方面,消费总体疲软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例如,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品的增长幅度分别是34.3%、5.6%和17.4%,这说明社会消费品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快速恢复,只是将满足需求的途径从传统零售变成了互联网销售而已。(11)贺小丹、陈博、杜雯翠:《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者信心的冲击效果与作用机制——基于中国35个城市居民问卷调查的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年第3期。这种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消费品的零售方面,在物流供应链、自动化机器人、数字及AI 医疗、在线教育、人工智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结构变化。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新冠疫情倒逼的结果,疫情对经济发展结构倒逼的逻辑主要有两条:一是疫情改变了人们居家和社交习惯进而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使人们改变了消费手段但并未改变消费内容;二是疫情防控对人们活动自由度的限制导致了局部经济的停摆,经济总量萎缩现象明显,倒逼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不断加码,催生新基建、智能化服务新业态等的发展,以此来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综上逻辑,无论后续如何刺激经济发展,传统路径和手段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经济发展结构的变化趋势已经步入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经济的发展轨道。
(三)新冠疫情对人力资源结构的影响
鉴于我国关于失业人口的统计口径与国外有着较大区别,再加上我国特有的扶贫政策为民生工作保驾护航,所以,与国际社会进行就业数据好坏的横向比较意义不大,但从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贫富差距、居民收入等维度来审视就业情况,我们基本可以得出2020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的结论。2020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向好主要体现在:我国对疫情防控在2月底就已经显示取得良好成效,基本上已经做到主要行业的全面复工复产,到第三季度末各行各业的就业空间已经被完全打开,劳动力供需情况趋于平衡,就业数据也趋于稳定。而就业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则主要反映在农民工就业数量同比下降和大学生就业面临困难:一方面,2020年第三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达到1.7亿,较第二季度末增加200万余人,但相较于2019年同期减少384万人,同比下降2.1%;另一方面,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也在明显加大,主要体现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校园招聘的用工需求锐减和招聘季时间缩短的双重冲击,截至9月份,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20—24岁被调查人员中,失业率相比2019年同期上升了4%左右。(12)柴畅:《国家统计局:7月份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依然存在》,《成都商报》2020年8月14日第3版。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疫情冲击,尤其是国外疫情的持续蔓延,需求终端难以恢复,致使制造业恢复节奏相对缓慢,企业用工需求同比降低,导致对农民工用工需求下降,同时,企业对未来用工需求存在不确定性的担忧,也导致对应届大学生校园招聘力度严重萎缩;二是国家启动了应对疫情冲击的促就业计划,鼓励就近就业、就地创业的政策也发挥了正面效应,使得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意愿增强、外出务工意愿下降,导致农民工务工统计数据同比下降;三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成为经济恢复的主要贡献力量,这些新经济、新产业无论是对农民工还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新技能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供需错位的现象,或者说,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技能转换(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这些新经济、新产业崛起的速度。总的说来,新冠疫情对人力资源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衰退导致人力资源原本较为弱势的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出现了过剩局面;通过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新产业在疫情中崛起,导致社会对用工技能的需求变化速度远高于人力资源原本自发的技能更新速度,造成人力资源的供需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性矛盾。
(四)新冠疫情对经济产生“可逆”和“不可逆”影响的小结
所谓历史不能重来,无论以后新冠病毒在人类科技面前可能会变得如何渺小,但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以及疫情肆虐下的经济衰退始终都会被记录在人类历史的大事记上。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然也会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些影响中,我们认为有的影响是可逆的,即疫情肆虐让经济偏离了既定的轨道,但是随着疫情的结束,它又将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而另一些影响则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即便疫情结束,它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甚至会直接引领经济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新冠疫情影响经济的这一年,实际上也是经济在十字路口选择方向的一年,疫情的影响甚至还可能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13)施震凯、诸梦婕、武戈:《“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及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2020年江苏省世界经济学会年会暨理论研讨会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6期。在疫情的影响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可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活力、规模和增长速度等方面,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逻辑,疫情限制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交方式,从而限制了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活力和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但这种变化也一定会随着疫情的结束,随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交限制的解除而再次恢复。然而,另一方面,就当前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来看,疫情导致经济结构的部分变化已经产生了“不可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疫情催生并固化了许多人们在社交活动中的新习惯,进而使得社会消费方式发生改变,最终引发国民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一系列产业的崛起都是人们居家和社交习惯变化并固化的结果,例如线上购物、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新消费模式持续火热,在线办公、远程问诊、在线教育等正在快速崛起。(14)杨良初、万晓萌:《疫情防控条件下“稳就业”若干思考》,《地方财政研究》2020年第9期。
综合这些“可逆”和“不可逆”的变化,不难发现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将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与人们新的居家和社交习惯变化并固化之间的速度上,在这一点上,制造业的升级速度显得更缓慢一些,其制造业的效率问题也会相对明显一些;(15)蒋浩:《疫情冲击下经济危局、变局、新局及应对》,《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1期。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产业虽然与人们习惯改变并固化的速度差并不明显,但产业发展方向的试错成本却相对较高,并且其风险主要由中小企业来承担,(16)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改革》2021年第2期。而中小企业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这就意味着疫情后新经济生态的快速恢复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与之相对应,这些“可逆”和“不可逆”的变化也会对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相应的积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一是新兴产业快速挖掘出内需增长点,促进经济内循环的健康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韧性的不断提升,使得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经济压力得到逐渐化解;(17)胡德宝、赵静:《新冠疫情和贸易摩擦双重不确定性下中国供应链重构的策略研究》,《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期。二是无论经济转型升级过程的痛苦程度如何,疫情始终都会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进程得以加速,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软着陆,将促使中国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18)李富有、王少辉:《经济内循环的内涵逻辑与内卷化挑战研究》,《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三、新冠疫情、疫苗突破和经济复苏问题的边界剖析
(一)新冠疫情与疫苗突破的问题边界剖析
新冠疫情与疫苗突破,看似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医学问题,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哲学属性。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瘟疫,最终也都被人类所战胜,而取得胜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严格的“社交管控”对病原体进行隔离(包括焚毁等),以达到阻断病毒传播甚至致使病毒灭绝的目的;(19)吕亚虎:《秦汉时期对传染性疾病的认知发微——以出土简文所载疠病为例的探讨》,《人文杂志》2020年第9期。二是通过研发疫苗,使人们接种疫苗后产生抗体以对抗病毒对人体的伤害,但病毒仍然存在,与人类社会实现共生。(20)高良敏、程峰:《历史与新域:新型传染病流行与控制的新叙述》,《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0期。在现代医疗技术发展之前的几千年中,人类战胜瘟疫的手段只能是依靠“社交管控”,所付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减少还是经济发展的衰退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古代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较差的情况下,甚至还可能会引发种族的灭绝。(21)Hsien-Te Kao and Jennifer Switkes,Epidemiological Perspective: Radicalization of Human Mind,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ciences,2018,39(6),pp.1297-1307.但是,“社交管控”手段在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相对较高的现代社会中,不仅管控成本可控,而且其成效往往也相对明显,从本次全球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来看,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也仅仅只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完全阻断了新冠疫情的传播。而广泛依靠疫苗研发来控制疾病的历史也只是近百来年的时间,而且疫苗的有效性、有效周期等对于不同疾病而言,差异性也十分明显,最重要的一点是,有的疾病虽然人类已经能够控制住它的蔓延,但是迄今为止也没能研发出疫苗,甚至还没能找到病因。所以,病毒和疫苗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病毒都能(或都必需要)研发出疫苗,因为病毒还可能会不断出现变异,那么,疫苗研发的成本就会十分高昂。例如,本次新冠疫情,病毒变异的速度就远远快于疫苗研发的速度,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已经突破的疫苗也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后续还要根据病毒变异的情况继续追加疫苗研发的投入。
依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新冠疫情与疫苗突破之间的逻辑和边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冠疫情的出现催生出人们对新冠疫苗研发的诉求,尽管截至写稿日期,我国所研发的新冠疫苗在临床显示效果明显,但疫苗的有效性是否能够强大到结束疫情的地步,并没有定数;二是新冠病毒的变异性相对较强,疫苗研发始终会存在较大程度的滞后性,这就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终结很有可能与疫苗没有关系,至少最后一个版本的病毒变异就应该与疫苗没有关系,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终结就始终与疫苗无关。依据新冠疫情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很显然中国政府是厘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才有一手强硬的严格管控和防控,一手致力于新冠疫苗的研发,强硬的严格管控和防控为的是切实有效地快速终结疫情,致力于新冠疫苗的研发是为了巩固疫情管控和防控的胜利果实。
(二)新冠疫情与经济复苏的问题边界剖析
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感染者无法工作,还要消耗医疗资源,而没有感染的人为了避免感染需要与他人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甚至是强制隔离或者自我隔离,也无法正常工作,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生产不足导致收入不足,收入不足又导致消费不足,最终导致整体经济的衰退,那么,无论是直观上还是理论上,我们都很容易推导并认可新冠疫情是导致整体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但是反过来,是否终结新冠疫情就意味着经济开始重回轨道,就会开始复苏了呢?惯性思维较强的人的确是容易犯这样的认知错误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即要厘清新冠疫情、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之间的边界和逻辑,才能为经济复苏的努力找准方向。首先,从前文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新冠疫情是造成本轮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但事实上,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次新冠疫情虽然是表征上的主要原因,但是否是其“根本性原因”,还是“触发式诱因”,其实很难有定论;其次,从逻辑推演的角度来说,假如“A导致B”,即便充要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也顶多说“知道B可以判断A的存在”,我们很难从“A导致B”得知“非A导致非B”的结论,因此,我们顶多在发现经济已经复苏之后,来得出新冠疫情已经被控制的结论,而不能得出如果新冠疫情被控制,经济就一定会复苏的结论。
而事实上,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债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居高不下,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如同在走钢丝,按这样的比喻,其杠杆率越来越高,就好比钢丝越来越细。以中国经济为例,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所发布的《2019年度宏观杠杆率报告》表明,2019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高达245.4%,且增速比2018年还上升了6.1%。(22)李扬:《2019年度宏观杠杆率报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19年,第39页。这就意味着,本次新冠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逻辑,除了它从根本上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工作和消费,从而影响到生产和消费能力之外,它还是诱发实体经济高杠杆率爆发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新冠疫情既是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又是“触发式诱因”,而经济的真正复苏则需要居民生产能力的恢复(疫情造成的根本性原因)和实体经济杠杆率降低到合理范围(疫情造成的触发式诱因)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然而,新冠疫情的结束仅仅是解决了劳动者“能不能上班”的问题,但是它并不能解决劳动者“有没有班可上”的问题。
(三)疫苗突破与经济复苏的问题边界
在恢复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而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投资、出口和消费,其实,这一表述仅仅是从客观上阐述了“如果投资、出口和消费能够并驾齐驱,就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并不能说“当前具备了投资、出口和消费的能力,经济就一定会增长”。当各类国民经济主体具备了追加投资的财力、增加出口的产能和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的消费能力时,如果他们对经济前景并不看好,他们仍然会表现出较重的观望情绪,所以,只具备了经济复苏的条件(或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所有具备经济复苏条件的经济主体愿意将自己的经济资源配置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去,此时,真正的经济复苏或增长才会出现,即当经济复苏或增长的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新冠疫苗的突破”所能解决的就是经济复苏的“信心”问题。依据前文“新冠疫情”与“疫苗突破”的边界剖析,疫苗研发总是会滞后于病毒变异的,所以,强硬的严格管控和防控为的是切实有效地快速终结疫情,致力于新冠疫苗的研发是为了巩固疫情管控和防控的胜利果实。那么,当疫苗研发在不断突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向公众传递一种疫情结束、经济将会复苏的信号,从而激发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疫苗突破与经济复苏的边界和逻辑并不是“疫苗突破导致疫情终结,疫情终结导致经济复苏这样的逻辑路径”,这也是大家最容易犯的认知错误。而它们之间的边界和逻辑在本节的三组关系中属于最为明朗的,即新冠疫苗的不断突破,会不断增强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当然,新冠疫苗的突破也仅仅是众多可以增强公众对未来经济前景产生信心的原因之一,而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恰好就是经济复苏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新冠疫苗的不断突破能够解决公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问题,但是它并不包含支配经济复苏的全部要素,反过来,如果有其他途径解决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问题,在驱动经济复苏的客观能力(投资、出口和消费)已经满足的条件下,有没有疫苗突破,经济也照样会复苏。
四、经济复苏的干预逻辑与建议
(一)经济复苏的必备条件
所谓经济复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指社会经济水平从衰退的趋势中触底不再衰退,并在事实上形成衰退趋势的拐点后,开始拐头进入不断增长的趋势轨道中。单从经济数据的表征讲,经济复苏可以被理解为,经济从萧条的状态回归繁荣,从较低水平的社会生产和消费回归到较高和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于是,我们可以将经济复苏分成两个阶段,即经济从衰退趋势中触底形成拐点的阶段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阶段。
1.经济衰退触底形成拐点的条件
经济衰退往往都会有具体的原因,包括根本原因和诱因,其中,根本原因会相对复杂、综合一点,短时间内难以厘清各种根本原因之间的关系,甚至关于这些根本原因的组成内容一时间也难以被一致认可;而诱因往往会清晰很多,就是我们俗称的“导火索”。以本次经济衰退为例,依照前文的剖析,新冠疫情既构成了本次经济衰退根本原因的一部分,又是本次经济衰退的独立诱因(导火索)。诱因是经济下行的初始动能,只要这个动能存在,经济下滑就会一直被加速,其实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物理学逻辑,即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作用力/质量,(23)牛文元:《社会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经济衰退触底形成拐点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再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经济下行的“降速”和“止跌”两个阶段,找到经济下行的诱因,并消除诱因,就可以消除驱动经济下行的驱动力(即物理学公式中的“作用力”),将经济下行的加速度逐步变为零的过程,就是经济下行的“降速”过程。经济下行的“降速”并不是经济下行的“止跌”,因为根据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理),我们容易理解即便在经济下行驱动力消失后,不再有经济下行加速度时,经济仍然会保持惯性下跌,所以,这就要给经济下行一个反方向的驱动力,使得经济下行的加速度变为负数,直到经济下行拐点的出现。由此逻辑,我们容易理解,新冠疫情是本次经济衰退的诱因,我们通过强有力的疫情管控和防控终结了疫情,就是消除了驱动经济下行的驱动力,完成了经济下行的“降速”过程;而自疫情以来,我国乃至全球各国所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经济刺激及纾困政策,就是给了经济下行一个反方向的驱动力,完成经济下行的“止跌”过程。
2.经济持续增长的形成条件
消除经济下行的诱因,可以完成经济下行的“降速”过程,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和纾困计划,可以完成经济下行的“止跌”过程,甚至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正增长。但是这些都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无论上述过程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那都是人为的虚假繁荣,都是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所吹起的泡沫。健康的经济增长则是以经济衰退触底拐点形成为起点,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任其市场经济自由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健康的经济增长就是“人们生产的更多,消费的也更多”,这也是经济发展本源的基本内涵。(24)邓晰隆、叶子荣:《经济发展本源视角下的经济区运行效率探究》,《江淮论坛》2013年第2期。经济学家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中,投资的拉动是为了使“人们能够生产的更多”,而出口和消费的拉动则是为了使“人们消费的更多”,最终,生产和消费会在一定水平上维持均衡,当低水平的均衡跃迁到高水平的均衡时,说明经济实现了正增长。在经历了新冠疫情肆虐后的经济发展中,经济要想能够进入到持续增长的轨道,经济衰退触底拐点的形成是其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修复国民经济结构和优化制度安排,使国民经济具备“投资、出口和消费”的能力是其基础条件;进一步优化社会营商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各类经济主体增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使其愿意投资、敢于消费,是经济步入持续增长轨道的必要条件。
(二)为经济复苏服务的宏观调控建议
1.充分利用我国制度优势巩固防疫成果,增强公众对经济复苏的信心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于疫情的防控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交隔离”管控,另一种则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群体免疫”模式,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已经不言而喻,我国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肆虐1年多的时间里,光美国就付出了超过56万人生命的代价也没能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而采取“社交隔离”管控的方式进行疫情防控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用过该种方法,最终效果虽然好于英美等国家,但却远不及我国,他们人口少于我国,但控制疫情所耗费的时间却比我国要长,而且这中间疫情还经过了好几次反复,迄今也没能达到像我国目前这样几乎完全终结的状态。我国疫情防控的成绩主要得益于我国优越的政治制度,上至党中央、下至村落社区,无论是信息技术能力还是政府行政能力,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制度优越性。目前,除了公众个人卫生习惯较疫情之前有较大变化之外,在生产和消费领域,我国的社会运转几乎与疫情之前没有太大差别,但是,国外疫情的情况还是十分严峻的,目前对我国疫情防控最大的威胁主要在于“境外输入”,而且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较快,为我们对境外输入病例的甄别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所以,我们建议:首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在继续保持现有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升疫情防控的智能性;其次,要加大病毒防疫的科研投入,与国际接轨,加强病毒检测、防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及时掌握新冠病毒变异的最新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提升对境外输入病例检测的精准性和快捷性;再次,以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原则,加强新冠疫苗研发的国际合作,加大对其他发展中和落后国家的疫苗援助,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提升疫苗的有效性;最后,要加大新冠疫苗接种的宣传力度,优化宣传技巧,以提高我国居民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只有这样,才能不仅控制住疫情、终结疫情,还要让公众不惧怕疫情,进而才能提升公众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我国经济才能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
2.科学把握经济刺激与纾困计划的力度和节奏,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
经济刺激与纾困计划始终都是经济下行的反向驱动力,它的功能是比较丰富的,可以在经济加速下滑的时候,与消除经济下滑诱因组合使用,达到快速降低下行加速度目的;还可以在经济惯性下滑的时候,逆向驱动以减缓经济下行达到止跌并出现复苏拐点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阻止经济下行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调整经济刺激与纾困计划的力度和节奏,还可以达到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目的。毕竟,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发展瓶颈问题,所以在那时,我们才推出了“互联网+”、“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 “工业4.0”等一系列可能优化我国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的国家战略。(25)邓晰隆、叶子荣:《农民工主动性技能提升转型的决策逻辑分析与启示——来自上海、成都和兰州的数据实证》,《中国软科学》2020年第3期。而优化经济结构助推产业升级的改革,实际上就意味着需要大力度地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商业模式,这种“做减法”的改革阻力势必会很大,而且如果力度和节奏把握不好,还存在导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在新冠疫情的诱因作用下,经济整体遭受打击出现下滑,但各行业的承压韧性却各不相同,其中,落后产能、落后商业模式往往会表现得更为脆弱。此时,经济刺激与纾困政策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即要解决大家“能活下来”的问题,然后,才是解决经济如何复苏的问题,而在整体性刺激经济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为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这就意味着经济刺激与纾困政策不能平均用力,行业和产业需要依据当前经济双循环的战略背景,朝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预期的经济结构方向,把握好经济刺激与纾困的力度和节奏,这种优化经济结构、助推产业升级的改革就属于“做加法”的改革,相对于“做减法”的改革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3.尽快建立“金融类危机处置机制”将经济的刺激性增长转变为健康增长
前文在讨论新冠疫情与经济复苏的问题边界时,就指出了2019年我国实体经济的杠杆率已经高达245.4%,这才为新冠疫情作为导火索肆虐经济提供了机会,所以,在2020年下半年的多个场合,货币当局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中反复提到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早在2017—2018年,我国曾经以行政方式限制债务增长而达到降低债务率的目的,而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十分理想,最后又不得不推出中小民营企业的纾困计划,于是,去杠杆的战略就变成了稳杠杆战略,(26)沈昊旻、程小可、杨鸣京:《去杠杆、稳杠杆与企业资本结构——基于实施效果与实现路径的检验》,《财经论丛》2021年第1期。但是,稳杠杆毕竟是用时间换空间,仅仅是货币当局主观上守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发生的底线,因为这个底线是通过现有的风险测试模型做出来的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如果只是采取稳杠杆策略使得债务上限始终游离于“底线”附近,而当出现某个偶然或突然事件时,这个底线的高低一旦发生变化,系统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还是会爆发出来,而且后果可能会更为猛烈。当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债务的不可持续性,而在新冠疫情之后,较大力度的经济刺激与纾困计划实施了整整一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时间和空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在当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只依靠“围堵”的方式,只能是把明知不可持续的风险进行“代际传递”,为后续的金融管理者增加工作难度之外,并不能解决任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问题。所以,我们建议:我国应该尽快建立起“金融类危机处置机制”,将系统性金融危机分阶段、分行业、甚至是进行个案处理的方式,利用“债转股”等市场化的金融工具对不可持续的债务问题进行“定向爆破”,以切实有效消除制约我国经济重回健康增长轨道的“根本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