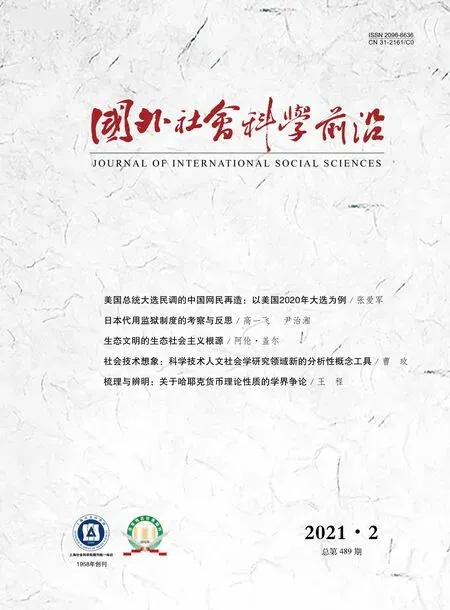社会技术想象: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的分析性概念工具
曹 玫
一、引 言
科学技术的全球化为科学政治学方向的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 STS)1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与国内常见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缩写相同,研究旨趣近似,本文翻译上参考了郭贵春、成素梅、马惠娣: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年第 1期的研究成果,建议译为“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背景下,科学技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论化,为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希拉·贾萨诺夫教授(Sheila Jasanoff)和汉阳大学金圣贤教授(Sang-Hyun Kim)在前人工作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概念,并通过对美韩两国核电发展与调控政策的对比分析,论证了“想象”概念的分析潜力:1Sheila Jasanoff and Sang-Hyun Kim, Containing the Atom: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Nuclear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Minerva 47(2), Jun. 2009, pp. 119-146.美国的核心社会技术想象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需要有效“遏制”潜在失控技术的负责任监管者,韩国的核心社会技术想象是“核能技术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国家不仅引介推广核能技术,而且将其纳入国家科学技术和政治实践中。接着比较了持有两种不同想象的两个国家对各种形式反核运动分别做出哪些截然不同的反应。2010年的4S年会(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上,组织委员会邀请贾萨诺夫教授在开幕式全体会议上就“社会技术想象力”发表演讲,再次证明了该概念的传播和感知意义。贾萨诺夫和金圣贤两位教授经过密切合作、开发,于2015年出版了Dreamscapes of Modernity: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现代化的梦境:社会技术想象与权力制造)一书2Sheila Jasanoff and Sang-Hyun Kim,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标志着“社会技术想象”作为分析性概念的成熟,书中开篇由贾萨诺夫撰文阐述“社会技术想象”内涵、定义,指出其作为重要概念能够用于描述科学技术进步的愿景如何伴随着公共利益、集体未来共同展开,后续全部为各国典型案例研究收录,包括奥地利核电、中国转基因水稻技术、韩国干细胞研究、印度尼西亚互联网发展、美国的生物伦理等,以此说明使用社会技术想象的作为概念分析工具如何能够引发我们对国家和跨国科技政治更为深刻的理解。迄今为止“社会技术想象”已经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STS研究平台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性工具,并在多个国家学术机构开拓了若干实践项目,被证明有助于加强既有STS领域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基础,已迅速被STS以及社会科学学术圈所接受,有望成为两个领域的学术核心。
本文综述社会技术想象的产生背景、提出、分析原理、研究方法及部分项目成果供国内学者参考,相信对社会技术想象这一分析性概念工具的进一步开发,将提供新的概念和经验资源,有助于改进科技政策分析和实施;评估新兴技术的风险和效益;制定标准和处理技术成果推广的不确定性;设计新的公众参与形式;开发技术伦理分析和审议的新过程;强调国际科技合作的机会和可能的模式以及促进中西方科学哲学研究者对话等。
二、社会学领域的“想象”与“社会想象”研究背景
在贾萨诺夫和金圣贤两位教授提出“社会技术想象”之前,许多哲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学者已经探索了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想象”,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明确地使用这个术语。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想象”并不被看作是“幻象”和“幻想”,而是重要的可以促成新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资源: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astoriadis Cornelius)认为想象力帮助产出有意义的集体系统,以实现解释性的社会现实;1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想象是帮助政治团体形成共同归属感的根基;2Benedict Anderson ,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想象提供一种我们如何构建并代表“他者”的凝视方式;3Edward W. Said, Imaginative Geography and Its Representations: Orientalizing the Oriental,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8.杰弗里·鲍克(Geoffrey C. Bowker)认为想象引导主体的简单化和标准化,以便更有效率地控制他们;4Geoffrey C. Bowker,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的“现代社会想象”,比人们在闲散状态下思考社会现实的智力活动要更深刻更广泛,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即人们通过想象了解彼此、了解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满足彼此的预期希望,以及包含支撑着这些期望的更深层的规范观念和形象。5Charles Taylor,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这种“现代社会想象”并不依靠专业的社会理论,因为理论是少数群体所拥有的,所以只能依靠故事、叙事等通俗文化,使得人们的实践和认同的合法性成为一种可能的共识。关于这种共识如何成为可能,泰勒又将“道德秩序”作为社会秩序运行的准则,准则是使得实践成为可能的直接认识的一部分,通过道德秩序的现代理论逐渐渗透和转变为社会想象,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开始转化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想象,这是对现代秩序延伸的认识,因为我们的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渗透和转变,也就不会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主导观点。
以上工作可以被解读为社会技术想象力学术研究的理论铺垫,为科学政治学方向的STS研究提供切入点,以帮助科学技术发展连接到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理论问题中。
三、“社会技术想象”的提出及其分析原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助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如何更好地刺激科技发展成为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科技部门日常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6Michael Gibbons, Camille Limoges, Helga Nowotny, and Simon Schwartzman,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London: Sage, 1994.而技术政策和科学政策占据的制度根基是不同的,但现实中对两者的政策支持又植根于相同的政治想象图景(国家层面)。在美国,这种历史渊源可以追踪到二战后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对战后美国政府科学政策规划制定国家介入模型(支持基础科学甚于应用技术)7Vannevar Bush,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https://www.nsf.gov/about/history/vbush1945. htm.、欧盟2000年达成的《里斯本条约》——计划将欧盟发展成最有竞争力、最具活力的知识驱动经济社会等诸多愿景。然而几乎所有植根于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在实施中都遇到了困境,比如获得国家政策支持的原子弹制造、航天计划、生物技术等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公众抵制或者出现其他未曾预料的矛盾,尤其是在全球贸易竞争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即便是某些理应进展顺利的信息技术也在跨国发展中遇到障碍。社会技术想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被引入STS领域用于关于科技政策的研究中,作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用于探究关于科技政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探索科技领域的规范性问题设计。1Sheila Jasanoff, Sang-Hyun Kim and Stefan Sperling,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https://stsprogram.org/admin/files/imaginaries/NSF-imaginaries-proposal.pdf.
如果说“社会想象”是整个社会成员关于社会运作秩序的一种设想,那么引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技术想象,就是通过科学技术连接了人们关于未来有序生活的一种美好期许。作为STS领域执牛耳的学者,贾萨诺夫如是定义了“社会技术想象”:2Sheila Jasanoff and Sang-Hyun Kim,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19.
我们将社会技术想象重新定义为:集体所有的、制度稳定的、公开表现的、理想的未来愿景,它由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理解所激发,且这些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秩序可通过并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实现。
贾萨诺夫的学术生涯另有一个重要概念:“共生”(co-production),即科学、技术、社会想象三者的关系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想象是同时产生的,进一步说,我们关于技术的想象和关于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形式、社会机构的想象是共生的。3Sheila Jasanoff,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共生”和“想象”紧密联系,想象被看作是“集体持有的、制度稳定的、理想可达的社会秩序”,并且这种想象可以从科学技术发展中得到可靠的支持,从而连接了“想象”与“科学技术”。这种连接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原因在“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中,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一些行动者和机构比其他行动者更有能力投射他们的想象,并让其他人自愿地、通过消费者和政府购买这些想象。这些行动者指以政府为想象场所的科学技术人员,这可为科学技术与政治权利的关系研究找到切入点,进而剖析这类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特殊行动者是如何构建出比其他行动者更为强大的社会技术想象力,并且借助这些想象力又如何加深了特殊行动者的既有权利。
从语词内容分析,“社会技术想象”这个词本身是混合的,跨越了社会科学(社会)、科技(技术)、人文(想象)三者,因此,它提供了一个适当扩展的解释性工作场所,在其中处理关于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和政治机构的联系,以及技术与负责任全球治理的社会嵌入性议题。随着一些实践项目的推进,这一概念预示着社会团体成员通过科技构建想象并参与未来的愿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文化理解,世界上其他行动者的想象力也在发挥着源源不断的作用,这恰巧与“共生”理念相一致;另一方面,公众对科技的希望和恐惧正以不可预测的方式与当前政策世界中的想象形式发生着联系;公众还根据自己对当权者的想象来构建行动,并根据他们对发现、创新、效率、进展、不确定性、证据、论点、价值、合法性的默许程度让决策者承担责任。因此社会技术想象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和框架,不能简单地用话语来定义,而是与国家权力的积极行使和对政治异议的管理有关,我们应看到它最初被引入是主要用于科技政策合理性的分析。
四、分析方法与可供分析的资料来源与已有研究项目
来源于不同行动者的“社会技术想象”因为跨越了科学技术发展、政治科学与社会的界限,故能够将想象范畴的主观和心理维度的元素与技术系统、技术政策和政治文化等硬质元素相结合,因此,最适合研究社会技术想象的方法是STS中的解释性研究方法。1Sheila Jasanoff, Sang-Hyun Kim and Stefan Sperling,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https://stsprogram.org/admin/files/imaginaries/NSF-imaginaries-proposal.pdf.而争论、冲突与矛盾就是很好的切入点,关于想象力的争论研究通常依赖研究者创造性地将各种来源的证据并列呈现,这里可以使用多种资料文本,例如与科学、技术和权力有关的文件,包括听证会记录、政策报告、法律简报、政治演讲、政府促进技术的行动倡议、针对公众对技术抗议的应对措施等,都为分析社会技术想象提供了一些最容易获得和最普遍的资源。
从性质上讲,官方文本倾向于精英们的想象;从事实上讲,视觉文本比语言文本更形象生动。视觉文本在非官方文本中尤为普遍,尤其是有了互联网这样的载体,很多行动者不制作官方文件,而是通过电影、视频、电视节目和广告等“灰色”文学传播想象,这些证据对于绘制当权者和公众关系的结构图、记录技术政策风险、想象科学技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尤为重要。这类材料包括了至关重要的非语言符号文化元素,对这类材料的分析方法也要依赖超越话语分析的一般技术。
已有研究项目始于问题的提出,即通过关注社会技术想象开始探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家和社会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通过集体想象被建构出来?科技的界限和目标是什么?促进科技进步的社会目标是什么?确定目标后,为实现这些目标,如何组织科技发展轨迹?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影响科技创新变革的相关参与者是谁?参与者拥有什么样角色和职责?关于这类问题的想象在社会的许多部门中都有迹可循,而不仅仅是在早先公认的科学技术活动中,甚至可能早于所谓公认的社会技术想象之前。预设社会技术想象的存在是这类项目开展的一个基本假设,即设想存在稳定的、集体实践的、模式化的方式,对这类想象的识别、阐明和批评,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技术政策的本质。以下简单介绍已有的研究项目:
(一)社会技术想象与科技政策的跨国比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
在哈佛大学的跨国跨学科科技政策比较研究项目中,将社会技术想象看作以创新科技项目的开发或实现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想象形式。通过从创新科技项目的开发入手,旨在研究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国家”和“全球主义”是如何被想象以及重新被想象的,而非简单地接受“国家”与“全球主义”这一既定事实。这项为期两年的跨国跨学科比较项目考察了美国、韩国和德国三国国家政治文化与科技政策制定中社会技术想象产生的异同。通过系统的跨国比较,该项目阐明三种不同的民主政治模式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中发挥作用的。该项目重点研究三项具体技术:核能、干细胞克隆以及纳米技术。研究者认为这一设计将提供对国家科技想象的历史与当代洞察。研究的第二阶段从几个方面分析了这些案例,包括处理国家需求、团结、暂时性竞争力、风险以及利益。研究采用定性的STS方法,综合了政策分析、法律、人类学和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1Sheila Jasanoff, Sang-Hyun Kim and Stefan Sperling,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https://stsprogram.org/admin/files/imaginaries/NSF-imaginaries-proposal.pdf.
研究的结论包括:美国的国家想象是政府强调技术在领导创新、促进竞争力和增长方面的作用,政策制定者推测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将为所有公民带来福利,即创新被视为财富分配和财富创造的驱动力,社会不平等本身需要通过科技政策加以纠正。韩国的首要国家目标是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赶上经济更发达的国家。除了国家安全以外,几乎所有的社会需求都服从于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先增长,后分配”政策就是一个例证。在这种想象中,韩国主要把科技视为发展的工具和资源,包括国家竞争力和现代化。因此,科技政策是由国家官僚、政治家和商界发展联盟共同推动的,并得到了精英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肯定与支持。公众历来被排除在科技政策制定之外,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公民,支持国家发展科技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民主转型之后,韩国的公民社会迅速发展,“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受到了多方批评,对核能等技术的风险和环境成本的争论也随之而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涌现并提出诉求,政府也开始承认,有必要对科技发展与政策制定进行公众审议。德国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提出了创新的必要性,认为最紧迫的风险是移民、老龄化和民族文化的丧失。德国经历了人才流失之殇,因此迫切希望减少接受了本国高等教育却离开本国的人才流失。德国对美国的实用主义、速度和灵活性很着迷,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寻求自上而下进行创新,并或多或少地平均分配了创新的收益,这些方面说明德国仍然像一个计划国家。
三国“社会技术想象”的比较研究成果加深了对全球科技政治的跨文化理解,从而为跨国合作和治理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二) “科技生活”(TechnoLife)
TechnoLife是欧盟FP7框架计划下的一个子项目2Kjetil Rommetveit, The Technolife project: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new ethical frameworks for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16,2013, P.23-45.,它采用了跨学科方法来研究新技术的伦理和社会影响。该项目由卑尔根大学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管理,邀请了丹麦、爱沙尼亚、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研究伙伴共同参与。TechnoLife联合会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开发需要获得综合的见解,以便建立“新的伦理框架”,而许多政策问题可以参考框架问题来解决,框架问题是研究基于既有的价值观、利益和程序的基础上人们如何分享以及界定社会、自然的共同想象,公民共同想象未来的方式以及人们对科技发展的关注和受鼓励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考虑如何介入想象和动态想象的社区,TechnoLife的目标是基于“社会技术想象”这一核心概念开发一种实验方法,该方法承认当地环境、体现、情感和人们的想象力是参与、施加影响和应用调节理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众”或“社区”,无论他们是谁,都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和能力,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使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更为贴合。
如何捕捉想象?该项目界定的重点是三个技术领域:生物识别技术、可视化地理应用和人体改造技术。针对这三个技术领域分别都开发了一个电影式短片,作为讨论的启发点。每部短片都包含了技术发展的基本信息,以及它们与伦理或政治问题的交集。这些短片以动作片和科幻片等为题材,有别于纪录片或宣传片,也不同于科学传播片,而是故意设计传递出模糊信息,其目的主要是让观众更多地处于情感层面,而不是“理智”或“理性”的层面(前提条件是观众已经对主题有了某种程度的关注和纠结)。
研究团队使用审议工具KerDST(http://kerdst.kerchantier.org/)的新版本(称为KerTECHNO)专门创立了一个“想象社区”作为虚拟论坛,确定了一些可能受到这些技术发展影响的公民,邀请他们进入讨论区,鼓励参与者分享经验,表达他们的态度和担忧,并讨论他们关注的问题。这些参与者被要求对电影中呈现的若干场景进行重构,并给出他们的意见或反应,以此作为随后研究讨论的起点。研究团队使用的工具中包括KerBabel审议矩阵(DM)和KerBabel IndicatorKiosk(KIK)(见http://kerdst.kerchantier.r.org/) 工具。KerBabel审议矩阵首先是一个排序和表示工具。在最初的形式中,它由三个维度或轴组成:场景轴、问题轴和涉众轴。其结果是三维结构,代表矩阵中的所有“节点”,在进行小组讨论之前列出了场景、问题和利益相关者,在实际的“审议”中,参与者根据一组场景对一组问题(同意/不同意/中立等)进行投票。每个参与者也可以发表评论来解释自己的投票。一旦投票结束,就可以开始一轮讨论,在这一轮讨论中,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查看自己和其他人对所讨论问题发表的“意见”,即通过颜色编码的图形表示法,说明他们的投票在三维矩阵中的位置。
研究结论认为现有的与公民交往的方法主要是在专家控制的认识论范围内,范围过于狭窄。专家认识论通常认为情感和社会想象对于控制和调节专家理性是多余的,而Technolife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新的见解,即通过构建虚拟社区并了解团体和个人如何看待新技术及其更广泛的伦理和社会影响。
(三) 技术政治文化:集合、排练和稳定性——维也纳大学
“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在国家背景下与社会秩序的具体想象共同发挥作用的。”1Ulrike Felt, Reordering the “World of Things”: The Sociotechnical Imaginary of RFID Tagging and New Geographies of Responsibili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Sept. 2018, https://doi.org/10.1007/s11948-018-0071-z.这项工作围绕具体的案例研究(主要在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材料科学领域),从三个不同角度探讨与社会技术想象相关的问题。第一个角度:公民对科技未来的看法,这一工作体系围绕“公民如何想象技术科学未来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自己在塑造未来中的作用”展开,调查了政府在引导公民认识中所援引的历史资源,以及公民对特定生物医学技术、纳米技术发展干预中的自我定位。第二个角度:逆向的社会技术想象,即技术抵抗的形式,是对应于国家社会技术想象的反想象方式,给出的具体例子分布在核能和转基因食品领域,这些技术在奥地利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逆向社会技术想象——“某些技术已经没有了技术社会化发展的空间”,研究的核心落在这种想象是如何沿着历史轨迹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角度:社会科学想象,视角聚焦在科学政策工具、制度发展以及科学家如何想象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上;调查了与科学有关的机构改革过程、类似中介机构(创业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内部的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中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
综上所述,研究者普遍认为他们对“社会技术想象”的研究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其获得的国家认同的想象是如何共同产生的。
五、争议与改进
社会技术想象在迅速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贾萨诺夫关于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不够清晰且过于宽泛,2Alexandra Keidiia, Imagining Internet in Contemporary Russia: An Attempt in Operationalization of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cience, 2019, pp.244-251.不能够给与分析过程完整指导:将社会技术想象定义为“稳定可达的集体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的想象”,这就假定了文本不能传递出想象的动力性与扩展性,而实际中的社会技术想象往往是持续变动的,如此定义未体现出社会技术想象的争议性本质。第二是对文本分析本身的诟病,对执行机构单一文本的分析未能展示制定文本的不同行动者的多种想象。第三是社会技术想象通常是面向未来的社会与技术相关联的秩序的愿景,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了决定论,要想在STS中发挥分析作用,这些愿景必须足够稳定,不仅要被充分解读,还必须关注形成这些愿景的地理文化背景,因为它们是想象和规划未来的“基础设施”。故许多学者在贾萨诺夫理论框架上拓展了社会技术想象的“运营性”分析,所改进的理论预设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把文本中持续稳定的社会技术想象看作是某一政府部门与整个政府共同达成的,二是将不同的社会技术想象定位于政府文本和该部门推行该政策的公众言论中,三是对所在区域的地理文化要素积淀做深入的剖析。
第一种类型的理论探索参考亚历山大·凯迪(Alexandra Keidiia)对俄罗斯联邦数字发展和通信部的工作研究,1Alexandra Keidiia, Imagining Internet in Contemporary Russia: An Attempt in Operationalization of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cience, 2019, pp.244-251.研究聚焦该部作为单个独立政府机构,其管理业务领域涉及通常的数字通信技术,尤为关注互联网技术。分析的文本采用了该部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文件:《俄罗斯联邦信息社会发展概念(2008年)》《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信息技术产业2014—2020年和2025年远景展望(2013年)》《电子政务概念发展规划(2013年)》。研究者认为这些战略政策文件反映了该部的主要工作领域:与公民和企业的互动、国家科技教育项目、提高公共行政效率等。与此同时,还听取了该部高级官员自2016年以来在论坛、会议和其他活动发表的公开讲话,因为研究者认为演讲是一种报告存在和从文件中获得想象力的形式,这些演讲就像是一个吸引盟友进入某个独立想象世界的工具,从而得出了结论:一个独立政府部门的想象只有在其他想象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存在,信息化社会的广义想象包括电子政府和作为工具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想象不是一个单独政府可以控制发展的。
第二种类型的拓展参考诺尔·朗格(Noel Longhurst)对英国国家、企业、科研人员和公民社会不同“制度环境”中产生的12种观点的研究。2Noel Longhurst, Mapping Diverse Visions of Energy Transitions: Co-producing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Sustainability Science (2019) 14, pp.973-990.鉴于许多国家都设立了能源系统如何快速脱碳的目标,但对这种“自上而下”、以技术为中心的转型愿景的批评日益增多,这些批评声称,转型是不可预测的。为此,朗格通过12种不同观点的研究,揭示了能源转型的不同观点能够通过集体实践产生共同愿景。通过引入社会技术想象(文中称其为一种新的基于合作关系的生产主义视角的科学技术研究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这四种视角在社会技术想象概念上四个维度的异同构成:意义、知识、行为和组织。与以往对能源转型的研究通常集中在政治文化、政权权力中心即国家主导想象上不同,研究者比较性地描绘了分散的、多样的和反霸权主义的愿景,揭示了通常被称为“技术性”的转变总是首先在社会和政治秩序上力图获得其规范性,然而这种“中心”转变和更分散的或更“另类”想象之间存在重要区别,这些差异揭示了能源政策有丰富的政治属性,从民间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愿景和想象被证明是社会技术想象中多样性的一个关键点,并倾向于为进步、社会变革和公众角色的替代敞开大门;强调了环境和集体实践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集体实践共同产生了能源技术发展的愿景。研究者最后建议,这诸多愿景揭示了他们各自偏袒与排他的社会政治维度,通过以这种社会技术想象的分析模式,可以提供一个更谦逊与负责任的政策制定依据,为未来的技术实践和社会技术变革实践打下基础。
第三种理论拓展见于艾力克斯(Alexis Saenz Montoya)基于“社会技术想象”与“共生”的概念去理解环境改造方案中社会和人文条件的复杂性问题,集中探讨了寻求河流恢复的社会环境研究中地理知识是如何协同生产的。3Alexis Saenz Montoya, Co-production Of Geographic Knowledge for The Socio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Urban rural Riparian Zones in Medellin, Colombia: Temple University, 2020.研究缘起于位于哥伦比亚洲的麦德林市河流周围的河岸带受到了非法城市化造成的加速生态退化的影响,多年来环境当局和基层社区团体一直在考虑什么是有利于河岸带再造林的理想方案,中心议题是如何在不驱逐低收入者的情况下进行生态恢复,经历不断地冲突、协商、达成共识,最终总结的经验是要恢复河岸带生态,就需要打破城乡梯度上的城乡二分法,因为政府行为体与社区行为体在生态保护与恢复区域的界定上有显著差异,研究者还建议在城市的边缘和坡地上建立一个有利于生态联系的生态保护区。由此可见,河岸走廊的生态恢复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必须考虑当地社区及其社区建立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生态系统。文章最后建议今后的类似项目要不断创造想象空间,共同生产有关河流及其河岸廊道生态恢复的知识,形成统一的社区干预措施。
杰西卡·史密斯(Jessica M. Smith)同样看到了社会技术想象过于偏重对未来的设想,为此在研究中将“社会技术想象”和人类学中的物质资源研究进行汇集比较,探讨了美国西部两个能源生产社区是如何理解能源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道德属性。1Jessica Smith and Abraham Tidwell, The everyday lives of energy transitions: Contested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in the American Wes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6, Vol. 46(3), pp.327-350.研究结论认为对能源社会技术想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跨国行动者在塑造“良好社会”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这些想象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传达信息和转化,由此阐明了社会技术想象的争议维度,以及它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定位,这些权力结构为道德行为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信念。尽管能源在国家社会技术想象中的作用几乎完全建立在它所能实现的消费力上,但对生活和工作在科罗拉多州富含铀的生产社区和怀俄明州富含煤炭的生产社区的人们的日常道德观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坚持一种“善”的能源生产信念,并且这种能源生产系统还为当地蓝领提供体面和高薪工作。研究者认为,国家层面的社会技术想象在地方范围内仍然是“有界的”,并不一定能够顺利地广泛传播并获得其既定影响力。这种有界性的社会技术想象,不仅揭示了社会技术想象的争议性本质,而且也说明了某地过去的物质组合和沉积物对想象未来的制约。
六、结 论
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STS)根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一直延续到冷战开始,至今形成了两条学术流,第一条起于早年历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家们对科学知识、技术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是托马斯·库恩1962年的经典研究——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有影响力的工作有助于形成科学历史和社会研究的新方法,其中科学事实被视为科学家社会条件调查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客观表征。第二条学术流则更多地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和控制,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可能给环境可持续性与人类生活带来的风险、利益和机会。在第二条学术流中,除了本文介绍的“社会技术想象”,还包括已经被国内学者熟悉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开放科学”与“技术预见”等概念工具,然而检索近年中文学术数据库发现国内关于“社会技术想象”的文献并不多见,而其在国外科学哲学领域已成为较为公认的成熟概念工具。通过阅读国外文献,笔者感觉“社会技术想象”相比其他概念带有更浓厚的人文主义意蕴,因为很少会有人去想象悲观的东西,想象本身即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个概念和国内“科学技术应服务于人民”以及“强调科学技术研究的应用导向价值”恰恰是理念一致的。为此,本文综述国外学术界关于这一概念的提出、发展、既有研究框架、方法与相关研究成果,展示“社会技术想象”概念的分析潜力,一是能够进一步促进中西方哲学对话,二是通过关注社会技术想象,我们可以开始探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通过集体想象被建构出来的?
那么,如何将这个概念引入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呢?笔者认为,我们要注意将已有的科学技术政策分析导入到“社会技术想象”这个想象空间中考察。首先看到作为一个处于复杂转型中的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我国主流的科技创新政策是自上而下的,并且基于统一的价值观和社会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指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四角相倚的创新体系”。在“中国梦”的国家想象下,设想共同通过提高生产力、促进全球合作和满足人民需求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近年来,高层领导已经充分意识到既要关注经济发展,同时也日益强调控制科学技术潜在风险,以确保其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以下问题来完成国家想象的分析: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如何实现既定的共同社会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科技发展轨道应如何组织?如何处理创新的优势和劣势?谁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相关参与者?每个团队或成员都有哪些角色和责任(例如国家、企业、科学界、工业界和公众)?而关于这类问题的想象很可能先于特定科学技术发展以前就已经形成了。
除了宏大叙事的国家想象,也存在着大量其他想象,可以说“社会技术想象”既是一种将社会成员聚集在一起的机制,也可以是一种抵抗的表现,就如同近年来涉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公众的重要问题常会举行的“听证会”。虽然“听证会”参与对象的目标指向有所不同,但在涉及与科学和技术的有关问题时,也确实有着冲突—协调—共识达成这一漫长的过程。如果把这个过程导入到想象空间中,就可以展示不同行动者的不同想象如何能够获得一种稳定长期的存在,为什么一些科学技术对于未来社会秩序的设想往往比其他设想更易赢得支持,换句话说,为什么有些秩序是以牺牲其他秩序为代价而共同产生的。
最后一点建议是,因为社会技术想象与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意-象”哲学有几分相通,所以可以将其作为文化基础而引入该研究。中国古人对“意-象”的看法是从《周易》的卦象开始的1朱志荣:《论〈周易〉的意象观》,《学术月刊》2019年第51卷。。《周易》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观物取象”。易象是“意-象”的重要源头,从中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其中对“象”的崇尚,乃是对宇宙及其生命奥秘的礼赞。《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观物取象”,是《周易》卦象的基础。《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是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象”在“言”和“意”起着中介作用。三国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认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故“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以卦象、言、意三者关系来说明忘掉言、象是得“意”的条件,只有忘掉了语言和物象,才能认识到思想和世界的本质“意”。王弼的“意”是和老子的“道”一样是虚无缥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远高于本文介绍的“社会技术想象”的层次,但“意-象”是接近于“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内涵的,因此古人意-象结构的看法是可以作为基础来引导我们如何将科学技术人文社会学研究中所分析的文本资源引入到“社会技术想象”这个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