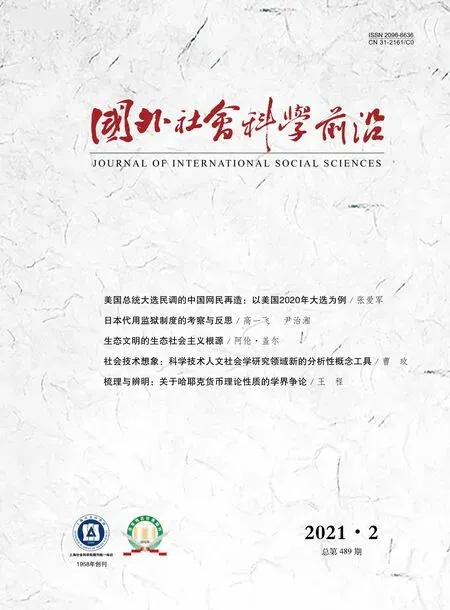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主义根源 *
阿伦·盖尔 /文 曲一歌 / 译
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生态文明”被纳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的目标写入党章,并将其纳入五年规划。201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呼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的追求相关联。在循环经济中,“一个系统设施所消耗的能源、水、材料和信息等,来源于另一个系统设施的输入”。1Geall, Sam and Adrian Ely, 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wards a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Quarterly, vol. 236, 2018, p. 1189.用于改善环境、减少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支出已大幅增加,但环保人士认为,这方面的支出还远远不够。鉴于生态文明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中心地位,生态文明的含义备受争议。
生态文明通常被认为是工业文明之后的产物。这可以解释为中国必须先实现全面工业化,才具备全面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它也可以解释为利用技术解决方案来处理工业化所产生的生态问题,这很像西方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需要挑战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带来的权力集中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认为,生态文明要求制度要使市场置于从属地位,并赋予地方政府以权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云飞教授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定义生态文明,他认为,生态学维度在不同程度上贯穿于所有文明之中,那些生态文明发展不充分的社会正在破坏它们的存在条件。张云飞教授认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相对薄弱,有必要恢复和推进遗失的早期生态智慧。2Zhang Yunfei, On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30, 2019, pp. 11-25.与此并不矛盾的是,清华大学卢风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战胜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和解决局部生态问题的目标。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生态破坏的主要驱动力,在避免这种破坏力陷于瘫痪的背后,这种更激进的观点往往(虽然并不总是)明确地与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主义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的观点,他是政府级生态文明的主要倡导者,他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在内的主要学者的大力支持。
对这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来说,资本逻辑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因此,正如潘岳所言:“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反对任何偏离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他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可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动力和制度保障。”3Wang Zhihe, Huila He and Meijun Fan, The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Debate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vol. 66, 2014, p. 10.据此,卢风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及其实践将否定和超越现代文明和城市文明,并与新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框架相联系,人们将通过这些制度框架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4Huan Qingzhi, Socialist Eco-civilis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Civilisation, vol. 27,2016, p. 55.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就等同于一种先进的生态社会主义形式。然而,如前所述,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要说明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并且生态文明蕴涵着生态社会主义,就必须理解生态文明概念发展的历史背景。
一、生态文明的俄罗斯之源:从组织形态学到生态文化
中国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sation)一词最早是由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提出的。19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1987年,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的报纸上。1Huan Qingzhi, Socialist Eco-civilisation and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m Nature Civilisation, vol. 27,2016, p. 52.“ 生态文明”最初的术语是“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后被翻译为“生态文明”。但在中国,“文化”和“文明”有时被视为同义词,“文明”一词在中国的使用方式如同“文化”一词在俄罗斯的使用。中国将文明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组成部分,每一种文明都是其他文明和更广泛文明的条件,正如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有不同的亚文化一样。“生态文化”的概念最初是由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被广泛使用。例如,1983年,尤里·伊万诺维奇·马宁(Yuri Ivanovitch Manin)在《生态学的社会方面》(Social Aspects of Ecology)中发表的《生态文化与共产主义》和V. S. 利比茨基(V. S. Lipitsky)在1983发表的《人格生态文化及其形成途径》。接着,一位主要的政府人物伊凡·T. 弗洛洛夫(Ivan T. Frolov)与T. V. 瓦西里瓦(T. V. Vasileva)和V. A. 洛斯(V. A. Los),在苏联的一份出版物《生态宣传》(Ecological Propaganda)中提出了“生态文化”的概念。同年,瓦西里瓦在一篇文章上就这个话题进行了辩护。2这些细节是由卡列维·库尔(Kalevi Kull)提供的,他是当时苏联一位活跃的理论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
伊凡·T. 弗洛洛夫(Ivan T. Frolov)是一位专门研究生物学的科学哲学家,也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bachev)的顾问。他后来成为苏联主要意识形态杂志《共产党人》(Kommunist)的编辑,之后又成为主要报纸《真理报》(Pravda)的编辑。1985年,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书记之前,弗洛洛夫在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和科学史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提出,面对全球生态危机,能够而且应该将人类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即战胜冷战。他详细阐述了这种生态导向的含义,他认为“把生物圈仅仅看作是资源的来源或废物的‘清除器’是错误的”。3D. R.Weiner, 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 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ëv,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399.弗洛洛夫认为,把美学和伦理价值重新整合到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和科学发展之中是同样重要的。他呼吁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物圈中心主义(biospherocentrism)。另外,弗洛洛夫反对社会生物学,该学说认为社会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复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使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合法化。弗洛洛夫援引马克思将人的特征描述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他提出人类本质上是文化存在者。4Ivan Frolov, Genes or Culture: 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Humankind, Biology and Philosophy, vol. 1, 1986, pp. 89-107.
生态文化的支持者赋予文化以重要地位实际上是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这是由布尔什维克前进派所倡导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教育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他被列宁任命负责环境保护。他拒绝将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the base-superstructure model)粗劣地解释为技术决定论。正是出于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进行机械化和教条化理解的考虑,马克思宣称,如果他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Friedrich Engels, Engels to C. Schmidt, London, Aug. 5, 1890,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7th Impression, vol. II.,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p. 486.此外,这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和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不同组成部分,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有必要创建一个新的文化,其中包括一个新形式的科学,以克服资本主义造成的认识上的缺陷和扭曲,由此反对资产阶级及其管理者的文化霸权。这在1918年得到了列宁的支持,但他想要一个更为实际的方向。2James D. White, Red Hamlet: The Life and Ideas of Alexander Bogdanov, Leiden: Brill, 2019, p. 392.
新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无产者文化运动(Proletkult),最初是受到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ksandr Bogdanov)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进行了描述,他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S.W. Ryazanskaya,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 19.在此基础上,波格丹诺夫指出,社会存在是有意识的存在,并将其纳入“文化”范畴。意识涉及文化的技术成分,也涉及协调人的文化意识形态成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说明经济学的范畴不是永恒的,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特定历史形式下的表达,马克思主要暗示了存在着能够替代这些范畴的新范畴。波格丹诺夫在《生活经验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ving Experience)和后来的《社会意识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中试图探寻新的范畴以作为对经济学范畴的替代。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经验,并且展示了如何通过自然的隐喻表达在社会生产组织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些隐喻理解、说明和再现这些现有的社会关系。
在提出这一论点时,波格丹诺夫并没有否定科学的成就。然而,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新进步将受到抑制,因为它们挑战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需要进行克服资本主义文化的斗争。无产者的文化运动试图克服过去所有文化的认知缺陷,同时将所有最好的文化纳入其中。正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所指出的,这种关于无产者文化的观点与1928—1931年苏联“文化革命”期间自上而下的观点非常不同,后者导致了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的产生。4Sheila Fitzpatrick, Cultural Revolution as Class War, in Sheila Fitzpatrick(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着重强调实践与改变世界。受其影响,波格丹诺夫认为,新的文化不仅需要推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还需要提供概念。通过这些概念,人们可以重新定义他们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实现自我组织从而创造未来。
这将是一个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别的未来。在这些概念的帮助下,人们将理解他们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工人们将能够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作。换句话说,人类将克服与他人、自然、人性以及自身创造力的异化关系,最终将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机械论的自然观。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表现为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工人阶级和自然一起倾向于被物化为为统治阶级赚取更大的利润(剩余价值)而进行斗争的控制工具。科学家或哲学科学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已经克服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并且能够自行组织起来推动科学的发展。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是理解世界的积极行动者,并努力克服他们科学理论中的二元论。以先进的科学发展成果尤其是热力学和相对论为基础,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赞赏。波格丹诺夫呼吁并着手发展组织的一般理论——组织形态学(Tektology),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由一个自组织的过程构成,它是在相互关联、斗争或统一中无限发展的一系列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组织综合体”。1James D. White, Red Hamlet: The Life and Ideas of Alexander Bogdanov, Leiden: Brill, 2019, p. 289.组织形态学关于世界的自组织过程的创造性阐发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方法,不仅让他们了解自己在自然、社会和历史中的地位,而且让他们能够组织和管理自己,而不是被管理者管理。2Arran. Gare, Aleksandr Bogdanov’s Histor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31, 2000, pp. 231-248.组织形态学启发了一般系统理论,是复杂性理论的先驱。
二、生态学、理论生物学和生态符号学
生物学在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初,在苏联广受青睐的生物学是反活力论和反唯心论的,本质上是实证主义和还原主义。然而,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开始发挥影响时,苏联生物学和心理学一起成为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主要中心——既不是活力论,也不是机械论,而是一种反还原主义的自然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卢那察尔斯基的大力支持,他同时还支持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茨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的工作以及他的生物圈(biosphere)和智慧圈(noosphere)概念。这些想法与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非常一致。3Arran. Gare, Soviet Environmentalism: The Path not Take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 4, 1993, pp. 69-88.甚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俄罗斯就已经是生态学和其他地球科学研究的主要中心,特别关注生物群落的共生关系。4Giulia. Rispoli, Between “Biosphere” and “Gaia”, Earth as a Living Organism in Soviet Geo-ecology, Cosmos and History, vol. 10, 2014, pp. 78-91.生态学的特点是对生物种群或生物群落的研究,而不是对生态系统的研究,其重点是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增强它们生存和进化的条件。这是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民主联邦制的基础,这种联邦制的基础是把互助作为生活的基本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生态学研究结合了热力学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具原创性、先进性的研究。
但是,这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斯大林的胜利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调查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1929年,卢那察尔斯基辞去教育委员职务,以抗议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虽然他们反对任何声称自然不可能被完全控制的主张,并且许多生态学家遭到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迫害,但这种激进的科学运动并没有完全被摧毁,而是在苏联持续了下来,正如道格拉斯·R. 韦纳(Douglas R. Weiner)在1999年出版的《自由的小角落》(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一书的标题中所描述的那样。
然而,这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是在苏联这个自由的小角落里发展起来的。苏联的工作引起了英国激进科学家尤其是生物学家的注意。1931年6月,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科学会议,发表了苏联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成果。俄罗斯对这次会议的贡献,由布哈林编辑并发表在《十字路口的科学》(Science at the Crossroads)杂志上。这对一些受到物理学和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启发的英国生物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进步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德国和俄罗斯生物学的发展,以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1Erik L. Peterson, The Life Organic: The Theoretical Biology Club and the Roots of Epigenetic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 55.这些社会主义者致力于发展生物学的新思想,主要关注胚胎学。其中最著名的是J. D. 贝尔纳(J. D. Bernal)、尼达姆·约瑟夫(Joseph Needham)以及C. H. 沃丁顿(C. H. Waddington),他们参加了1931年的会议,并于1932年成立了理论生物学俱乐部。由于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情怀,2Erik L. Peterson, The Life Organic: The Theoretical Biology Club and the Roots of Epigenetic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7, p. 119.因而他们未能获得剑桥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之后沃丁顿移居爱丁堡大学,并继续促进其“数学—物理—化学形态学”(mathematico-physico-chemical morphology)的发展。
他们的研究获得了支持,为活力主义者和分子生物学家的还原论纲领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分子生物学家用达尔文进化论综合了他们的思想以发展关于进化的综合理论,并最终发展了社会生物学。正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说,有机体是繁殖基因的生存机器。沃丁顿和他的支持者们建立了一个创新性的关系过程世界,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在地球上不仅创造了生命,而且创造了新的价值。虽然这整个研究计划在50年代被忽视和边缘化,但随着人们对生态破坏认识的发展和60年代激进主义的兴起,他们有可能获得支持并成功地推广这些想法。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沃丁顿在瑞士贝拉吉奥(Bellagio)组织了理论生物学方面的世界级会议,由沃丁顿编辑会议记录,最后出版了4卷本的《走向理论生物学》(Towards a Theoretical Biology)。由此,这引发了一场国际范围的理论生物学运动,为后来的后还原主义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参考点,包括辩证生物学、突变理论、复杂性理论和层次理论。3Arran Gare, Chreods, Homeorhesis, and Biofields: Finding the Right Path for Science through Daoism, Progress in Biophys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 vol. 131, 2017, pp. 61-91.沃丁顿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遗传认识论的坚定支持者,该认识论不仅挑战了行为主义心理学,而且对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这些理论生物学家最初关注的是单个生物体的形态,但他们也关注发展中的生态学。沃丁顿支持公开马克思主义辩证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理查德·列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列旺丁(Richard Lewontin)的工作。他还支持等级理论家霍华德·帕提(Howard Pattee)。帕提认为,生活、人类文化和人类制度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有利约束问题。这一观点后来成为与蒂莫西·艾伦(Timothy Allen)和斯坦利·萨特(Stanley Salthe)及其同事的理论生态学的核心。沃丁顿还发表了C.S.霍林(C. S. Holling)关于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恢复力的著作,霍林是为数不多获得诺贝尔生态学奖的生态学家之一。霍林参与了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并创办了《保护生态学》(Conservation Ecology)杂志,后来改名为《生态学与社会》(Ecology and Society)。此外,霍林激发了“恢复力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的灵感,这是一项旨在将生态思维纳入公共政策的运动,其理念是维持或创建有恢复力的生态系统。总的来说,这些理论家反对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简化形式及其通过竞争斗争和适者生存取得进步的理论教条,强调约束在进化中实现的共生和协同作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追求合法化,将经济人的利己主义置于从属地位,这作为一种进化的进程,为人们提供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条件,以促进人类生存条件的发展。沃丁顿本人也越来越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环境问题。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人造的未来》(The Man-Made Future)的开头是这样的:“无论未来如何,它都是人类创造的。世界范围内物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质上并且不可避免的是复杂的。它由一系列主要的世界性问题组成,包括人口、粮食供应、能源、自然资源、污染、城市状况等。这些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孤立地得到妥善解决。”1Conrad. H. Waddington, Man-made Fu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p. 9.沃丁顿认为,人类将通过了解这一点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创造未来,而不是让市场的力量来决定未来。
尽管这些激进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得以复兴,但早在1975年沃丁顿去世之前,这些思想就开始被边缘化。在接下来的30年里,它们被沃丁顿所描述的“COWDUNG”(占统治地位群体的传统智慧)排挤到了一边,这就是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德谟克利特—笛卡尔哲学”。在这种背景下,沃丁顿与苏联的理论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进行了交流。在1974—1975年期间,他与爱沙尼亚科学院动物和植物研究所生态系的卡列维·库尔(Kalevi Kull)进行了通信,并给他寄去了4卷本的《走向理论生物学》(Towards a Theoretical Biology)。1976年,理论生物学集团在塔尔图成立,恢复了爱沙尼亚生物学的反机械传统。这可以追溯到卡尔·恩斯特·冯·巴尔(Karl Ernst von Baer)和雅各布·冯·埃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以及最近在生态学和理论生物学方面的工作和有关理论生物学的国际会议,都得到了莫斯科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塔尔图和莫斯科的符号学者共同建立了“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学派”(Tartu-Moscow School of Semiotics)。该学派一直延续到现在。1964年出版的《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杂志于1991年以英文出版,成为研究文化与自然的符号学和符号过程的国际期刊。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符号学的工作相似,并受到索绪尔(Saussure)的影响,该杂志的撰稿人也受到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及其圈子的思想的影响,包括在20世纪20年代兴盛起来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帕维尔·N. 梅德韦杰夫(P. N. Medvedev)和瓦伦丁·尼古拉耶维奇·沃洛希诺夫(V. N. Vološinov)。近几年来,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而不是索绪尔。这些符号学家为法国符号学家及其会说英语的人提供了另一种工作选择。库尔加入了这一符号学派,并且后来成为《符号系统研究》杂志的编辑。他与丹麦的生物符号学家进行了密切接触,特别是激进环保主义者杰斯帕·霍夫迈尔(Jesper Hoffmeyer),后者提出了符号圈(semiosphere)的概念,符号圈领域起源于生活,并且是生物圈的中心。他们与来自捷克、奥地利和其他地方的生物符号学家一起,开展了国际生物符号运动,并每年举行一次集会。从2008年起,他们出版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杂志。库尔使塔尔图成为国际领先的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研究中心。
在关注生态符号学的同时,库尔和他的同事们正致力于重新定义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将人类文化解释为一种更复杂的符号形式。这促进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表述,将其直接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正如瑞典人类生态学家阿尔夫·霍恩伯格(Alf Hornborg)在1999年出版的《金钱与生态系统崩溃的符号学》(Money and the Semiotics of Ecosystem Dissolution)中所指出的,金钱是一种只有一个符号的代码,或者是一种只有一个音素的语言。它不可能提供适当处理复杂情况所需要的反馈,而且事实上,通过掩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正在驱使人类走向生态破坏。霍恩伯格在《生命的迹象:亚马逊流域人类生态的生态符号学透视》(Vital Signs: An Ecosemiotic Perspective on the Human Ecology of Amazonia)一文中阐述了这一点,并发表在《符号系统研究》杂志上。2001年,马克斯·奥尔施莱格(Max Oelschlaeger)在同一份期刊上发表了《生态符号学与可持续转型》(Ecosemio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一文。根据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奥尔施莱格接着论证了生态符号学论是如何促进国际文化变革的。正如他所说:“如果生态符号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娱乐,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大纲(暂定的或简略的)概述实用的生态符号学在某种程度上如何影响‘生态符号学’,即人类生态与生物物理生态的重叠,文化主体与自然主体的混乱界面。生物物理生态或自然与人类生态或文化的鸿沟威胁着生物物理灾难性进程和不可逆转的变化……主要的文化法则(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使这种分离永久存在,从而引导人类走向自然选择的命运。生态符号学理论应描述可促进适应性文化变革的过程。”1Max Oelschlaeger, Ecosemio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 29, 2001, p. 226.
生态符号学,根据其在人类生态中的位置(与“经济人类学”密切相关),将人类文化融入其对自然的理解之中,不仅为理解资本主义失败的原因提供了手段,也通过整合科学和人文重新思考已被接受的概念并实现社会转型,从而实现一种基于生态思维的文明。
三、李约瑟与中国的科学和文明
当沃丁顿从事他的理论生物学工作,并致力于环境问题和艺术创作之时,留在剑桥大学担任生物化学教授的李约瑟却转向了科学史。起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科学的胚胎学历史上,后来受俄罗斯人的启发,他知晓了西方科学曾经的成就和目前的失败。由此,他便开始了关于欧洲和中国的科学发展对比的重大研究项目。他后来的历史著作比苏联的科学史学家更详细地解释了17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唯物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系。通过利用新发展的成文法的隐喻性质,他展示了自然如何被视为运动中的物质,依据永恒不变的法则盲目而毫无意义地运动着,从而使资本主义的新兴社会秩序合法化。资本主义社会坚持和扩展这种自然观并将其纳入经济理论和其他人类科学。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延续了李约瑟在科学史研究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在1985年的《达尔文的隐喻》(Darwin’s Metaphor)中展示了达尔文主义是如何克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文化危机的。在这场危机中,经济发展与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帝国主义相联系,对殖民地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人们用以经济学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来比喻自然,然后利用它来捍卫经济学本身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
然而,李约瑟也发现了一个反传统思维方式,从莱布尼茨开始,贯穿于赫尔德(Herder)、谢林、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塞缪尔·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劳埃德·摩尔根(Lloyd Morgan)和怀特海以及理论生物学运动的著作中。这些思想家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关系过程或活动模式的领域,能够产生知觉、意识和精神,而不是运动中的物质。李约瑟认为,中国思想尤其是12世纪宋明理学大师朱熹对莱布尼茨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传统的思维方式。
李约瑟认为,莱布尼茨的独创性在于反对伽利略、牛顿科学传统,莱氏认为这一科学传统的根本原因在于朱熹对他的影响。根据朱熹的观点,自然是由能量(“气”)的形式(“理”)构成的,而能量(“气”)是通过阴阳对立但相互渗透且相互支持的原理或力量相互作用而发展的。关于朱熹,李约瑟写道:“在他的身后,有中国相关思维的全部背景;在他的前面,有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2,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291.虽然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但后还原主义科学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超越了还原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它吸收了所有文明的精华,现在正成为一门全球科学。李约瑟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以促进19世纪末开始的思想革命的全面发展,并将这种思想吸收到社会组织中去。从李约瑟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普遍受欢迎也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最初在中国被接受主要是为了借鉴西方社会关于工业化的观念,以克服建国初期的贫困和实现民族解放。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保留了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和民本传统,以及道家所倡导的对自然价值的尊重,儒家价值观避免了将人当作商品化的工具。此外,宋明理学家张载、周敦颐、程氏兄弟和朱熹将道家宇宙观融入儒家学说,主宰中国哲学长达700年之久,他们反对接受还原论的科学唯物主义。李约瑟对中国的研究同沃丁顿在理论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相结合,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在欣赏自己的学术传统(李约瑟的研究促进了这一传统)的同时,能够接受并推进生态学和生态思维方式。现在,李约瑟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1Arran Gare, Daoic Philosophy and Process Metaphysics: Overcoming the Nihilism of Western Civilisation, in Guo Yi,Sasa Josifovic and Asuman Lätzer-Lasar (ed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and Ethics in Chinese and European Philosophy, 2014, pp. 111-136.
四、作为生态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态文明
中国的生态文明倡议和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生态文化的探索,只是激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在更广泛的全球运动中的一部分。这些激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经常与敌对的知识环境作斗争,以促进其思维方式的发展,即创造使社会主义合法化所需的意识。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承认自己是具有创造性的参与者。
虽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维尔纳茨基、沃丁顿、李约瑟和库尔等都未曾提出全球生态文明的概念,但他们的工作为引出中国及其在理解中国的突出地位提供了理论背景。但是,却没有在其确切内涵上达成共识。弗洛洛夫和其他要求生态文化的俄罗斯人发扬了波格丹诺夫的文化观念,认为文化是人们在其基础上生产和组织自己的意识形式。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要求发展一种新的文化,既要克服以往文化的缺陷,又要吸收其中的精华。后还原主义科学对这一发展至关重要。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维尔纳茨基、沃丁顿、李约瑟和弗洛洛夫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主流科学的挑战,是创造真正社会主义的核心。换言之,他们所设想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包括对自然的新认识。李约瑟的著作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拥护社会主义,并提供了一个使生态文明概念不仅能够被提出,而且能够被政府接受的文化环境。生态文明的基础是这种激进的社会主义传统。因此,它涉及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作为一种自然生命形式的合法性的根本挑战。相反,它使得为挑战资本主义而建立的运动、机构和政府的轨迹合法化并保持下去,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生命形式以创建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这场斗争的每一个人都赞赏他们这一探索的历史、工作目标和成就,或者说,这一探索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并不意味着他们为创建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如果不了解这一历史背景,不了解激进科学传统的连贯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人们很容易接受生态文化或生态文明的概念,却无法理解它们的影响以及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挑战有多激进。如前所述,它们可以被解释为只不过是主流资本主义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被视为与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边际副作用,需要通过技术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一场重大的文明危机。然而,这场危机要求人们彻底改变理解自己的方式和他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如何组织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因此,生态文明的斗争是与文化遗忘症的斗争,即失去了过去在认识和保持连贯性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这种激进思想传统的激进含义。
即使有了这段历史,大多数人也可能忽略这些思想的全部含义(至少一开始是这样)。资本主义越占主导地位,商品形态就越强,人们就越难理解它的历史相对性,也就越难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关系,或者关于世界的不同理解。任何打破旧思维方式的做法都会被边缘化、被遗忘或者被误解,然后被重新表述以适应主流文化。那些参与发展可能挑战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经常被压制,或者他们的努力因缺乏资金而受到削弱。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人们对主流思想的挑战逐渐被削弱,他们将大学转变为跨国商业公司,并将其融入经济,将教育、研究和知识商品化,从而只支持为公司带来利润的教育和研究。
甚至还有一种对语言的歪曲,使得人们很难表达激进的思想,也很难理解这些思想及其意义。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概念最初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描述和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坚持更高的价值观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术语是从资本主义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的。因此,尽管马克思作出了努力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人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描述的,经济学范畴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形式,它们是一种特定文化和文明的内核,是可以被取代的。任何真正的文明人都不能容忍把人和自然的其他部分仅仅当作是满足他们欲望的手段,把知识仅仅当作是控制的工具。把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从它们的琐碎化中解放出来,使我们能够将科学视为文化和文明的一项重大成就和组成部分,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并将它视为对现实的连贯和全面的理解,既与其他文化相互促进也相互制约。
由于资本主义是依靠科学的,所以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挑战可能是最有效的。科学的进步表明,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并使之合法化的世界观正在失效。气候科学和生态学正带头挑战主流的假设。这一挑战有可能将科学从目前的分裂中拯救出来。罗伯特·尤亚诺维奇(Robert UIanowicz)认为,生态学应该成为定义科学的参考点,以克服目前阻碍理解进化现象、发展生物学和其他生命科学甚至物理学方面取得进展的观念。1Robert E. Ulanowicz, Ecology: The Ascend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这样的科学既有可能揭示控制自然的极限,也有可能揭示如何控制自然,同时也有助于理解自然的内在意义。通过发展一些概念,为如何诊断现代文明的疾病以及如何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创建健康的社会提供指导方针,以人类生态学取代经济学,成为制定公共政策的核心框架。
一旦有了崭新的思维方式的种子,尤其是当它们被包含在定义社区的叙述中时,它们便可以孕育完全改变社会和文明的创新型系统。把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官方的说法,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像是公关活动。然而,有了这一点,就以生态社会主义的形式复兴了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正如萨姆·吉尔(Sam Geall)和阿德里安·伊利(Adrian Ely)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叙述和途径》(Narratives and Pathways to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所说,这种叙述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影响到中国和国际社会走向可持续性社会秩序的途径,这一观点得到了毛里西奥·马里内利(Mauritzio Marinelli)的支持。1Mauritzio Marinelli, How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Intellectual Debate on Ecological Civilisation, Journal of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2018, p. 375.正在出现的一种新的、重新焕发活力的社会主义作为生态文明的宏大叙事,它可以挑战和取代还原论,后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在20世纪70年代推动了资本主义新的重大进步。
五、结 论
本文考察了生态文明的历史背景,解释了它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多样性。为了避免被边缘化,中国不得不接受和吸收大量来自欧洲的文化,这是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来实现的。这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同时也使中国人与欧洲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距离。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直被混淆和误解,在某些情况下,这导致了几乎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文化(尽管它存在问题)。在这些情况下,生态文明可以被理解为与西方社会特有的环境保护形式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中国仍然存在着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间接地影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这使中国人能够在不完全了解生态社会主义概念的根源的情况下,欣赏苏联生态文化概念与社会主义产生的共鸣。那种认为生态文明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思想,是恢复和捍卫过去文化(包括中国文化)优越性的一种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文化因商品化、标准化、同质化和贬低现实而受到压制。捍卫过去的文化与捍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呼吁全球生态文明并不矛盾,这是现在作为全球文化力量出现的宏大叙事。2Arran Gar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y Civilisation: 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London: Routledge,2017.即使不涉及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在引导人们行动的过程中得以展现,也将不可避免地揭示出其生态社会主义根源。
一旦了解了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就应该清楚地看到,没有必要再去谈论“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因为在现代世界,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事实上,生态文明不仅聚焦于资本主义的最终失败和资本主义必然被取代的根本原因,它还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应该努力创造什么。它可以提供一种替代霸权文化的选择,这种文化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而且可以克服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立。文明通常被定义为反对野蛮和堕落,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我们正面临着高科技野蛮和消费主义堕落的结合。对于古罗马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来说,文明人是那些能够自我管理的人,他们已经被培养或教育去这样做,具有理解、珍视和捍卫他们的自由的美德。更广泛地说,他们是那些能够理解生命价值的人。在古代的“文明”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口可以被文明化,依靠奴隶、农奴或农民来做养活他们所需的繁重工作。马克思意识到,尽管资本主义有种种缺点,但它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这些压迫性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来完成,所有人都可以文明化,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以拓展他们的社会和自然共同体生活。晚期资本主义通过使人们失去文明而使他们变得无能为力,把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的生活描绘成自由的,但他们的消费被无产阶级化,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马克思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灾难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造成裂痕,而且还造成森林的破坏和气候的改变。1Kohei Saito, Capital,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Delhi: Dev Publishers, 2018.生态学着眼于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体的“小家”或“大家”系统,为研究这些生物体之间或好或坏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从而拓展了这些家庭。生态学,包括人类生态学,提供了重塑经济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伦理、政治所需的思维形式。马克思写道,在未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将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生态文明的胜利将涉及创建一种秩序,将这一理念从个人推广到社区,再推广到共同体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共同体”(communities of communities)将包括整个人类以及所有生物群落,其中也包括当前的全球生态系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