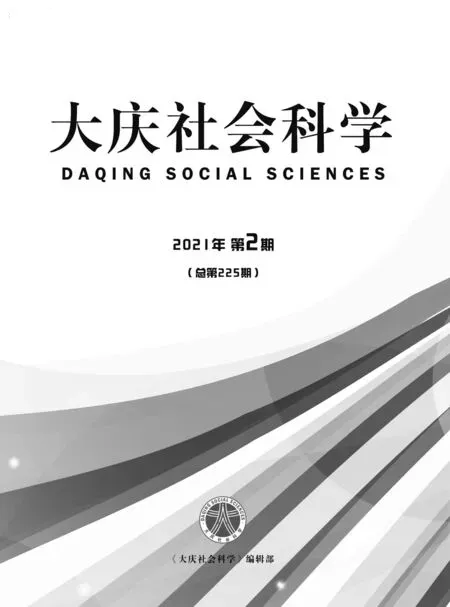庄子的和平思想探析
赵文丹,孙旭鹏
(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庄子哲学产生于战争频繁的战国中后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异常惨烈,普通民众生活在无助与绝望之中。庄子期盼能实现一种“至德之世”的和平局面,并且对战争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平思想是庄子哲学的重要内容,深入阐发庄子的和平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索人类和平的实现路径。
一、和平的平等根基
庄子生活在战争频繁的战国中后期,残酷的社会现实对庄子的和平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庄子不仅对战争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且深入剖析了战争发生的根源,他认为,一旦打破了人我平等的局面,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想要避免战争,实现社会和平,就须建立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
庄子对战争持坚决反对的立场。他认为战争根源于人类的不平等关系,一旦打破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战争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并进而威胁着个体的生命安全。庄子借寓言映射出当时战争所造成的惨状:“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一句“伏尸数万”可以反映出战争对个体生命所造成的威胁,“一场战争下来,动辄有几万人十几万人被斩首”[1]。在庄子看来,战争剥夺的是个体的生命权利,这是对生命平等的一种戕害,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他人的生命,怎么能够算是一种平等?一旦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平等关系,战争就随时可能发生。庄子借助颜回之口描绘出战争状态下民众生活的悲惨:“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庄子·人间世》)一句“轻用民死”,显示出庄子对战争充满着批判之情,认为战争是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伤害,是一种违反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战争不仅造成生命的伤害,而且也使个体的精神陷入痛苦的境地。正是在战乱频繁的社会背景之下,为了逃避战争对生命的伤害,产生了大量的隐者。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隐者依然面临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庄子借助楚国隐士接舆之口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庄子·人间世》)隐者尚且如此,陷入世事漩涡之人的精神痛苦尤甚。庄子描绘了将要出使齐国的使者叶公子高的精神状态:“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庄子·人间世》)由此可见,各国之间由于战争引发的紧张关系对普通人所造成的精神焦灼,正如王博所言:“也许,如果你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话,内热的情形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谁又会轻易地把生命弃之不顾呢?”[2]个体最重要的权利便是对生命的拥有,而战争正是剥夺个体生命权利的最大威胁。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保全生命所引发的精神痛苦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那些消极避世的隐者也依然不能逃脱这种精神痛苦。
庄子认为,人类想要走出战争的阴影,必须回归到一种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关系是建立在包容个体差异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禁要问,战争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局面,想要回归到一种平等关系又如何可能?庄子给出的解答是“不失其性”,即个体要做到顺应自然之性。“庄子就明确地反对‘机械’所引发的‘机心’”[3],庄子讲到:“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庄子·骈拇》)“不失其性”其实就是个体回归到一种本原状态,庄子认为这才是所谓的“正”,“至正之道,在于保全其自然的本性”[4]。徐复观评价庄子之“性”:“性即是道。道是无,是无为,是无分别相的一;所以性也是无,也是无为,也是无分别相的一。”[5]341所谓的“无为”即为一种自适其适的本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体获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庄子·骈拇》)“自闻”“自见”都肯定了个体的独立地位,并且这种独立的地位就是守住自身而不假外求。
总之,庄子深入思考了平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不平等关系。庄子认为,想要消除战争恢复和平,个体就必须回归到“不失其性”的本原状态,重新建立起一种承认并包容彼此差异的平等关系,建立人类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实现和平的前提。
二、和平的空想色彩
庄子认为,人类的平等关系对于实现和平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探究这种平等关系究竟具有怎样的实质内涵。通过考查我们不难发现,庄子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平等来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庄子看来,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隐藏着相互干涉而引发战争的危险。一旦消解了社会关系,就彻底切断了相互干涉的纽带,就会实现一劳永逸的和平局面,这种和平局面在庄子那里呈现出一种“至德之世”的空想色彩。
庄子试图在道德层面解除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认为这种道德上的社会关系本质即为一种权力关系。罗素认为:“传统的权力有习惯势力在它的一边;它无须时时刻刻为自身辩护,也无须不断证明任何反对势力都没有力量把它推翻。”[6]很显然,道德即为这样一种“传统的权力”,会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我们知道,在庄子同时代的儒家思想中,“仁义”作为一种道德学说大行其道,庄子认为儒家以“仁义”为本的道德学说,造成了人类之间相互依赖,这种社会关系不仅扭曲了人的本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异化后果,而扭曲与异化的必然结果就危及人类之间的和平共处。庄子认为,在自然的状态中人类之间是一种朴素无争的关系,天然地倾向于和平,这是一种顺应本性的状态。庄子断言正是“仁义”使得人们远离了自己的本性:“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在庄子看来,人们之所以“失其常然”,这是“仁义”出现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以“仁义”为本的道德学说破坏了原本倾向于和平的自然本性。正如杨国荣认为:“与儒家要求化天性为德性不同,庄子更多地趋向于从德性回归天性。”[7]201所谓“天性”亦即人类的自然本性。
进而,庄子深入揭发了人类以“仁义”之名来进行战争的实质。庄子认为,正是喜好“仁义”的名声,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庄子·人间世》)郭象对此注曰:“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复乃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8]146郭象在这里将暴君的“求恣其欲”与“求名”并列起来,实质的情况是,正是为了求取所谓的名声,才会引发进行战争的无限欲望,而“求名”无非就是求得所谓的“仁义”之名。庄子认为,想要从根本上解除战争所造成的威胁,就必须做到“应天地之情”:“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谯之间,无徒骥于锱坛之宫,无藏逆于得,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胜之恶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庄子·达生》)所谓“应天地之情”实质就是摒除了“仁义”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化解欲望的膨胀,解除人类在各种层面的社会关系,获得一种天然的和平状态。
庄子对社会关系的消解,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同时也是政治层面的,对“仁义”这种“传统的权力”的化解,最终是为了实现一种政治上的和平主义。其中,庄子理想中的“明王”在实现和平中具有核心地位。庄子那里的“明王”与儒家所称颂的“圣人”迥异:儒家的“圣人”是恪守“仁义”的;而庄子的“明王”却是抛却“仁义”,视万物为平等的。并且,庄子的“明王”其实就是指现实中的“帝王”,不过这种“帝王”却是不对万物加以支配的:“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庄子·应帝王》)庄子批判儒家以“仁义”为本的道德学说,来消解社会关系,使人性回归到一种天然和平状态;通过阐发其“明王”思想,尽力消解“帝王”对普通民众的压迫,实现一种政治层面的和平主义。然而,庄子所期许的这种和平状态由于无法付诸实践,充满着浓郁的空想色彩。事实证明,在现实世界中,和平与战争之间远非如庄子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庄子对于和平的实现太过理想化了。我们知道战争一般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是对和平的破坏,而正义战争则是对和平的保卫和塑造。用革命的暴力打破反革命的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某些特定的极端情况下,和平的最终实现往往需要正义的革命的战争来加以保证。庄子对战争采取了一概否认的态度并不可取,关键在于其并没有厘清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庄子渴望和平的态度是可取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导致其对战争与和平关系的理解存在偏差,从而使得其和平思想凸现着一种空想性。
三、和平的实现路径
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庄子实现和平的路径,那就是通过消解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乃至政治层面的社会关系,使每一个人都做到“不失其性”,从而实现一种包容彼此差异的平等状态。社会基于此种平等必然处于一种天然朴素的和平状态,庄子用“至德之世”来描绘这种社会理想。然而,一系列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每个人都做到“不失其性”是可能的吗?社会关系真的可以如庄子期望的那样被无限地加以消解吗?基于天然平等的“至德之世”真的是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吗?遗憾的是,基于对庄子思想的考查,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出圆满的解答。其实,庄子和平思想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关系,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可以被无限消解,最终回归到一种单纯朴素的人类社会,这明显带有鲜明的乌托邦色彩,最终难以付诸实践。
首先,庄子和平理念的实现是以人性为根基的。庄子认为,个体只要保持“不失其性”的状态,就可以实现一种包容彼此差异的平等关系。然而,按照庄子“不失其性”的指导,最终形成的结局是个体之间完全孤立与隔绝的状态。我们也可以在庄子的描绘中找到这种几近孤立与隔绝的状态:“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庄子·齐物论》)郭象注曰:“同天人,均彼我,故外无与为欢,而荅焉解体,若失其匹配。”[8]48其中,“若失其匹配”显示出个体与万物之间一种孤立与隔绝的状态,按照生活的经验与常识,个体与万物的完全隔绝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世界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的状态,个体的全然孤立只是庄子一种精神层面的理想。由此,“不失其性”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其根本无法在现实社会中造就孤立的个体,紧接着那种天然的平等关系也就无法实现,人与人之间注定无法摆脱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如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哈罗德·D.拉斯韦尔所认为的那样,“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情景”[9],既然人类之间无法做到完全孤立,产生社会关系就是一种必然,庄子的和平路径只有在完全忽略人的社会性的层面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人类注定进入到一种相互影响的社会状态,根本无法做到“不失其性”的孤立状态,也不可能消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人类天然平等基础上的和平明显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印记和乌托邦色彩。
庄子这种和平主义的乌托邦最鲜明地体现在其“至德之世”的理念中。在“至德之世”中万物和谐相处,没有任何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庄子从总体上勾画了“至德之世”的蓝图:“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和平状态,人类以及万物处于一种完全自由发展但又互不干涉之状态,“人们无知、无欲、无争,生活在绝对自由、安全、幸福的状态之中”[10]。然而,我们也会清醒地认识到,庄子的“至德之世”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不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社会关系也不可能被无限地加以消解,那种互不干涉的平等状态也如同镜花水月虚无一般。“至德之世”作为庄子和平理念的集中表达,尽管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极其诱人的社会画卷,然而其实现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其次,我们需要沿着庄子“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继续探讨和平的可能路径,庄子“至德之世”的美好理想固然是一种乌托邦,然而其对我们如何找到实现和平的路径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这便是庄子和平思想的现实意义。正如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认为的那样,“乌托邦理想推动着与日俱增的进步”[11]。导致庄子和平理想很难实现的原因在于,其完全将社会关系视为一种负面因素试图加以消除。无数的现实证明,人类和平的实现往往不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消解,而是通过对人与人关系的制约与平衡,特别是通过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才能赢得真正的和平。
总之,人类社会和平实现的路径,不能寄希望于消除社会关系,而应关注于如何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罗素认为:“假如你爱你的邻人,你就会希望得到权力来使他快乐。因此,如果对权力的爱好一概加以谴责,那就是谴责对邻人的友爱。”[5]213-214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联系,我们在当下想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幻想消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现实的,而只能依靠法律制度的建设来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制约与平衡。而在面对剥削压迫阶级以反革命暴力维护其强加给被剥削压迫阶级身上的不平等时,则必须采取革命的暴力来战胜反革命的暴力,最终赢得世界的真正和平。
——润心至德 立德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