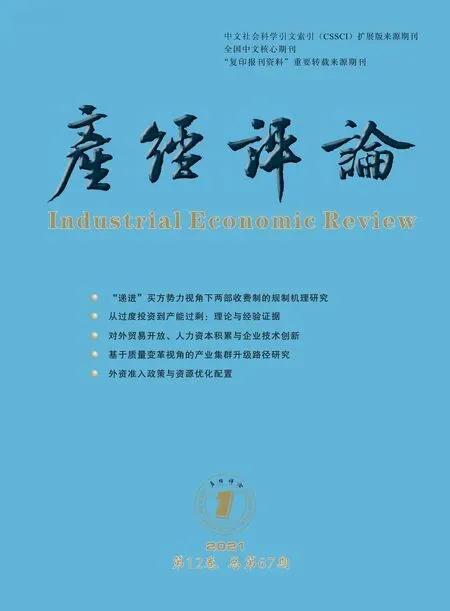网络时代的新组织形成与“四维”形式研究
孟 韬 赵非非 董 政
一 引 言
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在2018年12月《哈佛商业评论》的封面文章《科层制之终结》中指出,虽然按部门划分职能、职权明晰、标准化任务分配的科层制在大型组织中起到一定作用,但狭隘的科层制绝非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层之外还有新的可能性(Hamel和Zanini,2018)[1]。新世纪以来,以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网络信息技术呈现出井喷式发展势头。传统科层组织的弊端在数字化浪潮中愈发彰显,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布罗代尔钟罩”(1)布罗代尔钟罩(The Braudel Bell Jar)由秘鲁经济学家Hemando de Soto提出,意为影响或阻隔市场经济的各种社会安排。。无论是新生代互联网公司抑或传统企业都在寻求契合时代变迁的组织结构和形式。现实中,以阿里为代表的商业生态系统、以Linux等开源软件为代表的大众生产模式(2)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由哈佛大学教授Yochai Benkler提出,意为分散在各地的众多参与者利用互联网共同协作式提供、分享产品,尤其是知识产品的生产模式。、以海尔为代表的企业内创客平台、以网络论坛和社交软件为代表的虚拟社区等新的组织形式或组织现象层出不穷。
目前,国内外学者基于组织生态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协同演化理论等对上述鲜活的新组织现象或组织形式进行了相应解构。如果说组织研究就像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Davis, 2010)[2],那么“博物馆的新房间”(Lounsbury和Beckman, 2015)[3]也需要学者跟随时代节奏,做出理论创新。
本文从新组织形成的动因、遵循的基本导向、具体的新组织形式及其价值创造过程等问题的剖析中发现,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变革、认知转变和企业应变使得组织结构和形式发生改变,组织间或组织内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是新组织形成的根本动因。新组织因而可以摆脱科层制的“铁笼”选择并依托多样化的组织结构和形式解决网络时代下出现的种种新生问题。知识创造、协作创新和角色重构是新组织形成遵循的三个基本导向。新组织形式的“相对新颖性”表现在新结构、新主体、新形态和新要素四个方面。具体说来,组织间和组织内的新结构呈现出外部开放式协作、内部解构赋能的动态演化特征;“产消者”和企业内创客成为了组织的新主体;平台组织和社群组织是典型的新组织形态;知识要素取代或超越有形资产和信息资源成为组织的新要素。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本质上是由技术变革引发组织形式变化,进而导致组织能力提高形成的。此外,网络时代下,适时调整科层制这一组织设计的“默认选项”,对于深化理解新组织形式尤为重要。
二 新组织形成的驱动因素
新组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网络信息技术催生的新的组织现象和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大型企业组织演化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新形式和各种类型的网络组织(Ancona et al., 2015[4]; Miles和Snow, 1992[5])。在企业组织从L型(简单直线型)→U型(直线职能型)→M型(事业部型)→N型(网络型)组织演化及范式切换过程中,企业组织形式不断发生变化。换言之,新组织本质上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演进发生的组织结构与模式的演变与进化。
建立在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基础上,金字塔式权力分布的科层组织诞生伊始即被冠之以正式组织的名号。企业因科层命令替代自愿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Coase, 1937)[6]。也正是由于科层制在大规模生产协作和控制方面功勋卓著,科层架构已成为组织设计理所应当的“默认选项”。19世纪的美国通用公司的组织层级划分近20层,20世纪60年代尽管通用公司采用事业部制,管理层级仍有7层之多,直至如今,通用公司仍是经典的科层架构。但人们对科层制的“原罪”指责与诟病由来已久,如僵化臃滞、专业无能、权威徒有其表进而导致组织目标扭曲、异化人性(布劳和梅耶, 2001)[7]。此外,科层结构基于效率的操作性设计往往反过来产生仪式化或刚性行为,同时也无法克服目标置换问题(Merton, 1940)[8],它无法根据自身失误进行自我纠偏,其平衡建立在相对稳态的恶性循环基础上,演进则处于集权化、非人格化环境中(克罗齐埃, 2002)[9]。
与经典科层制相对的新组织往往被看作“后科层制”,核心特征在于减少科层中的等级制度与强制性要素,并向不那么严格抑或是不那么理性化的组织形式演进。关于新组织的形成,目前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主义、组织生态、企业战略、社会网络等多个理论视角。早期新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制度塑造着组织形式,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是对制度压力的不同应对策略的反应。最近,他们指出制度创业者对组织要素的创新组合之于新组织的形成意义深远(Greenwood和Suddaby, 2006)[10]。组织生态学者通过自然选择、物种进化来隐喻新组织形式的创生、繁衍与消亡。基于经典的密度依赖理论,把组织形式的出现归因于种群范畴合法性的正密度效应。后来他们引入“模糊密度”构念,意在揭示高密度对合法性的影响会由于受众对组织身份理解的不充分而减弱(Bogaert et al., 2016)[11]。企业战略学者将新组织的形成看作是组织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进行的战略调整,战略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决定着组织形式的具体形态(Lewin和Volberda, 1999)[12]。社会网络学者认为新组织的形成是社会生活中多个网络叠加导致的组织要素转移过程(Padgett和Powell, 2012)[13]。佘雪琼和王利平(2018)[14]基于“拼合”视角,将新组织形成的实质看作一个拼合的动态过程,组织要素的组合及合法性的获取分别是其产生及确立阶段的关键,制度逻辑则贯穿这一过程始终。
网络时代下的新组织突破了科层制企业边界内部简单分工协作机制。比如,模块化组织围绕新兴技术、产品研发以及附加服务性活动等关键价值链环节,将其他非关键环节通过外包、外购等方式逐层外推,采用跨组织边界作业方式,进而形成多维度复杂分工协作网络。得益于新技术发展和价值链重构,这类组织形式促使分工协作由不断细化走向融合深化,企业间交互更加频繁,关系更为紧密,生产效率与创新实现非线性突破。另外,由于组织间形成新的跨组织分工协作网络,彻底改变了价值创造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产业链条脱节等弊端,进一步延伸了企业价值链,使企业更容易发挥自身价值链优势并嵌入到全球价值链。
此外,网络技术的联通性、去中心化、去中介化以及去边界化特征对新组织形成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一方面,网络新技术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将组织结构逐渐拉平,组织层级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联通性、去边界化通过开放式资源整合不仅使企业价值链各环节联系日益紧密、组织内协同效率得到提升,还促使资源流动跨越组织边界,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不断创造用户价值。基于产业价值链拓展和多主体关系形成的商业生态系统中,系统成员以“共生、共荣”生态价值理念驱动价值创造过程,彻底颠覆了过去以单一经济效益指标衡量企业价值、组织能力的评判标准,进而实现组织形式的持续演化发展。传统因地理位置相近形成的产业集群也逐渐打破物理边界束缚,出现了信息空间中的“虚拟聚集”新组织形态。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认为新组织形成的根本动因在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变革、认知转变和企业应变扩展了组织间和组织内的合作秩序。互联网的去中介化特征在实现供需双方即时对接的同时降低了各个环节的交易费用,去中心性又将人人变成中心节点,人人都具有话语权。由于互联网去中介化和去中心性并存,真实世界被逐渐拉平,丰富了个体或组织的合作方式,组织因而可以选择并依托多样化的结构和形式解决网络时代下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新生问题。
首先,网络时代下的技术变革与创新主导了新组织的形成。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新技术的融合发展催生出新行业和新组织(斯科特和戴维斯, 2011)[15],技术变迁与创新业已成为组织变迁的直接驱动力量(邱泽奇, 2017)[16]。网络技术的外部性大大降低企业组织活动的交易费用,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契约,甚至心理契约构建起企业联盟、模块化生产、团队协作、大众生产等新的组织形式。另外,技术创新在加速信息传递、降低沟通成本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信息甄别能力,进而保证了新组织形式的稳定性和适用性。滴滴出行、Airbnb等分享经济组织的异军突起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新兴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变革与创新为供需双方基于分享经济平台实现实时匹配、链接提供了可能,进而激发双边网络效应,实现组织高速成长。
第二,网络时代下的消费认知转变诱发了新组织的形成。消费者主权意识的提升使其不再是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作为网络时代的新兴阶层越来越多地嵌入到企业组织活动中,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组织模式。消费者参与、用户创新使得消费者与企业的交互日益密切,开放式创新、民主式创新和价值共创大大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外延。另外,消费者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得组织渴求消费者知识从组织外部向内部转移,与组织内部知识交互、重组,因而外部知识的螺旋式流动跨越组织边界进一步打破了传统组织森严的层级制结构壁垒。服装个性化智能定制领域的典型企业酷特智能提出“人人都是设计师”价值理念,将“满足用户需求”作为全员工作出发原点,采用团队组织工作模式,按照消费者需求聚合,通过“去领导化、去审批、去部门、去科层、去岗位”打造极致扁平化组织,印证了消费者参与和认知转变对新组织形成的作用。
第三,网络时代下的组织和个体从多元、多维组织结构和形式中获得价值与意义。网络信息时代,组织运行中的现实问题日趋复杂化、叠加化、超常规化,科层制作为工业时代的通行机器齿轮在网络时空情境下的比较优势逐渐衰减,企业活力被固化的工作流程、直线式指挥链条、森严的等级制度所抑制,组织自变革、自创生、自激活成为现代企业组织的重要转型路径。海尔通过海创汇、创客实验室等创业孵化平台,为海尔生态圈提供开放性社会资源,并给与他们综合创业服务指导,将企业员工从被动的命令接受者变为自激活的创客,持续释放网络时代下员工与组织活力。
三 新组织形成的基本导向
传统科层组织是常规工业技术背景下,由命令、交易、竞争等线性思维主导,进行有形资产或信息垂直一体化的组织管理形式。其组织目标强调超越竞争对手或完成既定任务。新组织则是由计算机通信技术催生,以网络思维、整体思维等非线性思维为主导,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将各种资产,尤其是知识资产进行整合的组织管理形式。其组织目标强调参与者价值共创,协作利益优先。传统科层组织与新组织组织范式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传统科层组织与新组织组织范式对比
网络时代下,传统科层管理中的控制、协调职能日趋让位于创新、协作等组织范式,知识的传播与创造又使得企业组织突破了“应用知识的机器”的认知范式。随着组织范式和认知范式的切换,新组织形成表现出遵循知识创造、协作创新与身份重构三个基本导向。
第一,知识创造导向。新组织之所以或将成为取代传统科层组织的组织形式,根本就在于网络时代的新组织具有更为强大的知识创造功能。传统科层组织一般依靠设立专门研发部门自主研发来实施技术创新,但这种组织结构由于“知识碰撞”带宽较窄,组织学习往往带来“近视症”效果,创新产品或服务一旦遭遇市场“滑铁卢”,不仅转换成本极高,甚至直接威胁组织存续。而战略联盟、产业集群和商业生态系统等形式松散耦合的新型组织,由于组织边界模糊,知识异质性程度较高,有利于知识跨边界流动和互补知识集成式创新。企业可以基于前期经验积累形成的知识存量迭代式开发新产品和服务,降低试错成本和转化成本,进而加速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多重网络嵌入有利于企业提高知识创造绩效,知识整合发挥完全或部分的中介作用(梁娟和陈国宏, 2019)[17]。
第二,协作创新导向。面对日益网络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传统科层组织在链接外部伙伴时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信息过滤延迟、信息对接受阻等障碍,同时囿于本身机制僵化往往创新动能不足,无法精准把脉市场痛点以应对环境复杂性。而新组织可以通过创建“协作复杂性”(Schneider et al., 2017)[18]来减少相对于环境的复杂性差异,在协作复杂性的构建过程中,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使得协作创新成为可能。另外,与传统的权威、谈判等机制相比,新组织的信任机制降低了联盟网络中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在扩大合作范围的同时增强了组织合作的灵活性,从而使协作创新绩效得以提升(Powell, 1990)[19]。组织间和组织内信任关系弱化了契约不完备带来的道德风险,降低了交易费用,有利于知识、信息资源的互动与共享,进而激发协作创新活力。
第三,角色重构导向。新组织适应了网络时代组织行为主体的复杂角色特质。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流动的知识个体开始重新审视其之于组织的价值所在——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是顾客又是营销者,既是员工又是内企业家(3)内企业家(Intrapreneur)由Pinchot提出,是在既有企业组织内部进行创业活动的管理者或员工。。在后结构主义的视阈中,行为者是主动的智能体,他们作为组织场域的“即兴表演者”,通过主观认知网络驱动实际行为网络(奇达夫和蔡文彬, 2007)[20]。基于“员工——顾客”的传统组织内外部主体二分法界定限制了组织对于价值创造主体的认知,传统正式组织难以辨识复杂叠加的角色集合。而新组织为“员工创客化”、“顾客员工化”、“员工用户化”提供了角色重构的平台,在契合复杂叠加角色变迁的同时,有利于实现组织与组织身份的协同进化。
四 新组织的“四维”形式
人类历经了三次工业革命现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关头,新的组织现象和组织形式不断涌现。事实上,任何组织形式都是由于提供任务分工、任务分配、奖励分配及信息工作等四类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而得以存续,评价组织形式新颖与否主要是与可比目标的现有组织形式进行比较,很难以单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来展现新组织形式的新颖性(Puranam et al., 2014)[21]。由于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组织可以突破科层制这一组织设计“默认选项”,选择更为多元的组织形式或解决方案以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本研究认为,网络时代下新组织的“新”,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新结构(包括组织间和组织内)、新主体、新形态和新要素。下文从这四个维度归纳梳理纷繁复杂的新组织形式及现象,以期系统全面地认识新组织。
(一)组织间新结构
一般而言,广义的组织结构包括组织间的结构和组织内的结构。组织间的结构是不同组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进行某类活动的一种制度安排,组织内的结构也即狭义的组织结构,是在组织内部进行部门设置、工作分配、业务切分的一种组织设计和架构。网络时代下,组织间的新结构主要包括商业生态系统、产业集群和战略联盟等组织形式,其以主动链接、自发结网为主要行为特征,通过最大化搜寻可利用的互补网络资源要素扩张组织边界。在竞合逻辑主导下,协同共生、价值共创成为了组织间新结构的比较优势。
商业生态系统这一新概念首先由Moore(1993)[22]提出,他将企业看作是跨行业的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单元,系统中的企业围绕创新通过竞合实现共同发展。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组织、机构、个体组成的群落,并对企业本身、企业的顾客和供应商产生影响(Teece, 2007)[23],商业生态系统还强调系统成员的表现与系统整体休戚相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Iansiti和Levien, 2004)[24]。同时,商业生态系统也是一种结构,由一组多边伙伴的一致性结构(Alignment Structure)所定义,它们需要相互作用以便实现核心价值主张(Adner, 2017)[25]。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特征在于独特的或超模块化的非通用互补性,并允许管理者通过面对类似规则的一系列角色协调其多边依赖性,以避免与每个合作伙伴签订定制合同协议的必要性(Jacobides et al., 2018)[26]。阿里巴巴的商业生态系统可以看作是以电商为核心、以支付和物流为支撑打造的,通过交易平台连接买卖双方,促进社会资源协作运转,在此基础上向多个产业延伸发展,并利用消费者数据资产进行相关领域战略投资,营造站内站外流量生态。因此,商业生态系统由竞合逻辑主导、共生思维驱动,呈现出组织角色多样化、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优势互补化、组织关系依赖化和组织结构网络化等特征。商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新的结构形式使其价值创造模式不必采用纵向一体化或科层控制依然可以产生组织间协同效应。
产业集群有别于商业生态系统,强调地理位置相近的多主体基于人际关系与生产及交易关系构成的有机组织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网络组织形式。具体包括原子型结构、横向型结构、单核型结构、多核型结构及混合型结构五种网络结构形式(孟韬, 2009)[27]。产业集群同时也是介于科层组织和纯市场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其市场化效率虽然不及纯市场组织,但由于组织间优势互补、专业化分工效率较高,有利于化解内生交易费用,进而提高组织间协作效率。集群内组织通过长期协议方式建立起组织间信任文化,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产业集群整体稳定性。正是由于组织间形成的互补式、嵌入式网络结构,产业集群在优化集群内部资源配置的同时进一步使集群内组织成员朝着自组织方向演进。随着网络信息科技迅速迭代,产业集群逐渐突破物理边界束缚实现信息空间中的聚集,从而出现“虚拟聚集”等新的组织形态和结构(王如玉等, 2018)[28]。产业集群作为组织间的网络组织,其网络稳定性、位置中心度特征等对知识搜索和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作用(吴松强等, 2018)[29]。
战略联盟作为一种混合组织,描述了企业为共同利益、共用资源、共担风险,通过双边或多边合约缔结成的优势互补的企业间合作关系(Teece, 1992)[30]。战略联盟中的企业嵌入在联盟关系网之中,并由社会网络所塑造。嵌入式关系促进了合作伙伴之间更频繁的信息交流,从而影响联盟的成功以及进入联盟的企业的绩效表现。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经济使得企业选择联盟的对象、领域和手段更加丰富,企业之间点对点竞争逐渐演化为战略联盟、联盟网络之间的多重网络竞合博弈。由核心企业驱动的战略联盟组织形式表现出组织间关系日益密切的网络形态(Cloodt et al., 2006)[31]。而在战略联盟协同演化过程中,组织形式则表现出交叉型供需结构及多边联结的无边界网络结构(赵健宇和王铁男, 2018)[32]。近年来,联盟组合形式研究逐渐兴起,企业加入多个联盟的联盟组合行为成为战略联盟演进“催化剂”,一方面使得组织表现出联盟叠加、多伙伴联盟和重复联盟多元组织结构(韩炜和邓渝, 2018)[33],另一方面组织间关系更多地依靠信任、声誉、阶段式互惠等机制来维系。
(二)组织内新结构
组织内新结构所表现的新组织形式主要包括模块化组织、矩阵式组织、团队和阿米巴组织等。网络时代下,这些新型组织结构突破了传统科层组织垂直固化的等级命令体系,在激活个体和组织活力的同时,将组织触角延伸到更多的长尾市场,有利于全面拓展市场需求。这种新型的组织内部结构已经成为网络时代企业应对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不仅互联网高新技术企业内部厉行精英团队攻坚克难,传统制造企业也开始积极寻求新矩阵再造、阿米巴裂变等组织内结构变革。
Baldwin和Clark(1997)[34]发表的《模块化时代的管理》一文正式掀起了模块化研究的热潮。模块化首先成功应用于产品设计开发领域,继而成为一种组织设计实践。组织的模块化本质上是围绕产品或功能的模块化进行公司价值链切分(苟昂和廖飞, 2005)[35],而依靠价值链切分和重组形成的组织就是模块化组织。相较于传统科层组织、战略联盟和产业集群等组织形式,组织内部模块化通过在组织内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决策速度,增强组织弹性,各项工作任务得以并行展开,实现跨业务协同,极大地提高了组织整体效率。同时,组织内部模块化强调企业对价值链各个环节进行彻底切割、重新组合,让市场机制充分检验模块真实价值,增强组织整体竞争力。戴尔公司是组织内部模块化的较早实践者,其从组织结构、业务流程、部门职权、企业绩效与激励五个方面开展模块化设计,逐渐形成系统的组织建设过程。通过主导不同层级中的各成员单位协同合作,最终完成模块化生产与运作,使得企业能够有效提升运营效率、创新水平及应变速度。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结构和产品设计之间的契合往往被认为是模块化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即所谓的“镜像假设”,但组织从战略上“打破镜像”也可以表现良好(Colfer和Baldwin, 2016)[36]。因此,目前关于模块化力量的边界条件等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组织设计者需要密切关注模块化搜索的不同元素如何相互作用,并避免增量调整(Fang和Kim, 2018)[37]。另外,模块化还可能导致项目内的专业化从而妨碍协作(Richard et al., 2019)[38]。打造模块化组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同时又是一个动态演进与选择的过程,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激进和盲目进行模块化改造反而可能损害企业竞争优势。
矩阵式组织结构与传统科层制不同,这种组织结构可以依据产品、服务、功能和区域维度,产生两行或多行命令,其本质是一个应对复杂任务的企业内部多命令系统结构。矩阵式结构通过整合纵向和横向的双重指挥链条赋能组织,为组织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员工个人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平台,矩阵经理可以根据战略计划进行人员和资源的灵活组合。通过将跨职能的员工按项目聚集在一起,每一员工专注某一特定项目并共享企业资源,进而在降低协调困难的同时达到资源最优配置。但矩阵结构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违反等级权力链和统一指挥等传统管理原则,进而产生部门设置臃肿、角色界定不清晰、授权复杂及接口模糊等管理难题。Peters和Waterman(1982)[39]甚至曾经断言几乎“卓越公司”从不承认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事实上许多多产品跨国公司和基于项目的公司往往采用矩阵式组织结构。矩阵结构中的多权威关系是组织一些基本紧张关系的反应,而矩阵式组织的失败大多归咎于矩阵管理的不当(Levinthal和Workiewicz, 2018[40]; Galbraith, 2009[41])。
团队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矩阵式组织基于纵向维度的切分,较之矩阵式组织更为灵活。在过去二十多年,团队因其能够应变复杂多变环境而成为许多组织普遍采用的形式。团队将超出个人能力的大型、复杂任务分解成较小的部分,不同成员执行不同任务并将分解的任务组合成产品或服务(Mathieu et al., 2017)[42],因而富有流动性的团队合作更适合复杂混沌的外部环境(Edmondson和Mcmanus, 2007)[43]。组织内部解构赋能的团队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短时间内聚集项目团队成员,根据各自项目任务完成产品开发或服务,团队解散后,成员各自归队或重新加入新的项目,从而实现了人力资本的自组织、高效率充分运作。
将多人小型团队进行极致化分解,形成了以阿米巴组织为代表的组织内新结构。阿米巴(4)阿米巴(Amoeba)原指一种单细胞生物虫,通过不断调整姿态、形状并进行细胞分裂,巧妙应对周遭环境变化。经营理念由日本管理哲学大师稻盛和夫提出。阿米巴组织将大型组织切分为众多的独立核算、独立运营的小团队、小单元(称作“巴”),依靠众智达成目标,强调令每一名一线员工成为企业主角,施行全员参与经营,并将其塑造为具有经营意识的领袖(稻盛和夫, 2016)[44]。阿米巴组织结构是组织内部结构最为极致化的分解状态,它以分解为表征、以统合为目的,实质是通过战略事业单元(SBU)、微战略事业单元(Min-SBU)以及细胞战略事业单元(Cell-SBU)三级量化分权,将市场机制注入组织内部以激活个体与组织的新型组织结构。阿米巴组织这种“小而美”的组织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下移,以内部解构的形式赋能每一个微观个体,通过“个体价值的崛起”(陈春花, 2015)[45]激发创新力。中梁地产阿米巴组织强调“精总部、强一线、小组织”;“管头、管尾”;“支持不包办、过问不揽权”;“充分授权、经营即算账、算账即定价”等理念,将区域集团公司分为事业部巴、综合管理巴、市场营销巴和项目管理巴四类,甚至各巴中的成员也独立成巴,以各单位巴长为首建设小巴,推进权责利对等,实现企业组织的横向切割、纵向裂变。
总体来说,网络时代下新组织的结构表现出外部开放式协作、内部解构赋能的动态演化特征,与传统盒子套盒子式、封闭的科层组织架构的组织行为逻辑完全相左。组织间的新结构基于信任机制实现协作共生、价值共创,强调组织间竞合秩序下的跨边界链接、去中心化织网属性。松散耦合的外部开放式协作结构打破组织边界,使得异质性资源跨边界流动,从而提高了组织的吸收能力。而组织内的新结构基于自组织机制进行灵活解构、自由构型,强调组织的近可分解性、节点机动性和扁平化特点。在组织内部进行解构将传统金字塔组织架构拉平,管控幅度放大,赋能并激活自主的有机个体,构筑新的价值关系网络,为组织提供永续成长创新动能。
(三)新主体
网络时代下,组织的价值创造主体身份与边界变得愈发模糊。组织的价值创造来源主要涉及外部顾客或用户、内部员工两种新主体融合所实现的供需一体化及创新——顾客或用户成为了产消者,员工则成为了企业内创客。顾客和员工的角色转换与重构在网络链接红利、技术赋能驱使下,使得组织边界不断拓展、组织形式实现量子式跃迁。产消者(Prosumer)的出现可以被视为新组织主体变化最鲜明的表征。他们追求自我使用、自我满足而并非为交易而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人(托夫勒, 2016)[46]。作为新主体,产消者在引起社会经济变迁的同时,也孕育并催发出以大众生产组织、分享经济组织和企业内创业为代表的新组织形式。
学术界一般将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界定为“散布于各地的参与者通过使用互联网共同协作,提供或分享产品,特别是知识产品的生产模式”(Benkler et al., 2015)[47]。孟韬(2017)[48]根据“是否产出公共品”和“参与者或生产内容的专业性程度”两个维度将大众生产划分为维基产品、开源软件、用户创造内容及众包四种形式。不求经济回报、参与者众多、系统开放以及自发互动协作是其有别于企业组织抑或市场机制的基本特征(孟韬和孔令柱, 2014)[49]。大众生产既不受市场机制制约又突破层级制束缚,使用非经济激励为主的多种激励措施,凭借分权化、自发性群体实施开放协作式创新是其优于市场和企业的比较优势。大众生产的独特之处在于集市治理机制,Demil和Lecocq(2006)[50]认为相对于市场、层级和网络,集市治理具有以开放许可作为特殊的合同关系、双边交易受开源社群影响、弱激励与约束机制三个特点。这种集市治理本质上是网络治理的特殊表现形式,模块化生产、自组织及用户创新则是其作用得以发挥的条件。开源软件、Wikipedia、“用户创造内容”等都是典型的大众生产组织模式,其倡导的“人人参与、共同协作”理念正成为一股商业热潮,许多公司将这一理念运用于研发和管理创新中。
近年来,Airbnb、Uber和滴滴出行等分享经济企业以独特的模式获得了高速成长,分享经济热浪迅速波及汽车交通、住宿服务、金融服务、文化教育等诸多行业。分享经济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产品和服务需求端的消费者,还扮演着产品和服务供给端的提供者角色。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交易费用大幅降低,闲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作为“产消者”的分享经济参与主体秉承互联网分享、开放和协作精神,表现出类似于大众生产组织去中心化、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多样化参与动因等典型特征(孟韬等, 2019)[51]。目前对分享经济组织的研究还是一个新领域,学者们主要针对分享经济组织模式和分享经济组织形成机制两方面进行探讨。Mair和Reischauer(2017)[52]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分享经济组织(Sharing Economy Organizations)的概念,将分享经济定义为一个市场网络,个体在市场网络中运用多种形式的补偿进行交易并获取资源,通过企业运营的数字化平台进行调解,从而赋予企业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信任和互惠是分享经济组织的两大形成机制,同时也是用户参与分享经济的动机(Miralles et al., 2017)[53]。分享经济组织依托平台支撑,使得参与主体的身份根据实际需要实现多场景式即时切换、无缝连接,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同时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此外,在数字化技术助推下,创客使得传统的“福特主义”变轨并成功演绎出以满足消费者千人千面需求为特征的“创客运动”,他们将兴趣爱好发展成迷你帝国,变创意为实践。Pinchot(1985)[54]将创业型的员工定义为内创业者,他们是在企业内部将想法变为现实的企业家。企业内创客既是内创业者,同时也是内创业家,他们极富创新力地从事打破既有业务模式、重构企业组织边界、重组内外部资源的活动。企业内创客通过主动性、风险承担和创造新想法等创新行为从而提高了组织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Gawke et al., 2017)[55]。企业内创业既可以看作是公司层面自上到下的创业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个体层面从下至上的创新过程(Blanka, 2018)[56]。在海尔内部推行的小微创业模式,新技术的发展彻底激活了企业内创客集体式的创业精神基因,创新创业主体从网络时代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逐步扩展至全员创业、“人人都是CEO”。他们作为企业的触角精英组成各式各样的小微团队更加主动地对接市场、更加广泛地跨界交互、更加频繁地创造知识,使得网络时代的企业组织愈发彰显出人文色彩。另外,企业内创业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嬗变为信任主导的股权合作关系,在稳定企业人才团队、凝聚企业集体向心力的同时活化了人力资本动态组合。
(四)新形态
网络时代的平台组织、社群组织是两种典型的新组织形态。平台组织可以看作是组织形式进化的终极形态,而社群组织则突破市场与科层机制束缚实现自组织演进,成为生命力最强的组织形态。
与强调分层控制、专业分工的科层架构不同,平台组织是“一种面临新兴商业机会和挑战时构筑灵活的资源、惯例及结构组合的组织形态”(Ciborra, 1996)[57]。例如海尔ECO生态资源平台,以用户驱动机制跨界整合智慧家庭生态资源,加速全产业要素紧密链接,赋能小微企业实现生态价值最大化。平台组织的核心优势在于通过灵活匹配资源产出多样适应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演化能力,依托基础设施链接供需等多边市场的网络效应以及价值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的主导功能(井润田等, 2016[58]; Jacobides et al., 2018[26])。平台型企业具有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边界化结构特征(胡国栋和王琪, 2017)[59]。平台组织通过灵活分散的小微组织打造组织“前端”,紧跟市场脉搏,即时满足顾客定制化、个性化需求,不断迭代升级产品服务;通过建立风控、资源支持等组织“后端”为“前端”注入持续创新动力;通过项目甄选、利益绑定等“中端”机制实现前后端无缝链接。此外,平台组织还可以通过链接多网络、减少多宿主行为以降低去中介化风险构建自身比较优势(Zhu和Iansiti, 2019)[60],进而使其成为最有可能取代科层架构的新型组织形态。
对社群组织这类典型的新组织形态,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界定。即使“社群”这一概念在组织理论中涵盖诸如职业社群、学术社群、技术社群、实践社群、在线社群、开源社群和合作社群等众多表现形式(O’ Mahony和Lakhani, 2011)[61],此外还有品牌社群、用户社群和认知社群等。网络时代下,社群组织是由共同兴趣和目标的个体基于网络平台交互形成群体关系的新型组织形式。Seidel和Stewart(2011)[62]认为开源软件开发群体是一种社群组织,他称之为C型组织(Community-form Organization),该组织结构的特征表现为:成员非正式且流动、依赖自愿劳动、具有更高目标感的强大社区文化、产出基于信息的商品、共享组织知识和低成本高效沟通。社群组织这种新型组织形式既不依靠市场机制,也不受制于科层命令,而是通过自愿、自发、自利机制驱动。社群组织独特的价值功效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社群组织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即使当组织消亡后,由组织前雇员形成的社群依然可以导致新组织的诞生(Walsh和Bartunek, 2011)[63]。第二,社群组织突破了生产的地理边界,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即时交互,通过外包、众包等形式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第三,社群组织加速了知识创造过程,用户创新、民主创新使得产品和服务的迭代更新更加贴合市场需求。小米打造的“虚拟社群+分众互动的平台”即是一种社群组织,由最初的小米社区(小米手机用户交流平台)逐步发展为包括小米论坛、随手拍、酷玩帮、同城会、小米学院等社区开放式分众互动平台。其中小米论坛是小米用户最主要的互动交流平台,小米学院则是新产品研发数据库,而酷玩帮、同城会则是社区内容主题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五)新要素
传统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环境、战略目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和人力资源等等。伴随人类步入知识社会,知识已经成为现今重要的资源要素,使得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传统要素的重要性日益弱化(德鲁克, 1998)[64]。网络时代下,知识已经进化出了“新媒介”属性,并且与整个网络的嵌入程度愈发深入。知识正在变得无边界、层次弱化、中心过滤减少、更加公共开放并具有超链接特质(温伯格, 2014)[65]。知识要素也愈发分化,“个人的分立知识”或“知识分工”正逐渐取代“劳动分工”。另外,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换更为复杂化、知识网络的构建更加动态化、分层化,组织学习也更加强调学习能力的易获取性和可持续性。由此催生出诸如知识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和动态分形组织等形式。
知识型组织最早由瑞典财经分析家和企业家斯威比于1986年提出。知识型组织是一个将知识作为组织的重要资源、具有自组织功能的有机体,知识工作者在组织内外部进行知识交互、共享、创造与应用,并不断延展组织边界。其演化依次经历了知识型团队、知识型企业、知识联盟、复杂知识网络组织及虚拟知识组织等几个阶段(刘希宋和喻登科, 2008)[66]。知识型组织通过营造鼓励创新的组织氛围、灵活多功能的组织结构、利用知识工作者隐性知识持续学习促进知识创造。根据组织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与情境,运用知识共享工具、头脑风暴工作方法建立知识共享社区,并将知识管理纳入绩效考评,以利于激发知识工作者产出高质量的工作业绩。打造知识型组织本质上是一个将个人、团队知识资产转变为组织智力资产的动态过程,以市场需求为引领,构建开放自主组织学习氛围以实现组织和个体的协同成长。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如何将知识工作者的创新潜能激发出来以形成组织创新动能已成为知识型组织的重要议题。
1990年,彼得·圣吉基于组织学习、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提出学习型组织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一种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而持续培养组织成员学习能力和自我改造能力的组织形式。学习型组织由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变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团队学习五种要素组成(Senge, 1990)[67]。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层次扁平化、系统开放化及组织咨询化三个方面(傅宗科等, 2002)[68]。对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大多聚焦在理解学习发生的机制、为何某些组织比其他组织更善于学习、何时学习能够提高组织绩效、组织学习与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学习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等等。陈国权(2002)[69]提出一个学习型组织的过程模型,其中知识库位于该模型七个组成要素的中心位置。由于组织学习的动态复杂性,目前尚未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学习型组织模型。网络时代,学习型组织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组织绩效的维度化、民族文化的影响、非正式学习在创造学习文化中的作用、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干预措施、学习型组织的方式、成本收益、时间和地点等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Watkins和Kim, 2018[70]; Tuggle, 2016[7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进行学习型组织改造,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挑战不仅在于建立适当的系统来获取认知和行为能力,而且还要确保这些能力得以保留并易于检索。
近年来,建立在知识创造理论基础上的动态分形组织(Dynamic Fractal Organization)为促进知识转化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组织范式,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二元关系在“实践智慧”(Phronesis)螺旋催化下形成新的知识三元关系,进而推动组织边界内外的知识转化(Nonaka et al., 2014)[72]。动态分形组织作为自组织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其本质是建立在“多层次网络场”之上的知识三元关系。动态分形组织通过“多层次网络场”的构建实现必要的多样性,在获取知识三元关系的同时,完成知识创造与应用。例如,丰田的普锐斯汽车开发项目中,通过创造、合并、综合异质性的技术知识及横向技术开发形成知识三元关系,构建动态分形组织,从而实现了原有知识的充分应用以及新知识的探索式开发,并且最终使得丰田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保有竞争优势。
五 研究结论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计算机通信技术发展带来的技术变革、认知转变、企业应变,使得组织结构和形式发生改变,组织间和组织内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这是新组织形成的根本动因。新组织因而可以冲破科层制的“铁笼”,选择并依托多样化的组织结构和形式解决网络时代下出现的种种新生问题。知识创造、协同创新和角色重构是新组织形成的基本导向。网络时代下新组织形式的 “相对新颖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新结构、新主体、新形态和新要素,同时构成新组织的“四维”形式。具体说来:(1)新结构在组织间表现为商业生态系统、产业集群、战略联盟等组织间关系,在组织内则表现为模块化组织、矩阵式组织、团队和阿米巴组织等组织结构。(2)新主体方面,顾客或用户成为“产消者”、员工则成为企业内创客,他们一同构成了网络时代下新型组织主体,进而催生出以大众生产组织、分享经济组织和企业内创业为代表的新组织形式。(3)新形态则为组织终极进化形态的平台组织和生命力最为持久的社群组织。(4)新要素指的是知识成为网络时代组织的新型资源要素,知识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和动态分形组织等新形式应运而生。
组织是系统中的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系统。组织在自发扩展生成秩序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影响。网络信息技术的变革大大丰富了产品和服务样式,在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促使消费者个体意识和知识水平不断攀升。面对消费者认知和角色的转变,内生逐利本能使企业组织在外生技术赋能下得以根据具体的组织问题提出应对方案,演绎出千企千面的多样组织结构和形式。
组织是组织要素互构的场域,同时也是场域中互嵌的组织。网络时代下,分化的知识推动了知识利用类型和转移途径的变革, 同时又导致了组织结构形式和知识配置方式的变革(罗珉, 2006)[73]。在知识要素的作用下,新型组织结构和产消者、企业内创客新主体不断融合、交互进而催生出新的组织形态。知识成为新的重要要素资源并成为推动组织形式变迁、塑造组织能力的利器。
因此,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本质上是由技术变革引发组织形式变化,进而导致组织能力提高所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组织结构、组织主体、组织形态均发生了变异与进化,知识成为出现这些演化形式的最核心的价值创造要素,居于中心位置。组织形式此时已然变成了一种组织能力,在推动组织自身持续变革的同时助力技术创新。由此提出一个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综合框图,如图1所示。

图1 新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综合框图
通过对新组织的形成动因、遵循的基本导向、具体的组织形式和价值创造过程的解构,基于组织边界、主导逻辑和组织目标三个方面,分析对比各种新组织形式,如表2所示。

表2 新型组织结构和形式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新组织形式是科层组织演化过程中为克服其弊端出现的各种形态。多样化的新组织形式相对于科层组织尽管有其比较优势,但现实告诉我们,即便如京东、韩都衣舍等平台型企业,其组织形态虽然是众多企业的一个平台,就其本身内部的组织结构本质而言,可能仍然是经典的科层架构,这似乎又使得新组织形式成为科层制的变种。
对于组织而言,科层制的智力强化已使其成为大多数组织设计中的“默认选项”,其重要性甚至被誉为一种“科层神话”(5)詹姆斯·马奇(2011)[74]认为“科层神话”是指“问题可以分解成一层一层的子问题,行动可以分解成一层一层的子行动。组织采用科层结构并采用层级方式解决问题,依赖的就是科层神话”。。之于个体,科层制又赋予其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定程度的被迫参与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比自愿参与好” (克罗齐埃, 2002)[9]。Tiedens et al.(2007)[75]的实验研究发现,在面对完成一些工作任务时,参与者选择了科层而非其他社会安排,而实验样本则是“后科层”的年轻一代。这意味着堂而皇之地改变科层抑或是攻击它显得困难重重。
正如Pfeffer (2013)[76]所言,我们可能希望科层制消失,所以我们积极寻找证据来证实它的不重要和行将灭亡。不可否认的是,科层制的演化从未停息,但是在这一组织演进过程中,即使采用新组织形式的新兴互联网公司仍时有向科层制暂时过渡以寻求破局之道。网络时代复杂的外部环境要求组织重新审视个体既追求自由又寄望稳定、既理性又非理性的矛盾特质,同时要求组织着力平衡科层与网络、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标准化与定制化的对立统一关系。外部开放式协作、内部解构赋能作为组织结构演化的显著特征对企业组织管理范式影响深远。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利用清晰的指挥链、基于业绩的文化和团队反馈机制避免科层陷阱,发挥科层约束解决方案、聚合想法和结构化流程的关键功能(Sanner和Bunderson, 2018)[77],同时利用新组织形式的多样、灵活、非理性特征适时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应变,将科层制转变为“潜在选项”,对于理解网络时代下的新组织形式显得尤为重要。
新组织作为显著不同于传统层级组织的新兴组织现象和组织形式是组织研究的前沿领域。鉴于新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有研究较为分散凌乱,因此有必要对种种新现象以及现有理论进行反思和整合,本研究基于新结构、新主体、新形态和新要素四个角度构建理论框架,全面系统分析新组织及新组织现象。未来新组织相关研究的设想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国外管理理论对新组织现象和形式展开分析与论证,结合我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实际背景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有待进一步对新组织的形成与形式进行本土化研究与挖掘。其次,对新组织价值创造机制进行大样本实证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论推导的研究成果。最后,新组织是如何根据环境复杂性选择或调整某一具体的组织形式,这些新组织形式又是如何动态演化的,也是需作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基于马克思和韦伯文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