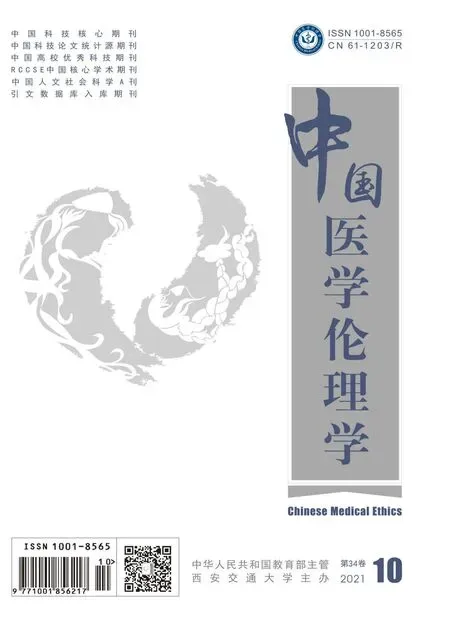儿科癌症试验中受试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戴志晴,尹 梅,王 彧,金琳雅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751801127@qq.com)
随着药物临床试验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数量的激增带来诸多伦理和法律问题。其中,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儿童受试者作为临床试验中的弱势群体,在认知、判断和表达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无法充分有效地理解临床试验的各类信息。儿科癌症试验中,儿童受试者经历的风险往往高于一般受试者的临床试验,因此,儿科癌症试验中儿童受试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更应受到关注,从而为儿童受试者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措施。
1 概述
1.1 关于儿童的规定
美国《联邦法规45 CFR 46》(2018版)规定“儿童是指根据进行研究所在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未达到同意接受该研究涉及的治疗或程序的法定年龄的人。”[1]美国及国际惯例对儿童的年龄划分为0~18周岁,与我国未成年人的年龄划分一致。2020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其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这与《国际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是一致的,《公约》规定儿童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任何人[3]。本文将儿科癌症试验受试者的年龄规定为18周岁以下,与国际惯例一致。
1.2 儿科癌症试验发展现状
尽管治疗小儿恶性肿瘤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儿童癌症仍然是儿童的第四大死亡原因。许多治疗小儿恶性肿瘤药物的剂量都是通过调整成人抗癌药物的剂量来确定的[4]。但是,许多儿童肿瘤在组织学上与成年人不同,儿童的生理可实质上改变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调整已证明对成人有效的抗癌药物的剂量来治疗儿童癌症仍存在儿童出现毒性反应的风险,故而必须在儿童中验证癌症药物的治疗剂量以获取最佳治疗剂量。
肿瘤学的第一阶段试验旨在确定新癌症药物的剂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与成人一样,在儿童中进行的癌症试验也存在严重毒性和受益前景有限的风险[4],加之儿童监护人对儿科癌症试验的认知不足、接受度不高,由此导致儿科癌症试验受试者招募困难重重。保护儿童受试者的合法权益,儿童研究必须满足比成人研究更严格的伦理和监管标准。目前批准儿科癌症试验可能过多地依赖对试验受益的看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益处的可能性和相关风险的大小。最大限度地提高儿童受试者直接受益的前景,并对具有社会价值但不太可能给儿科参与者带来直接好处的临床试验使用替代批准途径[5]。
2 我国儿科癌症试验中受试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儿童受试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立法不完善
《儿童权利宣言》规定:“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我国目前没有具体规定儿童受试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规,现存法规中虽存在关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章节,但其中对保护儿童受试者的规定篇幅较少。如2016年《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中规定特殊保护原则,“对儿童、孕妇、智力低下者、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受试者,应当予以特别保护”[6],但如何保护以及保护的具体措施并未提及。国内相关法规及相关文献对儿童的规定采取的是民法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相关法规只提及无行为能力受试者,而未提及或一笔带过儿童这个群体,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其权益更应受到完善的法律保护。因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未成年相关临床试验、保护未成年受试者的合法权益迫在眉睫,如此儿科癌症试验中对受试者的保护方能做到有法可依。
2.2 儿科癌症试验中受试者知情同意不全面
知情同意书是保障受试者权益的主要措施。大多数未成年人在药物临床试验中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到知情同意,需要征得其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意[7]。2020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新增了儿童知情同意的内容,儿童受试者应当征得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有能力做出同意决定的儿童还应当征得其本人同意,如果儿童受试者本人不同意参加临床试验或者中途决定退出临床试验时,应当以儿童受试者本人的决定为准,除非在严重或者危及生命疾病的治疗性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其监护人认为儿童受试者若不参加研究其生命会受到危害,这时其监护人的同意即可使患者继续参与研究。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儿童受试者达到了签署知情同意的条件,则需要由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之后方可继续实施[8]。GCP中新增的儿童知情同意的规定较为详细,但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问题,有能力做出同意决定的儿童以及达到签署知情同意条件的儿童的具体标准并未提及,如果仅按照生理年龄来划分儿童获取知情同意的能力就会存在一定的缺陷,没有考虑到儿童成熟度的问题。
2.3 儿科癌症试验中风险与受益监管不到位
儿科癌症临床试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直接受益前景以证明其风险合理。儿科癌症患者的父母认为应该对风险和受益作出判断。然而,接受这一观点则意味着,对研究进行独立的伦理和监管审查的唯一原因是解决知情同意(或父母许可)的充分性问题,尽管已有数十年的国际共识,但在提出参与研究的提议之前,研究监管还必须参考风险受益比。因此,即使父母可能因为参与试验的替代方法而给孩子带来严重或致命的不良事件,但是提供这样的判断可能是不合理的。大多数进入一期临床实验的药物最终被证明是不安全的或无效的。鉴于儿科肿瘤学试验的风险较大,并且可能保证为参与者提供潜在益处,直接受益标准下的批准有时可能缺乏足够的保护,并加深对研究受益的误解。因此,有必要设计监管途径,支持此类研究的批准,同时提供足够的保护。
3 我国儿科癌症试验中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3.1 完善关于未成年受试者权益保护相关立法
美国《联邦法规45 CFR 46》以及《联邦法规21 CFR 50》都对儿童在临床研究中的附加保护作了详细的规定。包括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职责,不涉及最大风险的临床研究,临床研究涉及的风险大于最小风险,但会给个体受试者带来直接受益的前景。临床研究涉及的风险大于最小风险,并且没有直接受益于个体受试者的前景,但是可能会产生有关受试者疾病或状况的一般性知识。其中,《联邦法规45 CFR 46》第二百零五条将对新生儿的保护独立于儿童之外,主要规定了能够纳入医学临床试验的新生儿所应具备的条件、知情同意及相关保护问题[1]。
目前,我国关于受试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中位阶最高的是《民法典》,其规定为研制新药、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开展临床试验的,应当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获得其书面同意[3]。受试者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缺乏保护未成年受试者的相关法律规范,可借鉴美国联邦法规或《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制定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关于未成年临床试验的法律或法规,从立法上保护规范未成年人临床试验,保护未成年受试者合法权益。张姝等[9]认为除非需紧急治疗或研究为该年龄段特有疾病或健康问题的情况下,在未获取大龄儿童安全性及有效性数据前,原则上不纳入新生儿。但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治未病”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以往发生的行为进行规范,还在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进行预测和规范。新生儿属于未成年人,但其毫无风险意识,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其合法权益更值得被保护,为避免新生儿的权益被忽视和滥用,可以参照美国《联邦法规45 CFR 46》,单独规定新生儿参与临床试验的条件、知情同意与保护措施等内容。
3.2 完善儿科癌症试验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虽然2020版GCP明确规定了儿童受试者知情同意的内容,但却并未明确告知有能力作出同意决定的儿童和达到签署知情同意条件的儿童的具体标准。有学者建议儿童临床试验中儿童版知情同意书按年龄分层设计[9]。学术界大多是根据民法中儿童民事行为能力年龄来区分儿童能否获得真实的意愿表达[10],然而仅按照年龄划分儿童取得知情同意的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考虑当代儿童认知能力不断提升,心智成熟较早的背景,家庭成长环境不同,相同年龄段的儿童其认知能力也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美国《联邦法规45 CFR 46》规定,在确定儿童是否有能力同意时,IRB应考虑所涉儿童的年龄、成熟度和心理状态。可以根据IRB认为适当的条件,对所有要按照特定协议参与研究的孩子作出判断,也可以对每个孩子作出判断[1]。故而,结合我国国情,可以考虑将儿童知情同意能力的判断权交给伦理委员会,结合每个儿童受试者的年龄、成熟度和心理状态来为儿童提供合适的知情同意方式,保障儿童受试者的切身权益。
在癌症试验过程中,儿童往往要接受反复放疗、化疗、手术等使其身心遭受巨大伤害的医疗活动,与一般的儿童临床试验相比对儿童的伤害更大,因此更可能在试验过程中产生退出的意愿。《国际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予以适当地看待[2]。在儿科癌症试验中应尊重儿童表达是否参加试验真实意愿的权利,但并非意味着必须接受其自决决定。尊重儿童自决权应考虑以下情况:一是研究涉及的风险不大于最小风险或研究涉及的风险大于最小风险,但会给个体受试者带来直接受益的前景。该种情况下,即使有父母的许可,如儿童反对参加研究其意愿也应得到尊重,除研究干预措施预示有治疗效果,且没有满意的替代疗法。二是这项研究涉及的风险大于最小风险,并且没有直接受益于个体受试者的前景,但可能会产生有关受试者疾病或状况的一般性知识。该种情况下,不得在违背儿童意愿的情况下实施临床试验,应尊重儿童的知情同意权。
3.3 评估儿科癌症受试者参加癌症试验的风险与受益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临床试验中,儿童受试者更易遭受权益损害。对此,可借鉴“最小风险原则”[11]。鉴于儿科肿瘤试验的风险要大于“最小风险”,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给受试者带来足够的受益,无法证明该试验风险的合理性,直接受益标准下的批准有时可能没有足够的保护性,并且对研究受益缺乏认识。尽管如此,一些研究还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必要设计一种监管途径,以支持此类研究的批准,同时提供适当的保护。
第一个是让伦理委员会更严格地审查风险和潜在受益,以便可以更放心地满足直接受益标准。在批准直接受益标准下的儿科试验之前,应使伦理委员会确信存在合理的理由支持直接受益的潜力。第二种选择是承认有必要通过改变途径来批准一些重要的儿科癌症研究,这些研究不同于低风险或直接受益标准。美国PDA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允许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或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在与专家小组协商并获得公众意见的机会后,批准原本不得批准的儿科手术。搜寻是否可以从道德上进行,并且“提供合理的机会进一步加深对儿童健康或福利的严重问题的理解,预防或缓解。”[12]
美国标准旨在严格限制儿童参与临床试验的条件,以充分保护儿科患者。但严格的准入标准可能会妨碍儿科中的重要研究,导致某些儿科临床试验被规定到其他法规的批准类别。因此,决策者应在保护儿童受试者的前提下使用该批准途径。例如,增加例行检查、专家评审等措施,以便迅速地发布指导意见,预先规定支持儿童受试者参与的临床试验类型,提高儿科癌症试验获得批准的概率,保障有效的儿童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使更多的肿瘤儿童患者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