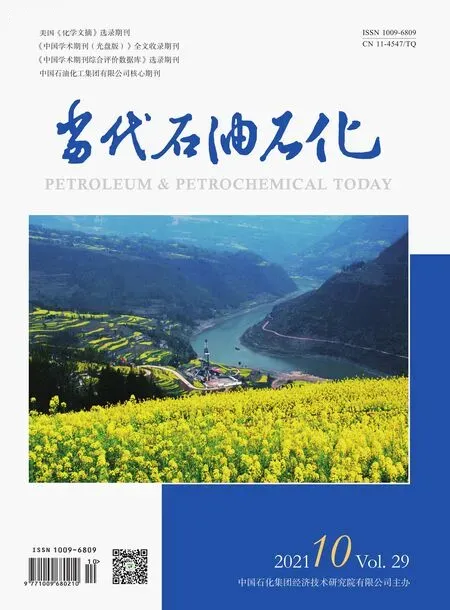国际原油市场供给侧变局与油价趋势研判
王一鸣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厅,北京100728)
2021年7月18日,“OPEC+”召开第十九届部长级会议,历经两周多的艰难磋商后,两大核心国沙特和阿联酋最终达成妥协一致,决定该组织自2021年8月起增产40万桶/日,直至现有576万桶/日的减产总量全部恢复;自2022年5月起,沙特、俄罗斯、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五国联手上调减产基线,一次性增产163万桶/日;减产协议延长至2022年底。
总的看,这次增产协议是2016年“美国增产+OPEC减产”体系确立以来,国际原油市场在供给侧出现的首次重大方向性调整,国际油价在历时长达7年的低位运行后,于去年年初启动暴力触底,并在此后一路强势上行,直接推动主要原油供给国进行政策调整。与此同时,在过往5年里,沙特两次试图挑战美国把控的国际原油市场供给秩序均以失败告终,导致美国对沙特日渐失信并重新调整中东能源战略,由沙特+阿联酋“双支点”取代原有的沙特“单支点”,本轮联合增产协议在历经了“双支点”首轮艰难的战略博弈后初现轮廓。
上一个10年里,美国率先发起页岩油气革命(2010-2015年)、推动构建“美国增产+OPEC减产”体系(2016-2020年),始终是国际原油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格局的主导者。新的10年已经开启,美国再一次率先酝酿推动中东“双支点”战略,以进一步削弱OPEC组织凝聚力与影响力,强化国际原油供给侧市场主导权,有关战略调整值得高度关注并审慎防范。
1 结构性变局的内生动因——OPEC组织分歧
本次联合增产协议的达成一波三折,OPEC组织遭遇2019年卡塔尔“退群”以来的最大路线分歧。会议原定于7月1日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上达成协议,此前的协议文本并不包含2022年5月提升减产基线条款,由于阿联酋在会上明确抗议自身份额分配不公,导致原定于7月5日召开的部长级会议被迫取消。历经两周的艰难谈判后,沙特作出妥协,同意按照阿联酋要求量身定做一次性提升减产基线条款,并扩大政策受益面,加入了自身和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三国。这一措施超出此前市场预期,直接导致协议出台后次日,国际油价创下近一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从这场重大分歧的驱动因素看,阿联酋革命性转变立场主要基于在能源政策、经济竞争和外交独立上的一些特定诉求。
能源政策方面,2020年11月,阿联酋宣布发现220亿桶陆上非常规可采石油资源、新增20亿桶常规石油储量,推动阿联酋可采石油储量达到1 070亿桶。消息公布后,阿联酋政府大为振奋,批复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在未来五年实施总价4 480亿迪拉姆(约1 220 亿美元)的新资本支出,大举推动其旗舰产品Murban原油上产,以支撑2021年3月推出的Murban期货合约,并期待着将其打造为中东地区新的基准定价。按照阿联酋政府的能源发展新战略,计划于2030年将原油产能由目前的400万桶/日提高至500万桶/日,在石油需求枯竭之前尽可能多地出售资源。然而,目前“OPEC+”的配额分配导致阿联酋有1/3的产能被闲置,成为OPEC集团内部受损最为严重的国家[1],其能源部长马兹鲁伊明确表示,阿联酋“牺牲最多”“完全不公平、且不可持续”[2]。本轮联合增产协议难产,根本上源于阿联酋急于上产的能源政策与沙特治下“OPEC+”缓慢增产的总体基调之间存在矛盾,抬升减产基线只是缓和这一矛盾的暂时举措,围绕中东地区能源份额、定价权、主导权的争夺才是两国战略分歧的根本原因。
经济竞争方面,沙特和阿联酋同时在2016年提出2030愿景规划,主张破除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经济的现状,促进经济发展多元化。但从实际成效看,5年来,沙特阿美公司IPO转型步履蹒跚、吸金成效低于此前市场预期;与此同时,ADNOC由于实施了核心资产的股权转让策略,成功吸引了诸多大型跨国公司作为股权投资者,资源上产将进一步驱动资产利润提升,因而得到各国股东方的一致支持。与此同时,沙特和阿联酋都在积极抢占转型发展先机,力图在后石油时代继续保持中东主导国地位。2021年年初,沙特宣布自2024年1月起拒绝与将中东区域总部设在其他国家的外国公司签订合同,迫使国际投资者在利雅得而不是迪拜或者阿布扎比开店。此外,沙特还瞄准了阿联酋长期主导的物流产业,正在着力将自身打造为中东新枢纽。目前看,阿联酋由于先天占据了地缘和人口红利,后发竞争优势正在凸显。沙特国内居民总数超过2 000万人,人均GDP 2万美元,而阿联酋仅有100万公民,人均GDP 4.3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对190个国家的“商业吸引力”调查,阿联酋排名第16位,而沙特阿拉伯排名落后至第62位[3]。在与阿联酋的经济竞争中,沙特必须为经济全面转型、人口结构调整付出更大成本,以吸引国家发展亟需的海外资金。
外交政策方面,沙特和阿联酋的政策一致性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但近年来双方在多项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战略分歧,屡屡在重大外交政策上分道扬镳。一是在也门问题上,阿联酋最初加入了沙特主导的打击胡塞武装战争,但于2016年6月退出军事行动,并主动担当也门战争调停人,令沙特非常不满。二是卡塔尔问题上,2017年两国联合中东国家对卡塔尔发起经济制裁,2021年年初沙特单方面退出并呼吁结束对卡塔尔的抵制,这次轮到阿联酋否决这一动议,拒绝与卡塔尔进行和解。三是在以色列问题上,2020年8月阿联酋与以色列达成“全面且正式”的和平协议,表示将支持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沙特仍然以中东地区反以桥头堡自居,对阿联酋的外交叛变高度敌视。
综上所述,阿联酋革命性转换能源政策立场,坚定与沙特分庭抗礼,既有当下能源亟需上产的客观诉求,也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性、结构性原因,OPEC组织内部出现战略分歧实属必然。有消息称,早在2019年卡塔尔退出OPEC时,阿联酋就曾动过“退群”念头,近来又开始着手谋划后OPEC时代的独立政策。从中长期看,如果联合增产协议最终难以落地执行,而沙特又拒绝在组织内部作出权势让步,可能进一步刺激两国矛盾发酵,阿联酋随时可能突发性“退群”,从而引发OPEC解体。届时,各大产油国将自行决定产量,不再受任何减产协议束缚,这是国际原油市场供给侧结构性变局的内生动因。
2 结构性变局的外部助力——美国的战略调整
在硬币的另外一面,始终对国际原油供给侧市场虎视眈眈的美国既是OPEC集团内部分歧的制造者,也是整个结构性变局的幕后推手。对于美国而言,页岩油气革命成功推动美国跃身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在总体体量和控制力上仍旧无法与以沙特为核心的OPEC集团抗衡,尽管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施加了强大的地缘影响力,但国际油价波动的主动权仍然牢牢掌握在OPEC集团手中。
这种战略被动在近年来逐步走深,导致双方罅隙不断。“美国增产+OPEC减产”体系确立以来,沙特两次强势挑战美国治下的国际原油供给侧秩序。第一次是在2014年,围绕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美沙大打市场争夺战,国际原油市场严重供大于求,国际油价应声从140美元/桶高位跳水暴跌;第二次是在2020年,沙特阳奉阴违默许“OPEC+”联合减产协议续约失败,美沙原油供给侧再次出现价格冷战,国际油价一路放量下跌至历史性负值。两次背叛过后,美国对沙特的盟友信任与战略耐心大幅衰减,沙特在美国和俄罗斯中间寻求战略平衡、坚决反对与以色列缓和关系、连同人权问题上的失当行径进一步冲击了美国的战略底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将整个中东能源战略全部系于沙特这一单支点的政策合理性。兰德智库、威尔逊中心等智库陆续出具相关战略报告,建议政府重新评估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重新调整针对该地区的战略投资平衡,以保证更加长远的美国战略利益。兰德报告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传统就是与当地盟友合作,通过1~2个盟友支点应来地缘威胁。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双支点”。此前美国在能源政策领域过于依赖沙特单支点,导致战略稳定性始终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调整中东能源战略的时刻[4]。白宫方面,特朗普政府明确表态“我们不会再忍受沙特人”,拜登政府近期频频向沙特隔空喊话要求增加原油供应,均体现了白宫对沙特单支点战略安全感的严重缺失。国会层面,两党保守派议员普遍认为“沙特正在发动经济战争,赤裸裸地向美国进行挑衅”,频频以取消沙特驻军实施威胁,甚至多次动议实施NOPEC法案,已经亮出了最为强力的政策武器。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在OPEC内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与沙特形成竞争博弈关系,这一新支点就是阿联酋。近年来,美国能源部门开始引导美国资本大举进军阿联酋能源市场,BlackRock和KKR全程主导了ADNOC的天然气管道项目,ADNOC的资源上产计划也得到美国股东方的大力支持。这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在于,美国亲自出面牵线,为阿联酋疏通能源外交市场。一方面,推动阿联酋与印度合作,明确表态担保印度作为ADNOC资源买家的合规性,鼓励印度削减沙特原油买单,将市场份额转至阿联酋;印度政府将ADNOC确立为唯一拥有印度战略石油储备租赁权的海外公司,充分凸显了ADNOC在印度石油保障中的重要地位和美国背书的关键作用[5]。另一方面,推动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缓和,并通过以色列提供军事辅助,武装阿联酋的安保能力,目前阿联酋已经拥有中东地区最具战斗力的空军,在军事建制上显著超过沙特。
沙特的式微和阿联酋的崛起是近年来OPEC集团至为关键的结构性变局,标志着美国的中东能源战略正在由单支点转向双支点,其直接影响是显著降低了OPEC组织的凝聚力和合法性。2021年3月,面对持续上涨的原油价格,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利领衔两党参议员小组提出NOPEC法案,这是自2000年以来国会第八次提案动议。以往,这一动议仅能在两党为数不多的持全球主义立场的保守派议员那里得到支持;卡舒吉暗杀事件后,一部分重视人权议题的自由派议员加入提案;油价暴力上涨后,以反建制反垄断为核心标签的激进派议员加入提案,提案背后的议员连线正在逐步壮大。这其中,以刚刚掌权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的决定最为关键,2001年舒默曾经亲自参与发起国会首轮NOPEC提案,并在此后多次支持该提案。近期消息显示,如果油价上涨持续助推美国通货膨胀,舒默将考虑带领民主党主流温和派议员支持NOPEC法案,将纸面威胁真正转为政策动议。如果美国最终下定决心,以双支点彻底取代OPEC集团,国际原油供给侧市场将会出现历史性的结构性变局。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据悉,沙特方面对此早有准备,早在2017年就已经提前针对后OPEC时期的能源政策进行研究,并在讨论政策时避免直接讨论油价,转而采取“维护市场稳定”等不留瑕疵的表述,以防范美国突发推行NOPEC法案留下政策口实[7]。
3 供给侧变局与国际油价趋势研判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原油市场在需求侧遭遇重创,供给侧主导国如何配合需求侧调整原油供给量成为决定国际油价的关键变量,“OPEC+”与美国的博弈关系成为近两年国际油价大落大起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前文分析,这一结构性变局将深刻作用于短中长期国际油价,总体方向判断是推动国际油价短暂触顶后理性回归价格均值。理由如下:
1)供给侧难以遏止供应上涨趋势。按照“OPEC+”联合增产协议,576万桶/日减产总量将在短期内迅速恢复,特别是2022年5月一次性抬升减产基线,将显著改变当下的能源供需结构。伴随北半球原油需求渐入淡季,全球原油库存开始逐步累积,美国政府甚至暗示可能考虑动用紧急石油储备,油价承压转向是结构性必然。这其中,供给侧的最大不确定性来自伊朗,近期美伊双方均频频表态希望加速伊核协定谈判,以帮助伊朗增加原油出口。一旦交易达成,伊朗向国际原油市场提供的供给增量将成为击毁油价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历史对比来看,2016年美国正式解除对伊制裁时,伊朗原油出口仅用时3个月就实现翻倍并回归主流水平。尽管当下伊朗原油外输受限,但近年来伊朗建立了大量的海上浮仓,出口量依然具有短期内迅速提升的能力。伊朗的原油浮仓在2020年底仅有400万桶左右,但在2021年出现了明显增长,目前已经超过1 000万桶,这也反映出伊朗对于2021年内制裁解封的乐观预期。
2)主导国难以维系高额经济成本。近日,美国频频隔空喊话OPEC,要求增产资源以平抑国际油价。按照数据统计,美国汽油价格每上涨1美分,就会增加10亿美元/年的经济运行成本。按照历史数据,布伦特油价超过90美元/桶,相当于美国汽油价格3美元/加仑,美国选民就会感受到成本压力,总统执政就会步入危险区[6]。然而这一次,在布伦特油价仅为75美元/桶状况下,美国7月份汽油价格已经达到3.14美元/加仑,创下2014年10月以来最高值。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生产特定规格汽油导致炼厂成本大幅上涨,成品油价格已经来到了4.35美元/加仑。当下,美国国内要求实施紧缩政策、压制通货膨胀的声浪与日渐涨,美联储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官员倒向紧缩政策立场,为原油价格设置天花板、降低通货膨胀风险源将成为白宫的关键政策举措。
3)技术面难以支撑油价高位运行。从技术面来看,国际油价同样不具备持续性的上涨动力。自2014年国际油价从百元高位跌落以来,过往7年里,油价始终在中低位周期震荡,其中最高点出现在2018年10月份的86.9美元/桶。越是临近这一区域,超买压力愈大,愈将面对强大的下行压力。综合供需结构和技术形态判断,短期内,国际油价大概率将在今年3、4季度利用疫情波动反复高位震荡,并抓住消息面向好契机再次向86.9美元/桶的历史高位发起冲击,形成双头M顶后导入下行区间。中长期看,由于供给侧格局面临结构性调整,供大于求局面将在一定周期内主导国际原油市场,国际油价总体将进入震荡下行区间,65美元/桶、55美元/桶分别是近年来较为重要的两个支撑位,最低可跌至去年年中构筑的45美元/桶支撑位,而后在中位区间震荡。
4 结语
综合以上,“OPEC+”联合增产协议标志着国际原油市场供给侧导向出现重大调整,“沙特+阿联酋”的“双支点”格局既是OPEC组织内部经济竞争与政治分歧的客观必然,也是美国外部施压与离岸平衡的操作使然,其直接后果是OPEC组织凝聚力与影响力的进一步衰退,其根本推动是美国在新一个10年正在酝酿的战略调整。短期内,国际油价仍有震荡上行触顶的市场动力,但着眼中长期来看,全球疫情波动反弹、美国财政政策收紧、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伊朗原油产能释放等均可能成为摧毁油价的最后一根稻草。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正在徐徐展开,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供给侧结构性变局和新能源替代革命的巨大冲击,国际油价很可能会重蹈第二个10年的旧路,历时两年艰难攀至高位,而后再次跌回理性的价格区间,再次迎来的可能是新一轮低油价的漫漫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