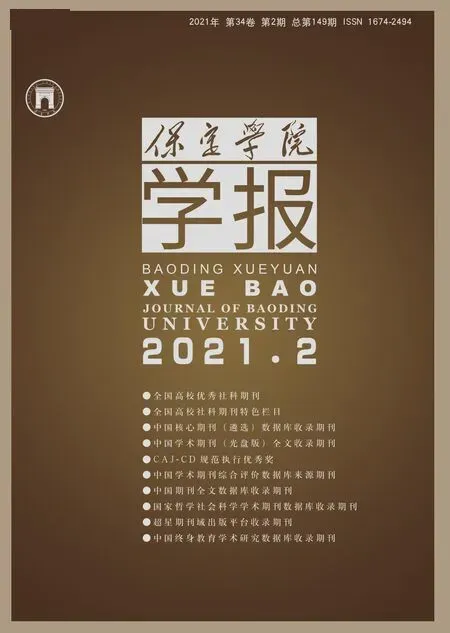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空间性比较
李 娟,钟志强
(1.南昌师范学院 人事处,江西 南昌 330032;2.南昌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六朝赋体文学改变了汉大赋铺陈众多物象的状物方式,转变为集中描绘某类具体中心物象。六朝状物抒情小赋呈现异彩,并逐渐成为赋体文学的主流,可称之为咏物赋。而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存在较为深厚的关联,这也是二者间比较的基础。以状物抒情为特色的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至少在三方面颇为类似,可资比较。第一,六朝时期留下了包括器物、动植物造型的工艺、绘画等艺术品;同时六朝咏物赋中也留存了相当数量对这类艺术品的语言描述,二者存在可比照分析的条件。第二,六朝咏物赋是通过语言状中心物象之形貌,造物艺术则无需语言形式的转化,直接呈现“物”的状貌。虽然状物方式不尽相同,但都是以感官(如视觉)传达,也因之存在比较分析的空间。第三,无论是视听感官传达,还是通过语言艺术,以联想等方式具象化中心物象,其实质都与传统意象思维相关。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在创作思想、艺术思维等方面颇类似,具有可比较的空间。
据统计,以“六朝咏物赋”或“六朝造物艺术”为主题的相关论文、论著约有数十部,但是研究二者间关系的成果则寥寥无几。我们只能跳脱文体或时代的限制来寻找可资借鉴的前人成果。如张自然《汉魏六朝咏琴文学的艺术学解读》[1]于梳理文献基础上,对某具体物类的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学阐释。又如汉画像石与汉赋关系的探讨,有李宏《汉赋与汉代画像石刻》[2]、李立《论汉赋与汉画空间方位叙事艺术》[3]等成果。虽不属于六朝时段的研究,但可为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关系的研究提供思路。上述研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比较研究。我们拟从空间视角、空间结构、空间层次表现三个方面探寻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空间性之间的关联。
一、空间视角:散点透视与中心聚焦
从空间视角来看,六朝造物艺术多应用散点透视法。散点透视法多应用于绘画、建筑群、壁画等空间跨度较大的艺术。“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4]。造物主体普遍接纳、采用这种视角随位置变换而呈现不同景致的表达方式。采用散点透视法表现物象,适用于将原本近大远小的物象处理成平列的同等大小的物象。在壁画、建筑群落、墓葬、绘画等空间跨度较大的艺术品中,其呈现车马、建筑群、人物等物象的方式为运动方向一致地分布于同一水平空间。在这水平空间中,物象间相互联系,画面富有较强的整体性。
如河南邓县出土的武士画像砖(见图1)[5]23,画像砖上造物艺术者并没有突出其中某位武士的形象,而是运动方向一致地水平呈现这列武士的整体画面。散点透视法“更加自由,更能使创作者尽可能地摆脱来自于客观物象外部形色的干扰和制约,也更加适应美术意象的传递和表达”[6]。即便在具体器物、装饰中,创作者也多用这种空间视角进行艺术表达。南京甘家巷1961年出土的“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即可为例。此器物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由瓶颈、瓶口及覆在上面以四角攒尖屋顶组成。屋顶下四角各有狮子头作为立柱。在此之下的瓶颈部分亦有上下两层,每层都雕饰了飞鸟、立熊、胡俑等。下部分是瓶身,在瓶肩、腹部位贴了共计8个胡人骑兽的图案。四隅的狮子、瓶颈雕饰的飞鸟等物象及胡人骑兽图案等都属于散点透视视角下的造物艺术表达。造物者从散点透视的角度将所思所见的物像并置在一个水平面内,这样物象虽多,却能得到一种无障碍的整体即视感。造物艺术主体往往不采取单一、固定的视点,艺术品及其雕饰物象的表现互不重叠阻碍,共同和谐地呈现于同一水平面。

图1 邓县武士画像砖
其实,“散点透视法”曾应用于两汉的赋体文学之创作实践中。汉大赋常通过平面叙述的表达来铺排万物,具有宏富巨丽之整体感。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有“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其中“左与右”的叙述;扬雄《蜀都赋》曰:“东有巴賨……南则有犍潜夷……西有盐泉铁冶……北则有岷山”亦含有平面四方之铺陈叙事的表达。李立将汉赋空间方位叙事分为:“左右”“前后”“南北”“东西”“上下”“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上下”等[3]。
但咏物赋的空间视角也有其自身特性。咏物赋与散体大赋相比,更注重中心物象的描摹。若以造物艺术方式相比拟,六朝咏物赋的空间视角可称为焦点透视法。我们以为,咏物文学界定中“以一物命题”的“一物”,应明确界定为“一种物类”,而不是个体的物,是在同一语境下形成的中心物象。此中心物象包含的数量,可以是一个、两个,也可以是一群[7]38。为了烘托中心物象,与中心物象相关的事物与之共同构成了中心意象。“咏物诗都是围绕中心意象做全力的描摹,因此诗歌中意象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平行,而是主次有别的”[7]293。这段话可用于评价咏物赋的中心意象与次要意象间的关系。因此,与造物艺术中不同,六朝咏物赋全篇都不离中心物象,营造中心意象。如曹植《九华扇赋》曰:
序: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汉桓帝,时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其辞曰:
有神区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对绿水之素波,背玄涧之重深。体虚畅以立干,播翠叶以成林。形五离而九折,蔑牦解而缕分。效虬龙之婉蜒,法红霓之氤氲。抒微妙以历时,结九层之华文。尔乃浸以芷若,拂以江蓠,摇下五香,濯以兰池。因形致好,不常厥仪。方不应矩,圆不中规。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时气清以方厉,纷飘动兮绮纨。[8]2412
曹植《九华扇赋》开篇先指出九华扇前身(原材料)竹的生长环境:生长于高岑之上,面对绿水、素波,而背靠重深之玄涧。这不同寻常的环境能孕育出所咏之物良好的品质。故下文紧接着铺陈其形体与内质之优美。所谓“体虚畅以立干,播翠叶以成林。……摇下五香,濯以兰池”。这是对制作九华扇的竹子优良内质、外形的具体描绘。而下文“因形制好”至结束都是描述九华扇的功用、形态。总体上看,全篇赋作句句都围绕九华扇这个中心物象为主题。文中同时还出现的竹子、高山、绿水、翠叶等次要意象。这些次要意象紧紧围绕九华扇,就如同车轮的辐条从不同的方位指向轴心——中心意象。《九华扇赋》中九华扇的生长环境、内质、外形、功用,甚至因其产生的联想、抒情都不离营造中心意象的目标。在描绘中心意象的过程中,咏物赋作家的空间视角,一般都是由中心物象之外的环境背景回到了物象本身,焦距拉近到“物”的一些局部的特征。因此,咏物文学创作聚焦式的空间视角也因之与偏向于采用散体透视的造物艺术存在差异。
二、空间结构:以小见大与细节传神
六朝造物艺术的创作倾向并非追求外在形貌而是内在的风神。比起形貌无遗的表现手法,内在神韵的传达更需要依靠空间结构的以小见大。如绘画艺术的空间结构表达就常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追求创作主客体在艺术上的完美融合。依据画面有限的空间结构巧妙设计,突显出创作主体的技艺感悟、人生体验、审美感受。现以《世说新语》中顾恺之画人的轶事为例:
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9]387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9]388
两则材料都与顾恺之的绘事相关。第一条是顾恺之为了画裴叔则得其神韵,便为裴“颊上益三毛”。颊上三毛与整个人物画相比,所占比例小,却能“以小见大”,获得欣赏者的接受与肯定——“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第二则材料顾恺之以“画人点睛”的艺术感悟——“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也演绎出了包括绘画艺术在内六朝造物艺术“小中见大”空间结构表现。朱光潜亦认为:“诗的境界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10]50他还说:“本是一刹那,艺术灌注了生命给它,它便成为终古,诗人在一刹那中所心领神会的,便获得一种超时间性的生命,使天下后世人能不断地去心领神会。”[10]50那么,六朝咏物赋在空间结构上的表达是否与造物艺术相同呢?事实上,六朝咏物赋同样也在艺术空间结构中采用小中见大的方式表达创作主体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
就空间的结构而言,“赋”在篇幅比例上有重铺陈轻讽谏的问题。赋的结构一般分为序、正文及篇末三个部分。赋全篇常常大幅铺陈、描摹周遭事物,而赋作篇末点明主旨的部分却往往占比例很小,也因之易被欣赏者所忽视。如《汉书·扬雄传》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11]3575汉赋铺陈出宏大巨丽的赋文,直至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还是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等皆是如此。虽然如此,其最终仍要点出主旨,这个易于被忽视的部分被称为“讽”。比起铺陈描述万事万物的部分,有时“讽”似乎并不重要。扬雄称此空间结构为“劝百讽一”并加以批评。“劝百讽一”固然被后人视为汉赋的弊病,但在儒教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汉代,文艺功用观仍是包括汉赋作者在内的知识阶层所秉持的共识。因此,当世人认为,篇幅宏大的赋作,其最重的其实是占比极小“讽”的部分。故《汉书·司马相如传》云:“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11]2609《文心雕龙·诠赋》也强调大赋讽谕部分的作用。其文曰:“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这种空间结构表达为六朝咏物赋继承并进行普遍实践。如三国殷巨《鲸鱼灯赋》:
横海之鱼,厥号惟鲸。普彼鳞族,莫之与京。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托于金灯。隆脊矜尾,鬐甲舒张。垂首挽视,蟠于华房。状欣欣以竦峙,若将飞而未翔。怀兰膏于胸臆,明制节之谨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于斯器。因绮丽以致用,设机变而罔匮。匪雕文之足玮,差利事之为贵。永作式于将来,跨千载而弗坠。[8]2441
又如晋人傅咸的《烛赋》:
余治狱至长安,在远多怀,与同行夜饮以忘愁。顾帷烛之自焚以致用,亦犹杀身以成仁矣。赋曰:
盖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冥,匪火不彰。故六龙衔烛于北极,九日登曜于扶桑。日中则昃,月亏于望。时迈靡停,昼不干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开之有伤。何远宇之多怀,患冬夜之悠长。独耿耿而不寐,待鸡鸣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转,起燃烛于闲房。扬丹辉之炜烨,炽朱焰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昼,继列景乎朝阳。慨顾景以增叹,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设觞。尔乃延僚属,酌醇清,讲三坟,论五经。高谈既倦,引满行盈。乐饮今夕,实慰我情。[8]2443-2444
六朝咏物赋继承了汉赋铺陈、描摹物象的表现手法。不同于汉赋对万事万物的铺陈,咏物赋的描摹集中于中心物象。殷巨《鲸鱼灯赋》紧紧围绕中心物象——鲸鱼灯的渊源、状貌、功用等展开铺排,仅结尾处“永作式于将来,跨千载而弗坠”等语点明主旨。但需明确的是,恰恰最后一句是创作主体情志的体现,并升华了主题。当然,点睛之笔也不限于曲终奏雅一种方式。如曹植《九华扇赋》、傅咸《烛赋》就是以序文的形式在赋文开始的部分点明主旨。此外,点睛之笔所蕴含的思想也越发多元化,如晋代江逌《扇赋》:
惟羽类之攸出,生东南之遐嵎。育庶族于云梦,散宗俦于具区。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畅,琼泽冰鲜。戢之则藏,奋之则举。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于一掌,引长风乎胸衿。荡烦垢于体外,流妙气于中心。[8]2414-2415
又如梁代刘缓的《照镜赋》:
夜筹已竭,晓钟将绝。窗外明来,帷前影灭。……阶边就水。盘中光映。讶宿粉之犹调,笑残妆之不正。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世间好镜自无多,唯闻一个比姮娥。曾经玉女照,屡被仙人磨。论时不假著,法用自应须。夏天金薄漠,秋日宝茱萸。银缠辟鬼咒,翠厄护身符。空处宜应插,非是畏钗梳。[8]2397
随着儒家思想对士人群体控制力的减弱,文学作品蕴含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六朝咏物赋通过以小见大空间结构表达的主旨思想也历经演变。大致由儒家思想中逐渐融入了玄学感悟以及求形似之文风,甚至是不自觉地带上了宫体色彩。如江逌《扇赋》篇末“荡烦垢于体外,流妙气于中心”就是玄学思想的表达,而刘缓《照镜赋》则是咏物文学日渐追求形似之风与小赋娱情功能思潮的产物。需强调的是,汉末六朝“小”的内容虽历经儒家思想、玄学、宫体娱情等演变,但反而能体现创作主体情志或创作主旨的部分。
综上可知,在空间结构的表现方面,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相似,点明主旨的文本在全篇中比例极低,一般在篇首或篇尾。这种以小见大的空间表现手法在六朝文艺创作中都被接纳与应用。
三、空间层次表现:虚实相交
在空间层次方面,“虚实相交”、有层次地表达作品的艺术性是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的又一个相似之处。“实”指创作主体描摹出的具体物象,“虚”则是文艺作品表现出的空间性倾向或者是一种通过布局隐性呈现空间性的方式。我们仍以六朝画像砖等造物艺术为例。创作主体冲破时空限制,把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物描绘在一水平框架。其构建出了造物艺术“实”的部分。而水平框架内被物象填充的部分外,还留存些许空间,这一留存的间隙,称之为“虚”。由于对预留空间需要艺术直觉的判断与营造技巧,因此虚的部分反而能决定文艺作品的艺术效果。
绘画或画像砖等造物艺术称其为“留白”。“虚实相交”这类空间层次表现方式,不会给人以压抑之感。其描绘物象与布局结构时不填塞过满,在水平面上留出适当的“空白”,帮助欣赏者获得平衡之感。如河南邓县出土的贵妇出游画像砖(见图2)[5]23,画像雕饰了四名女子,这些贵妇之间保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画面上下四方也都与砖的边缘留有间隙,画面整体呈现开阔感。

图2 邓县贵妇出游画像砖
中国画也极为重视“留白”的艺术表现技巧。华琳《南宗抉秘》说:“白,即是纸素之白。凡山石之阳面处,石坡之平面处,及画外之水、天空阔处,云物空明处,水足之杳冥处,树头之虚灵处,以之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皆是此白。夫此白本笔墨所不及,能令为画中之白,并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亦即画外之画也……”[12]“留白”重点并不是表现自己,而是为突出画像中的中心物象。笪重光《画筌》阐述曰:
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成妙境。[13]
水平画面中创作主体的“留白”实质起的是衬托作用,以反衬画面中的重要物象。若不营造好“虚”,就形成不了意境。宗白华也对此解释:“中国画很重视空白。如马远就常常只画一个角落而得名‘马一角’,剩下的并不填实,是海,是天空,却并不感到空。空白处更有意味。中国书家也讲布白,要求‘计白当黑’。中国戏曲舞台上也利用虚空,如‘刁窗’,不用真窗,而用手势配合音乐的节奏来表演,既真实又优美。中国园林建筑更是注重布局空间、处理空间。这些都说明,以虚带实,以实带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结合,这是中国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4]
六朝咏物赋在空间层次表现方面同样既虚实分明又虚实相结合。“实”的部分,造物艺术在填充物的选择方面往往根据画面需要并围绕绘画的主题而非随意择取。而六朝咏物赋的填充手法应用也围绕中心意象的营造而展开。“器物赋咏物的步骤大多先写器物原材料,然后写制作成器的过程,最后再对器物展开描绘。一般说来,大部分器物赋都遵循这个路子”[15]。与六朝绘画艺术于固定空间中填充主题意象相同,六朝咏物赋创作时亦有固定的主题框架。框架填充的第一个部分是原材料及其生长环境。如晋人庾阐《浮查赋》开篇就直接描写原材料巨木:“有幽岩之巨木,邈结根乎千仞。体洪佣以秀直,枕瑰奇而特俊。”接着描述原材料的生长环境:“冠率岭以高栖,独雍容于岩峻。混全朴于不才,倬凌霄而绝韵。故能纡馀盘骨丸,森萧颓靡。阳飘鸠结,华裂水洒。遗美贾于翠璧,蹶悬根于朽壤。”而嵇康的《琴赋》用大篇幅铺陈了制琴之原材料生长环境的优良:
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磪嵬岑嵓。亘岭巉岩,岞崿岖崟。丹崖崄巇,青壁万寻。若乃重增起,偃蹇云覆。……夫所以经营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丽,而足思愿爱乐矣。[8]2606
第二个部分填充的主题就是器物的制作过程。仍以嵇康的《琴赋》为例:
至人摅思,制为雅琴。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倕聘神……伯牙挥手,钟期听声。
赋文中出现制作处理原材料者皆为前代知名工匠,主要是想表达器物质量的优良。赋中出现的工匠有离子、公输般、工倕,而音乐名家则是夔、师襄、伯牙、子期、伶伦、田连等人。自枚乘《七发》开始,赋作中常以古代知名人士或宝物来借指或形容周遭万物。六朝咏物赋继承了这种状物手法,如曹植《宝刀赋》也有“乌获奋椎,欧冶是营”等描述。第三部分填充中心物象“实”部分的描写。这个部分可谓咏物赋最重要的部分。创作主体会从不同的视角,结合周遭时空出现的次要意象,集中描绘中心物象。这是作家高超摹物水平的表现。而在绘画、壁画、画像砖等造物艺术中除了主题式构图法之外,一般各部分画像比例相同,不分主次。而主题式的构图方式更多地是描述事件而非描摹一类中心物象。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虽然每部分出现的洛神形象不尽相同,但创作的主旨在于陈述曹植《洛神赋》的故事线索与主题。总体而言,“留白”不仅需要通过寓虚于实,塑造鲜明的意象,更需经营空白虚处,在艺术上达到“以形传神”的效果。
综合前文,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在文艺创作中的空间视角不尽相同。造物艺术主体往往不采取单一、固定的“散点透视”,物象间互不重叠,和谐呈现于同一水平面。六朝咏物赋家的空间视角则为“中心聚焦式”:由中心物象之外的环境背景回到了物象本身,焦距拉近至“物”的一些局部的特征。而在空间结构与空间层次表现方面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则相近或相同。在空间结构方面,六朝造物艺术的创作倾向并非追求外在形貌而是内在的风神。比起形貌无遗的表现手法,内在神韵的传达更需要依靠空间结构的以小见大。事实上,六朝咏物赋也在艺术空间结构中采用小中见大的方式表达创作主体的审美感受与艺术经验。空间层次表现方面,六朝咏物赋与造物艺术都以“虚实相交”的方式有层次地表达———不仅要正面着力塑造鲜明的意象,更需于空白虚处以形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