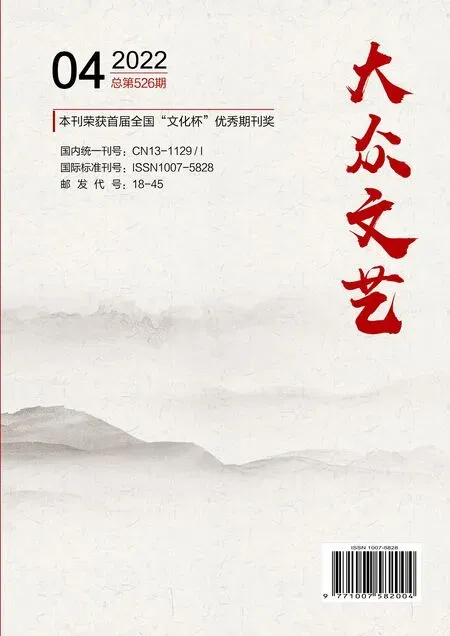小女人的大情怀*
——“思政育人”视角下萧红作品的价值研究
罗秋香 赵文敏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黔南 551300)
现代女作家萧红,创作生涯短暂,却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优秀作品。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自怨自艾,而是从女性作家特殊的艺术体验出发,书写她对女性群体、时代、国家、民族的大情怀,显示其作品丰富的“思政育人”价值。
一、强烈的女性意识
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彰显其强烈的女性意识。《生死场》写了一些生死都如动物一般的女人。王婆闲暇时反复述说自己的命运,跟别人讲起她那从草垛上摔下来死掉的孩子。她与前夫的儿子参加义勇军被枪毙,她闻讯服毒自杀,还没死,丈夫就着急到乱葬岗上去给她找位置,为了使她尽快断气,用扁担使劲压着她。金枝,一个美丽善良、淳朴勤劳的农家女孩。因懵懂与成业偷尝了爱情的禁果,在已怀孕的情况下嫁给成业,成业经常打骂她,甚至在她临产时还粗暴地占有她,导致她早产。女儿生下来后,成业嫌弃女儿吵闹,摔死了女儿。月英患上瘫病,丈夫到处给她请神、烧香,到庙前去给她索药,却不给她请大夫。她躺在床上动不了,让丈夫给她倒杯水,丈夫装作听不见,甚至把枕头换成了砖头。当王婆等来探望她时,她的下身已经腐烂生蛆。月英死后,被草草葬在荒山下。
在《生死场》后,萧红继续创作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中篇小说《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本是一个十二岁天真的小姑娘,只因别人说她不太像个媳妇,婆婆对她昼打夜骂,将她折磨生病后还听信庸医所言用开水洗澡驱邪,生吃全毛鸡,在被开水烫了三次后,凄惨的死去。
在这些作品中,萧红始终关注着女性苦难的生存,她充分意识到了不公平的时代与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在长期的压迫下,她们没有反抗的意识和反抗的权利,也麻木地认可了压迫存在的合理性。萧红“在对女性生命消亡毁灭的叙述中,却毫不心软地剖析着女性自身的病态心理和毒瘤根源,这表现出了萧红独特的、颇具理性的思考角度,她不再认为女性的不幸就是男性的欺压和社会的阶级压迫,而是更关注女性自身愚昧所带来的生存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涉及女性主体意识的层面,这种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二、深刻的国民性批判
萧红深入观察着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显示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同时,她还用女性的视角书写国民性的大主题。
《生死场》写乡民们“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批判直指国民的劣根性。王婆讲到孩子摔死时她并不难过,是因为想到麦子会有好的收成。而当她把自己家养的老马送进屠宰场离开时,是一步三回头,一路哭着回家,令人动容。二里半一生都守着一只山羊。小说就是从他找山羊开始的,他一边心疼得到处寻找,一边跟妻子说“羊丢了就丢了吧!留着它不是好兆相。”这个过程他就像阿Q一样用着精神胜利法。当大多数的村民们开始觉醒准备成立革命军,准备将他的山羊杀来盟誓时,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只公鸡替代山羊,最后全村只有他没有参加盟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自己的山羊,回家去了。无论是王婆还是二里半,他们奉行的不过是在“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在他们看来动物庄稼比人还要有价值,他们因循的规则制度使他们从来不去追问生命的价值意义,使他们愚昧、麻木。小说中写道女人生孩子,五姑姑的姐姐难产丈夫态度极其冷漠,而“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男人”,还像“患病的马一般”。萧红在这部分醒目地写了狗的生产和猪的生产,正是印证“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生育本是新生命的诞生,希望的起始,萧红在这里消解了生育的意义,呈现了一个群体如动物一般对生命的漠视。
《呼兰河传》用了孩子视角,回忆故乡的人物和民情风俗,看似一曲婉转的乡土田园歌谣,实则也是着眼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介绍呼兰河的环境时,作者突出介绍了呼兰河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这个大泥坑淹死过马匹和小孩,当地人也为这个泥坑建言献策,但没有一个人说起要把它填平,生命的逝去成为人们的谈资,为他们无聊的生活增添乐趣。作者借大泥坑呈现了他们的精神和生存状态:空虚单调、守旧封闭。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命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小团圆媳妇被旁人指指点点,婆婆对她进行“管教”,最后她被人们的麻木无知折磨死了。王大姑娘还没有出嫁时,人们对她是赞不绝口。当她嫁给了磨倌冯歪嘴子后,人们开始用最恶毒的话来诋毁她,她在人们的恶言白眼中难产死去。这些触目惊心的惨剧,并没有唤醒麻木人们,小团圆媳妇死后还是他们的谈资,说她的鬼混变成了大白兔,隔三岔五就到桥下哭泣;王大姑娘死了,想到冯歪嘴子家破人亡,他们又开始兴致勃勃去探听冯家的新情况。
如果说 “生死场”里的乡民和呼兰河的众生,他们的病态是由于封建保守的文化环境造就的,那么受过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又如何呢?在小说《马伯乐》里萧红刻画了一个敏感懦弱、自私平庸、逃避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伯乐出生在一个经济富足的家庭,可这个家庭充满了虚伪。马伯乐虽对这个家庭有诸多不满,但又无法脱离家庭。小说里写得最生动的就是他的“逃跑哲学”,想逃离家庭的腐朽就到上海去上大学,无奈却没有考上;想逃离父亲的经济控制,就到上海开书店;想逃离家人的鄙视,就以战争为借口,丢下妻儿父母自己一人逃到了上海。五四新思想影响了那个时代的青年,成为青年的精神向导。但也有很多像马伯乐这样的青年,他们对现实有很多的不满,也把国家民族挂在嘴边,却从不付诸行动,也没有行动的能力。作者就这样用幽默讽刺的笔调呈现了一个暴露现代知识分子弱点的典型。
萧红从鲁迅手里接过了国民性批判大旗,在她笔下从底层农村妇女到城市知识分子,骨髓里充斥着顽疾,她对国民性问题的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当时很多男性作家都无法匹敌的。
三、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
萧红是一个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家,她对国民性问题有自己认识。同时,战争中的颠沛流离,激起了她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使她的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情怀。
《生死场》中把麦子收成看得比孩子的命更重的王婆,最后支持自己的女儿参加了革命军,她女儿很快就牺牲了,她听到消息很是悲痛,却决绝地说道“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啊……比当日本狗的奴隶活着强得多哪!”这个历经苦难的女人,就像个战士,苦难还是没有将她打倒,反而将她推向觉醒。把羊看得比亡国还重的二里半,在亲人们都死去后,把心爱的山羊托付给了赵三,参加了革命军,从一个本分农民蜕变成了一个端着枪打鬼子的反抗者。赵三年轻时跟李青山一起组成“镰刀会”用来对抗地主涨租,之后失手打死小偷入狱,出来后变得胆小谨慎。当日本人的侵略愈加猖狂,他也走上反抗的道路。先是鼓励自己的儿子“年轻人应该有些胆量。”之后“逢人便讲亡国,救国,义勇军,革命军……”在盟誓大会上他说道“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轻,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很显然这一番动人的发言,萧红是把抗日精神灌输给了当时的读者,不可否认这样的作品对当时抗日救亡的作用,甚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北中国》讲了耿大先生夫妇苦等离家抗日的儿子归来的故事。写这篇小说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此时中国外患加内忧,标题“北中国”点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一个“北”字将完整的中国分开,中国不是统一中国,这不仅是外部入侵带来的,也是中国人自己造成的,这是“一篇应时的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分裂的政治性文章”,流露出作者对国家现状和命运深深的忧虑。小说开篇呈现家国衰败的景象,能证明“门第的久远和光荣”的大树要被砍掉,象征着家族永续繁荣的思想也将崩溃瓦解。大树倒下了,鸟窝随着倒在雪地上,鸟也没有家了,写老管家总感觉“这大少爷的走掉,总觉得是风去楼空,或者是凄凉的家败人亡的感觉”,从侧面反映着耿家这个小家的衰败。家已经衰败,国又逢难,才有小说中从未露面的耿家大少爷,那个懂得规矩礼法,又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青年踏上救国救亡的道路,最终献上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写这篇小说时国家正逢内忧外困,自己又贫病交加,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可小说却是表现萧红“对外族入侵导致家国分裂、传统断裂的悲恸”,和她深深的家国情怀,而不是她个人悲惨经历的投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众多的男性作家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萧红却用她的笔深刻地书写国民、时代与家国,展示着宏大的时代命题,传递着小女人的大情怀,这种可贵的品质无疑不是历经她打磨仍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注释
:①安晓情.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鸭绿江(下半月刊),2014(8):58.
②萧红著.萧红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7,67,20,41,43.
③萧红著.萧红小说名篇[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43.
④萧红著.萧红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64,60,63,66.
⑤(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58.
⑥洪珊.家国情怀的悲凉诗情——论萧红短篇小说《北中国》的三重悲剧冲突[J].南方文坛,2011(4):72.
⑦萧红著.萧红小说[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257.
⑧洪珊.家国情怀的悲凉诗情——论萧红短篇小说《北中国》的三重悲剧冲突[J].南方文坛,201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