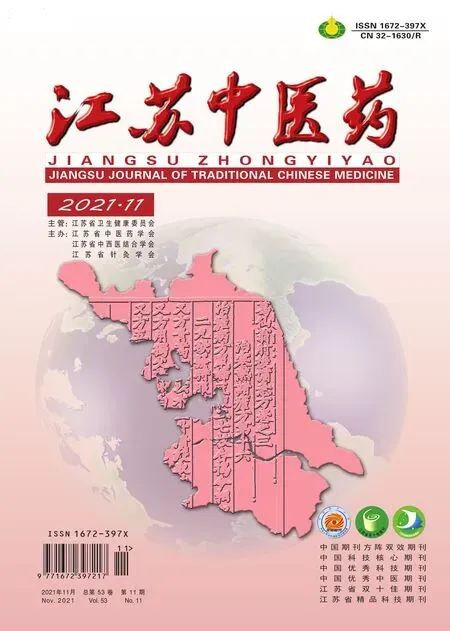新安医家从脾胃论治痹证特色
叶冠成 赵 歆 张泽涵 陈佳祺 王凤龙 马姝楠 张春艳
(1.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 100029;2.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100010;4.黄山市人民医院,安徽黄山 245000;5.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 100078)
痹证是当前一种较为常见的风湿类疾病,与西医的类风湿关节炎等有着相似之处[1]。该病往往以肢体关节疼痛、酸楚、麻木、重着以及活动障碍为主要症状,病程较长,且缠绵难愈容易复发,给患者的生活带来各种不便[2]。中医对痹证有着丰富的认识,早在《黄帝内经》中便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说法,认为风寒湿等外邪是痹证发病的病因之一。新安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中有着浓郁地域特色的学术流派,发源于古徽州地区。新安医学作为徽学十二大派之一,根植于辉煌灿烂的徽文化,起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医家辈出,学术争鸣活跃,自古便有“天下名医出新安”的美誉。痹证的发病往往包含不通则痛与不荣则痛两个方面,均与脾胃关系密切。且脾胃为后天之本,正虚往往可涉及脾胃,且痹证患者因病程较长需长期服用中西药物,最易因药毒而伤及脾胃,脾胃伤则对痹证康复雪上加霜。而当前对于痹证的论治多从祛邪和培补肝肾入手,涉及脾胃较少,新安医家对脾胃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本文从脾胃入手,总结新安医家论治痹证的思路,以期为痹证的治疗提供借鉴。
1 新安医家从脾胃论治痹证之理论依据
1.1 化生气血,濡养骨节 脾在体合肉,主四肢,因此四肢关节之疾患可责之于脾。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所摄入之水谷精微唯有经脾胃的枢轴之功,配合其他脏腑的相辅相成之力,方可化生气血,濡养全身,中气调和,五脏安和。新安医家罗周彦认为“脾胃之谷气实根于先天无形之阴阳,而更为化生乎后天有形之气血”,强调脾胃元气在疾病发病与预后中的重要性,即脾旺不受邪。脾胃虚损与痹证,二者有内在的关联。痹证往往以疼痛为主要症状,脾胃不足则全身气血生化不足,亦无以借脾胃运化之力而输布全身以濡养四肢关节,故其疼痛表现为“不荣则痛”。新安医家在痹证论治中重视固本培元,固本乃固肾这一先天之本,培元乃培脾胃后天之元。痹证的治疗,也多遵循固本培元理论,如固本培元法创始人汪机认为“内因之症,多属脾胃虚弱”,其再传弟子孙一奎认为“胃厚脾充,四肢健运”。新安医家吴谦主编的《医宗金鉴》中也有言:“所谓虚者,为荣卫、阴阳、气血、精神、津液、骨髓不足。损为皮、脉、肉、筋、骨、肺、心、脾、肝肾消损”,“虚损之人,虚损日久,流连不愈,而成劳”。吴谦将痹证的转化细化至各个脏腑,六极作为虚劳的严重表现,其中骨极、筋极症状与痹证非常接近,可认为是痹证发展的极端阶段与终末阶段[3]。脾胃不足,气血虚损,不荣则痛,可知此类痹证有本虚标实之性,为此应以扶正为本、祛邪为标进行治疗。
1.2 脾运痰瘀,脉通痹除 脾胃居中焦,主运化。若脾胃升降功能异常,则运化失职,全身水液无以代谢,因而停聚于体内,聚湿生痰。痰浊内生,亦可阻滞气机,气机调达不利,气机郁滞亦可阻滞气血和水液的运行,水湿不运,聚而化生痰湿,形成痰核、肿块等病理产物,此谓“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有形之实邪阻滞脏腑经络,影响四肢部位气血的运行,不通则痛,故出现肢体活动不利、酸胀麻木、疼痛等痹证之症状。正如汪机《推求师意》言:“由风寒湿气,则血凝涩不得流通,关节诸筋无以滋养,真邪相搏,历节痛者……或脾胃之湿淫泆,流于四藏筋骨皮肉血脉之间者,大概湿主痞塞,以故所受之藏气涩,不得疏通,故本藏之病因而发焉。其筋骨皮肉血脉受之,则发为痿痹”[4]560,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亦言:“其实痹者闭而不通之谓也,正气为邪所阻,脏腑经络不能畅达……致湿痰浊血流注凝涩而得之。”此外,脾运化功能正常,则可运化饮食中的水谷精微,使之转输于全身,以满足人体正常的生理需求,肌肉关节的濡养亦需要脾胃运化之水谷精微,恢复脾胃运化之功,不仅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水饮痰湿瘀血,还可为本已损伤的骨节提供水谷的濡养以促进其恢复,使骨节活动自如,屈伸有力,如李中梓《医宗必读》曰:“治着痹者,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亦不可缺,大抵参以补脾补气之剂,盖土强可以胜湿。”风寒湿均可致痹,其中又以湿邪最为缠绵难愈,祛湿之要,当以健脾为釜底抽薪之法。
1.3 营卫生化,卫外为固 脾胃之水谷精微化生营卫气血,如汪机言“营气、卫气皆藉水谷而生”。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气行于血脉,濡养脏腑,卫气则“温分肉,肥腠理”。若脾胃不足,气血营卫生化乏源。营血不足,则血虚气滞,气血运行受阻,骨节肌肉失于濡养温煦,从而发生痹证,出现骨骼关节疼痛。卫气不足,则机体卫外功能减弱,腠理不固,风寒湿邪更易侵犯人体,从而因外邪侵袭而发为痹。《症因脉治·痹证论》言:“痹之因,因气血不足,卫外之阳不固,皮毛空疏,腠理疏松,邪袭之,或露卧当风,冲寒冒雨,痹作矣”,新安医家罗美《内经博议》言“营卫之气不行以致肌绝,则痹聚在脾”,可见气血营卫之虚损乃痹证的一大重要成因。营卫二气均来自脾胃元气,脾胃功能恢复,则营卫生化无穷,可抵御外邪之侵,鼓舞内在邪气排出体外,如汪机所言:“脾胃无伤,则水谷可入,而营卫有所资,元气有所助,病亦不生,邪亦可除矣。”卫为阳,营为阴,脾胃强健则营卫生化有源,进而营卫调和,全身阴平阳秘,诸脏腑骨节得以濡养,机体卫外功能恢复,使外邪难以进犯人体,则各类痹证之症状得以缓解。
2 新安医家从脾胃论治痹证之临床特色
2.1 培元护本,正盛托邪 如汪机所言:“诸病亦多生于脾胃”,可知脾胃不足、中焦亏虚是各类疾病的重要病机,为此在治疗层面,新安医家以培补脾胃元气为纲,力求通过强健脾胃,进而培育正气,以期实现“脾旺不受邪”。程杏轩《杏轩医案》[5]168言:“四肢皆禀气于胃,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脾强胃健,四肢得禀谷气,脉道流行,自能充肤肌肉。”故程氏治“王氏妇痹证”一案,前医以风药治之无效,程氏认为患者病程日久,久病体虚,过服风药导致“肢挛头晕”,因此需要先培补中下二焦,故以十全大补汤治疗,随后症状缓解。程氏在此使用的十全大补汤以四君子汤和四物汤为底,调脾胃与调血双管齐下,对于痹证的治疗,既含“治风先治血”之理,又有补足气血生化之源之意,方中黄芪既可健脾,又是托里要药,肉桂则温补下元,故全方意在扶正祛邪[5]58。又如《医宗金鉴》以五痹汤、黄芪益气汤等治疗,方中以黄芪、白术、炙甘草等补益中焦之品为君,佐以羌活、川芎等祛风散邪之药,其意在先补已受损之脾元,脾胃健运方可气充血足,正气旺盛,从而利用强盛的正气配合祛邪之药托邪外出,此谓“补托”。若脾胃虚损程度不重,为虚实夹杂之性,则以扶正祛邪并重,此谓“解托”。在处方用药上,解托法多加升麻、葛根等升提之药,使邪得以外出,同时不仅仅局限于补,而是以参芪之物培补中焦元气,安和中州,托邪外出。二者虽有差异,但是其本均在调补中焦,寓脾旺不受邪之意。
2.2 健脾利湿,化瘀通痹 《脾胃论》言:“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则骨乏无力,是为骨蚀,令人骨髓空虚,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叠,此阴盛阳虚之证”,可知水泛之本在于土虚不能制水。故在治疗湿邪导致的痹证时,新安医家亦用薏苡仁汤等化湿之方。该方重用薏苡仁为君,利用薏苡仁健脾利水之性祛除经络骨节之水湿。如已故当代新安名家、国医大师李济仁教授认为薏苡仁有健脾利湿、疏利经筋之双重功效,故在使用过程中往往生炒薏苡仁合用[6]。此外新安医家常合苍术共奏健脾之功,培土以制水,土强则胜湿,如汪机言:“如因湿胜,宜以苍术、白术为主治”。孙一奎则创温经除湿汤论治湿胜之著痹,方中以参芪之物健运脾胃,使土强湿邪自去,并佐猪苓、苍术、白术、泽泻以利水渗湿,该方被孙氏誉为“治肢节沉重,疼痛无力之圣药也”[7]。孙一奎对于痰湿所致之痹,多以二陈汤化裁治疗,常重用苍术、白术等健脾祛湿之药,并佐竹沥化痰、陈皮行气,使气行则水行,对于痹证之“不通则痛”往往疗效显著。痹证之瘀阻乃气血运行不畅,故化瘀之法在通利脉道骨节,脾主运化,故瘀阻之本亦在脾虚。脾气健运,则气血运行通利,水湿得以代谢,瘀阻自化。故孙一奎治血瘀所致之痛痹时,创四物苍术各半汤、活血丹等方,如活血丹治“遍身骨节疼痛如神”,方中加健脾祛湿之苍术、白术、人参,均含强脾胃以运血之理。此外新安医家往往针对相应的症状,在健脾利湿的同时注意清利湿热。如孙一奎治一左膝肿痛医案,孙氏认为肿属湿,痛属火,为此病机在于湿热凝于经络,流于下部,故不可单用健脾利湿之药,而是加入黄柏、苍术、木通等清利湿热之品,以疏利中下二焦。由此观之,湿邪郁久而化热,故湿胜之痹在治疗中需审查病机,少佐清利湿热之药,有时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2.3 善用参芪,调和营卫 营卫之气来源于脾胃,营卫失和被认为是痹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仲景桂枝汤可谓调和营卫之要方,方中桂枝芍药并用以和营卫,大枣与炙甘草补益中焦,使营卫生化得以源泉不竭。故历代医家通常根据不同的证型,用桂枝汤化裁以调和营卫。如治疗虚实错杂、寒热并见之痹证,可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对于气血两虚之痹证,则以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此方用于内有虚损、外邪乘虚而入之痹,方中重用黄芪以卫外固表、脾肺双补,合桂枝汤以和营卫。新安医家汪机认为参芪之物最善补营,又为“补脾胃之圣药”,汪机在《石山医案·营卫论》中所言“是知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可见人身之虚皆阴虚也”[4]66。参芪均作用于中焦脾胃,为培补中焦之药,脾胃乃气血营卫生化之源,中焦健运则气血营卫生化源泉不竭,营卫调和则营血可濡养脏腑骨节,卫气固护肌表可防邪之深入,进而痹证之“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均可有效缓解。参芪补气,即补营气,亦即补营。参芪性味甘温,甘能生血,温能补阳;血为阴,生血即是补营阴;补阳即补气,气为阳,为此补气即补营之阳[8],如汪机所言:“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阳生阴长,义本诸此。”阴阳调和,则全身状态无偏颇之象,气血运行有序,全身脏腑各司其职,有助于痹证患者之预后。故汪机对于痹证的治疗,创黄芪酒、人参益气汤和冲和补气汤等方,此三方均用参芪以补中益气,并且于黄芪酒中,汪机特加入肉桂以和营卫通血脉。由此观之,营卫冲和,则气血运行得以调达通畅,而痹证的重要病机则在于气血运行受阻,故汪机论治痹证在培补脾胃,于调和营卫的前提下少佐活血温通之品,往往疗效显著。
3 验案举隅
杨某,女,66岁。2020年8月21日初诊。
主诉:关节、肌肉疼痛2年余。患者自诉2018年无明显诱因出现四肢近端肌肉疼痛、乏力,伴多关节痛,于外院化验血沉增快,并行其他风湿相关化验后予激素及甲氨蝶呤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缓解。2020年5月以来患者出现四肢多关节痛,累及双肩、双肘、双手指近端指间关节、掌指关节、双髋、双膝,晨僵大于1 h,颈、肩胛带及臀部肢带肌轻度疼痛,乏力明显,偶有腹痛腹胀,无头痛及视力下降,无口腔溃疡,无结节红斑及手指遇冷变白变紫。近3个月体重下降约5 kg,情绪抑郁,纳少,眠可,二便调。舌暗淡、苔白腻,脉沉弱。因门诊治疗效果不佳且病程较长,故于8月31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住院治疗。辅助检查:C反应蛋白(CRP)10.8 mg/L,血沉(ESR)48 mm/h。西医诊断: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诊断:痹证(脾肾亏虚,痰瘀阻络)。治以健脾益肾,化痰通络。予半夏厚朴汤合薏苡仁汤化裁。处方:
厚朴9 g,清半夏9 g,茯苓45 g,炒薏苡仁30 g,炒 白 术20 g,泽 泻15 g,桂 枝9 g,白 芍20 g,当 归10 g,杜仲10 g,巴戟天10 g,千年健15 g,怀牛膝12 g,焦麦芽10 g,焦山楂10 g,柴胡12 g。10剂。水煎,每日1剂分2次服。
2020年9月7日二诊:患者自诉关节肌肉疼痛程度减轻,仍有纳差,以初诊方加党参15 g、生黄芪30 g,继服5剂后症状缓解,后以补脾益肾、化痰通络为法,予出院带药。
按:患者老年女性,以关节、肌肉疼痛2年余为主诉。痹证以关节、肌肉等部位的疼痛为主症,并伴随活动障碍,观其症状,结合舌脉和实验室检查可辨病为痹证,病性属本虚标实。痹证病程日久,服大量免疫抑制剂等西药后往往伤及脾胃,导致脾胃亏虚,此为本虚。脾虚则运化不利,全身气血水运行受阻,气滞水停则化为痰饮,气滞血阻则发为血瘀,痰瘀互结于骨节,不通则痛,此为标实之象。脾胃不足则气血生化乏源,营卫虚滞。营卫不足,则无以濡养全身经络脏腑,不荣则痛。阳明多气多血,故调补脾胃则得以补足气血,气血充盛则全身肌肉骨节得以濡养,痹痛好转,然患者年老体弱,久病及肾,故不可仅局限于脾胃二脏,亦应兼顾肝肾,故选薏苡仁汤为底方加减治疗。方中炒薏苡仁利水渗湿健脾,伍大剂茯苓、泽泻、炒白术,共奏健脾利水之功,脾运则水湿自化,寓汪机痹证“补养气血为本,疏理邪气为标”之治疗大法。又合桂枝以温通经脉、温阳化气,取桂枝离照当空之意,以桂枝温煦久积之水湿。以杜仲、巴戟天、千年健、怀牛膝等温肾之药,补益下焦,仿孙一奎元气应是肾间动气,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根之意。正如其所言“赖此动气为生生不息之根,有是动则生,无是动则呼吸绝而物化矣”,通过温肾补阳以壮全身之阳,以固护下焦为法得以培元护本,培补先天肾元以固本培元,实为推动肾间动气,激发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从而使脾胃枢轴功能恢复,脾胃得以运化体内瘀阻之痰饮水湿。由于患者久病情绪抑郁,故合柴胡、厚朴、清半夏以疏肝理气、降气化痰,调达一身气机。脾虚之人,往往难以耐受所入之食,故少佐焦麦芽、焦山楂等和胃消食之药,保护本已虚弱之脾胃,并助消食化积,避免食积化热,积而生痰湿。二诊时因患者于住院期间大量使用免疫抑制剂和糖皮质激素等西药,对脾胃损伤较大,纳差等症状缓解较慢,故加参芪之物,仿汪机之意以增强培补脾胃之力,出院带药仍应重视调补脾胃,意在健运中焦,调和营卫,化痰通络。总而言之,全方以健脾为根本大法,使脾胃安和,痰瘀自化,痹痛好转。
4 结语
中医风湿病学滥觞于仲景,仲景《金匮要略》开中医风湿病辨证论治之先河,后世医家对于痹证的各类治法进行了不懈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痹证通常病程日久,病情缠绵难愈,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身体与心理痛苦。若单纯通过经脉瘀阻为法论治痹证,则必用大量虫类药以搜风通络,或以活血化瘀药攻伐气血,久病之人往往纳食较差,脾胃虚弱,此类攻伐之品对本已虚衰之脾胃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为此从脾胃论治具有独到的意义与价值。此外饮食与脾胃功能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不少人平素嗜食肥甘厚味,或过量饮酒,使得脾胃受损进而痰浊湿热自生,并成为痹证发作的病理因素,出现“不通则痛”。胃气衰败,脾土受损,脾胃元气亏虚则百脉失养,此谓“不荣则痛”。为此在治疗上应釜底抽薪,以调和脾胃为大法,以求从本清除此类病理产物。新安医家从脾胃论治,维护人体生命之本,安和五脏,调理中焦,对痹证的治疗不离固本培元大法,其意不仅在于强健脾胃以运化停滞之痰饮和瘀血,使脏腑骨节脉道气血运行有序;亦在于调和全身营卫,使水谷精微得以滋润濡养骨节,并使人体正气充足,风寒湿三气无以进犯人体。这样的治则治法在当今临床实践中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对于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所致之痹证疼痛,均有事半功倍之效。未来应对从脾胃论治痹证的临床经验进行深入地研究,以期拓展痹证的病机认识,并为痹证的治疗提供思路借鉴与基础研究,提升对各类风湿性疾病的治疗水平,并促进患者的后期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