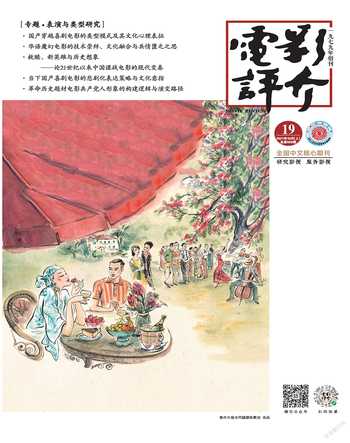儿童电影《小小港湾》的精神奇旅、想象视角与多重现实
王砾玉 郭威
《小小港湾》(伊韦塔·格罗福娃,2020)是斯洛伐克女性导演伊韦塔·格罗福娃(Iveta Grófová)的第二部作品,也是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奖的获奖作品。本片讲述了两个原生家庭生活不幸的孩子展开的一场生存的冒险,在充满想象力的奇妙旅程和残酷的现实中,导演试图寻找一条可以供纯真生命之舟停泊的港湾。
一、主体层面上充满想象力的精神奇旅
《小小港湾》改编自斯洛伐克女作家莫尼奇·科姆帕尼科维(Monika Kompaníková)由真实事件启发所创作的小说《第五艘船》。在原著涉及许多主题、甚至有几条叙事线索的前提下,导演伊韦塔·格罗福娃为了使电影叙事更加清晰,和编剧马雷克·莱斯卡克(Marek Lescák)一起决定把重点放在女主角亚拉和她的小伙伴克里斯蒂安两人的“冒险”故事上。虽然是一部以儿童为主要角色,并以儿童视角叙事的冒险影片,但《小小港湾》的故事全然并非迪士尼影片中那般故事结构精巧的欢乐成长故事,而是关乎爱的缺失、寻找与尽力补偿的一场精神的奇妙旅程。在亚拉的视角中,世界时而充满着色彩明丽的幻想,时而返回冷漠乏味的现实。这是一部很安静的电影,导演以细腻的情感基调、自然舒缓的叙事节奏、轻柔克制的配乐和充满视觉张力的画面增强了影片的整体艺术感染力。小女孩亚拉在外婆病逝、母亲离家出走后到车站寻找母亲,却意外捡到另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遗弃的一对双胞胎。她无可自制地对可爱的婴儿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情,并与玩伴男孩克里斯蒂安一起开始扮演起父母的角色,尽力照顾婴儿的生活。片尾处,克里斯蒂安的父母与警察一起搜查到4人居住的小屋,小屋却一反全片的写实风格,以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揭示这段伊甸园生活的幻灭:抱着婴儿的亚拉对克里斯蒂安说“我们出发吧”,两人随后驾驶着化为帆船的小屋滑下山坡,消失在蓝色的湖泊中。这一充满诗意与虚幻感的开放式结局处理,揭示了亚拉与克里斯蒂安幸福生活的脆弱与永恒,在予人深意的同时也引发观者更轻灵的想象和思考。当大人们牵着搜救犬、手拿工具步步逼近两人的“秘密基地”时,这片乐土最终必将如短暂的快乐时光一般消逝,克里斯蒂安将被父母带回毫无人情味的家庭,严加看管;亚拉也必将被夺走对两个婴儿的“监护权”,两人重新回到各自的孤独和与世隔绝之中。尽管如此,在外婆留下的花园中秘密组成的“小家庭”却是两个孩子变故发生前的伊甸园。尽管他们经济窘迫、毫无抚养婴儿的经验与金钱,却无私地奉献自己全部的爱,并通过这种消解孤独、令人圆满的力量纠正成人世界的错误,以游戏式和角色扮演般的“过家家”游戏,为自己冒险创造出一个在幼稚、脆弱、但对儿童来说已经足够完满的家庭。爱与孤独构成了影片的主要情感线索与叙事主题。亚拉与克里斯蒂安用离家出走、带着婴儿游荡在外来逃避充满孤独感原生家庭,并以想象性的家庭关系重塑自身“爱”与“被爱”的能力,试图以对“爱”的寻找与创造填补孤独与爱的缺失。
比起类型化的故事片,《小小港湾》以一种更为纯粹和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平等地探究儿童的心理世界。摇晃的手持摄影、景深长镜头与低高度平拍视角为观众展示真实的儿童生活,低饱和度的色彩基调为影片带来一种克制的忧郁感;同时,两位主人公又作为影片中生动鲜活、灵动善良的存在冲淡了沉重主题的忧郁感,为残酷的生活加上了一抹天真和自然的亮色。“真正的素材不仅是在明白说出来的范围的生活,而且是深藏在下面的生活——深深透过外部存在的表层的一系列印象和表现。”[1]《小小港湾》结合了儿童对世界的奇想与世界本身的冷漠,许多场景都试图在其描绘的客观情景外唤起观众主观心理与情感感受。在角色设定上,年仅10岁的小女孩亚拉与卧病在床的外婆艾琳娜、年轻不负责任的妈妈露西娅共同生活。外婆艾琳娜在被丈夫抛弃后终生郁郁寡欢,对女儿与外孙女都无比暴戾和冷漠;露西娅在缺失关爱的家庭中长大后,也宿命般地走上了艾琳娜的老路,整日将亚拉丢弃在家,自己混迹于不同的声色场中。女主角亚拉在冷漠、脏乱、凌乱的原生家庭中难以得到应有的关爱。影片中有一幕是母亲露西娅在挣扎着起床后与亚拉面面相觑,她不知道作为母亲如何面对女儿的目光,突然无聊地转起了料理台上平放的一柄餐刀。片刻后,刀尖在对准一瓶胡椒时停下,露西娅竟然笑着将这瓶胡椒粉倒入嘴里。这一幕实际展现的动作与人物非常简单:转刀子的动作本来只是露西娅的一时兴起,这位从未尽到责任的母亲带着想要逗逗自己孩子的笑容随手转了手边最近的东西,然后恶作剧般地吃下了胡椒粉;但在影片的精神层面上,这却是一次由成年人诱导未成年人进行的奇异的、未知的冒险。默默观察和模仿母亲的亚拉很快也开始玩这样的游戏,她和自己的玩具小马进行了同样的游戏,并假装“吃下”了石头。这样恶作剧般危险又无趣的游戏后预示着这位影片中成年人的爱是一种不确定的、随波逐流的爱,也象征着影片中的情感纽带,就如用刀子轉盘游戏一样不可预知、充满命运的悲剧性,但似乎又因此而有趣。《小小港湾》摒弃了确定性和类型化的叙事法则,采取了一种自然、纪实却充满感性的叙事方式,引导观众跟随主人公随波逐流般的命运,反思自己的选择与生活。
二、故事层面上儿童电影提供的想象视角
“儿童电影承载着用影像表达儿童世界的艺术使命,儿童世界与儿童电影本质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是透视儿童电影基本精神与艺术品质的理论基点。”[2]许多以儿童为主角的儿童片都会采用儿童视角对现实主义题材加以展现,包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阿巴斯·基阿鲁斯塔米,1987)、《天堂的孩子》(马基德·马基迪,1999)、《无人知晓》(是枝裕和,2004)、《何以为家》(娜丁·拉巴基,2018)等经典影片。在同类影片选择以儿童的生活视角再现现实生活时,一度位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幻想元素却在《小小港湾》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呈现。《小小港湾》对孩子日常生活的描述中贯穿女主角亚拉对世界的想象,以细腻而诗意化的视听语言将现实题材儿童电影中少见的浪漫与想象还给这个世界,为人们构筑了在严酷现实中一个美好却令人悲哀不已的儿童世界。在冷漠与残忍的世事间,亚拉与克里斯蒂安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为孤独的自我在自然界中寻找伙伴,从刺猬、到小马玩具、再到抚养弃婴,影片在以第三人称视角描述亚拉生活的客观情景之外,也特别为亚拉充满想象力的儿童视点留下了叙事空间,展现了她从简单的自由联想到富有创造性想象的想象发展过程。
想象是《小小港湾》中的孩子看待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并与周围的世界沟通的重要方式。在外婆病逝后,她留下的废弃花园变成孩子们的秘密花园与“小小港湾”,亚拉喜欢在那间屋子里玩角色扮演的游戏。一开始,亚拉扮演与母亲同名的“妈妈”,让玩具小马扮演“女儿”,她学着母亲的样子对着玩具小马说:“别叫我妈妈,叫我露西娅,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露西娅以敏感、开放、不带防备的心态感受并记忆着周围人的一切细微情绪,这句母亲对亚拉说了无数遍的话,与话语中的冷漠、无视、孤独和谎言一起被亚拉复述给了想象中的“女儿”。在亚拉的家庭中,以个人享乐主义为人生准则的露西娅过着充满随机性和未知的生活,这直接导致了亚拉的悲剧。但露西娅歇斯底里、毫无底线的生存状态中,也压抑着对爱的渴望与失落。失败的亲子关系悲剧性地在一代又一代身上重演:外祖母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在母亲与女儿身上重演,而亚拉以毫无察觉的方式复制着这一悲剧,并深陷其中,以此来慰藉现实中母亲一次又一次的缺席与无视。在没有生命的玩具小马之后,又出现了身为“女儿替代品”的宠物刺猬及双胞胎婴儿,这些越来越鲜活生动、越来越与自身相像的人和动物进一步实现了亚拉在想象中重造“家庭”的愿望。但这些携带着乌托邦或伊甸园性质的情感寄托,最终一个个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与终结:亚拉在陪着小马玩过“转刀子”游戏之后产生厌烦之情,将其遗弃;邻居男孩克里斯蒂安捡到的小刺猬栖身在一个小小的纸箱里,被亚拉偷偷藏在房间中,在母亲的朋友通宵达旦地狂欢时刺猬被发现,然后插满点燃的蜡烛戏弄,最后被母亲勒令丢出房间;两个孩子“抚养”婴儿的冒险并未给出现实意义上的结局,但片尾处却将儿童特有的想象视角升高至叙事主视角的程度,在最大的故事困境出现时不刻意渲染苦痛的情感,反而以高调情感的与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镜头的代替,让影片的情感在“幻境”中得到升华,成为永恒。
亚拉与克里斯蒂安在“过家家”的游戏中尽职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梦想着醒来之后成为一个大人——“我能说不,能够捍卫自己,能够做决定”,这一心理实际上是对渴望家庭温暖与母爱心态的折射。然而从玩具小马到人类婴儿,主体的需要与他者的要求之间总是有一道裂隙,亚拉永远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只能在欠缺与匮乏的深渊中挣扎着,只能不停地去需要。从始至终,亚拉所需要的不只是即刻和当下的满足,而是无条件的绝对满足,是来自他者(母亲或家庭)的、无条件的爱。某一具体需要的背后其实隐含一个絕对需要,那就是对无条件的爱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主体必须先去认同他者的要求。“他者的要求结构了主体的趋力。进而,主体在他者的领域中,通过他者的要求结构出来的驱力反过来又结构的主体对他者的要求,即要求他者无条件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拉康称此为‘爱的需求’。爱的需求的一个根本特性,在于它的无条件性,它要求无条件的满足。”[3]在母亲或母爱的缺席中,亚拉感受到的是一种爱的挫折,是渴望被母亲无偿给予爱的要求被拒绝的挫折;即使母亲在场的时候,亚拉对母爱的需要的暂时满足也不可能是先前遭遇到的挫折得到补偿,其在当下的在场反而会使母亲的缺席变得更具伤害性。《小小港湾》中,导演一方面为孩子们创造了一方让亚拉和她的小伙伴自由玩耍和想象的空间,他们在此穿行于丛林间,与小动物嬉戏玩耍,破旧的木屋成为他们远航的帆船;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显示着这一想象世界的脆弱。在无可挽回的缺失与伤痛前,亚拉只能通过变本加厉地以更多的资源来加以补偿,但这无助于挫折的解决。这样充满童趣又淡淡苦涩的情感,让观者的视线跟随着亚拉穿行在各个场景——夜晚的海边、邻居的别墅、田野与森林、废弃的花园,进而重新回到爱与孤独的“小小港湾”。
三、影像层面上多重现实情景的呈现
在《小小港湾》中,女导演伊韦塔·格罗福娃展现出独到的角度选取能力和叙事风格。影片时而令温存的画面与沉重的现实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用现实视角来展现原生家庭的撕裂,揭示残酷的生活真相;时而以儿童本真的想象视角,将充满苦难的人世间描绘为充满梦幻与诗意的幻想世界。影片既具有纪录片式的摄影风格,也具有如梦似幻的色调氛围。在影片开头,这一多重现实维度的特性就已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特写镜头(结合了部分CG技术)拍摄躺在树干上的女主角亚拉,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在她的身上。暖色调和高明度画面中的亚拉闭着眼睛,身下是碧绿的厚厚青苔;蚂蚁寻觅甜点一般爬上她饱满的肚子、穿行在她指缝间,又在她平静的脸庞上爬行。手持摄影的影像处理为这段影像带来了自然主义的风貌,缓缓移动的特写镜头将一切收入画框。“电影化的影片所唤起的现实就要比它实际上所描绘的现实内容更为丰富。这种影片里的镜头或镜头组合具有多种的含义,所以它们的再现范围是超过物理世界之外的。由于它们不断引起各种心理-物理的对应,它们暗示出一个可以恰切地称之为生活的现实,这里使用的这一术语是指这样的一种生活,它仿佛用一根脐带,仍然跟作为它的情感和理性内容的来源的物质现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4]亚拉躺在腐朽的树干上任由蚂蚁爬行的镜头中,阳光、蚂蚁、茂密的青苔、白皙饱满的皮肤是充满生机的,然而枯朽倒下的树干、女主角一动不动、近乎病态的平静似乎又暗示着毁灭与死亡。这一自然生命本真性与腐朽衰败并存的场景是对亚拉生活处境的一种暗喻。接下来,镜头拉远,小憩后的亚拉缓缓睁开双眼,从树干上坐起来,拍掉脸上和身上爬行的蚂蚁,跳过水洼和一望无际的葡萄田。下一场戏,亚拉回到凌乱、毫无人情味的家中,导演采用手摇镜头和中镜画幅,令房间的画框被摄影机画面完全框进边缘,显得房间窄小逼仄;低照度照明下具有胶片质感的噪点与冷色调,又显示出这里的嘈杂、潮湿与闷涩。久病缠身的外婆缠绵病榻,自顾不暇;母亲则对女儿毫不关心。从户外到室内,导演利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影调令观众跟随者亚拉的视角,感受转眼间生活场景从“梦境”到“牢笼”的转变。这是整部影片的开头,也昭示着10岁的女主角亚拉同时身处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整部影片的矛盾,在故事层面是亚拉对爱的求索与求而不得之间的冲突;在影像层面则体现为多重现实情景之间的来回拉扯。得益于文学文本的优势,《小小港湾》中充满了细腻的心理描写,儿童演员质朴生动的演技也丰富了不同现实层面的情感与节奏。以此为支撑,影片显示出多重现实情景的拉扯制造出的张力,而亚拉毋庸置疑位于这一裂缝中心。
亚拉作为母亲一晌贪欢的“副产品”,出生在未受到祝福的家庭中,她的成长也缺乏家庭给予的关爱。水的意象在影片中反复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在影片开头的梦境中,亚拉在蔚蓝透明的水中游动,象征母体的水对孩子的滋养和保护,但亚拉却被这场梦惊醒;在影片中部,亚拉为了吸引妈妈的注意力,从海边的高台上跃下,沉入深蓝的、不透明的海水中,等她遍体鳞伤地回到海滩时,妈妈却已经离开。母亲的彻底缺席与在场缺席,都让她心中对无条件的、纯粹的爱愈发渴望。于是,她只能如同陌生人一般游走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中,以近乎野蛮的生长方式攫取心灵的营养,疗愈内心深处的孤独感。
结语
《小小港湾》触及诸多成人世界的教育问题,却将故事的社会背景做极简化处理,将影片的重心转移到用电影语言呈现孩子的世界,最终以充满想象力的形式解释出角色心理上的创伤:母爱的缺席在亚拉身上撕开了一道不可弥合的伤口,亚拉只能拼命地把满足需要的具体对象象征化,使其成为爱的要求的象征或爱的能指。
参考文献:
[1][4][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71,35.
[2]郑欢欢.儿童电影:儿童世界的影像表达[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51.
[3]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