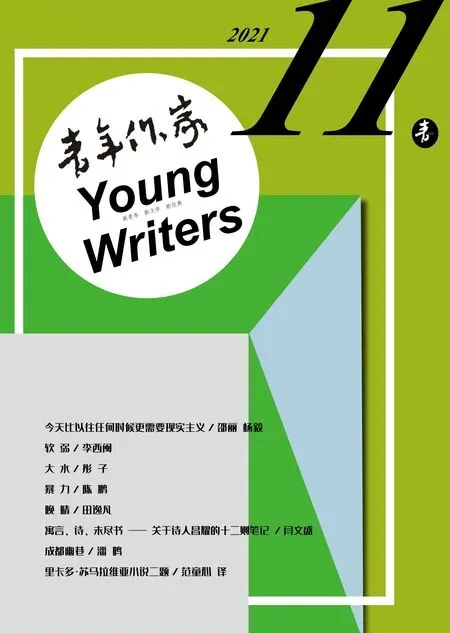里卡多·苏马拉维亚小说二题
【秘鲁】里卡多·苏马拉维亚
范童心 译
棕色的门
我的父亲一直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太多。但那几个经常来我家拜访的,总是对他尊敬有加,也很看重他多年来市政官员的身份。礼尚往来,父亲自然也同样善待他们。所以,有人专门前来告知菲利克斯先生去世的消息,也就不奇怪了。他们说,他是在卡拉巴亚街自己的印刷厂门前被一辆车撞死的,当时他正跟工人们一起往出走。“太意外了!”——这些人不住地重复着,一会儿看向父亲,一会儿面面相觑,仿佛刚从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中幸存下来。他们又说,菲利克斯先生是在被抬进印刷厂时断气的。叫来的救护车只能在等待当班警官的过程中,给躺在操作台上字模和纸堆中间的人开出死亡证明。
几个人对我父亲说,介于他们曾是朋友,他被指派为通知卢西亚太太和孩子们的人。菲利克斯先生的家人就住在临街的尽头,一道上坡路的最高处,那里是一个小小的广场,正对着桑塔安娜教堂。父亲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又很有礼貌地请在场的几个人先离开。我和母亲看到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再出来的时候套上了一件蓝色的夹克。我的母亲没有哭,但明显很难过。两个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父亲拉上夹克拉链的时候向我走来,命令我也准备出门,跟他一起去卢西亚太太家。我母亲想阻止,说这不是个好主意;但他已经走到我家的棕色大门边等着我了。我用最快的速度穿戴好,跨出门之前,母亲用手帮我顺了顺头发,跟我说别和卢西亚家的孩子打架。我点了点头,追上父亲,他已经走出去两米。
卢西亚太太有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两个人都很胖,喜欢唱歌。出奇的是,大一点的女孩唱得更好。另一个是男孩,虽然年纪小些,但体格发育得有些过度了,声带也没有自己的姐姐那般出色。两个人都戴着粗黑玳瑁框的大眼镜,这并不是那些年孩子和年轻人常用的款式,无疑是他们的母亲选的,因为她自己也戴了一副一样的。卢西亚太太并不像两个孩子那样过胖。她身形圆润,风韵犹在,一头长而直的栗色头发。直到今天,我仍记得她脸颊上密密麻麻的雀斑,集中在颧骨下方。
父亲和我停在两扇大门的正中间。那座房子的入口是一座古老的棕色木门,已经被蛾子咬得斑驳不堪。不过,因为够厚,又被重新粉刷过,依然坚固无比。门上面并没有门环,只能用手掌拍。我发现父亲抿湿了好几次嘴唇,好像为了能把话说清楚,抿多少次都不够。他又低了两次头,不知喃喃自语了些什么,估计是在演练怎么开口。正是在他第二次低头的时候,卢西亚太太突然打开了大门,惊讶地一动不动,盯着我的父亲。
她的身后是两个孩子。大些的辛西娅正在一丝不苟地用粉红色衣角擦拭眼镜,对她来说,震惊应当更为巨大,因为没戴着眼镜,根本认不出来我们是谁。我又看了看她的弟弟艾里亚斯,他似乎没有任何反应,一脸无所谓地看着我们。
父亲立刻站直了身子向朋友的家人问好,我在一边看得十分佩服。他一边说,一边向院子里迈进;而卢西亚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则同时后退着。我记不清他具体对那女人说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都穿过庭院,一起走进了一道窄门后的客厅。她应该是很痛苦的样子。
院落虽然不大,却极好地延伸了房屋的规模,里面装点着几个一样大的花盆,栽着大叶子植物。有好几扇门,都是棕色的,环绕在院子四周。每一扇都通向不同的空间——客厅、厨房、浴室和几间卧房,估计是艾里亚斯、辛西娅和他们父母的。
当院里只剩下我们三个时,大家都沉默了。父亲的造访对姐弟二人貌似无关紧要。辛西娅仅仅在一刹那间尝试了用近视眼穿透客厅的窗户,也很快就放弃了,接着她转向了我。我以为她会对我说些什么,盘问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她张开双臂,一下子抱住了我,把我紧紧箍了起来。我完全无能为力,而且喘不上气来。我试着把头往后仰,但还是能感觉到她炙热而急促的呼吸。我被箍得很紧,完全懵了,根本挣脱不开她的手臂。我之前完全没想到辛西娅的胸部已经发育得这么厉害了,特别是对她的年龄而言。或许是好奇占了上风,我暂时放弃了挣扎。这时我听到辛西娅咯咯笑了一声,好像老鼠在吱吱叫,接着又把我越抱越紧了。
艾里亚斯突然命令她把我放开。听到弟弟说话的那一刻,她的手臂才开始松动,直到终于放开了我。看到我重获自由,艾里亚斯抓住了我的头发,用尽力气猛地一拽,我直接摔在了浴室门旁边。我本能地挣扎起身,看他正走过来,就毫不迟疑地飞速躲进了浴室,还插上了门闩。浴室里面一片漆黑,但我完全不想开灯,或许这样更安全些,还能躲过那屋里的镜子必将反射出的荒谬表情。我还记得,从排水沟中散发出的刺鼻气味越来越浓,跟肥皂和消毒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那我也不想走出去,我已经彻底惊呆了,头很痛,很想哭。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想听听他们有没有逼我出去,却什么也没听到。不过,我却听到了一些别的动静,还发现了射进屋里的一小束光,那是一个小小的孔洞,让我能窥探到他们在外面做什么。这一看,让我的惊吓和疼痛都消失了。目睹院子里正发生着的一切让我平静下来,我只要默默观察他们,等待父亲叫我就好。
洞口只能让我看到两姐弟中的一个。有时候他们看上去正在争吵,有时候又像是在讲和。整个过程完全没人往浴室门的方向看。几分钟过去了,辛西娅走向几扇门中的一扇——应该是她的卧室吧——靠在上面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声音低沉、婉转,仿佛在为后面放大招做准备。突然,我也听到了艾里亚斯的声音,虽然他并不在我的视野里。他的嗓音有些尖细,但他明显知道怎样发声更好听。两个人练习的是一首他们经常在我父亲和菲利克斯先生举办的朋友聚会中演唱的歌。那一天是星期六,辛西娅和艾里亚斯跟随想象中的指挥歌唱着,却是在为他们自己而唱。他们唱出了难度极高的音调和旋律,我只能看见辛西娅,只见她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估计艾里亚斯的状态也差不多,应该也正靠在自己的门上。两人时而合作,时而轮番独唱,歌声一直无与伦比。
我几分钟后才意识到,辛西娅通红的脸上挂满了泪珠。她时不时用手背抹着眼泪,歌声却从未间断,也没有跑调。她唱出的旋律散开了一层薄薄的纱,在无比漫长的一秒停顿中,才能留下片刻沉寂让人得以听到客厅里传出的急促喘息声,我父亲和卢西亚太太正在那里。那些声音变得愈加不安,还总被听不清楚的呢喃声打断。
薄纱又铺开了。辛西娅的歌声继续流淌,越来越动听。我努力集中精神思考着这一切,想弄明白父亲和卢西亚太太到底在做什么。突然,浴室另一侧传来一声闷响,我不得不竖起耳朵。一切都是漆黑一团,我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响动是从哪儿传来的。窗子竟然开了,我眼看着艾里亚斯探身进来,身手敏捷得难以置信。我听得到他双手挂在窗框下时的喘息声。他快速地蹬动双腿,想找个能支撑的位置,却坚持不住了,摔在了浴缸边,嘴里还怪异地咒骂了一声,像个恼怒的小动物。这时我尝试着从屋里逃出来,但动作太慢了,已经被他抓住衣领。他打开浴室门,把我拉到了院子中央。他还在大口喘着气,很惊讶地看到自己的姐姐竟然还在唱歌。他冲她大喊,让她闭嘴,可她根本不理睬,继续唱着。这时她已经连眼泪都不去擦了。艾里亚斯把我拽到辛西娅身边,用另一只手去抓她。我的衣服被他拉得更紧,辛西娅也被他拉住了。后来他总算放开了我,辛西娅也刚刚停止了歌唱。我们三个人一齐向客厅的门望去,看到卢西亚太太和我父亲走了出来。卢西亚太太的双眼在那副厚厚的眼镜后面显得格外小,它们因刚刚大哭过而红肿,盯着地面。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她目光中的羞愧。两个孩子走向她,一边一个拉住了她的手,用痛楚的眼神盯着她看。随后,他们又都望向我,仿佛我才是那个该为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的人。见我不做声,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下,又不屑地看看我。
父亲说该走了,冲我做了个准备离开的手势。
我们走了出来。站在院外街上,能听到卢西亚太太在跟她的孩子们说话,但听不清楚说的什么,只看得到他们的脸庞都大汗淋漓。随后,即使有些费劲,父亲还是从外面把院门关上了,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家 庭
一
躺在厚厚的青草地上,四周是五彩斑斓的群山,我和我的女儿决定暂停休憩,去最近的镇上吃个午饭。她一下子就跳起身来,又拉住我的双臂,让我快点。身处新的气候之中,女儿的双颊泛出一片动人的光泽。她坚持要快点走,我却装出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随便在哪里都能睡着。我总会在出门前这样逗玛丽贝尔,她会更兴奋的。我的职责是,她放假在我身边的这段时间里,竭尽所能保护她。她母亲在她每次过来之前都会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但我最终能记住的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唯一因数次重复而清晰保留在我脑海中的是,玛丽贝尔的过敏药。我也曾经有过相同的过敏,更久以前,我的母亲也有过。我开车的时候,女儿又提醒我一次她的用药量。她说这些的样子认真而笃定,还用滑稽的手势强调着。
一路上,她指了三个餐馆给我看,但我都不想进去。还没到镇上,我可不想跟一帮卡车司机一块用餐,特别是玛丽贝尔在身边的时候。又开了几公里,我们在第四个餐馆停留了几分钟,只买了一瓶桃子汁。因为吃药的时间到了,她妈妈坚持说要按时服用。二十分钟过后,我们接近了一个小村庄。令我意外的是,这里有一家乡村餐厅,里面满是旅途中的家庭在就餐。玛丽贝尔立马发现了滑梯和秋千,高兴极了。我们刚走进去,她就问我能不能上菜之前去玩。我同意了,她很快就和其他的孩子打成一片,还把他们划分成小队,开始玩另一种游戏。从我的桌子能看到餐馆里的每一个区域,透过窗户也能看到我女儿正在和她的新朋友们疯跑。就餐区由三个呈U形排列的宽敞大厅组成,中间是厨房。服务员很快就把饭菜端上了桌,但我还不想叫玛丽贝尔。菜看着很诱人,也还有点烫,如果现在就命令她上桌,玛丽贝尔肯定有的抱怨。于是我叫了一杯红酒,等着她自己发现我面前的桌上已经摆满了碗盘,过来开吃。
我花了几分钟时间,观察其他桌子上的人。我有个习惯——在人群中寻找与我的朋友相似的面孔,这样不管在哪里都不会不自在了。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挺像玛丽贝尔的小女孩:脸蛋一样红扑扑的。我朝窗口望去,想看看女儿在哪里,但滑梯和秋千上都没有。我没有站起来,只是尽量直地挺起了身子四处搜寻她的身影。原来在那儿呢,一个小坡的边缘,类似一道山崖的底部,正准备往一个高高的茅草堆上跳。她一跃而下,轻轻落在了草堆上,我仿佛听到她往下掉时的笑声了。我又看着她站起身,用手摘粘在毛衣和裤子上的干草。她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显得少有的严肃,又让我心头一软。接着她突然不弄衣服了,又往坡上跑,估计想再跳一次。
我想再叫一杯红酒,于是举起手臂向服务员示意,却没有一个人看到。我耸了耸肩膀,自我打趣地垂下目光(每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我都会这么做)。不过刹那间我停住了,因为发现有一个短头发女人正定定地看着我,至少那一刻我认为她正在看着我。她跟一个小胡子方脸庞的男人坐在一起,那人正愤怒地注视着她,好像在等待某个答案。我向一边挪动了一下身体,以确认她是否真的是在看我;不过答案是否定的,我不过是恰好处于她空洞视线中的一个点而已,我的动作也让她有了反应——她打了个激灵,面向这边的目光变得有了焦点。随后她转向自己身边的人,两个人开始争吵,仿佛是在继续一场很久以前早已开始的争执。从我的位置听不到他们具体在说些什么,他们很小心地不去发出太大的声音,但从克制的肢体动作不难看出两人的怒火。她甚至把指甲掐进了那男人的手臂,对方没有动,我觉得应该是在勒令女人松开。我有些尴尬,就不再去看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玛丽贝尔身上。我女儿刚刚又往下跳了一次。看了她一会儿,我站起身离开桌边去带她过来——我有点担心,往干草堆上跳这么多次会不会受伤。
二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不用逼着女儿吃饭。我从未经历过那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为了一勺汤争个不休、讨价还价的烦人场景。我的母亲也曾说过,她也很省心,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总是很乖地把自己的盘子吃得干干净净,而她觉得世界上有这么多挨饿的人,确实不应该剩饭。我到现在都不清楚,那么做是为了顺从、怜悯还是极度自私。
吃完饭以后我们上了车,玛丽贝尔坐在前座,又开始安静地从毛衣上往下摘粘住的干草。我发动了车,往后倒到餐馆入口,看了看剩下的几辆车,暗自琢磨着哪辆才是那短发女人乘坐的。随后我很顺利地开上了高速,往塔尔玛的方向驶去。路上女儿让我陪她听了好几次她的一盘磁带,里面是一部卡通电影歌曲,我都已经会唱了。有时我会跟她一起唱,有时则会陷入短暂的神游,其中的我身处一个故事和幻想之中——我失踪了二十年,杳无音讯。归来后发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她或许会在面颊上给我一个吻,再献上一个拥抱,我们一起追忆往昔——那时候回忆必定已是古老而斑驳的了,却难忘而永恒。
我们在午后回到塔尔玛,与计划中一样。肯定得去看看我哥哥劳尔。幸运的是,他全家人当时都在,我的侄子侄女和玛丽贝尔久别重逢,特别开心,天黑之前一直在一起玩,唯一的间断只有晚饭和玛丽贝尔找我要过敏药的时候。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我、劳尔和他的妻子塞尔玛坐在舒服的沙发上聊天,开始说起家里的琐事。塞尔玛不失礼貌却绝对八卦地问我,玛丽贝尔的妈妈怎么样了。不得不说,我坦率的回答都令我自己惊讶:“她很好呀,在新家和新工作都挺开心的。”我这么说,内心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又看了看玛丽贝尔,仿佛她就是证明。劳尔对我会心地笑了笑。我又说,第二天我们会去尼诺度假村,在农庄里待几天,好好休息一下,玛丽贝尔也可以在那儿好好玩一玩。我的嫂子换了一种缓和些的语气,劝我说,得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了,或许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一切都会好的。我看到她把手臂朝着我的头伸过来,可能是想捋一下我的头发,就像对待她的孩子一样。我却本能地猛然向后一靠,闪开了,都没来得及克制自己。我瞬间觉得有些尴尬,想都没想就转向了哥哥。他正在慢条斯理地点一支烟,完全没意识到周围的一切,只专注于那即将熄灭的微小火苗。
三
前一天在餐馆见过的短发女人拉住了我女儿的手,帮助她站起身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摆弄胶卷,打算给玛丽贝尔在塔尔玛的中心广场拍一张照片。女儿正往回跑,却在中间滑倒了。当我冲到他们身边时,玛丽贝尔已经很平静了,甜甜地看着我。那个女人主动帮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我和玛丽贝尔拥抱在一起,还摆了很多其他姿势。我本来以为小胡子男人会随时出现,但时间一点点过去,并没有他的影子。不过,每隔一会儿她就会朝广场的一角瞥上一眼。不止一次,我们的目光同时向那个方向扫去;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视微笑。
拍完照片以后,玛丽贝尔在广场的花园里奔跑着,我们开始聊天。或许是我无欲无求的样子吧——我的朋友总是拿这点取笑我,将其称之为“倾听的耐心”——因为总有刚认识不久的人主动把一些自己的私密事告诉我,这个女人也不例外。“我可没想过和她组建家庭。”我打趣地对自己说。她那次讲给我听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
她叫珍妮。她对我坦白说,自己很喜欢在很多个再生纸做的本子上做笔记——我家里现在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本子了。珍妮说,她下笔之前,会先把要写的东西都记住,积攒了很多回忆之后,再分别记录在不同的本子里。就好像一个喜欢收集各种大大小小盒子的孩子,总觉得自己肯定能把它们很快都填满。她的数段回忆中我最感兴趣的一个,是和一个梦有关的。梦里面有两个女人——准确地说,是两个少女——坐在一个石头水池边,里面的水满满的。水池位于一个大广场的正中央。珍妮认出了其中一个女孩,但也意识到了那其实并不是她——她对我说,因为外貌过于相似,应该是那人的妹妹或女儿。另一个女孩则很不一样,歪戴着一顶鸭舌帽。后来,与很多梦境中一样,珍妮已经不是旁观的人了,而是变成女孩们中的一个,戴帽子的那一个。她很喜欢变年轻、变瘦、头发变长、动作或许更淑女的感觉。另一个女孩把手指浸入池中的水里——伸进去,拿出来,甩一甩手,又伸进去……就这么不停地重复着,满不在乎的样子。两个女孩都没有说话,只感受着轻轻的风、池中冰冷的水、从经过广场周围狭窄街巷的车辆传出的马达声、渐渐西沉的太阳,以及所有自然而然来到她们身边的一切。珍妮想说些什么,想趁着水池再许个愿。她不记得自己在梦里有没有来得及许愿了。两个女孩都笑着,开始奔跑起来。珍妮看着另一个女孩,有些惊奇,也享受着这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这样,她结束了自己的回忆和梦境,也是她笔记本上的一页。她把一只手伸向提包,在上面拍了拍。
“我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的。”
说完这句话之后,她转换了话题,开始问我女儿的生活习惯,还跟我说,她看起来非常聪明。这当然让我很开心。我确信这时候应该不会令她难堪了,于是问道:
“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她回答,“跟他爸爸住在一起,在国外。已经八岁了,但我们有五年没见过面了。”
后来她转向其他话题。最后,看到玛丽贝尔拉着我的外衣求我带她去看广场一侧的木偶戏时,她也开口与我们道别。是很简单的告别,她对我说,自己在等人,指了指远处的长椅,又伸出手跟我握了握。她往前一步想吻一下玛丽贝尔的脸颊,但我女儿做了个奇怪的鬼脸,就跑向了已在搭好的台子边排起队准备看表演的其他孩子。
“可以给我呀,如果愿意的话。”我有点过意不去地对她说,试图把难堪的一刻掩饰过去。
“下次吧。”她回答,走向其中一张长椅坐了下来。
她看上去很坚定,一直坐在那张椅子上等要等的人,没打算离开。半个小时之后,餐馆里见过的小胡子才出现。他开着一辆红色的汽车,按着喇叭叫珍妮。她坐上后座,车马上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