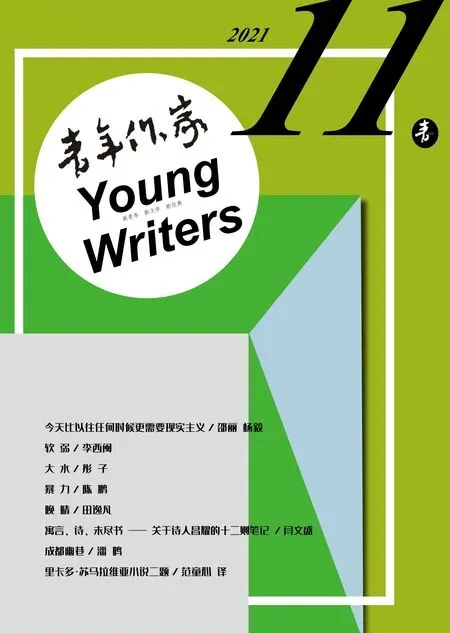须 弥
刘鹏艳
老胡在这条街上有年头了,老胡的铺子也顺着年轮,开得有张有弛。他开的是烧饼铺,门脸儿不大,街角人家依墙根儿搭的半间披厦,刚够塞进一只炉子、一条案板。城里年轻人不好这口,因而烧饼铺火不起来。不过街坊邻居图省事的,上下班带那么一块两块烧饼,生意也便有得做。可是不知道哪一天,有那么些年轻人,听说了老胡烧饼,一时间蜂拥而至,烧饼铺子倒成了网红打卡地。老胡本着脸说,你们拍什么呢?小年轻嘻嘻哈哈的,一手抓一烧饼,脑袋往同伴的手机前兴奋地一漾一漾,方头方脑的手机也好像跟着一漾一漾。师傅,给个镜头!系着雪白围裙戴着雪白套袖的老胡低下头,事不关己地哼一句,我不上镜。再有往前凑的,老胡就开始挥擀面杖轰人了,边上玩儿去,还有客人呢。当然也是作势。
有人来买烧饼,只收现金,概不找零。一只掉了漆的大白瓷缸子放在案板上,买家只管往里投钱,老胡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事儿,头都不带抬一下的。这也成了老胡烧饼的特色。那些只带手机来的,凡购物都指望扫一扫的,往往要上隔壁小超市兑换钢镚儿给他。
都说老胡有性格,打烧饼只打两种,葱油烧饼和白糖烧饼。人家说你换换口味呀,做点梅干菜的或者肉馅儿的,包管有人买。老胡一门心思摔打他的面团,两只手上下地揣,揣着喘着,不做,我打烧饼不在馅儿上。要换口味,容易,满大街的必胜客,他们外国烧饼才赶潮流呢,榴莲味儿的都给你做出来。人家就笑着啐他,这个老胡,犟脾气,说句笑话也较真儿。完了还是买他的葱油烧饼,或者白糖烧饼,吃不够似的。
论年纪,老胡也不算太老,不过大家一直这么叫,好像还是小胡那会儿,人就老了。老了就老了,老胡也不计较,又不是女人,多条褶子都吃不下饭。过日子么,谁还不是活着活着就老了。老胡打烧饼,一板一眼,打掉了多少个春夏秋冬,还跟当初那会儿似的,不偏不倚,那么大的劲道。也因此,老胡烧饼叫得开、叫得响,老胡一点不怀疑自己打出的烧饼,什么叫沾了网红的光?扯淡!要说沾光,网红才沾他的光呢,那些小屁孩,他们懂什么叫美食,什么叫地道?
一个烧饼两块钱,一天要是打一百个烧饼,老胡的日子就过得不错;要是打两百个烧饼,老胡的日子就很红火了。所以老胡给自己定了数,烧饼卖得再好,一天不超过两百个。也知道钱是好东西,老胡跟钱也没仇,可他光杆儿一个,除了吃点喝点,用钱的时候不多,和钱也就没那么亲。挣多少算够呢?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综艺大咖的话,人间不值得。说这话的那小孩儿才二十来岁,好像叫李诞,长得确实像颗蛋,小眼睛,笑起来眯缝眼就瞧不见了,一副天地混沌的样子。老胡引以为隽语。所以,没人见过老胡的第二百零一个烧饼。也有解释说这是饥饿营销,老胡不搭理,还有人说《西游记》是职场圣经,《红楼梦》是性教育读本呢,当真?那你就输了。老胡不是输不起的人,他压根儿没想过赢而已。赢谁?说大了天去,赢个“烧饼大王”的称号,还是一卖烧饼的。这些都没用。老胡摇头。人说,怎么没用呢?都能变成钱哪。老胡说,钱又有什么用呢?人就不说话了,觉得真不是一个档次的。
老胡活成了自己的样子,倒不是他妈教育得好。他妈是典型的城镇妇女,粗枝大叶的,教孩子也仔细不起来。小时候老胡都是一人上下学,脖子上挂根绳儿,绳儿上吊两把钥匙,一把是家里铁门钥匙,一把是家里木门钥匙。铁门生锈,锁眼也涩得慌,老胡拧钥匙往往要左三圈右三圈。不过这也不妨事,反正进得了家门,有什么可着急的?也是性子里浑然天成的憨,老胡做什么都不急不躁,乃至打烧饼,别人摔打几下就完了,他跟案板那儿耗着,不打出丰富的层次感来决不罢休。人说,老胡自在,一个人,想怎么着怎么着,换作别人,这个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拿钱不当回事儿,那不是天诛地灭吗?老胡一边仔细打他的烧饼,一边平心静气地说,我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不想养老的带小的?这不是我妈去得早么,我媳妇儿又跑得快,没来得及生呢。他说的是结婚俩月,就跟老婆闪离的事儿。闹不清楚怎么个情况,婚姻登记处一直是个忙碌的地方,爱恨别离都很平常,老胡也看得开,单是“性格不合”四个字儿,足够夫妻双方下定决心两不耽误了。
离婚的时候,女方拿走了全部动产。老胡说,你尽管拿,不过这房子是我妈留给我的,你算是高抬贵手,给我留一地儿睡觉吧。女方也仁义,划拉走股票存款,回头又让搬家公司把家具电器搬迁一空,连一根筷子都没留下。果然,留了栋干干净净的房子给老胡。老胡笑着流了眼泪,说妈呀,你真是我亲妈。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老胡几乎都忘了自己是结过婚的人,或者说,是有过家的人。
要是“家”就是房子的话,他不算无家可归。上了卷闸门,往回走,他心里还是有暖意的——因为那套厨卫齐全的两居室,是妈留给他的。铺子离家不远,撂颗石子儿的距离,也因此,老胡觉得打烧饼就跟小时候在家捏橡皮泥似的,所谓营生,就是个玩意儿。
打烧饼么,又不是挖矿吊梁,值不当那么辛苦。一天能打两百张烧饼,在老胡看来刚刚好,再多,就是跟自个儿过不去。那第二百零一张烧饼赚的钱,不如他泡杯茶、抽根烟。摘了围裙,取掉套袖,倚炉点着烟卷,把案板底下的酽茶端上来,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夕阳如水,染着金箔,斜斜洒在老胡的肩上、颊上,仔细瞧,头发上斑斑白白的,也不知是沾了面粉,还是沾了岁月。
一大早起来,照例是磕两鸡蛋,炒一大碗油汪汪、金灿灿的蛋炒饭。打烧饼是体力活儿,老胡不敢克扣自己。中午头呢,一荤一素两菜,也是正正经经地做,再加上二两老白干,美得慌。傍晚上简单点儿,熬粥,小米粥或者南瓜粥,不怕麻烦的还可以洒上八宝或者五仁,随着季节和心意,夹一块刚出炉的烧饼,简直是绝配。老胡心里有数,人活着么,也就图这一口了。穿不用瞎讲究的,能蔽体暖身就好,再怎么烧包,换着花样穿,不过是亮给别人看,他又不稀罕人家看的;住么,也不必太讲究,眼一闭,睡死过去,八个钟头不知道今夕何年,你晓得自己睡在哪块云头上?唯独“吃喝”二字,将就不得,否则,做人还有什么滋味儿?
这一天是霜降,秋过去有一段儿了,这家伙走道儿深深浅浅的,留下无边萧萧落木,松啊、柏啊、柳啊、樟啊、杨啊、桦啊,都给秋风吹了个遍,绿得老了,只能掉叶子。老胡不爱搭理这些树,他觉得它们都俗。只有槭树晓得脸红,他往往愿意仰着脖子,凝神静气地盯那么一会儿。老胡盯着槭树看,不光看它们的颜色,还看它们的形状,小爪似的,像活物。今年大旱,太阳一直那么好,都霜降了,还跟小阳春似的,冷不起来,槭树叶儿也就不那么红,或者说红得不那么透。红不透的槭树叶儿看起来涩得很,平常日子不打眼,不过在清晨的阳光下,倒能呈现出玉的颜色,青里渗红的古玉。老胡仰头望了一会儿,心里就满满当当的了,像是饿了几天的人,给结结实实塞了三张烧饼,又灌了一大茶缸子凉白开。
这种癖好是从哪年哪月开始的?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年冷得慌,老胡还是个孩子,放学回来逮着妈就要吃的。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妈一边骂他是饿死鬼投胎,一边张罗吃食。边边角角都搜罗尽了,只抠出一点儿哈了油的炸猫耳朵。妈拍着手说,没了,没了啊,再大的家业,架不住你成天吃,都怎么长的这是?老胡心说别人家也不知怎么养孩子的,怎么我一张嘴就把你们家吃穷了?嚼着猫耳朵,不吭声,满脸的嫌弃。妈说,你还嫌我了?都说儿不嫌母丑,你嫌我?老胡说我哪儿嫌你了?你满脸都写着呢!妈往他脑门上戳了一指头,转身去厨房择菜,准备晚饭,嘴里还叨叨着,从早吃到晚,一天三顿,没个够。这日子过的,就为一张嘴了。老胡也觉得是,人这一辈子,一睁眼就是个吃,除了这,没啥。上学什么的,都是为日后找口吃食。爸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你不上学,就没文化,没文化,就找不着工作,没工作,就没钱吃饭。他不能不信,妈小时候就没上过学,所以只能当家庭妇女,也就是屋里头烧饭的。爸呢,好歹上过两年学,在厂里得了份工作,要不然,一家子吃风屙屁。
光顾着吃了,穿的讲究不上,反正是——冻不着就好,也不图好看不好看的。爸是一年到头的蓝咔叽布褂子,妈倒是有两身换洗衣裳,不过也和“好看”不挨边儿,她那水桶腰,穿什么都浪费。
国庆没多久,厚衣服就套上了,然后是棉衣棉裤,阳历十月底,棉衣套上之后,就没再下过身。老胡妈说,这天儿冷得邪乎。忙着找裁缝,给老胡裁褂子。老胡窜得快,年年都得找裁缝。为这,妈也叨叨,都怎么长的这是?去年才做的袄儿,放了两寸还多,这就不能穿了。只能拿爸的旧袄儿先对付,锁了袖口,蒙上罩褂,看上去像套了条面口袋。老胡将就着,穿到学校,被人笑话了一圈儿。
这也没什么,刚刚改革开放,贫富差距拉开得不明显,老胡这样的孩子,不说是大多数,也绝不在少数。在学校里,老师跟孩子们描绘了二十一世纪的蓝图,说他们必定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不必急于一时,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以免到时候接不上班儿。老胡理解老师的话,应该是顶职的意思,他们院儿里,就有待业知青顶替父母岗位的,如果没文化,连顶职都办不了,这确实是个麻烦事儿。为这,老胡学习劲头儿不小,就差悬梁刺股凿壁偷光了,可考试分数出来,往往不尽如人意。老师摇头说这是基因问题。
现在想起来,老师说的可能不是这个词儿。那会儿还没人知道“基因”是个什么东西,不过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胡是老胡的爸妈生的,老胡爸妈都没读过什么书,所以老胡也读不进去。硬是读,只能把自己的脑袋读得一个变两个大。后来老胡爸妈也想通了,看见老胡在灯下没白没黑地熬,就劝,早点睡吧,这点灯熬油的,电费不要钱哪?老胡泄了气,读到初中毕业,也就罢了。
初中毕业之前,还是个孩子。那时候孩子发育晚,十几岁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回事,更想不出小孩子是怎么从大人身体里钻出来的。这当然也不妨碍什么,全中国的父母都是这么长大的,长大了,自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父母不跟孩子提这个,如果孩子提,必然讨一顿骂;好一点儿的,也是胡乱搪塞,捂半个嘴说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或是从对面小卖铺沽来的,形形色色,跟真相不沾边儿。老胡妈就跟老胡说他是捡来的。有好长一段时间,老胡都有一种冲动,看见垃圾桶,就想凑上去翻捡翻捡。有时候能翻到死猫死狗,但从没翻捡过小孩子,死的没有,活的就更没有。稍大些之后,老胡也知道妈骗他,自己可不就是爸妈亲生的孩子,不过还是克制不了那股冲动,见到垃圾桶,心里就像帆吃满了风,呼一下鼓荡起来。长成大小伙子的他,拦着心底里的那个小男孩,别,别去!不去也行,眼睛还往那边瞅着,黏黏糊糊的,脚步也变得有些磕绊。
妈给老胡抠搜了一小把哈了油的炸猫耳朵那天,老胡正憋着气。因为数学考试又得了个不及格,应用题几乎全军覆没,那个追及问题,“甲、乙绕着300米的环形跑道奔跑,甲每秒跑6米,乙每秒跑4米,问第二次追上乙时,甲跑了几圈”,真是把老胡气糊涂了。他不知道甲跑了几圈,也不想知道,知道这个跟吃饭有关系吗?如果没关系,干吗要学这个呢?他小小的逻辑充满了怨气和委屈,妈不懂,他也懒得跟妈说。妈大不了撩起围裙擦擦手,在他脑袋上摸一把,算了,咱还有58分呢。
老胡一口吃掉手心里的那一小撮猫耳朵渣,更饿了。妈还在厨房里张罗,离吃饭还早,老胡捧着瘪瘪的肚子,百无聊赖地坐在窗口写作业。
写作业就写作业吧,语文好歹是看得懂的。他识字儿不少,比爸妈都多得多,因而爸妈都夸他,那么厚厚的一本书也能读得通。可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可骄傲的,同班的同学,都读《骆驼祥子》和《巴黎圣母院》了,他读的不过是学校发的一本《课外阅读》。老师说要增加阅读量,课外要多读书,他狠狠读了好多遍,书都翻出毛边儿了。要是拿全班的《课外阅读》去评比,老胡的书最能显示出它的主人的刻苦程度,但也仅仅是刻苦罢了。现在他擎着《课外阅读》,不知第几遍地摘抄好词好句,忽然生出了厌烦的心思。他略显浮肿的小眼睛四处瞟着,不觉就飘到了窗外,落在窗外的树上、房上、电线杆子上。
窗口那儿正好有棵槭树,天冷了之后,红得愈发惊艳,把周遭的松啊柏啊杨啊樟啊都比了下去。这时节,别的树都是一副收缩的样子,要么焦黄了叶子一张张秃噜下去;要么绿得发黑,跟受气媳妇儿似的不敢张扬;唯独它,冷风冷雨的,倒是把脸蛋身段都催熟了,一簇火样地烧着了老胡的窗口。
老胡莫名地叹了口气,那叹息声不像是个小孩子发出来的,听来只觉得曲深幽折,含着无穷的不可说。他支了脑袋,瞧那小爪似的槭树叶,西风里摆摆手,又摆摆手,红彤彤的,烧心。
越过这棵冒火的树,稍后的地方,一排黑瓦的房顶影影绰绰,再后头,比房顶高出一截的电线杆子,因其伶仃的海拔,倒瞧得更清楚些。松松垮垮斜拉出的电线上立着几只鸟儿,高低错落地嵌在浑白的背景里,见出几分苍茫。那是穹隆的颜色。鸟儿在一片苍茫中变成几个黑点,又小又孤单。虽是几只,并不是独个儿,却分散着无依无靠的,比独个儿好不到哪里去。老胡无端地又叹了口气,把发酸的眼睛转到稍下方的位置。
电线下面是电线杆子,电线杆子下面呢,是一只垃圾桶。老胡感到很惊奇,比电线杆矮半截的房顶都瞧不清楚,怎么比那排平房矮更多的一只灰色垃圾桶,倒突兀地竖在眼前。更让老胡吃惊的是,垃圾桶下面还有个造型夸张的人头!慢着,怎么会有颗人头?老胡定睛望去,是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蹲在那儿划拉着什么。少顷,慢悠悠地站起来,探身往半人高的垃圾桶里去。她开始翻垃圾桶,翻捡得可仔细了,半个身子几乎隐没在垃圾桶里,完全瞧不见她发型夸张的脑袋了。远远地,老胡的心竟然拎起来,好像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又好像是终于看到了渴望多时的什么东西,一时间手脚冰凉,不能抑制地抖动起来。
那种莫名的冲动,顿时像吃满了风的帆,从他心底高高地涨了起来。他愣了一下,然后丢下书本和作业,不顾一切地奔了出去。
过道里,妈抓着把小青菜,在身后喊,哎,你干吗去?
我出去玩会儿。老胡头也不回。
妈嘀咕,作业写完了?这么快。也就是嘀咕,她管不着他的作业,比起管孩子学习这件事儿,择菜做饭容易得多。反正孩子爸快回来了,有什么作业要签字都不碍,于是提高嗓门添一句,别跑远了啊。
老胡绕过那棵着了火的槭树,噔噔噔一口气跑到垃圾桶那儿,怔怔地瞧着翻捡垃圾的中年女人。瞧清楚了,是个好看的女人,无论腰身还是脸蛋儿,都比老胡妈小一号,虽是披头散发,长相倒清秀。她身上穿的衣服也还干净整洁,不像是乞丐。老胡心里一阵咚咚跳,两只手垂在身侧,抓住自己的裤腿儿,揪扯成一团,脖子就那么僵硬地伸着,紧紧盯住女人的脸。你是谁?老胡心里问。眼睛也在问。整个绷直的身体都在发问。女人发觉有人在看她,也把目光转了过来。
那一刹,老胡给电着了似的。他一辈子都记得她的目光,清得像水,又混得像雾,她看他一眼,就像水里过了电,雾里起了风,他一下子就不知道动弹了。女人的目光绑住了他的手脚,一点点收紧,把他拉到她的鼻子前。她看着他,逼得很近,老胡以为自己被吓着了,其实不是,他差点就脱口而出,把心底蓦然冒出来的那两个字儿喊出来。然而还没有来得及,女人突然俯下身子,在他左颊上吧嗒亲了一口。
老胡刚想喊出声儿,女人就龇牙一笑,蹦蹦跳跳地走开了。这女人精神有问题,老胡灵醒过来,才发觉事情的真相可能是他遇上了个女疯子,而且他被女疯子亲了一口,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他拼命想把事情想清楚,偏偏越想越糊涂,看着女疯子越走越远,他觉得不能这么放过她,就拔腿向她追过去。
嚯嚯,女疯子回头看他追过来,口中发出奇异的声音,又蹦又跳地跑起来。嚯嚯,她一边跑跳,一边回头发出这样语义含混的音节,霍,霍,或者,活,活?老胡听她叫着,不知什么意思,却几近荒唐地执意要从中拆解出某种意思来,于是紧追不舍。他更起劲地挥动双臂,两只腿快速倒腾着,跑啊,跑啊,跑得额头上渗出了汗,女疯子还在前面不远不近的地方,朝他挥手,活,活。
这样跑了不知多久,老胡没觉得累,却觉得自己快要断气了。不行了,活不了啦。老胡慢下来,一只手向前伸出去,想要抓住虚空中的什么东西似的,终于渐渐软了下来,化在一片浓黑的夜色里。活,活,那声音藏在黑暗后头,一会儿远一会儿近,诱着上气不接下气的老胡。老胡拼着最后一口气,以为就要抓住它的尾巴了,可是,又让它一闪,不见了。老胡化成墨水瘫在地上,彻底失了望,没来由的,眼圈儿就红了,一滴眼泪吧嗒掉下来,像颗豆儿似的。
这时候老胡才觉得怕,早就黑了天,这地方灯火又稀得很,刚才跑得热出一身汗,现在冷风一吹,浑身的汗毛啪一下就奓开了。西风转成了北风,呼呼地吹,无数把小刀子割着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老胡扯紧了身上的衣服,还是不成,再怎么着,藏不住头脸哪。刀子尽拣着疼的地方割。他记得爸常说,人就活这一张脸了。唉,怎么这么重要的部位,不给缝件衣裳呢?老胡真想放声大哭。
夜里风吹得更紧,老胡在黑地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着方向,好像,黑是一重幕,死活撩不开它。又急又怕,又冷又饿,老胡终究还是个孩子,哆嗦着,撕心裂肺地喊出一声,妈妈——简直像是放出两头猛兽,终于把憋在心里的那两个字儿放出来了,可惜,老胡的妈听不见,连同那个让他心里莫名痴癫的女疯子,也听不见。
这晚的结果,是老胡的爸妈打着手电寻了他大半夜,到底在环城大桥底下把瑟瑟发抖的老胡给找着了。老胡妈抱着老胡就哭,你个倒霉孩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没考好就没考好呗,怎么学人家离家出走呢!老胡爸也哭丧着脸,你呀你,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哇,读书倒把人读傻了,命值钱,还是分儿值钱?老胡抱着臂打摆子,我要能考到高分儿就好了,那命才值钱呢。老胡爸直跺脚,屁话!老胡望着爸爸,哭出声儿,你不是说知识改变命运吗?你不是说老胡家还指望着我逆天改命吗?老胡爸一呆,舔舔干裂的嘴唇,爸以前跟你说的,就当放屁吧,你能学多少是多少,高小毕业也比爸妈强哪。
那晚是个分水岭,老胡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不再为学习的问题纠结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是爸妈亲生的,并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那个女疯子后来再没有出现,老胡怀疑她是从虚空里放出来的一个精灵,在那个初冬的夜晚,她让他跑在惊悸里,跑在荒原里,跑在彻底的无价值里,抖抖索索地打捞生命的碎片……往后他就知道,生命是从破碎里来的,那么大、那么大的虚空里,什么都被撕成了碎片,别说一张脸了。他对着虚空号啕,叫她一声——妈妈。值了。
老胡长大了之后,仍然解不出追及问题和鸡兔同笼,也分不清巴甫洛夫和屠格涅夫。他原谅了自己,谁让自己是爸妈亲生的呢。老胡爸去世早,下岗之后就一蹶不振;倒是老胡妈,虽大字儿不识一个,跟人练摊儿却显示出一个社会妇女的精明强干。老胡妈就靠摆地摊养活老胡,还挣下现在老胡住的这套两居室。
老胡不怕人说他没本事,大不了说他打一辈子烧饼,连个屋头暖脚的都找不着。他的人生境界是很开阔的,给人说闲话算不上丢脸。老胡甚至还有些窃喜,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顿悟了,一个人最没用的,就是一张脸。露着,给人看,自己难受,这叫什么道理?一年到头,吃好喝好,这是硬道理。这样过了好多个年头,都二十一世纪了。
二十一世纪早晨的阳光里,老胡暮气沉沉,他老了,一天只要打完两百个烧饼,就昏昏欲睡,好像这一天应该提早结束,因为该做的都做完了。可是这一天,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走到铺子前,“啪”地打了个响指,问他,这还没到中午头儿呢,就收工了?老胡的瞌睡给惊走了,抬头看老太太一眼,朝两边摊摊手,意思是烧饼都卖完了。老太太不信,伸着脖子到处看,啊哟,抖音上说你烧饼卖得好,我特地起个早儿,大老远地跑来,怎么竟没了?老胡笑,您还凑这热闹?老太太不满意地说,我怎么就不能凑热闹了?我才七十八,能做的事儿可多了。老胡肃然起敬,您打车来的还是走来的?老太太指着路边一辆钢蓝色烤漆的哈雷,我骑摩托来的。老胡吓一跳,您家里人不担心吗?老太太倒笑起来,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老胡心想我问得真多余。老太太没买着烧饼,笑眯眯地问,我预订两烧饼怎么样?一个葱油的,一个白糖的。知道你这儿只收现金,喏,这是四块钱,我明早来拿,你给我留着。说完一扭头,跨上烤漆锃亮的哈雷,把挂在摩托车把上的头盔潇洒地套在满头银丝上,一踩油门,轰一声消失在光影里。老胡半天没晃过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