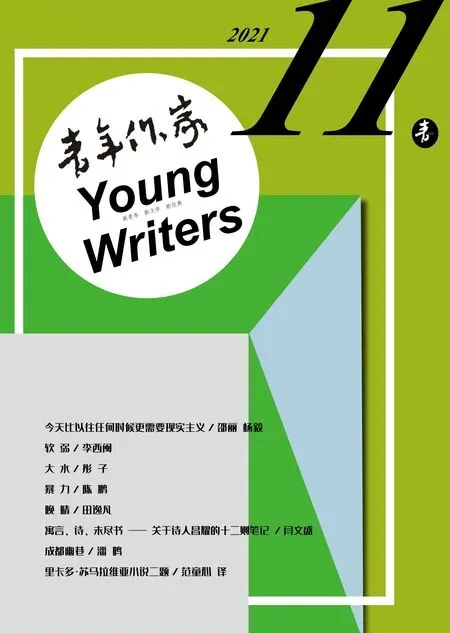梨花啊
南 子
那时候,奎依巴格镇每家都有一个院落,人们时兴在院子里种花种树。
我家种的花是晚饭花、夹竹桃、格桑花和美人蕉,树是两棵白杨树及一棵梨树。
一棵桃树的长成需要三年,一棵梨树的长成也需要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棵梨树刚移植到我家院子后,我没好好地关照它——可能它看上去太瘦小太孱弱了,每个见过它的人都摇头说,这树怕是活不了。
刚开始,我家人还能控制这棵梨树,时不时地给它浇水、剪枝和上粪。到后来的几年,这棵梨树一下子蹿得好高——有三米的样子。
当阳光出现在粗糙的泥墙上,树叶间的细小光斑闪烁着蜂拥而至,那些坚硬的柔软的、圆形的和长形的叶子,同时被淹没在阳光中,同时被阳光消灭和升华,被阳光遮挡或再造。它们的光影时而明亮时而暗淡,然后移动、消失。
一个深秋的晚上刮起了大风。
院子漆黑一片。天空好像密布着无数看不见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就是它——这棵梨树。
在夜晚的微光中,它好像和地底下某种神秘的力量接通了,随大风摇摆枝条,发出无可辨别、无从模仿的声音。在这种声音中,有一些事物在增长、在酝酿。然后,我看见这棵树像浑身通了电似的,带着阴郁的力量,让所有的枝条在风中疯狂摆荡。
那天,我刚从外面回到家,从院子这棵梨树下走过时,瞬间感觉自己像被它那股子力量吸住了,被无数根缠绕我的枝条束缚了,被未来巨大的生存吞噬了。
它在高处俯瞰一切,它的阴影笼罩我、逼视我,使我从此后只臣服于那些强健、霸道而又深不可测的事物。
我面色苍白,惊恐地一下子撞进屋子。我父亲看到后,看了一眼在狂风中摆荡叶片的梨树,嘲笑我胆子小,连树的黑影子都怕。
然后,他站在树下,盯着这棵树看了好一会儿,呆立片刻,轻轻说了句:“这树今天是有点儿疯——”
从这天起,我带着对未知力量的恐惧,经常长时间地观望这棵不开花不结果的梨树。看树干上的疤痕,看枯黄的有点营养不良的叶片,树下一层细细的羊粪,已出芽的格桑花秧子随风摇摆——我还经常用手在这棵树身的皱褶和裂缝处探寻,也不知自己究竟要寻找什么。
我沮丧于自己弱小的身躯和过于沉重的心事,将身子紧紧贴着这棵梨树。
很快,光阴裹成厚厚的一大团,旋转着,像飞一样。比飞还快。但这棵梨树一直是寂静的,仍不开花不结果,每天迎光而立,孑然一身。
我说不清楚,我身边有哪一种树的沉默会大过它。这沉默被重重围裹,被屏蔽在万事万物的倾听之外。
那个年龄的我面色苍白,有轻微的自闭、敏感,很少说话,一副心思很重的样子。我经常注视自己的掌心,试图想要洞见另一种平行的人生。我如这棵梨树那般寂静——把心里的渴望、秘密、痛楚深藏起来,只让文字泄露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我父亲看到我经常心不在焉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说我的心智就像这棵不开花不结果的梨树一样营养不良,没啥用。
那天,我父亲又重复这句老话时,我心里慌乱了一下,忽地,又浑身发痒了。
这是一个奇怪的毛病,我一听见父亲的声音,就浑身奇痒难忍。我想,这是不是这个人与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奇特的生物效应,让我一看见他,身体就痒得厉害,像是脊背爬满了温热的虫子。
这也许是心里害怕的缘故。当你害怕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身心会变得虚弱不堪。尽管我父亲已经很老了,但目光却依然如巨兽一样俯视我孱弱的灵魂。
此时,我渴望自己一个人走在边镇街头,而不是听着父亲在耳边絮絮叨叨,不断提醒自己该怎样怎样。当我走在镇巴扎上,把家里的一切完全抛在身后,这才深深吸了口气——明白在这个家里,自己的神经是多么的紧绷。
为了避开父亲的责骂,我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心绪,经常在秋日与几个同伴一起骑自行车在小镇郊外乱逛,累了,便躺在某个高坡的草丛中漫无边际地闲聊,看远处绿荫掩映的边镇,吃惊地发现,这座边镇在渐浓的暮色中显得格外寂寥和荒凉,像一座孤岛。
这一天,天还没有完全变黑,东方最后一抹桃红色正逗留在西天某处,很像嘴唇。田野浓酽的植物气息,像一层绿色的、无形的帘幕缓缓拉开。
在这层帘幕的下方,有枣树、白杨树、香柴胡、沙红柳、麻黄、芦苇、花苜蓿、野亚麻、野息香、沙茴香、黑枸杞、沙蓬、石蒜兰、马茄子、龙葵、槐树、榆树等多种柔和的影子——它们的气息干燥清洁,似乎不是来自田野,而是来自我的内心。虽处在昏暗中,却让人感到它有如冰一样的透明、洁净。
这时,小半牙薄凉的月亮将升未升——它或许就坐落在西天外远处的昆仑山上,似乎它就是从那儿出生的,其他时间里都在睡眠,只在夜晚独自悄悄长大。
就像我那样地悄悄长大。
天就要黑了。我们短暂地停止了嬉闹,不出声地朝着晚霞的方向呆望,若有所思。
同伴小燕西最怕天黑,天一黑他就饥肠辘辘,当饥饿感再次袭来,他站起身,朝着小镇的方向跑了起来,暮色沉沉地压住他的帽子,他的身体摇晃着,焦躁得像一头幼兽:“吃馕,吃烤肉,我要回去吃烤肉。”
“快滚回来——回——来——”他听到我们在唤他。
这时,另一个同伴安琪的口琴在手中熠熠闪光,他抓起来猛地一吹,呜呜呜的乐声在田野间回响。
他吹的是一首叫《白杨树》的歌。据说,这首歌曾是一位从上海来的知青写的:
白杨树戈壁滩上长着呢
白杨树昆仑山下长着呢
白杨树玉龙喀什河边长着呢
白杨树我家门前也长着呢
风吹倒了戈壁滩上的白杨树
风吹倒了昆仑山下的白杨树
风把玉龙喀什河边的白杨树也吹倒了
我家门前的白杨树还挺立着呢
更远处的田野上,晚归的农户朝着我们这群放肆的少年看,牛车轮子辘辘地滚过黄土大道,在黄昏中神秘回响。
这一晚的秋风多么浩荡,田野在晚风中无比枯寂。只要走到渠水旁边,就会发现过去的生活正掉下它关键的册页,像一堆发黄的落叶沿着渠水向远处飘去。
我与同伴在郊外的田野游荡着,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昼夜。
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长得像没有尽头。
那时的我,暂时在奎依巴格镇一家工厂做工。
每天,当下班铃声像往常一样在厂区回荡,穿着工装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像黑压压的潮水,从厂区大门喷涌到马路上。
马路笔直宽广,新疆杨的树叶在暮春暖水般的夕照中,有一种金灿灿的慵懒。那些年轻的面孔,也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
每一天从此刻开始,我和他们走向家庭,走向菜市场——走向相似的命运。
我骑着自行车夹在他们中间,熟练地按着车铃,灵活地变道。偶尔回过头看身边的他们略带疲惫的脸。板结的脸——自行车流在马路上拐弯的时候,他们一个挨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朝前驶去,那背影让我突然想到:“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不知谁比时间活得更长——”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我曾在这本书的这句话下划过一道线。
又一个春天的早上,好像是清晨8点左右,我走出家门,微亮的天色有一种昨夜暗暗修补过的、稚嫩多汁的蓝。但我感觉院子有什么不一样了。空气微微紧绷,我的心微绷,嗓子眼也是绷着的,半天才吐出“啊——”这个字。
“啊——”的一声刚出口,便是对世间某一事物最好的最极致的赞美。
这棵梨树终于开花了。
不,不是开出花来,而是花朵喷射出来——那么多脆弱的白色花朵簇拥在干枯、苍黑、遒劲的枝丫上,以磅礴的力量,犹带激情般喷射出,风一吹,花瓣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我一下子感到周围所有的人都静止了。画面凝固了。
一树的白色花朵开得密不透风,绚烂而又宁静。叶子是新发的,青翠油亮。树梢上一团团喧哗的白与绿对立,它的香气与早春的清寒对立,与周围的世界有着巧妙的切入和神秘的默契。带着不属于尘世的气息,在微风中摇动,仿佛春天正下着一场白茫茫的大雪——
梨树之上的天空,像燃烧一般的蓝啊,蓝得很不真实,让人想到电影《追捕》里的杜丘和真由美。
我站在树下,畏惧它突然的盛开,在这样的蓝天下朝上看,脸被日光照耀得闪闪发亮,被突然的激情胀满喉咙,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某种生活的禁忌被打破,欲望滚滚而来,不能停止的倾诉,滚滚而来。
我感觉自己精神的某一处,正凝聚成一个个生机勃勃的花苞,从某个地方探出头,大声应许此时此刻的微弱存在:我最终会变成那种人,或者终将成为那种人:一部分的我留在此地,而另一部分的我,在遥远处游荡,就要投身到远方热烈而蛮横的生活中去——
1999年夏,我离开了奎依巴格镇。经历了几次人生迁徙,疾病和绝望后,带着对永恒的、隐秘爱情的饥饿感混迹人群,开始了写作。
我从没写过这棵梨树。但我知道,它依然在南疆以南的某个荒僻角落,在蓝得忧伤的天空下,花朵饱含汁夜,独自开败。
有一年秋天,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梨树结果子了。味道酸涩,不好吃。
但我依然爱它,爱这棵梨树甚于爱白杨树——
梨树戈壁滩上长着呢
梨树昆仑山下长着呢
梨树玉龙喀什河边长着呢
梨我家门前也长着呢
风吹倒了戈壁滩上的梨树
风吹倒了昆仑山下的梨树
风把玉龙喀什河边的梨树也吹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