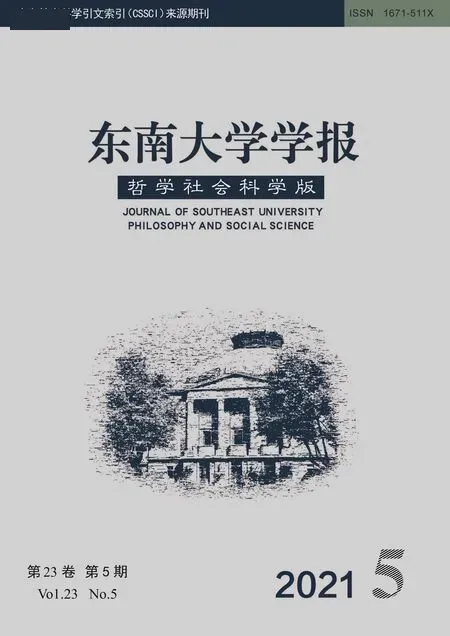中国古代“实录”曲史观辨析
伏涤修
(浙江传媒学院 戏剧影视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实录”曲史观主张剧与史通,历史不仅是剧作表现的对象,也是剧作表现的目的。“实录”曲史观史心浓郁,注重史据,和极力夸张渲染历史人事的“传奇化”历史剧创作观形成鲜明对照。“实录”曲史观虽然深受史官文化影响,但和“实录”史著观具有本质的区别,“实录”史著观要求理性客观地反映历史,反对臆造和虚构,“实录”曲史观则是“文备众体”地表现历史,它并不排斥也无法避免虚构和想像。按照“实录”曲史观创作的“实录”型历史剧只能做到大的历史脉络的真实和历史感的真实,如果过分强调细节的历史真实,反而会使历史剧失去戏剧的剧体属性。本文即对“实录”曲史观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影响进行辨析评价。
一、“实录”曲史观标榜以曲为史,崇尚据史实录
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影响巨大,诗有史,词有史,曲亦有史,一些文人创作历史剧时史鉴用心特别强烈,有些历史剧虽以戏剧样式出现,其根本宗旨却是为了“实录”历史,真实地再现历史风云,以曲为史成为一些文人创作历史剧的最高追求。最为典范的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孔尚任有关此剧创作目的与原则方法的表述,既是他创作《桃花扇》的心声感言,也是他以曲为史史剧观的集中体现。孔尚任明言他创作《桃花扇》是为了通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让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堕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犹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1)[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桃花扇小引》)。孔尚任不仅史心深厚,更是以著述信史的态度来创作《桃花扇》,他“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2)[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桃花扇本末》),为了与史吻合,孔尚任广泛查询史料,专立《桃花扇考据》,其考据目录包括无名氏《樵史》、董阆石《莼乡赘笔》、陆丽京《冥报录》、陈宝崖《旷园杂志》、余澹心《板桥杂记》、尤展成《明史乐府》、张瑶星《白云述》、王世德《崇祯遗录》、侯朝宗《壮悔堂集》、贾静子《四忆堂诗集》《侯公子传》、钱牧斋《有学集》、吴梅村《梅村集》《绥寇纪略》、杨龙友《洵美堂集》、冒辟疆《同人集》、沈眉山《姑山草堂集》、陈其年《湖海楼集》、龚孝昇《定山堂集》、阮大铖《石巢传奇》等。孔尚任还到南京、扬州等地实地采访,“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3)[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页。(《桃花扇凡例》),他历时十多年三易其稿才精心完成《桃花扇》,“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4)[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桃花扇本末》),追求历史真实乃至历史细节真实,是孔尚任《桃花扇》创作的根本追求。
在孔尚任等曲史派的心目中,“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据史实录,在戏场上呈现历史风云是他们最庄严的创作目的。冯梦龙称自己评改的《精忠旗》“从正史本传,参以《汤阴庙记》事实,编成新剧……然夫妇同席,及东窗事发等事,史传与别纪俱有可据,非杜撰不根者比”(卷九“《精忠旗》”条引冯梦龙《精忠旗叙》)(5)[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341页。,把依据史载作为历史剧创作的正途。孙郁《天宝曲史》反映唐天宝年间实事,作者宣称“是集俱遵正史,稍参外传,编次成帙,并不敢窃附臆见,期存曲史正意云尔”(《凡例》)(6)[清]孙郁:《天宝曲史》,《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影印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卷首第2页。。《鹤归来》是瞿颉为敷演其族祖瞿式耜祖孙二人事迹而创作,瞿颉自谓《鹤归来》情节全有所本,“《鹤归来》者,为族祖留守稼轩公、检讨寿明公祖孙二人作也。……其中情事,悉按《明史》及《粵行纪事》所载,以归核实。庶使观者知祖孙二人,扶纲植常,为不朽盛事,初非稗官小说子虚乌有之比”(《鹤归来·自序》)(7)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077-2078页。。董榕《芝龛记》以石砫土司秦良玉、道州守备沈云英两位女英雄事迹为主线,反映明万历、天启、崇祯至明清易代之时的政局和史事,作者言“此记大意,为秦忠州、沈道州二奇女衍传”,“所有事迹,皆本《明史》及诸名家文集、志传,旁采说部,一一根据,并无杜撰”,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也来源有自,绝不妄加虚构,“如小丑脚色中,石砫、小奚、来狩,见褚稼轩《坚瓠集》。顾昆山青衣马锦,取侯朝宗《壮悔堂集》,余仿此”(《芝龛记·凡例》)(8)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12-1715页。。汪廷讷《义烈记》演“东汉党锢之事,……剧中皆纪实多,本《汉书》列传”(薛应和《义烈记·序》)(9)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280页。。丁靖传《沧桑艳》演绎吴三桂、陈圆圆事,同样颇重考据,剧前附《陈圆圆事辑》,载录《明史流贼传》、《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陆云士《圆圆传》、纽玉樵《圆圆传》、丁靖传《圆圆传辑补》;然后附录各家不同的说法,包括明内臣王永章《甲申日记》、水居士《愤言》《〈新义录〉引〈天香阁随笔〉》、近世新出《圆圆记》等,作者言附录“数条与诸说异,存之以备参考”,其中水居士《愤言》后丁靖传加了按语,言此条“殆非事实,附存一说,以备参考”(10)[清]丁靖传:《沧桑艳》,清刻本,第14-15页。,作者既大量搜集史料广采众说,又谨慎甄别史料和各家之说,显示出作者如同治史一样的写剧态度。黄振自称《石榴记》“依本传考核,南宋端平时事,绝非臆撰”(11)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929页。(《石榴记·凡例》),夏纶《惺斋五种曲》对于所写的人和事“人其人,事其事,莫不名载国史,显有依据,绝非乌有子虚之比”(查昌甡《五种·总跋》)(12)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43-1744页。,也都是较为严格地依据史载创作的历史剧,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剧作者的实录精神、对历史记载的尊重。
二、“实录”型历史剧虽重史据,但都存有虚构
虽然“实录”型历史剧作家们强调剧依史载,但即使是非常注重史实考据的《桃花扇》,有违史实之处也很多。梁启超《桃花扇注》依照史料比勘剧本,对于剧中不合史载之处多有列指,下面列举几处:
《桃花扇》中有多出情节无史载依据,“此出并无本事可考,自当是云亭山人渲染之笔”(第三出《哄丁》注一)(13)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60页。,“闹榭亦未必实有其事,不过借以写复社少年骄气”(第八出《闹榭》注二)(14)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33页。,第十四出《阻奸》写侯朝宗劝阻史可法拥立福王事,“朝宗是时是否在史公幕,无可考。以阻奸事归朝宗,云亭点染耳”(第十四出《阻奸》注一)(15)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05页。。《桃花扇》中有些情节有历史依据,但剧中所写却与史载不合,如关于阻止左良玉军队东下事,历史上“事却与杨文骢无涉,《桃花扇》牵入文骢,渲染之笔耳”(第十出《修札》注二)(16)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52页。;再如剧中写侯朝宗、陈定生、吴次尾三人均被权奸逮捕,而历史上只有陈定生一人被捕,“然则当时被捕者只有陈定生一人,而吴次尾、侯朝宗皆逃而免。此文演三人同时被捕,点缀之笔耳”(第二十九出《逮社》注一)(17)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25页。;第三十一出《草檄》所写,“据吴梅村《楚两生行》,苏昆生在左良玉幕中似颇久,侯朝宗并无入狱事。苏之谒左,并不因侯。此出情节,作者虚构耳”(第三十一出《草檄》注一)(18)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55-156页。;“柳敬亭东下,乃为左良玉交欢阮大铖,并非传檄”,“敬亭下狱事全属虚构”(第三十三出《会狱》注二)(19)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83页。;福王从出奔至被田雄挟降,“前后凡经十二日,本出演为两日事,乃剧场从省略耳,非当时事实”(第三十七出《劫宝》注三)(20)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33页。。从人物安排来看,《桃花扇》中张瑶星曾任锦衣卫,然而历史上“瑶星未尝为锦衣卫堂官,不过荫袭千户虚爵耳。云亭殆敬慕瑶星之为人,欲用作全书结束,故因其曾荫锦衣,巧借以作穿插耶”(第三十出《归山》注一)(21)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39页。;剧中演杨龙友在清兵渡江后弃官潜逃,而历史上杨文骢虽曾依附马士英,但在清兵渡江后他率众抗击清军,身负重伤被执,清军劝降不成,乃将其杀害,清军重兵压境时,“杨文骢仍赴苏松巡抚任,与清兵相持,败后走苏州。清使黄家鼐往苏招降,文骢杀之。走处州,唐王立,拜后部右侍郎,提督军务,图复南京。明年(丙戌)七月,援衢州,败,被禽,不屈死。事详《明史》本传。《桃花扇》颇奖借龙友,乃不录其死节事,而诬以弃官潜逃,不可解”(第三十六出《逃难》注二)(22)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22页。;再如史可法死节实况,剧中所演“无稽甚矣”,“云亭著书在康熙中叶,不应于此等大节目尚未考定,其所采用俗说者,不过为老赞礼出场点染地耳。但既作历史剧,此种与历史事实太违反之纪载,终不可为训”(第三十八出《沉江》注一)(23)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43-244页。,“据此,则扬州垂破时,侯朝宗尚在史幕,大约自高杰死后,朝宗与史公相依顾久。本书于其间叙入狱、访棲诸节,皆非事实”(第三十八出《沉江》注二)(24)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44页。;剧作主人公侯朝宗,《桃花扇》写他最后出家保持了晚节,梁氏对比史实道:“侯朝宗并无出家事,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中副贡生,越三年而死,晚节无聊甚矣。……剧场搬演,勿作事实观也。”(第四十出《余韵》注二)(25)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295页。
张燕瑾归纳“《桃花扇》所写内容与史实之关系,就其大者而言,有四点与史不合”,“一是更动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二是改变了主要人物的结局”,“三是人物事迹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四是无中生有凭空结撰”(26)张燕瑾:《历史的沉思——〈桃花扇〉解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章培恒也指出,“人们常把《桃花扇》称为历史剧,甚至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但考诸实际,剧本所写,乖于史实者不少”(27)章培恒:《〈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章文列举剧中有关福王之立、侯方域入狱、侯方域与史可法关系、侯方域与李香君关系方面与史实的乖违,甚至认为“《桃花扇》所写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非事实”(28)章培恒:《〈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标榜实录考证的历史剧,和真实历史依然有不小的偏离。
被人们奉为信史的《桃花扇》都有如此多的虚构,其他历史剧更是不免虚构渲染之笔。冯梦龙称自己评改的《精忠旗》严遵史传,然而《精忠旗》中与史籍不合之处很多,有的增删虚撰的程度还很大。《精忠旗》第二出《岳侯涅背》写岳飞令张宪在其背上刻涅“尽忠报国”四字,张宪涅刻并无史载依据。第四出《逆桧南归》写秦桧之妻王氏与金帅、金国四太子兀术有私,秦桧、王氏受兀术派遣回宋朝充当细作,第十三出《蜡丸密询》写兀术写信给秦桧密授机宜,让秦桧逼迫岳飞撤兵,同时兀术私送情书给王氏,均为缺乏史据的情节,尤其写秦桧为金国奸细,纯为无稽之谈。第二十八出《银瓶坠井》写岳飞的女儿银瓶、妻子李氏在闻知岳飞、岳云被害之后跳井身亡,第三十出《忠裔道毙》写岳飞的另四个儿子雷、霖、震、霭均被谪徙押送岭南,岳震病死,岳霭跳潭身亡,岳雷、岳霖被押送的公差结束了性命,虚构成分很多,历史上岳飞并无叫银瓶的女儿,妻子李氏也未跳井身亡,除岳云是与岳飞一起被害、岳雷在岳飞平反前夕死于流放地外,岳飞其他儿子在历经流放后被生还召回,“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用中书门下省请也。于是飞妻李氏与其子霖等皆得生还焉”(卷一九三“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29)[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252页。。第三十七出《存殁恩光》写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岳珂与太学生程宏图上朝为岳飞辩冤,皇帝(宋高宗)下诏为岳飞平反,也与历史不符,历史上岳飞冤案是在宋孝宗受禅登基以后才得以昭雪,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岳珂并没有参与到岳飞冤案平反中来。《精忠旗》剧尾写高宗朝将秦桧、张俊、万俟卨三人罪状颁告天下,也乃与史有违的戏剧安排。
蔡廷弼《晋春秋》传奇是表现春秋时晋国历史的历史剧,作者创作此剧颇具史鉴之心,不过他坦承剧作对史实有所删削增造,创作手法上有“移屋就树”“烘云托月”等法,他在剧作中运用文学手法的原因就在于《晋春秋》是剧而非史,“然则史事可以意为删削增造欤?曰:此非史也,而传奇也”(《晋春秋·凡例》)(30)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981-1982页。。孙郁《天宝曲史》号称剧作情节全有依本,然而剧中与杨贵妃争宠的梅妃只是一个历史上不存在的影子人物,虽然梅妃形象不是作者的臆造独创,此前小说戏曲已经出现,但依然可以看到《天宝曲史》和正史差距不小。
于此可见,历史剧再如何注重史据和实录,从本质上说也只是剧而不是史,虚构和更改史实是历史剧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特征,历史剧的“实录”和历史著作的实录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三、“实录”曲史观和“实录”史著观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实录本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在位期间的大事,自南朝梁周兴嗣撰著记述梁武帝事的《梁皇帝实录》,历朝皇帝实录不断。由于实录是依据原始档案及皇帝起居注等第一手资料修撰而成,所记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及主要内容等方面,大都有史实根据,所以历代修纂正史,多取材于实录。
传信不传伪,注重可靠史据,历来是史家信奉的准则。《谷梁传》“桓公五年”言:“《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意为史著撰写应秉持客观审慎的实录态度,可信的,就作为可信的留传下去;可疑的,仍然作为可疑的留传下去。史著不能臆造想像,要有一说一,缺一不造一。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对史著和传闻及两者关系有精辟阐述,刘勰认为史著必须“务信弃奇”,对于不可信的东西,宁可从略或不写,也不可以穿凿附会追求奇异。“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资料有可疑的便从缺,因为要尊重真实的历史;而传闻(包括文学创作)则不然,“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对听到的事要夸大它的事迹,记载遥远的事也要猜测它的详情细迹,传闻运用到史著撰写中就会产生穿凿附会以讹传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过去史书上没有的,我把它记载下来以炫耀我知识的广博,这无意中就会发生错误,“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31)[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7页。,想像与夸大其辞是发生错讹的根源,是记述远古历史的大害。刘知几《史通》更是明确表示史著载述的历史事实要宁缺勿滥,“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史学家应“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卷五《采撰第十五》)(32)[清]刘知己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7-118页。,要求史著撰写中只重可信的史据,完全排除传闻疑讹之言。
经过历代史官的史书修纂实践和史家的史学阐述,实录成为史书撰著中坚持不易的精神、法则。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史心浓郁的历史剧作者也把据史实录当成历史剧创作的庄严追求。不过,历史剧所追求的信史实录和史著体现的信史实录不在同一层面,“实录”曲史观无法达到历史事实尤其是历史细节的客观真实,它追求的是历史本质、历史逻辑的真实和创作态度的严谨。
具体而言,“实录”曲史观和“实录”史著观的区别,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性质不同,“实录”史著观是针对客观的历史事实真实而言,“实录”曲史观和“传奇”曲史观相对来说,是针对历史剧和历史记载的关系。童庆炳提出历史1、历史2、历史3的概念,他认为“历史1”指的是“历史的原貌”即历史的客观真实,“历史2”指的是“历史典籍”或言历史记载,“历史3”指的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33)童庆炳:《“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由于历史2即历史典籍、历史记载也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筛选和评价,里面包含了主观、不尽可靠的成分,故历史2和历史1(即原本的真实的历史面貌)并不等同,“实录”史著观就要尽量挖掘隐藏在史书后面的真实历史。例如,赵氏孤儿事,《左传》和《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和《史记·赵世家》的记载不一致,究竟赵氏被灭族的过程和原因是什么,历史上有没有屠岸贾,屠岸贾是不是致赵氏灭族的罪魁祸首,《史记·晋世家》和《史记·赵世家》哪个书写更接近历史的真像,探讨这些是“实录”史著观的事。
而“实录”曲史观,是和“传奇”曲史观相对而言,“传奇”曲史观只取历史中的一些人事作为因由,不顾历史记载而随意或夸张地进行渲染改易,“实录”曲史观指的是历史剧创作应当尽量依据历史记载,不能以游戏历史的态度来创作历史剧,不能随意离开史载仅凭臆造和想象编写历史剧。元代纪君祥,依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创作出《赵氏孤儿》杂剧,剧作内容虽然未必符合历史的原貌,但情节大体符合《史记·赵世家》,我们可以认为《赵氏孤儿》杂剧是按照“实录”曲史观创作的尊重历史记载的历史剧。
二是手段不同,“实录”史著观要求如实记录,不允许臆造和随意发挥,“实录”曲史观则允许文学想象和艺术再造。“文之与史,较然异辙”(34)[唐]刘知己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0页。(卷九《核才第三十一》),“实录”史著观要求用史料说话,用科学语言理性地再现客观历史,“实录”曲史观要求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发挥艺术创造性,用文学语言鲜活地表现创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孔尚任一方面言《桃花扇》“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35)[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桃花扇本末》),另一方面也承认剧作在剧情和细节上“稍有点染”(36)[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1页。(《桃花扇凡例》),另外我们从梁启超等对于《桃花扇》所涉史实的考证,也可以看到《桃花扇》有违实录之义者不少。其他标榜“实录”的历史剧同样存有虚构。
之所以连《桃花扇》这样的“实录”型历史剧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虚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剧是剧不是史,它要进行艺术再创造,历史剧无须也无法做到历史事实的照相式实录真实,只能追求历史精神和历史逻辑的真实。史著重在客观实录,而历史剧必须重视故事性和艺术感染力,“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37)[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页。(《桃花扇小识》),为了把奇事生动地演绎出来,传奇(即戏曲,包括历史剧)不得不借助各种手段,“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38)[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桃花扇小引》),只有加以点染、摹写,才能把历史事件贯穿起来,使历史人物鲜活起来。历史著作是尽力复原历史图景,而历史剧只能是通过剪裁史料借助文学手段再造历史图景。虽然历史剧创造要基于史实,但面对大量的史料,历史剧作家必须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审虚实,人物塑造要语求肖似,剧作成效要重机趣,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通过各种文学手段,因此历史剧创作中文学想象和史料剪裁必不可少。
三是评价标准不同,“实录”史著观不允许违背历史真实的情况存在,“实录”曲史观只能做到大的历史脉络的真实和历史感的真实。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人物传记中虽然不免有想像,但不允许有事实偏差,也不允许把撰述者的个人好恶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秉持“实录”史著观的史家,对待笔端历史人物,不以撰述者的好憎态度,而以历史人物自身行事的善恶来评价,“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39)[唐]刘知己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02页。(卷十四《惑经第四》)。而历史剧包括“实录”型历史剧,作者褒贬爱憎的情感态度很鲜明,为了传达自己的创作主旨,剧作者总不免增删改易史料,情节和细节上总不免有和史实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桃花扇》写阮大铖欲通过杨龙友交好侯朝宗,他给侯朝宗、李香君赠送妆奁之资,然而剧中所写穿线中间人、阮大铖纳交手段和纳交时间均和历史实际不符,“大铖所夤缘以纳交者并非杨龙友,其纳交手段亦非赠香君妆奁,其事又在崇祯十二年而非在十六年,读朝宗所作《李姬传》自悉。……云亭度曲,惟取其意,而稍易其人其事及其时,既非作史,原不必刻舟求剑也”(40)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119-120页。(第七出《却奁》注一),梁启超虽然是以史家的眼光给《桃花扇》作注,往往指出《桃花扇》情节和史实的相违,但他对《桃花扇》此处有关史实的改易完全持认可的态度,原因就是史剧非史,不必用评价史著的标准评价历史剧。再如第三出《哄丁》所写为本事无考的渲染之笔,然而“当时之清流少年,排斥阮大铖实极嚣张且轻薄”,故梁启超认为,“观此可见当时复社诸子骄憨之状,‘哄丁’一类事,未始不可有也”(41)梁启超:《桃花扇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据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第60页。(第三出《哄丁》注一),《哄丁》出虽无确切史据,依然符合历史逻辑的真实,不算违背“实录”曲史观。
四、“实录”曲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按照“实录”曲史观创作的历史剧,虽然从概念上讲不等同于真实历史,但由于创作者史心浓郁注重依据历史记载进行演绎,故往往能起到史鉴之效。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言及《桃花扇》演出时观众的反映,“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42)[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明代“故臣遗老”之所以掩袂而泣、唏嘘伤心不已,就是由于《桃花扇》唤起了人们对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那一段刻骨铭心历史岁月的记忆,使他们深陷剧作营造的历史情境而悲不自禁。吴陈琰赞誉《桃花扇》为南明信史,“谱成抵得南朝史,休与《春灯》一例传”(43)[清]孔尚任:《桃花扇》,《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页。(《桃花扇·题辞》);刘中柱盛赞《桃花扇》“一部传奇,描写五十年前遗事。君臣将相、儿女友朋,无不人人活现,遂成天地间最有关系文章。往昔之汤临川、近今之李笠翁,皆非敌手”(44)[清]孔尚任:《桃花扇》,《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剧末跋语第1页。(《桃花扇·跋语》),陈四如称赞《桃花扇》“以桃花扇而诛乱臣贼子,以桃花扇而正世道人心。……《桃花扇》之义大矣哉”(45)[清]孔尚任:《桃花扇》,《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剧末跋语第2页。(《桃花扇·跋语》),黄元治认为《桃花扇》“作史传观可,作内典观亦可”(46)[清]孔尚任:《桃花扇》,《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剧末跋语第1页。(《桃花扇·跋语》):诸家评论,都是着目于《桃花扇》的史鉴之效。董榕以“实录”笔法创作《芝龛记》,剧中厚重的政治、军事斗争内容,使人们犹如感受到了明末纷纭多变的历史风云,剧作获得了文人、史家的交口称誉,蜗寄居士称《芝龛记》“虽名传奇,却实是一段有声有色明史,与杨升庵《全史谭词》当并垂不朽”(47)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25页。(《芝龛记·末出总评》);《光绪遵化通志》卷五十八“艺文·集部”只著录《芝龛记》这一部戏曲,且以较大篇幅引述董榕的《自序》和黄叔琳等人的《他序》(48)[清]何崧泰、史朴纂修:《光绪遵化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22)》,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3页。,同时评价《芝龛记》“组织明室一代史事,思精藻密,足为龟鉴,当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并传不朽,不得第以传奇目之”(49)[清]何崧泰、史朴纂修:《光绪遵化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22)》,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21页。(卷五十四“列传·国朝·九·董榕”条),于此《芝龛记》在《光绪遵化通志》作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实录”曲史观严肃地对待历史和戏曲创作,提升了戏曲的地位和品格。在文人心目中,传奇是小道,“传奇虽小道”(50)[清]孔尚任:《桃花扇》,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51)[清]李渔著,单锦珩点校:《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李渔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页。(李渔《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填词虽小技”(52)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743-1744页。(查昌甡等《惺斋五种曲·总跋》)。只有使传奇具有史鉴或垂诫功能,才能发挥传奇戏曲的风化教育作用。按照“实录”曲史观创作的历史剧,剧与史通,提升了戏曲的文体品格,吴梅认为《桃花扇》的信史写法,“传奇之尊,遂得与诗词同其声价矣。……故论《桃花扇》之品格,直是前无古人”(53)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609页。(《桃花扇·跋语》)。许廷录《五鹿块》反映春秋时期晋国重耳事迹,许廷录之孙许琴南把其祖创作《五鹿块》提高到著述《春秋》的高度,“夫传奇说剧行世者甚多,无非惩恶劝善。善恶之迹,往往见于史书。……此吾先祖演《五鹿块》之志,即作《春秋》之志也夫”(54)蔡毅编著:《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1562页。(许琴南《五鹿块·序》),这样的传奇就决非小道,具有了和史著经书一样的价值。
“实录”曲史观反对随意臆造的传奇化倾向,避免了胡编乱造的恶俗之趣。有些历史题材戏曲,过分偏离史实,完全不重历史记载,随意编造,不仅失去历史的本来面貌,有的甚至荒诞无稽,这样的过分传奇化的历史剧不要说没有反映历史的客观真实,就连历史情境、历史感的真实都大打折扣甚至荡然无存,过分臆想乱编的历史题材戏曲,徒披历史剧的外衣,和非历史题材的戏曲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历史剧创作中的浊流。提倡“实录”曲史观,正可以激浊扬清,保证历史题材戏曲不过于偏离历史剧应当遵循的创作轨道。如《曲海总目提要》批评《吉庆图》:“演明世宗时海瑞严嵩事,增饰点缀”,“作剧者浅陋无学,但闻明代有海瑞、邹元标,皆忠直之士,妄相纽合,不知相去辽阔,甚可哂也!”(55)[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993页。(卷二十七“《吉庆图》”条)再如《金钢凤》:“记五代吴越王钱镠事,以稗史中金刚女与镠相遇之说,而缘饰之。金刚者,言此女名铁金刚也。凤者,言王妃名李凤娘也。与正史全不合,说甚荒唐。”(56)[清]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本,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045页。(卷二十八“《金钢凤》”条)晚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传奇固不碍与史相出入,大节目亦不可不依也。”(57)[清]李兹铭:《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347页。李慈铭此处传奇实即指历史剧,历史剧可以和史实有出入,但虚构必须有度,大的脉络必须依据历史。历史剧如果虚构过度,不仅有违历史真实,也会造成历史感和艺术感的失真,也就必然会伤害到历史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实录”曲史观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环境的产物,“实录”曲史观尊重历史,注重史据,“实录”型历史剧不仅能真切地传达作者的史心,也能在不识字人占多数、听书看戏作为人们了解历史主要渠道的古代,给观众传播、普及较为符合历史真实的历史知识。当然,在肯定“实录”曲史观和“实录”型历史剧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历史剧不能过于依赖史载,如果过分依据史书而不知变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剧作就会失之于拘泥,进而也会影响历史剧的艺术感染力。
——从《桃花扇》序文看孔尚任创作心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