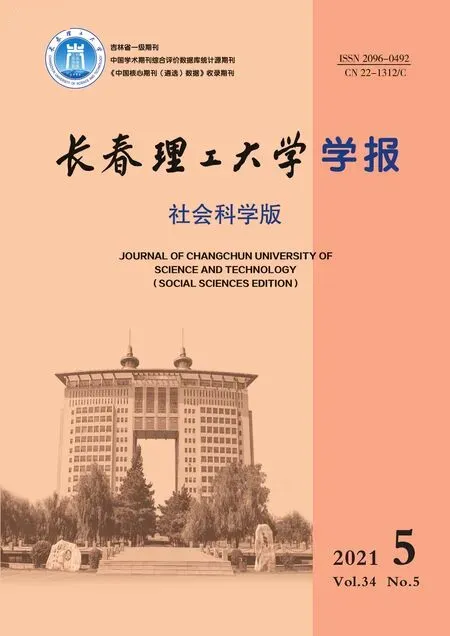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审丑性透视
付兰梅,乔文东
(长春理工大学,吉林长春,130022)
当代河南作家刘庆邦自创作以来便立足于平民立场,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生活的真善美,揭露假恶丑,并通过对丑的揭露来达到唤醒美的深层目的。
刘庆邦的300余篇短篇小说的风格可大致分为“柔美”“酷烈”与两极之外的其他风格三类,其中以“柔美”风格为主的作品有近百篇,如《梅妞放羊》(1998)、《鞋》(1997)、《小呀小姐姐》(1995)、《玉米地》(2008)、《眉豆花开一串白》(2006)等,主要展现了对故园、人性美的眷恋。以“酷烈”风格为主的不下百篇,如《走窑汉》(1985)、《鸽子》(2005)、《福利》(2005)、《兄妹》(1995)、《四季歌》(2007)、《做满月》(2007)等作品,透视了社会的冷峻与人性的黑暗。以《大活人》(2003)以及“保姆在北京”的现实题材系列为代表的其他几十篇小说,则“似乎从柔美与酷烈的两个极致中走出来,也是从民间的想象中走出来,走进现实的世界里”[1]。
学界对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关注多集中在审美层次上,对其审丑意义的研究则稍显不足。评论界更多关注其作品柔美的一面,对其后者“酷烈”风格作品的审丑层面上的关注则相对较少。“从主客体关系方面讲,所谓审丑是非和谐的对象在主体(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方面引起的否定性情感判断和否定性价值判断。从主体方面来讲,审丑是指个体对丑的否定性或作为否定性的丑的判断、品评、鉴赏、批判、宽容、改造等各种能力的总和。从客体方面来讲,审丑是指把握丑的否定性本质及其形态在社会历史中的演变和作用,其中包括作为否定性的客观对象的审丑活动本身。”[2]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审丑的维度来解读刘庆邦的小说创作,更能彰显其短篇小说的审美价值。
一、刘庆邦短篇小说审丑的含混表达
“含混”(Ambigu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本意为“更易”,自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1906—1984)发表《含混七型》后广泛用于文学批评中,多表达为一种模糊性和多重阐释性。在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中,作者对于涉及到人性丑的描写也多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来表现,除了直接表现以揭露存在的丑陋现象之外,更是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去展现审丑的复杂与矛盾。
小说《兄妹》中哥哥拿着妹妹出卖自己身体的钱去嫖娼,不以为耻,反倒以一句“兴啥啥不丑”来欺人以自欺。同样《三月春风》(1995)中从农村走出去的朱科在有了一定地位后禁不住某些不良风气的诱惑找了自己已为人妇的同学当情人,对诸如此类的丑陋行径的揭露都展现了刘庆邦在时代风云变幻中不沉湎于对发展和美的赞颂,而更加重视对快速改革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冷峻的思考并把这些丑的现象展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审丑是作为审美的反题衍生出来的,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审丑的认识上不一而足,在被认可的脱离审美附庸之后的审丑又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即从审丑维度去认识事物时,我们对于丑和美的古今认识会出现一定的混淆,当从一个视点认定一个事物丑的同时,又有人从另一个视点揭示它的美,这些视点多从心与物、形式与内容、主观与客观、相对性与绝对性等不同角度对丑进行正论与反论的辩证性分析。
如果说以上的两篇小说是对丑的直接揭露,那么在《走窑汉》(1985)、《晚上十点:一切正常》(1998)、《屠妇老塘》(1993)、《别让我再哭了》(2002)、《响器》(2000)、《幸福票》(2001)等小说中则充满了作者对审丑的含混表达。在刘庆邦的成名短篇小说《走窑汉》中,矿工马海州的妻子被队长张清奸污以后,作为男性的马海州,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在煤矿生存场域下男性的话语权而被人轻视,这与莫言所写的民间的暴力与野性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都在推崇一种来自民间的雄强美,而这种美是在游离于现代性之外所建立的。而从现代性视角来看,它无疑又是丑的,在美与丑、正义与邪恶之间表现了一种含混性。而后,毫无疑问,马海州遵从了这种无规约的规约,没有选择报警和走法律途径,而是自己拿刀捅了队长张清并因此坐牢。在这里又出现一对矛盾,马海州选择以一种不失去在煤矿作为男性的主体地位的方式拿刀捅了张清,此时他保住了他在煤矿生存场域下的男性话语地位,但却因此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作为伤害者的张清由于被刺了一刀而成为了被害者,这种被害者身份的确立却消隐了他的伤害者身份从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只是被降了职。而此时作为最大受害者的田小娥却没有任何话语权,甚至都没有给予她应有的人性关怀。在这里,作为民间“雄强美”代表的马海州取得了权力占位,作为伤害者的张清的丑恶却被作者有意遮蔽(这种有意被读者发现的遮蔽反而更能引起读者关注,从而使这个层面的审丑意义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而作为男性绝对权威下的最大受害者田小娥的失声同样是作者有意遮蔽后对于绝对男权的审丑强化,以含混的形式表达文本的多义性。
在《晚上十点:一切正常》中,煤矿的瓦斯爆炸看似是由于检查员李顺和溜号误工去小煤窑背煤赚钱导致的,但是煤矿经营不善,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大家都偷偷去小煤窑赚钱补贴家用,而李顺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客观来看他的行为和导致的后果是令人愤怒的,但考虑到实际情况和他的动机与无奈,这种看似“丑”的行为也应当被适当原谅。在《屠妇老塘》(1993)中,由于丈夫矿难去世,晏子一个人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艰难生活,衣食无着,万般无奈。后来有几个坏男人见她有几分姿色便拿几个钱来引诱她,迫于生活的艰难晏子便跟人睡了,以此来赚一些钱补贴家用,抚养孩子,从客观上尽管晏子选择通过做一些皮肉交易来赚钱的行为是丑陋的,但她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家庭与孩子选择牺牲自己去赚钱的方式便制造了一种审丑的含混表达,使我们对晏子的行为在厌恶之余注入了一丝同情。而《鸽子》中的煤矿老板表面上逢迎领导、苛责旷工,而背后却有着难言的苦衷并且不乏对矿工的关怀。《别让我再哭了》(2002)塑造了一个靠哭来给矿上解决麻烦的工会主席孙宝川,但实际上他的哭是一种负责任的哭,是一种为工人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凡是难以解决的矿难,只要孙宝川出马情真意切地大哭一场再加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一番说辞,准能解决问题,这本来是讲官僚主义及领导的不负责,而当读完小说后我们发现,刘庆邦有意在文本中制造一种隐含意义,客观上给我们展现了审丑的含混表达。类似这种审丑含混表达的小说还有《响器》(2000)中高妮对理想不懈追求的执着美与现实的冷峻残酷;《福利》中矿老板表面上的冷酷实际却减少了矿上的伤亡;《幸福票》(2001)中看似孟银孩攒幸福票(矿主发的嫖妓的票券)的丑陋行为的背后,潜藏的是孟银孩想用幸福票去换钱照顾家里的愿望;《看看谁家有福》(1980)中通过集体的人心异变和个体中仍有人保持的原有的纯真与善良的对比展现了审丑的含混之处。在《我和秀闺》(1981)、《地层下的笑声》(1982)、《汉爷》(1991)、《女儿家》(2002)、《走新客》(2002)、《舍不了那闺女》(2004)、《游戏》(2006)、《远山》(2008)、《送礼》(2007)等一系列小说中都呈现出审丑的含混表达。
只有透过刘庆邦短篇小说审丑的含混表达,并进一步挖掘其审丑的含混表达背后的主观意图,才能对其作品的审丑意义做出更加全面的把握。
二、刘庆邦短篇小说审丑的“心物二元”
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认为“心灵不是存在,物质无思维,两个相对实体独立存在,互不干涉,彼此平行,构成了两个世界本原”[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心物二元论”的哲学体系,在认识过程中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存在过度唯理论而难以平衡物质与心灵的弊端。如果说我们把上文论及的含混表达视为审丑的客观呈现,而“心物二元”则可以看做这种客观呈现背后的主观意图。
在《鸽子》中,黑色的煤矿与汤小明养的一群鸽子便在文本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象征了煤矿虽黑、煤矿工人虽黑,但是煤矿本身和那些矿工的心灵就像鸽子一样白,一样纯洁,这是作者以鸽子作比来从形式与内容角度辨证地看美与丑。如煤矿老板牛矿本身想要保护自己的员工却又不得不应付那些手握权柄的官员们,不得不牺牲汤小明的鸽子去讨好王所长,但没想到遇到态度十分强硬的汤小明,不得不跑几十里山路买了骡子肉又送钱给王所长才算了事。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一组对比,那些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们看似威风八面,实则乃是作者笔下丑恶的代表,是“心物二元”的正题。小说结尾是点睛之笔,死活不愿卖出鸽子的汤小明以为得罪了矿长,被解雇了准备要走,而矿长的一句话“不回去还愣着干什么!袋子里装的是不是鸽子?快把鸽子放开,那样时间长了会把鸽子闷坏的”[4]则更显余味悠长,作为老板的牛矿在遇到这样的员工后非但没有处罚他,还出乎意料地关心鸽子,这就使得人物形象有了立体感与层次感,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心灵的美与外现的丑是可以对立并存的,即我们所说的“心物二元”,但这种对立却蕴含着统一的美,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矿长先入为主的审丑想象此刻也得到了消解。
《别让我再哭了》这篇小说重点描写了工会副主席孙宝川以哭来处理矿难的过人之处,比如给矿难死去儿子的老两口当“儿子”照顾他们,比如被郑师傅死后儿子女儿的困境所触动,反倒哭求矿长帮他们解决工作等。人的内心与其所表现出的外在形象作为一种对立状态但却并不矛盾,作为官僚塞责态度代表的丑的形象反而使人产生崇高感。
在《福利》中矿主在矿工下井的井口摆上他给矿工准备的福利——棺材,表现出一种谁出事死了直接就能拉走的冷漠态度,矿主的冷漠及行为看似是“丑”的,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煤矿工人这个职业本身便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尽管如此危险还是有一些矿工不遵守规矩带违禁物品下井,这给煤矿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而矿主的这种做法客观上反而时刻在给工人提着醒——死亡,就在你身边,客观上促使工人更加遵守煤矿的规章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安全,具有了“美”的意味。在《幸福票》中刘庆邦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顾家的主人公孟银孩,他拼命地工作挣钱,也挣“幸福票”,看似努力挣“幸福票”这一行为是丑陋的、不堪的,但我们没想到的是别的矿工拿到“幸福票”都去“消费”了,而孟银孩却想着拿“幸福票”去找小姐换成现金补贴家里,他的这一主观行为与客观表现所形成的反差表现了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尽管表面做了令人不解的事却无法掩盖其内心的善良,促成了审丑的含混表达。《屠妇老塘》中晏子为了照顾没了父亲的孩子和家庭,不得已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而这种外在的丑却一点没有掩盖她作为一个伟大母亲的光辉。《晚上十点:一切正常》中李顺和的溜号本应被斥责,但背后流露出缺失家庭生活的难以为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内心的想法与客观的结果出现了矛盾,但这种主观上的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审丑的含混表达。
此外,在《都走吧》(2006)、《送礼》(2007)、《四季歌》(2007)、《远山》(2008)、《捉对》、《血劲》、《五月榴花》等一系列作品中,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心物二元”,才使得刘庆邦短篇小说呈现出多样化的审丑的含混表达。
三、刘庆邦短篇小说审丑背后的美学意义
我们在讨论丑的时候往往是以美作为对照,丑与美相伴而生,审丑与审美也相互依存。在刘庆邦的短篇小说中往往存在诸多丑的现象,但作家给我们展现丑却不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去揭露,去控诉。往深处看,我们往往读到他深层次的对美的渴望,对善良与正义的向往。所以,当我们读刘庆邦的审丑小说时,“不是为审丑而审丑,审丑不是目的,而是策略。它为真美提供了可资的对立参照,并适时形成一种张力完满、真实人性的建立,多元、共生的存在开始奠定勃发的价值土壤”[5]。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重新强化了审美的价值,还丰富了审丑的意义。
我们在上文对刘庆邦短篇小说审丑的含混表达及其主观上的“心物二元”进行了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作家都以审丑为基点倾注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将丑展现出来,让我们发现他笔下的丑并非单纯的丑,而是向美而生的丑,二者成为彼此的对照和共生的土壤。正如我们上文谈到的《鸽子》《福利》一样,作家在“鸽子”“福利”中都注入了美好的象征意义,而在文本中展现的却是老板逢迎领导和矿主的无情与冷漠,这本是一种丑的存在,但随即在后文中老板的面狠心善与矿主主观的冷漠却在客观上减少了伤亡,丑行丑态得以消解,美由此而生。我们在上文所论及的《别让我再哭了》《走窑汉》《晚上十点:一切正常》《草帽》《幸福票》等都在客观的审丑的含混表达和主观的“心物二元”的交织中绽放出审美之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审丑的含混表达甚至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总的来说,在对刘庆邦短篇小说的审丑进行观照时我们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审丑应该是多视角、多层次、多元化的,甚至是含混的。这样的审丑表达带来的强烈的审美陌生化效果,使小说之美更加绚烂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