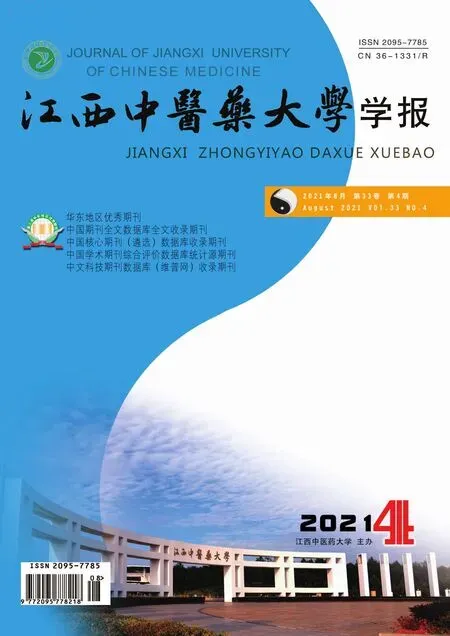新安医家江瓘父子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探析
★ 董妍妍 储全根(安徽中医药大学 合肥 230012)
江瓘(1503—1565),字民莹(或做廷莹),号篁南子,明弘治嘉靖年间安徽歙县篁南人。江应宿,明朝歙县人,江瓘次子。代表著作为《名医类案》[1],成书于1552年,收录了先秦至元明之间自扁鹊至江瓘父子等医家的临床验案约2 400余首,为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既是明以前著名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典范,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和临床诊疗价值。通过对书中江氏父子140余则医案的研究,深感其辨证论治、立法处方、用药施法俱能在继承中求创新,对中医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启示深刻。现就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探讨如下。
1 学术思想
江瓘阅读、整理了大量前人医案,撰集著作《名医类案》,既是对先贤的崇敬,也是对后学者的期望;既是对之前的医学知识的总结和继承,也是在此基础上对诊疗处方用药的创新。他认为论病当重视虚损,其用药多用温补,在此基础上,江瓘父子(即江瓘、江应宿)将自己的临床经验进行整合,结合江南地区区域特色及发病特点,提出“伤寒多属内伤”的观点,将温补思想灵活运用在伤寒病的治疗当中,扩大了伤寒病的治疗,开拓了相关领域的学说。
1.1 重虚损、善温补对《名医类案》中江瓘、江应宿医案进行整理研究,不难看出江氏父子二人善用温补,受类案辑编者个人学术思想影响,无论医案的选择和用药的特点,都偏于温补。
在《内伤》篇中,载有江瓘治疗程钜内伤的病案,患者“肌热多汗,时昏晕不醒,目时上窜,气短气逆,舌上白胎,腹中常鸣,粒米不入”,病症之重是显然的。江诊其脉 “两手脉皆浮大”,便告其家人说:“虚损内伤症也。病虽剧,不死……经云,汗出而脉尚躁疾者死,目直视者死,在法不治。然察脉尚有神,可救也。按此本内伤外感之症,今外邪已去,内伤饮食亦消导无余,惟惊惕房劳失调补,故气虚而汗,又湿热生痰,中气虚,挟痰,故时时晕厥也。法宜补中清痰。”根据脉之有神无神来判断病情的轻重,非精于临证者不能;用“补中清痰”的平易治法来救治危重病症,非老于用药者不能;能辨别外感内伤于疑似之间,更非谙于病机者不能。由此可见,其善用温补治疗虚证之娴熟。江氏临证案例,用药也多选用人参、黄芪、白术、附子类。
其重视虚损温补还体现在《名医类案》所收载的前代医案中。如《伤寒》案中载,元代滑寿治疗一人七月份患发热,服小柴胡汤二剂后,出现恶寒甚、肉瞤筋惕、脉细欲无,以真武汤加附子获效的医案后,江瓘评论说: “汗多亡阳,则内益虚。恶寒甚而肉瞤筋惕者,里虚甚而阳未复也,故宜真武汤,多服附子而效。”为该案使用真武汤并加用附子的用药机制进行了阐说。
1.2 伤寒多属内伤中医学自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奠定理论基础以后,东汉张仲景在继承发扬古代医家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以外感伤寒病为研究对象与实践基础,撰写《伤寒杂病论》,后世将其奉为“方书之祖”,举世宗之,经不断完善后,成“治病之宗本”[2]。江氏认为,“况江以南,温暖之方,正伤寒病,百无一二。”《伤寒论》虽为百代医方之祖,但其法唯宜用于冬月即时发病正伤寒。况凡外感寒者,皆先因动作烦劳不已,而内伤体虚,然后外邪得入,故一家之中,有病有不病者,由体虚则邪入,而体不虚则邪无路入而不病也,属内伤者十居八九。故治疗上需尊丹溪法,“以补养兼发散之法治疗,即伤寒亦用补法也”。
江氏一言,醒示医界重视江南一带虚体伤寒的辨治,倡用补养发散一法。不仅扩大伤寒病的治疗,且为明末张介宾“大温大补兼散”之剂疗治外感热病之先声,也为清代新安医家吴澄提出“外损致虚”奠定基础。
2 临床经验
《名医类案》内容记述详实,“凡察脉、证形、观变、易方,网罗纤悉”[3];涵盖病种广泛,内容全面,治疗方法丰富,为江氏父子临床辨证、遣方、用药方面提供诸多参考。根据书中所辑江氏父子诊疗病案及读案心得共123则,总结临床经验如下。
2.1 重视元气活用成方江瓘重视人体元气,认为伤风、劳瘵、疟疾、麻木、脚跟疮等多种内外科疾患均与元气虚损有关。“元气之虚,曰阳虚……阳虚者,温肺、健脾”(《虚风》),“夫久疟,乃属元气虚寒”(《疟疾》)、“两手指麻木……此热伤元气也”(《麻木》)等。结合江氏疾病的按语及病案中用药特点知悉,这里元气并非仅指肾气及先天之气,更多的指代肾气及中气,且偏于中气居多。
江瓘重视元气,活用成方,力崇“补中益气汤”,该方出自于李东垣《脾胃论》,由黄芪、甘草、人参、当归、橘皮、升麻、柴胡、白术组成,功能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用治脾胃气虚、气虚下陷、气虚发热诸证。方中“参内芪外草中央”,三者共补一身之气,白术、当归资气血化源,陈皮理气,升麻、柴胡升阳举陷,共建补中、升清、举陷之功,临证多有奇效。江氏认为,该方应用广泛,无论中气亏虚,或各类元气耗损之证均可以加减应用。
2.1.1 治久疟江氏认为,久疟属元气虚寒,涉及气血亏虚,脾胃亏虚之证候。胃虚则恶寒,脾虚则发热,故而出现寒热交作、吐涎不食,泄泻腹痛,手足逆冷之证。疟疾久证多有劳伤元气引起,可用补中益气汤加减,如伴有外感证,加川芎;伴停食,加神曲、陈皮。若外邪已去,当实表,补亏损之中气,方选补中益气以实其表。防止久病脾胃虚损,预后不良。
久疟多脾胃俱损,大抵内伤饮食者必恶食,外感风寒者恶食,审系劳伤元气;属外感者,主以补养,佐以解散,其邪自退。内邪用补中益气病自愈,外邪退却即用补中益气实其表。若邪去不实其表,或过发表,亏损脾胃,皆致绵延难治。因此,不问阴阳日夜所发,是否伴有外证,审察病因,属于劳伤元气的,即使有诸症存在,皆宜补中益气汤。如书中记载薛氏治妇人久疟及汪氏治久疟案,多用该方加减。
2.1.2 治下血证明代医家薛己用药偏补养,江瓘极推崇薛己,《名医类案》中收载薛案治疗下血案6则,多用补中益气汤取效。江瓘评价:“丹溪有曰:精气血气,出于谷气,惟大便下血,当以胃气收功。厥有旨哉!故薛立斋之诸案多本诸此。”
江应宿治友人朱姓者,患便血七年,遇寒加剧,伴面色痿黄,六脉濡弱无力,辨证中气虚寒。用补中益气汤,加灯烧落荆芥穗一撮,橡斗灰一钱,炒黑干姜五分,二剂而血止。后单用补中益气十余服以实表。
2.1.3 疗劳瘵损疾古人认为,劳瘵是因瘵虫食人骨髓,血枯精竭而成,不救者多[4]。江瓘认为,此病乃精竭血虚,火盛无水之证,脉多弦数,潮热、咳嗽、咯血,若肉脱脉细数者不治。他认为劳瘵可从阴阳虚实辨证,心肾虚而寒,是气血正虚,“以其禀赋中和之人,暴伤以致耗散真气,故必近于寒,宜”;心肾虚而热,是气血的偏虚,“以其天禀性热血少之人,贪酒好色,肾水不升,心火不降,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故致于热也”;肾虚寒证,治疗当于“温补以复元气”,肾虚热证,当“滋阴养血,凉肝补肾”。同时还有“挟外感邪热”以及“产后血虚,及劳心用力失血,饮食失调,暴伤血虚之症”均属于“正虚”之类,临床需多顾护阴阳气血的调理,采用相应的治法。
其子江少微治方某,年三十余,因劳役失饥,得潮热疾,六脉弦数,宛然类瘵疾,但日出气暄则热,天色阴雨夜凉则否,暄盛则增剧,稍晦则热减,已逾二年。江氏辨证此为内伤脾胃,阴炽而阳郁导致。补中益气汤加丹皮、地骨、阿胶、麦冬、五味子温补元气,滋阴养血而愈。
2.2 治法灵活不拘一法《名医类案》中治法应用广泛,治疗手段丰富,且往往数种并用,所载江氏父子医案,许多治法也是内病治外,外病治内,内外合治及针刺、艾灸、药膏、药酒、药浴、吹鼻、滴耳、吹喉、漱口、擦牙、催吐、敷脐等独特疗法的适时应用和准确把握,整理挖掘这方面内容,对疾病治疗和养生保健大有益处,同时这些验案体现出来的神奇功效对当今医务工作者也有重要启发作用。
2.2.1 外病治内《名医类案》记载有江应宿外病治内之例。如治一妇人颈瘿,因郁怒痰气所成,乃以海藻、昆布、海带、半夏、小松萝、枯矾、蛤粉、通草、龙胆草等合方为末,食后用酒调下三钱,一月愈(《肿瘿》)。他又记述本人某年盛夏北上,途中酷暑,由鞍马之劳,加之饮烧酒、食葱蒜,患痔如荔枝大,用川连一斤,无灰酒七斤,慢火煮黑,滴稠如蜜,加清酒调服,脱然如失,后再发再用,永不复发,应宿认为此疾“勿妄用穿针挂线烂药,内病不除,徒伤正气,致损天命,慎之”(《痔》)。
2.2.2 内病外治《名医类案》同时记载有江氏内病外治之案。江应宿云:“盘肠产乃中气虚、努力脱出,与脱肛同”,主张多服补中升提药,并以蓖麻子49粒去壳捣烂,贴产妇顶心(《盘肠产》)。江曾治张氏子手足疮痍大发,令内服防风通圣散,并与去风湿药煎汤洗之,月余而安(《疮疡》)。再如江应宿以香砂橘半枳术结合热盐熨,灸中脘、夹脐、膏肓等综合疗法治疗其长子伤食腹痛案(《心脾痛》)。又以人参白虎汤内服合白萝卜汁吹鼻中治岳母中暑热证案(《暑》)。皆精深高妙,内病外治,颇能启示后学[5]。
2.2.3 药膏、药酒、药浴治外症《名医类案》记载江应宿有用膏、酒等多种制剂和方法治疗外证的病案。如治程氏“脚发”,脚腿肿起如瓜瓠,赤肿痛楚难支,以广胶合麝香熔如稠膏,摊油纸贴之,外用好醋煮青棉布三片,乘热贴膏外,轮替更换,即肿消(《脚发》)。又治金氏患两臁赤痛痒,疮口无数,脓水淋漓,以猪板油合铅粉、黄腊制膏外用,旬日而愈(《臁疮》)。又治其次子因食杨梅引发遍身面目浮肿,予口服药的同时,取紫苏、忍冬藤、萝卜种煎水洗浴(《肿胀》)。
2.2.4 五官给药治患《名医类案》记载江应宿五官病案用药方式亦颇有特色。如治一妇患喉痹,用蟢蛛窠21片煅成性,枯矾、灯草灰等分,以鹅管吹喉中,即愈(《咽喉》)。治其夫人产后眼眶红烂,用槐树枝合青盐“水飞炒燥”后早晨擦牙洗之而愈(《目》)。治岳母六月劳倦头痛,用白萝卜汁吹入鼻中良愈(《暑》)。
2.2.5 善用单方、验方根据《名医类案》记载,江瓘还善于运用单方验方。如以乌药、香附二味组方,治一妇人“月候不调,常发寒热”,二服后诸症俱减(《师尼寡妇寒热》)。以温酒化下鹿角胶治眉发脱落(《眉发自落》),用桑树汁涂搽治小儿口疮(《口疮》),以生白矾火化滴涂治蛇虫咬伤(《蛇虫兽咬》),以五谷虫治小儿疳积(《疳积》)。治霉疮、顽癣、疥癞、诸顽癣、疮疥积年不愈者,制黄花酒,方用乌梢蛇酒浸,去头尾皮骨净肉一两,木香、人参、川乌、川芎、白芷、花粉、麻黄、防风、天麻、朱砂,当归、金银花各三钱,白蒺黎、僵蚕、白藓皮、连翘、苍术、荆芥、独活、羌活各二钱,沉香一钱,皂角刺、川萆薢各五钱,两头尖一钱,麝香二分,核桃肉、小红枣,各四两,好头生酒十五斤,烧酒五斤,以绢袋盛入坛,悬胎煮三炷香,取出置泥地,过七日服之。另熬苍耳膏,每服加一匕,后以治,俱效(《霉疮》)等。
2.3 四诊之中,贵在诊脉中医提倡四诊合参,其中脉诊在临床的运用甚广。江氏感于“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训,取“博历之意”,搜采“上自诸子列传,下及稗官私谱”中治法奇验之迹,“类摘门分,世采人列”辑录成册,意在“宣明往范,昭示来学”,欲使后学“溯源穷流,推常达变”。医案多详于脉证,江氏认为,诊病须四诊合参,四诊当中,贵在诊脉,脉晰则辨证精准,用药方能对证。
如治疗吴氏子发热证,前医从外感热病,方用五积散等发热剂无效。江氏切脉六脉皆洪大搏指,作虚外受风寒,用参、芪、归、术以补里,防风、羌活以解其表,加山楂以消导之,一服病减半。后因再次发热伴鼻衄、谵语服柴胡桂枝汤出现口干不除,脉象洪盛,按之勃勃然之状,予生脉饮合柴葛解肌汤加生地、黄芩、白芍一服而愈。又孙秀才患伤寒少阳发热证,服小柴胡不效,误投白虎汤后出现唇干、齿燥、舌干、身倦神疲症,江氏切脉带结而无力,辨为内伤证,生脉汤加陈皮、甘草一服,继加白术、柴胡等药而愈。(《内伤》)
对于一些重症急症,江氏更是详细描述脉象,以示后人。江应宿治许翰林颖阳公令叔息血痢,述脉沉细代绝,六脉代绝,少阴脉久久如蛛丝至者,提示胃中有寒湿也,寒湿伤脾,脾虚则不能摄血归源而下行,胃寒则不能食所致(《痢疾》)。饶州吴上舍仆,小腹卒痛,四肢厥冷。诊六脉沉伏,辨为中寒阴症(《中寒》)。浙商朱鹤子忽手足抽掣,由风、惊、火、痰治均无效,江诊之右手三部脉沉弱无力,左手滑大,辨有虚痰之证,由脾虚论治,用归脾汤加减而愈(《虚风》)。
2.4 生克制化,以情胜情《名医类案》收录诸多古代医家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诊疗疾病的案例,例如根据五行“思胜恐”之原理运用情志疗法治疗疾病等。还收录了劝说开导、顺情从欲、暗示转移、移情易性、情境疗法、认知行为疗法等诸多心理治疗的医案。书中还记载了“诈病”案例,即医者在辨别出“患者”装病、假病之基础上,根据诈病者之弱点,采取不同的诈治法,迫使装病者恢复常态,亦非常值得后学研究。
江氏临证亦颇有体会。如江瓘治一富妇,出现肿胀伴经水不去之症,脉象沉小而快,两寸无力,问其夫久外不归,予健脾理气泄浊之剂后,继予补中除湿、开郁利水之剂收效(《肿胀》)。江应宿治朱秀才母,恶寒头疼,恶心呕吐之风寒外感,症见两尺脉沉无力,辨脾肺虚寒证,因考虑寡居多年,多伴抑郁,治宜四君加疏肝散郁温中之品(《命门火衰》)。治弟妇厥之重证,因寡居,又因事忤意而起,从痰火论治,收效甚好(《厥》)。